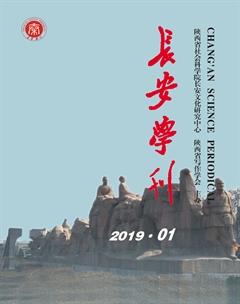小說《活著》與同名電影之間的對比分析
王雅琦
摘要:余華的長篇小說《活著》出版于1993年,1994年張藝謀導演將它改編為同名電影,搬上熒幕。電影保留了小說的基本內容,但在多處細節處進行了改編,將文字轉換為更適合電影創作的方式。通過分析小說《活著》與同名電影之間故事情節、傳播媒介、敘事手法、主題態度的不同,了解小說與同名電影對于“活著”的不同詮釋,明白應該如何真正的“活著”。
關鍵詞:活著;敘事手法;傳播媒介;主題態度;對比
文章編號:978 -7 - 80736 - 771 -0(2019) 01 -112 - 02
小說《活著》是著名作家余華的代表作品,出版于1993年。它講述了小人物富貴因嗜賭成性,從地主家的少爺淪為下地干活的農民,在坎坷的一生中經歷了數次的親人離別,最終只能與一頭老牛相伴度過晚年的故事。1994年,長篇小說《活著》被張藝謀導演改編成同名電影,搬上銀幕。電影由于傳播媒介、導演的個人理解等方面與小說有所不同,所以在改編時保留了部分原著的情節,但也適當的做了一些改編。本文主要通過對比兩者之間故事情節、敘事手法、傳播媒介、主題態度等方面,來了解小說《活著》與同名電影之間對于“活著”的不同詮釋。
一、“土地”與“宅院”的不同意象分析
在余華先生的小說《活著》中,故事是發生在南方的鄉下,主人公富貴將自家的一百多畝土地輸了個精光,由原先的地主少爺淪為了普通下地干活的農民。而在電影《活著》中,故事發生在北方的城鎮,主人公富貴是將自家的宅院作為賭債抵押給了龍二,從此淪為靠皮影戲謀生的手藝人。這點微小的改編,卻顯現了導演張藝謀的良苦用心。在近代,所謂地主就是土地的所有人。“地主”是一個稱呼,是一個階層的顯現,更是一種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所以,在小說《活著》中寫到:“四十多年前,我爹常在這里走來走去,他穿著一身黑顏色的綢衣,總是把雙手背在身后,他出門時常對我娘說:‘我到自己的地上去走走。”[1]這是在作為地主時的表現,對于自己擁有的土地充滿了一種自豪感。到田間的視察,其實是在宣布著土地的所有權,這與后來富貴將家產輸光后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富貴輸光家產后,小說中是這樣描述的:“我爹已不是走在自己的地產上了,兩條腿哆嗦著走到村口。”[1]“那天傍晚我爹拉屎時不再叫喚,他瞇縫著眼睛往遠處看,看著那條向城里去的小路慢慢變得不清楚。”[1]此時,一無所有的富貴爹,已失去了曾經的傲氣,也沒有了當初的財富和地位,自然不敢應農民的那句老爺。
在電影中,將“土地”改編成了“宅院”,這是導演花了很大的心思。宅院是一個家庭的避風港,它不止象征著財富,也具有“家”的寓意。在電影中,富貴將自己家的“宅院”給龍二抵了賭債,富貴爹說:“我以為我會死在這院里。”[2]說完這句話,對著富貴一通發泄后便撒手人寰。他不只是生氣失去了所有的財富,更多的悲傷在于人已年邁卻要被掃地出門,無家可歸。這里,“宅院”的失去,也預示著“家”散了,噩運的開始。富貴爹被氣死,家珍懷著有慶被父親接走,富貴帶著富貴娘和風霞相依為命。所以,這個關于“宅院”的改編是很令人深思的。將故事的大環境由南方的鄉下改編為北方的城鎮,導演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將小人物富貴一生的命運更加與當時的時代大環境結合起來,這也是為什么在電影中會用文字表明不同的年代。
二、傳播媒介的不同,電影與小說的敘事手法分析
小說《活著》主要是通過雙重視角來敘述主人公富貴的一生。在小說中,首先出現的是作為敘述人的“我”,從敘述人的視角來展開文章的寫作。因為作為敘述人的“我”遇見了一個名叫富貴的老人,他與一頭疲憊的老牛相伴。通過“我”與他的交談,從他那里了解到了他坎坷的一生。第二重視角,是通過小說主人公富貴的視角,自己作為故事中的主要人物——“我”來講述自己一生的坎坷經歷。每到故事的關鍵時刻,便會有作為敘述人的“我”與富貴之間的交談,通過交談來向讀者解釋說明故事中的重要細節,以及作為當事人的富貴的內心感受。由于小說與電影傳播媒介的不同,小說是文字媒介,電影是視聽媒介,所以決定了他們不同的敘事手法,以及不同的表現形式。
在電影《活著》中,導演直接以第三人稱敘事的方式來表現富貴一生的經歷,將富貴的生活通過攝像機鏡頭的運動展現在觀眾的面前。導演使用蒙太奇手法,通過鏡頭的拍攝與剪輯,來展現他想表達的觀點,但盡量不留痕跡的將攝像機隱藏起來,給觀眾感同身受,一種直觀的感覺。他通過特寫鏡頭來表現故事中的重要細節,通過劇中人物的對白,來表現當事人的內心感受。相對于視聽媒介來說,小說作為文字媒介,它的優勢是它客觀的講述故事,表達作品的主題。因為不同的讀者有不同的見解,由于理解的不同,他們會構建出不同的人物形象,符合自身審美和理解的人物形象。莎士比亞說過:“一千個人的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3],讀者可以有更多想象的空間。而電影作為視聽媒介,它的優勢在于不像文字那么的蒼白,它有多重手段可以用來表現導演此刻想表達的中心思想。例如:剪輯的方式、音樂的渲染、演員的表演等等。它能將小說中的人物形象,活生生的展現在銀幕上,給人以視覺的沖擊,更為直觀。但是,電影導演相比小說作家有更強的掌控力,它抑制了觀眾的想象,這有時會造成原著黨對于人物形象和電影改編的不認同感。
在電影《活著》中,將富貴由小說中輸光家產淪為農民,改編成為了一個皮影戲表演者。皮影戲在電影中貫穿始終,其實這處改編就和電影與小說的不同傳播媒介有關。電影是一種視聽藝術,它更注重的是視覺感受。相對于農民下地干活的場景,顯然皮影戲更具有看點。首先,皮影戲是中華傳統文化,電影本身是一種媒介,插入到電影中,也是對中華傳統文化的一種宣揚。電影《活著》在國外的傳播,也使皮影戲走進了外國人的視野。其次,皮影戲本身也是視聽藝術,與電影能較好的融合在一起,增強了電影的可看性。最后,皮影戲在電影中是一個貫穿始終的線索,在文革時期,皮影戲道具被燒毀,這也和時代政治背景聯系在了一起。這處改編就電影來說是相當成功的。
三、電影與小說對于主題“活著”的不同理解與表達
在小說《活著》的結局中,富貴爹娘相繼去世,有慶給縣長夫人抽血過多致死,鳳霞難產、家珍得軟骨病、二喜工傷相繼去世,連唯一的小孫子苦根也因吃豆子過多而撐死,只剩下富貴一人與一頭老牛為伴。余華主要想通過講述富貴一生坎坷的經歷,在經受了親人的相繼離世后,那份堅韌、樂觀、泰然處之的人生態度,表明“活著”的意義,以死亡反襯活著。“余華曾在《活著》韓文版自序中這樣說道:‘《活著》講述了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難,就像中國一句成語:千均一發。讓一根頭發去承受三萬斤的重壓,它沒有斷。我相信,《活著》還講述了眼淚的廣闊和豐富:講述了絕望的不存在:講述了人是為了活著本身而活著,而不是為了活著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著。”[4]這是余華先生對于“活著”的理解和態度,所以才有了小說中的現實悲慘結局。雖然,有慶、鳳霞、二喜、苦根都死于偶然,但是都是當時大時代下產生的悲劇。余華沒有過多的去表明態度,留給讀者自己去品味。但是,他對于“活著”的態度卻格外的強調,那就是為活著本身而活著,以樂觀的態度回歸生存的本真。
關于“活著”,導演張藝謀與余華先生有不同的理解和詮釋。在電影《活著》的結局中,富貴爹娘相繼去世,有慶被疲勞駕駛的區長意外撞到墻砸死,鳳霞難產去世,家中剩下了家珍、富貴、二喜和小孫子饅頭繼續著今后的生活。家里保留了老中青三代,基本維持了一個完整的家庭。尤其是在電影的結尾,富貴對饅頭說:“雞長大了就變成了鵝,鵝長大了就變成了羊,羊長大了就變成了牛。”[2]“饅頭長大了就不騎牛了,就坐火車,坐飛機,那個時候啊,日子就越來越好。”[5]此處,導演表明了他對于“活著”的理解和詮釋。他認為,“活著”是在經歷了人生的重大變故后,仍能以樂觀的心態,心懷希望,往前看,相信未來的生活會更好,做到精神上的“活著”。電影的結局相對于小說來說,沒有那么多的悲涼,多了一絲溫情和希望。在電影《活著》的最后結局中,二喜的存在代表的是家庭經濟收入和堅實勞動力,饅頭的存在就是這個家庭未來的希望,也是這個家庭生命的延續。
這樣不同的處理,其實也與電影和小說所處不同文化有關,電影屬于大眾文化,它需要對觀眾有一個主流價值觀的引導作用,具有積極樂觀,充滿希望的生活態度。而小說屬于精英文化,是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群追求的。它更多的是偏重讀者自身的理解,從中悟出自我需要的精神食糧。
四、結語
無論是小說《活著》還是電影《活著》,在國際上都多次獲得重要獎項,這是對于小說故事本身的肯定,也是對于同名電影改編的巨大肯定,將時代的縮影集中在一家人的身上,將大環境對于人民生活的沖擊,全集中在一個小人物的一生之中。通過講述小人物富貴一生的坎坷經歷,以及他對待巨大變故的人生態度,來告訴世人什么是“活著”,應如何“活著”。通過對比小說與電影故事情節、傳播媒介、敘事手法、“活著”的人生態度的不同,了解作家和導演他們對于“活著”的不同詮釋,以及什么才是應有的“活著”的人生態度,給世人以引導,令人深思。
參考文獻:
[1]余華.活著[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8.
[2]張藝謀.活著[CD],1994.
[3]莎士比亞,哈姆雷特[M].黑龍江:哈爾濱出版社,2009.1
[4]鄭娜,《活著》:向死而生——從小說到電影的比較分析[J].濮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