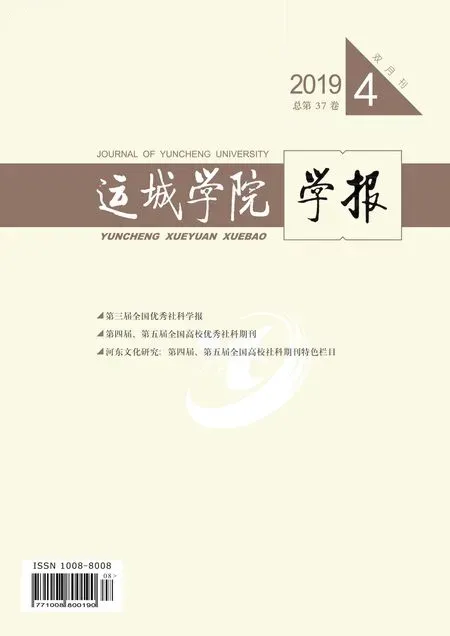跨法域累犯成立的認定條件
李 佳 純
(中國政法大學 刑事司法學院,北京 100085)
所謂跨法域的累犯是在一個法域犯罪并接受刑罰處罰,刑罰執行完畢以后,在一定時間內又在不同法域犯罪的犯罪分子。跨法域累犯成立的認定就是根據犯罪分子的國籍國法,依照累犯的成立條件對犯罪分子是否成立累犯進行判斷。
關于中國大陸刑法對跨法域累犯的認定這一問題,目前我國的刑事研究已積累了一定成果。國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一國兩制”下中國大陸與香港、澳門三地跨法域累犯的認定,即圍繞三個法域進行探討,具體研究方向有大陸與港澳跨境犯罪的基本特征、累犯制度的比較、刑事管轄的沖突與解決,以及大陸與港澳開展區際司法協助的模式等。中國大陸刑法對跨法域累犯的認定問題涉及累犯制度和域外刑罰執行的認定兩個問題。我國刑法學界對累犯制度的研究歷史悠久,其中累犯的構成、本質和累犯在司法實踐中的認定等研究為跨法域累犯的認定這一問題提供了深厚的理論基礎,如梁洪行《論累犯構成中的法域條件》。國內對域外刑罰執行認定的研究圍繞刑罰目的的達成、區際司法協助和跨境犯罪三個方面,其中刑罰目的達成的研究,即如何判斷域外刑罰是否達到我國刑罰報應和預防的目的,為跨法域累犯的認定提供了判斷的標準。
本文主要是研究中國公民在中國大陸以外地區犯罪并被判處刑罰,刑罰執行完畢后又在中國大陸犯罪,中國大陸法院在審判時對這些人的累犯身份如何認定的一系列問題,就這些問題進行詳盡的討論。(1)我國是多法域國家。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和臺灣雖同屬一個中國,但法律體系各不相同,屬于四個法域,故這里僅討論中國大陸刑法的認定標準。
一、跨法域累犯認定問題的產生
我國刑法明確規定了累犯的犯罪構成,因此認定累犯是否成立沒有太大爭議。至于對累犯的量刑,即“應當從重處罰”的從重幅度交由法官自由裁量。所以,在司法實踐中對累犯問題的處理似乎沒有難度。但是現實并不是這樣。隨著經濟實力和政治格局的變化,人口流動愈加頻繁,行為人在多個地方犯罪,即跨法域的累犯增多。針對這個問題,即使借用多種法律解釋方法,也難以解決。通過以下兩個案例說明。
案例一:2013年1月,被告人甲因信用卡詐騙罪被北京市昌平區檢察院提起公訴,案件調查過程中發現,甲在1995年曾因生產假藥罪被判處兩年有期徒刑,刑罰執行完畢后前往德國從事貿易工作。2008年甲因親屬相奸罪被德國某法院判處自由刑兩年零五個月,刑罰執行完畢后回國。請問應該如何認定甲的刑事責任?
案例二:2010年2月杭州,被告人乙一天晚上撬鎖進入一家當鋪,盜竊財產價值共六萬元。公安機關在偵查過程中發現,乙曾于2006年3月在日本因詐騙罪被某法院判處一年懲役,服刑結束后回國。請問,對乙應當如何定罪量刑?
這兩個案例都必須解決的問題是被告人累犯身份的認定,問題的關鍵有兩個,一是我國法院如何處理被告人在國外所犯之罪在我國刑法中沒有規定的情況。二是,我國法院是否承認域外的刑事判決和刑罰執行,這涉及被告人是否成立累犯和是否應該根據《刑法》第十條對前次犯罪追究刑事責任。
就第一個問題,通過分析案例一說明。首先由于親屬相奸行為在我國刑法中未規定,那么,不管被告人甲在德國是否被執行過刑罰,中國司法部門在對其在中國的犯罪行為進行審理時,不應當將他的前行為(在德國的行為)作為成立一般累犯的基礎,因為這是沒有法律根據的。面對中國公民在國外的行為所觸及的罪名在我國刑法中沒有規定的情況,例如德國的親屬相奸罪,由于行為本身在我國是沒有規范基礎的,在我國不構成犯罪,那么就不存在成立累犯的前提。因此,對甲應只針對信用卡詐騙罪的犯罪情節獨立定罪量刑。
至于第二個問題,《刑法》第十條的規定看似很明確,但是在案例二的情況下,仍然不知是否承認被告人乙在日本被執行的一年懲役,以及如何裁量被告人乙的刑罰。域外刑罰執行承認的問題不解決,就無法認定被告人乙是否是累犯。若是累犯,法條的具體表述是“仍然可以依照本法追究”,但是案例所描述的情況是否需要追究?如果需要,那么考慮到乙在日本已經接受過刑罰,“可以免除或者減輕處罰”是免除、減輕還是不免除減輕處罰?累犯的量刑雖然在法官自由裁量的范圍內,但是自由裁量的核心在于法官自身應當了解制度的目的以尋求合理結論的正當化依據,而不是法官按照自己的觀點判決。
通過這兩個案例發現,在司法實踐中關于跨法域累犯的認定問題很多,僅僅有《刑法》第六十五條是不足夠的。這一法條只在解決普遍問題上有明確的答案,一旦情節復雜,脫離法條的文字描述,累犯的認定就變得模糊不清。因此,我們應該思考累犯的本質是什么,一旦認清本質,對累犯的定罪量刑則迎刃而解。
二、跨法域累犯本質探究
(一)累犯本質的定義
研究跨法域的累犯問題,重點就是分析累犯的犯罪構成和本質。如果行為人滿足了犯罪構成,觸及本質,那么就成立累犯。相反如果行為人缺少構成要素,不涉及本質,那么就不能成立累犯。
累犯的概念很難從其自身得出,若想知道累犯的準確概念,必須從累犯的上位概念著手,分析其與其他同等地位概念的關系,才能把握在上位概念下的地位。累犯是刑罰裁量中的加重情節。因此,必須首先了解刑罰裁量制度,分析累犯與自首、坦白、立功和數罪并罰的區別和聯系,才能準確把握概念。由法條可得,累犯是刑罰裁量制度下一類需要加重處罰的犯罪分子。
《刑法》第六十五條說明,若要在裁量刑罰時判斷行為人是累犯必須滿足三個條件。一是累犯構成的罪過條件,即要求行為人犯前罪和后罪時都持故意心理。二是累犯構成的發生間隔條件,即后罪必須發生在前罪所判刑罰結束或赦免后的五年時間內,表明刑法只在懲罰有效且效力持續的特定期間內承認累犯的存在。三是成立累犯的刑罰條件,即后罪應當判決的和前罪已執行的刑罰都是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死緩。有期徒刑是國家當前能采用的最有效可行矯治罪犯的措施。“在刑法理論上,仍然認為自由刑是刑法體系的中心。”[1]由此可得,累犯之所以要從重處罰是因為國家發現自己最重要的懲治和預防手段對于這部分犯罪分子作用不大或沒有產生作用。這反映了一個事實,即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和死緩對這類罪犯的矯正程度不高,且累犯對刑罰的接受程度低甚至抗拒。累犯對于刑罰懲罰的痛苦感受力弱甚至麻木,對有期徒刑及更嚴厲的刑罰具有排斥性。具有前科者在受過刑罰處罰后再次選擇犯罪,足以表明犯罪人對于刑罰的懲罰與改造持根本否定的態度。[2]就累犯自身而言,特定的價值體系使這部分人抗拒刑罰的改善作用,忽略刑罰的痛苦。因而,累犯的本質在于行為人本身的抗刑罰人格。面臨累犯的抗刑罰人格,刑法必須針對這個內在本質加重懲罰。
因此可得,累犯并不只是一個文本的概念,或者是三個條件的框架。雖然第六十五條簡潔敘述了累犯的成立和后果,但是每一個條件背后都隱藏著充分的內容和案件,且這三個前提的硬性規定都是由行為人本身的抗刑罰人格衍生而來。僅僅對這個法條的生硬理解是不足的,尤其對于跨法域累犯,實際認定更困難。如果不認清累犯的本質,就會導致法官對刑罰的濫用,唯有通過判斷行為人抗刑罰人格的強度才能準確把握從重處罰的幅度。
(二)抗刑罰人格的量化
1. 累犯的成立時間
抗刑罰人格的量化是量刑的前提。分析抗刑罰人格,應結合這種人格產生的原因。刑法依照社會普遍價值體系和人格特征規定了多種刑罰以達到矯正和懲罰的功能,但一部分人不能通過這些預設的刑罰扭轉其價值觀,刑罰上的痛苦對其作用不大。這與法律的期待背道而馳,根據法律的預測,刑罰如特定量有期徒刑的執行效果在五年的時間段內足夠抑制行為人再次犯罪,而累犯再次犯罪的行為體現不出刑罰的功能。由此可得,抗刑罰人格的強度體現在累犯構成的發生間隔基礎上。再次犯罪的時間間隔成為判斷人格強度的要素之一,根源是刑罰在其執行完畢的瞬間,矯正和懲罰的效果達到最大。之后隨著時間的拉長,功能也會逐漸減弱。如果行為人在刑罰執行完畢后立即犯罪,那么說明行為人的抗刑罰人格很強,刑罰的抑制功能沒有達到。相反,如果行為人再次犯罪與刑罰執行完畢或赦免后的時間間隔越長,那么行為人的抗刑罰人格越弱,刑罰抑制再次犯罪的功能越強。
當然,行為人后罪發生的時間點可能與其他因素有關,例如受害人的行為、周圍環境和條件等。但是一般情況下,其他因素都相對確定,此時對抗刑罰人格的量化只體現在再犯與前罪刑罰執行完畢或赦免后的時間間隔。因此需要討論累犯的成立時間,如以下案例三。案例三:2008年,被告人丙因放火罪被北京市海淀區法院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于2008年3月7日交付監獄執行。2011年3月6日,丙刑滿釋放。在如下三個情況中哪一構成累犯:A:丙被釋放后,當天將鄰居打成重傷;B:丙被釋放后,監獄管理人員發現丙在2011年3月5日把同獄人員打成重傷;C:丙被釋放后,2016年3月6日將鄰居打成重傷。
在這個案例中,需要解決的問題是累犯的成立時間,此時應當結合累犯的本質進行分析。在司法實踐中,刑罰執行機關會在刑罰執行完畢當天釋放罪犯,那么累犯的成立時間包括刑期截止日當天嗎?累犯的本質在于自身的抗刑罰人格,其強度與時間間隔的長度有關。刑期滿釋放后,再犯時間間隔越短,抗刑罰人格越強。因此,如果不認定A是累犯,就違背了法律懲罰累犯的本意。從服刑人釋放的瞬間起,刑罰在事實和法律上都已經完成,所要發揮的矯正和懲罰的功能也已達到了最大,此時犯罪更加說明行為人對刑罰的麻木和抗拒心理。因此A情形下丙成立累犯。而C情形下,由于刑罰執行完畢已經滿五年,且法條的時間規定即五年是明確的,因而即使只經過一天也不成立累犯。同樣,B情形下也不成立累犯。雖然實質上打傷他人的行為發生在刑期截止日當天和前一天并無太大差別,但不能按照累犯的情形處罰,因為丙的刑罰未完成,不能開始五年期間的計算,應當依據《刑法》第七十一條處理。由此可得,累犯的成立時間從刑罰執行完畢的那一刻開始計算,至五年后結束。
2.累犯與犯罪形態
與累犯成立時間相關的問題是五年之內再犯罪的“犯”是指什么犯罪形態?以下是案例四。
案例四:2004年,行為人丁因走私毒品被戊揭發,判處有期徒刑五年,于2009年4月25日執行完畢。釋放后丁心懷不滿意圖對戊報仇。如下兩個情況下哪一成立累犯:D:丁于2014年4月24日購買斧頭等尖銳工具,并于2014年4月25日將戊砍傷;E:丁于2014年4月24日決定要對戊報仇,并于2014年4月25日將戊打傷。
根據以上對累犯成立時間的描述,丁成立累犯的最后時間點是2014年4月24日。D和E情形的共同點是都于25日著手并既遂。由D情形可得,丁在24日購買犯罪所需的工具,是犯罪預備行為,25日才著手并既遂。而E情形中,丁在24日僅產生犯罪意圖,25日才實施犯罪行為。那么累犯的成立需要再犯犯罪過程的哪一部分發生在五年的特定期間內呢?是犯罪預備、著手還是既遂呢?或者只要求行為人在該期間內有犯意產生即可?結合累犯的本質分析,行為人體現出抗刑罰人格就成立累犯。雖然抗刑罰人格是行為人的內在屬性,但這種人格必須通過行為才能展現出來,具有法律意義,否則就會有法律暴力干涉公民自由的嫌疑。如果以行為人產生犯意作為累犯成立的犯罪形態起點,而犯意產生的最初時間點在司法實踐中很難確定,因此無法判定累犯的成立。所以,必須以行為人抗刑罰人格外化的實際行為作為標準,所以在五年的特定期間內實施犯罪預備行為足以構成累犯,不需要在此期間內著手和既遂,也不需要在此期間內發生法律后果。因此丁在D情形中構成累犯,而在E情形中不構成。
三、域外刑罰執行對跨法域累犯認定的意義
(一)域外刑罰執行的承認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十條所得,我國在一般情況下不承認域外刑事判決,在極少情況下予以承認。因此不管行為人在國外接受或未接受過刑罰,都必須在我國再次接受審查。這是有原因的:第一,不同國家關于刑事案件的管轄原則不同,不能相互替代,刑事管轄只能適用國籍國法。因此,外國判決和刑罰執行很多時候只被看為一種事實,并不具有法律效力。第二,各國適用刑罰的方式有很大不同,如國外多適用罰金刑,并以罰金刑代替自由刑。這給我國繼續追究罪犯、對罪犯定罪量刑帶來很大困難。第三,刑法是一個國家最具有階級性的基本法,社會性質不同的國家在相同罪的認定和刑罰裁量上可能有很大不同。
對于累犯而言,刑罰執行完畢是非常重要的構成條件。跨法域的兩次及以上的犯罪,如果符合一般累犯的時間、刑種等條件,是否成立累犯的關鍵點就在于我國是否認可外國的刑事審判和刑罰執行。根據刑法的相關規定,我國原則上不承認,但又在一定條件下考慮行為人在國外已受到刑罰的事實。對行為人執行刑罰是為了使其感受到痛苦,從而起到阻止其犯罪的作用。從重懲罰累犯的目的是為了矯正其反抗刑罰的內在屬性和行為,威懾其不能繼續犯罪。如果行為人在外國犯嚴重罪行,并且依我國刑法亦構成犯罪的,刑罰執行完畢或赦免后,其又在我國犯罪,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和主觀惡性暴露無遺。[3]如果一貫采用不承認的態度,那么就相當于行為人沒有接受過刑罰,這是不公平的,可能增強行為人的抗刑罰人格,容易使行為人產生逆反心理。因此,即便認定域外刑罰在司法實踐中存在很多困難,我們仍然需要通過對具體案件的分析得出不同的結論,這有利于對行為人合理定罪量刑。
(二)刑罰目的達成的認定
刑罰本身沒有目的,但是國家制定刑罰是為了懲治罪犯。根據并合主義,報應和預防都是刑罰的正當化根據。國家制定刑罰、裁量刑罰和執行刑罰所希望達到的結果是對行為人的犯罪行為進行報復,警示可能犯罪的人并補償受害人。這是國家對刑罰執行效果的必然追求,是國家和罪犯長期斗爭的目標。刑罰目的雖然是預設的,但是從根本上制約著對刑罰的認定。
因此若想承認域外刑罰的執行,必須在報應和預防兩個方面達到我國在相同情況下處理同個案件所能達到的標準,也就是同個案件在我國發生時法律審判執行的結果。如果域外刑罰執行在預防和報應兩個方面都達到或超過了我國的標準,那么應當承認且免除處罰。如果沒有達到標準,有差距的話應繼續追究且減輕處罰;完全沒有效果的話應繼續追究且無須減輕處罰。
首先從報應角度分析域外刑罰執行是否達到我國一般標準。外國的判決和刑罰與我國法律體系之間存在差別,導致這些差別的原因在于價值體系的差異。報應目的達到的核心觀念在于從受害人角度考慮刑罰是否充分,因此保護管轄原則所涉及的情形需要重點考慮,即行為人以我國公民權益、社會和國家法益為犯罪客體犯罪而在外國接受審判并完成刑罰執行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受害人認可的法律和審判地的法律存在差異。
例如,根據日本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條規定,“以行使為目的,偽造、變造正在日本國內流通的外國貨幣、紙幣或者銀行券的,處兩年以上有期懲役。”[4]日本刑法認為中國公民在日本偽造人民幣是犯罪,但是其執行刑罰的原因在于偽造行為對日本本國金融秩序的破壞,而不是對中國貨幣信用和發行的維護。因此日本法院的判決和刑罰對于受害方即我國國家法益的保護并不充分,不能完成我國刑法對于制造假幣罪犯的報應目的,不能達到我國處理相同案件的標準,所以應該繼續追究。報應目的思想本身有限制追訴和規束刑罰的作用,且域外刑罰執行意味著行為人已經就應負責任進行清償,所以在國內繼續追究的話必須考慮這一事實,即對行為人可以減輕刑罰。
其次從預防角度分析域外刑罰執行是否達到我國刑罰標準,這點要結合不同國家對犯罪預防目的追求的差異進行理解。我國制定刑罰的目的之一是為了預防,包括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一般預防即通過對犯罪人適用刑罰,用刑罰威懾、預防尚未犯罪的人實施犯罪。一般預防的對象是尚未犯罪的人,例如有犯罪傾向的人和受害人等。特殊預防即通過適用刑罰,預防已經實施犯罪的人重新犯罪。”[5]域外判決通常僅考慮自己法域內一般預防的需要而忽略罪犯國籍國一般預防目的的達成。對于不同國家來說,一般預防的程度有所差異。例如德國刑法典第三十章做出對職務犯罪的規定,刑罰嚴厲程度比我國低。由于德國反腐制度更完善,犯罪率低,因此其一般預防的必要性低。相反我國目前的反貪制度與之相比還有很大差距,要想達到同樣一般預防的效果,我國規定的刑罰必然要重一些。
最后分析域外刑罰執行對行為人的矯正和懲罰是否達到我國標準,即特殊預防。對行為人矯正和懲罰的水平體現出不同國家刑罰改造罪犯的能力。一個國家累犯比例越高,改造罪犯的能力越低,特殊預防的水平越差。對于這方面的分析不能把行為人刑罰執行完畢或赦免后的表現作為參考,因為行為人在國內接受刑罰后也有再犯的可能。判斷是否達到我國特殊預防標準的方法是綜合考慮域外刑罰的質量、數量和執行方式與我國相同情形下的聯系和區別。
以上可得,對于承認域外刑罰執行,必須由報應和預防兩個方面加以分析。若域外刑罰執行達到或超過了我國刑罰報應和預防的目的,那么應當承認。一般來說,即使不承認域外刑罰的執行,在審判過程中也會考慮域外刑罰已經執行這一事實,從而減輕行為人的處罰。
那如何判斷域外刑罰是否達到我國刑法報應和預防的目的呢?結合累犯的本質,判斷域外刑罰是否對行為人進行足質足量的矯正和懲罰必須以我國刑罰執行的普遍情形作為標準。若相同或超過我國標準,那么行為人再次犯罪的事實就表明他對國內刑罰的抵抗性,體現出抗刑罰人格,因此在定罪量刑的過程中有必要加重刑罰。若低于我國標準,就不能體現出行為人的抗刑罰人格,不能作為累犯量刑。由此可得,域外刑罰執行不能作為跨法域累犯成立前提的情況包括兩種,一是域外刑罰與我國相同情況下所判定的刑罰完全不同質,即種類有差異。二是域外刑罰的強度不夠,刑罰沒有對行為人充分發揮作用。例如相同犯罪行為在日本判處拘役,在我國判處有期徒刑,那行為人不能作為累犯認定,即在外國接受的刑罰應當與我國進行種類和數量的比較。
因此,域外刑罰執行對跨法域累犯成立的作用與上文是否承認域外刑罰執行可以加以聯系。如果行為人在國外接受了和我國相同或超過的足質足量的刑罰,那么不應當就相同犯罪對行為人實施刑罰,相反應承認域外刑罰,認定累犯成立,加重處罰。如果是減輕處罰的情形,即仍需追究責任,那么說明雖然承認域外刑罰但仍不充分,這與刑罰尚未執行完畢行為人再次犯罪的法律效果相同,不能構成累犯。這時應分別定罪量刑,數罪并罰。如果完全不承認域外刑罰,這與行為人沒有接受刑罰執行的法律效果相同,既然沒有接受過刑罰,那么累犯就沒有成立的依據,累犯不能成立。在這種情況下,應當將行為人在域外所犯之罪和新罪分別定罪量刑,數罪并罰。
通過以上論述,可以對案例二中的乙定罪量刑。案例二中,從報應角度講,詐騙罪的受害人所接受的規范與審判地重合,且乙的刑罰對受害人來說是充分的,所以達到目的。從一般預防角度講,日本與我國沒有明顯的區別。從特殊預防角度講,達到了與我國相同情況下矯正和懲罰的目的。因此,應當承認被告人乙在日本接受的判決和刑罰,不再追究責任。這就具備了累犯成立的前提,加之乙時隔三年再次犯罪表現出的抗刑罰人格,所以應當認定乙是累犯,從重處罰。另外由于乙再次犯罪距刑罰執行完畢的時間間隔不長,所以從重幅度不宜過小。
四、結語
中國大陸與以外地區的跨法域累犯的認定問題,是我國對其他法域的刑罰執行的認定問題,沒有現實的范例可供借鑒,因而在這種背景下跨法域累犯的確定沒有參照。跨法域累犯認定問題,需要對我國累犯制度深入研究,對不同國家刑事法律體系進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