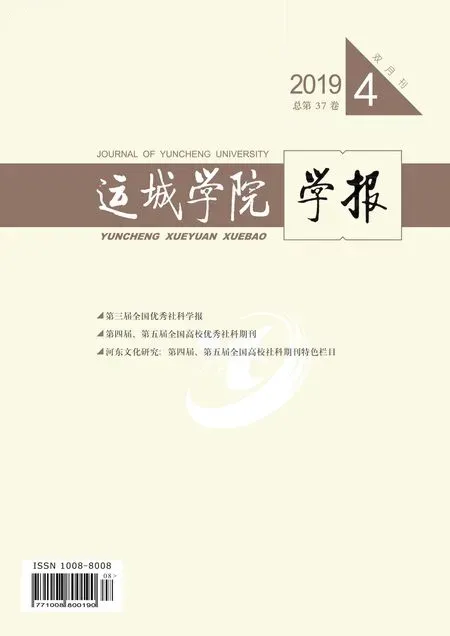意象研究的深化與拓展
——《中國(guó)古典文學(xué)意象研究》述評(píng)
雷 晶 晶
(陜西理工大學(xué) 文學(xué)院,陜西 漢中 723001)
意象,是中國(guó)古典文學(xué)批評(píng)中,尤其是詩(shī)歌批評(píng)中最常見、最重要的術(shù)語(yǔ)之一,同時(shí)也是意義最難把握的術(shù)語(yǔ)之一,因而以“意象”批評(píng)中國(guó)古典文學(xué)總是仁者見仁,莫衷一是。以汪裕雄(1)參見汪裕雄:《意象探源》,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頁(yè)。、陳植鍔(2)參見陳植鍔:《詩(shī)歌意象論》,北京: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1990年。、顧祖釗(3)參見顧祖釗:《論意象五種》,《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1993年第6期。為代表的學(xué)者,在“意象”的本義、內(nèi)涵、類型等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績(jī),創(chuàng)獲良多。以往大多意象研究,或直溯“意象”一詞本義,而忽視“意象”一詞能夠作為一個(gè)獨(dú)立的批評(píng)術(shù)語(yǔ)有其漫長(zhǎng)的發(fā)展、變化歷程,這一變化歷程恰代表著不同時(shí)期中國(guó)文學(xué)審美的發(fā)展要求和總體趨向;或削足適履、取西附中,受西方意象觀念影響,取image作為中國(guó)“意象”的翻譯基礎(chǔ),從而使“意象”的內(nèi)涵更加混亂復(fù)雜。而熊開發(fā)等人合作力撰的《中國(guó)古典文學(xué)意象研究》不僅分別追溯了“意”與“象”各自的本義,而且探析了“意”與“象”之所以能組合在一起,構(gòu)建和表達(dá)中國(guó)文學(xué)審美追求的原因。不僅縱向比對(duì)了中國(guó)文學(xué)批評(píng)中“意象”作為一個(gè)整體概念其內(nèi)涵的流變,而且橫向觀照了西方現(xiàn)象學(xué)的“境域”觀念與中國(guó)傳統(tǒng)“意象”思維;不僅研究了詩(shī)歌中的意象營(yíng)構(gòu),而且涉獵了不同文體中的意象典型;不僅是學(xué)術(shù)著作,也是美學(xué)論鑒。考訂更加精審,視野更加寬廣,具有很強(qiáng)的信服力,是中國(guó)古典文學(xué)“意象”研究的一部力作。
一、溯源辨流,考訂精確
“意象”之全部?jī)?nèi)涵若集合起來可是一個(gè)“大家族”,學(xué)術(shù)界至今也沒能為這一“大家族”找到一個(gè)統(tǒng)一的、明確的界定。[1]177因之,界定“意象”這一術(shù)語(yǔ)的本義和內(nèi)涵是研究“意象”的首要任務(wù)。“意象”作為一個(gè)整體概念首次出現(xiàn)于王充《論衡·亂龍》的“夫畫布為熊麋之象,名布為侯,禮貴意象,示義取名也。”[2]誠(chéng)如王少良所言“這里出現(xiàn)‘意象’一詞,并不用于文學(xué)創(chuàng)作情意觀照的“意中之象”來使用,但作為文學(xué)理論批評(píng)的一個(gè)審美范疇,意象在古代文論中使用得較為廣泛,它是作家情思的對(duì)象化表現(xiàn),能在讀者頭腦中引起超時(shí)空聯(lián)想。”[3]31然文學(xué)意象何以有此功能價(jià)值,還需追溯其本義、發(fā)掘其內(nèi)涵。值得指出的是,在“意象”成為一個(gè)獨(dú)立術(shù)語(yǔ)前,“意”和“象”分別有其各自的內(nèi)涵,“意”和“象”能夠組建在一起并傳達(dá)著中國(guó)美學(xué)精神,也有著歷史的必然。《中國(guó)古代文學(xué)意象研究》別有會(huì)心,全書分為上下兩篇,上篇專事意象理論研究,從字源學(xué)角度討論象、形、意、志、音、聲、言和心等幾組名詞的意義起源及相互之間的意義關(guān)聯(lián),視角獨(dú)特,資料翔實(shí)。該書的創(chuàng)新之處和理論價(jià)值,就在于其以字源學(xué)為切入點(diǎn),對(duì)“意”、“象”、“意象”肅源清流,從而見出其成長(zhǎng)主脈、變化焦點(diǎn)和發(fā)展軌跡,鉆研深透,理?yè)?jù)充分,從而為“意象”內(nèi)涵的清晰界定建立了堅(jiān)實(shí)基礎(chǔ)。
對(duì)“意象”內(nèi)涵的界定主要包括“象”的內(nèi)涵界定、“意”的內(nèi)涵界定、“興象”、“興趣”、“氣象”以及明清意象理論的內(nèi)涵界定和理論意義提煉三個(gè)具體方面,并通過剖析意象性思維特征,深化了“意象”理論的學(xué)理性。從字源學(xué)角度來看,最早的象形之“”是對(duì)實(shí)物的形象描繪,是對(duì)“一種寫實(shí)的具體的形象的‘大象’”[4]4的刻畫;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中雖亦采用象形之“”,但對(duì)其解釋已變成“南越大獸”,“象”成為“南方的一種很獨(dú)特的動(dòng)物”[3]4,成為對(duì)不再存在于現(xiàn)實(shí)中的某種形象的想象性描繪;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從文字學(xué)角度推理:“人部曰:像者,似也。似者,像也。”[5]從形聲造字的角度引申出“象”的抽象意義,成為對(duì)想象活動(dòng)本身的表達(dá)。“象”的內(nèi)涵的三個(gè)階段的變化得到了明確認(rèn)識(shí)。著者通過舉示原初的、有代表性的文獻(xiàn),提煉“象”內(nèi)涵拓展的節(jié)點(diǎn),得出了明晰的線索,并析出其內(nèi)涵特質(zhì),為“象”的內(nèi)涵界定提供了文獻(xiàn)根據(jù)。
接下來展開對(duì)意象之“意”及相關(guān)語(yǔ)匯的辨析。著者依據(jù)《說文解字》等文獻(xiàn),詳細(xì)辨析了“志”與“意”,“意”與“心”,“音”與“意”等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從而明確闡述了“意”的內(nèi)涵及特性。根據(jù)《說文解字》:“志,意也。從心之聲。”[6]由此可知,“志”是個(gè)單純的形聲字,“志”上之“士”就是“之”;“志”與“意”相類,與“心”相關(guān)。“意,志也。從心,察言而知意也。從心從音。”[6]“意”從心從音,是指“意”是“音”“心”兩個(gè)字形(字義)的結(jié)合,那么“音”和“心”又有哪些涵義呢?著者借助佛教對(duì)人的意識(shí)活動(dòng)中的“六識(shí)”的認(rèn)識(shí),指出,“心/意想什么”是“綜合了全身心的感知能力以及經(jīng)驗(yàn)的一種精神活動(dòng)”[4]14。“音”是聲之有節(jié)者,是有意味的聲,是被“人為”過的聲,因而“音/意”就有了“有意義的表達(dá)”的內(nèi)涵。因之見出“意”就是一種表達(dá),“就是意味、意義的注入”[4]16。著者通過追溯“意”“象”各自本義和流變過程中內(nèi)涵的變化,為準(zhǔn)確理解“意象”的特征和基本內(nèi)涵夯實(shí)了基礎(chǔ)。
“意象”并不是突然或偶然出現(xiàn)在古代文學(xué)批評(píng)的術(shù)語(yǔ)中,也不是一開始就成為中國(guó)傳統(tǒng)詩(shī)學(xué)中流行且重要的核心用語(yǔ)。在“意象”成為一個(gè)獨(dú)立完整的批評(píng)術(shù)語(yǔ)之前,還有與之相近的一系列語(yǔ)匯。著者選取了幾組曾經(jīng)在文學(xué)批評(píng)上產(chǎn)生了較大影響的術(shù)語(yǔ),與“意象”進(jìn)行比較,如“興象”說、嚴(yán)羽的“興趣”說、“氣象”說與意象的關(guān)系。著者同樣采用字源學(xué)方法,詳細(xì)考證其內(nèi)涵之間的差異,從而突出對(duì)“意象”的豐富意味的界說,提出“中國(guó)傳統(tǒng)的‘意象’從開始就是‘意’與‘象’兩個(gè)獨(dú)立詞義的融合”[4]9。因此,意象的內(nèi)涵即是意與象本義及特性的融匯與互滲,“意”必須為發(fā)自內(nèi)心的真情所駕馭,并與“象”之形態(tài)和特性形成和諧的關(guān)系,在主體情感的統(tǒng)攝下,自然與理想,感性與理性,具象與抽象都達(dá)到高度的和諧,這樣意象才會(huì)收到生動(dòng)感人的效果。最后,著者列舉了明人具有代表性的意象理論觀點(diǎn),如李東陽(yáng)推崇詩(shī)歌“意象具足”,王廷相《與郭價(jià)夫?qū)W士論詩(shī)書》的“示以意象”、“詩(shī)貴意象透瑩”,何景明《與李空同論詩(shī)書》的“意象應(yīng)曰合”,王世貞的“意象衡當(dāng)”、“象必義附”等;重點(diǎn)論述了王夫之情境論的意象觀。著者通過擢要提煉,清晰描繪了“意象”理論的成長(zhǎng)路徑。“意象”內(nèi)涵的更新與豐富不僅是文學(xué)批評(píng)家自覺審美追求的直接表征,也是古典文學(xué)不斷走向成熟的生動(dòng)體現(xiàn)。從這個(gè)意義上說,“意象”是中國(guó)古典文學(xué)走向成熟過程中重要的“見證者”、“參與者”和“建設(shè)者”,“意象”之研究范圍看似較小,但所觀照的領(lǐng)域卻極為博大。《中國(guó)古典文學(xué)意象研究》的研究?jī)r(jià)值正在于此。
二、內(nèi)外觀照,立見明確
在對(duì)“意象”進(jìn)行字源學(xué)考察的同時(shí),著者析出其特質(zhì)并與西方“意象”“印象”(image)作比較,有了一個(gè)由外而內(nèi)的參照視角,既往對(duì)意象特點(diǎn)研究的未察之處,在此便得到突破,從而獲得對(duì)中國(guó)古典文學(xué)意象特點(diǎn)更全面的呈現(xiàn),對(duì)意象的研究具有更特別的意義。不像“image”那樣是一個(gè)完整的詞匯,多元意義的混合成中國(guó)“意象”帶來其意義的復(fù)雜和豐富。在西方“image”概念下滋生出的“意象”“印象”指的是人的大腦對(duì)萬事萬物的一種反映、一種印象,因故image側(cè)重于模仿之實(shí)形,著者進(jìn)一步提出,“‘image’(形)這個(gè)詞翻譯成‘形象’更好,若簡(jiǎn)單對(duì)譯成漢語(yǔ)的‘意象’,顯然有些不貼切。”[4]11通過比照,著者提出“象”的具體性、經(jīng)驗(yàn)性、虛擬性,“意”的語(yǔ)言性、思想性,“意象”的隱喻性、直觀性等。在橫向的比較中,不僅突出了中國(guó)意象的獨(dú)特性,也補(bǔ)充了對(duì)西語(yǔ)意象的認(rèn)知。同時(shí)充分論證了“我國(guó)文學(xué)藝術(shù)的民族特點(diǎn)之一,是偏重于表現(xiàn)作者的主觀感受,表現(xiàn)內(nèi)心世界”[7]23;傳統(tǒng)的印象式批評(píng)如“在審美批評(píng)中,人們發(fā)現(xiàn)某些作品意蘊(yùn)深邃、豐厚,發(fā)人深省,耐人尋味,所給予人的感受遠(yuǎn)遠(yuǎn)超出文字本身的含義”[7]23于此獲得了理論的支撐。
西方學(xué)者對(duì)“意象”的看法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西方的認(rèn)知方式,并不一定就完全符合于中國(guó)的“意象”實(shí)情。只有在對(duì)比中全面觀照中西“意象”的核心差異,才能抓住各自本質(zhì),從而得出既符合中國(guó)“意象”實(shí)情,又突出中國(guó)“意象”特色的研究理論。這應(yīng)是《中國(guó)古典文學(xué)意象研究》的初心和用心所在。同時(shí),在差別的對(duì)比中,由小見大,可以看出、東、西方在“意象”這個(gè)范疇上所顯示出的審美理念的不同,將中國(guó)古典文學(xué)置于世界文學(xué)的視野中統(tǒng)籌觀照,將其推向了更廣闊的研究空間。
特別值得關(guān)注的是,《中國(guó)古典文學(xué)意象研究》觀照了西方批評(píng)論著,對(duì)柏格森的“內(nèi)在綿延”時(shí)間和胡塞爾的“內(nèi)時(shí)間意識(shí)”自由運(yùn)用,以此來研究“意向性思維特征”,并通過圖示的直觀呈現(xiàn),說明構(gòu)成內(nèi)時(shí)間意識(shí)的三重方式,即原初印象、滯留、前攝,解釋意象性思維的構(gòu)成性特點(diǎn),揭示出意象性思維的內(nèi)在規(guī)律,即意象性思維有起始點(diǎn)或中心點(diǎn);意象呈現(xiàn)的思維有內(nèi)在的秩序和規(guī)律;意向性思維的指向性;意向性思維具有念念不斷、念念相續(xù)和相滲相融的本質(zhì)性特征,從而將隱秘模糊復(fù)雜的意識(shí)活動(dòng)以直觀的形態(tài)展現(xiàn)出來,將“意象”的研究向精深化推進(jìn)。
除此,引西方文論“境域”觀念對(duì)意象的研究也頗為精細(xì)、獨(dú)到。著者借助現(xiàn)象學(xué)家胡塞爾和海德格爾哲學(xué)體系的中心概念境域(horizon),觀照焦點(diǎn)意象和邊緣域意象,提出物象只有置于一種陳述關(guān)系中才可能成為意象。意象不是一個(gè)個(gè)具體的事象,意象“不可能是單一的、與他者無關(guān)的存在”[4]103,“沒有絕對(duì)的個(gè)體存在,任何個(gè)體的存在總是關(guān)乎整體存在的。任何一個(gè)細(xì)小的存在其實(shí)都是存在于一個(gè)關(guān)系中的,它能夠在這里,能夠被我們所注意,是被許許多多的因素決定了的。”[4]103意象只是境域這個(gè)整體中一時(shí)成為前景、焦點(diǎn)的某個(gè)存在。由此深化了袁行霈關(guān)于意象是“主觀化的客觀形象……客觀化的主觀情意”[8]50-63,批評(píng)了蔣寅的“物象既然融入了主觀情意,怎么還能叫作客觀物象”[9]70的唯物世界觀的二元認(rèn)識(shí)論,即將主、客觀現(xiàn)象視為截然不同的兩種存在。著者立足“意象”這一研究對(duì)象,縱覽中國(guó)古代杰出理論成果,博觀當(dāng)代人文學(xué)術(shù)精要,采他山之石以攻玉,納別水之址以厚己,從而對(duì)意象理論的研究取得了極為突出的表現(xiàn)。
三、論賞結(jié)合,體類精當(dāng)
針對(duì)具體作品中的某一“意象”深入探究,著文立說的“意象批評(píng)法”,一直是文學(xué)重要而普遍的研究方法。“意象批評(píng),是一種以意象為喻的批評(píng)方法。”[10]90“是指以具體的意象,表達(dá)抽象的理念,以揭示作品的風(fēng)格所在”[11]198。《中國(guó)古典文學(xué)意象研究》下篇“作品意象分析”就是通過“意象批評(píng)法”展示了古典文學(xué)的獨(dú)特魅力。尤為可貴的是,著者突破了文體限制(以往對(duì)“意象”的研究多集中于詩(shī)詞論析),采取縱向思維,由唐至清,對(duì)包括詩(shī)歌在內(nèi)的戲劇,如王實(shí)甫《西廂記》,湯顯祖《牡丹亭》;張可久散曲;小說如蒲松齡《聊齋志異》等典型作品都進(jìn)行了深入研究,凝練出“意象”之于“敘事”的三大功能:凝聚敘事主題、貫通敘事結(jié)構(gòu)、調(diào)控?cái)⑹鹿?jié)奏,對(duì)“意象與敘事”的認(rèn)識(shí)達(dá)到了新的高度。
從全書的結(jié)構(gòu)上看,下篇對(duì)具體作品的論析既是對(duì)上篇意象理論研究的具體實(shí)踐,又通過其獨(dú)到論述驗(yàn)證了上篇意象理論研究取得的成果。上下兩篇既獨(dú)立自存,又相互印鑒,脈絡(luò)清晰,特色鮮明,在論證結(jié)構(gòu)上臻于完善。既符合今人閱讀習(xí)慣,又便于操作,同時(shí)也切合開展中國(guó)古典文學(xué)意象研究的初衷。
值得指出的是,下篇語(yǔ)言雋秀,論析深入,既能帶來學(xué)術(shù)的思考,同時(shí)也是美的享受。如在研究唐人詩(shī)歌創(chuàng)作中意象由繁到簡(jiǎn)的意象構(gòu)成手法里,著者針對(duì)“鄉(xiāng)問”主題,先正向列舉,后逆向列舉了王績(jī)《在京思故園見鄉(xiāng)人問》、晚唐無名氏《問來使》和王維的《雜詩(shī)》,召喚出意象營(yíng)構(gòu)“從繁復(fù)到簡(jiǎn)潔,從焦點(diǎn)眾多、意象紛繁到越來越集中,最后集中在某一點(diǎn)上”[4]117的特征,在比較和鑒賞中,既完成了理論探索,又帶來思維通透的愉悅。在研究李商隱詩(shī)歌意象構(gòu)成的隱喻手法中,著者獨(dú)辟蹊徑,通過對(duì)“源域”和“目標(biāo)域”的分析,提出“文學(xué)不僅原本就是活生生的事件的再現(xiàn),還是創(chuàng)作者和讀者對(duì)活生生的事件的投入和經(jīng)歷。”[4]124解讀了李商隱使用的隱喻手法,在《錦瑟》中經(jīng)歷“華年”(目標(biāo)域)里如迷夢(mèng)、春心、珠淚、云煙般的事件及其刺激起的全部的理智和情感活動(dòng)的意義就是《錦瑟》全部的創(chuàng)作意圖。著者的論說啟示了新的文學(xué)探索路徑,具有啟發(fā)文學(xué)研究的思想價(jià)值。
《中國(guó)古典文學(xué)意象研究》在前輩學(xué)者已有的研究基礎(chǔ)之上,不僅借助現(xiàn)代研究理論將研究向更精深的方向推進(jìn),更將其與古典敘事、抒情文學(xué)緊密相連,從而使該書具有視野開闊、取精用弘的特點(diǎn)。當(dāng)然該書也存在些許問題。或由于《中國(guó)古典文學(xué)意象研究》一書是四人合著的智慧結(jié)晶,一方面集眾人之智,發(fā)揮了各自所長(zhǎng),在理論思辨、作品研究和表達(dá)方式上都取得了突出成績(jī),但另一方面,由于各自研究背景的差異,思維的斷層和節(jié)奏的失控類似不足也明顯存在。最為突出的一點(diǎn),上篇部分較有特色和代表性的意象理論成果在下篇中沒有得到具體作品中意象研究的呼應(yīng)。下篇雖有“體類完備”之優(yōu)勢(shì),也選取了典型的作品作為研究對(duì)象,但忽視了對(duì)這些作品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借鑒和比較,仍采用傳統(tǒng)意象批評(píng)的方法,沒有充分利用上篇中業(yè)已提出的新的理論視角和理論方法,其結(jié)果造成下篇語(yǔ)言的連綴和語(yǔ)義的復(fù)陳。如下篇張可久散曲中的意象研究、張岱詩(shī)歌意象研究等篇目。總之,對(duì)上篇獨(dú)到的理論成果運(yùn)用不足,上下兩篇沒有充分結(jié)合,進(jìn)而影響了全書的研究效益。同時(shí),對(duì)意象的種類以及意象與有唐以降文學(xué)的關(guān)系、功能、影響論說不足,對(duì)唐前文學(xué)典型“意象”也少有涉及,因而題目似有過大嫌疑,書名如定為《意象理論與有唐以降文學(xué)意象研究》,似乎更為妥當(dāng)。此外,該書雖在對(duì)比分析中否定了將意象譯為image的翻譯基礎(chǔ),卻未能提出新的更為確切的意象所對(duì)應(yīng)的西語(yǔ),在對(duì)外漢學(xué)的交流研討中恐多有不便。但是瑕不掩瑜,《中國(guó)古典文學(xué)意象研究》不僅是意象研究的最新成果,更以其獨(dú)特的研究視角,扎實(shí)的文獻(xiàn)考據(jù)和現(xiàn)代的理論思辨,對(duì)中國(guó)古典文學(xué)中的“意象”理論及作品意象分析有深入的挖掘,成為極有價(jià)值的成果,實(shí)現(xiàn)了對(duì)“意象”研究的深化與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