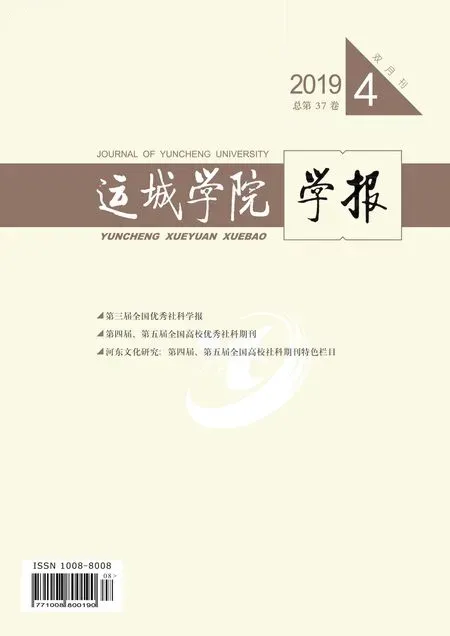《二十四詩(shī)品·悲慨》之獨(dú)特的悲情美學(xué)意蘊(yùn)
袁 俊 偉
(蘇州大學(xué) 文學(xué)院,江蘇 蘇州 215123)
一、悲慨之獨(dú)特的悲情內(nèi)涵
司空?qǐng)D(837~908),河中虞鄉(xiāng)(今山西運(yùn)城臨猗)人。(本文關(guān)于《二十四詩(shī)品》之真?zhèn)沃妫娑徽摚視喝鹘y(tǒng)看法,即為司空?qǐng)D所作。)司空?qǐng)D《二十四詩(shī)品》,以《雄渾》啟首,又化《沖淡》,并以《流動(dòng)》作尾,陰陽(yáng)調(diào)和,大化流衍,大多取超詣沖和之詩(shī)風(fēng),超塵入道之詩(shī)境,構(gòu)建了其“韻外之致”的美學(xué)理想,講求“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及“味外之旨”,做到“近而不浮,遠(yuǎn)而不盡”的詩(shī)學(xué)意境,總體而言是道家一種純真素樸、超逸玄遠(yuǎn)之境。在中國(guó)以儒家詩(shī)教為綱的文論發(fā)展史上,司空?qǐng)D這種超逸沖淡詩(shī)風(fēng)也啟開由唐至宋以平淡沖和節(jié)制為美的禪韻詩(shī)學(xué),并在后世的歐陽(yáng)修、蘇東坡、嚴(yán)滄浪、王漁洋、袁子才及王靜安等人身上得到了傳承和發(fā)展,完善了中國(guó)文論的博大體系。然而,縱覽全品,其中《悲慨》一品,“大風(fēng)卷水,林木為摧。適苦欲死,招憩不來(lái)。百歲如流,富貴冷灰。大道日喪,若為雄才。壯士拂劍,浩然彌哀。蕭蕭落葉,漏雨蒼苔。”無(wú)疑已偏離了他自己所設(shè)詩(shī)學(xué)理想,呈現(xiàn)出一種迥異于常的面貌,其悲情內(nèi)蘊(yùn)甚至超越了中國(guó)傳統(tǒng)美學(xué)范疇的范圍,具有了一種近似于西方悲劇的美學(xué)意蘊(yùn),給后世留下了一個(gè)很大的悲情美學(xué)闡釋空間。“悲慨”二字,自古多有解釋,“悲壯慷慨”、“悲涼嘆慨”、“悲憤惋慨”、“悲歌感慨”等,總體情調(diào)是悲,悲壯和悲憤的色彩漸弱了些,更多了幾分悲嘆和悲情。這種審美類型,讓人有一種有悲難言、有苦難訴的心理體驗(yàn)。似乎是某位詩(shī)人看落日樓頭,聽斷鴻聲里,正欲起吳鉤,舉手把欄桿拍遍,然而卻又把手放下,嘆一句“可惜流年,憂愁風(fēng)雨,樹猶如此!倩何人喚取,紅巾翠袖,揾英雄淚!”(辛棄疾《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然而,此品中雄才和壯士是否是英雄,尚且值得商榷。我們可對(duì)《悲慨》一品,做一番細(xì)究。首句“大風(fēng)卷水,林木為摧”同末句“蕭蕭落葉,漏雨蒼苔”形成一種呼應(yīng),同樣可以看作是寫外在之景,也可以看作是一種因果,風(fēng)卷木摧后,徒留下一片蕭葉雨苔的狼藉景象,叫人無(wú)盡唏噓。這種景物描寫,亦有隱喻的成分,楊廷芝以《詩(shī)經(jīng)》中的極為苦寒而惡劣的“北風(fēng)”和“雨雪”來(lái)解,“大風(fēng)卷水,聲不可聞;林木為摧,感且益慨。起手似有‘北風(fēng)’、‘雨雪’之意。”[1]115“大風(fēng)”在社會(huì)層面可借喻黑暗暴虐的專制力量,與其相對(duì)的“水”同“林木”就成了迫害之下的受害者,“卷”、“摧”二字,可見大風(fēng)力道之大,速度之快,破壞力之強(qiáng),形成摧枯拉朽之勢(shì),這是一種毀滅性的力量。孫聯(lián)奎在《詩(shī)品臆說》中說:“大風(fēng)卷水,其瀾必狂;林木為摧,其巢必復(fù)。”[1]38所以,我們可以認(rèn)為一股來(lái)自于社會(huì)的恐怖力量正在摧毀一個(gè)有生命的群體,家國(guó)動(dòng)蕩,民不聊生。
“適苦欲死,招憩不來(lái)”,又可作“意苦若死”,表現(xiàn)了生命個(gè)體在大風(fēng)的恐怖力量之下產(chǎn)生的生不如死、痛苦欲死的創(chuàng)痛,無(wú)法排解。“適”有受苦之艱,“欲”則有無(wú)法忍受之意。人在這時(shí)會(huì)產(chǎn)生生命本能的“憂生”之嗟和“憂世”之嘆,故而有了“百歲如流,富貴冷灰”,前一句脫自《古詩(shī)十九首》的“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主人公這時(shí)悲慨于生命的短促,有一種無(wú)法揮掉的孤獨(dú)感,或許還能由此生出形而上的憂慮,極為悲愴。后一句中的富貴在這種憂生中也變成了過眼云煙,徹底冷絕了,人生危卵,富貴何求,只道是“舊時(shí)王謝堂前燕”。倘若把這一句看作大風(fēng)中的憂生,那么“大道日往,若為雄才”便是憂世。憂世直面人世的困厄和凋敝,是一種社會(huì)層面上的憂患和不安,整個(gè)社會(huì)同廣大的群體之間產(chǎn)生了無(wú)法調(diào)和的矛盾,便造成了憂世的痛苦。其實(shí),憂生中必有憂世,憂世中必有憂生。“大道”既有天地之恒道,又有社會(huì)之世道,后者更偏于社會(huì)倫理政治之道,即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禮記·禮運(yùn)》)不過,大風(fēng)下道統(tǒng)不復(fù),綱常已廢,“大道”徹底淪喪了,人同花草魚獸蕓蕓眾生也跟著慘遭毀滅。這時(shí)候,理應(yīng)有具備大略的雄才橫空出世,扶大廈之將傾,挽狂瀾于既倒。然而,我們卻未看到“若為”二字,一方面可看作百姓渴求誰(shuí)是雄才,一方面可看作對(duì)于即便有了雄才也只能是無(wú)力回天的嘆息。這時(shí)的悲慨已然是全部陷入了絕望,社會(huì)同個(gè)體生命絕無(wú)半點(diǎn)亮色。
“壯士撫劍,浩然彌哀”是全詩(shī)最有感染力的一句,雄才尚且無(wú)功,壯士徒有空勇又怎奈何,而且壯士本應(yīng)拔劍,如今卻黯然低撫,恐怕也是消盡了擔(dān)當(dāng)。我們腦中所現(xiàn)不是那位“風(fēng)蕭蕭易水寒”的壯士荊軻,他早就消泯掉了悲壯之氣和慷慨之力,我們似乎看到的是欲將投水的屈原。“浩然彌哀”場(chǎng)面之大,悲痛之絕,似乎整個(gè)洪宇都陷入萬(wàn)馬齊喑的哀彌之中,它讓人在內(nèi)心里產(chǎn)生了一種恐懼,有一種西方的悲劇美感。最后一句“蕭蕭落葉,漏雨蒼苔”與開首形成沖撞渲染,叫人徹底陷入哀莫大于心死的處境。如果按照中國(guó)特有的美學(xué)形式,應(yīng)該用一種豪邁的氣勢(shì)一改前面的哀傷,然而我們并沒有看到仰天大笑的李白,更沒有看到鐵馬冰河的陸游,而是聽見杜甫深嘆了一句“無(wú)邊落木蕭蕭下”,何遜低唱了一句“夜雨滴空階,孤館夢(mèng)回”。這便成了《二十四詩(shī)品》中最獨(dú)特的悲慨之悲情美學(xué)內(nèi)涵,當(dāng)然時(shí)人也有總結(jié)概括,“悲慨”或體現(xiàn)出“天命難違的無(wú)力之悲”、“時(shí)光易逝的無(wú)奈之悲”、“事功難立的無(wú)助之悲。”[2]
二、悲慨之中西方悲劇色彩的辨析
諸多學(xué)者在解釋“悲慨”時(shí),同西方的悲劇審美形態(tài)做對(duì)比,得到了很好的研究成果。張國(guó)慶教授認(rèn)為“《悲慨》展現(xiàn)了一出近乎西方式的悲劇,一種中國(guó)罕見的悲劇型態(tài);‘悲慨’不僅是一個(gè)風(fēng)格概念,也是一個(gè)近乎‘悲劇’的美學(xué)范疇。”[3]217他厘清了西方悲劇中三個(gè)具體類別,即作為戲劇種類的“悲劇”、作為美學(xué)范疇的“悲劇”和作為一般美學(xué)概念的“悲劇性”,然后就中西悲劇的差異對(duì)《悲慨》進(jìn)行具體分析,最后認(rèn)為“雖然中國(guó)古代明顯缺乏對(duì)悲劇的認(rèn)識(shí)和對(duì)悲劇理論的探討,但《悲慨》卻以獨(dú)特的方式將標(biāo)準(zhǔn)的悲劇美學(xué)精神揭示了出來(lái);雖然中國(guó)古代戲劇中只有苦戲怨譜,但《悲慨》卻以獨(dú)特的方式展現(xiàn)了一出近乎西方式的悲劇、一種中國(guó)罕見的悲劇型態(tài);雖然中國(guó)古代明顯缺乏對(duì)悲劇的認(rèn)識(shí)和對(duì)悲劇理論的探討,但《悲慨》卻以獨(dú)特的方式將標(biāo)準(zhǔn)的悲劇美學(xué)精神揭示了出來(lái);雖然中國(guó)古代沒有‘悲劇’這樣一個(gè)美學(xué)概念,但《悲慨》的‘悲慨’卻因?yàn)榫哂信c‘悲劇’極為相近的理論內(nèi)涵而成了一個(gè)與‘悲劇’非常相近的美學(xué)概念!”[3]217
張國(guó)慶教授所認(rèn)為的“悲慨”美學(xué)內(nèi)涵更偏于西方的悲劇。悲劇作為西方的一種基本審美類型,本身具有悠久的歷史。亞里士多德說“悲劇是對(duì)于一個(gè)嚴(yán)肅、完整、有一定長(zhǎng)度的行動(dòng)的模仿”[4]19,并且揭示了悲劇給人的審美體驗(yàn),即借助于引起人們的憐憫和恐懼之情來(lái)使人們的靈魂得到凈化和陶冶。黑格爾提出“矛盾沖突論”,認(rèn)為悲劇產(chǎn)生于理念的分裂。尼采受叔本華影響,認(rèn)為悲劇誕生于古希臘兩種精神,即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悲劇就是二者的結(jié)合,人要擺脫痛苦,就要借助于藝術(shù)在悲劇中體驗(yàn)生命永恒的美好。后來(lái),車爾尼雪夫斯基把悲劇概念同崇高概念相結(jié)合,認(rèn)為崇高是悲劇的本質(zhì)屬性,悲劇性也就是崇高性。然而以西方理論概念來(lái)解決中國(guó)問題,本身值得商榷。況且學(xué)界對(duì)于中國(guó)無(wú)悲劇之說的爭(zhēng)議由來(lái)已久。西方悲劇有其悲劇性,中國(guó)的悲劇是否需要依其理論原則來(lái)界定。如果相悖,是否就不能認(rèn)為算是悲劇,從而否定中國(guó)有悲劇的存在。
這場(chǎng)爭(zhēng)議的開端應(yīng)是王國(guó)維的《紅樓夢(mèng)評(píng)傳》,他由叔本華悲觀主義關(guān)于悲劇的三種劃分,認(rèn)為《紅樓夢(mèng)》是中國(guó)唯一一部悲劇,且是“悲劇中的悲劇”,因?yàn)橹袊?guó)無(wú)悲劇傳統(tǒng),《紅樓夢(mèng)》在樂感精神主導(dǎo)的中國(guó)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后來(lái)李澤厚有了中國(guó)樂感文化、西方罪感文化之說。不過,王國(guó)維以叔本華哲學(xué)將《紅樓夢(mèng)》主題解釋為“欲望之解脫”也可以算作一種“強(qiáng)制闡釋”。他后來(lái)在《宋元戲曲論》中做了修正,“明以后,傳奇無(wú)非喜劇,而元?jiǎng)t有悲劇在其中。就其存者言之:如《漢宮秋》《梧桐雨》《西蜀夢(mèng)》《火燒介子推》《張千替殺妻》等,初無(wú)所謂先離后合,始困終亨之事也。其最有悲劇之性質(zhì)者,則如關(guān)漢卿之《竇娥冤》,紀(jì)君祥之《趙氏孤兒》。劇中雖有惡人交構(gòu)其間,而其蹈湯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劇中,亦無(wú)愧色。”[5]98他在這里雖然還是用叔本華的悲劇理論來(lái)解決中國(guó)問題,卻也否定了“中國(guó)無(wú)悲劇”之說。
現(xiàn)代諸多學(xué)者也就這個(gè)問題進(jìn)行了討論,如蔡元培認(rèn)為西方重悲劇中國(guó)尚喜劇說;胡適在《文學(xué)進(jìn)化觀念與戲曲改良》中說:“中國(guó)文學(xué)最缺乏的是悲劇的觀點(diǎn)。無(wú)論是小說,是戲劇,只是一個(gè)美滿的團(tuán)圓。”[6]203魯迅先生在《中國(guó)小說史略》中表明中國(guó)少悲劇:“凡是歷史上不團(tuán)圓的,在小說里統(tǒng)統(tǒng)給他團(tuán)圓,沒有報(bào)應(yīng)的,給他報(bào)應(yīng),互相欺騙——這實(shí)在是關(guān)于國(guó)民性的問題。”[7]246我們?nèi)绻?lián)系到新文化運(yùn)動(dòng)中那個(gè)以新文化代替舊文化的全盤否定的時(shí)代背景,不難認(rèn)識(shí)到,這批新文化大家本身就存在一個(gè)立場(chǎng)問題,即為了啟蒙與國(guó)民性療治而故意貶低了中國(guó)的悲劇價(jià)值。所以寇鵬程曾有過思考,“中國(guó)無(wú)悲劇從某種程度上說是個(gè)偽命題,因?yàn)檫@是長(zhǎng)期以來(lái)我們只注重悲劇的超越性而忽視了它的共鳴性結(jié)果。共鳴與超越本來(lái)是悲劇生成的兩個(gè)機(jī)制,但是現(xiàn)在悲劇的‘雙軌’審美機(jī)制變成了‘單軌制’,由此而單方面地將一大批悲劇排斥在所謂‘真正的悲劇’之外。”[8]這一現(xiàn)象就相當(dāng)于在某些時(shí)代,某些人為了強(qiáng)調(diào)文學(xué)階級(jí)論而刻意去批判文學(xué)的人性論。
文學(xué)既可以承載超越為主題的思想,也應(yīng)該寄托共鳴為旨?xì)w的情感,不能厚此薄彼。如果說西方的悲劇更注重崇高感的凈化和升華,那么中國(guó)的悲劇則偏于悲情化的憐憫和共鳴。西方的悲劇應(yīng)該被稱為“崇高悲劇”,無(wú)論是命運(yùn)悲劇、性格悲劇、社會(huì)悲劇,它總是在強(qiáng)調(diào)反抗意識(shí),人們就應(yīng)該在與社會(huì)、自然等的沖突對(duì)抗中尋求一種解脫后的精神升華,內(nèi)心深處就是一種海洋文明中的罪感文化來(lái)主導(dǎo)。中國(guó)的悲劇則是一種“悲情悲劇”,在“苦情”、“怨譜”中,理解人生的苦境,尋求一種惺惺相惜的理解與悲憫,從而在共鳴中得到內(nèi)心的慰藉,能夠繼續(xù)生活下去,這就是農(nóng)業(yè)文明中樂感文化的寬慰了。西方悲劇中的主人公都是預(yù)設(shè)好的要挑戰(zhàn)天神的英雄人物,中國(guó)悲劇的主人公則是渴求菩薩保佑的小人物;西方悲劇的結(jié)構(gòu)往往是一悲到底,非要置于一種極端的處境,在魚死網(wǎng)破的對(duì)抗中得到深刻的主題,中國(guó)悲劇的結(jié)構(gòu)卻有著悲喜交替的過程,往往更以大團(tuán)圓結(jié)局,寄托著中國(guó)人生活的一種天人合一式的希望。
在中國(guó)悲劇中,還會(huì)用一種悲壯的色調(diào)來(lái)化解悲哀,這便是傳統(tǒng)儒家把惻隱之心轉(zhuǎn)化為英雄氣概的一個(gè)過程,誠(chéng)如朱光潛在《談惻隱之心》中引用孔子的“仁者必有勇”、“滔滔者天下皆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之與而誰(shuí)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以及釋迦“我不入地獄,誰(shuí)入地獄!”等來(lái)說“古今偉大人物的生平大半都能證明真正敢做敢為的人往往是富于同類情感的。菩薩心腸與英雄氣骨常有連帶關(guān)系。”[9]62故而在中國(guó)文論中又有司馬遷的“發(fā)憤說”,韓愈的“不平則鳴”說等。中國(guó)的悲劇與其文學(xué)精神一樣,總體而言就是揭露黑暗、諷刺社會(huì)、維護(hù)人的尊嚴(yán)的人道主義文學(xué),于是便有了杜甫、關(guān)漢卿等為民說話的文學(xué)家和戲劇家。“悲慨”僅僅是中國(guó)悲劇的一種罕見類型,我們可以看到其悲壯的成分削弱了,悲涼的成分增加了,似乎看不到英雄氣概,而是英雄落幕的悲情,它讓我們感到了一種近似西方絕望超越的悲劇之美。我們可以借助西方悲劇理論來(lái)理解悲慨的美學(xué)內(nèi)涵,但是絕不能用西方悲劇理論來(lái)定義悲慨這一罕見的中國(guó)悲劇類型。所以,張國(guó)慶教授才會(huì)認(rèn)為“悲慨”表現(xiàn)出了西方悲劇美學(xué)精神,這是一種同西方悲劇大體相當(dāng)?shù)壤碚摳拍詈兔缹W(xué)范疇,更是一種獨(dú)有的中國(guó)的悲劇類型。
三、悲慨之悲絕人格情調(diào)
中國(guó)詩(shī)論的對(duì)于詩(shī)歌的欣賞和品評(píng)往往重直覺感受和印象評(píng)賞,印象式的批評(píng)話語(yǔ)往往有諸如“氣象”、“風(fēng)骨”、“格調(diào)”、“氣韻”等名詞性術(shù)語(yǔ),還有諸如“豪放”、“灑落”、“悲慨”、“凄婉”等形容詞性術(shù)語(yǔ)。“悲慨”一品應(yīng)該算是后者。葉嘉瑩曾就形容詞性批評(píng)術(shù)語(yǔ)有過評(píng)說,“雖蘊(yùn)涵有評(píng)者對(duì)作品的極精微的了解和辨別,然而這種批評(píng)方式畢竟過于簡(jiǎn)單和抽象,關(guān)于此種不足,中國(guó)批評(píng)傳統(tǒng)有另兩種批評(píng)方式來(lái)補(bǔ)足。其一乃以作者之人格性情為解說其作品風(fēng)格的依據(jù),其二則是舉出另一種富有詩(shī)意的意象來(lái)作為抽象之風(fēng)格的具體描述”[10]243以人論詩(shī)的傳統(tǒng)自古有之,如孟子的“知人論世”、“知言養(yǎng)氣”(《孟子》),曹丕的文氣論(《典論·論文》),劉勰的“觸類以推,表里必符”(《文心雕龍》)等。司空?qǐng)D的《二十四詩(shī)品》中諸多饒有趣味的仙人形象就是一種以人格論詩(shī)的明證,且以各種意象來(lái)喻示就是以具體意象描述抽象風(fēng)格的典范。
諸多學(xué)者會(huì)引證很多詩(shī)人及其作品來(lái)研究“悲慨”,如項(xiàng)羽“力拔山兮氣蓋世,時(shí)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垓下歌》),陳子昂“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lái)者。念天地之悠悠,獨(dú)愴然而涕下。”(《登幽州臺(tái)歌》)柳宗元“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刺史》)等,這些詩(shī)人的作品都可以表現(xiàn)出“悲慨”中闊大、悲痛之感。司空?qǐng)D在寫作《悲慨》時(shí),或許也會(huì)聯(lián)想到他們的形象,然后將其總結(jié)成悲慨的詩(shī)論,借他人酒杯澆心中塊壘。我們自可把《悲慨》一品看作司空?qǐng)D的詩(shī)歌作品,結(jié)合其生平和詩(shī)作進(jìn)而考察詩(shī)人悲慨的生命人格情調(diào)。當(dāng)然,我們知道這種以人論詩(shī)和以詩(shī)論人的批評(píng)方式存在著缺點(diǎn),“評(píng)詩(shī)人往往把作者人格的價(jià)值與作品本身價(jià)值混為一談;在評(píng)說時(shí)不從作品本身之藝術(shù)成就立論而津津于作者為人行事之評(píng)述,這當(dāng)是本末倒置的一種價(jià)值的誤植。”[10]246這就有新批評(píng)學(xué)派關(guān)于詩(shī)歌的“真摯性”討論了,艾略特曾有“詩(shī)人不表達(dá)自己人格”的論說,這當(dāng)是他“無(wú)我觀”的延伸。西方文論為了表現(xiàn)藝術(shù)的獨(dú)立價(jià)值更偏向于抽離詩(shī)人來(lái)看待詩(shī)歌,韋勒克也有過類似表述,“一首詩(shī)的真摯性似乎沒有什么意義。真摯地表達(dá)什么呢?表達(dá)產(chǎn)生這一意象的感情狀況嗎?表達(dá)寫詩(shī)時(shí)的感情狀況嗎?或者真摯地表達(dá)這首詩(shī),也就是說表達(dá)詩(shī)人寫作時(shí)腦子里形成的語(yǔ)言結(jié)構(gòu)嗎?當(dāng)然是最后一條,詩(shī)應(yīng)該真摯地表達(dá)詩(shī)。”[11]232
我們認(rèn)識(shí)到完全以詩(shī)人人格性情的價(jià)值來(lái)衡量詩(shī)歌價(jià)值也有不妥,但是透過作者之人格性情來(lái)闡釋其風(fēng)格特色又是十分必要的。而中國(guó)詩(shī)論向來(lái)有追求文論人格化的旨趣,歆慕于一種高尚之人格,我們?cè)谇砩狭丝吹搅吮芸吹狡涓邼嵉南悴菝廊嗽谖勰嘀袘K遭毀滅,方才有了悲慨的審美感受。中國(guó)文論無(wú)論是儒道,都在追求道德人格,中國(guó)的文論最終可能還是會(huì)歸于一種人格和境界的討論中去。司空?qǐng)D的《二十四詩(shī)品》大多數(shù)寄托了老莊的精神境界和理想人格,一如各種仙人形象。或者深受當(dāng)時(shí)佛教美學(xué)意境的影響,“《二十四詩(shī)品》乃唐代美學(xué)融攝佛學(xué)的垂范。在這一理論體系中,藝術(shù)世界的本體是剎那生滅的絕對(duì)存在;藝術(shù)世界的創(chuàng)造主體是能夠體現(xiàn)絕對(duì)存在的有覺生命;藝術(shù)世界的生成來(lái)自于有覺生命對(duì)于絕對(duì)存在的生命禮贊。”[12]然而,悲慨一品的獨(dú)特痛苦還要進(jìn)入儒家淑世主義來(lái)討論。司空?qǐng)D好以味論詩(shī),追求醇美,曾在《與李生論詩(shī)書》中言說,“醇美者有所乏也”,“償復(fù)以全美為工,即知味外之旨矣”這里的醇美就是全美,就是本真之美了。其中又有“然直致所得,以格自奇”[13]98這就是他詩(shī)中美的追求,我們也可以從人格中窺見一些詩(shī)格。“悲慨”一品當(dāng)然有他這些詩(shī)歌美學(xué)的追求,只是他的這些詩(shī)美追求遭到了毀滅,我們也可以從悲慨中看到司空?qǐng)D某個(gè)人生階段的悲慨生命情調(diào)了。
司空?qǐng)D的生命軌跡也是頗多坎坷,晚年似乎生活在一種無(wú)法調(diào)和的心理矛盾中,內(nèi)心境界無(wú)比悲涼,又時(shí)而故作曠達(dá)超脫之音。他曾有治國(guó)之志,自然也講三不朽,在《將儒》曾說“憂天下而訪于我者”以建功立業(yè),從而改變“儒失其柄,武玩其威”的“道之不振”的局面,重整李唐氣象。可是這個(gè)王朝氣數(shù)已盡,他不得已遁世于中條山王官谷,寫下大批極具悲慨哀情的詩(shī)歌作品表達(dá)亡臣之傷,剛出長(zhǎng)安時(shí),他說“身病時(shí)亦危,逢秋多慟哭。風(fēng)波一搖蕩,天地幾翻覆。孤螢出荒池,落葉穿破屋。勢(shì)利長(zhǎng)草草,何人訪幽獨(dú)。”(《秋思》)這就是黃巢起義時(shí)人民的寫照。“家山牢落戰(zhàn)塵西,匹馬偷歸路已迷。冢上卷旗人簇立,花邊移寨鳥驚啼。本來(lái)薄俗輕文字,卻致中原動(dòng)鼓鼙。將取一壺閑日月,長(zhǎng)歌深入武陵溪。”(《丁未歲歸王官谷有作》)這個(gè)時(shí)候,他就用佛老思想來(lái)遁世,“詩(shī)中有慮猶須戒,莫向詩(shī)中著不平。”(《白菊》)“此身閑得易為家,業(yè)是吟詩(shī)與賞花”(《閑夜二首》其二)“儂家自有麒麟閣,第一功名為賞詩(shī)”(《力疾山下吳村看杏花》)等。但是內(nèi)心的悲痛是騙不了自己,他大多數(shù)作品都是“風(fēng)荷似醉和花舞,沙鳥無(wú)情伴客閑。總是此中皆有恨,更堪微雨半遮山”的悲涼感慨情調(diào)。最終,這位耐辱居士在人間浩劫之中,也沒能像仙人一樣“御風(fēng)蓬葉”、“超以象外”,在“薄言情晤”后淪為了大道日往下的拂劍壯士,《新唐書.司空?qǐng)D傳》有記“哀帝弒,圖聞,不食而亡,年七十二”,他立功不得,著《詩(shī)品》立言,最后把自己演繹成了一幕決絕悲情的“悲慨”,用自己的人格完成了一次立德。“悲慨”也化作了司空?qǐng)D的人格生命情調(dià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