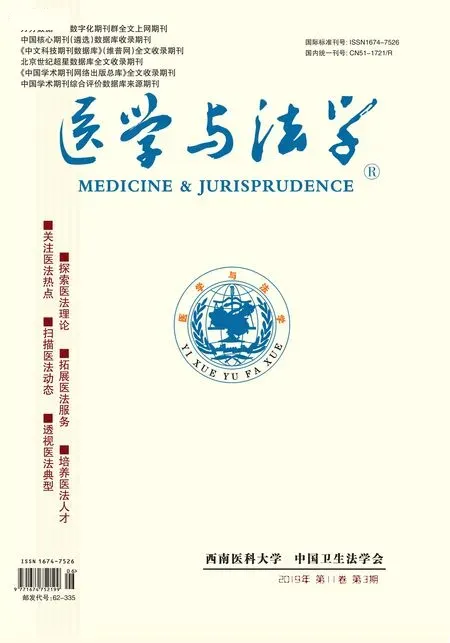從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試析全球團結原則的落實方法
裴任
當今世界人類距離全球健康還很遠,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底層人民每天處于疾病與死亡的威脅之中,其健康權得不到保障。在過去,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時常強調發達國家對于發展中國家的援助,這被稱為“健康援助”。然而,美國勞倫斯·O.戈斯廷教授指出:“把全球健康的嘗試看成是一種健康援助從根本上是不足的,因為它意味著世界按照需求被分成了捐贈者與授予者。這過于簡單,國家間的合作,無論是鄰國之間還是各個洲之間,也是共同承擔健康風險和共同培養應對風險的能力”,并且“‘援助’的概念也預設和加強了一種一方為施舍者而另一方為依賴者的內在不平等關系”,同時“它也意味著施舍者決定了全球健康援助的數量和目標”,甚至意味著“接受國不能為它們國家的居民承擔全部的責任,因為它們可以把指責轉嫁于捐贈者”。[1]可見,“健康援助”這一概念本身存在問題,需要構建新的全球健康治理機制。
一、“全球團結原則”的含義及其所面臨的問題
為了糾正“健康援助”這一概念的弊端,戈斯廷教授提出了全球團結原則,他認為:“全球團結要求一種平等的合作關系——所有參與者,無論是國內的還是國際的,都要盡自己的義務并為世界各地的人民保證健康和安全條件。”[2]也就是說,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無論是富人還是窮人,抑或是全球形形色色的組織,都應當負擔促進全球健康的義務;健康的全球治理絕不是一種單向的施舍與援助,而應當是一種共同負責的合作關系,這被他稱為“全球團結”。[3]
全球團結原則有兩個核心要素,第一個是“平等”,第二個是“共同擔責”,這使得全球團結原則符合“全球健康正義”的理念,但同時也使得其實現有難度:首先,當今國際社會各國的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實力并不相同,地位并未實現真正的平等,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發言權有著很大的不同,在全球性框架中所能得到的利益也有著天壤之別;其次,各國的國際政策基本都是從本國利益出發并進行考慮的,如果在一個共同負責的系統中,一國承擔責任后不能有效、公平地實現其本國的利益訴求,那么就無法讓該國有繼續承擔責任的動力。
因此,究竟如何實現公平、有效的利益分配,從而實現“平等”與“共同擔責”兩個要素,最終落實全球團結原則,是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二、為全球團結原則的落實而可資借鑒的新視角與方法
2011年5月,第六十四屆世界衛生大會上通過了《共享流感病毒以及獲得疫苗和其他利益的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簡作《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建立了大流行性流感中病毒菌株的共享機制以及疫苗和其他利益的分配機制。
該框架的原則部分,提到“會員國承諾在平等基礎上共享H5N1及其他可能引起人間大流行的流感病毒以及各項利益,并將其視為全球公共衛生集體行動的同樣重要部分”以及“承認采取集體行動減輕公共衛生風險的必要性”,這些表述已經體現了各會員國在“平等”的基礎上“共同擔責”的思想,充分地體現了全球團結原則的要素,是與全球團結原則相契合的。而由于此種契合的存在,在謀求全球團結原則的落實方法時,《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的制度設計也就有了借鑒意義。
筆者認為,《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主要有以下兩個值得借鑒的機制:
(一)實質平等的利益分配機制——以風險與需求標準傾向于發展中國家
分析、總結《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中利益分配機制,其體現為三種具體形式:
第一種是“世衛組織儲備-分配機制”。該機制的主體是世界衛生組織,其第一步是儲備規范,即世衛組織通過施行該框架第六部分“大流行性流感防范利益共享系統”之第6.8條“抗病毒藥物儲備”和6.9條“流行性流感防范疫苗儲備”的規定,對發達國家及地區的疫苗生產商以及其他機構、組織、實體所生產的疫苗、藥物和相關設備進行提成,同時也接受捐獻,然后將這些資源儲備起來;其中,發達國家及地區主要承擔著“要求其國內(或地區內)生產商優先考慮并滿足世衛組織PIP疫苗儲備的需求,捐贈足夠劑量的H5N1疫苗”的義務。在資源數量不足時,世衛組織還可以根據第6.14條“可持續和創新性籌資機制”之規定,通過“使用世衛組織流感監測和應對系統的流感疫苗、診斷試劑和藥品生產商每年向世衛組織繳納的伙伴關系捐款”和會員國的自愿捐款,來提供和有效調配大流行性流感疫苗和抗病毒藥物,從而補充不足的儲備。其第二步是分配,世衛組織把這些資源按照“公共衛生風險和需要”的標準,分配給受影響國家、發展中國家等。
第二種是“供應量保留和分層定價措施”機制。這一機制通過該框架第六部分“大流行性流感防范利益共享系統”之第6.10條“在大流行期間提供疫苗供發展中國家使用”和第6.11條“提供大流行性流感疫苗”及第6.12條“分層定價”等規定來予以實現。一方面,發達國家及地區負擔著要求其流感疫苗生產商在每個生產周期為發展中國家保留一部分供應量的義務;另一方面,考慮到發展中國家市場無力負擔昂貴的疫苗和藥物,當生產商將疫苗和藥物銷往發展中國家時,應當進行分層定價。分層定價,則是具體通過要求生產商考慮有關發展中國家的收入水平并且與發達國家及地區有關當局進行洽談達成定價來實現的。
第三種是“技術轉讓措施”機制。這一措施通過該框架第六部分“大流行性流感防范利益共享系統”之第6.13條“技術轉讓”的規定來實現。其具體的方式又分為兩種:一種是直接的技術轉讓,即發達國家及地區應當要求流感疫苗、診斷試劑和藥品生產商作出具體努力,將這些技術酌情轉讓給其他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最終使發展中國家有研究和生產能力;另一種是接受PIP生物材料的流感疫苗生產商向發展中國家流感疫苗生產商頒發“非專屬性、免使用費許可證”,以便使用其技術、專門知識等。兩種不同形式的技術轉讓的義務,與捐贈或保留疫苗的義務、捐贈或保留抗病毒藥物的義務并列在附件SMTA2協議中,與世衛組織簽訂SMTA2協議的疫苗、藥物生產商等實體可以從中選擇至少兩項履行。
筆者認為,該機制的可借鑒性有兩個方面:
首先,在上述三種具體機制中都有對于發展中國家利益的傾斜保護,這實際上是《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利益分配機制對于“平等”價值的體現。《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的原則部分第(3)條提到,“有必要制定一個平等、透明、公平和有效的框架,共享H5N1病毒及其他可能引起人間大流行的流感病毒,并共享利益,包括向需要者尤其是發展中國家需要者提供和分發負擔得起的診斷試劑和包括疫苗在內的治療工具”。這種“平等”是一種“不同情況差別對待”的實質平等,其利益分配機制將向發展中國家傾斜。美國著名學者羅爾斯曾經指出,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制度的設計和安排中也必須對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進行某種限制,來確定哪種不平等是正當合理的,是允許存在的。[4]因此羅爾斯提出第二正義原則,他認為“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應當這樣安排,使它們:第一,在與正義的儲存原則一致的情況下,適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5]發展中國家可以看作“最少受惠者”,此種“不同情況差別對待”的實質平等無疑符合正義原則的要求。
其次,該利益分配機制傾斜的標準,是以風險和需求為導向的。這同樣已經體現在該框架的原則部分第(8)條中,即“應當根據公共衛生風險與需要與所有會員國分享由共享H5N1病毒及其它可能引起人間大流行的流感病毒帶來的利益”;以及該框架第六部分“大流行性流感防范利益共享系統”之第6.0.2條第(iii)和第(iv)項的明確規定中,即“根據公共衛生風險和需要,優先將對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受影響國家甚為重要的利益,諸如包括抗病毒藥物及其他可能引起人間大流行的流感病毒疫苗作為首要重點,尤其是在這些國家自己無力生產或取得流感疫苗、診斷試劑和藥品時更要如此。在確定優先次序時,將根據透明原則以專家對公共衛生風險和需求的評估為依據”和“根據接受國的公共衛生風險與需求,通過技術援助和技術、技能及專門知識轉讓以及擴大流感疫苗生產,逐步建設它們在這方面的能力”。這些規定表明,在《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中,無論是分配疫苗、診斷試劑和藥品等直接物質利益,還是分配技術、技能、專門知識和生產能力等無形的長遠利益,分配優先次序的確定標準都是“公共衛生風險與需要”。英國學者戴維·米勒認為,對于團結性共同體而言,“實質性的正義原則是按需分配”。[6]該框架以風險和需求為標準的做法,與戴維·米勒對“團結型共同體”中利益分配機制的界定相符合,對于落實全球團結原則有著重要意義。
(二)疫苗生產商的利益保證措施——以成本收益調控促進生產能力擴大
由于目前全球化的發展,流感全球大流行暴發后,不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事實上都處于大流行性流感的威脅中,此時,最本質的問題——同時也是矛盾的根源就出現了,目前的疫苗、診斷試劑、藥品等資源的生產能力還尚未豐富到可以充分有余地供應全球的程度。《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的制定者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在該框架的原則部分第(15)項對“全球流感疫苗生產能力仍不足以滿足大流行時的預期需要”表示了嚴肅的關切。之前所分析的以需求和風險作為標準的傾斜式的利益分配機制,也只是在這一根本問題之下所能采取的最優措施而已,雖然優先保證公共衛生風險最大、需求最緊急的國家的供應是最合理的,但是終究要犧牲優先次序劣后的其他國家的利益,最終也會影響全球團結的實現。因此,如果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關鍵還是在發展疫苗、藥品、診斷制劑的研發、生產能力,保證充分的疫苗、藥品的供應。目前,這些資源主要由疫苗、診斷試劑和藥品的生產商生產,因此,具體而言,就是要保證與發展生產商的生產能力。同時,提高生產商的能力,從另一方面講,也是在促進全球團結原則中“共同擔責”要素的實現。在該框架中,明確了采取一系列的發展生產能力的措施:
第一,在之前利益分配機制中所介紹的技術轉讓措施,其本身也是對于發展中國家疫苗生產商的生產能力的建設。在發展中國家的生產商獲得生產技術或者無使用費的許可后,其生產能力顯然將會獲得提高。
第二,《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第六部分之第6.6條“實驗室和流感監測能力建設”與第6.7條“管制能力建設”的規定,使得擁有先進的實驗室監測能力和管制能力的發達國家負擔了與發展中國家合作的義務。[7]發展中國家對于流感的研究、監測以及迅速鑒定和批準疫苗、藥物和診斷試劑的能力將獲得提高。這兩條也是在間接發展生產商的生產能力。原因在于,一旦種子病毒被開發出來,測試、許可和批準是必需的,加上之前設計疫苗的時間,可能等疫苗準備好的時候,病毒可能已經迅速蔓延開了。[8]如果發展中國家對于流感的研究、監測以及迅速鑒定和批準疫苗、藥物和診斷試劑的能力獲得提高,生產商將研發出來的疫苗、藥物和診斷試劑投入生產前需要等待的時間也會相應變短,這等于是提高了生產能力。
第三,該框架采用了成本收益調控的思路,保證發達國家生產商的利益。截至2017年,全球排名前十的疫苗巨頭都位于發達國家及地區,占據全球市場份額92.2%[9]。因此,對于發展生產能力而言,首要的任務還是要保證發達國家及地區的生產商的利益;只有生產商的收益高于成本,能夠獲得利潤,并且利潤高于沒有該框架的情況,生產商才可能積極地參與該框架并且擴大生產,使可分配的疫苗、診斷試劑、藥品等利益增加。具體而言,當采取的措施有以下兩種:
第一種是科學界定“義務”并且適當維護其利益。其一,在前述的《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第6.14條“可持續和創新性籌資機制”規定中,雖然生產商應當向世界衛生組織繳納伙伴關系費用,但是“企業將根據自身的性質和能力,在透明和公平的基礎上分攤費用”,同時,該條之6.14.2還提到“考慮到所有會員國和PIP生物材料接受者希望根據自己的能力逐步以資金或實物方式為PIP利益共享系統作貢獻”,其中的“PIP生物材料接受者”就包括生產商,世界衛生組織已經考慮到了生產商“根據自己的能力”和“逐步”的要求,對于義務進行了合理限定。其二,在第6.13條“技術轉讓”中的6.13.4亦提到,接受PIP生物材料的流感疫苗生產商在發放非專屬性、免使用費許可證時,可以“遵從任何現有許可證發放限制條件,并根據互相商定的條件”,這也是對于生產商利益的維護。其三,在SMTA2協議第4條“接受者的義務”中,針對疫苗或者抗病毒藥物生產商,協議列出了六種義務,生產商只需要選擇其中兩種承諾即可,避免了給生產商施加過重的負擔。其四,如果將針對全球流感監測和反應系統內部實驗室的SMTA1協議與針對生產商等外部實體的SMTA2協議對比來看,還可以發現,《大流行性流感框架》對于生產商的知識產權予以了保護。具體的表現為,在SMTA1協議中,明確規定“提供方和接收方都不應謀求獲取與材料有關的任何知識產權”,對于這些具有特殊地位的研究實體,協議的價值取向明顯是側重于公眾健康價值,而不是保護知識產權,于是才采納了立法過程中發展中國家排除知識產權保護的意見。而在SMTA2協議中,對于外部的生產商,沒有不得謀求知識產權的表述,而是規定了可選擇承諾的轉讓技術的義務。由此可見,SMTA2協議是保護生產商的知識產權的,只是以技術轉讓的形式予以限制。
第二種是提供公共物品。其一,根據SMTA2協議向生產商提供由會員國(主要是發展中國家)分享的病毒菌株樣本,并且向其提供相關的基因序列數據和分析結果。獲得病毒菌株樣本,是研發疫苗、藥物等產品,從而進入市場的前提。世界衛生組織通過《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第五部分“共享H5N1病毒及其他可能引起人間大流行的流感病毒的大流行性流感防范系統”,從會員國獲得分享的病毒菌株樣本等PIP生物材料,會員國一旦提供,也視為同意了兩個SMTA協議,即同意世衛組織將該生物材料向內部實驗室和外部實體轉讓。然后,世衛組織與外部生產商簽訂STMA2協議,向其分享生物材料供其研究和生產疫苗等產品,同時也使其承擔合同義務。其二,在《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第六部分“大流行性流感防范利益共享系統”之第6.3條“提供大流行性流感候選疫苗”規定中提到,應當將PIP候選病毒疫苗提供給流感疫苗生產商,且不得有任何偏向。所謂候選疫苗,即世界衛生組織推薦作為疫苗使用的流感病毒,或者可用于開發疫苗的其他材料。世衛組織提供候選疫苗,將降低生產商的篩選成本,從而彌補其在傾斜性的利益分配機制中承擔其他義務所增加的成本。
三、結語
為了保護利益分配機制的弱者一端,利益分配機制應當是實質平等的,對于不同的情況差別對待,總體而言應當向弱者傾斜。而由于總體資源不足,在差別對待時,應當采用風險與需求導向,來確定分配的優先次序。通過上述措施,充分落實全球團結原則“平等”與“共同擔責”要素。
全球團結難以落實的問題的根源在于資源生產能力的不足,因此,在利益分配機制的強者一端,由于生產者仍然是“共同擔責”的主力,要適當地保障生產者的利益,促進其擴大生產,輔之以技術轉讓、擴大生產主體、減少行政阻力等措施,保證和發展資源生產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