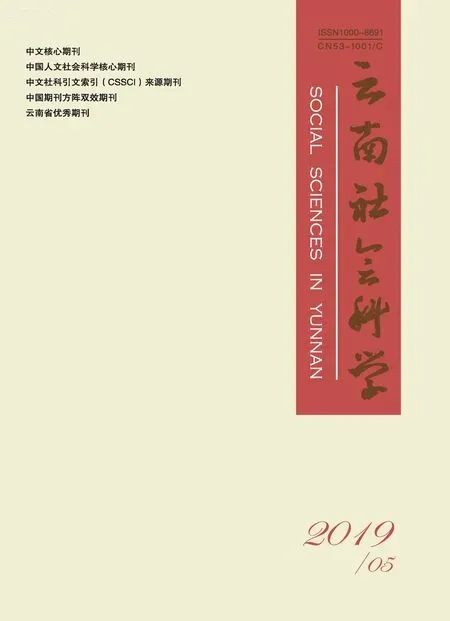《民法典物權編(草案)》中的“正常經營買受人規則”
紀海龍 張玉濤
相較于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以下簡稱《物權法》),《民法典物權編(草案)》(二次審議稿)(以下簡稱《草案》)對動產抵押制度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造。首先是將物權法第188條和第189條合并,不再單獨規定浮動抵押的登記對抗,而是將其整合至一般動產抵押的登記對抗制度中。由此,草案在立法上明確了浮動抵押只是動產抵押的一種特殊形態。相較于一般動產抵押,所謂浮動抵押的特殊性只是在于其也覆蓋未來取得的財產。即,針對物權法下浮動抵押究竟是英式浮動抵押還是美式浮動抵押的爭論,①所謂英式浮動抵押,是指在抵押財產“結晶”之前,抵押權并不具有優先效力,其不能對抗結晶前在相同抵押標的上設立的其他擔保權(例如登記的動產抵押權),從而導致的結果是一般動產抵押優先于浮動抵押。而美式浮動抵押,準確說并不應將之稱為“浮動”抵押,因為在該制度中擔保物并非是“浮動”的,而是“確定”的;只是擔保物也包括未來的財產。一旦擔保人未來獲得了當初約定的擔保物,則擔保權自動附著于擔保物之上;并且如果在擔保人獲得擔保物之前擔保權人就已經對擔保權進行了登記,那么擔保物權可以溯及到當初登記時具備優先效力。對此參見龍俊:《動產抵押對抗規則研究》,《法學家》2016年第3期。將物權法下的浮動抵押理解為上述英式浮動抵押的觀點,參見曹士兵:《中國擔保制度與擔保方法》,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7年,第309頁。《草案》明確選擇了美式浮動抵押。與將浮動抵押明確為一種特殊的動產抵押相配合,《草案》將物權法第189條第2款中針對浮動抵押設置的“正常經營買受人規則”②物權法第189條第2款規定:“依照本法第一百八十一條規定抵押的,不得對抗正常經營活動中已支付合理價款并取得抵押財產的買受人。”而物權法第181條規定的便是浮動抵押。,擴大到了所有動產抵押領域。《草案》第195條規定:“以動產抵押的,不得對抗正常經營活動中已支付合理價款并取得抵押財產的買受人。”
對于正常經營買受人規則被擴大到所有動產抵押領域,學界存在完全不同的觀點。有學者對此完全持否定態度:“在抵押權的制度邏輯上,草案第195條若不以‘浮動抵押’為本,將構成草案第197條所確立的抵押權追及效力制度的體系違反,不能作為草案創新動產擔保物權的制度規范,應刪除其規定而恢復《物權法》第189條(浮動抵押權的對抗力)第2款的表達。”①鄒海林:《論〈民法典各分編(草案)〉“擔保物權”的制度完善——以〈民法典各分編(草案)〉第一編物權為分析對象》,《比較法研究》2019年第2期。而同時,亦有學者表示出對該條文的認可。如高圣平教授指出,草案第195條將“正常經營買受人規則”上升為動產抵押權效力的一般規則,從而明確了動產抵押權和動產抵押物取得人之間的權利順位規則,值得贊同。②參見高圣平:《民法典擔保物權制度修正研究——以〈民法典各分編(草案)〉為分析對象》,《江西社會科學》2018年第10期。
本文首先基于正常經營買受人規則的比較法、利益衡量和法教義學分析,對草案擴大正常經營買受人規則的適用范圍是否妥當予以回應。進而,由于該規則適用范圍被擴大到所有動產抵押領域,實踐中被適用的場合被極大增多,可以想見,在民法典正式通過后,該條必然會面臨持續性的爭議與解釋問題。基于此,本文也會從解釋論角度入手,借鑒比較法的制度經驗,基于既有民法理論和制度,對草案第195條進行法律解釋操作,以助益正常經營買受人規則未來在動產抵押領域中的法律適用。
一、草案第195條“正常經營買受人規則”的制度價值
從相關立法參與者撰寫的文獻可知,《物權法》第189條第2款規定的正常經營買受人規則,乃是立法者綜合考量浮動抵押特性的產物。具言之,由于浮動抵押的財產包括現在的和將來的財產,因此在浮動抵押期間,抵押財產始終處于持續變動的不特定狀態。為了保障抵押人得以維持正常的商業經營活動,法律例外地賦予抵押人以自由處分抵押物的權利。③物權法第191條第2款規定:“抵押期間,抵押人未經抵押權人同意,不得轉讓抵押財產。”據此,物權法以“限制抵押物轉讓”為原則,而浮動抵押中“抵押人有權自由轉讓抵押物”的制度設計顯然即是一種“例外”。既然抵押人對于財產的處分構成有權處分,那么就沒有理由要求買受人在交易前對該動產之上是否存在其他已登記的權利進行查詢核實。換言之,法律給予浮動抵押財產買受人以必要的保護,是保障浮動抵押人正常經營的必要手段,且有助于維護交易安全和秩序,降低交易成本,以適應現代商業之需要。④參見胡康生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釋義》,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414-415頁;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民法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條文說明、立法理由及相關規定》,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346-347頁。學者們在分析“正常經營買受人規則”的制度價值時,亦普遍立足于浮動抵押本身的特性,以前述依據加以說明。⑤參見程嘯:《擔保物權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351頁;梅夏英、高圣平:《物權法教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364-365頁。
可見,對于《物權法》第189條第2款規定的正常經營買受人規則,無論立法者還是學者,均普遍將該規則與浮動抵押視為不可分割,分析前者之制度價值必以后者為根基。我國臺灣地區謝在全教授亦言:“此項營業常規處分制度,系針對浮動擔保權之特征而設,故企業固定資產擔保權無適用余地。”⑥謝在全:《浮動資產擔保權之建立——以臺灣地區“企業資產擔保法草案”為中心》,《交大法學》2017年第4期。而草案第195條則與此不同,將正常經營買受人規則與浮動抵押制度分割開來,將該規則的適用范圍擴展至整個動產抵押領域。從而,首先在制度價值層面便應對此提供合理的解釋和論證。
(一)效率價值: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經濟效率
比較法上,《美國統一商法典》(以下簡稱“UCC”)第9-320條、《歐洲共同框架參考草案》(以下簡稱“DCFR”)第IX-6:102條和聯合國《貿易法委員會擔保交易示范法》(以下簡稱“示范法”)第34條雖然表述方式不同,但均在實質上確立了“正常經營活動中的買受人免受擔保物權約束”的規則。并且,也均未將該規則與浮動抵押制度捆綁在一起。換言之,在上述規則體的起草者看來,于整個動產擔保領域內,均有給予正常經營買受人以優先保護的必要性。而該必要性最為直接的體現,就是其有助于降低市場交易的成本,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
根據DCFR第IX-6:102(2)(a)項,只要交易行為發生在轉讓人的正常經營活動中(the transferor acts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its business),買受人即可被推定為善意,并因此而免受標的物之上所附著的擔保權的約束。關于設置該規則的意義,DCFR起草者著重強調了其對于促進交易便捷所起到的積極作用。“如果當事人無法再信任轉讓人對貨物的占有,且還必須調查這些財產之上是否存在登記的擔保權和保留所有權交易,那么這必然構成對通常商業的巨大障礙。①Christian von Bar and Eric Clive ed., Principles, Definitions and Model Rules of European Private Law, Draft Common Framework Reference, Full Edition, Volume 6, Munich: sellier. european law publishers GmbH, 2009, pp.5604-5605.”與之類似,《示范法》第34條第4項亦有“正常經營活動中的買受人取得不附帶擔保權之財產”的規定。②“A buyer of a tangible encumbered asset sold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the seller’s business acquires its rights free of the security right.” See UNCITRAL Model Law on Secured Transactions 34(4).同樣地,《貿易法委員會擔保交易立法指南》(下文簡稱《立法指南》)在解釋該條之立法目的時,亦重點強調了交易效率的考量因素。具言之,如果法律不賦予買受人以對抗擔保權人的優先效力,那么買受人不得不在購買這些有形資產之前調查其上的求償權,而這一情形將會造成相當可觀的交易成本,而且會極大地妨礙正常經營過程的交易。③See UNCITRAL, UNCITRAL Legislative Guide on Secured Transaction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07, p. 202.此外,在美國法上,UCC第9-320條(a)款之規定,④“a buyer in ordinary course of business……takes free of a security interest created by the buyer’s seller,even if the security interest is perfected and the buyer knows of its existence.” See UCC 9-320(a).亦被學者視為降低交易成本的重要手段。⑤See William H. Lawrence, William H. Henning and R. Wilson Freyermuth, Understanding Secured Transactions (Third Edition), Newark, NJ: LexisNexis, 2004, pp. 253-254.
綜上,“正常經營買受人規則”本身所具有的效率價值,已為當前世界范圍內的示范私法規則體所明確肯定。比較法上,該規則在整個動產擔保領域內皆有適用空間。《草案》第195條之規定修改了物權法第189條第2款,將“正常經營買受人規則”推向了一個更為廣闊的制度轄域,顯有與世界立法潮流接軌之勢。該規則的貫徹實施,使得在交易構成出賣人正常經營活動時,買受人不必耗費精力查詢標的物上是否存在權利負擔。此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經濟效率。可見,正常經營買受人規則所具有的效率價值與浮動抵押制度并無邏輯上的必然聯系。《草案》第195條使得前者有效擺脫了后者的約束,將導致該規則促進交易的功能得以在更廣闊的空間中充分發揮。⑥值得一提的是,在草案頒布之前,便有國內學者以交易效率為核心依據,主張一般動產抵押物的買受人也應類推適用物權法第189條第2款的規則。參見龍俊:《動產抵押對抗規則研究》。
(二)公平價值:符合各方預期
“正常經營買受人規則”下的法律關系,主要涉及三方主體,即抵押權人、抵押人(出賣人)和買受人。對于《草案》第195條如何尊重和平衡這三方當事人的利益,須作進一步的分析。
1.對于買受人:保障其完整權益
“正常經營買受人規則”的核心意旨在于保護從相關經營者處購買動產的買受人。⑦See William H. Lawrence, William H. Henning and R. Wilson Freyermuth, Understanding Secured Transactions (Third Edition), p. 253.據此,買受人不必耗費過多的審核成本,僅基于其購買行為隸屬于作為出賣人的正常經營活動,便能夠獲得不附帶任何擔保權的動產標的物,從而保護其作為市場交易主體的合理預期。相較于《物權法》第189條第2款,《草案》第195條進一步加強了對買受人的保護:在限制條件(“正常經營活動中已支付合理價款并取得抵押財產”)維持不變的基礎上,買受人就動產所享有的優先效力進一步增強,不僅優先于浮動抵押權,也可以優先于附著于該動產之上的所有動產抵押權。
2.對于抵押人:促進其商業經營
《草案》加強對買受人利益的保護,同時也意味著對出賣人商業交易活動的激勵促進。正如《立法指南》所指出的,如果不賦予買受人免受擔保權約束的權利,那么因交易成本的提高,“設保人在其正常經營過程中出售庫存品的能力將大受限制”①UNCITRAL, UNCITRAL Legislative Guide on Secured Transactions, p. 202.。
3.對于抵押權人:符合其商業預期
首先,作為抵押權人,其在與抵押人簽訂抵押合同之時,便應已明知抵押人乃從事特定經營行為的經營者身份,其對于買受人從作為從事特定經營行為之經營者的抵押人處取得動產這一未來事實具有心理預期,即在此存在“默許”處分的因素。正如《立法指南》所述,正常經營買受人規則的起始邏輯在于,其基于商業實踐合理推定了這樣一種情況,即有擔保債權人將會授權擔保人不附帶擔保權出售資產。②See UNCITRAL, UNCITRAL Legislative Guide on Secured Transactions, p. 202.其次,當抵押人兼為債務人之時,給予買受人以優先保護,可促進抵押人經營活動的開展,在客觀上有助于增強債務人的償債能力,繼而使其有能力如期向債權人清償債務。最后,如果抵押權人并非具有上述推定之心理預期,其也可以通過其他途徑予以救濟,例如可在簽訂抵押合同時,約定未經抵押權人同意抵押人不得轉讓抵押財產,一旦抵押人違約,抵押權人可以主張違約責任。
綜上所述,《草案》第195條較為合理地實現了各方當事人利益的平衡,總體上符合各方當事人的預期,貫徹了法的公平價值。
(三)法教義學角度:該規則是動產善意取得制度的必然邏輯延伸
《物權法》第106條規定了物權善意取得制度。據此條,善意取得所有權的要件之一是處分人無權處分。所謂處分人無權處分,包括兩種情形。一是處分人以所有權人身份轉讓動產,但其實他并非所有權人,只是受讓人善意信賴其為所有權人;二是受讓人雖知悉處分人非為所有權人,但善意信賴處分人的處分獲得了所有權人的同意。③德國法下的善意取得制度中,《德國民法典》第932條處理的便是第一種情形,即受讓人善意信賴動產屬于處分人所有;而《德國商法典》第366條第1款則是處理的第二種情形,即受讓人善意信賴非屬于所有權人的處分人享有處分權限。例如寄售商店出售二手貨,買受人明知該二手貨并非寄售商店所有,但可以合理信賴所有權人同意了寄售商店出售該二手貨。此后一種情形,即為對處分權限的信賴。
在物上存在負擔(例如動產抵押權)的場合,也存在善意受讓人的保護問題。與上述善意取得所有權的兩種情形相似,在物上存在負擔的場合,也存在兩種不同的受讓人善意。第一種是受讓人善意信賴標的物上不存在負擔,從而隨著其取得標的物之所有權,物上的負擔也同時消滅。理論上,無論受讓人是從有權處分人處取得所有權,亦或是從無權處分人處善意取得所有權,只要受讓人善意信賴標的物上不存在負擔,其均可無負擔地取得標的物所有權。在中國法下,《物權法》第108條明文規定,在受讓人從無權處分人處善意取得動產所有權的場合,④之所以認為物權法第108條只是規定了善意取得所有權場合的無負擔取得,而并不覆蓋有權處分所有權場合的無負擔取得,是因為該條明文規定的適用前提是“善意受讓人取得動產”,即善意取得所有權。且此善意受讓人中的“善意”指向的只是處分人是否享有處分權,而非標的物上是否存在負擔,因為該條但書明確規定了善意受讓人在受讓時知道或應知物上負擔的情形排除此條適用;如善意受讓人中的“善意”也指向標的物上是否存在負擔,那么在其知道或應知物上負擔的場合(即惡意),該但書就可被轉化為善意受讓人惡意的情形除外,此顯屬邏輯矛盾。如其善意信賴標的物上不存在負擔,則動產上的負擔消滅。但對于受讓人自有權處分人處取得所有權的場合,受讓人善意信賴標的物上不存在負擔的,如銀行在甲之鋼材上設定動產抵押權但未登記,甲出讓該鋼材于乙,乙善意不知銀行之抵押權,則應適用《物權法》第188條(動產抵押未經登記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以實現受讓人無負擔取得的效果。⑤德國法下,《德國民法典》第936條處理的便是動產上存在負擔情形受讓人的無負擔取得。該條并不區分受讓人是自所有人處正常取得所有權亦或自非所有人處善意取得所有權,一體規定受讓人善意相信物上無負擔的,隨著受讓人取得該動產所有權,其上的負擔亦消滅。參見Schwab/Prütting,Sachenrecht,30.Auflage,VerlagC.H.Beck,2002,S.216,Rn.439.第二種是受讓人雖然對于物上存在第三人權利并非善意,但可善意信賴該第三人同意所有權人可以無負擔地處分該物。此即為對處分權限的信賴。正常經營買受人規則所處理的案型即屬此類。例如銀行在甲之鋼材上設定動產抵押權且登記,甲出讓該鋼材于乙,由于銀行之抵押權已登記,所以可以認定乙應知該抵押權的存在,但如果甲作為鋼材貿易商以出賣鋼材為業,則乙可以合理信賴銀行同意甲無負擔地轉讓鋼材所有權。即便銀行并未在協議中對此作出同意,法律也推定銀行作出了此等同意。
從比較法角度看,雖然中國法下的正常經營買受人規則本質上來源于美國UCC第9-320條,但其實德國法下亦存在極其類似的規則。《德國商法典》(以下簡稱“德商”)第366條第2款規定:“物上負擔有第三人權利的,在[受讓人的]善意指向出讓人或出質人享有以無保留該等[第三人]權利的方式處分該物的權限時,《民法典》中有利于自無權利人處取得權利之人的規定,亦適用之。”例如,在某動產上存在用益權(德國法下的一種用益物權),①對于此例,在德國法下,尚需假定用益權人出于某種原因將該動產交予所有權人占有,因為按照德民第936條第3款,如標的物被享有權利的第三人(此例中即用益權人)所占有的,受讓人無法基于德民936條(以及德商366條)無負擔地取得標的物。所有權人出讓該動產所有權給受讓人,受讓人雖然知道該動產上存在用益權,但善意信賴用益權人允許所有權人無負擔地轉讓該物的,則《德國民法典》(以下簡稱“德民”)中關于善意取得的規定(此處指德民第936條)適用于此情形,法律后果便是受讓人取得不負擔用益權的完整所有權。雖然在德國法下,由于德國不存在不轉移占有的動產擔保物權(例如中國法下的動產抵押權),從而德商第366條第2款的適用范圍極其有限。②對此可參見Oetker/Maultzsch, 6.Aufl. 2019, HGB§366 Rn.48-50.但假如德國存在不轉移占有的動產抵押權,那么基于德商第366條第2款,便能得出與正常經營買受人規則基本相同的效果。③參見Moritz Brinkmann, Kreditsicherheiten an beweglichen Sachen und Forderungen, Mohr Siebeck, 2011, S.403.該作者認為德商第366條與美國UCC第9-320(a)條具有類似功能。
二、草案中“正常經營買受人規則”的適用要件
可以預見,在正常經營買受人規則的適用范圍從浮動抵押擴展至所有動產抵押后,未來適用該規則的案件數量將會極大增多。但國內學界對于正常經營買受人規則尚未給予足夠關注,對于該規則的具體構成要件的研究并不多見。下文便對此規則的構成要件進行具體解析。
(一)“正常經營活動”
對“正常經營活動”的概念界定是準確理解和適用“正常經營買受人規則”的前提。對于何為正常經營活動,中國《物權法》及草案均未有規定。首先應當明確的是,就經營主體而言,經營者必須依法具有從事相關商業活動的經營資格;且本條規則僅適用于動產抵押物之“出賣人”的正常經營活動情形,即此條中的正常經營活動只是指買賣行為屬于出賣人的正常經營活動,而非指向買受人。④對此的詳細分析可參見董學立:《論“正常經營活動中”的買受人規則》,《法學論壇》2010年第4期。就此而言,買受人即便是消費者,即其并不從事經營活動的,也可適用該規則。其次,就經營財產范圍而言,交易標的物應為出賣人通常銷售的動產,即出賣人應當是從事銷售此類貨物之人(in the business of selling goods of that kind)。假如出賣人是生產電視機的廠商,則其出賣電視機,便構成正常經營活動,但如果其出賣生產電視機的生產線或設備,那么此就不屬于正常經營活動。⑤參見龍俊:《動產抵押對抗規則研究》;董學立:《論“正常經營活動中”的買受人規則》。似乎將出賣設備也一概納入該規則適用范圍的觀點,參見胡康生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釋義》,第415頁。再者,就交易方式而言,經營者出售動產抵押物的行為,必須符合其自身或其所在行業的通常或習慣性做法(usual or customary practices)。⑥See UCC1-201(b)(9).例如,如果出賣人通常只將某類財產賣給零售商,而此次出售則是賣給批發商,⑦See UNCITRAL, UNCITRAL Legislative Guide on Secured Transactions, p.202.那么該行為就不屬于“正常經營活動”。
此外,關于正常經營活動的范圍是否應局限于買賣活動,學界存在一定爭議。有學者認為,正常經營買受人規則的一個重要目的在于保障抵押人的正常經營活動,從而維持生產經營所需的、所有對抵押財產的處分行為都應該能夠自由進行。因此,包括租賃、買賣、設定擔保等在內的經營性行為,都應當屬于“正常經營活動”。⑧參見鐘維:《民法典編纂背景下我國浮動抵押制度的釋評與完善》,《廣東社會科學》2018年第4期;木拉提、李軍:《域外法律制度對完善我國浮動抵押制度的啟示》,《社會科學家》2018年第3期。筆者認為此種觀點值得商榷。
從解釋論的視角而言,《物權法》第189條及草案第195條均將不受抵押權追及之主體規定為“買受人”,顯然法條在文義上僅適用于買賣活動。從而將正常經營買受人規則擴大至租賃、設定擔保等,于法無據。那么,在立法論層面是否應擴大該規則的適用范圍,或在法律漏洞填補層面是否應類推該條規定將之擴大到租賃或設定擔保等情形呢?本文認為對此應區別對待。本文否認將該條無限制地類推到租賃或設定擔保等情形,但認可在滿足特定條件下,本條規則可被類推適用到租賃情形。
本條所謂正常經營活動,乃是指擔保人(出賣人)為從事出賣相關貨物之人,且如上文所述,本條規則本質上為一種特殊的善意取得規則(即保護受讓人對出讓人具有無負擔處分權限的善意信賴)。而在擔保人將抵押動產出租給承租人的場合,涉及的是承租人的信賴保護問題。對于抵押權和租賃權的優先順位問題,現行《物權法》以及《草案》都進行了處理。《物權法》第190條后句規定“抵押權設立后抵押財產出租的,該租賃關系不得對抗已登記的抵押權”。雖然《草案》第196條(對應《物權法》第190條)將此句刪除,但并非意味著草案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立場。對于抵押權設定在先租賃在后的場合,草案實質上是適用草案第194條,即未經登記的抵押權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包括善意的承租人)。反對解釋草案第194條,便意味著已經登記的抵押權,原則上可以對抗任何第三人(包括承租人),因為抵押權已經登記的場合,對于抵押權的存在承租人應構成惡意。但在草案第195條的正常經營買受人規則中,即便買受人就知悉抵押權的存在而言構成惡意,其也由于作為出賣人的擔保人是從事出賣此種貨物之經營主體,從而買受人可以善意信賴出讓人享有無負擔出讓擔保標的的權限,并因此受到保護。將此原理準用到租賃上便意味著,即便擔保人將抵押動產出租給承租人,即便該抵押已經登記從而承租人就知悉抵押權的存在而言構成惡意,但如果擔保人以出租該等動產為業的,承租人也可信賴出租人自擔保權人處獲得了無負擔地出租該動產的權限,從而可基于對《草案》第195條正常經營買受人規則的類推,使得擔保權人的擔保權不得對抗善意承租人的租賃權。比較法上,美國UCC第9-321(c)條對此進行了明文規定,即正常經營活動中的承租人可對抗在先的動產擔保權,即便其知悉該動產擔保權的存在。
而對于擔保人在同一動產上再行設定擔保則有所不同。對此應依照擔保權優先順位規則對多個擔保權進行排序(即適用《草案》第205-207條),而不應類推正常經營買受人規則。其原因在于,正常經營買受人規則下,其實是在擔保人為以出售某類貨物為業的商人時,法律推定擔保權人同意擔保人無負擔地出售該等貨物,買受人對此推定同意的合理信賴應受到保護。但在同一動產上存在多個競爭擔保權時,即便是擔保人是以提供擔保為業的,也很難想象在先的擔保權人通常都會愿意放棄其擔保權的優先順位。從而在擔保人就同一動產再行向第三人提供擔保的情形,原則上不得類推適用正常經營買受人規則來給后續的擔保人提供額外保護,而是應對此情形適用擔保權順位規則。
(二)“已支付合理價款”
在商業實踐中,判斷買受人所支付的價款是否合理殊為不易。基于法條表達的抽象性,有學者嘗試將物權法第189條第2款中的“合理”概念進一步細化,主張對于合理價款的界定應以接近市場價格為準,如果支付的對價在常人看來與市場價格相距甚遠,就不能構成合理價格。①董學立:《浮動抵押的財產變動與效力限制》,《法學研究》2010年第1期。筆者建議,對此應借鑒現行民事法律規范中已有的類似規定,為合理價格的判定提供稍具操作性的判斷方案。就此而言,《物權法司法解釋(一)》第19條與《合同法司法解釋(二)》第19條之規定,②《物權法司法解釋(一)》第19條處理的是,如何對物權法第106條(所有權善意取得)第1款第2項所稱“合理的價格”進行認定判斷的問題。《合同法司法解釋(二)》第19條處理的是,如何對合同法第74條(債權人的撤銷權)規定的“明顯不合理的低價”進行判斷的問題,并進一步延伸出“明顯不合理的高價”之判斷標準。尤其值得關注。這兩個條文均涉及對市場交易中轉讓價款之合理性的判斷,對草案195條中“合理價格”的解釋,應與其保持必要的協調。尤其是鑒于正常經營買受人規則本質上是一種特殊的善意取得,《物權法司法解釋(一)》第19條關于物權法第106條(善意取得制度)中所規定之“合理價格”的解釋,當然具有更大的參考意義。具體而言,在判斷買受人支付價款是否合理時,應當根據轉讓標的物的性質、數量以及付款方式等具體情況,參考轉讓交易時交易地市場價格以及交易習慣等因素綜合認定。
就此要件而言,物權法第189條及草案第195條中正常經營買受人規則的適用,均要求合理價款“已”被支付。物權法在此要求價款已經被支付,此做法不知源于何處。在比較法上,在正常經營買受人規則中要求買受人已經支付價款,無法找到先例。無論美國UCC、示范法還是DCFR甚至我國臺灣地區“企業資產擔保法草案”中,均無此要求。且在此要求買受人已經支付價款,也與一般善意取得制度中的合理對價要件不相協調,因為物權法第106條規定的一般善意取得,并不要求該合理對價已被支付。或許有人會說,要求合理價款已被支付,使得擔保人(很可能同時為債務人)的一般責任財產并未因出賣擔保物而減損,從而有利于擔保權人即債權人利益的保障。但不應忽視的是,即便價款尚未支付完畢,擔保人針對受讓人的價款請求權也屬于擔保人一般責任財產的范圍,也可被強制執行。從而該責任財產不減損的立場,亦很難立足。總之,在立法論上,建議取消該價款應已經被支付的要求,只要擔保人和受讓人之間約定了合理的價款即可。
(三)“取得抵押財產”
本條亦要求買受人“取得抵押財產”。如上所述,在大陸法系的教義學框架內,正常經營買受人規則乃是一種特殊的善意取得,即無負擔地取得所有權。從而從規范目的來看,此處取得抵押財產應是指取得抵押財產的所有權。①參見李莉:《浮動抵押權人優先受償范圍限制規則研究》,《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14年第3期。依動產物權變動之規定,經由轉讓繼受取得動產所有權,要么經由交付,要么經由交付的替代(《物權法》第23條以下:簡易交付、占有改定和指示交付)。受讓人基于實際交付取得抵押財產的所有權,自然滿足“取得抵押財產”這個要件。有疑問的是,通過簡易交付、占有改定或指示交付的方式受讓所有權,是否滿足此條中“取得抵押財產”的要件。
基于善意以剔除負擔的方式取得所有權,德國法要求在簡易交付的情形下,受讓人必須是事先從出讓人處而非從其他第三人處取得占有(德民第936條第1款第2句、德商第366條第2款);在占有改定的情形,要求受讓人應基于出讓人的交付而取得占有,即取得人方面排他性的占有(德民936條第1款第3句、德商第366條第2款);②須注意的是,德民936條第1款第3句在文義上只是要求“基于出讓取得占有”,而非基于出讓人的交付取得占有,但學者結合德民第933條進行體系解釋,認為德民第936條第1款第3句中的取得占有,應主要指基于出讓人的交付取得的占有。參見 MünchKomm/Oechsler, BGB, 6.Aufl., 2013,§936, Rn.8; Staudinger/Wiegand, BGB, 2011,§936, Rn.14.在指示交付的情形,受讓人應自出讓人或第三人取得占有。即,對于基于善意以剔除負擔的方式取得所有權,德國法要求受讓人取得的占有具有特定的“強度”。那么,對于中國法語境下的正常經營買受人規則,是否要求受讓人取得的占有應具有特定的“強度”呢?例如,銀行設定動產抵押于甲生產的電視機,并將該抵押登記,甲將電視機轉讓于乙,并約定雖然所有權轉讓于乙,但先替乙保管一段時間(占有改定),此時在德國法下(為舉例方便在此忽略德國法并無動產抵押這個制度),乙雖然在甲乙進行約定時就取得了電視機所有權,但此時電視機上尚存在物上負擔,只有在乙基于甲的交付取得占有(即甲完全放棄占有)時,電視機上的負擔才被去除。德國法下占有改定情形的善意取得,要求受讓人須取得物的直接占有,此要求有利于銀行控制擔保風險。如果銀行去真實查看出賣人的存貨,那么只要存貨依舊由出賣人占有,那么銀行就可放心其擔保權尚存在,即此要求防止銀行的擔保權被秘密地去除掉。那么在中國法下是否應設此要求呢?筆者認為在《草案》第195條規定的正常經營活動要件下,無此必要。理由在于,正常經營買受人規則下,由于出賣人是以出賣特定貨物為業之商人,從而買受人的信賴保護這個砝碼會更重,即買受人處的更強的保護交易安全需求,壓倒了對銀行的保護。③對于一般動產善意取得情形,受讓人是否可基于占有改定善意取得所有權,此存在爭議。本文認為,一般而言,為了保護所有權人的所有權不被秘密地善意取得,應當否定占有改定方式的善意取得。但在受讓人處的交易安全需求極高的場合,如受讓人通過拍賣或者向具有經營資格的經營者購得動產的,應允許占有改定或指示交付方式的善意取得。對此較詳細的討論可參見紀海龍:《解構動產公示、公信原則》,《中外法學》2014年第3期。
在UCC的框架下,正常經營買受人規則的適用也不要求受讓人實際占有動產。根據UCC第1-201(b)(9)項之規定,即便買受人未取得實際占有,但其如果“就該貨物享有向出賣人主張交付的權利(has a right to recover the goods from the seller)”,那么也可構成正常經營買受人。此外在美國的司法實踐中,對于正常交易買受人規則的適用,甚至都不要求買受人取得所有權,只要買賣標的特定化后,買受人針對出賣人享有交付該標的的請求權即可。①參見宰絲雨:《美國動產擔保交易制度與判例——基于美國〈統一商法典〉第九編動產擔保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111-115頁。對于中國物權法第189條第2款持此解釋的觀點,參見董學立:《浮動抵押的財產變動與效力限制》。對此做法筆者不敢茍同。原因是,該規則本質上是為了保護受讓人對出賣人享有無負擔出讓標的物的信賴,而在標的物雖已被特定化,但受讓人尚未(基于動產所有權移轉的規則)取得標的物所有權之時,尚談不上受讓人無負擔地取得所有權了。
綜上而言,所謂買受人“取得抵押財產”,是指買受人基于動產所有權移轉的規則取得動產抵押物之所有權。
(四)買受人“善意”
就正常經營買受人規則,《物權法》第189條第2款和《草案》第195條在給予買受人特殊保護的同時,均未規定“善意”的要件。依其規定,即便買受人在受讓動產標的物時非為“善意”,甚至明知附著該物上的抵押權的存在,且抵押權確實完成登記,也不妨礙買受人順利取得無權利負擔的動產所有權。但正如上文所述,正常經營買受人規則本質上是一種特殊的善意取得,其當然應要求買受人的善意。只是在此受讓人的善意,并非是指其不知且不應知轉讓標的物上擔保權的存在,而是指其不知且不應知擔保權人不允許擔保人無負擔地轉讓擔保物。
此亦是比較法上的普遍做法。我國臺灣地區“企業資產擔保法草案”、UCC、示范法和DCFR中的“正常經營買受人規則”,均不要求買受人善意不知標的物上負擔擔保權。換言之,買受人明知標的物上負擔擔保權,也不影響其取得無負擔的動產所有權。但在這些規則體下,如果買受人知悉該交易侵犯了擔保權人基于擔保契約所享有之權利,則買受人構成惡意,其取得的動產所有權便附有負擔。具體而言,受讓人在正常經營買受人規則下的惡意,需要同時滿足三個層層遞進的條件。首先,買受人需要知悉該動產標的物上存在擔保權;其次,買受人須知悉出賣人與擔保權人之間存在“就該動產限制或禁止出售”之約定;最后,買受人還應知悉,其與出賣人之間的買賣行為確會侵犯擔保權人基于前述擔保協議所享有的權利。換言之,在UCC和示范法對“正常經營買受人規則”的制度安排中,買受人的主觀要素被規定為構成要件之一。
而與之相比,《物權法》第189條第2款和《草案》第195條對買受人主觀狀態全無限制。學界普遍認為如此有失妥當。就如何在《物權法》中引入買受人的主觀要件,國內學界有觀點主張借鑒UCC第1-201(b)(9)之規定,將“買受人明知購買行為會損及抵押權”這一惡意因素,直接涵攝到“正常經營”的概念之中。②參見李莉:《浮動抵押權人優先受償范圍限制規則研究》。具言之,如果在先的抵押合同中約定,抵押人不得對抵押財產再進行處分,且買受人明知抵押合同中存在此種條款,即買受人明知抵押人的出售行為會違反其與抵押權人的約定,那么買受人的行為便不屬于“正常經營”的范疇,買受人因此而不得適用“正常經營買受人規則”受到優先性保護。③參見鐘維:《民法典編纂背景下我國浮動抵押制度的釋評與完善》。但此種觀點并不可取。此觀點將善意要素解釋到正常經營活動的概念范疇之中,不僅混淆了主觀與客觀要件的概念差異,而且將“對買受人的限制(善意)”與“對出賣人的要求(正常經營活動)”混為一談,頗為牽強。
從立法論的角度看,如果立法者在《草案》第195條中增加但書規定,如增加“但買受人明知該交易侵犯了抵押權人基于抵押合同所享有的權利除外”④示范法即采類似的制度設計模式。See UNCITRAL Model Law on Secured Transactions 34(4).,當然最為理想。如果民法典正式通過時《草案》第195條未發生變化,則也可以通過法學方法論的操作對此漏洞加以填補。由于《草案》第195條的文義中,并未體現任何買受人善意要件,而在買受人明知該交易侵犯了抵押權人基于抵押合同所享有之權利的情形,又理應對買受人的權利進行限制(即買受人取得的所有權上附有抵押權),此時法條中不存在此限制便構成法律漏洞。此法律漏洞可基于目的性限縮加以填補。本條的法律意旨,乃是為了保護買受人對抵押權人允許(以出賣此等標的為業的)抵押人無負擔地出賣此等標的的信賴。從而在買受人不具有此等信賴時,應限縮《草案》第195條的文義,不允許買受人無負擔地取得此等標的的所有權。
當然,如果存在擔保人(即出賣人)和買受人惡意串通損害被擔保人利益的情形,亦可直接適用民法總則第154條,認定擔保人和買受人之間的合同無效。但需要注意的是,此時合同無效導致的法律效果是買受人壓根不能取得擔保物的所有權,而非能夠取得擔保物所有權只是其上附有擔保負擔。①雖然此處不排除《民法總則》第156條部分無效規則的適用,但相較于惡意串通制度(或一般的悖俗無效制度)+部分無效制度,對《草案》第195條進行目的性限縮顯然來得更加直接。
三、多個買受人競存時的對抗效力
《草案》第195條之規定,所設想的法律關系構造基本是圍繞著“抵押權人-抵押人(出賣人)-買受人”這樣的案型。不過,有可能適用“正常經營買受人”規則的情形不止于此,還可能會出現數個買受人競存的情形,對此需作進一步分析。
(一)抵押物“一物二賣”
多個買受人競存的一種典型情形是,抵押人利用其占有之動產抵押物進行“一物二賣”。顯然,僅有一個買受人可能滿足“正常經營活動中已支付合理價款并取得抵押財產”的完整要件,此時其可以依據草案195條之規定,取得無抵押負擔的動產所有權。而其他買受人,無論是否善意、無論是否已支付合理價款,均無法取得動產所有權,只得向出賣人主張違約責任。
(二)抵押物多重轉讓
多個買受人競存的另一種情形是:抵押人將動產轉讓給買受人之后,買受人再將其轉讓給第二買受人,此時便存在第二買受人能否擺脫抵押權負擔的疑問。
1.第一買受人符合“正常經營買受人規則”的情形
對此需首先判定,第一買受人是否滿足《草案》195條之要件。如若滿足,那么其自可獲得無抵押權負擔的所有權。此時,第一買受人為動產的所有權人,擁有該動產之處分權,自可進行自由轉讓。而第二買受人就其從有權處分人處所受讓的動產,也應享有無抵押負擔的所有權。美國法下此被稱為“庇護原則(shelter principle)”②所謂庇護原則,是指一項權利的權利人可將該權利以相同的形式和相同的屬性出讓給受讓人,例如該權利在出讓人處不受制于某項擔保權的,那么在受讓人處也不受制于該項擔保權。UCC第2-401(1)項即體現了此原則。參見Steven L. Sepinuckeds, Practice under Article 9 of the UCC,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2008, p.652.又可參見UNCITRAL,UNCITRAL Model Law on Secured Transactions Guide to Enactment, Vienna: UnitedNations, 2017, p.94.,此做法亦在比較法上存在成例。③《示范法》第34條第7項規定:“如果有形設保資產的買受人或其他受讓人取得其權利不附帶擔保權,則任何后繼買受人或其他受讓人取得其權利也不附帶該擔保權。”我國臺灣地區“企業資產擔保法草案”第28條規定:“企業浮動資產擔保權之目標為有形資產者,處分人依營業常規有償處分該擔保目標時,該處分之相對人取得之權利,脫離企業資產擔保權之負擔……前項之相對人取得之權利脫離企業資產擔保權之負擔時,自相對人取得該資產之權利者,亦脫離該擔保權之負擔。”
2.第二買受人符合“正常經營買受人規則”的情形
爭議較大的問題是,若第一買受人受讓的是一個有抵押負擔的動產,隨后,第一買受人在其正常經營過程中將該動產轉讓給了第二買受人,且后者完全符合正常經營買受人規則的要件,那么第二買受人能否依據該規則取得無抵押負擔的動產所有權?④第二買受人之外的其余間接買受人,如第三、第四買受人等,皆屬同理。對此,比較法上的處理模式有所不同,大體有兩種做法。
第一種做法是,第二買受人就其所取得的動產,僅可不受第一買受人所享擔保權之約束(如果第一買受人就該動產享有擔保權的話),而不能擺脫之前其余擔保權的負擔。美國UCC采此做法。依其規定,其對“正常經營買受人規則”施加的一個重要限制即為,買受人能夠脫離的權利負擔僅限于由買受人的出賣人所設定的擔保權(a security interest created by the buyer's seller)。⑤See UCC9-320(a).依此,第二買受人不能基于該規則脫離他的出賣人(即第一買受人)的出賣人所設定的負擔。關于為何作此規定,有學者指出,或許立法者的意圖在于:在當事人雙方均無過失的時候,最終的損失應由在交易中與有過錯的當事人有密切聯系的一方承擔。①董學立:《美國動產擔保交易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166頁。對于該規則的具體適用,UCC的正式評注舉了一個頗為清楚的案例加以說明:“以制造家用電器為業的某制造商擁有一臺制造設備,該設備受到貸款人已公示的擔保物權之約束。其后,該制造商將該設備出賣給一個以買賣舊設備為業的經銷商。買受人向該經銷商購買了該設備。根據UCC9-320(a)款之規定,即使買受人具有正常交易中的買受人身份,其也不能免受貸款人之擔保物權的約束,因為這一擔保物權并非由其出賣人——經銷商創設,而是由制造商創設。②Official Comments (3) to UCC 9-320(a).”該例中的交易鏈條為:貸款人-家電制造商-舊設備經銷商-買受人。舊設備經銷商為第一買受人,其從家電制造商購買生產設備(而非家電),不滿足正常經營買受人規則,從而其取得的家電上負擔貸款人的擔保權。而該例中的買受人作為第二買受人,其自就設備經銷商購買設備,滿足正常經營買受人規則。但按照UCC的規則,由于第二買受人只能擺脫其直接前手出賣人所設定的擔保權,從而在該例中第二買受人取得的所有權上負擔貸款人的擔保權。
另一種做法是,如果第二買受人符合“正常交易買受人規則”的一般適用要件,那么,其所取得的資產將不附帶任何擔保權。該種規定主要是出于交易效率的考慮,被部分國家采納。③See UNCITRAL, UNCITRAL Legislative Guide on Secured Transactions, p.207.但立法指南在此并未指出究竟有哪些國家采納了此做法。DCFR第IX:-6-102(2)(b)項亦明確采此做法。
面對比較法的不同做法,應如何解釋草案第195條之規定呢?筆者贊同上述第二種做法。理由有三:第一,從《草案》195條的規范文義上來看,“正常經營活動中已支付合理價款并取得抵押財產的買受人”并不局限于第一買受人。換言之,基于文義解釋的視角,無論是第一買受人還是間接買受人,只要其符合上述第195條規則的適用要件,均應賦予其對抗任何在先抵押權的優先效力。第二,采取第二種做法是貫徹交易效率的應有之義。正如《示范法》立法指南所述:“如果要求在正常經營過程中購買擔保資產的人(包括消費者)向上追溯所有權鏈條,將對商業造成妨礙”④See UNCITRAL, UNCITRAL Legislative Guide on SecuredTransactions, p.207.。第三,鑒于正常經營買受人規則本質上是一種特殊的善意取得,在最終買受人滿足正常經營買受人規則的要件時,沒有理由不保護最終買受人的善意。
四、結 語
正常經營買受人規則與浮動抵押制度并不具有邏輯上的必然聯系。《民法典物權編(草案)》第195條突破了“正常經營買受人規則”的原有制度框架,將該規則的適用范圍由浮動抵押拓展至整個動產抵押領域,實乃一大進步。正常經營買受人規則本質上是一種特殊的善意取得規則,即法律推定抵押權人允許抵押人在其正常經營活動中無負擔地出賣動產抵押標的,買受人可以善意信賴抵押權人該等同意的存在,從而法律保護買受人的此種信賴,規定即便已經登記的動產抵押權也不得對抗出賣人之正常經營活動中的買受人。本文基于此思路,對正常經營買受人規則的具體構成要件和法律后果,進行了探討和細化,并對《草案》第195條中存在的法律漏洞提出了漏洞填補的建議,以求該條規則在接下來的民法典立法進程以及未來民法典具體適用中得到進一步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