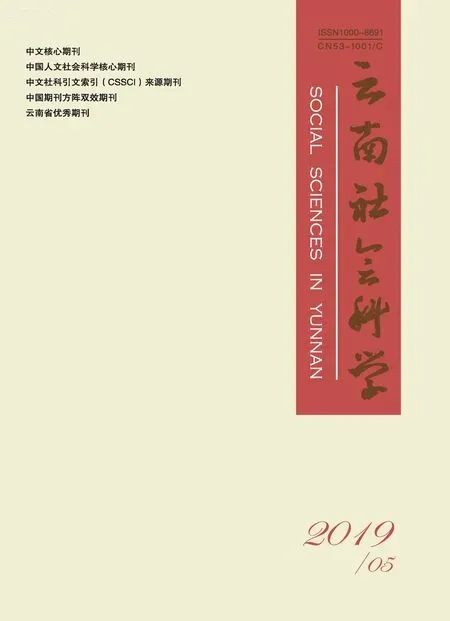互動視角下進城農民工的階段性回流
——基于中國東部三大經濟區的調查
孫 健 田 明
一、問題的提出
中國農民工的流動形態具有一個特殊規律:它是一個既有流出又有回流的過程。①蔡昉:《勞動力遷移的兩個過程及其制度障礙》,《社會學研究》2001年第4期。進城農民工常年在城市生活與工作,受過城市現代文明的熏陶,具備一定的技能、眼界和社會關系,這些農民工若能夠經常性地回到農村,將會為留守人員與農村社會帶來城市的文化與資源,對改善留守人員生活質量與推動農村社會發展產生重要作用。然而,從當前形勢來看,一方面隨著城鎮化步伐加快與戶籍制度逐步改革,居住證、積分落戶等政策在多地得到執行,有效降低了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障礙,多數農民工通過持續務工以實現城市定居;②傅晨、李飛武:《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背景下戶籍制度創新探索——廣東“農民工積分入戶”研究》,《廣東社會科學》2014年第3期。另一方面基于對城鄉間收入、公共服務等差距的考量,那些短期內無法明確定居地的農民工也不想離開城市,普遍成為了在城市中“流而不返”的滯留型農民工。③鐘水映、李春香:《鄉城人口流動的理論解釋:農村人口退出視角——托達羅模型的再修正》,《人口研究》2015年第6期。美國社會學家莫頓在其發展的結構功能主義中提及,一件事情或一種現象產生的客觀后果分為兩種,能夠被人們想到和認識到的稱為“顯功能”,而未被人們想到和認識到的稱為“隱功能”④[美]羅伯特·莫頓:《社會理論和社會結構》,唐少杰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5年,第90-95頁。。在城鄉融合發展背景下,良好的公共政策逐步為農民工提供多元的發展機會,實際上給予了他們外出務工中的更多出路,但是很多進城農民工卻基于現實利益選擇滯留城市。這種務工狀態不僅使得公共政策未能徹底地實現人口調控初衷,還觸發了城鄉融合發展中的“雙刃劍”問題,一方面難以充分實現農業轉移人口的城市遷移,另一方面無法為鄉村積聚穩定的人力資源,最終造成人口分居城鄉兩地的農民工家庭產生了情感交流匱乏、凝聚力不足與結構功能失衡等問題。其中,眾多農村留守家庭嚴重缺乏勞動力,不僅面臨著巨大的經濟風險,留守人員由于缺少足夠的情感關懷,還對家庭中的外出人員有著情感需求。①崔巖:《流動人口心理層面的社會融入和身份認同問題研究》,《社會學研究》2012年第5期。對于那些徘徊在城市中的農民工,他們大多缺乏與城市居民同等的社會福利與公共服務待遇,在繁重辛苦的勞動中缺失情感關懷及來自家庭與親人的情感支持,同樣也會產生情感問題。②楊菊華:《中國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研究》,《中國社會科學》2015年第2期。
在家庭成員空間分離的研究中,普遍強調互動是解決情感問題的有效方式,其中以面對面的互動最為典型。③黃穎、段成榮:《論農村留守妻子家庭中的互動儀式》,《廣東社會科學》2012年第4期。對于城鄉相隔的農村人口,因受到各種條件的限制,面對面互動顯得極其困難。農村留守人員大多為老弱病殘、婦女兒童等特殊群體,他們很少有足夠的能力與機會進城,因此,多數進城農民工家庭成員的互動發生于外出人員從城到鄉的階段性回流過程中。農民工階段性回流雖說是短暫的,但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農村人口的情感需求,并緩解了留守家庭的勞動力缺失等現實壓力,對增強農村家庭凝聚力與促進農村社會穩定起到積極作用。諸多學者對農民工回流問題進行了研究,但目前對農民工階段性回流的研究還不夠充分,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過于關注農民工回流的行為表現,缺少時間維度的引入,缺乏對農民工在一定周期內回流效果的深入探索;第二,過多秉持農民工回流的結果導向,對農民工務工過程中的動因探索尚不全面,缺乏對農民工家庭、務工層面中顯性與隱性因素的綜合探討。事實上,進城農民工在退出農村、進入城市、社會融入等環節中均存在程度問題。④張桂敏、吳湘玲:《文化墮距理論視角下農民工市民化“困境”與“出路”的分析》,《云南社會科學》2018年第3期。因此,本文基于中國東部三大經濟區的調查,在加入時間維度后,著重考察進城農民工以年為周期、階段性回到流出地的程度效果。通過對進城農民工階段性回流的系統探究,一方面能夠提供回流人員的動態信息,從而推動農民工回流的便利性,更好地解決留守人員情感缺失等問題;另一方面能夠揭示農民工滯留城市的機理,從而增加農民工互動機會以改善勞動情緒,更好地改善農民工在城市的精神狀態。
二、理論假設與樣本情況
(一)理論假設
德國社會學家西美爾被認為是歐洲第一位互動理論家,他認為“社會”是人們在互動中協調、沖突、吸引、排斥等關系的統一體,既不能將社會理解為獨立于個體的單純客觀過程,也不能把社會歸結為個人行動。在他看來,社會包括“形式”與“內容”兩個方面,現實社會是由無數的事件、行動和互動構成的,為了處理社會中的復雜內容,人們總是通過各種形式來整理內容。在具體的互動中,形式是“人們交往所展現出來的具體樣式”,內容是“致使人與其他人交往的動力、目的和想法”⑤[德]蓋奧爾格·西美爾:《社會學——關于社會化形式的研究》,林榮遠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年,第4-8頁。。西美爾的互動思想集中在互動的形式、類型、群體、距離等要點上,在延續這些思想的基礎上,互動理論呈現出百家爭鳴的局面,相繼發展出符號互動論、角色理論、擬劇理論、社會交換論、常人方法論等,但至今仍未形成統一的理論范式。⑥[美]喬納森·特納:《社會學理論的結構》,邱澤奇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1年,第5-10頁。綜合來看,這些互動理論多是從微觀層面研究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特別是從行為、心理、符號、意義及角色等不同角度,研究互動的條件、方式、作用、情境和過程,主要觀點集中在以下5個方面:第一,強調互動與角色的緊密性,認為人在社會關系中的地位規定了人的互動行為,互動是一個角色創造的過程;第二,強調互動中存在著各種關系,包括統治與服從、沖突與凝聚、合作與競爭等;第三,關注距離在互動關系中的作用,認為互動形式和互動意義是互動中的個體與其他個體或事物之間相對距離的函數;第四,明確了互動的表現維度,包括向度、深度、廣度、頻度四個維度;第五,明確了互動的表現類型,包括個體間互動與群體間互動、社交情境互動與工作情境互動、情感性互動與工具性互動等。
基于農民工階段性回流是滿足農民工家庭成員情感需求的基本方式,本文將進城農民工階段性回流認定為外出農民工與家庭留守人員的互動行為,即在互動視角下探討進城農民工從城到鄉的階段性回流效果,并通過分析農民工的家庭角色、家庭關系、外出距離、心理認同等互動要素,為農民工階段性回流的研究提供更多解釋工具。在互動視角下,進城農民工階段性回流的向度與廣度集中在流出地的農村家庭,而回流的差異化效果主要在于一定周期內的頻度與深度,其表現規律能夠呈現出外出農民工與留守人員進行互動的基本形式,還能夠揭示出外出農民工促成家庭整合的實質內容。因此,進城農民工在務工周期內持有的階段性回流策略,是在各種經濟與非經濟利益比較后做出的理性選擇,應當強調角色、關系、距離、認同等互動要素的重要影響。基于此,本文提出三個互動假設:
假設1:角色假設。農民工作為農村家庭的組成人員,家庭角色需要是引起農民工與家庭成員互動的關鍵因素,進城農民工的家庭角色越重要則階段性回流越強烈。
假設2:關系假設。農村家庭成員之間具有合作屬性,家庭成員間的親密關系對成員互動起到牽引作用,進城農民工的家庭關系越親密則階段性回流越強烈。
假設3:距離假設。空間距離制約農民工家庭成員互動的條件,近距離務工的進城農民工的階段性回流相對強烈,在務工情境中內心伴隨性的身份認同具有一定影響。
(二)樣本情況
本文數據采用2017年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課題組在中國東部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經濟區中,對在該區域城市進行務工的外來農民工所做的問卷調查。調查地的選取采用分層抽樣方法,抽取的9個城市分別為:上海、無錫、江陰、深圳、江門、鶴山、北京、廊坊、霸州。在實地調查中,選定的農民工年齡不小于16周歲且從兩方面進行了限制:一是在當前務工地連續工作時間不少于3年;二是當前務工地為本市外(區)縣及以上地區。通過這些限制,排除了進城農民工在務工地轉換中發生階段性回流的效果偏差。經過篩選,調查共回收問卷2031份,有效問卷1836份,在剔除農民工家庭中沒有留守人員的樣本后,共得到分析樣本1023個。本文數據分析的具體方法有:一、雙向計分法,應用在農民工家庭關系量表的得分計算上;①農民工家庭關系量表借鑒家庭功能評定量表(FAD)設計,量表共計12道題目,用以測量農民工家庭成員間親密關系的程度。“雙向計分法”,即正向題選項按照1到4賦值計分,負向題選項按照4到1賦值計分,農民工家庭關系的得分范圍為12分到48分,其含義為得分越高則家庭成員間關系越加親密。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應用在農民工特征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結果分析上。
據調查數據顯示,中國三大經濟區中的進城農民工以男性為主,占比為62.3%,已婚人群為51.9%,即保持婚姻狀態的農民工居多;平均年齡為32.81歲,即群體偏向80后出生的中青年,“新生代”成為了三大經濟區中進城農民工的主力軍;受教育程度平均為11.55年,即群體偏向高中及同等學歷。在家庭情況上,進城農民工家庭的人口數平均為4.08人,僅父母留守的比例為56.4%;家庭2016年收入平均為94212.16元,家庭承包土地面積平均為5.42畝;進城農民工的家庭關系平均為36.50分,處在得分范圍的中高水平,表明進城農民工家庭的成員間親密關系整體偏好。在務工情況上,進城農民工當前務工的月收入平均為5160.72元,年收入平均為61928.64元;外出務工時長平均為9.58年;跨省務工人員的比例高達58.3%;在務工情境中的身份認同上,持有“老家人”觀念的比例為60.4%,即秉持農村固有身份認知的農民工占據多數。在階段性回流效果上,進城農民工的回流頻度平均一年3.52次,回流深度平均一年19.27天,每年不到20天的回流時長呈現出明顯薄弱性。經核算,每年的回流深度系數僅為0.055,相對回流頻度來說很不理想,也不容樂觀。
據統計,進城農民工發生階段性回流的原因占比較高的是過節團聚(為71.3%)和探望親人(為63.4%),這表明節日效應和親情關系等要素對農民工的階段性回流有拉動作用。這一結果與互動視角下的相關假設異曲同工,即符號、角色、關系等互動要素深刻影響著外出農民工的階段性回流效果。其他原因還有如“回家帶孩子”“回家辦社保”“回家看病”“掃墓與上墳”等事件性緣由,這些具體結果則補充說明了現階段農村家庭中各種繁瑣性事務對于進城農民工階段性回流的一些特定影響。
三、變量選取與實證分析
(一)因變量
本文將進城農民工的階段性回流作為因變量,在互動視角下選取了兩個測量維度,選擇“近3年平均每年回家的次數”為指標來測量回流頻度,選擇“近3年平均每年回家的天數”為指標來測量回流深度。基于調查中已對農民工樣本進行了務工時空的條件限制,因而選擇“回家次數”與“回家天數”能夠相對準確地測量出進城農民工在一定周期內的階段性回流效果,且在操作意義上符合互動理論的基本內涵。最后,將回流頻度與回流深度作為聯合因變量來衡量進城農民工的階段性回流效果。
(二)自變量
本文將影響進城農民工階段性回流的特征因素歸結為3個方面:①進城農民工個體特征,選取了農民工的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婚姻狀況4個變量。②進城農民工家庭特征,選取了農民工家庭的成員留守情況、去年年收入、承包土地面積,以及農民工家庭成員間的親密關系共4個變量。③進城農民工務工特征,選取了農民工的務工距離、務工時長、務工月收入,以及在務工中內心伴隨性的身份認同共4個變量。
(三)實證結果
本文運用統計軟件spss20.0對調查數據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在數據處理上,首先對一些自變量進行虛擬變量處理,而后將所有自變量引入模型,最后在模型中加入“回流頻度”因變量進行逐步回歸得到模型A,加入“回流深度”因變量進行逐步回歸得到模型B。從模型解釋力來看,回歸模型的預測率分別為36.42%與38.53%,具有一定解釋力。回歸模型得到的是影響回流頻度與回流深度的雙重結果,能夠支撐進城農民工階段性回流效果的綜合分析。
1.進城農民工個體特征的影響
就進城農民工個體特征對階段性回流的影響而言,呈現出以下幾種特征:其一,年齡的影響具有分散性。相對30-39歲群體,16-29歲群體與回流效果呈正相關,表明年齡偏小的農民工階段性回流較為強烈,年輕農民工擁有相對偏高的人力資本條件,他們能夠在務工中爭取更多機會來實現頻繁且充分的階段性回流。此外,50-59歲群體與回流深度呈正相關,表明年齡偏大的農民工階段性回流天數偏多,即他們在務工中存在長期回家的滯留狀態,原因在于接近于務工生命末端的農民工難以實現城市穩定就業,他們通常采取的是一種臨時性進城的務工模式。然而,60歲以上群體與回流效果呈負相關,原因在于60歲以上的農民工基本完成了務工生命周期,他們多是由于務工隨遷、身體條件等因素而長期滯留城市。其二,受教育程度的影響存在明顯分野。相對高中及同等學歷群體,小學及以下群體與回流頻度呈負相關,初中群體與回流效果呈負相關,表明教育層次偏低的農民工的回流效果偏弱,這與他們大多從事體力勞動的職業密切相關,即在高強度勞動中無法獲取空閑時間,也難以積攢余力來進行回流。相反的是,大專與本科及以上群體與回流頻度呈正相關,表明受教育水平較高的農民工階段性回流的次數偏多,因為他們一般從事相對正式且穩定的職業,在外務工期間易于獲得休息時間以實現較為頻繁的回流。
2.進城農民工家庭特征的影響
就進城農民工家庭特征對階段性回流的影響而言,呈現出以下幾種特征:其一,家庭成員留守情況對回流頻度的影響微弱,但對回流深度的影響較為強烈。相對其他留守情況,僅配偶留守群體與回流深度呈負相關,表明在僅有配偶留守的情況下,核心家庭中另一方的回流天數偏低,意味著他們需要長期在外務工以實現核心家庭的盡快轉移。然而,配偶及子女留守群體與回流效果呈正相關,即當核心家庭出現多成員留守時,外出人員在核心家庭中的角色變得越加重要,外出農民工的回流效果也將變得越加強烈,即他們需要更加充分的回流互動以保障更多家庭成員,尤其是留守子女的情感需要。此外,僅父母留守的群體與回流深度呈正相關,即原生家庭中的父母留守會提升外出子女的回家天數,留守父母由于年老需要身體照顧及心理慰藉,導致承擔照顧角色的外出子女需要長期回家進行陪伴。因此,以上結果驗證了互動視角下的“角色假設”。其二,家庭上一年收入的影響存在分野。相對60001-90000元群體而言,處于偏低的30001-60000元群體與回流深度呈負相關,這表明收入相對偏低的家庭中外出農民工的回流天數偏少,意味著他們需要更多時間在外務工以擺脫家庭的相對貧困。然而,相對偏高的12萬元以上群體與回流頻度呈正相關,表明擁有較多資本的家庭能夠有效支撐外出農民工的經常性回流,以保障家庭成員更為深層次的情感需求。其三,家庭關系與回流頻度呈正相關,但對回流深度無明顯影響。該結果表明進城農民工家庭關系越親密則農民工回流的次數越多,意味著他們在家庭親密關系的牽引下,會盡可能地保障回流次數以穩定家庭成員間的互動,部分驗證了互動視角下的“關系假設”。
3.進城農民工務工特征的影響
就進城農民工務工特征對階段性回流的影響而言,呈現出以下幾種特征:其一,外出務工距離的影響具有明顯分野。相對本省外市務工群體,本市外(區)縣務工群體與回流效果均為正相關,表明本市務工對農民工的階段性回流具有強力支撐作用,無論是從經濟成本還是從行動便捷性上來看,近距離的回流互動都是外出農民工易于接受的。與之相反,外省務工群體與回流頻度呈負相關,表明遠距離務工制約著農民工階段性回流的次數,客觀呈現出跨省務工農民工從務工城市回到農村老家的匱乏性與艱難性,且從回流成本上來看,跨省回流的經濟與心理消耗是多數農民工及其家庭難以承擔的。因此,以上結果驗證了互動視角下的“距離假設”。其二,身份認同的影響比較集中。相對持有“既是本地人也是老家人”觀念的群體,具有明確的“老家人”身份認同群體與回流效果均為正相關,表明沉淀于多數農民工內心深處的農民固有身份,對階段性回流具有強烈的牽引作用。此外,持“既非本地人也非老家人”觀念的群體與回流頻度呈負相關,表明“雙非認同”群體的回流次數相對偏少,他們由于缺失身份認同而通常面臨無處扎根的尷尬境地,在迷茫的務工情境中難以主動爭取更多的回流機會。
四、進城農民工階段性回流的現實境況和政策支持
(一)階段性回流的耦合困局和策略分化
1.進城農民工處于家庭責任與務工約束的耦合困局
進城農民工依靠固有稟賦在發達地區持續務工,但他們從城到鄉的階段性回流效果,即每年的回流頻度平均不到4次、回流深度平均不到20天,卻遠遠滿足不了外出農民工與家庭留守成員的情感需求。進城農民工階段性回流存在薄弱性,主要源于農民工個體、家庭與務工特征的復合影響,形成了制約階段性回流的現實困局,其表現為家庭責任與務工約束的情境耦合。基于以上研究結果,筆者認為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其一,角色耦合。核心家庭中配偶及子女留守、原生家庭中父母留守,意味著外出農民工需要承擔家庭角色所賦予的責任,促使他們表現出相對積極的回流效果。然而,外出農民工在承擔親屬角色的同時,還要在務工行動中承擔著核心的勞動角色。進城農民工家庭年收入平均為94212元,其中農民工個人務工年收入平均為61928元,占到整個家庭收入的65.7%,即他們不僅要通過外出務工以保障個人生存,整個家庭還要依賴他們維持生活。因此,雖然外出農民工基于家庭責任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回流,但是務工壓力卻限制他們做出充分的回流。其二,能力耦合。進城農民工大多在農村家庭中充當主力,這源于他們在家庭中處于相對優勢的個人能力及其相對應的家庭責任,因而年輕的、具備較高受教育層次的農民工能夠爭取一定回流機會,以盡可能地滿足農村家庭成員的情感需求。然而,多數農民工在城市中的個人能力卻相對處于弱勢,過多的階段性回流會導致務工中的職業風險、資源斷裂及收入減少,且極易讓他們失去狹窄的城市就業空間。總體來看,進城農民工外出務工的首要目標在于降低家庭生存風險、保障家庭發展能力,他們更多傾向于選擇竭力維護家庭長期穩定的階段性回流方案,因而其在有限的城市務工周期內能夠實現的多是低水平的回流互動。
2.進城農民工的階段性回流策略出現多維分化
進城農民工雖然處于階段性回流的耦合困局,但是他們在務工過程中的諸多特征,例如受教育程度、家庭情況、務工距離等仍對回流效果起著明顯作用。隨著社會的發展與進步,農民工群體在變得更加理性的同時,通常會基于不同情境來選擇滿足個人及家庭成員情感需要的方案,因而在務工中持有的階段性回流策略出現了多維分化。基于以上研究結果,筆者將其概括為4個方面:其一,農民工代際間的策略分化。年輕一代表現出更加平穩的回流效果,而年老一代走向兩極分化,他們或將長期回到老家或將長期滯留城市。其二,家庭結構間的策略分化。核心家庭中的農民工根據配偶與子女的留守情況而選擇回流策略,多成員留守對階段性回流產生拉動作用,而原生家庭中的農民工更多根據父母留守狀況而選擇相應策略。其三,家庭經濟條件間的策略分化。經濟較差的家庭通常選擇外出持續務工,而經濟條件較好的家庭更加能支持外出人員的頻繁回流。其四,務工情境間的策略分化。近距離務工、具有老家人認同的農民工表現出強烈的回流效果,而遠距離務工、具有“盲向”認同的農民工表現出微弱的回流效果,多是根據經濟與非經濟成本測算而選擇回流策略。總體來看,進城農民工之所以產生以年為周期的階段性回流的策略分化,主要源于他們在城鄉流動中面對不同個人、家庭及務工等情況,會根據多維利益而選擇相應的回流策略,從城到鄉的階段性回流既是一種空間上的歸巢,也是一種家庭角色與固有身份的回歸。
(二)基于“家本位”思維強化政策支持
1.制定農民工法定假日,減少農民工回家障礙。
家庭成員的地理分割,阻礙了家庭成員之間的生活照料與事業互助,家庭成員相距越遠,所能提供的支持力度也就越小。①楊菊華、李路路:《代際互動與家庭凝聚力——東亞國家和地區比較研究》,《社會學研究》2009年第3期。由于家庭成員的長期分離,農民工家庭生活的不完整成為了外出務工人員最大的隱痛和暗傷,而農民工的階段性回流對于解決這一問題有著關鍵作用。中國在1981年出臺了《關于職工探親待遇的規定》以解決職工同親屬長期兩地遠居的探親問題,但這里的職工只包括國家機關、國有企業、事業單位的固定職工,農民工未能包含在內。農民外出務工的確增加了小農家庭的收入,但小農家庭的情感生活被掏空了。因此,政府亟待洞察農民工階段性回流中的情感力量,不僅要保障農民工在勞動中應享有的假期福利,還需要增加農民工進行親情互動的機會。筆者認為應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方面,設定農民工法定假日,盡快保障農民工享有同其他勞動群體一樣的探親福利,并設定農民工法定假日來促進農村人口往來,如除了享受正常法定假日外,每年可另外增加20天假日,其中春節假期不應低于10天;另一方面,減少農民工回家障礙,積極為農民工提供專門的車票補助及特定的探親渠道,其他回家支持項目由用工單位同農民工協調安排。最終,通過提升農民工回家效果以強化農村人口的情感互動程度,從而有效滿足農民工家庭成員的情感需求,維系好農民工家庭的親密關系。
2.促進農民工家庭遷移,支持就地就近務工。
現階段農民工的流動不單依附于傳統“城-鄉”二維模式,而更多表現為一種“農村-務工地-遷移地”的三維模式。農民工在務工地期間,多是與父母、配偶、子女等家庭成員分開,僅在春節等重要節假日才得以團聚。家庭遷移對人口異地分離問題起到了緩解作用。但是對于多數農民工而言,家庭整體遷移難以實現,而且隨遷人員在流入地面臨的就業、住房、教育等問題還會影響農民工家庭的生活質量。尤其對于外出距離較遠的務工,農民工所能獲取的社會資本更為有限,遷移成本與遷移風險也更大。②孔建勛、鄧云斐:《社會資本與遷移距離:對云南跨界民族外出務工者的實證分析》,《云南社會科學》2016年第6期。對此,政府在全面考察農民工群體的流動模式后,要針對不同情況為農民工家庭尋找適合的出路:一方面,要順應城鎮化趨勢,促進農民工舉家遷移。通過考察農民工家庭情況與人員外出務工的內在邏輯,給予農民工更多務工區位的匹配方案,并針對性地提供各種家庭福利保障,從而推動農民工家庭成員的共同隨遷,讓農民工家庭能夠在城市定居下來。另一方面,支持農民工就地就近務工。對于一些偏遠地區,制定相關政策引導農民工就地就近務工,并支持農民工主動回流就業創業,從而實現農民工家庭的進一步整合,最終朝著更切實際的就地就近城鎮化方向發展。
3.關注留守人口情感問題,尊重農民工情感勞動。
中國快速的城鎮化在重視“農轉非”的同時,往往忽略了農村留守人口的大量存在及其非物質層面的各種需求。農民工家庭成員由于長期分離引發了情感需求,外出農民工則通過務工中的階段性回流,來補償農民工家庭成員的情感缺失,其蘊含著農民工逆務工初衷的內在邏輯:一是外出農民工需要履行自身角色,通過回流互動達到對留守成員的照顧與關心;二是外出農民工需要掌握家庭情況,通過回流互動獲得家庭信息與務工支持。然而,很多農民工在務工中存在著人力資本、就業崗位等方面的限制,致使他們無法與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勞動待遇,很難保障階段性回流的充足效果,造成了留守成員缺乏深度關照,農民工缺乏深度支持的雙向困境。因此,在城鄉統籌發展的關鍵時期,政府亟需要解決進城農民工回家探親深度不足的問題:一方面,應持續關注留守人員的情感問題。給予農民工留守家庭成員多方面的親情援助,通過為留守人員提供更多的進城互動機會,加強各種交流媒介建設促進農民工家庭成員間的經常性溝通,以此減輕農民工在城市務工的后顧之憂。另一方面,號召社會各界尊重農民工情感勞動。積極地在城市建設農民工情感互動平臺,暢通一系列滿足農民工情感需求的表達途徑,并對農民工的階段性回流互動提供更多支持路徑,以此增強農民工的精神動力與工作熱情,使他們能夠更加順利地在城市完成務工周期的過渡。
五、小 結
中國“家本位”文化一直占據主導地位,但隨著現代化進程的不斷加快,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口開始涌入城市務工,農村人口因就業等原因遠離農村家庭成為了常態。①朱波、高艷云:《外出務工人員與留守家庭成員聯系緊密程度研究——基于山西省臨縣1200戶農戶的調查數據》,《農業技術經濟》2017年第10期。對于新一代農民工而言,現階段農村的現實狀況依舊無法承載他們多元化的發展需求,同時基于城鄉間存在的差距,他們依然是以農民工的身份,來到離家鄉很遠的城市打拼,將生活的希望寄托于城市務工之路上。然而,很多人在城市中卻難以獲得理想的職業和充足的收入,既無法實現農村家庭的整體遷移,又無法回鄉發展,在持續外出過程中引發了城鄉兩地家庭成員的情感問題,其通過階段性回流來暫時性地慰藉個人及家庭成員的情感需求。在中國三大經濟區中,進城農民工依據各種現實情境來選擇階段性回流策略,在務工周期內的階段性回流主要受到家庭角色、親密關系、相對距離等互動要素的影響,而傳統經濟要素的影響并不明顯。因此,對于進城農民工而言,從城到鄉的階段性回流更多是將個人與家庭、工作與生活的時空進行匯集,是對家庭中個人角色與能力的一種回饋方式,也是對農村家庭實現整合的一種內容投資,其不僅關系到農民工及其家庭成員的各種情感需求,更加關乎到社會發展中城鄉資源與文化的有效銜接。事實上,本文所探討的農民工不僅代表著進入中國核心經濟地區務工的進城農民工,也代表了其他從不發達農村地區到發達城市地區務工的廣大農民工,他們大多經歷過城市務工歷程的多重洗禮,但卻由于各種條件的制約而難以實現充分的回流互動,只能通過減少回流的方式來實現持續務工,以犧牲親情互動的代價來換取整個家庭的美好未來。基于此,在城鄉統籌發展的關鍵時期,政府與社會不僅要為農民工提供更多家庭團聚的機會,更加重要的是要為整個農民工家庭的發展制定長遠的和細致可行的規劃,以促進農民工家庭分居問題得根本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