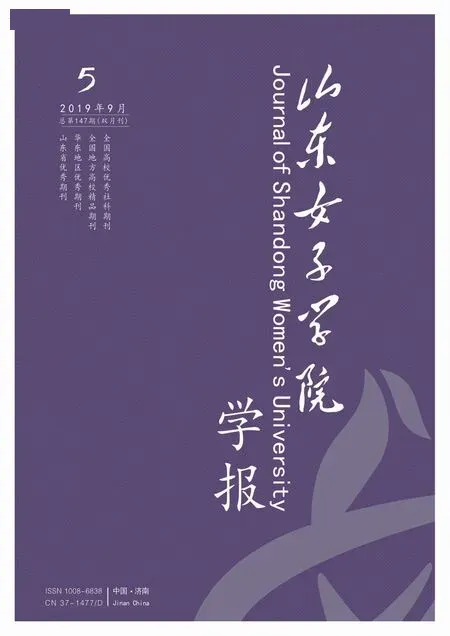重讀經典:布迪厄的《區隔》對社會性別理論批判的啟示
魏 丹
(南昌大學, 江西 南昌 330031)
一、社會性別理論的發展階段
法國結構主義大師布迪厄的場域、慣習與資本等概念是學界分析學術場域、教育場域以及藝術文化場域的重要工具,其著作成為學界被引次數最高的作品之一。研究女性主義和社會性別者往往會提及布迪厄的另一著作《男性統治》,書中指出,現有性別秩序的改變并不靠將女性和男性對立起來,或者如激進女權主義一樣靠極端地仇視男性、反對男性而實現。女性主義同其他哲學理論一樣,其產生需要一定的社會基礎,同時也是人類發展、追求自由平等和全面發展的結果。但從18世紀法國大革命以來,女性主義便和婦女解放運動密不可分。女性主義(feminism)起源于法國,最初翻譯為女權主義,集中體現了女性個人權力斗爭的中心目標。歷史上出現過三次婦女運動浪潮,前兩次浪潮促成了自由主義、激進主義、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四大流派的產生,第三次浪潮則催生了后現代、心理分析、第三世界女性和生態女性主義四大理論分支[1]45-47。
社會性別理論是對性別概念和性別差別的含義進行的哲學分析[2-3],是對資源分配和社會管理中實施社會公正和平等的一個分析框架[4],是對女性所處不平等位置的批判[5]。批判性是社會性別理論的重要特征。在論及后現代女性主義理論時,學者往往會涉及福柯關于身體和懲戒凝視的觀點、德里達書寫語言說和拉康三界說(象征現實、想象現實和現實的現實)等關于主體和話語的論述。布迪厄的《區隔:品味判斷的社會批判》(下文簡稱《區隔》)[6]則被視為社會階層分析利器。隨著20世紀90年代第三世界國家的崛起,女性主義發聲的主體也更加多元化了,傳統的白人中產階層女性的聲音雖依然占據重要地位,如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7],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奧秘》[8],凱特·米利特的《性別政治》[9],但白人中產階級女性已不是唯一發聲主體。
女性主義從其誕生之初就充滿了批評意味,如女性的角色、地位不是天經地義的,而是社會歷史文化影響的結果,因而是可以改變的。除此觀點之外,社會性別理論如何走得更遠?女性的附屬地位主要受制于父權制的影響,父權制背后又蘊含了什么樣的因素與權力邏輯?布迪厄在《區隔》中以慣習、場域、資本等概念構筑的社會空間和社會階層理論指出,應當以更具關系性或結構性的方式研究女性的處境和現有的性別秩序。女性主義分析與批評開始紛紛注重階層、種族、公民權、勞動場域、個體地域來源等因素,如英國學者露絲·里斯特從公民身份、宗教、階層等方面分析了女性群體內部的巨大差異[10];李靜君從性別和地緣的角度切入到工作現場,分析了階層、性別與地緣之間的復雜微妙的權力關系[11]。
二、社會性別理論的二元對立困境
從對大眾傳媒中女性“被觀賞性”形象的批評,到對文學作品中女性意識缺失的批評,再到對現實社會中男女兩性不平等的批判,批判性無疑是社會性別理論的重要特征。但Toril Moi認為,籠統的橫掃一片的批判性觀點的提出并不難,難的是如何進一步剖析這些觀點在哪些具體的社會現實結果上得到了印證[12]。社會性別理論批判的實體和對象是否清晰?社會性別理論是否能夠突破傳統的男性與女性的二元對立?其批判能否走得更遠?
英國的社會學家Janet Wolff稱“只有通過對社會性別隔離、文化生產的社會關系、文本的關系性、社會性別和社會結構等進行系統的分析,女性主義文學批判才能真正找準對象。”[13]布迪厄對文學、語言、美學等領域以文化生產與再生產場域理論,詳細分析與批判了權力結構及其在場域內的再生產邏輯,其《男權統治》更清晰地論述了性別隔離及其權力生產機制,這些理論有助于為社會性別理論明晰批判對象,突破男性與女性的二元對立,為社會性別理論提供更清晰準確的批判方向。
布迪厄的《區隔》一書明確提出了其理論抱負:力圖超越社會科學長期以來的宏觀與微觀、理論與經驗、象征性與物質性等知識模式的二元對立局面,因此他主張研究關系性,注重分析文化和社會權力的再生產。也正是基于這個基礎,布迪厄在其《區隔》中提出,社會理論應當既能夠分析宏觀的社會空間結構,也能夠用于微觀層面的分析。他在《區隔》論著中涉及了食物、衣著、音樂品味、裝飾風格、擇友特點、電影類型以及學生同教師交談的感受等各個細節方面。因此,布迪厄的社會空間與社會階層理論不是帕森斯式的宏大、巨型理論,而是既有社會結構的宏觀分析,又有深入日常平凡世俗的社會生活進行的微觀分析。Toril Moi指出,并非其他社會學家不分析日常生活,但唯有布迪厄揭示了如在餐館中吃魚這樣平常微小的事例同社會領域中的位置之間的復雜、具體、特殊的聯系,并對此進行了細致深入的分析[12]。
因此,布迪厄的《區隔》及其理論對社會性別理論研究的啟示意義在于,首先,社會性別理論研究不能僅僅停留在宏觀社會結構上一般化地論述男性的優勢地位和女性的劣勢地位,或者從生產方式中探究女性地位形成的歷史原因,也就是不能泛泛地談女性是第二性,是社會文化建構的,而需要深入微觀的日常生活中去探究男性和女性的細致差異,同時揭示日常生活經驗中男性和女性的差異與廣泛的社會歷史結構、制度結構之間的關系,即為社會性別理論提供關系性視角。其次,布迪厄的由階層、品味、區隔等形成的社會空間概念為分析男性與女性之間的結構性地位提供了重要分析工具,甚至能夠進一步細化女性群體內部的差異,為社會性別理論研究提供微觀生活視角。再次,布迪厄的理論視域有助于社會性別理論突破傳統的個人/社會、公共/私人領域的二元對立分析,從而將社會經驗層面男性與女性社會地位的差異與社會空間、制度結構與權力的再生產機制相聯系,為社會性別理論批評走得更遠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啟示。
三、階層與品位——社會性別分析的切入點
布迪厄認為,差異(區隔)是無處不在的。然而并不存在社會階層實體,真正存在的是各種差異構成的社會空間,階層在某種意義上只存在于一種現實的虛擬狀態中,它不是已經形成,而是將被建構[14]。
布迪厄對階層的界定有廣義與狹義之分,狹義上的階層僅僅是指諸如年長者、穆斯林或婦女、黑人、巴黎人與外省人等某一類特定的群體;而廣義上的階層則包含了年齡、宗教、種族、性別、居住地等在內的因素,其范圍之廣、包容性之強,幾乎涵蓋了社會系統的每一因素[14]。本文對布迪厄階層理論的分析主要基于在性別這一因素所形構的社會空間中,對男性和女性由于位置不同所形成的男性主導(統治)地位和女性從屬(被統治)地位的對比分析。因此本文的階層概念主要是采用了布迪厄對階層狹義范疇的定義。本文著力于對男性和女性不同社會空間位置的結構和權力關系進行分析。
社會世界的區隔并不建立在社會的真空地帶。社會空間中行動者占據的位置,即不同資本的分配結構,是行動者斗爭的武器[14]。品味與階層緊密聯系,它是指一個階層中實踐活動和商品消費的特定風格。慣習使得某階層中的行動者在選擇交往的人、進行消費或參加實踐活動時按照一種統一的特定的風格行事。比如:工人和廠長在飲食、吃飯方式、運動方式、實踐方式、政治觀念、表達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系統的區別。慣習意味著不同的選擇,是分類的原則,不同的觀念意味著不同的趣味。它將好和壞、正確和錯誤、特別和普通等作了區分,但是這種區分并不是嚴格統一的。可能某一種行為或同一種商品對某些人來講是區分的標志,而在另一些人那里則可能僅僅是作為一種炫耀等。這種不同的社會類別以原則、觀念、趣味、實踐、商品等表達了不同的符號意義,構成了一種真正的語言含義。在每一個社會空間中的不同位置,以及該位置附著的商品、實踐、行為舉止、功能等構成了一個象征體系,形成了一個區隔標志。
區隔是指一些固有的舉止和行為方式的特征,以及區分這些特征的界限。這個特征是聯系性的,需要通過和其他的特征相關聯才能加以界定。區隔的概念是空間概念的基礎,社會空間是指根據行動者或群體所在位置,其所擁有的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所建構的一個領域[14]。
布迪厄關注差異,特別是關注同質中的分歧,其據此形成的階層理論,為社會性別理論提供了很多可借鑒的視角。男性和女性在社會空間中同樣形成不同的品味和位置區隔,在觀念、趣味、商品等不同方面形成不同差異。布迪厄關于階層與品味,通過大量的實證調查收集資料,并在此基礎上構建社會空間中的階層、品味區隔圖景。在社會性別研究中,同樣可以通過同一社會階層的男性和女性的品味、觀念、消費的實證調查構建性別差異下的區隔圖景,以更直觀的方式去了解男性和女性的具體日常微觀生活的細致差異。這一差異與區隔圖景的展示,并不意味著能改變當前女性的弱勢地位,女性突破自身邊緣階層的途徑在于摒棄自身已有的生活旨趣愛好、審美情趣與消費方式,而培養同男性一樣的品味。差異是不可避免的,而差異并不是形成位置的最終原因,其主要取決于慣習的作用和權力的再生產機制。階層和品味為社會性別理論提供的啟示是我們要研究性別與品味或者性別、階層與品味之間的關系,研究這種差異形成的位置構成。區隔理論雖然用于描述社會不同階層在社會空間中形成的不同位置結構,但是其也具有推廣性,可以用于分析社會性別秩序,為社會性別理論提供更深入的理論分析體系。
四、資本的空間架構與象征暴力——社會性別秩序的成因
布迪厄在《區隔》中指出,社會成員依據其所擁有的資本結構和資本總量在社會這一大型的空間坐標場上占據不同的空間位置。不同空間位置上的互動與交往形塑了不同的思想觀念、認知行為、生活方式、性情傾向與審美情趣。即不同的社會階層有不同的品味、愛好旨趣與行為模式。與此同時,這些空間位置之間有社會距離,社會成員作為行動者的距離是以品味和趣味的差異顯現出來的。“如果不能建構出位置空間,你就毫無機會看到你借以觀看事物的立足點。”[14]與此同時,布迪厄建構了一個三維的“社會空間”來安置社會世界中種種分配不均的資本和權力關系,“社會空間基于社會場域中資本的運作、分化與分配構建而成,擁有了資本,就意味著擁有了社會理論與社會權力,不同的行動者和群體為社會空間的不同相對位置所定義。”[14]簡言之,布迪厄認為擁有資本則意味著擁有權力,資本分配的不平等意味著權力的不平等,正是這些不平等形塑了不同的社會行動者在社會空間中的不同位置。
布迪厄在社會空間這一大坐標場上,以資本總量為指標區分垂直的社會階層差異。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的總和構成了資本總量,其中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最為重要。“各階層(class)以及同一階層內的各部分(fraction),從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都最為豐富的階層到兩者都最為貧乏的階層作出劃分。居于最上層的是專業人員(professions),他們擁有高的收入和高的學歷,出身于統治階層(dominant calss)的家庭(專業人員或高級管理人員),能夠享受和消費大量的物質及文化產品。處于中間的是辦公室雇員,他們學歷較低,通常來自于工人階層(working class)或中等階層(middle class)的家庭。在最底端的是各種水平的體力勞動者和農民,他們收入最低,沒有學歷,幾乎都出身于工農階層家庭。”[14]
布迪厄以資本構成結構區分在水平坐標上社會成員的階層差異。比如統治階層內部,藝術生產者和大學教授擁有豐富的文化資本,但其經濟資本較少,是統治階層中的被統治者;而工商業資本家擁有豐富的經濟資本,而文化資本相對較少。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的不平均分配也是統治階層內部分化的主要根源。在此基礎上,布迪厄描繪出一個由“首要對立”與“次要對立”共同建構出的趣味社會階層空間圖[14]。
布迪厄的資本與社會空間理論為現有的性別結構、性別階層分析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在《男權統治》一書中,布迪厄提出男性的統治與女性的附屬地位關系存在于所有的社會空間、次空間中,即存在于私領域的家庭,公領域的學校、勞動力市場以及大眾傳媒、政治空間中。“即使婦女在公共職務中所占比例真的越來越高,留給她們的也總是最低級和最不穩定的位置。有一個事實無疑是婦女在勞動力市場上所處地位不確定的最佳證明,即如果其他情況都一樣的話,她們得到的報酬總是比男人少。雖然她們持有同男性一樣的文憑,得到的職位卻比男人低,尤其是從比例上看,她們受事業和工作不穩定的影響最大,且最容易被打發到兼職工作中去——這尤其會使她們幾乎必然被排除出權力活動和升遷的通道。”[15]150在社會現實中形成了公共空間尤其是生產領域的經濟中男性的絕對統治權;而女性則在諸如家庭、生育等私人空間中擁有著象征性的權力的局面。這是布迪厄對于性別權力秩序的現實刻畫。然而這種社會秩序是如何形成和發揮作用的呢?布迪厄認為,性別區分結構除了體現在性別化或強或弱的學科、職務和職位中之外,還通過女人甚至她們周圍的人在其選擇中使用的三個實踐原則起作用:第一,適合女人的只能屬于家庭職能的延伸部分:教育、護理、服務;第二,女人不能對男人行使權力,即使其他情況都一樣,男人也可能比女人更容易登上權位,而女人只能居于次要的輔助位置;第三,賦予男人操縱技術用具和機器的壟斷權。
這種原則是被統治的女性和統治的男性共同默許的,其以不易覺察的方式產生作用。布迪厄稱這種作用為象征暴力。“更令人奇怪的是,法定的秩序,連同它的統治關系,它的權利和破格優待,它的特權和不公正,除了幾個歷史事件之外,能夠如此輕易地永久延續下去,而最無法忍受的生存條件可能常常以可接受的甚至是自然而然的現象出現。此種服從是我稱之為象征的暴力即溫柔的、受害者本身不易察覺的、看不見的暴力的結果。”[16]J.Morris將這種象征性、持續作用且不易覺察的暴力稱為女性的習得性無助[17],布迪厄稱顛倒的或否定的皮格馬利翁效應持續、過早作用于女性身上,最終形成了幾乎難以覺察的象征暴力。
社會空間中以性別區分的結構生產和再生產的固有模式以象征暴力發揮歷史超驗性作用,成為社會成員共同遵守的準則而被普遍認同。男性在社會結構、生產和再生產活動中得到普遍認可的優先權。另外,男性的優先權還體現為習性固有的模式,這些模式被客觀接受,是所有社會成員認知、行為和思想的模式,因此以歷史超驗性發揮作用。男權統治被視為一種常識的客觀性,女性因此接受和模式化這一客觀性以及由此形成的權力關系,可以說,女性自身在某種程度上參與“制造”了象征暴力[16]46。
社會性別理論認為,女性的性別特征同階層、種族等不同要素融合起來,使得女性問題呈現出復雜且層次多樣的特點。布迪厄的區隔理論為社會性別分析提供了資本及社會空間分析的一整套工具,依據男性及女性的資本及位置能夠構建一個社會性別空間位置區隔圖,以社會現實經驗和更細致入里的方式探索女性地位的狀況及其權力結構。而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結構構成同階層的社會空間位置,形成具有結構同源性的特征,即形成遵循同樣等級序列的差異。因此,運用布迪厄的區隔理論,以資本為標尺既能夠區分男性和女性的分層等級差異,形成高低左右不同的性別秩序,同時也能夠融合種族、宗教等其他因素細化女性群體內部的差異。這些現有的性別秩序及階層差異通過象征暴力以歷史超驗性在全部社會空間中發揮作用。
五、形成社會性別理論新秩序的可能路徑
婦女運動的幾次浪潮歷史性地揭示了男性與女性權力秩序現狀的改變,不應將女性和男性對立起來,或者有激進女權主義一樣以極端仇視男性的態度。事實上,在雄性氣質過度渲染和張揚的西方世界,男性往往也是受害者。正如布迪厄所闡述的,在長期自我貶低、自我否定的社會化作用下,女性習得了服從、克制和失語等消極道德,男性則成為了男權統治表象下的囚徒和隱形的受害者。“男性特權也是一個陷阱,而且它是以長久的壓力和緊張換來的[15]71-73”。
要改變現有的性別秩序,需要從性別秩序生產和再生產的機構機制中去努力。布迪厄認為,性別秩序或者男性統治秩序的再生產活動,主要是由三個機構完成的,這三個機構是家庭、教會和學校。“如果家庭單位是男性統治以最不可辯駁和最顯而易見的方式表現出來的一個地點的話,那么在家庭中起作用的物質和象征力量關系的永久化原則,則基本上處于這個單位之外,存在于諸如教會、學校或國家機構以及它們特有的公開或隱秘的、官方或非官方的政治活動之中。”[15]67同時在考察性別分工再生產的制度因素時,布迪厄認為需要考慮到國家的作用,“國家通過父權制的規定和禁令來認可和加強私人父權制的規定和禁令,公共父權制被納入所有負責管理和調節家庭單位的日常生活的機制中。”[15]168
不僅如此,布迪厄啟示,社會性別理論政治行動需要從社會空間結構和權力的再生產機制去消解男性統治,而消解途徑則需從國家、學校著手。“政治行動只有真正考慮到所有的統治作用,才會在長時期內借助不同的機制或相關的制度所固有的沖突,促進男性統治的逐漸消亡。因為所有的統治作用都是通過(無論在男人身上還是在女人身上)被歸并的結構與重大制度的結構之間的客觀同謀實現的,不僅男性秩序,甚至整個社會秩序都是在這些重大制度中實現和再生產的。”[15]171-172
布迪厄的社會理論既能夠為社會性別理論批判提供清晰的結構方向,同時也能夠搭建宏觀社會層面與微觀生活層面的橋梁,其理論具有較強的滲透性和伸縮性,能夠解釋宏觀問題、中觀問題以及微觀現象:不僅可以解釋男性和女性性別秩序問題,也可以細化女性群體內部的差異。社會性別理論研究可以在布迪厄社會階層與品味理論的啟示下,通過經驗研究構建男性與女性品味區隔圖景。同時,分析象征暴力如何在性別秩序、性別區隔中發揮作用。社會性別理論運動只有從制度性結構著手,分解權力機制生產和再生產的結構作用機制,才能夠消解男性統治。在男性統治秩序下,男性和女性同樣是受害者。因此,當前的社會性別理論批判在借鑒布迪厄理論的基礎上,有可能消解傳統的性別二元對立的局面,走出傳統男性與女性對立或男性與女性無差異的理論歧途,從社會空間結構和社會制度作用方向著手,從國家—權力機制和學校—權力再生產機制等方面去分析。這是布迪厄社會理論的重大啟示意義。布迪厄社會理論為社會性別理論問題提供了重要的范式,值得社會性別理論研究者進一步探索和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