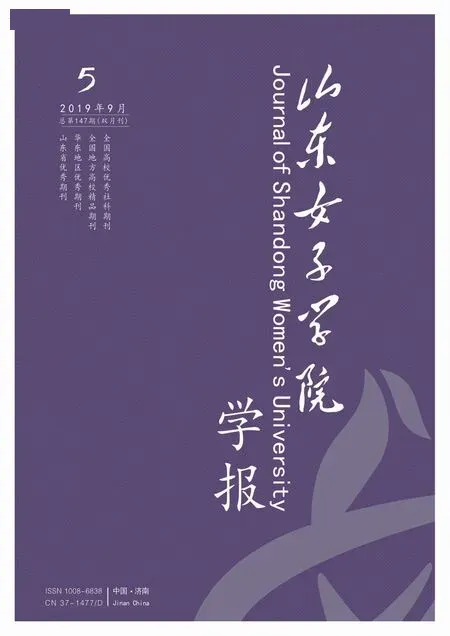性別的單一自覺
——1990年代女性文學話語生產的再考察
張 開
(南京師范大學, 江蘇 南京 210097)
在對女性文學進行世紀末的回眸時,王曉明曾批評女性文學創作不由自主地回避了公共生活,并滋養了“個人”的“物質欲望和官能沖動”[1]。無獨有偶,賀桂梅也把矛頭指向了1990年代單核結構的女性話語,她批評女性文學創作和研究“往往從單一的性別視角考慮問題,而無法從更廣泛的角度面對婦女的社會/文化問題”[2]。
上述論斷能夠代表學者們針對1990年代女性文學達成的某種學術共識,即由于受限于單一的性別話語框架,令女作家在茲念茲的性別議題中實際無法介入廣大女性群體所面對的社會、文化問題,即便“女性文學”能夠在社會公眾論域中迅速擴散、在文化市場中暢通無阻,但最終只能營構女作家精神世界的虛假繁榮,而無法在知識階層以外的讀者群體中產生更廣泛的影響。學者們指認了女性文學視角的局限性,并預言單一的話語方式必然限制女作家的藝術創作。然而,清楚指出其話語方式的局限性僅僅應當是發現問題的開始,而非蓋棺之論。有待解決的問題是,承接十七年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與新時期啟蒙文學資源而來,1990年代女性話語為何嬗變,并生成了以性別為單核結構的女性話語模式?
以往涉及1990年代女性文學及相關話題時,我們習慣于從故事和技巧角度抽象討論其文學性,而忽略了文學生產方式的轉型。1990年代的文學空間是由作家、批評家、書商、大眾傳媒等多種因素交織而成的合力場域,如果說女性文學的書寫傳統與女作家的創作激情是話語生成的原動力的話,那么批評家和文學市場則賦予作家以書寫的價值感,并向作家暗示了能夠取得聲譽與經濟效益的特定話語方式,從而引導作家對這種話語模式進行主動獲取、習得以至歸趨。因而,在討論1990年代女性文學的走向和困境時,我們選擇以作家、批評家、圖書出版為視域,以知識考古學的方式爬梳女性話語資源的生成理路。
一
1990年代女性文學寫作接續著1980年代女性文學的傳統,是其延伸、發展的結果。歷史的延展性表現在,這兩個十年中的女性文學創作共同表達了“告別革命”的價值取向。也就是說,以性別為單一核心的女性話語在1980年代女性文學的話語實踐中早已著床。從代際角度看,早于林白、陳染開始文學創作的女作家張抗抗,在1980年代就已經設想過文學題材與人類生活空間的性別屬性。她在西柏林國際女作家會議上按照性別將人類生活空間分為大世界與小世界,并認為“女作家的文學眼光既應觀照女性自身的‘小世界’,同時也應該投射到社會生活的‘大世界’”[3]。這一句式是偏正的,作家將“小世界”視為女性“自身的”歸屬,而與之相對應的“大世界”則被當作外在于自身的社會空間。在這一男性/女性、大世界/小世界的二元結構“裝置”中,張抗抗把“小世界”指派給女作家,視之為女作家最適合棲息的精神領地。可實際上,大/小兩個世界共同構成了人類生活的整體,我們無法人為地從生活中將女性剝離出來。并且,這種把女性派定給特定空間的做法恰好顯示出女作家深受男/女性別觀念模式影響,并不自覺地將自我“他者化”。
1990年代的女性文學正是伴隨著女作家對“小世界”和“身體經驗”的性別認同和想象逐漸起步的。女作家不僅順理成章地接受了前輩作家留下的思想資源,并且相較于前輩而言,在社會業已轉型的1990年代開始創作的她們,不需要過多背負轉型期的敘事倫理負擔,她們身段輕盈地將性別單核話語模式推向某種極端。就文學創作而言,女作家一方面從性別角度回憶并敘述歷史中被遮蔽、壓抑和扭曲的女性經驗,同時宣告其文學創作從大歷史、公共空間中退場;另一方面走進“鐘形罩”或“一間自己的屋子”,在西爾維婭·普拉斯和弗吉尼·伍爾夫式的小世界中登場,于社會生活之外的幽閉空間中探索個人性的、“獨特而隱秘”的身體經驗。也就是說,退場與登場構成1990年代女性作家面對歷史/現實、國族/家庭、社會/個體時的基本選擇傾向。
1990年代女作家的歷史重述,與普通的歷史文學相比有較大差異。如果說普通的歷史文學在一定程度上“兼有歷史記載、政治研究、法律審判及新聞報道的某種功能的話”[4],那么女作家的歷史文學創作對男作家的歷史文學和歷史元話語的解構意義要遠大于其對中國女性集體記憶的正面建構。女作家長于以反諷手法重寫歷史(history),呈現文本態歷史的話語建構特性,以此顛覆男作家的歷史話語,給男權中心的歷史體系制造危機。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是1980年代后期成為文壇主力的女作家。王安憶頻繁在“叔叔的故事”(Uncle’s story)中制造斷裂,目的是消解為右派作家贏得廣泛社會聲譽的“苦難敘事”。叔叔們(1)叔叔們指右派敘事中帶有理想色彩的男性角色,他們以《布禮》中的鐘亦誠,《綠化樹》中的章永璘、《雪落黃河靜無聲》中的范漢儒等形象為代表。在男作家筆下是在反右運動中受難的普羅米修斯,在王安憶的故事版本中卻被還原為卑瑣的肉體凡身。針對同一段歷史故事,兩性話語提供的歷史情節大相徑庭,結論亦相互矛盾,男性歷史在悖反的話語關系之中“金身脫落”。女作家重述革命歷史,部分源自于革命、戰爭對于中國二十世紀女性來說“不是一個“事件”、一個時段,而是她們曾經的生活內容或生活環境”[5]。但應該注意的是,女作家的歷史重述重點不在于系統想象,建構女性的國家、民族經驗,而在于指陳男性的蠻橫霸權與女性的無奈艱辛,在于呈現男性史述的卑瑣虛偽與作為歷史接受者的女性的蒙騙受屈,在于最終忘卻甚至退出有關“大世界”的痛苦記憶。這是由于,只有放逐“大世界”之后,女作家才能心無旁騖地專注于營構“小世界”中獨特而隱秘的經驗,以性別為單一向度的女性話語才能夠以合法的身份出現。從這一角度看,1990年代女作家的歷史文學創作致力于喚醒“母系”歷史記憶的同時,也從事實上剝離了文學的家國情懷。
“私人化寫作”是女性文學異軍突起的重要標志,“私人化”是女作家創作現實題材時的最典型特征。從陳染、林白、徐小斌,到衛慧、棉棉,1990年代女性的“私人化寫作”可謂高潮迭起。私人化寫作的最大特征是題材內容的私人性,它無關社會、民族、國家等時代議題,是女作家在“小世界”中登臺后發現身體經驗的結果,這一寫作潮流直接推動了性別單核話語的形成。陳染是典型的“室內的作者”,她的《無處告別》《與往事干杯》《私人生活》等作品無不著意于對女性獨特而隱秘的經驗進行刻畫。這里的女性經驗主要是指身體經驗、性欲求與性行為等內容。倘若抽離其代表作《私人生活》中的上述經驗,這本小說已無多少主干情節。《上海寶貝》中的女主角一方面是中國青年天天的情感伴侶,另一方面是德國中年馬克的性愛伙伴。與其說衛慧將精神/肉體、愛/性放置在二元對立的框架中,對性愛這一復雜現象作了簡單化處理,倒不如說女主角的精神訴求和情感角色是為了動物化、官能化的性游戲作冠冕堂皇的掩蓋,為其放縱的性行為裹上倫理色彩。因此,王澄霞將1990年代“私人化寫作”的發展脈絡描述為:隱私→女性隱私→身體隱私→下半身隱私[6]。性觀念的解放無疑能夠推動婦女解放,推動人性的自由和解放。然而,世紀末登場的九丹和木子美在“性愛日記”式的《遺情書》中自曝隱私或杜撰隱私,在“實錄”的旗幟下大膽奔放地對女性身體進行二次拍賣。這不僅在挑戰倫理底線,存在道德上的“硬傷”,同時也是對藝術的褻瀆與不恭。
考察1990年代女性文學創作,不難窺見自然的性別身份如何取代了女性的國家、社會、家庭等多元身份屬性,步步為營地在歷史/現實題材中成為女性文學的創作方向和言說方法,并最終占據了女性話語的中心。女性文學創作以“祛蔽”為目標,打撈女性歷史記憶,反映女性現實經驗,原本大有文章可做。但是,關于女性的文學想象被簡單化了,女性成為自然性別意義上的單向度的人。
二
如果說女作家對文學分工的設定及其文學實踐是促使以性別為單核結構的話語生成之“根本”,是女作家的文學創作活動生產了女性文學的主題和概念的話,那么文學批評家、理論家則憑借其專業知識,對女性話語的內涵進行界說和闡釋。毋庸置疑,是批評家的批評實踐、理論概括讓女作家有意無意的性別表達更加顯豁,讓獨立于集體與階級、民族與國家之外的性別問題獲得了自足性。在性別單核話語的合法化過程中,理論家對女性文學概念的界說以及批評家對女性文學創作的同步批評是兩個重要環節,兩者共同生成了女性文學及女性話語的規定性。
女性文學概念的正式提出可以追溯到20世紀30年代。譚正璧在其著作《中國女性文學史話》中,率先使用了“女性文學”這一概念,從性別維度對文學史進行了重新整合。從對“人的發現”的角度看,女性文學概念的提出順應了晚清以來文學現代化的必然趨勢,然而這一概念卻不斷遭遇尷尬和駁詰,其中最常見的問題是:文學是否具有性別屬性,是否存在與之相對應的男性文學?這些詰問促使理論家、批評家從性別維度出發,為“女性文學”尋求相對于普遍的文學,尤其是男作家的作品而言清晰可辨的核心品質。到1980年代后期,女性文學已經形成較為普遍的廣義和狹義兩種概念。廣義概念認為女性文學指女作家所寫的表現女性生活、體現女性風格的文學;狹義概念同樣將女作家指認為唯一合法的寫作主體,但是更加強調女性意識,將女作家與女性意識的組合視為這一概念的特定標識。兩者都試圖使女性文學中“女性”與生物層面的自然性別相區別,指向更具有學理性的內涵。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兩種概念當中,無論是“女性生活”還是“女性意識”,其內涵都相當曖昧,甚至可以說是任人填充的能指。如何從人類生活中剝離男性生活并提純一種“女性生活”,抽象的“女性意識”又如何通過生命經驗得到表現?無人作答。因而,準確地界定女性文學這一概念顯然成為了賦予其規定性的關鍵。劉思謙認識到了已有界定的不足,整合廣義及狹義的女性文學概念,并使之具體化。她認為女作家和女性意識的組合模式最能夠切近女性文學的精神實質——“獨特隱秘的女性經驗和對女性價值的體認”——是男性作家和保留男權中心意識的女作家們不可能超越、不可能采用,也未能企及的領地[7]。在這一表述中,獨特隱秘的女性經驗與對女性價值的認同感成為區別女性文學與非女性文學的關鍵。雖然女性價值到底是什么仍舊是含混不明的,但獨特隱秘的女性經驗卻不由分說地指向了初潮、性欲、懷孕、生產和哺育等相關隱秘的女性經驗,尤其是身體經驗。存在的問題是,除此之外,獨特而隱秘的女性經驗是否還囊括其他內容?如果沒有,我們重新組合廣義和狹義的概念不難發現,所謂女性文學指的是由女作家為寫作主體,注目于女性小世界或者身體經驗的文學。女性文學的界定,既體現學者對女性文學創作的整體性把握,又通過與文學現實的互動,重塑女性文學以性別為單一核心的話語形態,反過來將身體寫作指派給女作家。
1990年代的女性文學創作與女性文學傳統的最大區別在于,女作家悄然置換了宏大議題,性別不再是民族解放的載體,也不再是翻身道情的介質;性別本身構成了談論的最終目標指向。而性別話語方式的習得與合法性的獲取是在與批評家積極對話的過程中逐步實現的。批評家通過文學批評積極回應了1990年代的女性文學創作,同時也對女性文學的可能形態進行前瞻性的預見。也就是說,批評家實際參與了1990年代的女性文學話語方式的形塑過程,這不僅為女性文學生成性別單一向度的話語樣態提供了理論依據,同時也論證了這一話語方式的合法性。批評家的任務之一是重塑評價標準,發現被遮蔽的文學景觀。具體到女性文學批評而言,孟悅、戴錦華兩位學者的著作《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具有范式意味。她們較早引入了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并將其應用于中國女性文學研究實踐。她們認為,由于男性文學史家普遍缺乏自覺的性別觀念,相關史述中女性文學作品的真實情態被遮蔽在“地表之下”,因而那些偶而被提及的女作家也只是處在掛名狀態的“空洞能指”。因而她們以“女性身體”“女性苦難”為核心關鍵詞,重新解讀了包括廬隱、馮沅君、冰心、凌叔華、蘇青在內的中國現代女作家及其創作,并認為“國家與民族的歸屬感很大程度上是男性的”[8],關于國家的敘事不能解釋與抹去女人身體所承受的種種苦難。隨著女性文學批評標準的提出,許多過去被批評的作家如今被重新接受,在她們之中,蕭紅的文學史地位變遷最具有典型性。魯迅在給蕭軍、蕭紅的信中,曾針對《生死場》序言補充道,“有一句‘敘事寫景,勝于描寫人物’,并不是好話,也可以解作描寫人物并不怎么好。因為做序文,也要顧及銷路,所以只得說的彎曲一點”[9]。胡風也曾批評蕭紅“對于修辭的錘煉不夠”。然而,以女性文學批評的后見之明看蕭紅,上述缺點恰恰構成了蕭紅文學創作的藝術特征,是蕭紅“用詩的語言和思維寫小說”[10]的結果。
造成女性文學批評祛蔽功能喪失的因素不一而足。但是,在諸多因素之中,研究者的性別經驗及由此產生的價值取向無疑起到關鍵性作用。由于女性學者具有天生的性別優勢,利用西方性別話語資源是她們的自然選擇,這就使得她們自覺地親近孟悅、戴錦華、劉禾等前輩學者,并且沿著她們的路走得更遠。我們不能抹殺從性別視角取景時看到的別樣景色,以及她們對女性隱秘經驗作出的系統闡釋。但是,每一個文學現象都是立體、多面的,如果僅將研究視野局限在性別取景框架中,便不能夠做到“橫看成嶺側成峰”,甚至錯誤地將女性文學研究引入一道從女性主義立場看女作家寫女性經驗的“窄門”。比如在整理1990年代女性文學創作時,劉思謙曾率先提出“女性新歷史小說”這一概念,并從語素角度強調女性新歷史小說應涵蓋以女作家為創作主體的性別因素,以歷史為主要內容的題材因素以及相對于傳統歷史小說和男性歷史小說而言的文學新質等特征[11]。這一研究視角,無疑有助于發現女作家在處理歷史題材方面的異質性,但由于其博士研究生張兵娟等人在進一步對女性新歷史小說作分類研究時采用了單一性別視角,過度關注并盛贊小說中呈現的女性經驗,尤其是以女性身體經驗、情感經驗、輪回命運作為闡釋中心,忽略了故事、技巧和話語層面的多種面向,而將女性文學批評模式提純為單一的性別話語模式(2)張兵娟的相關論述散見于《一道奇異的歷史風景線——女性新歷史小說及其批評概覽》等文章中。。可以說,當文學研究的目的完全被性別意識形態化之后,文學批評的言說方式也隨之被扭曲為具有排他性的系統。從文學立法角度看,以“女性經驗”為核心視點的文學批評對1990年代以性別為單核結構的女性話語的形成來說,其影響或許不是敲邊鼓式的推波助瀾,而有可能是決定性的。
三
以往我們習慣于從文學本體的角度抽象地談論女性文學的異質性特征,談論女性故事中的性別經驗以及講故事的敘述技巧,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雜志、出版對女性文學話語的形塑功能。特別是對于1990年代女性文學來說,如果無視1990年代文學生產方式與傳統女性文學創作環境之間的區別,我們可能就無法理解在商業化和現代傳媒背景下促成女性文學話語呈現單一向度的重要原因。1980年代前期,作家大多依附于作協、文聯等國家單位,是處于計劃經濟框架之中的國家公務人員,主要依靠工資而非稿酬與版稅生活。這就意味著,作家無需把寫作視為謀生的手段,在供給制語境下,工資——“鐵桿莊稼”作為個人的經濟來源,具有旱澇保收的特點。創作數量和寫作質量給予作家的僅是聲望、名譽等象征性資本。但是,從1980年代中后期的社會轉型開始,文學一方面遭遇了被迫“斷奶”的局面,“除少數必須補貼的期刊外,其余期刊都要‘獨立核算,自負盈虧’”[12],原本抱定了“鐵飯碗”的作家和文學相關從業者今后必須自謀出路;另一方面,文學傳播媒介原本在政府嚴密規范和監管下,并不具備獨立性,但經濟制度的轉型、國家監管力度的適度調節,使傳媒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主體性。具體到對1990年代女性文學生產方式來看,女作家逐漸朝市場歸趨,向市場靠攏,同時報刊、雜志和書商共同操作、制造了女性文學一波又一波的“熱潮”。也就是說,1990年代蓬勃發展的文學市場和大眾傳媒生產了“女性話語”、“包裝”了女性文學,即便這種作用不是決定性的,在女性文學話語日趨單一化的1990年代,至少起到過推波助瀾的作用。
1990年代女性文學創作隊伍曾呈現出“四代同堂”的繁榮局面,這批女作家中不僅有“文革”結束后開始創作的張抗抗、張辛欣、張潔等人,還有1980年代中后期成為文壇主力的王安憶、池莉、方方等人;有1990年代初登文壇便引領女性文學風潮的陳染、徐坤、徐小斌等人,也有世紀末在傳媒策劃之下集體亮相的魏微、衛慧、棉棉等“70后”女作家。隨著自由作家與自由撰稿人重新成為一種職業志向、生活方式和身份選擇,女作家中包括林白在內的自由撰稿人,在以文學市場化為背景的1990年代普遍交上了好運,不斷地出版自己的新書,又不斷地領取稿費,成為市場的寵兒;女作家中也有像鐵凝這樣供職于文化管理部門與科研機構的體制內作家,由于被市場之風吹動心襟,主動加盟書商的出版、策劃活動,為出版社量身定做了包括《無雨之城》在內的有失創作水準的作品。我們雖然不能據此指認作家對文化市場投降納表,但是也沒有必要遮掩1990年代文學與商業聯姻這一事實。既然整個社會都已經被納入到了商業軌道,文學創作活動也難免與商業接軌,就有必要正面回應“商業和經濟的價值取向也將同樣是文化創造的重要標準和目標”這一問題[13]。因此可以說,同時追求價值與價格、靠近文化市場是多數作家的必然歸趨。作家為了滿足市場并尋求讀者,就不得不琢磨讀者的欣賞口味,甚至投其所好地進行“目中有人”的創作。
既然在文化商品營銷過程中,必須將女作家與女性文學放置在“被看”的位置上,那么就需要相應地創造出能夠引起觀看欲望的內容,即魯迅先生在《論照相之類》一文中所說的,“我們中國的最偉大最永久的藝術是男人扮女人”[14]。只不過對女作家而言需要的不是易裝,而是將自己還原到最為本質的生理層面——好看的層面。因此,1990年代突顯女性氣質和生理性別的文學書系成為商業熱點和消費時尚。尤其是在1995年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召開前后,出版商、文學期刊、批評家和作家相互聯合,創造了商業價值與文學熱點的雙重效益。僅此一年,就有四川文藝出版社策劃出版的“紅辣椒”叢書,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藍襪子”“紅罌粟”“金蜘蛛”叢書,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她們”叢書等書系相繼問世。以上書系名稱有意挪用傳統文化中的女性象喻,并將其當作吸引顧客的招牌,這不僅違背了女性話語,不能顛覆傳統性別文化秩序,反而以自然性別作為商業競賣的標簽,加深了大眾對傳統女性角色的刻板印象。除去書系名稱將性別符碼轉化為商業符碼這一策略之外,叢書中的序言以及廣告語同樣強調了女性話題的異質性、神秘性和趣味性。比如,王蒙在“紅罌粟”叢書序言中突出了女性的“心軟,心細,感情化,神經質”等特點;程志方則在“她們”叢書題記中強調“她們是他們。我們是我們”,從自然性別層面將女性“包裝”成與男性相區別的“她者”。此外,上述兩種叢書將那些能夠反映作者趣味和審美選擇的生活照作為插圖,與文字信息共同構成了可看并且好看的視覺內容,也就是說“寫女人”和“寫作的女人”共同構成了被閱讀和被觀看的賣點。這意味著,不僅女性文學作品能夠成為文化商品,就連女作家自身也無法避免被商品化的命運。
因此,女作家如何看待性別因素被制造成賣點,如何回應女性現代意識被扭曲和誤讀,如何在價格看漲而價值跌落的現實悖論面前進行選擇就顯得尤為重要,因為她們對市場期待的回應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女性文學的話語方式及其走向。以“紅罌粟”叢書為例,其中包括了當時活躍在中國文壇上的22位女作家的新作和力作,這種系統性、大規模地為女作家集體出書的現象在中國現代文學出版史上實屬罕見,結果證明這種策劃方式具備了相當大的市場號召力。叢書封面上一朵朵潔白、殷紅的罌粟既是良藥又是毒品,它們象征著妖嬈而美麗、誘人卻危險的女性魅力,更是對傳統文化觀念的女性形象——天使與惡魔集合體的現代演繹。有意味的是,該叢書的名稱“紅罌粟”并非男性的性別設計,而是女作家的自我命名,是1994年夏天女作家在河北教育出版社組織的筆會上的集體智慧的結晶[15]。也就是說,女作家面對書商暗示與市場期待時,在理性、自覺的情況下進行著判斷和選擇。女作家以此自喻,或許暗示了這套叢書對于傳統話語方式構成了挑戰,從這一角度看具有一定的解構意義。然而,即便隱喻修辭和詩意表達能夠為女作家的表態提供較大的闡釋空間,女作家可在此空間之內進行解釋和辯駁。但不容置疑的是,由于女作家自身性別立場的游移與曖昧,她們并未對被觀賞、被把玩、被消費的境況進行批判,反倒心甘情愿地將私人化的身體表述作為吸引讀者的招牌。隨著文化市場的成熟發展,商業資本和大眾傳媒會以強大的力量重塑女性話語,突顯出性別向度在女性話語中的重要位置。到1990年代末,衛慧登場,“并詢喚他們來看看上海寶貝的乳房”時,可以說,“女作家不再以‘女’字為恥,而是以比較自如的心態來面對這一曾經是1980年代文化識別方式中的‘第二性’身份”[16]。
勾勒1990年代以性別為核心的女性文學話語知識譜系,分析其在不同領域中的運作方式,目的是對其走向進行檢省并糾偏。我們發現,在新啟蒙語境之下,女性文學回避了革命、國家、民族等宏大議題,追求“純文學”的創作目標,并將個體化、私人性的生活經驗指派為女作家最應表現的題材范疇;從生產方式角度看,市場對作家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女作家接受了批評家和書商的提議與策劃,主動歸趨并習得了使女性文學變得“好看”的話語方式,最終使性別因素兀立在女性話語的核心位置。由此可見,作家、批評家以及文學市場共同推動了女性文學話語的生成,盡管女性文學話語存在各種各樣的表述,但事實上其共同突顯了性別在女性文學話語中的核心位置。作上述梳理,不是要把顛倒的再顛倒過來,否定私人化的寫作形態,而是試圖探尋女性文學創作與研究的多重可能性與活力,使女性文學不至于淪為少數人的烏托邦,而能在更廣闊的天地里創造出真正詩意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