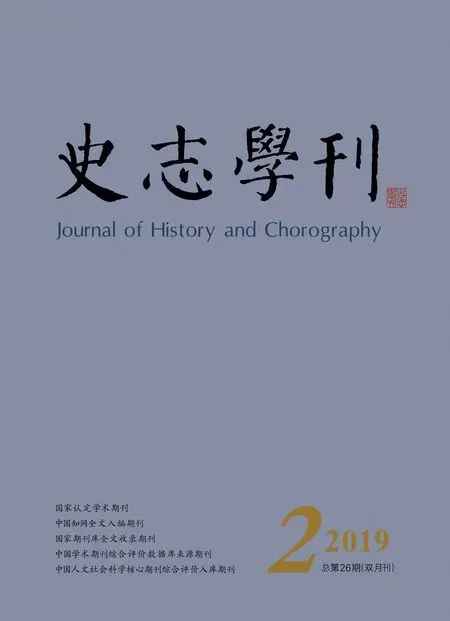關于張頷創作《西里維奧》的時間與背景探討
郝岳才
(中石化山西石油分公司,太原030024)
一、有關北風、《北風》詩刊與北風社
關于北風一詞。從王文光的長篇小說《墻頭草》及其后來的解讀文章中似可以界定“北風”一詞的內涵。早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王文光就寫過一本反帝反封建的長篇小說《墻頭草》,由上海啟智書局張藍霄出版,曾翻印10余次,達10萬冊之多。出版時,王文光并沒有用自己的真名實姓,而是以“北風”筆名問世。該長篇小說的內容,表面看是反對奴隸制的羅馬故事,好像是譯本,但卻是實實在在的創作,除“虐柔”是歷史人物及羅馬大火是歷史事跡外,其他人與事都屬虛構。王文光在其《五十年來的經歷與目睹》(三)一文中作了這樣的釋讀:“‘北風吹起墻頭倒,墻倒草也了’,羅馬大火燒得遍地通紅,由馬可領導的勞動人民收拾殘局重建新天新地。‘貫牢’家族反映著國聯也反映著官僚。國際上是以水晶(暗指蘇聯)為領導力量,國內是以馬可(暗指馬克思主義)教導下的工人階級為戰斗先鋒。‘墻’是封建官僚與帝國主義的社會基礎及制度,‘草’是它的統治集團,‘北風’是從蘇聯傳來的革命浪潮,‘火’是革命運動,‘紅’是赤化。‘金鳳’是指中國中上層資產階級與其知識分子,其‘夢’寫出了南京政局。”[1]王文光.五十年來的經歷與目睹(三).山西文史資料(總31輯).(P161)由此可見,王文光當時以北風筆名出版《墻頭草》一書是具有特殊意義的,“北風”所指乃從蘇聯傳來的革命潮流。
關于《北風》詩刊。從現有的資料分析,在杜任之[2]杜任之.我的回憶(六).山西文史資料(總84輯).(P117)、王文光[3]王文光.五十年來的經歷與目睹(五).山西文史資料(總33輯).(P177)、李毓珍[4]李毓珍.我的自傳.原平文史4.(P207)、徐士瑚[5]、馬作楫[6](P144)等的回憶文章中,盡管對《北風》詩刊的創刊說法上有些差異,但總的來看內容指向是一致的,即1948年1月15日至6月11日,一共刊出7期,最后在梁化之警告下停刊。刊物由李毓珍教授創辦,張頷與馬作楫是參與者。創刊之初,杜任之與王文光即與李毓珍溝通,有意識地把《北風》作為地下民盟的宣傳刊物。這也正是《北風》詩刊非反內戰、爭民主不刊的緣由。關于《北風》刊名的內涵,盡管上述幾位參與者或見證者的回憶中均未提及,但聯系到王文光筆名“北風”以及對北風一詞內涵的界定,《北風》刊名的內涵自不言而喻。
關于北風社。由于歷史的原因,北風社的資料更為有限,連其出版有幾種書籍都不得而知,但從當時圖書出版的情況分析,北風社即是《北風》詩刊的注冊單位,自然以北風社的名義出版書籍也便順理成章,李毓珍為張頷所作《西里維奧》的序文即為明證。也就是說,北風社在其短短近5個月時間里,不僅出刊了7期《北風》詩刊,也出版了《西里維奧》等北風系列叢書。與此同時,王文光也出版了《曉塵庵一弄》詩冊,以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與官僚四大家族為主要內容,同在黃河書店出售。盡管目前找不到當時出版的《曉塵庵一弄》詩冊,也不好臆斷其是否為北風系列叢書,但與北風社的關聯是顯而易見的。
二、《西里維奧》的創作與發表時間
李毓珍(筆名:余振)在《西里維奧》單行本序文中言,該詩曾先后在《工作與學習》《野草》《周末文藝》等刊物分章發表過,而且,原來的詩名是《雪維歐》。本來,根據上述三種雜志即可核實《西里維奧》的創作與發表時間,但鑒于雜志存世甚少,已無從直接查核,只能從各種零星的記載中復原。根據張頷口述:“我那首長詩,就是看了他(余振)翻譯的一篇普希金的小說,覺得好,在他的鼓勵下寫成的。我跟他認識早了,抗戰后回到太原就認識了。一開始不認識,到了省議會才認識的。”[1]韓石山.張頷傳.山西出版傳媒集團,三晉出版社,2014.(P158)而到省議會工作的時間,他說是在“閻錫山在省城各機關搞‘三自傳訓’前”。而1947年9月,先在太原開了各機關全體人員的斗爭動員大會。韓石山由此得出張頷到省議會的時間在八九月間,定在8月。而《北風》詩刊1948年1月創刊時,《西里維奧》一詩已經以《雪維歐》之名先后在《工作與學習》《野草》《周末文藝》等分章發表。據此似可得出張頷認識李毓珍最早不會早于1947年8月的結論,那么張頷《西里維奧》的創作時間也似可鎖定在1947年8月至1947年12月間。但新的疑問又產生了,同樣是張頷口述:“沒多久,我就辭了《青年導報》的職務,離開同志會太原分會,去省議會當了秘書。《工作與學習》雜志,在此之前就停辦了。”“辦《青年導報》和《工作與學習》,時間都不長,報紙一年多,雜志更短些”[1](P98)。而《工作與學習》雜志,1946年5月10日創刊,到12月25日,近7個月,共出刊16期。半月刊,逢10號、25號出版,普通16開本[1](P107)。照此,如果《工作與學習》雜志辦到1947年5月即超過一年。則可判斷《工作與學習》大體在1947年5月前停刊,最多辦刊26期。也就是說《雪維歐》部分章節是在這一時段前發表于《工作與學習》雜志,具體應在17—26期之間刊載。此一推斷,與張頷1947年8月到省議會前《工作與學習》早已停刊的說法一致。既然《工作與學習》雜志在1947年5月前已經停刊,而且還刊載過《雪維歐》,那么早在張頷到省議會前的5月份,《西里維奧》已經寫作完成并分章發表。如此又產生了新的疑問,張頷認識李毓珍的時間一定是他到省議會前。那么到底二人相識于何時?根據李毓珍的回憶,“山西大學校長徐士瑚先生來信,邀請我回山西大學。于是1946年5月,我應邀前往,并向徐校長推薦了被解聘的徐褐夫、季陶達、王文光三教授。”[1]余振.緬懷杜任之先生.文史月刊,1998,(6).(P3)“因為一篇文章被特務毆打,《北風》詩刊又被迫停刊。我向杜先生和王文光先生提出離開太原的意思,等他們二位征得山大徐校長同意后,我于6月份中下旬離開山大,到了蘭州大學。”[1](P5)說明李毓珍在山西大學任教的時間在1946年5月至1948年6月中下旬間。張頷口述:“后來跟余振先生熟了,可能近期的一個日子是普希金的誕辰或是忌日,那時不叫普希金,叫普式庚,余振提議紀念,我同意了。我們看重的是普氏同情十二月黨人,是反對沙皇統治的。我把這個意思跟智力展說了,沒想到智力展不同意。我心想,你平常還說怎么喜歡普希金的詩歌,這會兒開個紀念會都不同意,那好吧,我就拿了張普希金的畫像送到他家里,看墻上有個地方,給掛了上去。”[2]韓石山.張頷傳.山西出版傳媒集團,三晉出版社,2014.(P110)到底是普希金的誕辰或忌日,張頷回憶不起來。其實,普希金的誕辰在6月6日,忌日則是2月8日。李毓珍1946年5月到山西大學執教后,一直到《工作與學習》停刊,最有可能的便是1947年2月8日的普希金忌日。排除1946年6月6日與1947年6月6日的理由自不待言,前者李毓珍1946年5月才到山西大學,還談不到與張頷熟悉的程度,后者到1947年6月《工作與學習》已經停刊。正是圍繞著普希金2月8日的忌日,在李毓珍提議下,張頷游說同志會太原分會的智力展,借《工作與學習》和《青年導報》陣地搞一次圍繞普希金的紀念活動。最終,盡管智力展沒有同意,但李、張二人還是作了積極的努力,在這一期間張頷受李毓珍鼓勵,改寫普希金小說《射擊》為《雪維歐》長詩,部分章節首先發表在張頷主辦的《工作與學習》上,但隨著《工作與學習》停刊,只能在《野草》與《周末文藝》上分章發表剩余的詩章。由此也便可以看出,張頷創作《雪維歐》的時間在1947年初,隨后便分別在三個雜志上發表。1947年初期的太原,正處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以紀念普希金忌日的方式宣傳反抗專制的民主思想,可以說是當時知識界的一種獨特斗爭形式。《雪維歐》長詩看似由普希金作品改寫,但在當時的背景下無疑是借題發揮,借對俄國“十二月黨人”的同情,鞭撻反動統治,抒發反對內戰,爭取民主的思想。與王文光創作《墻頭草》有異曲同工之妙。
三、北風社與《西里維奧》單行本
張頷1939年冬從南漳到鄉寧縣投奔抗日前線一直到1948年底在北京城工部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10年來,始終在杜任之的領導或影響下工作,杜任之是他走向革命的領路人。1945年抗戰勝利,張頷從孝義回到太原后不久,曾一度被閻錫山軟禁甚至差一點處死的杜任之也于1946年春隨山西大學回到太原。作為文學青年,進步青年,雖沒有領導被領導關系,但張頷經常到山西大學,出入于杜任之、趙宗復等省城進步學者形成的文人圈子,而且不時在報紙刊物上發表一些進步文章,針砭時弊,影響輿論。特別是利用工作之便,以《工作與學習》與《青年導報》為載體,組織發表一些專題性文章,比如杜任之的一些文章即在《工作與學習》雜志以筆名,或以張頷自己的名字發表。再比如1946年6月4日端陽節,也是國民政府確定的詩人節,便由《工作與學習》雜志社和青年學習會在民眾教育館舉辦了紀念屈原座談會,參會者有30余人,山西大學教授田依文主談,訓導長杜任之擔任主席,郝樹侯、張光鑒、商性齋、李浪均發言,最后由杜任之作總結。看似一個紀念性座談會,當時的現實意義不言而喻。在張頷有可能面臨“三自傳訓”風險的時候,也是杜任之、趙宗復為他提供保護,離開同志會太原分會調入省議會。1947年暑假期間,王文光借南京中央大學探親之機,與民盟中委之一的劉王立明見面并提出加入民盟,劉王立明與上海另一位中委周新民介紹其加入了民盟,并帶回了在太原開展民盟工作的任務。王文光回到太原,即與杜任之、李毓珍建立起山西最早的民盟組織,由王文光任秘書,杜任之負責組織工作,李毓珍負責宣傳工作,并迅速在進步教授與學生中發展盟員。1948年1月李毓珍創辦《北風》詩刊即有意識地作為民盟的宣傳刊物來辦刊,自然非反內戰、爭民主的詩作不刊。如此也就可以理解為什么張頷與馬作楫會參與到《北風》詩刊的創辦中。這其中既有李毓珍的因素,更有杜任之的因素。當然,《北風》詩刊作為民盟的宣傳刊物,張頷不知,馬作楫也不知,只有王文光、杜任之、李毓珍知之。在1月15日到6月11日《北風》詩刊的編輯發行過程中,李毓珍借助北風社這一陣地,幫助張頷出版了詩集《西里維奧》。據溫慶華《翻譯家余振傳略》記載,“1948年6月,他(余振)應好友徐褐夫之約,赴蘭州大學俄文系任教。在蘭大期間,其譯作《普式庚詩選》《列孟托夫抒情詩選》和著作《俄語文法高級教程》,由上海光華出版社出版。其弟子山大學生馬作楫的詩集《憂郁》和青年詩人張頷的詩集,經由他的推薦亦由該出版社出版。”[1]溫慶華.翻譯家余振傳略.文史月刊,1999,(5).(P145)馬作楫的詩集《憂郁》確實如溫慶華記述的那樣,現仍有原本存世。據馬作楫回憶,“我感到鼓舞的是李毓珍教授還以‘北風詩社’的名義,支持我在上海光華出版社于1948年出版了我第一部詩集《憂郁》。”[2]馬作楫.關于《北風》詩刊的點滴回憶.文史月刊,2002,(2).(P37)但溫慶華所述上海光華出版社亦為張頷出版詩集卻并未指出具體的詩集名,也許指的是北風社出版的《西里維奧》,也許是另有詩集出版。但前者可能性更大。在這一段時間里,盡管張頷、馬作楫均非民盟盟員,也不知道《北風》詩刊承擔了民盟宣傳刊物的職能,但他們用自己的行動參與了反內戰、爭民主的宣傳實踐。
在《北風》詩刊被迫停刊,李毓珍、王文光、杜任之被迫離晉,白色恐怖愈演愈烈的情況下,作為進步青年,作為杜任之的追隨者,繼杜任之1948年7月1日離開太原飛抵北京后的8月中旬,張頷也飛往北京,在杜任之任教的華北文法學院擔任了校辦公室秘書,并秘密加入民盟組織,年底前又在城工部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由一名愛國進步青年鍛煉成為一名共產黨員。在張頷的成長過程中,杜任之等的影響不可或缺,趙宗復、李毓珍等的影響不可或缺,參加民盟的活動并成為民盟盟員不可或缺,在白色恐怖的環境中追求真理,追求民主,堅持斗爭不可或缺。而創作發表出版《西里維奧》即是其在白色恐怖下堅持斗爭,追求民主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