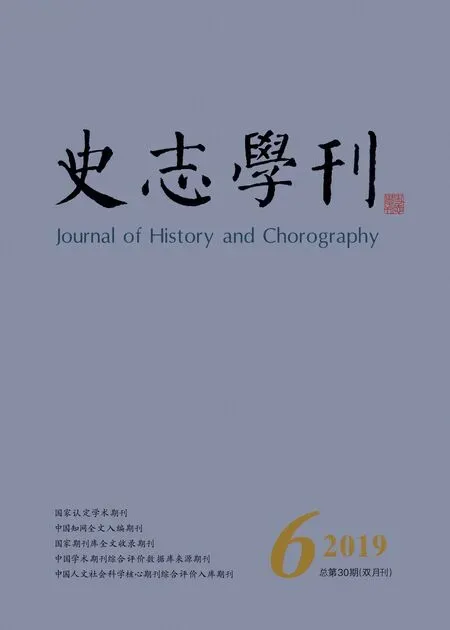古代草原絲路貿易流動性探梳
馬曉娟
(新疆師范大學歷史學與社會學學院,烏魯木齊 830017)
絲路學是當下學界的一個熱門話題,其中所包括的草原絲路及其貿易研究則頗為豐富。但是關于草原絲路貿易流動性,目前還無專文考察。正基于此,本文對此問題做了嘗試性的綜合探討與梳理,以期對相關問題作以補充與豐富。
從實際考察來看,比起綠洲絲路相對固定的路線與站點,草原較為空曠的大漠、草場與森林區則決定了草原絲路東、西、南、北各個方向上的路線,以及人文族群間勢力范圍變動性較大,體現出了較強的流動性。這一流動性也正是草原絲路貿易一個顯著特點。由于自然環境與生產生活的差異,農耕區的物資比之草原區要豐富得多,故農牧貿易是草原絲路貿易一個最基本的支撐點。草原絲路貿易流動性具體實質也主要展現于此。
一、貿易對沖區的變動性
翻閱千年歷史記載來看,農牧間貿易是在交往博弈中而進行的。故農牧對沖區或者說政治力量交界區的變動性,首先就是草原絲路貿易的變動性第一個實質體現。其主要表現于兩個方向上的對沖區及變化。
1.南北對沖區的起伏。
歷史上的南北對沖區分界線,既有草原內部的,也有南北農牧間的。但是游牧群體本身所產物資因有太多相類性,因此草原貿易最大對象還是農耕區物資。故這里主要來談談農牧間的對沖區。二者間最主要的體現是長城,它也是農牧分界線。正如西漢時漢文帝給匈奴冒頓單于的信中所言:“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1](西漢)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59.(P2902)依據文獻看,先秦與游牧族群相鄰的中原諸侯國均在邊界區建立了長城,如史所載:“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筑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筑長城,自代并陰山下,至高闕為塞。而置云中、雁門、代郡。其后燕有賢將秦開……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余里。燕亦筑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1](西漢)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59.(P2885-2886)由此看出,各諸侯國不僅建立了長城,而且在長城一線還設置了郡縣,起到“衛城”與“拒胡”之效應。當然,這些長城一線郡縣也成為農牧經貿交流的最前沿地區。但是這種分界線隨著時代發展是變化的。秦統一六國后,在原有諸國北部長城基礎上不僅做了連接,也新修了不少長城,這一新形成的長城,即萬里長城,成為秦與北部游牧族群的分界線。從東到西,這一北部長城大致經歷了當時的遼東郡、遼西郡、漁陽郡、上谷郡、云中郡、九原郡。比對今天,大致經歷的地區是丹東、沈陽、呼和浩特、蘭州一線。比較戰國時代北部所修長城位置,秦時所修北部長城已經是大幅度北移了。其原因,一如《史記》云:“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眾北擊胡,悉收河南地。”[1](西漢)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59.(P2886)同時“使蒙恬北筑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余里”[1](西漢)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59.(P280)。因秦原本就處于諸侯國西部,故北移中西北部長城所推動的幅度最大[2]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冊3-4《秦時期全圖》).地圖出版社,1982.。正如《史記》所言:始皇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為四十四縣,城河上為塞”[1](西漢)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59.(P253)。這說明秦朝比之戰國時代,農牧貿易分界線也做了向北、向西延伸。但是這一農牧交界線,在秦漢之際隨著南北人文政治實體的變遷,也發生了變化。若《史記》載:“十余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于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于故塞。”[1](西漢)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59.(P2887-2888)冒頓單于興盛后,“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郉、膚施,遂侵燕、代。”[1](西漢)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59.(P2890)而當時中原正處于楚漢之爭,故歷史上所修長城并非是固定的。各代都有修長城之記載,如描述北魏時期的記載:“八年春,筑長城,距五原二千余里,置守卒,以備蠕蠕。”[3](北齊)魏收.魏書.中華書局,1974.(P2400)這是北魏抵制北部柔然之舉。北朝末與隋朝時,北距突厥而修的長城記載,如史云:“顯祖親御六軍,北攘突厥,仍詔斐監筑長城。”[4](唐)李百藥.北齊書.中華書局,1972.(P554)隋煬帝時“發丁男百余萬筑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5](唐)魏征等.隋書.中華書局,1973.(P70)直到近代時,中國境內還留有這樣的遺跡,如《清史稿·內蒙古志》載:“東界吉林、黑龍江,西界厄魯特,南界盛京、直隸、山西、陜西、甘肅,五省并以長城為限。北外蒙古。”[6]趙爾巽等.清史稿.中華書局,1977.(P2396)縱觀歷代文獻,雖然長城成為農牧分界線標示性建筑,但從來沒有真正阻擋住過農牧之間的往來。從歷史長河來看,這一農牧分界線隨著雙方力量的消長也是處于南北浮動當中。當然,這分界線同時作為農牧交易的對沖區,也是處在南北起伏流動當中。從文獻來看,這一分界線的緣邊貿易歷代多有記載,如史載:漢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1](西漢)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59.(P2904)。甚至漢武帝與匈奴交惡初期時,匈奴“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1](西漢)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59.(P2905)。北魏時期,如《魏書》載:“蠕蠕王阿那瓌既得返國,其人大饑,相率入塞,阿那瓌上表請臺賑給。詔孚為北道行臺,詣彼賑恤。孚陳便宜,表曰:……貿遷起于上古,交易行于中世。漢與胡通,亦立關市。今北人阻饑,命懸溝壑,公給之外,必求市易。彼若愿求,宜見聽許。”[3](北齊)魏收.魏書.中華書局,1974.(P424-425)這是柔然與北魏緣邊的交易。突厥與隋朝的緣邊貿易,如《隋書》載:“明年,突厥部落大人相率遣使貢馬萬匹,羊二萬口,駝、牛各五百頭。尋遣使請緣邊置市,與中國貿易,詔許之。”[3](北齊)魏收.魏書.中華書局,1974.(P1871)突厥與唐時的緣邊互市記載,如《舊唐書》云:“十五年,小殺使其大臣梅錄啜來朝,獻名馬三十匹……上嘉其誠,引梅錄啜宴于紫宸殿,厚加賞賚,仍許于朔方軍西受降城為互市之所,每年赍縑帛數十萬匹就邊以遺之。”[7](后晉)劉昫等.舊唐書.中華書局,1975.(P5177)除了正常的貿易,長城緣邊也時常成為游牧者對農耕區非正常的物資掠奪區。這類記載也不絕于史。如《后漢書》載:“時北匈奴猶盛,數寇邊,朝廷以為憂。會北單于欲合市,遣使求和親,顯宗冀其交通,不復為寇,乃許之。”[1](南朝宋)范曄.后漢書.中華書局,1965.(P2949)《后漢書》云:“五年,鮮卑寇幽州。六年夏,鮮卑寇三邊。”[1](南朝宋)范曄.后漢書.中華書局,1965.(P2990)《隋書》云:“后數載,突厥寇邊。”[2](唐)魏征等.隋書.中華書局,1973.(P60)
上述無論是何種性質的貿易,從地緣政治角度來說,農牧貿易程度,包括數量、內容、頻率,都是由北向南逐漸減弱。這則體現了南北貿易“由粗到細”或者說由密集到稀疏的流線性特點。這一流線性隨著時代發展,同樣處于南北對沖區的起伏當中,東西方向也不例外。
2.東西對沖區的伸縮。
南北有長城作為對沖區,東西方向也有。當然,有些地段是以山川為界限的。因為東部面臨大海,所以農牧東西方向對沖區,主要體現于西部。西部對沖區的影響也遠大于東部,史書對此也多有反映。依據古文獻與歷史地圖,可以清晰的看到這一點。秦、漢西部就有著巨大的差異。一如《漢書》所載:“自周衰,戎狄錯居涇渭之北。及秦始皇攘卻戎狄,筑長城,界中國,然西不過臨洮。”[3](東漢)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2.(P3872)到漢武帝張騫始開西域后,匈奴右地渾邪、休屠王(降漢),“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列四郡,據兩關焉。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于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犁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3](東漢)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2.(P3873)向西的發展,也造就了農牧的交匯,若《漢書》云:“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時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絕南羌、匈奴。其民或以關東下貧,或以報怨過當,或以誖逆亡道,家屬徙焉。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為天下饒。”[3](東漢)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2.(P1644-1645)
比之南北對沖區,東西對沖區也尤其顯現于草原內部。當然,草原內部東西對沖區并沒有長城為界限,只是勢力范圍的東西伸縮。因為東西方向發展,不僅意味著草原內部貿易,也意味著草原所獲南部農耕區物資的東西交流,以及在東西部較遠的農耕區所獲物資的相向流動。結合地理環境與文獻看,一個草原勢力的興盛,首先表現的就是向南推進與東西拓展。東西拓展就意味著東西對沖區的大流動。如《史記》云:匈奴冒頓單于時“東襲擊東胡……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4](西漢)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59.(P2889-2890)。這之后在西部有了進一步拓展,冒頓單于在給漢文帝的信中夸耀到:“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強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4](西漢)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59.(P2896)這意味著草原原有東西對沖區的解體,新區域的建立。這一舉動不僅意味著冒頓單于統治下的匈奴掌控了更多草原東西貿易權,也意味著東西貿易線路的拓展。這在后來突厥、契丹、蒙古先后崛起于北方草原之時均有展示。
從經濟視角來看,無論是中國農耕區與草原東西對沖區貿易,還是中國北方草原內部東西貿易。整體來說,都是由兩邊向中心減弱。這是貿易里距、時間與成本決定的。以中國農耕區的西部草原對沖區貿易區來說,就是由西向東逐漸減弱。這在《明史·西域傳》中有體現,如其言:“洪武中……帖木兒首遣回回滿剌哈非思等來朝,貢馬十五,駝……其國中回回又自驅馬抵涼州互市。帝不許,令赴京鬻之。”[5](清)張廷玉等.明史.中華書局,1974.(P8598)這說明東西與南北對沖區貿易類似,草原貿易都是先緣邊互市再深入內地。因為貿易里距越長,意味著成本越高,風險也越大。除非,長距離后的利益遠大于緣邊貿易,如官方的貢賜貿易就是如此。《三國志·倉慈傳》對此有展現,如其載:“太和中,遷燉煌太守。郡在西陲……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貿遷……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為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為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1](西晉)陳壽.三國志.中華書局,1959.(P512)不難看出,這些西域人的敦煌貿易是西部緣邊貿易,若能在這里獲得既得利益,就會停止向東去貿易;若此地得不到既定利益,就會遠赴京師獲取貢賜貿易。這說明緣邊貿易是第一波貿易。
古代的緣邊貿易發展到近代,表現的就是邊境貿易或者說國境貿易,因為真正的國家概念與定型產生于近代。這在《清史稿》有清晰的展示,如其載:“雍正五年秋九月,與俄訂《恰克圖互市界約》十一條……喀爾喀北界,自楚庫河以西,沿布爾固特山至博移沙嶺為兩國邊境,而互市于恰克圖。”[2]趙爾巽等.清史稿.中華書局,1977.(P4483-4484)具體地點、貿易路線及管理等,如所云:“互市處在恰克圖南買賣城,有路南通庫倫,北達上烏丁斯克,與新修鐵路接。有俄國領事署。貿易茶最盛。車臣汗、土謝圖汗兩部事亦歸監理。”[2]趙爾巽等.清史稿.中華書局,1977.(P2439)這是一個平等的互市貿易體現。
歷史上,除了緣邊貿易,與之相對應的,另一個較強貿易區則是政治中心貿易。
二、貿易中心區的流動性
在古代,政治中心也往往決定著經濟中心。因為經濟實力是政治實力的保障與基礎,所以一個政治中心通常也是經貿中心。但是,這一中心區也會隨著時代變遷而變化。草原貿易流動性的第二個表現正是這個貿易中心區的變動。它包括兩方面。
1.草原掌舵族群中心區域的流動。
雖然,草原游牧生活處于流動當中,但是這種流動性是具有相對性的。因為族群屬部都具有相對的勢力范圍,所以一般性的流動,也是處于一個相對的范圍內。同樣,掌控草原的政治中心區也是一個相對穩定區,如王庭所在地。這個王庭所在地,就是草原貿易中心區,或者說貿易集散地。貿易既有自覺自愿的,也有強迫非情愿的。后者最大表現就是,每年屬部定期向政治中心區王庭所交的實物與非實物賦稅。這是最高政治統治者的權力體現。當然,作為最高統治者,在獲得這些“賦稅”以及從其他區域或人群獲得財物后,除了自己享用與對外貿易外,也會相應的拿出一部分分配給屬下,但會有等級差異。這也是維護統治一個重要手段。這可視為是一種上、下的官方“貿易”。史書也多有記載,納賦稅的,如《史記·匈奴列傳》:“秋,馬肥,大會蹛林,課校人畜計。”[3](西漢)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59.(P2892)在屬部的上下關系中,也是如此,若《漢書·西域傳》云:“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須、尉黎間,賦稅諸國,取富給焉。”[3](西漢)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59.(P3874)若不能交賦稅的,就會受到懲罰。如《漢書·匈奴傳》載,烏桓需“與匈奴皮布稅。匈奴以故事遣使者責烏桓稅,匈奴人民婦女欲賈販者皆隨往焉。烏桓距曰:‘奉天子詔條,不當予匈奴稅。’匈奴使怒,收烏桓酋豪,縛到懸之。酋豪昆弟怒,共殺匈奴使及其官屬,收略婦女馬牛。單于聞之,遣使發左賢王兵入烏桓責殺使者,因攻擊之……頗殺人民,驅婦女弱小且千人去,置左地,告烏桓曰:‘持馬畜皮布來贖之。’烏桓見略者親屬二千余人持財畜往贖,匈奴受,留不遣”[3](西漢)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59.(P3820)。可見,匈奴對屬部烏桓的拒不交皮布稅與反叛行為是絕不能容忍的,不惜用武力逼其就范。當然,正常情況下,如前述最高統治者獲得相應財物后也會分配給部下。一個部落內部也實行這樣的操作。如《舊唐書》談及西域突騎施蘇祿時云:“有所克獲,盡分與將士及諸部落。”[4](后晉)劉昫等.舊唐書.中華書局,1975.(P6068)若一個首領不能很好執行向下分配,就會出現屬部離心離德,甚至是反叛的舉動,亦如上引同傳之內容:蘇祿“先既不為積貯,晚年抄掠所得者,留不分之……其下諸部,心始攜貳。有大首領莫賀達干、都摩度兩部落,最為強盛……莫賀達干勒兵夜攻蘇祿,殺之”[1](后晉)劉昫等.舊唐書.中華書局,1975.(P6068)。唐初突厥吉利可汗被眾叛親離,也有類似原因。這是造成政治統治解體的一個重要因素。一旦解體,草原政治中心區會相繼變化,貿易中心區也會出現變化。故結合歷代史書與歷史地圖冊來看,草原政治經濟貿易中心區,即王庭所在地,也會隨著人文變遷而處于一種變化當中。從長時段看,表現出的就是一種流動性。若東漢、三國時的單于庭比之西漢時期,就向西遷移了[2]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一冊13-14《西漢時期全國圖》、40-41《東漢時期全國圖》與第三冊3-4《三國時期全國圖》).地圖出版社,1982.,這是緣于匈奴實力的衰弱與東北鮮卑勢力的向西發展。與此同時,鮮卑也向南部發展,故而鮮卑庭也向南推進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北部草原最大兩個爭雄的族群掌舵者是柔然和高車,二者間的政治中心也在博弈中出現了大移動。突厥興起后,草原政治中心又掌控于它之手。突厥衰落后,回紇、契丹、女真、蒙古相繼崛起,使得草原政治經貿中心或者說貿易集散地,從縱向歷史角度來看,處于變動或者說流動當中。作為貿易交換的主要對象農耕區,也是如此。
2.農耕區政治中心的變動。
草原貿易一個支撐點源于農耕區物資,其中貢賜貿易是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貢賜貿易大部分發生在農耕區政治經濟中心,故這個中心的變動也體現著草原貿易的變動性。這個中心,最大體現者就是朝都,即一般意義上所說的京師。若東漢、三國曹魏京師所在地洛陽比之西漢京師長安就向東遷移了。這樣草原族群向南部的貢賜貿易也會在地點上發生轉移。而到魏晉南北朝,這一中心發生了分化,也意味著貢賜貿易的多向流動。若當時的柔然同北朝政治中心有貢賜貿易與南朝政治中心也有貢賜貿易。如《魏書·蠕蠕傳》云:延和三年二月“吳提遣其兄禿鹿傀及左右數百人來朝,獻馬二千匹,世祖大悅,班賜甚厚”[3](北齊)魏收.魏書.中華書局,1974.(P2294)。這是柔然與都城在平城時的北魏貢賜貿易。又如《宋書·文帝紀》云:“芮芮國遣使獻方物。”[4](南朝梁)沈約.宋書.中華書局,1974.(P89)這是柔然與南朝宋(建康)的貢賜貿易。當北魏孝文帝改革后,都城從平城遷移到了洛陽,也意味著政治經貿中心向南遷移了。無疑,貢賜貿易中心也會隨之南遷。
總的來說,在農耕區統一時期,貢賜貿易大多數是流向一個政治經濟中心,但是分裂時期,農牧貢賜貿易會發散性的向多個政治權力中心流動。
故無論是草原政治中心區,還是農耕政治中心區變動,都會帶動草原上、下貿易及與農耕區貿易的大流動。貿易中心在流動,同樣貿易輻射區也會流動。
三、貿易輻射區的流動性
貿易中心區周邊就是貿易輻射區,政治中心區周邊就是隸屬或者說屬部區。前后兩者一般來說,在古代是一一對應的。隨著人文群體力量的消長,政治經貿中心區會發生變動,其周邊的政治經濟輻射區,即下屬或者說屬部區也會發生變動。從長時段來看,這一相對中心區的貿易輻射區也處在一種流動性當中。這主要表現為這樣兩方面。
1.草原內部貿易東、西、南、北相向、相反流動。
這方面就是上文所點到的,每年政治輻射區屬部會向所屬汗庭納賦,其中包括各種各樣的土特物產。這一舉動,表現出的就是物資的“匯流”,或者說東、西、南、北屬部向汗庭貿易集散地中心原點匯聚物資的展現。物資體現的是相向流動。當然,作為最高統治者在接收到各種物資后,除了自用與對外貿易外,也會向屬下以饋贈方式,給予分配。這一行為,反映出的是物資的“回流”,或者說汗庭貿易集散地中心原點向周邊屬部散播物資之舉。這時的物資流動表現的是反向流動。這一“匯”一“回”就體現出了上、下的“貿易”往來。當然,其中的貿易不平衡,甚至是不平等是顯而易知的。但這也正體現了輻射區與中心區的政治、經濟地位之差異。但是,輻射區并不意味著是固定不變的。
2.草原內部勢力變遷所引起的輻射區變動。
如上所言,草原政治勢力的消長,會帶來政治中心區的變動。同樣,力量的消長博弈也會帶來輻射區的變動。一個最高政治中心,就是一個最大貿易集散地,如匈奴、突厥、契丹、女真、蒙古強盛時期,這樣周邊輻射區針對的是一個中心。但是當一個政治中心衰落時,屬部或者說原有輻射區力量就會逐漸變大,進而出現多個政治中心或者說貿易集散地。當多個政治中心在博弈時,輻射區也會發生巨大的變動,甚至有些小部落,或者說力量薄弱者,成為兩個政治中心區的輻射區,歷史上稱之為“兩屬之”。《史記·大宛列傳》云:康居“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1](西漢)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59.(P3161)這是典型的“兩屬”現象,是一個處于兩大政治勢力間小勢力的不得已之選擇。若東漢時,匈奴衰落,形成南北匈奴的格局,此時鮮卑、烏桓興起。三國至南北朝時,鮮卑南下,草原柔然、高車相繼興起。當柔然衰落時,其屬部突厥興起。當突厥衰落時,回紇、突騎施、葛邏祿又迭起。當回紇衰落時,契丹又大范圍興起。后繼女真、蒙古草原勢力,都有類似發展軌跡。故每個掌舵族群衰落時,也意味草原內部勢力的變遷,進而也引起了輻射區的變動。無疑,官方性的上、下貿易,在區域間也會發生重大的流動性變遷。同樣,貿易中心的輻射區變動也會帶動物品流向性變動。
綜上,草原生活的流動性是導致草原絲路貿易流動性的直接性因素,若把歷史變遷放入其中又增強了其時空維度中的變動性。而歷史變遷中人文群體政治勢力的變動性,使這一流動性充滿了更多變數。但是,不變的是多種形式的人文貿易或者說物產交流,無論是在草原游牧群體自身間,還是農牧間,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