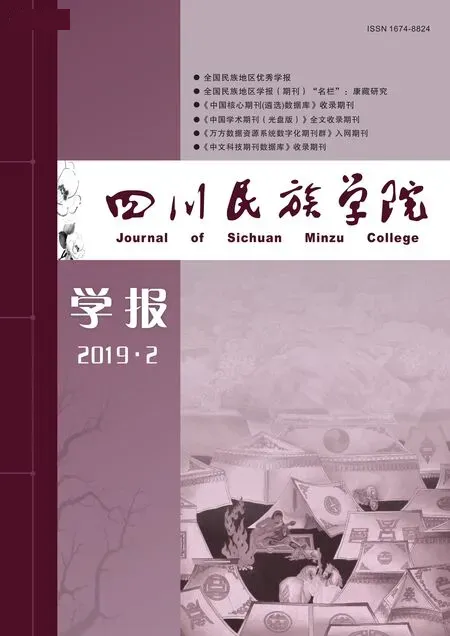儒家人文思想產生的內在理路
李汶陜
在人類的歷史長河中,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間曾出現過極其璀璨的文明,這一時期所產生的思想對后世帶來了重大影響。雅斯貝斯將這一時期稱之為“軸心時代”。雅斯貝斯曾指出:“人類一直靠軸心時代所產生的思考和創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飛躍都回顧這一時期,并被它重新點燃,自那以后,情況就是這樣,軸心期潛力的蘇醒和對軸心期潛力的回歸,或者說復興,總是提供了精神動力。”[1]依雅斯貝斯所言,軸心時代所帶來的文明對于后世的發展有著原動力的作用,比如文藝復興就是站在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帶來了新的具有創造力的文化的進步。
有學者認為,“軸心時代”是人類文明的一次“井噴式”的發展。它決定著一個民族的發展方向。在中國的“軸心時代”先后出現了孔子、老子、墨子等諸子百家。為何春秋時期會出現如此大的文化的綻放?主要是由于,一是禮壞樂崩,社會秩序混亂,有理想有抱負的知識分子開始思索社會發展的理想模式;二是西周時期人文主義的萌芽,人們開始關注世俗社會的發展以及人的發展;三是知識分子地位的逐漸提升,使得社會的精神層面不再由統治階層所把控。雅斯貝斯曾指出:“前軸心期文化,像巴比倫文化,埃及文化,印度河流域文化和中國土著文化,其本身可能十分宏大,但沒有顯示出某種覺醒的意識,古代文化的某種因素進入軸心期,并成為新開端的組成部分,只有這些因素才得以保存下來。”[1]那么在中國的前軸心期最為突出,轉變最為劇烈的應該是西周。
西周時期,人們逐漸將天命與道德相聯系,把政治與德行相掛鉤,注重祭祀帶來的心理層面的影響,形成完備的禮樂體系。儒家文化是我國傳統文化中的主流文化,對民族性格的養成、精神的培育都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西周時期的重要改革者周公是孔子一直所追尋的對象。孔子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述而》),自己只是追尋前人的腳步。余英時先生在《軸心突破和禮樂傳統》一文中曾指出,儒、墨、道三家都是突破了三代禮樂而興起的。所以,本文認為西周時期文化的轉變對于后來形成的儒家文化有很大的影響。本文將主要從巫的理性化、周朝的天命觀嬗變以及周禮的重構三個方面來闡述西周時期基本觀念與儒家文化之間的聯系。
一、巫的理性化
巫作為從古至今與人類始終相伴隨的文化,人們常常將它與“薩滿”“巫術”“迷信”“神秘”等詞語相聯系,一般被作為“陳腐”的迷信文化來對待。但在上世紀90年代,有學者提出不同的觀點,認為“中國上古思想史的最大秘密,是巫的特質在中國大傳統中以理性化的形式堅固保存、延續下來,形成中國思想的根本特色,成為了了解中國思想和文化的鑰匙所在。”[2]我們基于此點開始討論巫的理性化過程對于儒家人文主義形成的影響。
巫在殷商時期就有記錄,但巫的緣起應早于此時,甚至無法確定它的具體產生時期,馬林諾夫斯基曾指出:“巫術永遠沒有起源,永遠不是發明的編造的,一切巫術簡單地說都是存在的,古已有之的存在。”[3]《說文解字》中記載:“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褎舞形,與工同意。古者巫咸初作巫。”陳來曾指出:“‘無形’指神,‘褎’即袖。事無形即事神,此說以事神為巫主要功能。”[4]也有學者認為巫原為“舞”,鄭玄《詩譜》中記載:古代之巫實以歌舞為職。《公羊傳·隱公四年》何休注:“巫者,事鬼神禱解以治病請福者也。”認為巫與醫相通。因此,古代的巫是具有事神,以歌舞為職,與醫相通的多重角色。
首先,“絕地天通”將人神分離,人們開始更加關注世俗世界的生活。所謂“絕地天通”就是絕地民與天神溝通之道。在遠古社會時期,各部族之間或攻伐或聯盟,大大小小的部族有上萬之多。那時的人們主要通過巫與上天溝通,或祈求風調雨順或驅災驅病。有學者認為曾出現過一段民神同位的時期,即家家為巫。據說,自蚩尤作亂之后,三苗之民,風氣大壞,統治者依靠刑法來整治社會,一時間,人民苦不堪言,凡是遇到有無辜、不幸之事都要禱告“天”。為了不讓“天”被人間的“瑣事”所煩擾,開啟了“絕地天通”。
《國語·楚語下》中記載觀射父關于“絕地天通”的解釋:“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威嚴,神狎民則,不蠲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災禍存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恢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我們可以看到在遠古時期曾出現民神同位、民神雜糅混亂現象。有學者認為觀射父對于“絕地天通”的解釋是站在人文理性的立場上為中國宗教指出的一條道路,即如何處理人與神的關系。在《論語·雍也》篇中:“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春秋時期,孔子把“以神設教”作為“鬼神”的主要功能,對它的態度是“敬而遠之”。
“絕地天通”的開啟,是將地民與天神之間相隔離。從此人神分離,各司其業。與神溝通的能力逐漸成為統治者的專享。他不僅是國家的領袖也是巫的首領。“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墨子·兼愛下》)當出現天災時,作為國家最大的巫要親自向天禱告,承認自己所犯的過失,以祈求風調雨順。統治者將神權與政權掌握在自己手中,并出現將道德與民心作為統治的依據的傾向,這無疑是人文主義的發展。
其次,《周易》的形成使得人們的認識由具體經驗提升到普遍概念。人們對于《周易》的理解通常是占筮之書。《周易》包括《易經》和《易傳》,相傳,《易經》為周文王所作,由卦、爻演變為64卦和384爻,以“陰陽”轉化為內容,并對萬物進行性狀歸類;《易傳》由孔子所作,是對于卦辭和爻辭的解釋。并將其配于相應卦之后形成《周易》(文中所指《周易》均為《易經》)。《易》有三本,包括《連山》《歸藏》和《周易》,其中前兩本已經失傳。
巫作為人間與神溝通的特殊身份者,自有獨特的一套方法。人們常常將薩滿與巫混為一談,認為兩者為一物,都是通過跳舞、特殊的感受、神的附體來表達神意。當然這些大多數情況都是為了驅災辟邪。在一般的選擇中,則是由占卜來表達神意。常見的占卜方式有獸骨占卜、龜甲占卜和蓍草占卜。無論哪種占卜,人們都需要占卜得出的一些現象,根據《周易》上的記載進行解釋。在夏商周三代時期,占卜行為已經是具有一定的規則。有學者推測占卜的行為應該在這之前就有,到夏商周三代逐漸形成體系。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述而》)這是孔子對于《周易》的高度評價。孔子為何為《易經》作注?陳來曾指出:“《周易》是以數為基礎,這使得擺脫神鬼觀念而向某種宇宙法則轉化成為可能,這雖然不見得是始作《周易》者的意愿,但卻是人文化過程得以實現的內在根據。”[4]這也就是說《周易》具有內在轉化的潛質,孔子正是看到了《周易》的這種特質,才開始為《周易》作注,當然孔子的根本目的仍是“托古御今”,通過古典的研究、注釋,賦予其新的內涵。《周易》以陰陽變化為內容,打破了長久以來人們對于具體事物的具體經驗的認識。正是它存在這種陰陽變化的內容,使得孔子有把它轉向具有人文性的可能性。
最后,西周時期的祭祀和鬼神觀念的轉變。西周的祭祀對象包括:天神、地袛、人鬼。祭祀原本是由巫覡文化發展而來,到西周初已經形成一套完整的祭祀體系。祭祀的行為也由驅病驅災、占卜問天,轉變為具有更多人文意義上的祭祀。在《祭神》中記載:“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御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此皆功烈于民者也。”把有功于人民的人列為可以祭祀的對象,這無疑是將人民地位的逐漸提升,突出了民本思想。
海鳥曰“爰居”,止于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文仲之為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為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國語》)陳來指出:“展禽所說,參以《禮記》,不但突出了先祖先王人世功德的一面,而且這種功德祭祀已多少帶有紀念性的意味,而非純粹的宗教性祭享祈福,這顯然是文化理性化過程的產物。周代以后祖先祭祀越來越突出并且社會化,其主要功能為維系族群團結,其信仰的意義逐漸淡化。”[4]在《國語·楚語下》中,觀射父對于上古祭祀行為解釋道:“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其中我們可以看出祭祀的作用在于展示孝道,以安撫百姓,穩定國家。
《禮記·祭法》中記載說:“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對于祭祀和鬼神的觀念,西周時期已經發生轉變,在“絕地天通”之后,“天”已屬于統治階層的權力來源的手段,而對于祖先的祭祀,其主要的功能也是維系族群的團結。“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春秋時期,孔子對于“鬼神”的觀念是“敬而遠之”不去討論。“未知生,焉知死”更多的是對于現世生活的關注。祭祀和鬼神在孔子那里也成為為現世世界服務的對象,通過“以神設教”對百姓進行教化,以達到安穩現世生活的作用。
巫作為遠古時期與神溝通的代表者,其不僅具有一定的權力,而且也是當時人群中具有一定知識的人。從“家家為巫”到“絕地天通”是將權力集中、團結和鞏固社群的表現。具有一定知識的巫,在殷商時期就已具有巫史的身份即既是與神溝通的人又是記載其占卜的人。因此《周易》的產生不能僅僅作為一本占筮之書,其文化的轉變更為深刻。巫通常用舞蹈、唱歌等形式做為祈禱上天或與神溝通的方式之一。他們往往有固定的特殊的形式。王是巫的首領,最大的巫,王將神權與政權相結合掌握在自己手中。巫的祭祀行為逐漸演變成一種具有文化功能的禮樂系統。由此,巫由作為企圖控制天的非理性行為內化為具有一定文化功能的禮樂系統即由非理性向理性的逐漸轉變。
二、周朝天命觀的嬗變
在早期先民,對天的認識往往形成了一個民族的宗教信仰。在“軸心時代”,以色列的“先知”通過與神的交流,傳達著平和、忍耐的信念,這對于以色列民族的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在中國,人們從對自然宗教的信仰逐漸轉變為倫理宗教,這就意味著人文主義在中國文化中的一大發展。殷商時期,人們對于天的觀念仍是“先王有服,克謹天命。罔知天之斷命。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盤庚》),認為“天”授予人間王朝的政治權力和政治壽命。到文王時期,對于“天”有了新的解釋,在《牧誓》中有:“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一個王朝的生存與否不再是由“天”賦予其權力的直接決定,而是要依靠統治者的德行。對于“天”的信仰發生了微妙的轉變,使得人文主義開始逐漸登上思想史的舞臺。
周公作為西周時期統治階層的精英知識分子,他所做的一系列改革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中大部分思想體現在周公攝政時期所作的三誥之中。無論是出于政治的需要,還是個人理性的自覺發展,他主要思想表現在提出“天命靡常”和“敬德保民”,將統治者的合法性問題歸于德行之上,并將統治階層注重個人的德行發展為德政的現實性問題之上。周公所作的改革產生的影響對于后期儒家的發展,尤其是對于儒家創始人孔子的影響是無可比擬的。
首先,“天命靡常”(《大雅·文王》)的提出。《康誥》:“惟命不于常。”《君奭》:“又曰:天不可信。”殷商時期人們對于天的觀念還停留在統治者只是天在人間的代理人,天具有決定一個王朝的統治壽命的神秘權力。到西周時期,則轉變為“天”是變化無常的,甚至是不可信任的。這種對于“天”觀念的轉變奠定了中國幾千年的天命觀思想。 從“孔子不語怪,力,亂,神”(《論語·述而》)一部分人對于“鬼神”避而不談的態度,可以看出春秋時期對于“神”的信仰已經不具有十足的信任。
三代時期,商滅夏,殷滅周,其打的旗號均是“天命”所致。《尚書·湯誓》:“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牧誓》:“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在連續的王朝更替之后,周朝的合法性問題以及周朝如何才能在歷史的行進當中避免被其他王朝所代替,這或許是周公思想發生的關鍵點,是對于王朝更替的憂患意識。
“天命靡常”提出對“天”不再完全的依賴,確實具有進步意義。人們將更多的關注點放在世俗社會之中,既然“天”不再是完全可靠的,那么什么將成為統治者依存的支點呢?由此,發展出對于統治者德性的要求,以及對于民的關注。
其次,重民思想的產生。“天命靡常”作為基本的認識點,周公希望統治者認識到“民”的重要性。在《召誥》中記載:“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吁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百姓抱著妻兒哀告上天,上天哀憐百姓,將治理人世的大命轉移給周人。這體現了“天命”依據民意,強調了人民民意對于王朝統治的重要性。
《泰誓》:“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泰誓》:“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上天”的懲罰會根據人民的民意。隨著“民”的地位的提升,“天”的地位逐漸下降。《無逸》:“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從對“民”的關注逐漸增加到對“民事”的關注,對于世俗世界的關注。
重民思想的產生,無疑是將關注點落實在現世社會,這就不同于西方國家對于“神”的強烈的依賴。從對“民”的關注,對“民事”的關注逐漸發展出對于統治者的要求,需進行“德政”。
最后,德政觀念的出現。在討伐商紂王的《牧誓》中就有指出,商紂王無德,武王天命所受。在《召誥》中:“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可以看出“德”對于一個王朝的重要性。
武王死后,因成王年幼,由周公攝政。而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本是受命監視商人,卻在周公攝政后勾結武庚叛亂。由此發生了三監之亂。周公出兵用了三年時間平定叛亂。這期間周公的天命觀逐漸形成。在《康誥》中有強調:“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體現了民本思想。《康誥》:“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有身,不廢在王命。”這里就將天命與道德相聯系。在《康誥》中提出:“惟命不于常。”天命是變化不定的,因此統治者要依靠自己的德行去治理天下。
《召誥》中說:“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這里是說皇天收回了對于殷的受命,而讓周王作其長子。周王得到了治理天下的大命,幸福與憂患與之俱來。君權神授的思想一直作為統治者證明其政權合法性的有力依據。所以,他們仍然相信天命。但是需要解釋如何防止天命未來由姬周轉向他姓,這就要依靠“德政”來實現。
西周時期所形成的天命觀,對于人民認識世界的態度帶來極大的轉變,對于儒家后來形成的人文主義精神和“德政”觀念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從“天命靡常”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把“民”的地位逐漸提升,也形成了具有倫理道德意味的“德政”思想。將倫理與政治相聯系,弱化了“神”的權威,將人們的關注點引向世俗社會,引向對人本身的關注。
三、周禮的重構
儒的職業雖早有存在,但是儒家真正的起始應在孔子思想的形成。因此孔子之前并無儒家文化,孔子及其弟子組成儒家,并以孔子的思想體系作為最初儒家的思想體系。孔子自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其一生最為推崇的便是“周禮”。孔子名為推行“禮樂制度”,實則“托古改制”,以期達到“大同”社會的理想。西周時期所構建的宗法血緣關系的等級制度以及相配合的禮樂制度,使得西周在一段時期內社會秩序井然。西周經過變革帶來的人文的轉向對于孔子人文主義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甚至在整個中國思想中對于“天”“神”等概念的認識都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中國思想中以人為本突出人的重要性以及更關注于世俗社會的表現不同于西方世界對于“上帝”“彼岸世界”的理解。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以儒家文化為主流,儒家文化決定著中國人的大部分思想觀念。儒家文化的起源應追述到西周時期人文的轉向,這并不能說明中國文化的源頭唯有西周文化。而是說,中國文化經歷了很長時間的積累到西周時期或因為政治的變革或因為歷史發展的必然性等原因通過一系列改革完善了長久以來形成的文化體系,并帶來了人文意識的轉向。
西周時期經過一系列的改革,產生了“敬德保民”“明德慎罰”的思想,形成了與宗法等級制度相配合的禮樂體系。由祭祀的禮儀制度以及社會中的禮儀規范發展而來的禮樂體系,規定了社會等級,規范化了人們的日常生活的行為,鞏固了社會組織,穩定了社會秩序。同時,起到了教化百姓的作用。當然,最重要的是通過禮樂制度讓人們形成具有感性認同的共同的心理情感。這對于形成國家意識、民族意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禮樂制度鞏固了社會等級制度。西周初期,對于剛經過大戰的周族如何管理國家,如何避免重蹈商朝的覆轍,充滿了憂患意識。西周通過分封建國的方式,希望建立起以血緣為紐帶的分封國家,通過禮樂制度確立起等級分明的社會制度。從橫向和縱向兩個方向組織成具有網狀的、嚴密的、有彈性的國家形式。
祭祀的禮儀以及社會中的禮儀規范經過周公的系統化形成周朝的禮樂制度。這套禮樂制度具有嚴格的等級劃分,祭祀的人員安排、場地大小,用的音樂等都與其身份地位有關。人們按照自己的等級執行相應的禮,這是合乎規矩的。禮的等級代表了一種身份。在《論語·八佾篇》中記載: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按照周禮規定天子用八侑,卿大夫用四侑,士用二侑。季氏是正卿,只能用四佾,他卻用八佾。孔子對于這種破壞周禮等級的僭越行為極為不滿。天子有天子的禮,卿有卿的禮,各在其位,各行其禮。
這套禮不僅用于朝廷,還延伸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家庭是這個社會中一個普遍而又極為重要的場合。在家庭中也有等級秩序,父要行為父禮,子要行為子禮,男行男子的禮,女行女子的禮。從家庭到社會,各行其禮,秩序井然。從一方面來說,它形成了尊尊、親親的傳統;另一面,從家庭到社會都是上下有序,鞏固了社會等級制度,維護了社會的穩定。
禮樂制度對于西周建立一個統一穩固的國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同時在西周形成的具有完備系統的禮樂制度,到了春秋時期,孔子將其發展為具有人文主義內涵的一套禮樂文化,道德仁義成為其主要的內容。
其次,禮樂制度具有教化百姓的作用。《國語·周語》中記載:“古者先王即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于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諸侯春秋受職于王以臨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庶人、共、商各守其業以共其上。猶恐其有墜失也,古為車服、族章以旌之,為贄幣、瑞節以鎮之,為班爵遺踐以列之,以聞嘉譽以聲之。”由此可以看出統治者的主要目的是用禮樂制度來教化百姓。
禮要求對于長輩,兄弟的規范行為,要求男女有別,這是道德的教化。將道德與禮相結合,禮就成為規范人們行為的一套外在的行為標準。有子曰:“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人之本與!”(《論語·學而》)禮成為道德與政治的紐帶。
禮樂制度與道德相結合形成一套具有人文主義的現世的規范體系,在關注人的同時,更強調其內心的真摯的情感,逐漸轉變為具有個人內修的行為,這形成了中國不同于西方世界的“他律”宗教的“自律”行為。人人心中自有法典。
最后,禮樂制度具有建立共同心理情感的作用。孔子時期已將仁寓于禮之中,對待父母、兄弟、姊妹,要行其禮,更重要的事行禮時要具有內在真摯的情感。禮樂與道德相聯系,人們愿意主動的遵循禮,維護社會的穩定,國家的統治。
對于鬼神的祭祀也是同樣的,在特定的時間特定的場合,經過一定的禮儀,人們相聚在一起,由統治者代表世俗世界的人去向“鬼神”禱告,形成了嚴肅、獨特的氛圍,日久天長,逐漸成為人們內心某種共同的心理情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谷既沒,新谷既升,鉆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天稻,衣夫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愛于父母乎!”(《論語·陽貨》)李澤厚指出:“孔子把‘三年之喪’的傳統禮制,直接歸結為親子之愛的生活情理,把‘禮’的基礎直接訴之于心理依靠。這樣,既把整套‘禮’的血緣實質規定為‘孝悌’,又把‘孝悌’建筑在日常親子之愛上,這就把‘禮’以及‘儀’從外在的規范約束解說成人心的內在要求,把原來的僵硬的強制規定,提升為生活的自覺理念。”[5]禮經過孔子的重新詮釋成為具有內在依據,人們自覺向往的行為規范。
禮樂制度從祭祀的儀禮逐漸走向具有人文主義的豐富內涵。祭祀禮儀經周公的重新整合形成了具有規范社會行為,穩固社會秩序的作用。其內在已經具有了培養人文主義的土壤,再經由孔子的重新詮釋,道德與禮相結合,形成了中國特有的禮樂制度文化。共同的心理情感的培養對于一個民族的文化認同、民族認同、國家認同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西周時期作為中國傳統天人關系改變發生的第一站,其產生的影響和意義不同凡響。對于形成中國倫理道德的政治體制,儒家人文主義的思想,都起到了基礎作用。這對于一個民族而言是具有方向性的改革。西周的文化同樣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是經過了歷史的積累,在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前提下,實現了人文的轉向。儒家思想作為中國文化的主干,其形成的倫理道德的文化體系成為了中國的文化基因。我們對儒家的人文主義思想起源的探析旨在對于文化傳承的連續性,尋找其發生的多重因素,將其系統的展現出來,從而為文化的復興與振興汲取營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