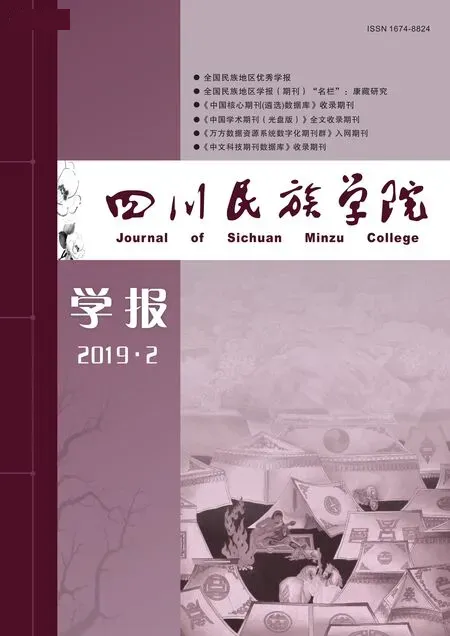吐蕃時期康區“丹域”之名的由來及歷史文化之談
更藏卓瑪 吉加本
公元七世紀贊普松贊干布對內制定了《赤則本謝之法》為根本法的各項法律制度,劃分了以“告與雍”為主的等級制,進一步建立健全了吐蕃的軍政制度;對外用武力擴張其勢力,康區的昌都和丹域在這一時期歸為吐蕃屬地。這一歷史我們可以在《德烏宗教源流》和敦煌古藏文文獻資料中可見。而文中重點講解的“丹域”在吐蕃時期是唐蕃古道上唐蕃使者的必經之地和佛教的主要傳播地,更是吐蕃時期青稞的重要產地,素有“青稞寶庫”之稱。
一、“丹域”之名的由來
由于文獻資料的欠缺,目前還難于對“丹域”之名的由來作出系統的介紹,只能引用零散資料探究其大致情況。吐蕃時期,“丹”名的寫法在古藏文文獻中記為“mdan”,而在其他歷史文獻中記有“vdan”或“ldan”。根據諸多文獻的記載“vdan ma”的叫法極為廣泛,其vdan ma實際上為ldan ma的多音詞。丹域一般指原甘孜州鄧柯一帶,鄧柯一帶在古藏語中被稱作“vdan khog”“vdan ma”。按藏族古代先民對地名命名的習俗,“丹域”之名的由來可能與歷史上“丹瑪”姓氏的部落長期統治該地而其部落名冠為地名有關,相傳石渠鄧柯一帶是嶺國隸屬的丹瑪部落12萬戶的主體所在地,是格薩爾王未成王前征服的“丹瑪青稞宗”地方。另外,有文獻記載吐蕃赤松德贊時期的文職大將兼譯師丹瑪·澤芒和格薩爾王三十員大將中的擦香丹瑪相察均誕生于此地。依此筆者認為丹域之名可能以“丹瑪”部落的統治而得名。
根據今天的行政區域的劃分,鄧柯隸屬于石渠縣。然而,據“丹瑪十二萬戶部落”的記載,在古代丹域所在范圍極其廣泛,即青海玉樹囊謙縣、西藏昌都江達縣、四川甘孜石渠及德格縣均屬于丹域,史稱“上丹瑪”“下丹瑪”,其地理位置大致是金沙江西邊為上丹瑪,金沙江東邊為下丹瑪。正如《吐蕃地名研究》所示,丹域“分為上丹瑪和下丹瑪兩部。以金沙江為界,江西為上丹瑪(西鄧柯),江東為下丹瑪(東鄧柯),上丹瑪現屬于西藏自治區昌都地區江達縣,下丹瑪為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縣洛須鄉及德格縣俄支、俄南、阿須鄉等地。”[1]
二、丹域境內的唐蕃古道走向
吐蕃時期為了與周邊邦國的交流聯系,常派遣使者,同時也為文化經濟交流的需要開拓了諸多大小各異的古道,其中青藏高原的唐蕃古道最為重要。文獻記載唐蕃古道是當時驛站相連、使臣仆仆、商家云集的交通大道,比如“籠區(slungs)”“籠館(slungs bon)”等相關名詞在敦煌吐蕃文獻中的反復出現,不僅證實了唐蕃古道上建有驛站,同時也能證實有驛站管理者職務一事。
唐蕃古道橫貫我國西部,聯通我國西南,是唐代以來中原內地去往西藏、四川、青海三省區乃至印度、尼泊爾等國的必經之路,其功能遠超于道路本身。它不僅是和親納貢、貿易交流的官驛大道,更起著維系唐蕃和盟、加深民族友好的紐帶作用,故有“千年平安道”“黃金路”“文化運河”之美譽。其路線始于唐朝國都長安,途經甘肅臨夏、青海樂都,此路線為東段;從青海省西寧經共和縣、興海縣、貴南縣、同德縣、瑪沁縣、甘德縣、達日縣,進入今四川境內色須(石渠縣)再到青海玉樹結古鎮、囊謙縣,進入西藏境內烏齊縣、丁青縣、巴青縣、索縣到那曲地區再經過當雄縣到達邏些(今拉薩),此路線為西段。
史籍所載松贊干布沿著唐蕃古道討伐唐朝與吐谷渾,文成公主沿著此路入藏的歷史雖過一千多年但至今仍稱為佳話。近年來學術界對唐蕃古道的路線爭議不斷,但是鄧柯的所屬地色須(石渠縣)是唐蕃古道上的必經之路一事已成為學術界的共識,正如石碩教授所言“由川藏道北部支線經原鄧柯縣通向青海玉樹、西寧乃至旁通洮州(臨潭)的支線。”[2]1980年旅居德國的格西白瑪次仁首次在石渠縣鄧柯(今洛須鎮)發現了吐蕃時期的摩崖石刻及造像,并用德文對這一石刻進行了介紹。隨后英國藏學家黎吉生和瑞士籍藏學家艾米·海勒對石刻的銘文、造像進行了相關討論,這些相關文章只涉及了摩崖石刻的部分內容,而2012-2013年在同一個地方發現的另外幾處摩崖石刻,為研究丹域的歷史文化方面提供了更有利的文獻資料。2016年7月來自各地的專家學者齊聚于石渠縣對摩崖石刻進行實地考察,印證了石渠縣是唐蕃古道上的重要樞紐。同時在雅礱江周邊發現的摩崖石刻和造像,證明了雅礱江流域也有唐蕃古道的路線,這一發現對唐蕃歷史和這一區域的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線索,具有很高的文獻和學術研究價值。
鄧柯的摩崖石刻和造像被當地人稱之為“照阿拉姆”,依據專家學者對石刻造像的研究分析發現皆為赤松德贊時期。除照阿拉姆的遺址之外,在洛須村、更沙村和煙角村等地相繼發現了吐蕃時期的石刻,以上發現的四個地點統稱為雅礱江的洛須鎮石刻群。除此之外,在雅礱江流域的長沙干馬鄉須巴神山山腳處也發現了當時的幾種石刻造像,“按時間推斷這些石刻造像有些于赤松德贊在位期,公元755-796年所刻,另外有些是在之后的赤德松贊和赤熱巴巾在位時期所刻,大約在公元800-840年左右。”[3]洛須鎮石刻群和長沙干馬鄉須巴神山石刻造像的發現,足以證明鄧柯是途經衛藏與朵康、吐蕃與唐朝的一個重要渡口。此外,仁達摩崖題刻中記載,“益西央在岳(yol)、隆(klong)、奔(vbom)、勒(led)、堡烏(v bovu)等地亦廣為造刻。”[4]贊普赤德松贊繼位后,為平息邊界爭端、推動唐蕃和盟,利用高僧益西央在唐蕃邊界的影響,詔令高僧益西央擔負起和盟與興佛的使命,益西央遵照贊普的詔令率領他的和盟、興佛團體前往唐朝完成唐蕃和盟的職責,途中經過岳、隆、奔、勒等地并沿途大量鑿刻佛像、經文來傳佛弘法。其中石刻中出現的隆(klong),實則為松贊干布在康區修建的鎮邊寺之康龍塘卓瑪拉康,所在地為今石渠縣洛須鎮(原鄧柯),現今也被稱之為康龍塘;岳(yol)、奔(vbom)依據史料認為是康巴地區地名的統稱,其中的岳的具體位置,青海民族大學教授葉拉太先生根據都松茫布杰與南詔的結盟歷史認為在“四川省甘孜州南邊[1]”,但是具體的所在地卻未說明。亦據《敦煌古文獻》公元703年岳地召集會議并在此年贊普都松芒布杰在南詔逝世,以及漢文史料中記載的岳對吐蕃統治南詔之事有關聯的文獻,認為岳(yol)有可能是芒康縣扎玉(brk yol)地方其真實性有待考證。奔(vbom)的地理位置有學者認為是玉樹貝考(奔考),藏學家唃嘶扎西才讓認為是“芒康縣下方的幫達(spom mdv)鄉”。[5]據唃嘶扎西才讓的觀點及藏漢史料記載進行比較,筆者認為“奔”為芒康縣幫達之地,因幫達是奔的讀音變化而得來的,在古藏文中pa和ba字可以變換使用,由此出現了bom字寫成pom而出pom字讀音,根據藏文語法的規律bom字前加v字而讀作abom音。而石刻中出現的堡烏(v bovu)之地因資料欠缺難以斷定其具體的地理位置。
綜上所述,發現鄧柯在地理交通上處在特殊位置之外,它在吐蕃對外擴張以及吐蕃與各地交往中發揮著極為重要的紐帶作用。依據仁達摩崖題刻中記載的高僧益西央在鄧柯隆(klong)、芒康奔(vbom)等地鑿刻佛像和經文的遺跡,可以看出,在昌都仁達至石渠鄧柯、芒康等地也有唐蕃古道的路線。此外,吐蕃時期通過此古道在丹域建立了商貿交流地“下集市”以及傳佛弘法的佛教寺院,亦有史料記載元朝大臣多達納布途經石渠鄧柯進入西藏拉薩。可見丹域在地理位置上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三、佛教在丹域地區的傳播與歷史名人
丹域在許多后弘期文獻里寫作ldan yul,松贊干布時期此地稱為康龍塘,同時修建了康龍塘卓瑪拉康。根據文獻記載,康龍塘卓瑪拉康的建立標志著佛教在丹域的初期傳播。公元八世紀中期赤松德贊組織建立了桑耶寺,由印度高僧寂護和蓮花生大師主持開光,寂護大師擔任寺院堪布,七名吐蕃貴族青年剃度出家,出現了首批藏族僧人,史稱“七覺士”。同時邀請唐朝的禪定大師曼和尚和印度的寂護大師等高僧大德來翻譯佛經,從而佛教在藏區的傳播弘揚達到了鼎盛。而佛教在丹域傳播時我們不得不說的一個歷史人物,那就是高僧益西央,《蓮花遺教》中介紹當時翻譯大師時以“撥·益西央、阿雜爾·益西央”之名把高僧益西央名列吐蕃128位譯師之列。另據“譯師丹瑪澤芒、南喀寧布、以巴廓·益西央”、“比丘大譯師益西央”等稱謂的出現能夠確定其譯師的身份,且等級屬高級譯師類。據《蓮花遺教》載“丹瑪澤芒、南喀寧布、益西央翻譯醫學典籍138部左右。”[6]再據《娘氏宗教源流》載“蓮花生大師、毗盧遮那、南喀寧布、巴益西央等人翻譯了大量的密宗修法和佛教護法神的修法。”[7]綜合上述文獻不僅能探究其譯師的身份,還可以看出益西央參與了多部續部和密宗典籍的翻譯工作。而佛教在丹域的傳播發展過程中,益西央究竟起著怎樣的作用?據法藏敦煌卷子P.T996所載,益西央“在50余歲之前,修持于無往無分別之境,信解無住之要義,領悟諸了義經典之義,順隨眾善知識之經教、秘訣及自性修持,了悟天竺、漢地及藏地禪定實修者之經教、秘訣、要義及大乘經藏之真實說教,以達究竟。”[8]說明了益西央兼通藏、漢、梵三種文字及主修禪宗思想亦修大乘佛教,據以上引言中益西央的宗教思想,再結合赤松德贊時期“頓漸僧諍”中禪宗一派的失利之史,不難發現其所修教法與贊普大力扶持的佛教思想相悖,導致他遠離吐蕃政治中心遠赴朵康,同時也促成了在康區傳教弘法之使命。根據諸多文獻記載吐蕃贊普赤德松贊時期高僧益西央遵從贊普詔命率領和盟、興佛團隊在唐蕃古道沿線的昌都、鄧柯等地鑿刻大量佛像和經文,其興佛和盟工程延伸到唐蕃古道和絲綢之路交接點,他們所經之路不但對唐蕃古道的開拓起到了重要作用,對佛教在丹域地區的傳播發展同樣起到了促進作用。另外一個歷史人物則是赤松德贊時期九大譯師之一的大譯師毗盧遮那,據史料記載毗盧遮那從印度學習密乘經典返藏后,遭到苯教徒及學習顯宗的印度高僧的反對,贊普迫于壓力將其流放到康區察瓦龍,即今芒康、鹽井以西怒江河谷一帶。據《青史》所載“尼峨生根所著的《秘密藏續釋》,這一釋論是由譯師毗盧遮那在窩都吐杰降欽寺中譯出[9]”,“窩都應為窩額(vog tngo)之訛,其地即昌都擦雅境內。”[10]依上引言可以印證毗盧遮那在康區傳佛弘法的蹤跡。而窩都吐杰降欽寺,據“在多康建立龍塘度母殿和窩如(額)強彌勒寺”[11]所言,即指擦雅香堆的強康大殿(彌勒佛寺),與仁達佛堂、康龍塘卓瑪拉康被認為是吐蕃早期在康區修建的三座鎮邊寺院。毗盧遮那因長期在鄧柯周圍的昌都察雅地區興佛傳教而得名為“康祿巴”。探究竟不難發現其流放促成了他向康區傳教弘法的契機。最后,不得不談的是公元11世紀的覺吾賽增和菩提伽耶摩訶大師,兩位大師因在鄧科修建講經院而揚名衛藏地區,使得窩拉貝西繞、仲頓巴等人前往朵康鄧科地區拜覺吾賽增大師為師。依據上述文獻所記可以看出,丹域即鄧柯一帶對佛教在康區傳播發展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紐帶作用。
四、吐蕃時期在鄧柯建立的“下集市”
鄧柯地處石渠縣南邊,在西藏、青海及四川三省區的交界處,平均海拔3000米左右,其地理面積為428.7平方公里。1978年撤銷鄧柯縣,將原轄區鄉鎮分別劃入石渠、德格兩縣。據史料記載該地地勢開闊、氣候溫暖、水資源豐富,為農業、畜牧業的發展提供了優越的生態條件,適宜農業、畜牧業的發展。
吐蕃時期,藏區分上、中、下三部區域并建有諸多的集市區。據《德烏宗教源流》所載“噶邏祿、絨絨、丹瑪稱下集市三區。”[11]其中丹瑪(即丹域)是當時為了康區經濟的發展而建立的重要的商貿區。根據史料、傳說“青稞和絲綢”是丹瑪地區的主要產物,而青稞作為主要產物之史可依據格薩爾文獻發現其重要性,“嶺國大將丹瑪原是丹瑪部落之人,年幼時被丹瑪薩賀爾王驅逐到嶺國。丹瑪十歲時,要求丹瑪薩江王子歸還他應得的屬地屬民以及財物,王子不允,兩國(嶺國和丹瑪部落)遂發生戰爭。薩江戰死,丹瑪青稞宗歸屬于嶺國,丹瑪成嶺國之臣,兼領丹瑪部落。丹嶺之戰發生在格薩爾年幼未稱王之前。”[12]而青稞在丹瑪有悠久的種植歷史,是當地主要的經濟來源之一,所以青稞成為“丹嶺之戰”中嶺國獲取的最重要的戰利品,丹瑪也被稱為嶺國格薩爾王的糧倉。依此青稞可以看作是丹瑪(鄧柯一帶)的特產,鄧柯也可以看作是康區青稞的主要產地。至今,在藏區有許多青稞種子來歷的神話傳說,也有青稞栽培的悠久歷史的傳說,青稞制作的糌粑更是千百年來藏族人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主食。亦據吐蕃時期“漢地面、突厥玉、吐谷渾刀、丹瑪絲綢、蘭鹽稱為吐蕃五商”[11]的史料,發現丹瑪地區除青稞之外還有以絲綢作為交換的商品。赤德祖贊時期瓜州城(今甘肅臨夏)是商品交流的一個重要區域,“唐廷從”兌巧(上方)“取來的眾多寶物,原先儲存在瓜州城,吐蕃攻占后將其全部接收,上層仕人因之得到許多財寶,屬民黔首也普遍獲得上好唐絹。”[13]而此段史料中記載的上好唐絹是否為丹瑪絲綢或從丹瑪地區傳至衛藏地區值得探究。另外,鄧柯作為唐蕃古道上一個主要的交通要道,從唐朝運往吐蕃的絲綢大致要途經此地,因此顧名思義“丹瑪絲綢貿易”之名的來源是否與此有關?有史料記載在康區東邊有一條從打折多(今四川康定)到道孚、爐霍、德格的古道路線,根據這個路線以及當時吐蕃與印度之間有絲綢貿易來往的歷史,認為“打折多(drrtsemdo)”這一地名可能以絲綢交易而產生,因打折(drrtse)在藏語中是絲綢品質優良之意,但由于資料的欠缺而無法考證。然而丹瑪所在地的鄧柯一帶有商貿交流區是毋庸置疑的,如《敦煌古藏文文獻》記有公元678年都桑芒布杰“季冬,在于簞召開。對熱桑王崩日葉日庸與庫·赤聶主松降罪。”[13]其降罪之地在于簞即丹域降罪之因很有可能與丹瑪的青稞和絲綢貿易的虧損有關,因降罪的熱桑王崩日葉日庸是芒松芒贊時期贊普任命的農作物交易大臣,如“熱桑王之相仍達爾夏作大宗農作物交易。”[13]。依據上述文獻發現丹瑪一帶在公元7世紀左右是唐蕃、吐蕃與其他地方商貿交往的重要渡口,是吐蕃贊普在康區一個重要的經濟源地,是吐蕃時期建立的下集市三區之一,至今也有與此有關的昌拖(khromthok)、崇格(khromdge)等以古代“khrom(集市)”為命名的地方,根據“丹瑪絲綢貿易和丹瑪青稞宗”的史料,從古代起青稞和絲綢可以堪稱是丹瑪一帶的主要特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這一帶人們主要的經濟來源。
結 語
通過對格薩爾文獻、敦煌古藏文文獻資料的分析研究,再結合相關的神話傳說,丹瑪即丹域,位于金沙江流域,橫貫于西藏、四川、青海三省區。在吐蕃時期,此地是唐蕃使者的必經之地,是商家貿易往來的交易區,更是唐蕃使者在康區傳教興佛的佛教重地。根據文獻的研究分析發現,丹瑪即丹域不僅地理范圍廣泛,而且也是吐蕃贊普的一個重要經濟源地,隨名出現的丹瑪絲綢貿易、丹瑪青稞宗、丹瑪下街市,更能體現出吐蕃時期此地是唐蕃文化、經濟交流的重要渡口。高僧益西央、毗盧遮那、覺吾賽增和菩提伽耶摩訶大師等高僧大德相繼在此地修建講經院、翻譯佛經、鑿刻佛像經文等興佛傳教工程的延伸,充分體現了丹域是吐蕃時期佛教傳入康區重要的交通要道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