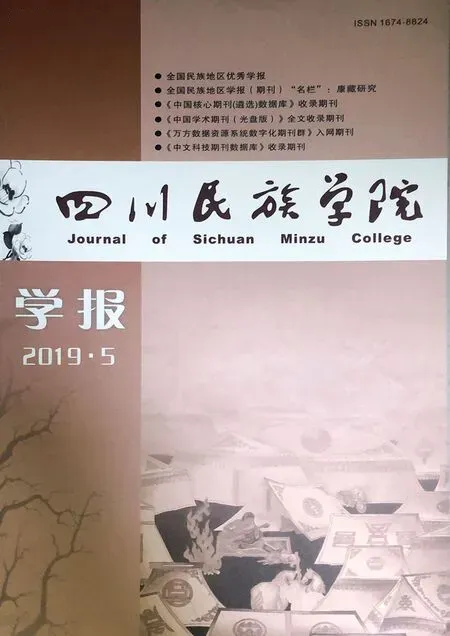圖像儀式下瑤族婚禮的展演、想象與文化
——以廣西全州縣蕉江瑤族鄉界頂村為例
胡 媛
從海德格爾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提出的“世界成為一副圖像”的斷言到九十年代美國視覺文化學家米切爾及德國藝術史學家波姆不約而同提出的“圖像轉向”,開啟了圖像研究的新時代;但目前為止,學術界仍然缺少從民族志的研究視角對儀式和想象構建化的過程性的相關研究。事實上,以圖像敘事來考察儀式運作和想象構建化的過程,更能表達圖像儀式的能指是什么。
一、儀式展演:圖像敘事的民族志書寫
廣西全州蕉江瑤族鄉,東鄰灌陽縣、西南與興安縣漠川鄉交界,北與安和鄉接壤。瑤族集中在蕉江、大源兩個村公所,占全鄉總人口的13.45%,界頂村是其中的自然村之一。獨特的地理環境及瑤、漢等民族長期雜居的社會環境,歷史上曾有 “以女招贅完娶”“換婚制,換女不換男,換人不換物”“對歌自由戀愛”等婚俗,這些現在在界頂村均已消失。但是在具體婚禮過程中,形成的一整套有著瑤、漢特色的婚禮儀式,依然保存完好。一套完整的婚禮儀式是由各種“講究”的小儀式組成,這些儀式不斷地發生著、有條不紊地組織安排著傳統模式,人員之間的互動,從而構成婚禮儀式的圖像化敘事。
(一)婚禮籌備:布置新房、迎客、備酒席
婚禮的籌備是一個較長的過程,但是一般在結婚的前幾天才開始逐漸有“婚禮”的氛圍和儀式感,并隨著結婚日期的靠近強化,本文以婚禮的前一天作為研究的起點。作為婚禮的前奏曲,這天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布置新房、迎接遠方客人、備酒席。新房的布置包括貼對聯、裝飾房間等,但最有儀式感的是鋪床。鋪床人選必須是兒女雙全、婚姻幸福、沒有離異史的女性,事實上,有過離異的人在這天和結婚當天走進新房均被認為會影響新人的幸福,所以他們會自覺地遠離新房。這種“講究”和“自覺”暗含傳統文化意象的意義,即對幸福的追求和對不幸的忌諱。鋪床時,把被子背面朝上,上面放有染了紅色的雞蛋、花生、紅棗、桂圓、兩小支四季青和一條毛巾等物品,然后就著被子包住,并疊整齊放在床頭正方,上面壓著兩個枕頭。第二天迎接新娘回來,再把被子打開,晚上睡覺會有“好孕”,這樣的禮俗寄寓著對求子求孫的渴望。為何界頂村人對鋪床如此講究?通過其繁瑣的過程、意義的豐富可推測出:在界頂村人看來,床像大地一樣,是生命孕育的開始。可見傳宗接代作為中華傳統的理念,貫穿了整個民族文化,而不是單一地體現于某一民族思想中。關于迎客,當地人有以鞭炮聲宣示客人來到的認同。從這天開始,有專門負責放鞭炮的人,鞭炮聲音的長短是相對而言,有其規律性:有客來時放短鞭炮;正式開餐時放長鞭炮。這種不約而同的認知性,即是當地文化性知識的一種表現形式。客人到直接給禮金,負責接收禮金的一般是由有一定文化、人品好、結婚且家庭幸福的本家族男子當任;禮金當場拆開、算好、填寫在“禮金薄”上。從禮金上看出,當地人對“6”“8”“9”等數字很是鐘情。關于酒席的配備,這天基本把所有的菜肴都準備好,大概80%的客人在這一天都已經到來,所以晚餐是僅次于第二天正席的副席,葷菜以常見的禽畜為主,如豬肉、牛肉、羊肉、鴨肉、雞肉等,魚蝦很少但都盡量配有;素菜有青菜、蘑菇、辣椒、湯等,整體還算豐富,體現了當居民的飲食習慣。同時,通過這種婚前籌備,如來往人員的熱鬧、婚房的裝飾、屋內的擺設等,創造了一個迥然于平常的空間環境,無時不在提醒著所有參與者“此時此地”的特殊性,從而構建著人們特殊的、指向性的行動,同時重新建構了時間與空間的秩序,儀式感由此而產生。
(二)婚禮過程:迎親、敬酒、鬧洞房
1.迎親
迎親是結婚的重頭戲,新郎帶上車隊和伴郎等人員早早出發,務必要在12點之前把新娘接到家里拜堂成親,送回新房,以免誤了時辰,因為12點之后就是正式的婚宴。現在的迎親工具都是小轎車,比較方便。出發迎親前,在每輛車的左透視鏡掛一塊2-3斤的生豬肉,回來時,女方家會在車的右透視鏡另掛相同的一塊豬肉,這也暗含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男左女右”的意象。這塊肉除了作為司機的勞務分得外(司機還有主家另外給的禮金),更寓意有去有回,成雙成對的好兆頭。當然,如果男方家沒有掛豬肉去,女方家也不用回禮。迎親隊伍在鞭炮聲中出發,一般盡量保持車隊的連接性,如不被其他車輛穿插,以免不吉利。男方到達女方家,經過重重關卡搶到新娘,也就意味著新娘的出嫁。新娘家的送親隊伍,走在最前面的是放鞭炮的,鞭炮聲有開路、歡送之意;接著是拿著當地特色餐桌等嫁妝的人;再到新郎新娘;后面跟著一群送嫁的娘家親戚;最后面的是放鞭炮的。送嫁的親戚一直把新娘新郎送到車上,目送車開遠了才離開。在新娘上車的地方燃起久久的鞭炮和煙花,以示歡送和遙寄美好生活的祝福。在男方家,早早準備好“回人”的祭禮用品,包括泡濕的米(大概1斤左右,有一小把染了紅色的灑在米堆正方面)、煮熟的一塊肉(1斤左右)、酒、酒杯、香、紙等放在一個托盤上,接新娘回來下車時,就在村口面對新娘回來的方向,就地祭祀,告知新娘家的先人、祖宗,叫他們回去,就此道別,以后不要來騷擾新娘,新娘會成為男方家成員,開啟新的生活。“回人”儀式即是把新娘的先人靈魂請回去,體現界頂村人萬物有靈的世俗世界觀。新娘下車的同時,燃起了長久的鞭炮和煙花,表示歡迎和喜慶。于此,在伴娘、伴郎、長輩等人的陪同下,新人直接到自家祖宗靈前拜堂,正式認祖歸宗。拜堂結束后,新人被親戚朋友送到新房門口,由新娘開房門,意味著以后這個家就是由新娘掌管了;新娘進房后坐在新床上,這時長輩會先讓一群小男孩進房滾床,然后再讓一群小女孩進去滾床,這樣的先后順序多少反映了重男輕女思想的存在。小孩滾完床,昨天鋪床的長輩再把被子打開,把里面能吃的東西讓主家人先吃之后全部分給在新房里每一個人,其他不能吃的則放到柜子里,再把被子反過來鋪好。此時有長輩端來糖果、花生、紅棗等,新娘拿著一大把紅包(紅包在前一天已準備好,里面一般是幾塊錢),分給來討紅包的人,不分大小老幼,討新娘的紅包寄意著行好運。迎親對新娘而言是從娘家到夫家的過程,是一種身份、生活的轉換;對新郎而言是身份、責任的確認,從而建構人生的新秩序。
2.敬酒
新娘要一直呆在新房,直到午飯時才能走出房間,給客人敬酒,新郎則沒有要求。新娘不能隨意走出新房的行為一來照顧新娘初來駕到,人生地不熟的尷尬,二來也是古代女子不能拋頭露面風氣的遺留。新郎、新娘的午餐是有專人端到新房里的面條,必須是面條,有長長久久、白頭偕老之意,吃完面條,要等到晚飯才能吃飯。敬酒是按順序從長輩開始,敬酒時,客人可以“捉弄”新人,如把各種湯、飲料、酒等混合一起讓新人喝下,要求新人吃指定的菜等,意味著婚后的生活充滿了酸甜苦辣,要學會承擔;同時也有鬧洞房的小前奏之意。新人敬完酒后,一般新郎父母也隨后給客人敬酒,感激客人來參加婚禮。敬酒儀式實際就是向親戚朋友介紹新娘,彼此接納認同的過程,通過此途徑,親戚朋友互相認同,視彼此為共同體的存在。
3.鬧洞房
作為婚禮最熱鬧的場面,鬧洞房集合了老中少幼各路人馬,且極具當地的民族特色。界頂村鬧洞房樣式很多,如用鍋底灰抹新人的臉,把新人打扮成各種怪樣游村等,但不管怎樣的形式,最終都會圍繞著“打油茶”這一主題。界頂村鬧洞房不是在婚房,而是在客廳等寬敞的地方,這樣可以容納更多人。時間是晚飯過后,同村的人相約而至,來的人都會帶上一串鞭炮,等人差不多就放鞭炮,人越多鞭炮放得越多,其他人聽到久久的鞭炮聲,就知道鬧洞房開始了。鬧洞房開始,先用鍋底灰把新郎新娘的臉抹黑,當然其他人也可以相互抹,就是一場以新郎新娘為主體的大狂歡的。一般在客廳放一個燃著的炭盆,上面架著個鍋(炒米用),旁邊放著一堆剛折回來的青松葉,新郎新娘坐在炭盆的一邊,對面是一群繞著炭盆坐成橢圓狀的小孩,每個小孩的手上拿著把扇子。如果旁邊有人問新人問題,而新人不愿回答或回答不出,就把松葉蓋在炭盆上,叫小孩使勁扇火,濃煙滾滾,往往把新人熏得淚流滿面;所以一般別人怎么問就怎么答,要不就被熏。鬧洞房的人各顯神通,插科打諢、唱山歌等,熱鬧非凡,而各種奇葩的問題或要求卻也把新人“整得”苦不堪言。在界頂村人看來,洞房鬧得越熱鬧,以后的日子過得越紅火,所以沒人會幫新人“說情”,除非是新娘有孕在身等特殊情況,這樣可能會鬧伴郎伴娘或新郎家里其他成雙成對的人,如父母、哥嫂、弟媳等。由于結婚的人都會經過這一關,因此在鬧新人的時候也要注意分寸,以免到自己結婚時別人“報復”。鬧的過程會不時地放鞭炮,洞房要一直鬧到新人能把油茶煮出來,并且讓來鬧洞房的人認可了且喝下油茶才算結束。事實上,整個過程里,都是不同的人在“拷問”新人,都沒給機會炒米、煮油茶,因此這油茶也不是那么好煮,特別是外地媳婦,要在鬧洞房之前向長輩取經如何煮油茶,以免到時煮不出油茶。實在煮不出來,鬧到一定程度的話,也不會太為難新人,會有其他長輩煮好端來給各位喝,也就當新人完成任務了。由此可見,油茶在當地人生活中的重要意義,它是界頂村招待客人的“見面禮”,即客人來時,一定要先煮油茶給客人喝,邊喝邊聊天,然后再準備正餐。現在界頂村人依然保持著早上喝油茶的傳統。而“鬧”在體現本土美學范疇意義的同時,通過“鬧”本身緩解了新人身份轉換的尷尬,讓新人在“鬧”的環境下“無聲”地過渡到另一種身份、生活的狀態。
汪悅進認為:“任何儀式,無非是在于通過一系列緊鑼密鼓的‘走過場’來促使某一個體在短短時間內突發性地完成一個象征性的由此及彼的狀態轉化和過渡,乃至激變。”[1]瑤族儀式化的婚禮固然可以在某種意義上被看作公共性的“表演”,但就其本源而言,則事關當事人即新郎新娘的個人利益,即一方面向社會宣告自我身份、角色的改變,另一方面也是在踐行著“禮尚往來”的社會機制。而一場傳統的婚禮,對界頂村人來說,“不僅構建著親密的家族群體,同時也創造了關系緊密的想象共同體。不僅僅在日常生活的儀式實踐中人們相互之間會形成歸屬感、信任感和集體感,在共同的家庭回憶和想象中也會出現類似的情感。儀式平衡著家庭生活的穩定性與變動性,為家庭成員擬定一個基本的框架,使每個個體都基于此框架去自我表達和自我成長。”[2]
二、想象認同:圖像地域的秩序建構
瑤族婚禮儀式的展演過程,有著米歇爾圖像分類中視覺性圖像與知覺性圖像的混合的特征,即儀式不僅在于鏡像化的投射,亦有感知性的形象生成。亦如克里斯托夫所說的:“儀式的展開過程,也是人們自我表達的過程、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呈現過程及社會化的過程。同樣,也是在社會化的展現中,儀式生成了人類的自我表達、人與人之間關系等。”[2]即儀式在展演的同時,創造、聯系、維護、建構宗族關系、鄰里關系、鄉情關系等以地域關系為框架的族群所共享的符號性、想象性知識。
(一)宗族關系的認同
筆者在界頂村調研時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即村里幾乎所有的同姓宗族都沒有一個類似祠堂之類的地方祭拜先祖,但在各自家里都有祖先的祭臺,各拜各的祖先;家里祭拜先人的儀式也很隨意,一般是家里的老人在逢年過節時簡單地拜了了事,并不要求全家人或者年輕人一起拜。那么,界頂村人的宗族關系是如何建構的呢?在筆者的走訪中發現,首先在婚禮過程中,只要有時間的,本家族人都自覺地參與到婚禮各項工作中,如洗碗、洗菜、做飯、煮菜等。這種自覺性本身就是宗族身份認同的表現,因為只有本家族人才會自愿來做這些繁瑣的事情,而婚禮的舉辦無疑給這份“自覺性”提供了聯系、融合宗族關系的機會,并對他們自我身份的進一步確認——我們是本家。他們以自己不同的經歷為婚禮的舉辦參謀策劃、提供勞力智力,不僅延續婚禮的傳統性,而且無形中建構了對宗族血緣關系的確認,因為只有處于同宗族的人,才會在先人一脈相傳下來的婚姻儀式里,體驗其中的親切感和熟悉感。其次,婚禮的舉辦,如一次宗族大聚會,把親戚從四面八方召集回來,表面是參加婚禮、相見、敘舊,深層則是對宗族關系的認同,這對于沒有宗族祠堂的界頂村人而言,意義非凡。
(二)鄰里關系的維護
筆者進一步調研發現,界頂村不僅沒有宗族祠堂,即便是唯一的一個村廟都少有人問津,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有這樣一座廟的存在,更別談知道廟中擺放的三座神像是誰。大多村民知道廟山這個地方,因它就坐落在界頂村旁邊,卻不知道廟山之所以為廟山,是因為山上早前有座廟,后因年久失修,無人問津,廟就荒廢了直至消失,從而成了界頂村的廟址,這也是筆者問了很多老人后知道的,50歲以下的人,幾乎不知道。2014年在廟山上重新修建了一座小廟,里面放著三座神像,只知道其中一座是白龍騎大王,剩下的兩座即便是村里的道公也說不清是誰,一般人更無從知道,都說大抵是觀音菩薩或土地神之類的神。于是不懂為何神的三座神像就放在了廟里,而廟不是開放性的,守門人不在的話就鎖住。筆者第一次去的時候,沒遇到任何人,大門緊閉,只能靠著門望,里面除了三座神像和三個蒲團,并無他物。問村人為何鎖住,說怕被偷或破壞。廟被鎖住了,難道平時沒人來嗎?村人答,幾乎沒人去。那么守門人是誰?村人答,是村中信神的兩位大媽,她們自愿每天去廟里看門,然而其中一大媽被兒子拉回去了,不許她呆在廟里……
那么在這樣一個缺乏神崇拜和信仰的偏僻村落,它以什么來搭建村落的人際關系、維護村落的安穩以及保持村風的淳厚樸實呢?以此,傳統婚禮習俗對鄰里關系的影響就顯示出來。界頂村的婚禮都辦得比較大,一般都在30桌以上,這樣的規模在農村是相當大的,因此鄰里之間也是一種互助的生活形式。在界頂村,以村為單位,共享一套婚禮習俗,族群之間無甚區別,因此更容易產生共鳴。如果說婚禮過程中的“迎親”“敬酒”等儀式是宗族人群的狂歡,那么“鬧洞房”則是鄰里甚至是鄰村等更大人群的狂歡。“鬧洞房”作為一種習俗,與親疏遠近無關,鬧的是一種歡樂、氛圍、情緒,即人最本真的情感釋放。因此,中老年人鬧的是對過去回憶的再現;青年鬧的是對未來婚姻的憧憬;少年鬧的是對愛情的懵懂與羞澀;幼童鬧的是熱鬧與好奇,無形中把所有人集合一起,共享一場狂歡游戲。筆者調研時,剛好遇到在同一天里,村里有5對新人同時結婚,于是看到了村里幾位鬧洞房“高手”,輾轉于不同的地點,以歌以舞掀起了狂歡的高潮。這樣流動性的鬧洞房,或者說鬧洞房本身就是人際關系的串聯,它活絡了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性,拉近了彼此間心靈的溝通,這才是隱藏在傳統婚禮習俗下的本質功能。
(三)鄉情關系的建構
界頂村山多地少,許多年輕人以外出廣東等地打工為生。外面世界的精彩與村莊的偏僻、閉塞形成了巨大的落差,以此,城市與村莊之間如何建構年輕人或者說是走出村莊的這些人的鄉土情感呢?故土的認同不只是“家在那”那么簡單,而是一種深入骨髓的文化認同感,這種認同在界頂村更多是通過儀式來建構的。對在外營生的人而言,外面的世界無疑擴大了他們的認知視野,同時也讓他們有意識地確認自己的文化特性。獨特的習俗如傳統婚禮儀式是一種身份的劃分,只有處于這個地域或者說這個村落才會出現的東西,它如血液流淌于身上,是一種自我主體的顯示和表征。而相比現代社會的簡單化、機械化、物質化等,具有濃郁人情味的傳統婚禮更契合人性的本真,它有古老的儀式、貼近生活、熱鬧、釋放情感等形式和作用。因此通過傳統的婚禮儀式,調和了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關系,很好地過渡到故土、鄉情等情感表述。近年,界頂村在外面的年輕人越來越多地一定要回家辦一場傳統的婚禮,不僅是回饋父老鄉親,體現禮俗往來互動的鄉里關系,也釋放了故土情懷,詮釋作為村莊成員應經歷的一個人生儀式,它如人生洗禮,宣示著某種身份的確立。生活需要儀式感,因為儀式本身就是一座橋梁,溝通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歷史的關聯,同時建構了親密的家族群體關系也創造了關系緊密的想象共同體。
綜上,界頂村的婚禮習俗跨越族群,演繹為以地域為特征的文化形態,從而建構出以家庭為核心,向四周輻射的地域共生關系,并使之成為一種“已然”的現象并為大家所接受。由此可見,所謂的歷史、空間、文化秩序,是作為主體的人“創造工具和符號,為我們自身鑄造一個‘非自然的’環境——即習俗的、文化的和人造的環境”[3],以此通過某種儀式化的想象,達到文化認同的共生性。
三、文化堅守:圖像話語的自我表達
克里斯托夫認為:“儀式是以一種可觀看、可感知的方式呈現和展演社會關系和社會事件,并以它的方式作用于這些社會關系和事件,對其結構化并進行相應的調整。”[2]即通過儀式本身的意圖、內容和展演背景等,使每一個參與儀式的人都能親歷一些共同記憶。從上文可知,界頂村人對神的觀念是比較淡薄的,然而不信神的話,為何有這樣一個古老廟址的存在?而在被荒廢了幾十年后,僅是因為村里近幾年不大太平又集資重新修建,以求村寨平安,但在建好后,卻少有人去拜?筆者在不斷地追問中探出了矛盾行為背后的原因。在中國村落文明發展過程中都會有這樣的現象:越是偏僻的地方,特別是少數民族居住的地方,其民族特色的神信仰崇拜就越豐富,民族禁忌也越多。然而,界頂村地處偏僻,早前的廟山雖有座很大的廟宇,但去拜的人不多,再加上“文革”期間認為是迷信行為而被禁止,從此更是“一蹶不振”,直至被遺忘。但是不管界頂村人信不信神,廟是存在過的,說明神也是存在過的,因此神的存在是界頂村一種合理的展現,以致恢復廟的建設,即恢復神的存在。“人類是一種歷史性的存在,因此人的自身認同和集體認同問題都必須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去看,所有的認同都是在一定的時空系統中人們歷史活動的過程和產物。”[4]界頂村人對村廟的矛盾行為表現出的正是在特殊政治環境中,被割斷的歷史感對神崇拜的消失;在社會發展中,被遺留于歷史中的對神存在的堅持和延續。而神崇拜、神信仰等觀念的淡薄,直接導致了界頂村人對生活習俗的重視,如婚嫁喪葬等人生禮儀,并以此重構他們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以瑤族傳統婚禮習俗為例,它無疑是在現代社會中傳統文化自我堅守的傳達。
(一)雜糅共生
隨著社會的發展,界頂村瑤族很多外在的形式都已漢化,如服飾、生活習慣等,早前的“兩頭扯”婚俗也僅存留在相關史料的記載里,現在的婚姻是男娶女嫁的普遍形式。但是操辦婚禮的詳實過程所體現出的儀式卻是界頂村獨有的村寨文化,它是在具體的環境下形成的文化特色。由上文可知,界頂村的婚禮儀式有自己的獨特性,如送一套吃飯的臺櫈、在車燈上掛豬肉、回門、鬧洞房時唱歌等,但有很多細節又跟漢族相似,如拜堂、敬酒、讓小孩滾床等。這些不同中雜著相同,相同中雜著個性的婚禮習俗,正是界頂村瑤、漢長期雜居孕育的文化特性。這樣的文化個性經過大浪淘沙和時代的洗禮逐漸沉淀下來,它是一種平穩過渡,不具備強迫性、入侵性的文化形式,從而形成一套承載著界頂村人習俗認同和時代認可的儀式。
(二)自我主體的形成
界頂村傳統婚禮不被現代化瓦解,有著自身獨立的主體意識,追其根源有三方面。首先瑤族傳統婚禮它是在特定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下產生的,它的儀式體現了界頂村生態環境的原始狀態,即它的存在與當地生活、生產融為一體,且得到當地人的認可。如廣西全州作為桂西北的出口,它是廣西最冷的邊界,當地人廚房不設灶臺,只在廚房中間挖一個大小1平方米左右,深20厘米左右的洞,即火塘。做飯時把三腳架放在火塘上,鍋放在三腳架上即可生火做飯。四方炭盆桌(桌子中間鏤空放炭盆,鍋放在炭盆上)與四張長凳子是當地的特色飯桌,冬天的必備。冬天時,當地人圍著炭盆桌,邊做飯邊烤火邊吃飯,一舉三得。因此把一套樸實、簡單的地方餐桌作為嫁妝的大禮,其實是有著深刻的生活內涵,它不只是嫁妝,亦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文化傳統,更是先人為了適應環境而發明的生存方式的智慧體現。其次瑤族傳統婚禮體現的是一種普世價值,具有普世意義,因此得到社會的認同。由上文可知,瑤族傳統婚禮習俗無論是表現形式還是內涵意義,于社會、于人生、于個體都合乎人情順乎事理,都寄意著祝福和對美好未來的憧憬。它這種樸素、實在的價值觀念是人生最真實、內在的本質要求,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體系具有傳承性,與現代社會的價值根基具有一致性。最后是瑤族傳統婚禮具有文化自覺性和適應性,它不是神秘的、不可預知的,它帶有廣闊性和融合性,因此能夠保持自我的同時吸收社會新元素,熔煉成自我文化的展現。它不會因社會的發展而被淘汰,相反,它不斷地調整自身的形態,以適應社會的變化。
(三)獨立的文化體系
瑤族傳統婚禮呈現的文化多元性與自由性的特征說明,即便是同一支系的族群,由于其所處的具體環境不同而呈現出不同的文化個性。如界頂、蕉江兩個自然村同屬于蕉江瑤族自治鄉,是同一瑤族支系,卻因不同的村落不同的生存環境,界頂村與蕉江村出現截然不同的信仰追求。蕉江村有著根深蒂固的神靈信仰,因此神靈崇拜在當地很盛行;而對界頂村人來說,他們有著“萬物有靈”的觀念,但是對神并不狂熱。但是界頂村人通過另一種文化信仰體系來建構自身在現世的存在感,即對人生禮俗等生活習俗的重視來重構他們的生存價值體系。界頂村的這種文化體系,體現的是瑤、漢兩族在長期雜居中形成自己獨立的文化體系:首先它展現了與當下主流文化的單一性、趨同性的“大同”之下的“小異”,即傳統瑤族婚禮是獨具個性魅力的村寨文化;其次它對人生的關照,潛藏于人與人、人與村落、人與社會的關系中,是一種文化認同的紐帶;最后它提供了一種傳統文化如何傳承發展的范式,即在對傳統文化的繼承,對現代元素的吸收容納的基礎上,重構自己的文化主體。從中可以看出文化的滲透、包容,甚至是在兩族文化共筑的基礎上,重新形成的,讓瑤、漢兩族共同接受的文化體系。
帕諾夫斯基認為“圖像學是一種詮釋的方法,它乃是由綜合而來,而非分析”[5],瑤族傳統婚禮從圖像學而言,它如一幅歷史畫卷,承接著界頂村瑤族、漢族先人的儀式形態、民俗信仰、文化構造等,又啟示著現代語境下界頂村瑤族、漢族人民的生活常態、信仰關照、文化形態等。瑤族傳統婚禮沒有闡釋其內涵,甚至很多人不知道由眾多小儀式組成的婚禮儀式具體有什么樣的意義,但是在傳統“講究”的傳承下,代代“講究”也就構成了婚禮的真正結構形態,透過這個形態,我們看到了界頂村人的生活、環境、社會、歷史、文化與過去的勾連,與現在的呼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