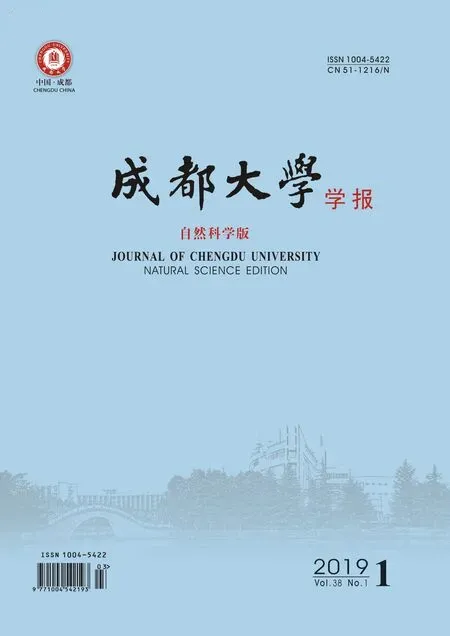運動性心肌肥大及其信號通路研究進展
李 欣,鮑高山,余文祿,代海斌
(成都大學 體育學院,四川 成都 610106)
0 引 言
研究發現,年齡、膽固醇升高、糖尿病、肥胖、高血壓、心室質量增加及體力活動不足是心血管疾病的相關獨立危險因子[1].其中,心室質量增加一般是由心肌肥大造成的,心肌肥大是指心臟因應答過量負荷造成的血流動力學改變而產生的質量和體積增加.目前有研究顯示,成熟的心肌細胞仍具有部分復制和修復能力[2],但大部分成熟的心肌細胞是終末分化細胞,喪失了分化能力,即心肌肥大是由心肌細胞體積的增大造成的,而不是由心肌細胞數量的增多造成的.
心肌細胞有著很強的肥大適應性,當心臟承受過度的工作負荷時,心肌細胞對這一復雜事件的反應就是肥大.工作負荷系機械刺激,其信號必須翻譯為促進細胞生長的電信號和(或)生化信號.當心肌承受過度的機械應力時,根據拉普拉斯定律,心室壁的厚度需增大,以減輕壁應力.然而,心臟中存在著大量的非心肌細胞,如成纖維細胞、冠狀血管樹細胞和間質細胞,會在心肌細胞對超負荷發生應答的早期,就發生了肥大和增生,進而產生間質纖維化,造成心臟舒張功能的損傷,在舒張性心衰和心律不齊發生過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心肌質量會隨血流動力學負荷的改變而不斷變化,在心血管系統,由于生理性活動或病理性變化引起的血流動力學功能的持續增加,都會導致心臟/體重比值的變化[3].
1 心肌肥大分類
1.1 生理性心肌肥大
經典的理論認為,除正常的生長發育外,生理性心肌肥大包括兩種形式:一種是運動性心肌肥大.力量訓練可以增加外周阻力,導致心臟后負荷增加,形成向心性肥大.長期耐力訓練增加靜脈回流和血流量,導致心臟前負荷增加,形成離心性心肌肥大,此時心肌細胞的適應改變足以滿足人體需要,心臟功能維持在正常水平.但目前對運動性心肌肥大的性質仍充滿爭議,并不能認為其是嚴格意義上的生理性肥大[4].另一種是,妊娠型心肌肥大.在懷孕的第二期和第三期,心臟輸出血流量增加,以配合胎盤的血流量,導致了一種持續的容積負荷,心臟產生適度的離心性肥大.生產后心臟容積負荷回復正常,心肌肥大發生逆轉,同時胎兒基因的表達未見增加,因此,妊娠型心肌肥大可認為是嚴格意義上的生理性肥大.
1.2 病理性心肌肥大
當肥大應答不能使心室壁應力回復正常時,肥大反應持續進行,導致心臟發生病理性改變[5].病理性的壓力負荷刺激因素包括系統性高血壓、外周阻力增加、主動脈瓣狹窄和主動脈縮窄.病理性的容積負荷刺激因素主要是瓣膜性回流.病理性向心性肥大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心室壁厚度與心室腔半徑的比例顯著增加,而病理性的離心性心肌肥大其心室壁厚度和心室腔半徑比例基本正常.對病理性向心性肥大的研究發現,隨著心肌肥大狀態的持續,心肌毛細血管密度和線粒體體積降低,常伴有心肌成纖維細胞、血管平滑肌細胞、細胞外膠原蛋白和內皮細胞的激活,纖維狀膠原細胞不成比例地增加,堆積在細胞外膜和細胞間,替代壞死的心肌細胞.這種結構的變化導致心臟彈性和收縮力下降,進而心功紊亂.病理性離心性肥大也受到因結構重塑造成的間質纖維化的影響.
就其定義來說,生理性心肌肥大應是一種不會形成或引起疾病的適應性改變,與病理性肥大有著完全的區別.但臨床證據表明并非如此,即使是妊娠型心肌肥大,也有一定比例的圍產期心肌病發生;單純性高血壓早期,心臟只會出現一般水平的離心性肥大,此時心臟的基本功能保持正常;壓力超負荷型心肌肥大射血表現正常,但收縮功能失常.由于在肥大過程中,心臟的結構、功能和質量都是獨立的變量,即無論是代償性肥大還是失代償的肥大,心臟大小和形狀都會發生改變,形成心室重構.因此,將心肌肥大簡單地按生理性和病理性分類的方法往往會因心臟的結構和功能因素而造成重疊,尤其是對于傳統理論中認為是生理性肥大的運動性心肌肥大,對其肥大的性質一直未達成共識.
2 運動性心肌肥大
2.1 不同運動類型對心臟的影響
目前,對心血管系統的運動刺激分為兩類:耐力運動型和力量運動型(大部分運動都結合了耐力和力量刺激,為混合型項目).耐力運動的急性應答包括最大攝氧量、心輸出量、每搏輸出量、收縮壓的增加,伴隨周圍血管阻力的降低;力量訓練的急性應答包括輕度的最大攝氧量和心輸出量的增加,以及血壓、外周血管阻力和心率的增加.耐力運動可以認為是一種等張運動,使骨骼肌血管和冠狀動脈血管擴張,心排出量和冠狀動脈血流量增加,造成血壓的輕度升高,起到容積負荷的作用,左右心室腔擴大,心室壁厚度輕度增加,出現離心性肥大;壓力負荷主要表現為心肌細胞體積增大,線粒體絕對數量雖然增加,但心肌細胞中每單位體積的線粒體數量卻發生了顯著降低.力量訓練可以認為是一種等長運動,使肌肉的應力明顯增加,外周血管阻力明顯增大,血壓明顯升高,心室壁增厚明顯,而左右心室腔擴大不明顯,出現向心性肥大.
通過對前人的研究進行meta分析,Pluim等[6]發現動力性運動和靜力性運動所產生的心臟改變存在不同,混合型運動產生的改變介于兩者之間.理論上耐力運動后應形成一種單純的離心性心肌肥大,但實際結果是在舒張末期左心室腔直徑增大,左心室壁的厚度增加超過預期,左心室壁與左心室直徑的比例顯著增高.理論上力量訓練后理應發展成向心性肥大,實際表現為左心室腔直徑相對增大,而心室壁顯著增厚.從事混合運動的人群左心室腔直徑增大幅度最高,心室壁厚度相對增高.考慮到運動造成的心率和血壓的升高,認為心室腔直徑和心室壁的增加對心臟適應耐力訓練是有益的.運動強度極大時,心輸出量可從靜息狀態下的5 L/min上升到40 L/min.心臟通過心室腔的擴張來適應這種容積負荷的增加,血壓也可升高至69/175 mmHg.這表明,耐力運動中不存在單純的容積負荷,在長期耐力訓練中,心臟要同時適應容積和壓力負荷,所以左心室腔的內徑和左心室壁的厚度才會同時增加,且心室壁厚度的增加超出理論預期的水平.在大強度的力量訓練過程中,動脈血壓顯著增加,可達350/480 mmHg,此時心率和心輸出量都發生了增長,心率平均為102次,峰值可達170次.同理,單純的壓力負荷也是不存在的.因此心臟對力量訓練的適應應是左心室內徑的相對增大和心室壁的大幅增厚.賽艇和自行車運動是典型的混合型運動,高水平的自行車運動員可以用接近極限心率來做功并持續很長一段時間,收縮壓和平均動脈壓增高,收縮壓可達200 mmHg.在賽艇比賽中,心率可達190次,血壓峰值可達200 mmHg.因此,心臟對這種極大的容積負荷和較大的壓力負荷的適應應是左心室內徑和心室壁厚度的大幅度增加.
2.2 運動性心肌肥大與心臟疾病
對于一般心臟疾病的患者來說,心臟的肥大往往伴隨著一定程度的心功不全.對于大多數長期進行體育鍛煉的人群來說,心臟的肥大并不一定代表某種心臟疾病或危險因素,但對于部分個體而言,心肌肥大的確會增加心衰的風險,且伴隨著一些心血管功能的異常改變.部分長期進行體育鍛煉的人群會發生迷走神經張力增高,出現竇性心動過緩、交界區心律,文氏型房室傳導阻滯第一期以及心室早期收縮、非持續性室性心動過速等癥狀.有相關報道指出,長時間中小強度的耐力運動會造成心臟短暫的可逆性的收縮和舒張功能紊亂,發生心肌細胞損傷,20%~50%的運動員會沒有臨床自覺癥狀,只表現出心電圖表型的變化,發生急性透壁性心肌缺血病變.由于運動強度、頻率、方式的不同,對運動員心肌肥大的研究成果不完全適用于普通鍛煉人群,那么中等強度耐力運動所誘導的心肌肥大是否會發生一些病理性改變,如果伴隨著運動性心肌肥大而產生了一些病理性改變,其究竟是一種正常的“生理性現象"還是向心衰發展的病變基礎,目前未見系統的報道.因此,運動性心肌肥大在未發生一些趨向于病理性改變之前,可以認為是一種生理性的適應改變,但其的確具有潛在的向一些心血管疾病發展的風險[7].
3 心肌肥大的信號通路研究進展
3.1 PI3K/Akt/mTOR信號通路概述
研究發現,PI3K/Akt/mTOR信號通路是生理性心肌細胞肥大的代表通路[8].生長因子、胰島素、運動等刺激可以激活PI3K,PI3K平時以靜息狀態定位于細胞質中,在受到相關受體或接頭蛋白刺激后,被募集異位至細胞膜,磷酸化磷酸肌醇至磷脂酰肌醇3,4,5三磷酸,并募集PDK1.PDK1不能被PI3K直接激活,在磷脂酰肌醇3,4,5三磷酸存在時其T環發生磷酸化,使其成為PI3K的第二信使.磷酸化的PDK1可以特異性地磷酸化Akt T環上的蘇氨酸殘基308,并間接激活C端疏水模序中的絲氨酸殘基473,從而完全活化Akt[9].激活的Akt主要通過促進mTOR的表達來發揮促細胞生長生存功能,并在蛋白翻譯機制中起到重要作用.mTOR是一個高度保守的絲氨酸(蘇氨酸)激酶,是細胞營養狀態、能量狀態的傳感器,它處于PI3K/Akt信號通路的下游,能感受并整合經PI3K信號通路傳遞的生長因子信號,在調節細胞生長和細胞周期中起非常關鍵的作用.mTOR的主要下游靶蛋白包括p70S6K和eIF4E,mTOR既可以通過影響p70S6K的活性來調控核糖體mRNA的翻譯過程和蛋白的生成,也可以通過改變4E-BP1的磷酸化狀態,減弱4E-BP1與eIF4E的結合,調控翻譯起始復合物的功能,其中eIF4E的水平和活性決定了核糖體與mRNA結合的速度[10].
3.2 Gq信號通路概述
研究發現,在細胞膜表面有種因子參與激素引起的腺苷酸環化酶活性的改變,其既非受體亦非腺苷酸環化酶,最后認定該物質為鳥嘌呤腺苷酸結合蛋白或簡稱G蛋白.Gq蛋白家族與其它的G蛋白一樣,包括α、β和γ 3個亞基,在應答鳥嘌呤核苷酸的過程中發生激活和失活的循環.這些細胞膜結合蛋白與G蛋白偶聯受體作用并激活后,可將細胞外的GTP依賴性信號轉導為細胞應答.Gq蛋白最重要的作用在于維持心血管的正常功能,其在調節血壓、心肌肥大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AngII和血管舒張素可與Gq蛋白偶聯受體結合,調節血管張力,Gq蛋白自身的修飾可導致凋亡和肥大的應答.低表達的Gq對心臟沒有影響,中等程度的表達可導致心肌細胞肥大和小幅度的心功紊亂,高表達的Gq則可導致心臟顯著增厚、心衰、致死率增加[11].而過表達Gq的心臟面對壓力負荷時,心肌細胞凋亡增多.此外,抑制性多肽的過表達可干擾受體與Gq的偶聯,阻止壓力負荷造成的心肌肥大發展和心功紊亂.配基激活的受體與Gq蛋白作用后,募集并激活細胞膜上的磷脂酶C-β(Phospholipase C-β,PLC-β).PLC-β將磷脂酰肌醇4,5二磷酸水解為2個第二信使,甘油二酯(Diglyceride,DAG)和三磷酸肌醇(Inositol 1,4,5-triphosphate,IP3).DAG可以激活PKC,從而對心肌細胞的凋亡、壞死、觸發肥大基因轉錄產生作用.IP3與內質網上的IP3受體結合,釋放鈣離子進入細胞質,激活肥大應答基因.鈣離子的持續釋放會導致鈣調磷酸酶和NFAT轉錄因子的激活,而鈣調蛋白依賴性激酶II的激活以及NFAT信號通路在促進心肌病理性肥大中具有重要作用.這些證據表明,體內Gq蛋白信號通路的激活對病理性心肌肥大具有關鍵作用.
3.2.1 PLC-β/Gq蛋白通路.
目前,在細菌、酵母、果蠅、蛙和哺乳動物體內已發現20種不同結構的PLC蛋白.雖然真核生物的PLC異構體的同源相似性較小, 但均具有兩個功能結構功能域,即約170個氨基酸殘基組成的X結構功能域和約260個氨基酸殘基組成的Y結構功能域.在真核生物中,由于分子量及氨基酸序列的不同,PLC包括PLC-β、PLC-γ和PLC-δ 3種亞型,但只有PLC-β可被Gq蛋白直接激活,PLC-β包括β1、β2、β3和β4 4種異構體,均可被Gq蛋白激活,其敏感性大小依次為β1>β3>β2,其中β4較為特殊,其活性被核苷酸抑制,且主要在視網膜中表達[12].由于mRNA剪接的不同,β1又包括2種剪接變異體,β1a和β1b;β3也有2種剪接變異體,β3a和β3b;β4則有β4a、β4b和β4c 3種變異體[13].剪接變異體的差異主要在于蛋白C端堿基序列的不同,β1主要分布在心臟和神經組織,β2在平滑肌、肝臟和腦中表達,β3幾乎在所有組織中存在,而β4只在視網膜中表達.這4種異構體分子結構差異不大,具有相同的X、Y和PH結構功能域,但無SH結構功能域.X和Y結構功能域是酶活性區,可水解PIP2,生成DAG和IP3.PLC-β可被活化的G蛋白偶聯并激活,G蛋白中的GDP被GTP替換后,α和βγ的親和力下降36倍,而與PLC-β的親和力因其亞型不同而增加40~200倍[14].α和βγ可和PLC-β結合,具體結合的亞基則根據PLC-β的不同異構體及不同剪接體有關,Gq一般與PLC-β1結合,在此過程中PLC-β1的C端起到重要作用,PLC-β1與Gq的結合位點在C端尾部,如果C端不完整,PLC-β1雖仍具有完整的蛋白活性,但失去了被Gq激活異位至細胞核或與其它細胞器的能力.PLC-β的X和Y結構功能域是酶活性區,當PLC-β被G蛋白激活后,其異位在細胞膜上,水解PIP2,生成DAG和IP3.DAG可激活PKC,IP3可作用于鈣庫,釋放鈣離子,完成各種生理效應.
3.2.2 DAG-PKC/Gq蛋白通路.
DAG是胞內激活PKC的主要物質,被PLC-β水解形成的DAG代謝速率很快,不能長期維持激活PKC的作用,發現DAG可由PLC-β催化細胞膜上的磷脂酰膽堿產生,以維持PKC的長期效應[15].PKC是一個重要的絲氨酸(蘇氨酸)激酶家族,在細胞對激素、生長因子以及經Gq偶聯受體傳遞信號的神經遞質的應答中扮演重要角色.哺乳動物的PKC共有11種異構體[16],其中的傳統型,包括對鈣敏感的PKC-α、PKC-βI、PKC-βII和PKC-γ;新型,包括缺失鈣結合位點的PKC-δ、PKC-ε、PKC-η和PKC-θ;非典型異構體,其不對PKC的典型激動劑佛波醇酯應答,包括PKC-ζ、PKC-λ和PKC-μ.IP3導致鈣離子的釋放,促使鈣離子敏感性PKC的異位,而DAG可以激活傳統型和新型PKC異構體,使心肌細胞核內一些轉錄因子如c-fos、c-jun、活化轉錄因子-2等發生磷酸化,從而改變心肌細胞內基因的表達狀態,導致某些心肌蛋白如α-肌動蛋白、β-肌球蛋白重鏈和心房利鈉肽等合成增加,引起心肌細胞肥大[17].過度表達PKC的轉基因大鼠出現了明顯的心肌肥大,提供了PKC參與肥大反應更為直接的證據.目前認為,PKC是肥大信號傳遞中一個分子限速開關,是肥大信號傳遞的共同通路之一,在肥大反應的發生、發展中起到重要作用.在體內和組織細胞培養的實驗研究發現,PKC信號轉導途徑參與調節細胞的收縮功能和肥大反應,PKC作為心肌肥大信號途徑之一,其分子機制與細胞核受體和細胞內因子將肥大刺激信號傳入細胞,引起細胞基質鈣離子濃度增加有關,不同分型的PKC以時間和特異性酶依賴性調節不同的MAPK級聯反應.PKC-α是人心臟中最常見的異構體,它通過調節受磷蛋白和心肌肌漿網Ca2+-ATP酶的磷酸化來調節心臟的收縮,PKC-β對于心肌肥大、收縮和新生兒心肌生長具有重要作用;在壓力負荷造成的離心性肥大中, PKC-βI和PKC-βII異位,磷酸化活性增強,激活心室肌球蛋白輕鏈,引起鈣離子敏感性增加從而增強肌力和ATP酶的活性,可能是造成肥大性心臟收縮和舒張功能增強的主要原因.應用轉基因(PKC-β)小鼠研究發現,PKC-β能引起心肌結構及功能的嚴重異常,當心臟PKC-α和PKC-β表達減少時,生長因子表達減少,可以明顯改善心肌重構[18].PKC-δ在缺血性壞死和心肌細胞收縮功能紊亂中具有決定性作用;PKC-ε在心臟缺血再灌注中起到重要的保護作用,當其被激活時,其從細胞質異位至內質網,直接激活ATP敏感鉀通道,降低ROS產生和鈣負載,對心臟起到保護作用.而通過對豬離體心臟的研究發現,病理性的急性機械應力只會導致PKC-ε的快速異位.此外,PKC的下游效應子PKD可以直接磷酸化組蛋白去乙酰化酶5,使其轉運進細胞核,導致肥大基因的激活[19].
4 結 語
隨著對運動性心肌肥大研究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在運動因素誘導的心肌肥大過程中,心臟的結構、功能和質量都是獨立的變量,即無論是代償性肥大還是失代償的肥大,心臟大小和形狀都會發生改變,形成心室重構.因此,不能完全將運動性心肌肥大簡單地按生理性和病理性來分類.此外,相關的研究已表明,當運動性心肌肥大時,心肌肌肉蛋白合成的信號通道并不與生理性心肌肥大的蛋白合成信號通路完全一致,其具有自身獨有的信號傳遞特征[20-21].因此,假設運動性心肌肥大處于完全的生理性肥大和病理性肥大之間的灰色地帶,屬于嚴格意義的“生理改變之下、病理改變之上”,不管是對于健康大眾還是競技運動員,都應該提高警惕,并注意運動的方式、時間、強度、頻率并形成規律的體檢觀念,將運動性心肌肥大風險控制在最小范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