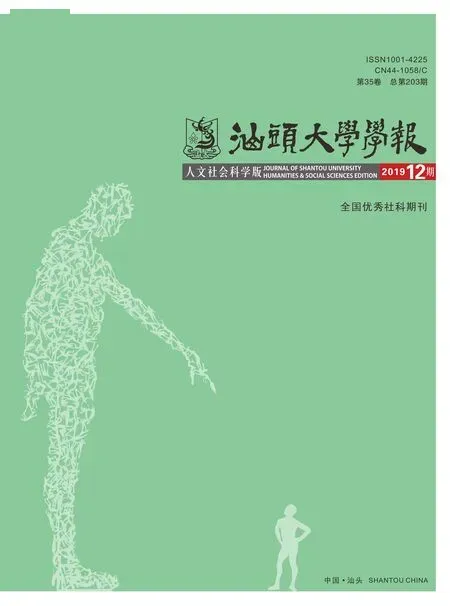互聯網史的全球坐標
——《勞特利奇盧德里奇全球互聯網史手冊》前言
引言
自1969 年互聯網正式誕生以來,已經過去了50 年,對互聯網史的研究終于初具規模。本書問世之時,恰逢這一研究領域的學術雜志《互聯網史》(Internet Histories)誕生之際。其他標志性的進展還包括若干本重要的論文集、雜志特刊、學術論文和專著。本著媒介精神的原則,在數字人文科學、數字社會科學和相關的信息技術輔助研究(e-research)誕生的背景下,我們認為日益增加的數字資源,互聯網史網站、資源、文檔和數據庫也同樣標志著互聯網史研究領域的進步。
然而,我們大致可以做出如下論斷:目前英語世界現有的互聯網史,還主要是對北美和歐洲國家情況的紀錄,也僅僅紀錄了這些國家情況的某些方面。例如,對美國互聯網早期歷史的學術研究已經頗為成熟。在《發明互聯網》(Inventing the Internet)一書中,Janet Abbate 追述了互聯網的起源,特別描述了通過阿帕網(ARPANET)的發展,技術及其含義是如何同時產生了變化。Patrice Flichy 研究了美國90 年代的網絡文化熱潮,當時最明顯的標志是《連線雜志》(Wired Magazine)的廣為傳閱(Flichy 2007)。在《從反主流文化到賽博文化:斯圖爾特·布蘭德、全球概覽和數字烏托邦的興起》(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culture:Stewart Brand,the Whole Earth Network,and the Rise of Digital Utopianism)一書中,Fred Turner 探索了隨著計算機網絡和數字文化的出現,軍事-工業研究文化與反主流文化之間所產生的聯系,而這一聯系早在互聯網出現之前就已發展起來了(Turner 2006:9)。William Aspray 和Paul E.Ceruzzi編撰的《互聯網和美國商業》(The Internet and American Business 2008)一書中收錄的各篇文章展示了互聯網的設計和使用在美國商業中的重要軌跡的各個視角。
在歐洲國家,互聯網史研究剛剛興起。牛津互聯網研究中心于2001 年在英國成立。自成立以來,該研究中心一直是歐洲和全球互聯網文化研究的要地。在其他地區,一位開創性的歐洲學者是Niels Brügger,他發起了丹麥互聯網史的重要案例研究,同時也開創了網頁歷史研究這一領域(Brügger 2010 and 2013; Burns and Brügger 2012;Brügger 2016a and 2016b; Brügger and Schroeder 2016;Brügger 2017;Brügger,Ankerson,and Milligan 2017)。其他領軍人物還包括:法國研究者如Valérie Schafer(Schafer and Tuy 2013)、Benjamin Thierry(Schafer and Thierry 2012)和Camille Paloque-Berges(Masutti and Paloque-Berges 2013);倫敦大學研究者如Jane Winters,主持了《大英國區藝術和人文學科數據》(Big UK Domain Data for the Arts and Humanities)(BUDDAH;http://buddah.projects.history.ac.uk/)項目來紀錄英國網頁歷史;阿姆斯特丹大學“數字方法倡議”(DigitalMethodsInitiative)項目的研究者,包括Anat Ben-David(2010,2012,and 2016)、Anne Helmond(Helmond 2015)和Ester Weltevrede(Weltevrede and Helmond 2012)。當然,還有Richard Rogers 的開拓性著作《數字方法》(Digital Methods,Rogers 2013)。然而,在歐盟地區,雖然對互聯網史有不少本地案例研究,但目前還沒有不同地區之間的比較研究。
在其他國家和地區,對互聯網歷史的研究還很少,尤其是缺乏系統性的學術研究。在許多國家,技術專家社區與互聯網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尤其是那些互聯網協會或互聯網名稱和數字地址分配機構(ICANN,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等治理機構中的行動者,是第一批參與者歷史的撰稿者,也得到鼓勵和資助來撰寫制度史。除了美國和歐洲之外,其他國家的互聯網史專著為數甚少(中國和韓國例外,參見Zhou 2006,Lee 2012),多個國家之間的網絡史比較研究就更少了。國際上對互聯網多樣化發展路徑歷史最早的研究,來自于對某些特定國家的互聯網情況的研究(例如由Peter Lang 出版社出版的、Steve Jones 主編的《數字結構》(Digital Formations)系列)。為了講述互聯網在特定環境下的情況,研究人員必須設法了解當地互聯網的具體特征——即使只是將其與全球互聯網的“已接受”歷史聯系起來。在各專業學科領域,還展開了對互聯網史的另一批研究。因為一段時間以來,各學科需要加深對互聯網的了解,因其已經成為世界各地媒體、傳播、文化和技術動態的核心(參見Bruijn and van Dijk 2012; van Dijck 2013)。因此,越來越多的對各地區國家的研究,包括發展中國家,讓我們注意到互聯網在Web2.0、社交媒體、移動互聯網以及其他數據技術和基礎設施方面的國際發展方式(參見Donner 2015)。
然而,雖然有一些用當地語言發表的研究,對互聯網在北美和歐洲以外的國家的早期情況進行了介紹,這些研究卻并未譯為英語,英語學術界在談及這些國家的互聯網史時,也很少提及這些研究。日本是一個特別值得一提的例子。自公文俊平(Shumpei Kumon)于1988 年發表了突破性著作《網絡社會》(Nettowāku Shakai)以來,在早期BBS和互聯網文化方面一直有著豐富的日語文獻。然而,在整個90 年代,對日本互聯網傳播采納情況的英語評述,還主要依賴于美國人敘述。這些美國人或是曾在日旅居,或是曾訪問過日本,對網絡傳播應該是什么情況,腦海中已經有了一定的預設(參見本書中麥克利蘭〈McLelland〉的章節)。雖然從21 世紀初開始,在日本計算機技術(Gottlieb 2000)、網絡文化(Gottlieb and McLelland 2003)和移動媒體方面(Ito,Okabe,and Matsuda 2005)有了開創性的英語學術成果。然而,這一研究領域還存在不少真空地帶——在學術研究方面如此,在對這一新生領域已有研究的充分了解和繼續推進方面也是如此。總的來說,由于在真正的國際化、全球化背景下理解傳播、媒體、數字技術和文化的重要性,缺乏地方歷史的參考成為一個重大的障礙。隨著互聯網史逐漸發展為一個成熟的學科,我們可以預見,隨著本地語言的互聯網史一手研究不斷增加,現有的非歐美背景下互聯網文化的早期研究將做出大幅度的修改。
在對互聯網史的研究和興趣不斷增強的背景下,本章介紹了本書的獨有視角和對互聯網史這一研究領域的貢獻:充分展示掌握互聯網史全球性的迫切性。
一、媒體史研究框架下的互聯網史
讓人沮喪的是,互聯網史的研究發展緩慢,對這一研究領域的認可也很緩慢——至少在參與這一領域的人看來,情況是這樣的。當然,必須承認目前互聯網還處于不斷建設的過程中。如同其他傳媒形式和技術一樣,研究歷史的依據、保證和必要性僅僅需要時間。
畢竟,報紙和新聞界的歷史可能現在已經相對成熟,但是在未來相當一段時間內還有發展空間。盡管人們不斷預測新聞界的消亡,它亦然極具復雜性和吸引力,而且對更廣泛的歷史研究也有重大意義。最近一個充分發揮其研究潛力的例子是電視的歷史。電視作為媒體已經發展了好幾十年,用于支撐電視史研究的基礎已經逐漸成型,目前有私人收藏庫和檔案庫,也有大眾檔案庫和商業檔案庫作為補充,研究概念、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已經多樣化,也有不少研究項目正在進行。
還有許多其他與互聯網史研究相近的例子,最值得一提的是計算史研究。從事計算機技術、信息科學、信息技術學科、科學技術研究等領域的學者,以及歷史學家,不少都對計算史有著強烈的興趣。這種興趣的結果是強大的資源和支持,包括專門的學術和職業團體,獎勵、獎項和助學金,頗具規模的資料庫和檔案庫,以及不斷發展的分散式專業知識和越來越多感興趣的研究人員致力于開發該領域并保持發展勢頭。還包括重要學術期刊,如《IEEE 計算史年鑒》(IEEEAnnals of the History of Computing)和《信息和文化:歷史期刊》(Information & Culture:A Journal of History)。
并非所有的互聯網研究都在大學進行。就像電話全盛時期的貝爾實驗室,或互聯網和移動通訊歷史時期的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署(DAPRA,US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和日本電報電話公司(NTT)(Goggin,Ling,and Hjorth 2016),在當代互聯網研究中,重大的、高價值的研究正在通過領先的行業研究實驗室(尤其是微軟實驗室和英特爾公司)的研究人員產生和流通。然而,這些得到行業或商業贊助的研究并不關注互聯網的許多方面。例如,某些應用所吸引的使用人群可能與其設計方或贊助商的本意有別(參見麥克利蘭〈McLelland〉的章節中對日本早期計算機網絡的討論、趙棟元〈Jo〉的章節對韓國早期互聯網文化的討論,以及謝弗和蒂埃里〈Schafer and Thierry〉的章節中對法國米尼特爾〈Minitel〉系統的討論)。
電話和電信的歷史是另一個頗具說明作用的例子。在這些領域,研究更為分散,不同研究之間缺乏系統的整合和培育,并且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解除電信管制以來,這一領域來自行業的資金和動力已經耗盡。盡管如此,該領域依然產生了很多重要的研究,涉及各個不同的學科,包括歷史、經濟、法律、社會學和傳播學等(Fischer 1992;Hills 2007; Moyal 1984; Rens 2001)。然而,目前來看,盡管學界對移動通信的發展進行了廣泛的研究,這方面的系統性研究還很少,特別是缺少全球背景下的研究(Agar 2003)。考慮到全球上億人只能或主要通過移動手機(越來越多的智能手機)使用互聯網,這方面的研究更是尤其重要,這也是2015 年互聯網協會《移動互聯網的演變和發展》(Mobil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報告所強調的(Internet Society 2015)。
更另人驚訝的是,傳媒史作為一個發展完善的領域,在相當一段之間之后才把互聯網史作為該領域研究內容的一部分。之所以產生這種現象,部分是因為技術本身不斷變化和發展,隨時會出現新的重要應用,需要進行分析和解讀。隨著新的應用和內容的不斷迅速出現,現有的程序和內容正在進行更新或刪除。正如Brugger 所著的章節中指出的那樣,對網頁資源進行存檔的過程并非易事,因為網頁中有著極為密集的互文“內容”,所以幾乎無法把某一特定時刻組成網頁的超鏈接全部保存下來。舉例來說,某位媒體歷史學家想要說明雅虎地球村網絡托管服務(GeoCities web hosting service)如何讓第一代公共網絡用戶熟悉個人主頁的功能可見性(affordance)。據報道,該服務于2009 年關閉前共產生了3800 萬個網頁(Shechmeister 2009)。雖然他努力對這些網頁進行了存檔,查閱全部網頁的過程依然困難重重。
另一個困擾互聯網史的問題與媒介(medium)的定義有關。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整個媒體史的普遍問題。互聯網在其相對短暫的歷史中已為廣泛的用途和應用程序提供了支持。“互聯網”這個詞常被用來指代各種不同事物,我們不會是第一個指出這個問題的人。對這一概念的最佳定義仍然是技術上的規定:互聯網以作為其技術體系核心的協議為中心,即包括與TCP/IP 協議有關的的各個層級(layer)、元素(element)和應用程序。在20世紀60-80 年代中期,人們關注的重點是互聯網的發明,以及互聯網在有限幾所機構、部門、國家和社會團體中的應用。當時,至少從技術歷史這一傳統角度來看,互聯網是什么樣子比較容易界定。計算史方面的資料、電信基礎設施和治理等方面的資料都容易收集,這些資料的相關性也很強。隨著九十年代初期到中期互聯網的普及,我們需要認識這種新的媒體形式;而對互聯網的認識又決定著我們如何理解媒體和媒體的作用。當然,互聯網從誕生之日起,本身就是一種媒體。所以對媒體史的研究需要把互聯網囊括在內。作為一種媒體形式,互聯網史與演講史、新聞史、電影史、廣播史和電視史一樣,亟需我們進行研究。
互聯網史正式作為媒體史研究的一部分而受到認可,還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因為互聯網是一種相對新興的媒體形式,因此對這一領域的專門歷史研究還處于萌芽狀態。研究所涉及的概念上的、研究方法上的和收集檔案上的難點也尚未得到妥善的解決。從事互聯網史研究的人可以從其他媒體史研究中獲得啟發,也可以對其他研究進行靈活運用和充分整合。例如,我們考察八十年代末互聯網的興起時,需要考量一系列令人困惑的技術、應用程序、文件格式和使用方法。當然,我們依然可以用TCP/IP 協議來判定什么是互聯網,什么不是互聯網——至少表面看起來如此。然而,隨著物聯網的發展,或者互聯網與無線技術、移動電話、廣播、傳感器以及其他網絡和技術的交織而產生的雜糅性,對互聯網的恰當界定,以及對哪些互聯網史與研究相關的界定更顯得尤為重要。
另外一個問題是,如同對媒體、對文化的理解一樣,目前互聯網的主要概念還基于有限的互聯網經驗、使用和概念,也主要是從英語用戶、特別是北美用戶的視角出發,因為北美和一些歐洲國家是最先使用互聯網的地區。英語用戶的文化、語言和社會價值觀對互聯網的影響很大,甚至鐫刻在網絡技術協議層面上。例如,互聯網域名使用的是英語。然而,在如今的互聯網上,英語已經成了少數語言。使用漢語、日語、韓語、西班牙語、俄語和其他語言的群體迅速增加,并在各種互聯網技術、應用和文化的發展及本土化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考慮到互聯網史領域本身的構成,我們認為該領域的誕生必須是全球范圍的——或者至少是在全球范圍內重生。
二、互聯網史——生而全球?
從某種程度而言,互聯網技術與報紙、廣播、電影、電視等其他媒體形式不同。后者起源于多個國家,歷經幾十年的發展,然后才成為全球傳播網絡的一部分。以電影史為例,19 世紀末,彼此獨立的電影業在英國、德國、法國、美國等不同國家同時興起。然而,互聯網的早期歷史與美國的創新活動緊密相關,因為美國軍方對計算機骨干網的必要基礎設施提供了資金支持。對許多國家而言(日本和法國例外),最初的計算機網絡需要與美國已經建立好的基礎設施建立連接。這就使得這些國家和美國以外的計算機廠商必須接受美國設立的協議和使用條款。雖然在八十年代早期,在法、日等國有一些獨立的國家計算機網絡,在美國也有不接入互聯網的計算機網絡(Aspray and Ceruzzi 2008; Carey and Elton 2010),然而,當80 年代末國際互聯網連接可以使用時,這些系統都停止使用了。因此,可以理解早期的互聯網史主要是關于美國互聯網的發展,北美以外的許多互聯網史也都強調本地互聯網與美國技術骨干網的首次連接。
我們常常忘記,早期電影是默片,可以為不同的觀眾提供不同的字幕。然而,互聯網上的信息與此不同。在80 年代末到90 年代初,互聯網上的大部分資訊都是英語。因此,主要是大學的研究人員和計算機愛好者對這些信息感興趣,他們也是非英語國家最早的互聯網用戶。日語、西班牙語和中文用戶的迅速增加減少了英語在總體語言使用中的比例,但直到90 年代末,英語還是互聯網上的主要語言。對英語的偏愛不僅僅是美國技術文化前身的產物,也是輸入和顯示文本所必需的計算機代碼的一部分。美國信息交換標準碼(ASCII)最初在1963 年開發,只能輸入并顯示羅馬字母以及與英語相關的數字和標點符號。特殊字符的輸入和非羅馬字母特別是漢語和日語等基于字符的腳本的調節是個重大問題,經過20 年的研究和創新才得以解決。標準英文打字鍵盤(QWERTY Keyboard)最初發明的時候,是為了避免19 世紀打字機經常出現的英語單詞字母組合(例如th 和st)的干擾。然而,讓人驚訝的是,這樣的鍵盤依然是目前主流的人機交互界面,即使在不使用羅馬字母進行日常交流的國家(譬如日本)也是如此。語言(包括其文字系統)和文化的密切聯系意味著有些國家在初期使用互聯網時,相對于其他一些國家而言更具優勢。這也說明,技術的設計和應用從來都不是中立的。因此,互聯網技術的全球史不應該假設技術的中立性,而應一開始就研究不同的當地文化和社會環境。
本書的重點是論證以下觀點:要充分理解互聯網、特別是互聯網研究,需要接納、回應、研究并深入了解在互聯網技術的早期應用階段,不同地區的本地因素。這些因素目前依然繼續形塑著不同國家和不同語言社區的互聯網文化。互聯網史有一套同時位于不同地區和不同情況下的全球坐標體系。如果不能理解這種多樣性,我們充其量只能得到一幅不完整的畫面。本書旨在引導并激發互聯網史的根本擴張,使其跨越更廣泛的全球、國際和比較的維度。這樣做的原因不僅是因為這會讓互聯網史更為完善、準確和豐富,也是因為這樣的歷史會讓我們對互聯網本身有更深入的了解。本文認為,對全球互聯網史的深刻認識將有助于我們理解歷史在當前和未來對互聯網闡釋的使用和濫用。因此,本書延續了互聯網研究中一個不斷發展的主題:從國際視角理解技術及其文化的必要性。
三、互聯網研究的國際化
互聯網研究是一個跨學科領域,迄今已有20多年的歷史(Jones 1999; Consalvo and Ess,2011;Dutton 2013)。這一領域吸引了全球的研究學者,并一直以北美為中心,而且越來越多地以歐洲為中心。互聯網研究協會(AoIR)首屆會議(IR1)以《跨學科現狀》(The State of the Interdiscipline)為標題,于2000 年在美國堪薩斯州勞倫斯舉辦。除了在亞太舉辦的兩次(2006 年澳大利亞布里斯班舉辦的IR7 和2014 年在韓國大邱舉辦的IR15),2000-2017 年間的十八次會議中,七次在美國舉辦,五次在歐洲,兩次在英國(至本文截稿時仍是歐盟的一部分),兩次在加拿大。從很多方面來說,互聯網研究是一個開放的領域,歡迎不同國家、語言和文化視角的研究。然而,通常情況下,這一領域的研究框架(如AoIR 會議中使用的研究框架)還是以美國、歐洲和其他英語國家為中心(我們注意到澳大利亞在互聯網研究的發展和認同方面進行了大量研究;尤其是1999 年Matthew Allen在科廷大學設立了第一個互聯網研究課程)。互聯網研究和IR 會議的大多數參與者來自多個學術團體和協會,因此為這一領域的國際交流帶來了其他的經驗和資源。
考慮到在許多早期的互聯網文化報道中存在對英語的偏愛,于2009 年出版了《互聯網研究的國際化:超越英語范式》(Goggin and McLelland 2009)一書,以強調和支持互聯網研究的多文化、多語言和國際多元化工作。該書的研究基礎是大量關于語言和技術之間關系(與互聯網相關,特別是Danet and Herring 2007)、文化與技術之間密切聯系的理論化(指的是富有成效的聯系,而不是許多公眾普遍認為的非西方國家的某種單一和落后的“文化”是技術進步的巨大障礙),以及國際視角下互聯網技術研究的著作(Hunsinger,Klastrup,and Allen 2011)。
現在“國際化”(internationalizing)轉向已經確立,這一轉向既有其局限性,也有其優越性。它與“去西方化”(de-Westernizing)、“后殖民主義”(post-colonial)、“世界主義”(cosmopolitan)等方法并行發展,有時有些不穩定。然而,隨著它的發展,近年來,在互聯網研究領域,精靈已經完全跳出了瓶子的國際化趨勢已經萌芽。我們注意到中國和印度等新興大國的復雜崛起、俄羅斯的回歸和世界其他地區的各種復蘇。如果這不是“中國世紀”,那就是“亞洲世紀”,需要轉向“亞太”(對美國而言);又或者是“拉美世紀”、“非洲崛起”、“金磚國家”的興衰,以及阿拉伯世界的持續關鍵地位和發展。拋開這些口號不談,顯然,地緣政治以及區域內、國家內、次國家和散居地(diaspora)的重新配置正在經歷一個漫長而持續的過程。這給互聯網研究帶來了諸多挑戰,也帶來絕佳的機會。
其中一個關鍵的挑戰在于國際上將研究和大學組織起來,以及對研究和研究人員(和基礎設施建設)在經濟上的贊助、評估和報酬。一段時間以來,大學一直圍繞著全球市場“競爭”的定位,尤其是對生源的競爭,也包括對科研經費、學校聲譽和影響力的競爭。國家系統依然對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大學有決定性影響,這也加深了學校對相對少數學術質量評價指標的依賴。這些指標往往把英語作為唯一的全球科學傳播和交流語言。最著名的期刊排行榜是湯森路透科學網(Thomson Reuters Web of Science)的期刊排行,還有Scopus 和最近的谷歌學術排行。在這些期刊目錄中,可以參與排名的期刊絕大數使用英語。這種英語的主導地位受到越來越多的挑戰,各主要學術協會都對國際化需求做出了回應。國際傳播協會(ICA)力圖超越其北美中心,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國際協會為此它在拉美、亞洲和其他地區召開了區域性的國際傳播協會會議,并已發起和支持兩份中文和德文期刊,作為其享有盛譽的學術出版物的一部分。國際媒體與傳播研究協會(IAMCR)在其創辦組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授意下,特別是在其“主體世界”(majority world)成員的努力下,已經長期致力于多語言的、真正意義上的世界性研究。當然,IAMCR 及其會議主辦方在使用三種官方語言(法語、西班牙語和英語)召開學術會議方面還有不少實踐上的、資源上的困難;更不用說協會成員的各種語言問題了,其中許多成員依然繼續使用歐洲主要語言之外的語言運營和出版刊物,這些刊物在其社群和勢力范圍之外很少得到承認。盡管如此,在不同的研究領域,已經有大量的國際化實踐活動。例如,在區域研究或亞際文化研究等領域,跨文化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以及多語言、多文種的出版行為已經比較普遍。
這種情況被人們認為是理所當然的。許多人會說大學是非常世界性的全球機構。在那里,研究——尤其是互聯網時代的研究——應該在世界各地的團隊和群體中開展、流通和利用。哪種語言便于操作,就使用哪種語言。我們并不否認這種觀點,但是那里也存在許多鮮為人知或討論不足的差距、損失、勞力和協議條款。特別是在互聯網這一領域,對互聯網史全球坐標的認識上的不足、或是研究上的不夠深入,導致我們對互聯網意味著什么、互聯網會變成怎樣的認識是極度匱乏的,至少是相當片面的。
在《全球互聯網史手冊》一書中,我們希望通過書中各章節對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國家和區域的互聯網發展情況的詳盡的和對比的歷史研究,對“互聯網(the Internet)”是一個“去地域化(deterritorialised)”的技術這一概念提出質疑。正如伊藤(Ito)所言,技術并不是通用的;反之,我們必須關注“技術在跨國家舞臺上的異質同構性(heterogeneous co-constitution)”(Ito 2005:7)。因此,要深入理解互聯網,應該充分了解相關的不同使用文化,而這些使用文化很大程度上受到語言、文化和地理位置的影響。我們的假設是,一旦如此詳細的、多樣化的互聯網圖景被組合起來,就有可能通過所謂的“全球在地化(glocal)”(或是全球化/本地化)想象(imaginaries),對技術的全球性或國際性特質有更深入的了解。正如本書所證明的那樣,“全球互聯網史”(global Internet histories)是一個方便的術語,可以豐富、擴充、整合、催化有關互聯網的廣泛資源、調查、概念和對話。
我們常常忽視以下情況:已經寫就的互聯網史的傳播和應用塑造和想象了今天的互聯網。奇怪的是,人們已經并且正在研究互聯網史,而且不僅僅是用英語進行研究!因此,跨互聯網、傳媒、文化和技術研究的一項基本任務就是翻譯這些“錯過的敘事”(Campbell-Kelly and Swartz 2013)。
四、章節概覽
手冊類圖書的優勢之一是,可以呈現不同領域的大量研究,并可以使章節之間形成對話關系。為了鼓勵閱讀某些特定章節和其他同類章節,我們把本書中的內容分成七大主題(參見下文目錄)。
本書的第一部分是“構建概念和研究方法”。這部分中的章節探討了互聯網史研究中出現的困難、方法、偏見和倫理問題。幾位作者在闡釋互聯網應用在具體地區環境下所產生的不同聯系點和多樣性方面,在研究方法和認知上保持了高度的自知性。例如,羅賓·曼賽爾(Robin Mansell)探討了與互聯網意味著什么或是代表著什么有關的各種“社會意象”(social imaginaries)如何影響關鍵的政府或產業人士——這些人的決定又進一步影響到整個技術的推廣和管理。然而,僅僅關注這些關鍵人物的互聯網史忽視了技術可以經過多種途徑為不同的權益相關者所重新想象(reimagine)。作者鼓勵我們考慮個體如何把自我想象為積極的技術施動者,而不僅僅是技術使用者。查爾斯·艾斯(Charles Ess)的文章指出,自1998年文化態度與通訊技術(CATaC,Cultural Attitudes towards Technology and Communication)系列會議以來,互聯網研究一直在其框架內進行。艾斯認為,在研究和理解互聯網的過程中,對技術的文化構架起到關鍵作用。文中特別指出這樣一個傾向:研究往往僅依賴來自一種語言(即英語)的信息,在美國進行的研究尤其如此。作者注意到,文化態度與通訊技術系列會議首次在挪威的奧斯陸舉辦國際會議,迫使美國的參會者考慮網絡配置(configuration)的某些方面為當地參會者帶來的困擾。例如,挪威語的三個常用的元音(φ,?,?)當時并未收錄在美國信息交換標準碼中,這就需要挪威的參會者對自己的名字進行音譯,這樣才能顯示在互聯網搜索引擎中。
尼尚特·沙阿(Nishant Shah)對互聯網史在印度的情況進行了綜合全面的介紹。文章中提了到作者主持的里程碑式項目,該項目得到位于班加羅爾的互聯網和社會研究中心的支持。沙阿反思了不同的互聯網史,對互聯網史編纂進行了有啟發性的、豐富的思考。他提出了研究印度互聯網史的三個著眼點,對互聯網的國際化思考極有裨益。這3 個著眼點是:機體(body)、情感(affect)和中間狀態(the state in transition)。沙阿指出,“書寫互聯網在印度的歷史,就是書寫印度的歷史”,這一經典的論述適用于全球各個地區的互聯網史。尼斯·布格(Niels Brügger)撰寫的章節以作者對丹麥的.dk 網域(web domain)進行歸檔的工作為例,探討了對內容進行歸檔的種種困難。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樣,網頁與書籍和電影等傳統媒體完全不同,因為網頁是由超鏈接(hyperlink)構成的,這就使得網頁不是單一的媒體,而是內容豐富的“多層媒體”(strata)。然而,作者指出,建立這樣的檔案很有必要,因為它不僅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互聯網在過去的發展,也可以對當今互聯網上發生的狀況有更深入的了解。
本書的第二部分的內容是“重新思考互聯網的演化過程”。這一部分就如何研究和理解互聯網的各個角度提供了多方面的視角,指出對技術的發展進行準確分析和定位的重要性。瓦萊麗·謝弗(Valérie Schafer)和本杰明·G·蒂埃里(Benjamin G.Thierry)研究了傳說中的法國米尼特爾系統(Minitel system),這一案例經常被作為計算機網絡在北美商業模式之外的一種選擇。謝弗和蒂埃里(Schafer and Thierry)對互聯網在法國的發展進行了生動有趣的描述。在法國,互聯網的發展和與米尼特爾(Minitel)有關的技術系統、生態系統、商業模式和使用方法間錯發展,有時平行、有時互相影響,然而又各具特色、截然不同。兩位作者回顧了米尼特爾和互聯網發展規劃中的“多次逆轉過程”。文章得出的結論之一是:“只有時間才能證明互聯網的米尼特爾化究竟是數據經濟演化中轉瞬即逝的一個片刻,還是由米尼特爾創立,又在幾年后被蘋果公司巧妙地升級的一個永恒的模式。”尼古拉斯·約翰(Nicholas John)的文章與上述討論相關。該文對互聯網服務提供商(ISP,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在以色列的出現進行了細致的研究。考慮到以色列是高科技先驅國家,這項研究頗具價值。約翰指出在互聯網提供商涌現的過程中,不同的社會行動者(actor)對互聯網的理解完全不同;此外,他還討論了在以色列情境下對“以色列特色”的不同理解。約翰引用了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理論,提到在這一階段的特色是不同元素的重合:隨著海外資本和以色列經濟精英的投資,以色列經歷了從“科技資本”到純粹的“經濟資本”的轉變,“當地慣習”(local habitus)和“全球場域”(global field)之間也產生了積極的緊張關系(productive tension)。文章談到對巴西互聯網的研究(參見本書中戴維斯等〈Davis et al.〉的章節),同意我們不應“認為互聯網在新的國家的擴張是理所當然的,我們應抵制簡單的確定性敘事(deterministic narrative)……其次,我們應認識到不同機構在建構互聯網時面臨的種種困境”。約翰引用了曼賽爾(Mansell)的意象(imaginaries)這一概念(參見本書中曼賽爾所著的章節),指出“在社會行動者(social actor)(其實也包括科研人員)可能產生的各種意象中,具備的功能之一是對社會和文化的定位。”這一論述和費爾南多·古提耶瑞斯(Fernando Gutiérrez)對互聯網在墨西哥的演化的章節中所述的觀點一致。正如古提耶瑞斯所言,在早期,大學是網絡連接的重要地區,但是隨著最著名的互聯網濫用的例子之一——薩帕塔國家解放軍(EZLN,Zapatista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的出現,互聯網在墨西哥的發展迎來了關鍵的時期。1994 年1 月1日,服務器設在美國大學的一個網站對反映墨西哥陰暗面的視頻進行了存檔,引發了薩帕塔國家解放軍在網上對其展開的斗爭。墨西哥的“互聯網之年”是1995 年,當年,著名的《勞動報》(La Jornada)報紙在網上創刊,同年,墨西哥政府和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互聯網的基礎架構和網絡接入也發生了顯著增長。古提耶瑞斯引用了國際互聯網調查(World Internet Survey)中的數據,分析了在被不平等發展割裂的國家中,連接(connection)和接入(connectivity)之間的悖論關系。在這樣的環境中,知識、能力和互聯網使用方面的巨大差異與互聯網的融合、創新和意義并存,墨西哥的媒體和文化也經歷著重新定位的過程。
斯圖爾特·戴維斯(Stuart Davis)、喬·斯特豪(Joe Straubhaar)、瑪莎·范托斯-巴蒂斯塔(Martha Fuentes-Batista)和耶利米·斯賓塞(Jeremiah Spence)的章節考察了同樣位于拉美地區的巴西。巴西與墨西哥的情況截然不同。戴維斯等剖析了互聯網在巴西社會的成型,并指出,“在很大程度上,信息通訊技術(ICT,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的融合是由非政府機構的創新性融合自下而上驅動的,這些非政府機構為了滿足用戶的需求,設法創造連接互聯網的新途徑。”然而,正如戴維斯等指出的一樣,“這些工作受到公共網絡接入情況和國家電信市場規則自由化等方面國家政策的很大影響,同時,也受到為了滿足消費者網絡接入需求的私企的影響。”第二部分的最后一個章節講述的是東歐的情況。在這章中,卡塔澤那·卡米斯卡-克羅圖克(Katarzyna Kamińska-Korolczuk)和巴巴拉·科耶斯卡(Barbara Kijewska)對互聯網在波蘭和愛沙尼亞的發展做了生動有趣的對比性論述。互聯網在波蘭和愛沙尼亞發展的同時,也是兩國從蘇聯獨立,重新建設自由媒體系統的時期。兩位作者發現,“今天的年輕一代生來就使用互聯網,他們在私人生活、社會生活和職業生活中都頻繁使用網絡,”然而,“很難預測互聯網使用者的增加是否會帶來公民社會復興的過程中對互聯網信任的增加。”在這個問題上,可以看到波蘭和愛沙尼亞兩國采用了不同的路線。在波蘭,對互聯網的社會角色的警惕性扮演重要的角色;而在愛沙尼亞,兩位作者注意到“人們把創新科技的發展當增強主權的機會。”
第三部分的內容是“早期計算機網絡、技術和文化”。這部分中的章節講述的是前互聯網時代的案例研究,以及早期網絡電腦媒介交際系統(Internet 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s systems)的案例研究。這些章節旨在探討在特定的區域環境下,早期的使用行為如何影響了計算機技術的主流推廣(mainstream roll-out)。考慮到“互聯網”經常被形容為“全球化”的、“去區域性的”(deterritorialized)技術,人們可能會認為使用互聯網的特定文化可以應用于可以接入互聯網的任何地方。然而,BBS 的案例顯示,情況常常并非如此。互聯網技術的哪些部分可以使用、哪些部分受到偏好取決于各種文化因素,包括語言的使用情況、市場和政策因素,如政府規范、競爭和定價等。
卡米拉·巴勒克-勃赫斯(Camille Paloque-Berges)探討了法國互聯網史中不為人知的部分,即從1983 年開始的Fnet 的發展。Fnet 是一個非正式的基礎架構,支持以Unix 操作系統為基礎的開放通訊網絡。正如巴勒克-勃赫斯指出的那樣,Fnet是一種“影子基礎架構”(shadow infrastructure),是一個“非正式的、實驗性的、不被承認的機器網絡,附屬在已有的電信網絡和使用并重路由(reroute)學術界的公共資源的同類型網絡上”。因此,Fnet具有很多后來被認為是互聯網的主導精神的特點,比如“開放性、去中心化的、協作性、多樣化、全球化”這樣的特性。在馬克·麥克利蘭(Mark McLelland)撰寫的章節中,作者探討了日本在使用計算機作為大范圍的日語輸入、顯示和交際語言之前,所必須做出的一些社會上和文化上的轉變。最初,在電腦媒介交際(CMC,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中輸入并傳輸日語復雜的文字系統遇到了很大困難。BBS 系統最初并不是由政府使用,而是由不同的計算機公司使用;這意味著不同公司提供的“個人電腦交際”(personal computer communication)各有其不同的通訊協議。這就產生了一系列的公司“局域網”,約有一百萬日本用戶首次在這些局域網上用自己的母語接觸了電腦媒介交際的功能可見性。90 年代早期,英語在互聯網上廣泛使用,人們需要熟悉英語才能連接國外服務器,撥號上網費用也頗為昂貴。這意味著對大多數日本用戶來說,上網并沒有那么普遍。此外,個人電腦相對較低的普及率意味著直到90年代末可以上網的移動電話發布,日本的互聯網使用率才快速上升。梁麗莎(Li Sha Liang)、林意仁(Lin Yi-Ren)和黃厚銘(Arthur Hou-Ming Huang)合著的章節強調了在臺灣互聯網文化的發展過程中BBS 階段的重要性。與日本的情況類似,早期的電腦媒介交際網絡并非受到政府方案的支持,而是由少數大學校園的電腦高手和電腦用戶開發出來的。然而,和日本只能使用緩慢的撥號上網的情況不同,從1992 年開始,臺灣大學的網絡連接由傳輸控制協議/因特網互聯協議(TCP/IP)模式提供,這就使得多名用戶能夠以相對高的速度連網。臺灣大學在宿舍為學生提供免費網絡,并從學生中聘用了行政人員,這就使得BBS 網絡在學生中迅速蔓延。學生對這些網絡的廣泛參與鼓勵了BBS 在社會活動中的使用,這一特色一直保留至今。趙棟元(Dongwon Jo)的章節考察了韓國的H-mail 系統,該系統是韓國的第一家公共電子郵件服務,于1987 年韓國數據傳播公司(DACOM,Korea Data Communications Corporation)創建。這一章節展示了技術提供者和技術使用者之間的對抗關系如何為早期的網絡社會活動提供了舞臺,也影響了韓國今天的互聯網文化。目前韓國盡管有政府監管,網絡用戶的社會活動依然高漲。伊沃·弗曼(Ivo Furman)的文章考察了互聯網在土耳其的使用情況。文章描述了以Hi! Türkiye 網絡(口語中稱為Hitnet)為中心的充滿活力的BBS(Bulletin Board System①本處并非作者首次提到BBS,然而作者在這里才第一次給出BBS 的英文全文。譯文依照原文標出英文原文。)生態。這些論壇在1992至1996 年間處于活躍時期。土耳其的Hitnet 基于Fidonet 網絡協議。正如弗曼所言,“雖然隨著互聯網時代的來臨,BBS 通訊網絡很快消亡,早期的BBS 用戶依然是土耳其最早的在網絡發布文字的人,也是最早開始通過電子交流進行遠距離協作的人。”弗曼的敘述顯示,BBS 的早期使用者對土耳其互聯網交流生態的成型起到重要的、持續性的作用。
第四部分是“互聯網上的想象社區”。這一部分考察了互聯網及其功能可見性可以讓用戶在特定語言和國家社群中構建想象社區(imagine community)。這些案例研究指明了使用互聯網方式上的多樣性。在亞洲地區,中國是相對較早使用互聯網的國家,上網人群經歷了從個人電腦上網到移動設備上網的轉變。在不丹和巴布亞新幾內亞,互聯網的接入要晚得多,大多數人都使用移動設備上網。對某一社會使用互聯網技術之前的已有傳播系統的狀況的了解,對理解上網人群和當地媒體(如政府報告、科學新聞〈science journalism〉、大眾新聞和廣告等)使用這一新興科技的途徑至關重要。
這部分的第一篇文章是艾尼沙·道迪(Anissa Daodi)對電子阿拉伯語(e-Arabic)的出現的思考。這篇文章具有特殊意義,因為作者對阿拉伯情況的描述展示了大部分英語使用者所不熟悉的情況。在阿拉伯,同一語言社區有兩種不同的語體,但各自的用途不同,這種情況稱為雙語體(diglossia)。阿拉伯語有正式語體和口語語體之分。正式語體的語法更為復雜,多用于書面語。除當地方言外,阿拉伯語還有一種口語語體。因此,在輸入和顯示阿拉伯語時,除了其文字在字符上的特征外,通過電腦使用阿拉伯語進行非正式的書面溝通并非易事。道迪概括了第三種語言形式的緩慢發展,她把這種語體稱為電子阿拉伯語。這種新興語體中有文字上的轉變,也有方言上的雜糅,還有從其他語言引入的外來詞。這一現象引發了相對年輕的上網人群與年長的文化捍衛者之間的對峙,后者認為這種語體是錯誤的、不標準的。道迪指出,這一新興的、不受規則制約的語言形式對年輕人為自己發聲、表達自己的想法和顧慮至關重要。余海清(Haiqing Yu)的章節涉及對中國互聯網的研究。文章的重點不是基礎架構、管理方法和軟件推廣的時間線對互聯網的定義,而是日常上網人群對互聯網的理解。通過這一研究,作者指出從中國的互聯網還能得到很多信息。與對中國的社會和政治層面的負面報道,特別是對“中國防火墻”的報道不同,余指出中國居民自身對未來還持有相當樂觀的態度。她解釋道,對互聯網的講述,和對互聯網擊破階級壁壘、共享信息并連接人群的能力的講述是這種樂觀態度的重要部分。文章提議,對網絡審查造成的阻礙的評價在中國境內和境外有所差異。
里斯·瓊斯(Rhys Jones)的章節探討了早期互聯網在使用威爾士語的媒體中的情況。當時,互聯網技術和美國聯系緊密。人們擔心互聯網會進一步加強英語的霸權地位;少數人使用的語言(如威爾士語)則會成為這一過程的犧牲品。然而,與此同時,不少使用互聯網的人卻反對這一論調,他們認為,電腦媒介交際很可能會讓世界上講威爾士語的人互相聯系,從而推廣威爾士語,這一現象發生在早期翻譯關鍵的計算機和互聯網術語的過程中。在韓國互聯網推廣的最初階段,也發生了這一現象(參見本書中趙棟元〈Jo〉的章節)。邦蒂·埃韋森(Bunty Avieson)的章節中也討論了不丹互聯網對語言使用情況的影響。作者發現,在當地,互聯網引入時,廣泛的民主化進程正在影響著整個媒界。因為當地不少口語語體沒有書面語形式,人們對印刷媒體的接觸受到限制。然而,電腦媒介交際的到來(通常是移動客戶端上網)開創了通過聲音進行聯系的方式,一個不識字的農民僅僅需要學會點擊幾個簡單的圖標,就可以使用APP 和其他使用者取得聯系。信息通訊的功能可見性也為使用者熟悉羅馬字母提供了激勵,他們可以使用羅馬字母對當地語言進行音譯,進而傳達信息。
莎拉·羅根(Sarah Logan)和約瑟夫·諏訪丸(Joseph Suwamaru)合撰的章節講述了巴布亞新幾內亞(PNG)的情況。文章指出,雖然一些巴布亞新幾內亞的教育機構和澳大利亞的大學網絡之間存在速度緩慢的撥號上網,直到2005 年手機市場放開監管,全民上網率才從3%上升到隨后十年的80%。該文章指出,巴布亞新幾內亞主要是一個口語社群,可移動網絡提供的便利——特別是Facebook 上狀態的更新——在該國非常流行。Facebook 也提供了一個平臺,讓處于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國家媒體渠道環境下的人們交流新聞。和巴布亞新幾內亞的情況一樣,緬甸也是近期才普及的互聯網。隨后,移動網絡和移動通訊得到普及,這兩個進程彼此平行,互相交織。里奇·林(Rich Ling)、奇特拉·潘沙帕克派恩(Chitra Panchapakesan)、拉吉夫·拉基特(Rajiv Aricat)、艾莉莎·歐勒加(Elisa Oreglia)和梅·O·勒文(May O.Lwin)的章節也探討了這一問題。該文討論了緬甸人使用移動電話和數據接入的情況,指出“數據想象”這一重要現象在塑造形象、意義和知識方面的作用。文章也指出了使用互聯網的潛在可能,雖然緬甸居民還不能直接使用互聯網。文章還討論了在移動電話在一些商業部門和社會團體中的使用情況及其影響。這些團體包括三輪車經營者、廢棄布料收集者、垃圾處理者、制磚工人、泰米爾語飛地上的居民和農民等。文章指出,“數據想象”這一概念可以幫助我們認識到互聯網普及的過程中人們對數據接入的想象所涉及的各種想法、民間傳說、二手科技、文化適應等因素。
第五部分的主題是“社會互聯網的歷史”。這一部分從歷史角度入手,分析了21 世紀早期的重要發展特征之一:社交網絡系統在全球的廣泛使用和社交媒體的出現。本部分的章節探討了一系列以當地語言、粉絲和社區為基礎的網絡系統。此外,要充分理解某一應用的使用情況,需要了解對使用者有影響力的既有媒體文化,也需要了解產業、政策、社會環境,以及國內外技術的本土化情況。田村匡紀(Takanori Tamura)從歷史角度分析了人類互動如何影響了人們對互聯網的想象。他特別分析了自我敘述(self-narratives)——即人們對自身的描述——這一重要現象。在互聯網時代來臨之前的日本,人們通過電腦媒介交際進行自我敘述。田村認為,在互聯網時代到來之前,人們通過自我敘述在日本國內網絡上進行交際,這為之后的網絡和社交媒體的發展提供了便利環境。這種自我敘述和早期以計算機為媒介的交流模式,促進了私密公民權利(intimate citizenship)的發展,使日本2011 年核泄漏和地震等危機后的社會活動成為可能。蒂姆·海費爾德(Tim Highfield)的文章講述了博客的重要歷史。海費爾德承認,博客如今聽起來已經落伍了。他在文章中提到,“在社交媒體流行之前,博客曾是一個頗具創新、廣為流行社交媒介。如今,在互聯網時代,博客的光輝時代似乎已經成為遙遠的過去。”文章的主要內容是“博客作為交際平臺、寫作體裁和影響力量的歷史簡述”。文中指出,“博客圈(blogosphere)從來都不僅僅是一個談論政治、交流名人八卦的平臺,也不僅僅是個人日記的網絡版。”海費爾德寫道,“博客的歷史是整個媒體圈(mediasphere)歷史的一部分,因為寫博客的人除了寫博客抒發個人感想之外,還閱讀其他博客和媒體,進行評論、提供鏈接并分享其他內容。除了使用自己的博客外,他們也使用其他的交際平臺。”亞可·蘇敏芬(Jaakko Suominen)、佩特里·沙瑞科斯基(Petri Saarikoski)、瑞卡·圖爾蒂艾寧(Riikka Turtiainen)和沙里·奧斯曼(Sari ?stman)的章節考察了歷史對現在和將來的意義,開拓了我們的研究的視角。幾位作者討論了芬蘭的各種社交媒體服務和平臺,這些社交媒體如今大部分已經被人遺忘,包括IRC-Galleria(使用者主要是青少年的相冊)、Jaiku、Qaiku(微博平臺)和Vuodatus(博客平臺)。其實,盡管互聯網在全球的應用情況十分復雜,國家內部和區域內部的社交媒體平臺還是十分活躍。需要記住的是,芬蘭以技術實驗著稱,在全球互聯網文化中扮演重要角色,在移動電話文化中也扮演重要角色。以上3 篇文章提供的案例表明,目前依然有對國家內部社交媒體服務的需要。芬蘭需要為芬蘭用戶提供的平臺,在其他相對小體量的國家也有這種需求。然而,我們對全球各種不同社交媒體平臺的軌跡、意義和經驗還知之甚少。蘇敏芬等在文中指出,在他們的案例研究中發現,“難以預計的是,這些社交媒體和它們的生命周期具有特殊的芬蘭特色,與中國、日本、韓國和日本等大體量國家,或是其他人口稠密的國家相比,沒有太多的比較價值。”正因如此,幾位作者呼吁我們對“對類似國家的案例進行比較研究”。周葆華(Baohua Zhou)、桂師慧(Shihui Gui)、追崎加藤(Fumitoshi Kato)、大橋夏菜(Kana Ohashi)和拉里薩·赫奧斯(Larissa Hjorth)所著的章節探討了世界上兩個最大的市場,中國和日本的大型活躍社交媒體的情況。章節討論的重點是微信和LINE 這兩個融合移動信息平臺(convergent mobile messaging platforms)。幾位作者對比了互聯網興起的兩段不同的歷史,以及從互聯網時代到智能手機階段的轉變。他們指出,“互聯網在中國的興起的階段性相對明顯,從Web1.0……到Web2.0”,日本和中國的情況不同,“因為有手機(日語稱為攜帶keitai)的存在,從早期開始,通過個人電腦上網和通過移動電話上網就已經融合。”除此之外,政府在孵化和激勵互聯網技術中扮演的角色也不同。楊凌(Ling Yang)的文章也聚焦于中國的互聯網。文章討論了中國網絡粉絲社群的歷史、實踐和問題。該文首先討論了互聯網平臺和技術的演化如何促進了網絡粉絲社群的產生,例如BBS,百度貼吧、新浪微博和騰訊QQ 等媒體。文章還討論了粉絲字幕(由粉絲制作字幕的外語媒體)和配對(為明星或媒體上原創故事中的人物進行配對)這兩種網絡行為為對中國的粉絲文化和整個社會的深遠影響。作者指出,雖然網絡上的各粉絲集團可以帶來主動感、認同感和歸屬感,粉絲集團也常常產生激烈的沖突。這些沖突往往與性別問題或政府審查有關。
第六部分的是“網絡及新興媒體形式”。這部分內容中,首先是克里斯蒂娜·司布真(Christina Spurgeon)對全球網絡廣告的發展的各種趨勢和多樣性發展的總結。文章條理清晰,內容簡明扼要。這一研究方向需要大量的國際化研究。在此背景下,司布真號召研究人員“密切注意廣告在闡釋互聯網史方面的重要性”。海斯·馬溫迪·馬布韋澤拉(Hayes Mawindi Mabweazara)的章節探討了非洲的情況,這一案例研究分析了以互聯網為平臺的數字新聞的演化過程,并簡述了相關研究。文章內容全面,分析透徹,提供了理解數字新聞的另一種方式,解釋了數字新聞研究作為西方學者主流知識體系之外的領域,是如何發展成型并繁榮壯大的過程。作者表示,“以互聯網為基礎的新聞的歷史,以及對互聯網和新聞在非洲的相互關系的研究,在許多方面采用了新聞學之外的研究系統,其特色是對互聯網在非洲提供的機遇和挑戰的各不相同的、有時彼此矛盾的意見。”艾莉莎·弗里曼(Alisa Freedman)的章節著眼于數字文學這種媒體形式,數字文學的代表是日本移動電話和網絡小說的出現。對弗里曼而言,這種以互聯網為基礎的數字文學“重新肯定了,而非否定了日本紙質書籍的重要性,為全球由粉絲創造的文化如何進行商業化運作提供了模式”。更進一步說,手機和互聯網小說的情況明確顯示,這一文學形式被新生的“日本互聯網的使用習慣(如上網方式、圖像語言、用戶識別和公司搭售)”所控制和引導。同樣重要的現象是互聯網文化的發展“鼓勵了對日本邊緣社會人群的討論,特別是不良少女和宅男(otaku)”。賽薩爾·阿爾巴蘭-托雷斯(César Albarrán-Torres)的章節探討了互聯網博彩這一少有人研究的現象,文章考察了多個地區,討論了網絡博彩的復雜意義,既涉及發達的北半球國家,也涉及發展中的南半球國家。文章重點討論的是哥斯達黎加的案例,在該國,網絡賭場早在21 世紀初就已設立。文章指出,需要把網絡博彩理解為“長期的文化實踐行為和產業活動對網絡空間的適應,這一適應穿越了空間和司法的邊界”。作者對這一適應過程加以密切觀察,指出隨著互聯網博彩行為在發達國家的擴大,以及在發展中國家涌現的博彩服務器,我們應關注隨之產生的法律問題和勞動力問題。這些問題都是由阿爾巴蘭-托雷斯首次提上研究議程的。安德魯·韋倫(Andrew Whelan)的章節討論了音樂和互聯網這一廣受歡迎的領域。韋倫并未對通常討論的主題進行重新整合,他明確提出,文章并非“典型的對互聯網上出現的數字音樂的編年史,或是對互聯網上音樂的制作、發行和消費的前期的文化的編年史”。文章涉及與網絡音樂的主要互動關系和發展歷程相關的問題,旨在“強調典型的歷史對一些值得關注的問題的合法化或模糊化”。作者特別關注了兩個重要的議題,其一是“音樂分享作為社會媒介行為的實踐配置,這一配置長期存在,并可能與新的發行形式和模式產生互動”。另一議題是“數字音頻因‘互聯網音樂可進行自我交流的特性’而產生的社交屬性。互聯網音樂之所以具有這種屬性,是因為它從誕生伊始,因其設計上和功能可見性上的特性,就體量很小,易于被操縱和重新整合”。第六部分的最后一個章節由特奧多爾·米丟(Teodor Mitew)和克利斯多弗·摩爾(Christopher Moore)合撰,探討了互聯網歷史的一個重要課題——互聯網游戲。和韋倫的文章類似,兩位作者考察的重點從歷史編撰學角度和理論角度出發,重點討論如何通過游戲空間(game space)、游戲技術和游戲模式(modality)①原文在此處有一個下引號(”),但是前文沒有對應的上引號,略去不譯。這一“棱鏡”來“考察互聯網游戲的歷史”。兩位作者強調了“互聯網既為游戲的非物質化提供了可能,又把游戲重新物質化,投入新的全球市場,該市場既有官方消費渠道,也有非官方消費渠道;既有授權商品的發售,也有粉絲的角色扮演(cosplay),還有其他的參與性媒體文化(participatory media culture)行為”。文章發現,“互聯網技術,特別是高速寬帶網絡連接的普及,使得新的游戲空間成為可能,活躍于空間的人群包括重新配置游戲模式的人,同時,產業制作的正式模式中也包括了這些人群,擔任測試員、游戲增強程序(mod)制作者、社區領袖等角色。”
第七部分是“公眾、政治和數據社會”。在最后這部分內容中,幾位作者紀錄并評價了與政治體系的健康有關的問題。這些問題在互聯網的辯論和研究中頻繁出現,然而,在互聯網史如何影響了對這些問題的理解方面,研究還幾近空白。伊勒姆·阿拉圭(Ilhem Allagui)的章節對阿拉伯地區與數字媒體有關的互聯網史和互聯網的角色進行了綜述和反思。近期,阿拉伯地區(特別是該地區的民主化斗爭)受到了廣泛關注。阿拉圭剖析了阿拉伯互聯網史與社會和政治變革有關的重要階段,并指出幾次著名的起義是社會行動者斗爭的結果,并非技術革新的結果。文章發現,“這些起義是線上和線下社會活動者斗爭的結果,其中有些人為國犧牲,有些人幸存下來。”阿拉圭稱,“人們相信‘革命’會自動進行下去”;然而他本人卻認為“革命并不會自動繼續,技術可以賦權于人民,引發并不前后一致的集體行動。技術使得推翻集權政府的人民運動成為可能,但同時也給伊斯蘭國(IS)的“圣戰”軍隊進行擴充和實現其社會政治目標提供了可能”。恩達·蒂里亞圖提(Endah Triastuti)的章節描述了印度尼西亞作為“數字國家”的誕生過程。該文分析了促進印尼互聯網持續發展的各種因素。文章特別強調了“在前專制體制(前總統蘇哈托)垮臺后,媒體文化中權力的流通,特別是在信息通訊技術中的流通”。作者稱,“與印尼的互聯網產生關系就意味著斗爭、濫用、壓迫和對前政權用廣播和電視等傳統媒體強迫人們接受的國家觀念的反抗。”蘇珊娜·薩爾加多(Susana Salgado)的章節探討了非洲葡萄牙語地區各國(安哥拉、佛得角、莫桑比克、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生動有趣的案例。這些國家有著相同的通用語言、也都曾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各國都曾宣稱要建立民主政權。該章的出發點是:“這四個國家的共同點是,國家民主化進程的開始的階段,同時也是互聯網在全球的擴張的階段。”本章的討論很有啟發意義,其中心內容是經歷民主化進程的國家中在網絡上進行政治交流的機會。文章強調了獨立網絡新聞媒體渠道和博客的重要性,也強調了公民在參與政治生活和政治變革過程中使用網絡的重要性。
李光碩(Kwang-Suk Lee)的章節旨在用“綜合的、歷史視角的研究方式”來探討韓國的數字化抵抗行為(e-resistance)。文章綜合分析了“自上而下驅動技術化未來的歷史引擎,例如信息技術政策、政府管理、市場活動,以及其他影響數字技術的權力條件”。文章還分析了“自下而上由互聯網用戶自主建立的數字文化的不同演化階段”。文章強調了韓國互聯網和行動主義的亞文化史,討論了韓國的數字社會活動,強調“在對權力和各種社會影響的編碼過程中,政治緊張局面如何存在”。本書的最后一篇文章是胡泳(Hu Yong)的章節。該文討論了在中國的互聯網發展進程中,從輿論到輿情的措辭轉變,也討論了對信息的管理工作。在一段有力的評論中,作者指出,“輿情監控系統的運作反映了中國互聯網管理的悖論:普通用戶可以接觸到更多的信息,但是對民眾的真實情感的反映卻很少。”作者提出,“從輿論到輿情的措辭上和行動上的改變,是中國的信息管理和社會管理變化的結果。”輿情這一措辭反映了中國力求保持良好政府形象的時代精神;同時,它也是管理民眾的有效方式,阻止其反思基本的民主和社會變革。
結語:互聯網史的未來
2015 年,Thomas Haigh①原文為“Haight”,拼寫有誤,此文作者為Thomas Haigh,譯為托馬斯·黑格。等人編撰的《互聯網史》(Histories of the Internet)特刊序言中寫道:
縱覽學術歷史和流行的迷思,我們認為,互聯網范圍的擴大已經產生了對不同歷史的需求,這些歷史記錄了眾多技術和社會實踐的發展,它們彼此融合,共同創造了今天以互聯網為基礎的網絡世界。
(Haigh,Russell,and Dutton 2015)
隨著互聯網史發展成為一個專門領域,它將越來越需要考慮互聯網在特定地區、特定人群中的實際發展情況;探索主流的敘事、迷思和隱喻;關注互聯網的“小”歷史和另類歷史;調查不同語言和不同文化群體的互聯網史,不同人群的互聯網史(例如“老人”和“年輕人”,被排斥的群體和邊緣人群、少數群體和多數群體),南半球發展中國家和北半球發達國家的互聯網史;也需要考慮跨地區的互聯網技術和文化的交叉融合(crossfertilization),以及互聯網在未曾預計的軌跡上,在地區內、地區間和國際上的交流情況。這通常意味著來自一個充滿生機的互聯網傳媒生態的對當地空間和場所、特定亞文化、一個特定平臺或技術的全新的、密切的、集中的關注。
在參與了本書三十六篇不同國家、地區和主題的案例研究之后,我們清楚地認識到,雖然“互聯網”現在是一個有著“全球”范圍和影響力的技術,特定的互聯網使用文化,特別是西方英語國家用戶更為熟悉的文化,并不能在可接入互聯網的任何地方復制。互聯網技術的可用和偏好取決于地理、相關基礎設施等因素,也取決于市場和政策因素,如政府法規、供應商之間的競爭、定價等等。和這些考量同樣重要的是眾多復雜的文化因素,這些因素很難為外人所識別,在他們無法接觸用當地語言寫就的互聯網文化文本的情況下更是如此。這些不太明顯的因素包括不同地區對傳播概念、信息構成信息使用和分享、隱私和安全問題——以及,最重要的——對閱讀能力的理解。我們所謂的“閱讀能力”,絕非僅僅指可以閱讀和理解傳統書面文本的能力,而是指有效使用當今的融合媒體設備所涉及的全部“新閱讀能力”。
提高閱讀能力的需求的一個方面,是要求我們跳出寫在自己文化中的對互聯網是什么或意味著什么的一套假設,認識到另類互聯網史和互聯網使用文化的重要意義。與其將其他地區視為在“追趕”當前西方模式的過程中,我們更需要認識到,互聯網文化的地方實例如何提高了我們對技術及其功能可見性的整體理解。
(Routledge Companion to Global Internet Histories)
杰拉德·戈金、馬克·麥克利蘭編
紐約:勞特利奇,2016
譯文說明
1.原文為學術論文,翻譯時的首要考量是譯文可以幫助讀者盡量準確地理解原文、檢索原文提供的大量學術信息。
2.為保證譯文準確性,翻譯時盡量貼近原文。譯文中可能有少數不符合中文習慣的表述,如進行靈活翻譯,可能會改變作者本意,故盡量照原文譯出。
3.文中涉及的傳媒學、社會學和計算機方面的術語盡量按已有通用譯法譯出。原文為論文集的前言部分,大量內容是對論文集中章節的總結介紹。因并未提供各章節內容,僅憑前言中的簡短介紹,無法準確把握各章內容。故術語翻譯可能有不盡準確之處,特在譯文中標注原文,并提供術語對照表,以供參考。
4.因并未要求翻譯參考文獻部分,特保留原文中文內引用部分的外語人名,以便直接根據文內引用人名查找對應參考文獻。
例:(譯文第7 頁正文部分)
當時,《網絡雜志》(Wired Magazine)一度廣為傳閱(Flichy 2007)
(原文第20 頁參考文獻部分)
Flichy,P.(2007)The Internet Imaginaire,Cambridge,MA:MIT Press.
5.本互聯網手冊中收錄章節的作者名和正文部分出現的人名均按習慣譯法譯出,并提供人名對照表。人名音譯(尤其是中文、韓文、日文名的音譯)僅供閱讀便利,查閱相關文獻時建議使用外語人名。
6.文中的組織機構、會議名稱、書籍雜志名稱均在括號內標注英文原文,以便檢索相關信息。
7.原文少數疏漏之處用腳注標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