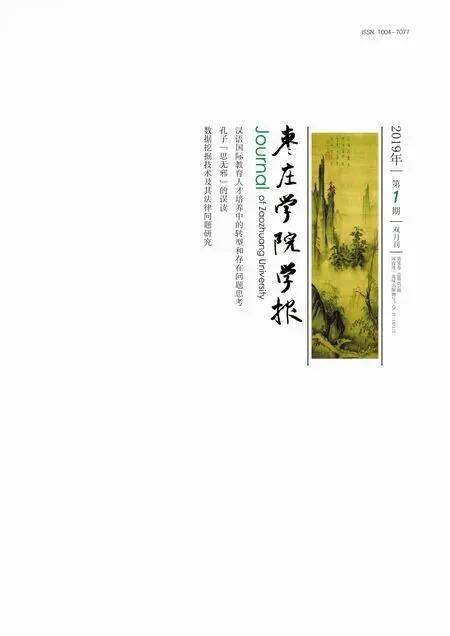多維文學時空的建構
——閔凡利新論
裴爭
(棗莊學院 文學院,山東 棗莊 277160)
每個作家都活在兩個時空里,一個是他生活著的真實的社會時空,一個是他創造的虛構的文學時空。對于社會時空,作家跟我們每一個普通人一樣,被生活裹挾著、推動著,身不由己地往前走;而對于他自己創造的文學時空則不同了,在這個時空里,作家就像一個高級建造師,他挑選甄別各種材料,搭建起一個超越時間藩籬和空間界限的超級時空。作家的兩個時空并不是彼此隔絕孤立的,它們有時候相互并列、平行運行,有時候又相互映照、彼此糾纏,有時候還會交錯疊加、互為表里,它們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雖然作家的文學時空完全是他個人建造的,但其中的建筑材料卻是來源于真實的世界,但是由于加工的方式不同,這些材料在新的時空里呈現的方式也是千奇百怪、變化萬千的。對一個作家來說,要想構筑他自己的文學時空,他需要利用方方面面、形形色色的“建筑材料”,這些“材料”包括:歷史傳統、人文思想、地方風俗、時代思潮等等,更重要的是還要有作家本人的個人意識、獨立思考、體察領悟、責任擔當……來對這些“建筑材料”進行加工、修飾、雕琢、鍛造等,只有這樣,一個宏偉、瑰麗、迷人的文學世界才能夠真正建成。閔凡利就是這樣一個構建了自己獨特的文學時空的新銳作家,他用近20年的創作構建起一個由虛而實、由幻而真的多維文學空間。
一、玄禪哲理的心靈空間
不同于一般作家,初涉文壇的閔凡利較早熱衷建構的是一個玄虛而抽象的文學時空,他自創了一種所謂的“新禪悟小說”。其實“新禪悟小說”這一稱謂存在諸多不科學之處,首先,在中國的文學歷史上并不曾存在過一個“禪悟小說”的文學流派,既然不存在“舊”,那么“新”也就無從說起;其次,閔凡利的這類小說并非宗教文學,也不是對禪宗教義的弘揚和感悟。據悉,閔凡利本人也不是佛教徒,也無意為宣傳某一種佛教理論而創作,盡管如此,“新禪悟小說”的名稱里有一個“禪”字卻不能說跟禪宗毫無關系,但二者的關系并不在于表面名稱的借用,而在于內在思維方式上的不謀而合。
禪宗是中國佛教宗派之一,禪宗的這個“禪”字本來是從巴利文Jhāna “禪那”音譯來的(梵文是Dhyāna),“禪那”的漢譯為靜思,是指上升到某一種境界、層次的冥想。但“禪”在中國卻獲得了另外一種理解,它是指對本體的一種領悟,或是指對自性的一種參證。禪宗祖師一再地提醒弟子,不可一味地去冥想和思索,否則就會失去禪的精神。胡適一貫認為中國禪并非來自于印度的瑜珈或禪那,相反的,卻是對瑜珈或禪那的一種革命。也許這不是一次有目的的革命,而是一種基于中國文化的自然轉變,但無論是革命或是轉變,“禪”不同于“禪那”卻是事實。中國人把“禪”解作頓悟,是一種創見,是中國文化接納外來文化時把其融匯到中國傳統文化體系的過程,也足證中國人不愿囫圇吞棗地吸收印度佛教,而是把其本土化、中國化,這種“拿來主義”為我所用的精神正是中國文化長久屹立不衰的根源所在。
理解了中國禪宗的宗旨和其對印度佛學的改造,我們再來看閔凡利的“新禪悟小說”就能發現他們之間的相似之處。二者關注的都是心靈、情感的自然流露和展示,而非形式上的殫精竭慮地冥想和行為上的不遺余力地追求。閔凡利曾經在一次訪談中這樣定義“新禪悟小說”:“所謂‘新禪悟小說’就是以佛道中人的故事為背景,通過他們的生存狀態和心路歷程的追訴,展示生命的禪機和玄妙。”[1](P56)盡管閔凡利經常在“新禪悟小說”中借佛門中人來說事,但在具體的作品中,真正領略其“禪悟”精神的卻不一定是僧人和尚之流,他把故事設定為禪佛的背景,只是為了借用他們的身份境遇達到一種自我反思的目的。因此,所謂“新禪悟小說”其根本乃是一種哲理小說,是對社會、人生、自我的一種感悟和哲思。比如他的“新禪悟小說”的開山之作《神匠》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以塑造女神像著稱的神匠接了一個和尚的活兒,和尚要在自己20年化緣所得的新廟宇里塑一尊觀音的神像,而且要以他提供的一個女子的畫像為藍本。觀音像塑好后,神匠先給神“洗塵”,就是往神身上涂抹他的汗水,因為神匠認為:神有了人味神才是神,神才能活。然后,他給神“安心”,因為:“神是人變的,人和神都是一樣的,都有心。”[2](P2)但這次神匠給這尊觀音安的“心”非同尋常,竟然是他自己的心。為了讓這尊觀音更靈動逼真,他把自己的真心獻了出來。原來,和尚提供給神匠的這尊觀音像是神匠已經去世的妻子,神匠第一眼就認出了自己妻子的畫像,但他仍然用自己的真心為和尚塑造了這尊觀音像,為的是和尚也曾經愛戀神匠的妻子,和尚出家就是因為這段無法忘卻的情感,而此時面對神匠的真心,和尚終于明白:真正能夠贏得感情的不是物質和名利,而是汗水和真心。《神匠》奠定了閔凡利“新禪悟小說”的所有基石,所謂“禪悟”乃是“人悟”,所謂“神性”乃是“人性”,“新禪悟小說”悟出的都是人世的真理和真情。從這個角度來講,可以用一個更寬泛的概念來概括閔凡利的“新禪悟小說”,那就是“哲理小說”。
如果說對人的本性的領悟是閔凡利“新禪悟小說”跟禪宗在本質上的相同點,那么“頓悟”則是二者在表現形式上的相同點。它通過正確的修行方法,迅速地領悟佛法的要領,從而獲得真理。這就是禪宗的不著一字得真諦的原理。這一“頓悟”的法門被閔凡利充分地應用到自己的“新禪悟小說”中來,雖然他不可能做到“不著一字”,但他卻做到了使用極少量的文字來闡明一個深刻的道理。為了最少最經濟地使用文字,閔凡利的“新禪悟小說”幾乎都是以“小小說”這種最短小精悍的藝術形式出現的,很少有長篇大論。閔凡利用小小說的形式來表現“新禪悟小說”恰如禪宗用頓悟的法門來修行。但另一方面,文字的少并不表示思想含量和價值情感的少,有時候甚至恰恰相反,深藏在文字背后沒有說出的哲理反而更多,這也是閔凡利對小小說情有獨鐘的主要原因。他曾經這樣評價小小說:“小小說是精致的、精妙的、易把玩的。作為此種文本,形式限制了她是短小的,然而她的內蘊卻不短小。就如一杯海水與一盆海水,雖然態勢上數量上有大小多少之分,但他們都是水。都是海的一部分。內里都有海的深邃和驚濤的聲響,她的心野無垠而空曠,似天空一樣高遠而遼闊。這是小小說的意境。”[1](P49)這也正契合了閔凡利所推崇的海明威的“冰山理論”,露出來的僅僅是八分之一的冰山一角,另外更多的理念和情感深藏在文本的深處,需要讀者自己去發掘。《神匠》也是閔凡利對海明威“冰山理論”的最好驗證。閔凡利在他的一篇文章《<神匠>寫作的前前后后》中曾經提到,有了這篇小說的思路后,他曾經計劃把《神匠》寫成一個中篇,筆墨的重點放在那個女人身上,而且已經寫了接近兩萬字了,但后來他放棄了原來的想法,把女人作為一條暗線,把和尚和女人的感情也作為暗線,原來的近兩萬字最終僅用了三千字就把所有的理念和情感都充分完整地表達了出來,而且絲毫不遜色于一個中長篇小說的含量,甚至由于用筆的含蓄,給讀者留下了更大的藝術想象的空間。
盡管閔凡利的“新禪悟小說”跟禪宗“頓悟”的形式有諸多暗合之處,但閔凡利的禪悟小說畢竟不是宗教故事,我們讀這類小說跟讀宗教故事會有不同的感覺,原因就在于它是閔凡利獨立的創作,無論是在結構的謀篇布局還是在語言的風格特色上都能顯示出作者獨具的匠心,個人風格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如果要追根溯源“新禪悟小說”的材料來源,只能說它們來自于作者本人的心靈感悟和哲理思索,來自于作者坎坷曲折的人生道路和心路歷程的外化,也是作者經過深思熟慮后得出的人生價值觀。只有了解閔凡利的奮斗道路才能真正理解他為什么曾經熱衷于這種飽含人生哲理的“新禪悟小說”。閔凡利出生于20世紀70年代初山東滕州鮑溝鎮的一個農民家庭,不同于當代文壇上大多數的作家都有過大學教育的經歷,閔凡利沒有名牌大學的學歷背景,更沒有顯赫的家世依托。由于家境貧寒,初中畢業后閔凡利就過早踏入了社會的大門。20世紀八九十年代,當社會進入一個經濟利益和物質主義至上的時期時,一無所有的閔凡利曾經經歷過相當艱難的一段歲月,坎坷的經歷讓閔凡利習慣于深思,當同齡人在紛紛討論下海、經商、升官、發財的話題時,閔凡利卻在思索人生的價值和意義,因此,當他把個人的生存之路和人生的價值所在統一起來時,呈現給我們的便是一篇篇短小精粹的哲理小說,這是他初涉文壇的藝術奉獻,也是他體察人世滄桑后的個人選擇。因此,閔凡利建造的這個玄禪哲理的文學空間最重要的材料不是禪宗佛教,而是他個人的藝術心血和哲理思索。這個時期的閔凡利追求的是唯美的藝術,他追求主題的深刻、玄奧,追求人物內心的純凈、簡單,追求敘事的凝練、明快,追求語言的簡潔、精致。總之,閔凡利小說創作的起點是空靈的、玄禪的,是藝術至上的。
二、俠儒交織的江湖世界
除了“新禪悟小說”,筆者關注到閔凡利的另一個文學時空是俠儒交織的江湖世界,這個文學時空主要由其小說《死貼》《活鏢》等武俠小說構筑而成。閔凡利的武俠小說在很多方面都有金庸武俠小說的影子,離奇的故事情節、鮮明的人物形象、深刻的文化內涵,唯一不同的是閔凡利武俠小說基本都是短篇,而金庸的小說基本都是長篇。閔凡利的武俠小說盡管篇幅短小,但內蘊卻是異常豐富,可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死貼》是閔凡利武俠小說的代表作,這是一篇不到三千字的短篇,卻最終被改編成一部長達九十分鐘的電影,足見其內涵的豐富程度。在當今這個短篇的素材時常被寫成長篇的時代,閔凡利反其道而行之,足見其文學旨趣的不同凡俗。而就武俠小說本身來說,閔凡利的追求也的確跟一般意義上的武俠小說有所不同,原因是他的武俠小說所建構的這個世界不是一個純粹的江湖世界。他所建構的江湖世界總是混淆著俗世道德,黑道規矩中夾雜著“白道”精神,俠義英雄也是儒家精英。《死貼》就很好地體現了閔凡利的這一武俠小說理念。表面看來,《死貼》寫了一個充滿傳奇色彩的江湖世界。江湖第一大殺手集團血光門是一個極其看重江湖規矩的門派,講義氣,重然諾,接過的貼從沒有誤過。這一次,血光門的主人接了一個頗為棘手的死貼,刺殺善州的一個愛民如子眾口皆碑的地方清官孟仲,為完成這個帖子,主人特意派了他最得力的殺手如蟻,如蟻殺人從未失過手,他有一個規矩,在刺殺自己的對象前總要替他們做一件事,讓他們無牽無掛地走。這次也不例外,即將被刺殺的孟大人讓如蟻替他去綁架地方首富黃玉霸,好獲得一大筆贖金,為的是籌集款子在善州的荊河上游修一道堰閘,防止荊河泛濫成災。如蟻幫孟大人籌集到修建堰閘的款子,并給孟大人留出了一個月修堰閘的時間。當堰閘完工后,孟大人主動以身試劍,就在孟大人倒下的那一刻,如蟻的主人趕到,此人竟然是孟大人的哥哥,更出人意料的是這個死貼就是孟大人自己差人送給哥哥的。孟仲導演這出戲主要目的是想利用江湖手段籌集款項,整修堰閘,為民造福,另外一個私心就是希望以自己的死勸諫哥哥退出江湖,不再殺人。《死貼》這部小說真正的過人之處不在于結尾的出人意料,而在于它顛覆了所謂的武俠世界。首先,閔凡利所建構的這個武俠世界并不是一個純粹的江湖世界,它是一個正統儒家文化和民間俠義文化綜合而成的俠儒江湖。正因為此,血光門的主人接到刺殺孟仲的死貼后才會如此的猶豫、犯難,猶豫犯難的背后一方面當然是兄弟親情的不舍,更有違反民意,擅殺忠良的不忍。所謂的官方與民間并不是涇渭分明的,官方有時候需要顧及民間的理念,民間更要遵守官方的規矩,否則二者都將不復存在。其次,在作者看來,真正的俠義英雄或許并不是武功高強的武林人士,而是心存仁愛之心的儒雅文人,《死貼》中的殺手如蟻也算是個另類的俠義英雄了,號稱“仁義的殺手”,但他為了一人之仁,比起孟仲的為了千萬人之仁,自然不可同日而語。雖然孟仲煞費苦心地讓自己的哥哥退出江湖,其實他自己也是江湖中人,而且是江湖中真正的儒俠。其實,江湖就在人的心中,每個人心里都有一個江湖,又如何能退出江湖呢?
閔凡利為什么能夠創作出此類俠儒交織、多種文化共存的武俠小說呢?他構筑的這個江湖時空的材料又源于何處呢?筆者考察了閔凡利生活的時代背景和地緣文化特色,得出以下結論:閔凡利的武俠小說材料有兩個來源,一個是時代文化背景,一個是地域及歷史文化儲備。他少年游俠的青春期正趕上香港新派武俠小說風靡大陸的時期,他的“武俠夢”,是隨著金庸、梁羽生等人的武俠小說在大陸的流行而催生出來的。除此之外,他之所以能構筑起這樣一個俠、儒共生的江湖世界還源于他生活的地域文化和歷史文化。閔凡利出生的滕州自古以來就有“三國五邑之地,文化昌明之邦”稱號,是個地杰人靈、人才輩出的地方,歷史上,滕文公、孟嘗君、毛遂、魯班、墨子等歷史名人,都活躍在這一片土地上。這其中最著名的是春秋戰國時期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學家、軍事家和社會活動家墨子。墨子“替天行道”的俠義情懷,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武俠小說的精神淵藪。因此,筆者認為,閔凡利兼顧平民的武俠精神來源于他遙遠的老鄉墨子。除此以外,閔凡利武俠小說還有另外一個精神來源,那就是儒家思想。滕州北鄰孔孟故里,孔子的“仁愛”理念和孟子的平民思想始終彌漫在滕州上空,儒家思想對閔凡利的影響也幾乎是深入到骨髓里的。正因如此,我們才能在閔凡利的武俠小說中看到一個“俠儒”的江湖。
三、鄉土滋潤的啟蒙空間
“臺灣柏楊先生說過:‘每一個民族都有他的生存空間——歷史舞臺,中國人亦然。中國人的歷史舞臺是世界上最巨大、最古老的舞臺之一,這舞臺就是我們現在的中國疆土。’”[3](P2)閔凡利生于在滕州,長于滕州,有著幾千年的文化歷史積淀的滕州給予閔凡利的饋贈是豐厚的,不僅有改革開放40年來新觀念的影響,也有兩千多年來儒家思想的浸染,更有生生不息的民間文化的熏陶。在閔凡利的作品中經常出現“善州”這一區域標志,滕州古時因滕文公善政,曾被孟子稱為“善國”,閔凡利作品中的“善州”大概就是由此得來的。但他作品中的“善州”又不能完全等同于現實中的滕州,閔凡利自己曾經說過:“善州是我想象中的城市,她是虛構的。是我大部分小說中人物集中活動的場所,內里有滕州的影子,但不是滕州。在我眼里,滕州她不是城市,他只是鄉村的一個擴展,是個大鄉村。最多是個大鄉鎮。而善州,她比滕州要大,她是魯南風俗、民情及各大城市的總和。”[1](P55)應該說“善州”就如同沈從文筆下的“湘西”和莫言筆下的“高密東北鄉”,它是一個文學意義上的空間,也是作家的精神家園。作為一個從中國北方最尋常的農家走出來的作家,長期的鄉間生活讓閔凡利浸染了濃郁的鄉土情懷。但閔凡利寫的鄉土題材的小說又非傳統意義上的遠離故鄉后又思鄉懷舊的“鄉土小說”,閔凡利的鄉土題材作品并沒有回憶的情結,因為他始終生活在他所書寫的這塊土地,時刻浸潤著這一方土地的風土人情和人事變遷。這種寫作狀態的不同給閔凡利的鄉土小說帶來不一樣的素質。由于并沒有遠離書寫的對象,閔凡利的鄉土小說也更逼真更寫實,同時也更具泥土氣息,更能體現作者的鄉土情懷;同樣由于沒有遠離過故鄉,對鄉民身上所殘留的小農意識和劣根性有更深刻的了解,因此揭露出來也更鞭辟入里,深入骨髓。
閔凡利的鄉土小說創作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寫鄉間小民雜事的,通常篇幅短小,人少事小,但卻意蘊雋永。另一類繼承了魯迅、老舍、蕭紅等現代作家揭露國民劣根性的文學傳統,書寫人性深處的自私、虛偽、愚昧、麻木,繼承了現代文學的啟蒙傳統。
先說第一類作品。耳濡目染于鄉間的人和事,讓閔凡利對這類題材駕輕就熟,寫來充滿真摯的深情。《王朝村事》是閔凡利早期的一個短篇,分兩個小節,寫了兩個感人至深的老農民。第一個題目叫《駝》,寫王朝村一個叫磚頭爺的農民平凡而辛苦的一生。磚頭爺是王朝村“背棺頭”的,這是一種地方流行的下藝差事,就是把裝有死人的棺材從堂屋背到大門外的棺材架上,這種活計辛勞、危險,還被人看不起,但為了掙口飯吃,磚頭爺憑著一把子力氣干起了“背棺頭”。終于,在一次被棺材時被壓斷了脊背骨,從此成了駝背。臨死前,囑咐兒子讓他死后直著身子走,兒子為滿足他的愿望在他死后找人用杠子壓平了他的駝背。第二篇題目叫《在天之靈》,寫一個叫道恒爺的老人在老伴死后思念成癡,堅信她還會回來,整日抱著老伴的紅襖到處跑,兒子們看不下去,在母親墳頭燒掉了紅襖,老人也撲倒在老伴墳頭紅襖燒成的灰燼上死去。這兩個故事讀來都讓人心酸,然而卻都是至情至性的鄉間的人和事。
書寫地域風俗文化是閔凡利此類小說最重要的特色,也是他作為一個滕州本土作家給予滕州人民最好的回饋。對紅白喜事中白事的看重是滕州這一地方獨特的鄉風民俗,閔凡利有一篇小說《喜上梅梢》描寫魯南地區農村辦理白事的整個流程,是一篇風俗文化小說,甚至可以作為風俗文化史料來看待。其中對死者的敬畏和對禮儀的尊崇很能見出魯南地域文化經過歷史的淘洗所留存下來的古風民情。小說通過給剛剛病逝的大青娘辦喪事的過程,完整還原了魯南農村的喪葬禮儀。從報喪、搭靈棚、設靈薄、封口、封門、塞耳、看日子、出殯、下葬、燒五七、燒百天等等一系列事情可以看出魯南地區辦理白事的規矩和禮儀,而其中砍哀杖子的訣竅、孝帽子的疊法、紙谷堆擺放的學問、喊路的章程、寫喪簡的格式,甚至不同身份的人不同的哭法,更能見出風俗禮儀中包涵的人情冷暖。中國素有“十里不同俗”的說法,而喪葬禮儀更是千差萬別。試舉《喜上梅梢》中的一個喪葬禮俗:“老習俗,人死了,要在嘴里塞一個剝皮的熟雞蛋。俗稱封口。因為人一死,胃里會窩住一口氣,這口氣就是‘殃’。說有人死了,口如果封不住,會有蛾子飛出來,撲著誰,對誰就不好。”[4]從閔凡利對喪葬禮儀詳細的描述中,我們不僅能夠感受到他對地方風俗禮儀的詳細了解,更能夠見出他對人情世故的通曉諳熟,這正應驗了那句話“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
如果說對風俗禮儀的描述折射出閔凡利浸染于鄉風民俗的故土情懷,那么他對當地農民自私、愚昧、麻木的書寫就反映出他對啟蒙文學傳統的繼承和發揚。魯迅在《阿Q正傳》中用“精神勝利法”詮釋了國民的精神劣根性,閔凡利的小說則用“面子”一詞來探討當代農民身上依然存在的虛妄卑劣的精神病態。閔凡利有一篇非常出色的短篇《張山的面子》,真實記錄了一個普通農民對“面子”的看重和為了掙得“面子”而做的荒唐事。因為一個偶然的事件,張山的老婆跟村長黃運河有染的事成了張村公開的秘密,其實張山早在一年多前就在自己家里撞見自己的老婆和村長的好事,但他懾于村長在村里的淫威,更礙于自己的面子,張山就當這事沒有發生過一樣。但沒有想到這事被自己不懂事的兒子在學校里說了出來,隨后全村人都知道了,再裝不知道,面子上也就過不去了。為了挽回面子,張山想要在大街上當面罵村長一頓,但又怕村長給“小鞋”穿,所以先請村長的客,希望村長能同意他這個掙面子的打算,無奈村長也為了自己的面子斷然拒絕了張山的辦法,萬般無奈的張山做出了另外一個“勇敢”的舉動,去強奸村長的老婆,雖然沒有得逞,但卻鬧得整個張村都知道了這件事。張山最終因強奸未遂罪被關押,但出來后,他卻受到了張村人尊敬,因為他掙回了自己的“面子”。這出因“面子”問題而上演的荒誕劇在魯南鄉村有著深厚的現實基礎,這是幾千年來封建傳統文化在民間土壤的變種,是阿Q“精神勝利法”的遺傳基因再現。
如果說《張山的面子》是借“面子”問題批判了今天農民身上依然殘存的國民劣根性,那么《張三討債記》則借一個討債事件思索當今的農民最缺失的是什么。老實人張三借給奸猾的李四兩千元錢,幾次去討債都因李四耍手腕一無所獲,最后張三決定蹲門要賬,不還錢就不走了,卻又中了李四的“美人計”,不但沒有要來自己的錢,反被李四敲詐了兩千五百元錢。陳曉明教授曾這樣評述《張三討債記》:“李四壞到極點,張三又老實到極點,這樣二元對立的二個人不斷上演著存在的游戲。這里面包含著博弈論的那種結構,好/壞,對/錯,就象翻牌一樣總是不斷試錯,張三的牌總是翻錯了,最后他還是錯了。這篇小說無情地嘲笑了我們流行的好人得好報、善最終戰勝惡的流行法則。”[5]陳教授從倫理道德層面對張三和李四的評判固然到位,然而在我看來,這部作品更加不容忽視的一點在于揭示了新時期農民身上依然存在著的卑劣、愚昧和無知,這恐怕是中國將長期存在的社會現實。結合《張山的面子》,我們看到閔凡利的農村題材作品并沒有超越五四的“啟蒙文學”,他對待農民的態度也依然有魯迅式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閔凡利的落后,恰恰相反,這正說明了閔凡利對當今農村的現實有著清醒的認識和了解,如果說對中國農民的啟蒙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完成,那么啟蒙文學也不應該在短時間內結束,不同的作家所要做的只是如何在這一主題下寫出自己的特色,寫出地方的特色,閔凡利恰恰做到了這一點。
四、批判現實的責任空間
近年來,閔凡利最大的成就是著力開拓出批判現實的現代知識分子責任空間。“現代知識分子與他所生活的現實世界有著一種不相容性,‘批判’是他們與現實唯一的聯系點,他們的基本任務就是不斷揭示現實人生,社會現存思想文化的困境,以打破有關此岸的一切神話。”[6](P377)對于他的這類創作,筆者暫且稱其為“新批判現實主義小說”。如此定義這類小說是基于三個方面的原因:首先,從文學淵源上看,閔凡利的這部分作品秉承了19世紀歐洲文學的批判現實主義小說的傳統,以揭露社會中某領域存在的黑暗現實為己任;其次,從其產生的現實基礎來看,我國尚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發展階段的限制不可避免地造成人們思想觀念落后、法制意識不強、民主理念缺失等社會問題,因此,“新批判現實主義小說”在當下仍有很強的社會現實基礎;再次,就作者本人來說,現代知識分子面對不合理、不公平的社會現狀敢于擔當的責任意識和批判精神是這類作品產生的內在創作動因。閔凡利的“新批判現實主義小說”最主要的代表作是《債主》《我疼》《天皇皇》《皆大歡喜》等。
閔凡利首先把批判的鋒芒指向中國農村最廣大的基層政府,從鄉鎮一級,甚至村支部的層面來對當前農村現狀做出一針見血的批判。《債主》講述鄉鎮政權對私營企業資產的不法侵占和巧取豪奪,不僅使私營企業無法正常運行,甚至導致私營企業主走投無路,不得不鋌而走險,以綁架的方式討回借給鄉政府的錢。小說講述私營企業主趙青海、趙大慶父子先后借給當地鄉政府23元,屢次討要都被鄉長張偉峰以種種借口賴賬不還。當趙氏父子面臨生意場急需資金盤活和趙大慶的母親突發心臟病急需手術費救命時,鄉鎮干部卻依然置人民生命財產于不顧,變著花樣玩弄權術、欠賬不還。不論是老趙的公開起訴和無奈下跪,還是小趙的私下請客、拉關系送禮,最終債務依然追討不回來。被逼無奈的趙大慶只好鋌而走險,伙同他人闖入鄉長張偉峰家里,控制住張偉峰,從其家中搜出幾十萬別人送的禮金,拿走了鄉政府尚欠自己的15萬元錢。結局當然是趙大慶鋃鐺入獄。雖然小說最后張偉峰也因被檢舉揭發而入獄,但小說中揭示的鄉鎮干部腐敗弄權的現狀卻是觸目驚心的。這些所謂的人民公仆手握人民賦予的權力,干的卻是巧取豪奪中飽私囊的勾當,不僅喪失了責任與義務,甚至連做人最基本同情心也沒有了,讀來的確讓人憤懣而寒心。《債主》中所涉及的鄉鎮政府拖欠私營業主錢款的事情曾經是基層非常普遍的現象,但鮮有作家敢以如此尖銳的筆觸書寫此類事件,閔凡利以一個現代知識分子的責任和普通公民的良知觸及此類題材,不能不讓人佩服他的勇氣和擔當。
閔凡利有著敏感的神經和大膽的筆觸,敢于寫別人關注不到的事情和別人不敢觸及的題材。《天皇皇》就是一篇觸及當今農村普遍存在、但又很少被人關注的事情。由于農村青壯勞力常年在外打工,留守在家的婦女便時常面臨生理需求無法得到滿足的狀況,于是非正常的兩性關系在農村就大量存在,這里固然有你情我愿的男女偷晴,但也不能排除大量的像小說《天皇皇》中描寫的那樣,在村長王柳淫威下的性侵犯。小說表面上寫了一個殺人的刑事案件,“角豬村長”王柳一而再、再而三霸占老實巴交的農民王大帥的妻子張雨玲,王大帥終于忍無可忍舉刀將王柳砍死。在作者看來,王柳的死和王大帥的伏法并非這類事件的結束,這種普遍存在于當今農村的既違反道義又違反法律的行為并未找到真正的解決辦法。男人外出打工的生存需要,留守婦女的隱忍與無奈,不良社會風氣的漫漶,給“角豬村長”們欲望的泛濫、惡意的橫行創造了可乘之機,原本維持鄉村次序的倫理道德蕩然無存,原本民風淳樸的鄉村日漸消失。作者讓我們看到維護鄉村倫理的最后一片遮羞布的滑落,更讓我們深思商品經濟沖擊下的農村精神生活的缺失,這是一個長期接觸到農村基層的知識分子面對道德滑坡、倫理缺失的鄉村一聲無奈的嘆息,是一首唱給衰頹的中國鄉村文明的挽歌。值得一提的是這篇小說敘事手法的新穎,小說的各個部分分別使用了敘事、說明、描述、目擊者證詞、議論、證詞、閃回、哭訴、新聞報道、補述等不同的敘述語言來一遍遍還原事情的原委。作家力圖從不同視角再現整個事件,使這個鄉村案件的不同側面以不同的方式刻印在讀者的腦海。
閔凡利的“新批判現實主義小說”中所涉及的諸多問題,恰恰是中央政府近幾年建設“新農村”政策要著力解決的現實問題,其中拖欠私營業主債務等問題已經開始通過法律手段或者行政手段加以解決。閔凡利的此類小說已經發揮了真正的社會效果,這對于有良知、有責任的知識分子來說應該是一件非常值得欣慰的事。
綜上所述,閔凡利所建構的這個多維的文學時空,是他長期藝術創新和哲理思索的結晶,也是他浸潤于滕州的風俗、歷史和文化的地域饋贈,更是一個現代知識分子的良知體現和責任擔當,這一文學時空的建構全方位、多角度地折射出閔凡利文學追求的日趨成熟和藝術風格的日趨穩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