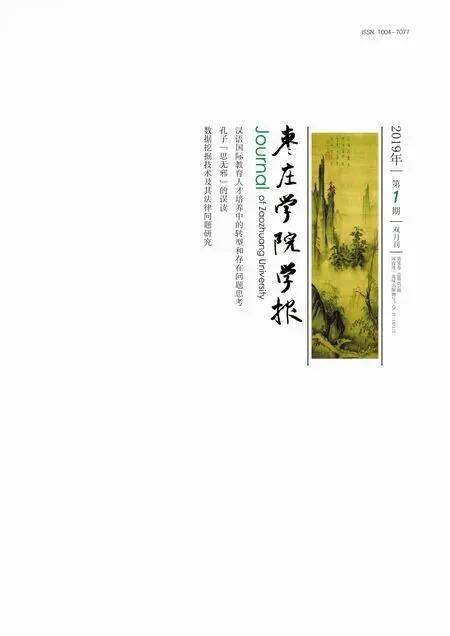神性·知性·血性
——趙月斌的文學世界與評論天地
顧瑋
(棗莊學院 文學院,山東 棗莊 277160)
中國當代文學已經腳步穩健地走過了“改革開放40年”,伴隨著歷史沉浮成長起來的中國作家為中外讀者奉獻了屬于自己的歷史記憶與個性書寫,同時也為評論家們提供了豐富、多元的文化樣本和寫作資源。
從棗莊滕縣走出的趙月斌就是一位身兼二職的“文學守護者”,他既是“70后”新生代作家代表,也是一位特立獨行的非學院派批評家。他將自己的思考內化為一種精神特質,在小說中營造了一個奇幻的文字王國,“嬗變出嶄新的藝術蘊含”[1](P239);又用剛健的批評之筆在文學評論領域開拓出一片沃土,不斷培育出具有鮮明“趙氏”風格的奇花異草。40年來,他在文學的熔爐中不斷歷練,在哲學、美學著作中徜徉漫步,具有了深厚的中西學養和宏闊的世界眼光,他能堅守自己的文學理想,努力做一個“骨子里有血性,精神上不失高貴的作家”[2],使自己的“文學評論與文學創作相得益彰”[3](P1),全面、真實地展示出一個作家應有的時代擔當,肩負一個評論家“重整乾坤”的文化使命,在文學創作與批評的道路上不斷前行。
一、天馬行空的“神性”世界
作為“生在紅旗下”的70一代寫作者,趙月斌年少即懷揣著文學夢想,14歲開始寫詩,1987年首次發表作品,在他22歲開始嘗試小說創作時,文學已經失去了社會轟動效應,文學觀念開始多元化,伴隨文學的商業化思潮涌現,新生代作家崛起,作家們面對的是個體寫作的艱難生存環境。趙月斌于先鋒小說式微之時寫出了《紅血》《醒尸》《一妻三妾》等六篇小說。親歷了改革開放后中國社會翻天覆地的變化,經受了開放多元的思想和價值體系的沖擊,趙月斌逐漸擁有了屬于自己的文學認知和經驗表達。1998年夏秋他重新開始小說創作,寫了《謊言與真實》《我是禿子》《尋找公主白雪》《一九六O年的月餅》等一系列怪異、荒誕的短篇小說,在這些離經叛道、天馬行空的神性世界中,作者得以將小說當作盾牌,隱藏自己,釋放真實的自我感覺、認知和經驗。《雨天的九個錯誤》是2014年出版的短篇小說集,其中的幾篇小說均是現實的土壤里開出的奇花異草,不由得讓人想起馬爾克斯和卡夫卡的魔幻世界。
趙月斌曾說:魔幻現實主義在我們的傳統里是常態,中國的傳統小說有“內在的神性”、巫性,比如莫言的《生死疲勞》中的“六道輪回”即是基于民間傳統之上的中國經驗和中國精神。趙月斌的短篇小說也有著某種程度的“神性”和“魔性”,以頗為先鋒的面目出現:《關于合歡的三種說法》運用重復敘事,衍生出三個不同走向的故事。少年成長為一棵“合歡樹”,這是在童年記憶片斷中虛構出的新的“真實”。帶有戲謔、寓言性質的《狂犬日記》似乎是向魯迅的《狂人日記》致敬之作,寫了一條有思想的狗,試圖擺脫狗的天性(吃屎)成為一匹狼,最終無所逃遁,做回了狗被吊死的故事。《啞巴歌手》揭示了個性被塑造和規訓的真相。《十年懷胎》中揭露了以“生男”為人生使命的韓淑英被異化為非人,心靈被扭曲的荒誕事實。《深夜裸行》中自以為悲壯的隱秘裸行成了一場他人眼中的行為藝術,被消解為委瑣和滑稽。《我是禿子》寫了一個玩世不恭又特立獨行的底層青年,想揭示真禿子而剃了光頭,最終自己再也長不出頭發的故事。《羊皮記》寫了四清運動中反四類分子的荒誕,一個走投無路的女人鉆進羊皮,變成羊逃跑了的離奇事件。《尋找公主白雪》中千年古尸醒來與情人約會,演繹了一場人鬼情未了的穿越戲。
謝有順在2018世界華文創意寫作大會上說:“好的寫作從來是精確而富有想象力的,是實證與想象力的完美結合。”趙月斌的小說亦是如此,他將歷史細節、時代背景深埋于作品中,在表現人物、事件的視點上有接地氣的質感,但在敘事上又自由奔放,天馬行空,注重形式創新,追求神性意味,有從現實抽離的明顯意圖。趙月斌做到了實證與想象力二者結合,將無比現實的意味賦予了荒誕不經的形式,精準地呈現給讀者。作者試圖隱藏自己,以不同身份、年齡的“何斯”或其他人物出場,但每一個人物都代表了他的一面,每一段人生中都有他自己的影子。如《追念一九〇九》中的金殼郎、大桑樹,《啞巴歌手》中的大蔥,《關于合歡的三種說法》中大片的艾草,是抹不去的童年印記。《在深夜裸行》中的裸行者,《狂犬日記》中瘋狗,《誰是禿子》中長不出頭發的人,《啞巴歌手》中命運被設定的歌手,都有可能是另外一個“我”,“我”的精神碎片。在寓言、象征、隱喻的背后,難以隱藏的是作者對人性真善美的探尋,對歷史真相的追索,對蕓蕓眾生的悲憫情懷。在看似戲謔、荒誕的怪異表象之下,是作者對歷史的反思,對人性和良知的拷問,對鄉村倫理體制的質疑反抗,對審美理想的執著追求。
20世紀90年代是“個人化寫作”的時代,趙月斌在寫作這些短篇小說時,亦拋棄了宏大敘事,在廣闊的時代背景中,截取了生活的橫斷面,從活生生的個體切入歷史,進行細節化的個人敘事,運用隱喻、夸張、戲謔、反諷、變形等現代派技法,融合歷史、現實、民俗、政治、神話等因素,將普普通通的個人故事變形成帶有寓言、傳奇性質的“現實主義”小說。
二、《沉疴》:潰敗的鄉村倫理
“一部偉大的作品,不單需要某種怪異特征,不單需要顛覆及創新,更需要一種強有力的自足性,其內涵應‘具有高度的復雜性和矛盾性,而絕不是一種統一體或穩定的結構’。”[4](P11)趙月斌在2016年出版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沉疴》,便是他努力向偉大作品靠攏的文學實踐。《沉疴》其實是1999年的舊作,作者說這是回到自己的村莊,回到親人的小格局中寫就的“不加偽飾的私心話”,讀者看到的卻是充滿矛盾、悖論和蓬勃生命力的家族秘史。
在《沉疴》這部長篇小說中,作者一反之前的奇幻手法,以親歷者、觀察者的身份,以寫實手法講述了一段“非虛構”的鄉村生活。“全書共九章,每章四部分,均以三、二、一、〇為序號,三為何斯自述,二為《沉疴》原文本,一為何斯父母口述,〇為何斯注解。”[5](P3)小說的正文是上卷,下卷為三個獨立篇章:《一九六〇年的月餅》《十年懷胎》《尋父記》,“‘卷下’三篇雖為虛構作品,卻與《沉疴》有互文之效,其中的人物亦有互通,所以,卷上、卷下完全可以合而為一,構成一部完整的書。”[6](P313)多元視角形成了鄉土敘事的多重文本,長孫“何斯”自述和“何斯父母”自述是第一人稱的主觀視角,他們的言語中帶有強烈的情緒;“原文本”是全知客觀視角,態度較為冷靜;對禮俗、俚語的“注解”部分又回到了“何斯”的視角,對事件的原貌做了補充說明,可視為補敘。三種視角的轉換,相互補充,造成了互文的效果。作者試圖從多個視角,借助鄉村“生死場”,展示大家庭難以平衡的人際關系,重點講述“爺爺”去世前后家庭結構失衡,“長孫”目睹“長子”在與親戚的矛盾糾紛之中痛苦、煎熬的狀態與忍無可忍的反抗。作者不惜筆墨,用地道的家鄉方言和俚語,寫出了喪事禮俗的過程,真實還原了物質匱乏時代鄉村精神萎縮的面貌,揭示了家庭倫理失范后,鄉村倫理的種種危機。
血緣親情是整個儒家倫理思想的感情基礎,仁的根本是孝敬雙親,友愛兄長,而禮是仁得以實施的形式和途徑。在小說中,祖宗留下的禮制只剩下了外在的形式,其內涵——忠、恕為核心的“仁”卻蕩然無存。以書中的長輩——“奶奶”為例,這位母親根本不是傳統意義上能為子女遮風擋雨,具有隱忍、犧牲精神的母親,她全無舐犢之情,是個“放債式”的母親。她有偷竊的惡習,偷鄉親鄰里的,偷自己爹的,跳井被救后還死不悔改,故伎重演。她打著“殺富濟貧”的旗號,偷二兒子的麥子救濟三兒子,連她偏愛的女兒家的錢也不放過;她不僅自己偷,還慫恿自己的孩子行竊。偷竊事件間接導致了“父親”在招飛行員和民辦教師時受牽連,被人檢舉、揭發“剔”了下來。她在家強勢慣了,對子女和孫子如同對待與其有利害沖突的對手,從不真心相待,不是打壓就是虛偽地拉攏利用;對自己的親人常常惡言冷語,連打帶罵,因長子當了別人家的孝子懷恨在心,當著外人的面指著兒子的額頭謾罵、羞辱,挑撥女兒和兒子們的關系,教唆女兒們與長子作對;因為相信巫言,在“爺爺”治病的問題上幾次反復,極盡折騰;“爺爺”痛苦離世后,在“奶奶”的攛掇下,一家人終于撕破偽裝,面露猙獰,在“爺爺”的墳前吵架,雞飛狗跳,場面混亂,幾乎要打起來。小說用了大量篇幅刻畫了“奶奶”的形象,可謂觸目驚心。在農村,劣跡斑斑的潑皮無賴不在少數,他們通常游手好閑、好吃懶做、打架罵街、搬弄是非,甚至坑蒙拐騙、不知羞恥,頗遭鄰里村民和家人嫌棄,可大家又拿他們沒辦法,只能忍受。作為女性,如此自私、無賴,對自己的子女如此刻薄,實屬少見。
小說中“父親”這一長子形象頗具典型性。大家庭中的長子是孝悌的忠實實踐者,歷來要恪守家道,承擔著家族事務管理的重任。在等級嚴格的家庭秩序中,一旦以父子為主軸的家庭秩序出現崩塌,長子就會成為社會、家庭、代際之間矛盾斗爭的集結點,成為明爭暗奪、互相傾軋的家族矛盾的犧牲者。在現代文學的人物長廊中,覺新(《家》)、瑞室(《四世同堂》)、蔣蔚祖(《財主的兒女們》)、曾文清(《北京人》),都是刻畫相當成功的長子典型。他們具有溫柔敦厚、謙和秀雅的君子之風,但在新舊文化的夾縫中生存艱難,在各種復雜的矛盾中,長子為求得表面的和諧穩定,只能以家族利益衡量自己的行為準則。《沉疴》中作為“長子”的“父親”,在“爺爺”去世之后也陷入了噩夢一般的家庭矛盾中,瑣屑的爭吵,加上掰扯不清的事實,無意義的爭辯,讓父親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壓力。“爺爺”去世意味著家庭權力中心崩塌,維系親情的紐帶徹底斷裂,母子關系惡化,姑嫂、姑侄、祖孫、兄妹等至親之間爭吵、謾罵、仇恨,長子突然成了眾矢之的,各種無端猜忌涌現出來。旺盛的文化生命力在藏污納垢的家族關系中,在親人之間的戰爭中消耗殆盡,最后一絲人倫溫情彌散在故鄉寂寥的精神荒原上,只留下人間煉獄般的疼痛、傷害、怨懟、無奈和憤怒。
傳統鄉村是建立在“血緣”“地緣”基礎上,以人情為紐帶,以互信為基礎的“熟人”社會。鄉村倫理首先體現夫妻關系、父(母)子、婆媳、兄弟等家庭成員之間等,其次體現在社會倫理,即鄉親、親戚、鄰居之間的關系方面。如果家庭倫理混亂,道德失范,社會倫理失序,會造成整個鄉村社會精神家園的失落與離散。
中華民族歷來是重視親情、人情的,但血緣親情之中也有權力的爭斗,親情、人情中也滲透了交換的因素,親屬、熟人之間的交往也要衡量回報的大小。世態炎涼是中國人特別的感觸,說明親情、友情、交情在面對利益和權力時的軟弱性。在中華民族五千多年的文化傳承中,一直奉行儒家的“仁禮合一”,婚喪禮儀是禮儀之邦最重要的人情禮俗,是反映地域社會倫理道德和忠孝觀念的一面鏡子。在禮崩樂壞,經濟困頓,溫飽成問題的饑饉年代,儒家倫理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鄰里和睦的美好溫馨的家族關系,往往只是虛幻的海市蜃樓。《沉疴》撕開了鄉村倫理溫情脈脈的面紗,讓讀者看到了在金錢、利益面前,血緣、親情、人倫組織成的生活圈子內部的腐敗和混亂。卷下的三個短篇也從不同角度展示了這種鄉村倫理的潰敗:《一九六〇年的月餅》中一家人面對一塊月餅極力爭搶,甚至“死不瞑目”。《十年懷胎》中因為兒子是農村家庭血脈的延續,家家戶戶拼命生兒子,這種生育壓力導致了婦女的精神崩潰。《尋父記》中的出走——“尋父”——回鄉,解構了父親的存在,給“我”留下了難以愈合的代際傷痛。
改革開放以后,伴隨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農村城鎮化進程的加速,鄉土世界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劇變。現代化和市場化不僅改變了農村的面貌,也改變了村民的生活觀念與生活方式,社會階層的分化日益明顯。大批青壯年農民進入城市打工或生活,失去了對土地的依賴與敬畏,鄉村傳統家庭結構迅速崩塌,“家”的凝聚力不斷減弱,家庭倫理道德約束力隨之弱化,人倫親情日益淡化、冷漠,長幼有序、倫理孝道等傳統范式遭遇到巨大的挑戰。
最能彰顯鄉村文化的婚喪禁忌、民俗禮儀也只剩下了“形式”的空殼,內容早已異化、變味兒。鬧喪、號喪本為表達哀思,安慰亡靈,現在卻成了講門面,講排場和互相攀比的現場,更有“喜喪”上大家嘻嘻哈哈爭搶糖塊,毫無對死者死亡敬畏的鬧劇,顯示出喪禮的虛偽性。正如小說中所言:重孝只是實用主義禮儀,并非真心表達哀思的沉重。行“來往”,來往的不是感情,而是物質和金錢。活人和死人都要爭面子,為了面子眾人參與集體表演,維持禮數上的周到,許多禮節竟成了折磨人、拖累人的形式。小說中“爺爺”彌留之際,被強行穿上壽衣,爺爺看到壽衣后受了驚嚇,大叫“啊!鬼,鬼!”這是真孝心還是對彌留之際的老人的殘忍?禮金的多寡,送禮的時機均有講究,總有不滿,盡管長子表現得隱忍、懦弱,委曲求全,竭力平衡家庭關系,仍然引起了家人的挑剔和猜忌。喪禮期間,“長子”、母親和三個妹妹之間用禮羞辱對方,打擊對方。“燒轎”時,三個妹妹竟然說“哥,給咱爹背搭子”,當著長兄的面喊“殤了”的哥哥背搭子,屬于很惡毒的咒罵了。“燒五七”時,“長子”忍無可忍,也會借“換服”羞辱三個妹妹,讓她們灰溜溜地出村,坐在地上大哭。這時的“禮”哪里還有仁的影子,已經淪為親人互相攻訐,爭奪權力,自己長臉,讓對方丟面子的武器。
《沉疴》為鄉村社會學研究提供了一個有意義的樣本和重要個案,從中我們看到了當代中國農村真實的狀態,鄉村文化的斷裂,倫理道德觀念的變遷,使得故鄉再也不是可以詩意棲居的“文明野地”。對于許多從農村走出的年輕人而言,故鄉似乎僅留存在童年的記憶里,駐足于精神層面——那個能讓人魂牽夢繞,牽引出永恒鄉愁的美好之地。而若干年后,地理意義上的故鄉可能已呈現出文化潰敗、生態破壞的狀態,更令人痛苦的是,在逐利動機的驅動下,家庭關系、人際關系扭曲變形,鄉土世界的價值,鄉村文化的精神陷入到一種真空的狀態中。
盡管面臨如此多的矛盾與糾結,作為五百里外的異鄉人,作者仍要時不時回到故鄉的“場”中,過去希望擺脫俗事糾葛,現在又暗自接近那個精神之源。小說中對魯南俚語俗語,民風民俗的記錄,充分證明了一個極具原始生命力的鄉村并不因為個人的喜好存在或消失,無論詩意還是鄙俗,高貴還是丑陋,這一切就是原生態的鄉村生活,這種身體在鄉、精神逃離或身體逃離、精神返鄉的矛盾與背反,是我們不能熄滅的尋根渴望,是我們與故鄉揮之不去的情感糾纏,也是從鄉村走出的趙月斌從青年到中年心態的真實寫照!作者對鄉村倫理式微的反思,對鄉村生活意義的探尋無疑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
三、評論:重建文學理想精神
改革開放之后,伴隨著思想大解放,理性回歸,文藝復興,趙月斌作為20世紀80年代成長起來的文學青年,可以盡情遨游在優秀世界文學的海洋中,他如饑似渴地閱讀了大量的社會學、哲學、文學、傳記,并將自己的思考、體悟、心得灌注到文學批評之中。趙月斌做過教師、職員、編輯、專業作家,最終以“文學批評家”為學界所熟知。如今,他已在《文藝爭鳴》《當代作家評論》《上海文化》《小說評論》《十月》《山花》等報刊發表文學評論和小說、隨筆等文學作品300余萬字。他的評論集《迎向詩意的逆光》入選了“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2011年卷,并榮獲了第七屆劉勰文藝評論獎,評論《置身于苦難中的黑色英雄(莫言論)》獲得了第二屆泰山文藝獎,他本人也入選了山東省“齊魯文化英才”。趙月斌在文學批評領域的成績足以證明自己的實力。但他謙虛地說自己的評論“沒有玄奧的理論支撐,也沒有強大的體系架構,有的只是掀不了風浪上不了臺面的漏網之魚。”[7]
趙月斌有身為評論家的擔當和責任感,無論在山東省作協任職還是兼職當文學期刊編輯時,都以獨到的眼光和學識,展示出獨樹一幟的“趙氏”批評風格。別人的批評冷靜客觀,他偏毫不掩飾自己的真性情;別人的語言現代、后現代術語滿天飛,他卻想象力飛馳,從自己的感性印象出發,進行詩意的表達。在《偉大的小說離我們有多遠》中他竟然用“好看”“好讀”“好玩”來評價獲得茅盾文學獎的作品——阿來的《塵埃落定》,這種完全不按套路出牌的批評,也是對當今學院派過于呆板無趣的程式化評論的反撥。讀他的評論,除了能看到他對當代文壇眾生相入木三分的勾勒,還能欣賞到作者不可復制的情緒體驗、靈魂感悟和語言之美,所以他的批評風格才被稱為“作協派”“感悟派”批評(黃桂元)。
趙月斌的評論文章語言靈動、詩意十足,充滿對生命的觀照與熱情,因而他筆下的作者們個個形象飽滿,可歌可哭。例如在他的萬字論文《逍遙與沉迷——胡河清論》中,趙月斌憑著作家的藝術直覺,展示了胡河清生存的悖論狀態——“銳不可當,又脆弱如冰”,既有陽剛之氣,又有女性的“羞澀與溫柔”,“胡河清是這片土地上孤獨的嬰兒,他有赤子之心而無護心之鏡,他一再談起‘審美’,最終卻沒有擁抱審美的人生。”[8](P8)這些基于深度理解和情感共鳴的文字,是浸潤批評家情智的肺腑之言,帶有批評家感覺和個性體驗的鮮活氣息。
他說詩人曹有云是在“存在的深淵里吶喊”,他評臧利敏的詩“纖毫畢現,溫厚慰藉”,他最欣賞王小波身上率真、無畏的“孩子氣”“詩人氣”,他稱莫言是一位“既粗礪又細膩、既狡猾又真實、既土包子又標新立異、既桀驁不馴又謙卑謹慎、既劍拔弩張又撕心裂肺的作家”,他評價張煒身上“既有齊文化的仙道傳統,又有魯文化所代表的士大夫精神”,張煒的小說《獨藥師》是“可以照亮靈魂的立命之書”。這些評價以敏銳的藝術直覺穿透文學作品的肌膚,把脈作家的精神向度和氣質,表達了知識分子挺拔的精神立場,獨到的藝術見地,是理論性和可讀性都很高的批評文本。
比起寫作,趙月斌更愿意做一個像伍爾夫那樣的“普通讀者”,正因為他首先是一個優秀的讀者,在日常閱讀中積累了所思所感,才有了這些用功細讀文本之后的副產品。他輕松自如地穿越于作家作品,對當代文壇眾生相用心描繪、品評鑒賞,他的批評是隨筆體,卻有著雜文味。與雜文形象說理的手法相類似,他的論證縱橫開闔,鋒芒畢露,汪洋恣肆,不拘一格,很多文章有一針見血的鋒芒和內力。他敢于向名家和獲獎名篇開刀,毫不客氣地將賈平凹的《高興》、劉震云的《我是劉躍進》、余華的《兄弟》、閻連科的《風雅頌》等小說斥為“偽現實主義”,對作家剽竊新聞,想象力衰頹的事實進行了犀利而深刻的剖析。他說:“作家對內在自我的關照,對本真生命的省察,以及對這個世界的感知、追問與體恤,才是文學創作最根本的起點,更是現實主義得以建立的基石。”[8](P196)小說不應該是“滯后、繁復化的新聞”。他批評在“底層寫作”“為底層代言”的文學潮流之中,許多作品打起了關懷底層,關注小人物的旗號,許多作家儼然成了“底層寫作”慈善家,把文學的功德箱簡化成了扶貧文學和弱者文學。他批評底層敘事“慣于套用一種憐貧送暖的模式”,“制造凄慘難過的苦情故事或勵志感人的溫情小品”以博人眼球。
趙月斌之所以對名作家開刀,是因為他對優秀作家、偉大作家的期待甚高,判斷標準嚴苛。他拒絕將作家定義為“手藝人”、碼字匠,他認為“作家不應單是一種職業身份,而必須具有精神的擔當和思想的責任,寫作也不該是止于打鐵似的炫巧耀技,而是要錘煉進生命的寬廣和靈魂的重量。”他認為作家是“以文學立命”的知識分子,“他要有足夠超拔的精神向度,”“不勢利,不茍且的主體意識”。作家如果“肉身尚存,靈魂出離,精神化為烏有”就是“作家已死”。[9]
趙月斌不僅對作家這一身份有自己的界定,在多篇評論中他還談到了批評家的主體意識,在《重尋批評的靈魂》中,他說一個優秀的批評家應該具備幾個特質:知性、理性、感性、詩性、血性。他批評了“五四”以來中國文學批評的鈍化、軟化、媚俗化傾向,魯迅那樣的硬骨頭批評家幾近覆滅,他認為批評家要有荷戟獨行的挑戰精神,投身于“英雄式的努力”。在趙月斌的批評實踐中,他將自己的“主體意識”滲透到作家作品,目擊文學現場,臧否當代文學。挑戰權威時他犀利如老吏斷獄,遇到對胃口的作家時又難掩傾慕,頗有溢美之詞。
趙月斌以自己的實力一步步成為擁有話語權的批評家,但對年青作家,他常懷有溫情悲憫之心,體恤年青作家的才情不濟,筆力不足,并給予更高的要求。自2008年起,趙月斌做過多年的兼職編輯,比如《時代文學》的特約主持人,《百家評論》編輯部主任。在主持《時代文學》的“魯軍新勢力”“魯軍新看點”時,他關注山東的新生代作家,推出“山東青年小說家專輯”,追蹤研究、陸續編發了數十位青年作家的作品,為本省文學新人新作撰寫評論,使得許多文學新人脫穎而出,受到文壇和評論界關注,可謂功莫大焉。同時他激勵獎掖新銳,發展山東省的文學寫作事業,用朱向前的評價來說他是個具有“土本情結”和“新人情懷”的評論家。
總之,趙月斌是一位有思想,有風骨,兼具知性和血性的批評家。這么多年來,他一直在文學評論領域堅守神圣的文學理想,對山東地域文學的偏愛與深情,對好作家好作品的殷切期盼,對“道德理想主義”的追尋使得他有傳統的一面,對有意味的形式的尋覓又讓他自帶一種神性、詩性的現代審美氣質,在眾聲喧嘩的文學批評界,他始終向世界最優秀的文學經典看齊,向普世的人性關懷、終極關懷靠攏,保持一顆“寧靜的童心”,堅定地做一個中國文學理想精神的守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