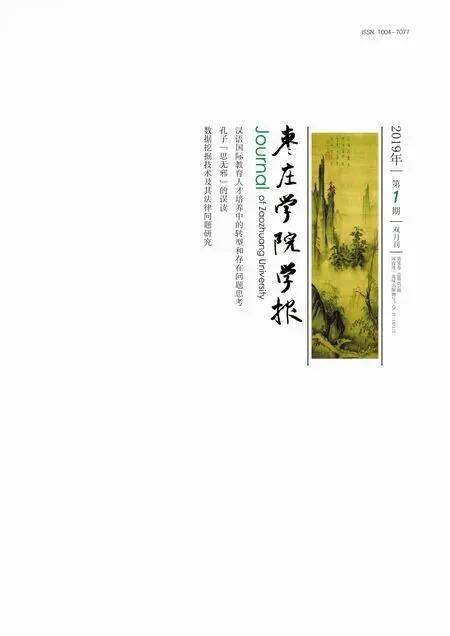多維的現實主義空間
——論畢四海的小說創作
曹新偉
(棗莊學院 文學院 ,山東 棗莊 277160)
在畢四海近40年的小說創作生涯中,我們可以看出他涉獵多種題材,若說以孟家莊為依托的鄉村與商旅小說著意于以現代意識觀照齊魯文化,而政治小說的通過對官場文化的透析來挖掘政治人性,無疑是他對中國當代文壇的獨特貢獻。作為一位現實主義作家,他有著濃郁的現實情懷,及時捕捉時代信息,反思中國傳統文化,同時,他還有強烈的文體自覺意識,創新求變意識。他始終探索藝術表現方法的各種可能性,試圖以更有效的藝術形式表現時代,展示人物精神,多維度審視豐富復雜的歷史與文化,是一位富有藝術創新和探索精神的作家。
作家汪曾祺慧眼識珠,1987年給畢四海的第一部短篇小說集作序的時候就說:“畢四海是一個老實人,但他的作文是不老實的,有寫實的,有荒誕的,有意識流的,有變形的,有超現實的。”[1]評論家何鎮邦也指出這一點:“畢四海在藝術上是個很不安分的人”[2]“不老實”或“不安分”,都說明了畢四海在藝術創作上雖然堅持用現實主義方法,但并不愿意循規蹈矩。
一、及時捕捉時代信息
畢四海是一位有足夠思想敏銳性和思考深度的作家,其藝術視角總是能夠及時捕捉到時代變遷的信息,做一個時代的探索者和先行者。他深受魯迅啟蒙文學觀的影響,始終堅持文學為人生的創作理念,密切關注現實,不斷出擊社會問題,并將其行諸小說創作。《承包者》《W不是故事》等是畢四海長期關注急劇變化的中國社會發展進程,并進行深入思考的結果,這類小說冷靜而尖銳地揭示了當代農民企業家所處的惡劣的生存環境:沒有自由競爭的規則,沒有平等的社會氛圍,而是拉關系走后門行賄受賄等填滿了他們的生存空間,這種競爭的結果,往往是優秀者失敗出局。這樣的現實令人感到沉重,顯然不利于中國私營企業的良性發展。中篇小說《輪回》把人物置于尖銳的矛盾沖突中加以表現,塑造了兩個不同類型的農民企業家形象。他們的發跡及墮落是社會轉型期及商品經濟大潮下的產物,必然經不住社會歷史的滌蕩、淘洗,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和警示作用,是特定社會歷史時期的藝術備忘錄。
《選舉》對中國式“民主”和“選舉”制度的表現,是這位具有高度歷史責任感和社會責任感的作家、九屆全國人大代表為社會提交的一份“議案”。小說不僅揭示出政治生活中存在的官僚主義問題,對政治化的人性和人性化的政治進行了毫不留情的剖析和批判,而且還揭示出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艱難根源,呈現出了這種人物所存在的社會環境與文化基礎。這是一種封建人治下長期形成的集體無意識:民主選舉縣長,不管某人有無能力,是“排隊也該排到人家龔彬了”“軟到位”“安全升格”之說,體現了國人對選拔領導干部論資排隊心理的認同;黨政一把手大多是水火不相容,這叫“虱子多了不咬人,頭羊多了亂羊群”,或“一山容不下二虎”,顯現了國人的專權意識及狹隘自私心理;而被選舉者請客送禮拉關系、搞串聯,“作家評職稱也要說一說的”,則顯示了國人重感情、輕理性,不實事求是、不負責任的公民素質……這種種社會文化心理與政治化的人性和人性化的政治是相輔相成的。薩特存在主義理論指出,存在的即合理的。當代評論家施戰軍說:“畢四海的‘政治的人’,則是一種中國式人性胎記的展現,它有時是一種利益支配下的自覺,但更大程度上是一種國人的集體無意識。”[3]作家向我們呈現了這種種觸目驚心的思維定勢及幾千年的文化積淀,并將其集中體現在我國社會主義民主進程中的一個重要程序里,給讀者以強烈的心靈震撼。
1986年初,畢四海的長篇小說《東方商人》第一部由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隨后他又進行《東方商人》第二部的寫作。1990年內蒙古電視臺和中央電視臺攜手合作,把《東方商人》改編成22集同名電視連續劇,1995年在央視一套黃金時間播映。電視劇播出后,全國轟動,旋即榮獲全國電視劇政府最高獎第15屆“飛天獎”及第13屆“金鷹獎”,隨后原著又榮獲山東省首屆“精品工程獎”。畢四海由此作而被認為“中國商旅文學的開拓者”,一舉成名。翻開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以民間商人為主人公和探討商旅文化的小說可謂寥若晨星,這與汗牛充棟的軍事題材與農村題材小說形成了非常鮮明的對比。這種現象除了與“重農抑商”的農業文明有關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即當代主流意識形態對商業經濟長期貶抑的結果。畢四海在創作《東方商人》的1984年,《人民日報》還在討論長途販運是不是投機倒把問題;1985年,《東方商人》(第一部)在上海《青年報》連載時,有媒體斥之為“毒瘤”進行批判甚至“圍剿”。但人們的思想認知水平畢竟要隨社會的發展而逐步提高,隨著中國市場經濟制度的確立,一個新的商業文明時代必然到來。1991年,著名小說批評家雷達對《東方商人》進行了恰當的評述:“幾乎可以肯定地說,這是一部具有一定的認識價值、審美價值和文化價值的長篇小說。它填補了中國當代文學的一項空白,給我們提供了從新的角度思考民族歷史和民族靈魂的一個契機。”[4]2006年山東省作協副主席吳義勤,從中國文學史角度對這部小說給予了充分的肯定:《東方商人》對中國傳統民間商人和商業文化的重新思考,開啟了其后商賈小說的先河。小說對中國商人和商業文化的重新思考,對當時人們意識深處的商業觀念形成了強烈的沖擊,其藝術成就顯然不僅體現在突破小說題材禁區問題,更是體現在把商業文明在中華民族文化歷史中如何定位問題。
顯然,畢四海是一位有著強烈社會責任感的作家,一位對現實、對時代充滿激情的人,其藝術觸覺總能及時捕捉時代信息,以極快的速度對之進行藝術表現,讓讀者看到當代中國社會變革的側影。畢四海在《骨髓抽樣分析》一文中說:“我怎么也更新不了這樣的觀念——文學不為人生、不為社會、不為中國的改革傾注一份關懷;不讓文學的認識功能給中國人‘提個醒’,文學也就太‘私人化’了,太‘邊緣化’了”。
二、現代意識觀照下的齊魯文化
所謂現實主義創作方法中的“直面現實”,不僅僅指一些敢于反映重大社會問題、有巨大勇氣揭露當前社會復雜而尖銳的矛盾,塑造黨和人民利益的維護者形象,展現正反雙方驚心動魄的斗爭等等;也指需要深入現實的平凡狀態,關注普通百姓的喜怒哀樂,關注他們在改革進程中的心理、精神及命運變遷;更重要的是,“直面現實”還需要質疑、反思與批判精神。因此現實主義作品還需要有敢于深入現實與本質的精神,如這些矛盾是如何產生的,它和社會制度、人的本質及當前政治是否有必然聯系,我們應該如何去反思與批判它。更進一步說,“直面現實”還需要對現實有文化的哲學的思考,即把“現實”形而上學化,使“直面”具備終極關懷的指向性。
畢四海對鄉村生活的關注,主要以“孟家莊”系列小說為代表。它們通過對農民生態和心態的透視,揭示農民身上沉重的精神負擔,呈現現代的鄉村生活中傳統文化無所不在的影響。《家雀子樓春秋》僅僅用了不到3000字,就為我們勾勒出孟家莊近40年的歷史變遷及人物命運的變化,并揭示出深刻的文化內涵。小說開始煞有介事地運用了具有反諷話語交代故事發生的時間、地點和人物,并別有深意地進行久遠的歷史追溯:“亞圣公孟子的第65代子孫在鄒縣混窮了之后,流浪到了青陽河畔,安家,扎根,開花,結果,如今已是‘碩果’10代了。”這里的“一語雙關”絕不是故作深沉,而是同整篇小說的格調、意蘊一致,向讀者透露了十分重要的信息:即古老的齊魯文化仍然非常有生命力地“汩汩流淌”在這些現代農民的血脈之中,不但源源不斷,而且枝繁葉茂。孟家莊人向來以“孝”為先。土改時,村里唯一的一座二層小樓,就這樣順理成章地分給全村輩分最高的“老”祖宗——10歲的槐爺了。而槐爺也無愧為全村的“爺”,他不僅是村人紅白喜事的主心骨,而且在他心里,所有的孟家莊人都是“一個爺爺的公孫”,必須恪守孟家莊的道德倫理規范。已守寡十年的芳嫂在槐爺眼里美麗且賢惠,可當芳嫂有意和鰥居多年的他“合為一家”時,他鄭重地叫了聲“孫媳婦”,將其拒之千里之外。改革開放后,隨著黨的農村政策改變,當年的“小地主”又富裕了,不僅建起了一座三層小樓,還要娶“芳嫂”做媳婦。故事的結尾是,槐爺雖然還是那個德高望重、助人為樂的“爺”,可解放后槐爺坐了30多年的那把“上首椅子”,在不知不覺中已經讓位給鄉長了……亞圣第X代的子孫槐爺面對著1980年代中期巨大的社會倫理變革,困惑而又惶惑不安的心理在不言而喻之中。而讀者的感受卻是黯然的:傳統的孝道倫理沒有隨社會的改革開放而發生變化,只是純樸的“孝”道觀念在現實利益面前讓位于權力文化了——家族的輩分再高也高不過“父母官”。這意味深長的一筆啟示讀者:孟家莊的“爺”地位固然顯赫,擁有經濟實力的三層樓主人的地位正逐步上升,但在村民心理居最高位置的仍是擁有政治的權力者——即春秋興廢,歷史嬗變,但萬變之中有不變,這不變的是我們民族文化心理深層對權力的崇拜,對特權階層的默認。無論是被族人尊奉的“爺”,還是為村人垂涎三尺的小樓,在權勢這閃閃發光的寶座面前,全都黯然失色。小說呈現出了一個沉甸甸的、凝固的文化實體,雖然幾十年的歷史變幻是作為動態背景出現的,但作為文化實體卻是靜態的,甚至是封閉的、凝固的。孟家莊人的行為所昭示的歷史發展趨向,始終不能擺脫齊魯文化倫理的迷霧。小說呈現了政治權力在國人思想中的核心地位與經濟利益對人性的支配作用,我們不僅驚嘆,畢四海對國民性痼疾有著如此獨到的認識和深度的思考。
在《東方商人》中,對齊魯文化的審視仍是畢四海關注的一個重要主題。小說極為細膩地描寫了生活在20世紀初葉的一個棄農經商的秀才,靈魂深處非常典型的痛苦、掙扎與蛻變:一只腳雖踏進了商海,但另一只腳仍艱難跋涉在農民文化土地上尷尬的生存狀態。小說向讀者呈現出了近現代知識分子豐富復雜而又充滿矛盾的文化性格,給人們提供了一個儒商的復雜文化課題,其蘊涵著的對中國傳統農業文化和現代商業文化的反思,對國民性問題的探討,是發人深省的。我們注意到,他關注的人物大多明確標識出為亞圣子孫,意味著這些人物雖生活在現代,但每個細胞里都有亞圣孟子的遺傳,進而意味著他們都是被傳統文化所左右的人,都是觀念作用下的人,即使是東亞巨商孟洛川也不能輕裝上陣。這種頑固觀念像鋼鐵一般堅硬,敲不碎、打不爛,而且盤根錯節,互相制約,同時也互相滋潤,它是一種滲透到骨髓里、滲透到了遺傳基因中的人生觀念:家族、官本位、光宗耀祖、傳宗接代等等,都被表現得鮮活生動。畢四海試圖以現代意識對齊魯文化予以觀照與剖析,貫穿情節背后的當下文化的憂慮與思索,使小說具有濃郁的文化意義及文化品格。
中篇小說《都市里的家族》描寫了一個當今社會的“怪胎”馮老板,他身居高位,用隱蔽的非法手段挪用公款炒股完成了原始積累,然后辭職下海,暴富一方,過著最現代的生活,享用著現代物質文明成果,骨子里卻被數千年的封建意識所左右,養著一妻一妾,為得到傳宗接代的“龍子”費盡心機。而這位小妾是省城大報的著名記者,受過高等教育并標榜現代觀念的知識女性,卻甘為籠子里的金絲雀。小說以馮老板的“現代小妾”口吻展開敘事。揭示了當代中國相當一批新興的資產階級、上流社會、知識人類,不僅不會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的新生力量,反而是倒行逆施、放縱享樂、醉生夢死、危害社會的“毒瘤”這一嚴重的社會問題,表現了中國都市家族中的封建性特征,并指出這種傳統意識的根深蒂固性,形象地展示了現代都市與古老的傳統文化千絲萬縷的聯系。由此我們看到,畢四海對中國農業社會文明本質的深刻領悟和我國現代化前景的深沉憂慮,提醒人們要清醒意識到:當代中國在走向現代文明進程中的道路是曲折和艱難的,享受了現代化的生活未必就是現代人,擁有了現代化的機器和技術也不一定就是現代社會。學者吳義勤對此有一段精彩的評論:“這可以說就是作家為我們揭示的中國現代化的悖論。在此意義上,小說中的‘家族’既是一種寫實性的存在,又更是一種文化性、精神性、寓言性的象征,它表達的是作家對于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畸形的文化現實與精神現實的深刻洞察。作家意在表明,人的現代化以及精神的現代化才是社會文明進程的根本。”[5]畢四海在總結自己的創作時說,我想使我的作品在重構民族靈魂及精神的過程中起到一點作用,最起碼要提醒人們,我們的傳統文化有問題。但同時,洶涌而來的現代文明卻使人瘋狂地聚斂財富,瘋狂地攫取權力,瘋狂地滿足自己各種各樣的欲望。現代文明同樣讓人懷疑。因此,我將不停地拷問現代的人類文明與現代人的靈魂。
畢四海敏銳地感受到,陰暗的愚昧的傳統文化習性在“現代”人們心理上有著濃厚的積淀,在現實生活中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因而深刻反思與剖析改革開放的社會環境下,傳統文化對現代社會和現代生命的潛在而頑強的影響力,揭示中國社會文化心理結構轉變的艱難性,展現中國傳統社會的文化結構和綿延不絕的內在力量,成了他小說中國民性批判的一個首要著力點。
三、人性審視下的多維視野
畢四海不僅僅注目于歷史社會政治之“變”,他似乎更潛心于表現人性之“常”。作為一位有自覺文體意識的作家,面對一體的、穩定的現實主義審美模式危機,他勇于挑戰。當代現實主義強調“真實性”,特別是巴爾扎克和托爾斯泰式的“客觀真實性”,因此對文學的各種假定性手法如象征、擬人、夸張、怪誕、變形、夢幻、神話傳說等缺乏應有的認識和尊重,以“實錄”作為細節真實的標準,不但束縛了文學的想象,而且也使之呈現出千人一面的“重”“大”“拙”的風格。在傳統現實主義原則、經驗、技術等都面臨著“更新”焦慮之時,他大膽嘗試在傳統現實主義為主導的創作方法中采用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的某些手法。
畢四海的小說一般都以人物為主,多種角度切入,不僅給讀者自然化、生活化多側面的立體感,而且更有利于走進人物的心靈世界,揭示出人性的豐富性、復雜性與微妙性。被汪曾祺先生稱為“一首散文詩”的《蛙鳴》是一個精致的短篇,它通過捕捉德香爺在夏夜乘涼時聽蛙鳴的心理瞬間,用意識流手法揭示了孟家莊30年的人事變遷和德香爺的深層心理,呈現出了人性的某種文化內涵。《都市里的家族》《魔圈》等也成功地在現實主義手法中,融入了意識流、象征、荒誕等多種現代藝術元素,讓生活自身在反諷與幽默中顯示自身的荒誕。
《一個人的結構》是一篇用現代主義手法對分裂人性心靈記錄的小說。一個現代知識分子突然有一天徒具空殼,沒了影子,他的意識和靈魂分裂成8個方面,分別用1、2、3、4、5、6、7、8這樣的符號來代替。8個符號代表了這個男人心理和生理、欲望和理智的8個側面,互相糾纏,互相依賴,又互相廝打,互相斗爭,此消彼長。最終八個無影無形的思想意識重新鉆進了這個男人的軀殼,靈與肉的分裂宣告結束,思想與肉體重新合而為一。小說運用了向內轉的敘事視角,人物與事件減少,情節淡化,小說主旨通過主人公的感受和自我表現反映出來,這種主觀因素增強且重視人內心世界的表現方法,多角度地把一個現代知識分子分裂的靈魂入木三分地揭示了出來。就如同魯迅評價陀思妥耶夫斯基寫人一樣,能夠從“善”中看到“惡”,再從“惡”中敲打出“善”,這樣始能見出“人”的靈魂的深。
《財富與人性》在敘事結構上采用漁網式結構和散點透視法。小說總共涉及到數十個人物,每一節由某一個人物的故事和自述組成,它是一個故事情節的扭結點,作家對這一個個散點深入挖掘、透視、觀照。這一個個點交織成一個巨大的漁網結構,它把歷史、現實、文化、人性等等包容進來,疏而不漏。因而小說在敘事手法上打破了傳統的線性時間推進法和敘述人“終身制”,以一個個人物為敘述視點展開敘述,自然的時間鏈條就被一一折斷,線性時間在小說中變成一個個線頭,這些線頭交織、纏繞,重新組織一個藝術空間。同時,小說還不僅以人物統領敘事,而且在每一個人物敘事中,都運用了第一人稱內心獨白和第三人稱全知全能敘事相結合的方式,在自然時間、現實空間之外又引入了心理時間和心理空間,這樣既能對人物的心靈世界洞幽察微,又可對廣闊的生活現實進行全方位的展示。其表現手法既大開大闔,又可細針密線;既運筆如風,又可精雕細刻;既鋪陳渲染,又可疏朗勁道。
畢四海在創作中靈活地綜合運用各種藝術手法,形成了一個多維的現實主義空間,在某種程度上對傳統的現實主義之“真實”與“情節”進行了巧妙的建構,有利于他對文化與人性這一主旨的探究,是作品故事情節的需要,也是思想內容的需要,顯示了畢四海的文學審美表現在尋求突破中的藝術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