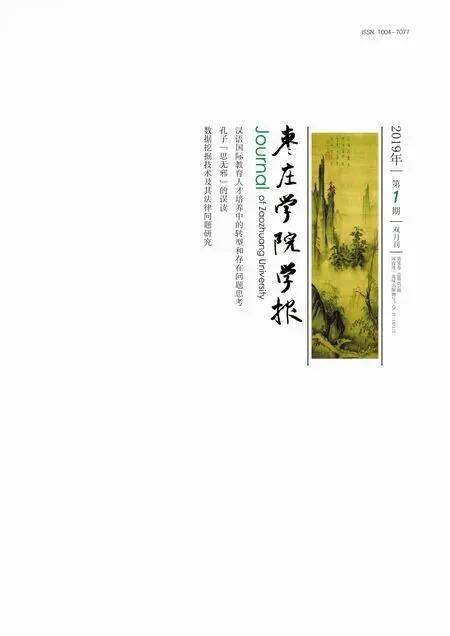中國古代勸進之“穩定”心態論
王承斌
(許昌學院 文學與傳媒學院,河南 許昌 461000)
本文所論勸進,主要指古代臣子在帝王繼位前所行的勸即位行為。①在中國古代王朝更替過程中,這類事件較多。一直以來,人們對此一般持否定態度,認為勸進主要是臣子為謀功名富貴而向帝王示忠、阿諛奉承。勿庸諱言這種心態在勸進中時有發生,有時還較為明顯。然我們的認識若局限于此,則會失之膚淺。古人勸進思想實較復雜,追求穩定是其中非常重要的方面。客觀認識這類事件,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封建社會士大夫之思想和生活態度。
一
中國古代勸進事件中有明顯的求穩定目的,表現之一便是勸進言辭中有大量“天下不可一日無君”“帝王不可久曠”“安社稷”“寧海內”等內容的表述。
如兩漢之際的混戰中,劉秀部下以“帝王不可以久曠,天命不可以謙拒,惟大王以社稷為計,萬姓為心”[1](P21)勸進。三國時諸葛亮等在蜀勸進劉備: “愿大王應天順民,速即洪業,以寧海內。”[2](P888)西晉滅亡后,劉琨、慕容廆等勸進司馬睿:“蒸黎不可以無主……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3](P146)南朝劉宋太子劉劭弒帝后即皇位,眾叛親離,劉義恭等勸進劉駿:“今罪逆無親,惡盈釁滿,阻兵安忍,戮善崇奸,履地戴天,畢命俄頃,宜早定尊號,以固社稷。”[4](P1646)南朝梁傀儡皇帝蕭綱被害后,侯景自立為帝,梁朝滅亡,徐陵、沈炯等人以“萬國豈可無君,高祖豈可廢祀”[5](P119)來勸進梁元帝。后燕皇帝慕容盛在國內兵變中被殺,群臣以“國多難,宜立長君”[3](P3105)勸進慕容熙。安史之亂暴發后,唐玄宗逃亡四川,無心理政,國家混亂,裴冕等人勸唐肅宗“愿陛下順其樂推,以安社稷。”[6](P242)五代十國時后唐莊宗李存勖死于兵變,長子李繼岌亦亡,國家無主,動蕩不安,群臣勸進李嗣源“行監國之儀,以安宗社。”[7](P490)又后唐李從珂起兵擊敗閔帝,馮道等勸進說:“洪基大寶,危若綴旒,須立長君,以紹丕搆……一日萬機,不可以暫曠;九州四海,不可以無歸。”[7](P629~630)北宋滅亡后,南逃大臣耿南仲、汪伯彥、張俊等人以“中原不可一日無君”[8](P11347)勸進宋高宗趙構,期盼“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9](P107)“亟行天討,興復社稷。”[8](P11278)元代蒙哥汗去世后,在激烈的皇位爭奪中,趙良弼等人勸進忽必烈:“今中外皆愿大王早進正宸,以安天下,事勢如此,豈容中止,社禝安危,間不容發。”[10](P3744)又元成宗去世,成宗次兄之子愛育黎拔力八達等人以“神器不可久虛,宗祧不可乏祀”[10](P479)勸進武宗。明建文帝朱允炆實行削藩,燕王朱棣發動靖難之役,攻入應天府后建文帝下落不明,臣子以“天下豈可一日無君”[11](P272)勸進朱棣;明英宗被俘后,國家無主,“時議者以時方多故,人心危疑,思得長君以弭禍亂。”[11](P479)在瓦剌大軍逼近的生死存亡關頭,于謙等大臣憂國忘身,勸新主朱祁鈺“早正大位,以安國家。”[11](P479)等等。
這些勸進多發生在局勢動蕩之時,無論是天下無主、群雄紛爭,還是天下有主卻不能治國理政而致混亂,臣子們勸進中所說之“安社稷”類絕非虛言,他們勸進新主即位,是渴望在亂世中輔佐君王,君臣同心協力、名正言順地“安社稷”“弭禍亂”,再建穩定統一大業,實現個人治國、平天下之理想,此乃儒家思想之體現,這在許多勸進言辭中表現明顯。如劉秀部下勸進時所說“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1](P21),“其所志”便是他們心中建功立業之志。南朝梁末徐陵、沈炯等勸進梁元帝:“待陛下昭告后土,虔奉上帝,廣發明詔,師出以名”[5](P119),希望與君王一同“廓清函夏”[5](P117),實現其“治平”愿望。北宋滅亡后,耿南仲、汪伯彥、張俊等人勸進宋高宗趙構,期盼“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君臣同心協力“亟行天討,興復社稷”等,均是此意。有些勸進言辭中還有鮮明的憂國憂民色彩,如兩晉之交劉琨等人勸進時說:“自元康以來,艱過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宸極失御,登遐丑裔,國家之危,有若綴旒……四海想中興之美,群生懷來蘇之望。”在回顧了元康以來社會動蕩不安、國家危在旦夕之后,緊接著指出民眾內心的悲憤:“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茍在食士之毛,含氣之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況臣等荷寵三世,位廁鼎司,承問震惶,精爽飛越,且悲且惋,五情無主,舉哀朔垂,上下泣血。”“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3](P146)飽含了對國家、民生的殷切關懷,對新帝登祚穩固社稷、安定萬民的殷切期待和深摯的憂世情懷,感人至深。
“治國、平天下”是古代士人的人生理想,是許多人為之奮斗終身的目標。混亂的時局,尤能激起士人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他們勸進那些手握兵權、有聲望者“進正宸”“正大統”以定人心,希望君臣共同努力穩定局勢,進而再現統一穩定之盛世局面。其中包含的穩定心態、“治平”思想十分明顯。這一點較好理解,無須多論。
二
勸進中穩定心態的第二種表現是強調“正名位”。如劉邦統一天下后群臣勸進說:“誅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為王侯。大王不尊號,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12](P379)諸將“皆疑不信”,主要是因此前周代分土封侯為帝王之權力,劉邦不即帝位,則分封諸將行為名不正、言不順,故被分封者疑慮不安。南朝劉宋時劉義恭等勸進劉駿“宜早定尊號,以固社稷”,即早稱尊號以正名。南朝梁末徐陵、沈炯等人以“待陛下昭告后土,虔奉上帝,廣發明詔,師出以名”[5](P119)勸進梁元帝。代國滅亡后,拓跋珪率兵平亂,許謙等以“宜正位居尊,以副天人之望”[13](P2734)勸進。隋末混亂中,裴仁基等勸起義軍首領李密即尊位“正位號”[14](P5774),又裴寂等人以同樣意思勸進李淵。②兩宋之交,南逃臣子以“當天下洶洶,不早正大位,無以稱人望”[8](P11470)勸進宋高宗。元泰定帝崩,群臣以“擾攘之際,不正大名,不足以系天下之志”[10](P3328)等勸進圖帖睦爾(文宗)。明代靖難之役后,臣子勸進燕王朱棣:“殿下為太祖嫡嗣,徳冠群倫,功在社稷,宜正天位,使太祖萬世之洪業,永有所托。”[11](P272)明英宗被俘后,于謙等大臣勸進新主朱祁鈺“早正大位,以安國家”等。
有人認為這類“正名”說法只是勸進者為取悅被勸進者、為謀私利而尋的借口。實際上并非如此,正名位是封建社會鞏固政權、維持穩定秩序的重要措施和必須手段。
首先,在天下無主而致的混亂紛爭中,正了名位,建立合法政權,可獲得政治上的主動,最終雖未必能成功,卻能在一定程度上獲得民眾認同,給士人以歸屬感,③能增強凝聚力——“系天下心”,更順利地爭奪人才、臣服雄杰等。在古人看來,“是非之正,取之逆順。逆順之正,取之名號”[15](P354),“名茍不正”則難以服眾,會“事有不從”,而憑“帝命以伐有罪”,“師出以名”,則名正言順,會更有號召力,更利于鞏固現有政權乃至平定混亂、統一天下,正如魯昌勸進晉元帝時所說:“諸部猶怙眾稱兵,未遵道化者,蓋以官非王命,又自以為強。今宜通使瑯邪,勸承大統,然后敷宣帝命,以伐有罪,誰敢不從。”[3](P2806)從中不難看出他們渴望輔佐新主建功立業、實現“治平”的愿望。當然,亂世中不是任何人、任何情況下正名都有此效果,只有被勸進者本身是尚受擁護的已亡政權合法繼承人,即舊皇室之后裔,如司馬睿之于西晉王朝,趙構之于北宋王朝等;或亂世紛爭中功勛顯赫而受眾多士人擁護者,如漢光武帝劉秀,金太祖完顏阿骨打等。若兩條都不具備而稱帝號,則無甚作用甚至適得其反。
這種“正名”作用在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上有較明顯體現。曹操挾持漢天子,將“名”控制在自己手中,代表著中央與正統,在四處征伐過程中取得了巨大優勢。“漢天子”招牌,對社會上一些中小軍閥產生了強烈影響,為曹操贏得了當時重要社會力量——士家大族的支持,贏得了社會輿論的支持、雄才俊杰的依附等。相反,反對曹操便為不義,是悖禮叛逆。名分之“正”的作用在此得到了充分體現。這方面,筆者在《先唐勸進文中正名思想論析》一文中有過論述,可參看。雖此“正名”與本文所論有差別,然無本質不同。勸進中的正名主張也正是看到了這一點。
其次,就禪代而言,當時舊皇雖在,但大權旁落,權臣勢大,出現君不君、臣不臣現象。這是“名”之亂,不符合應有秩序與規范,對安定民心、維持統治秩序不利,極易導致政治上的混亂。因權臣長期執政,故禪代之際朝中大臣基本上都是權臣集團成員,他們之勸進雖有謀集團利益、謀個人政治資本之嫌,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包含著通過正名來改變名實不符現狀以消除隱患、更好地維持統治秩序之意圖。眾所周知,歷史上因權臣執政引人不滿,臣子與失勢君王聯合奪權,或者借“勤王”、盡忠王室之名行反叛者不在少數,這在曹操、司馬昭、武則天等人身上均發生過。④無論是真心維護皇權,讓其名至實歸,還是別有用心,這種奪權、叛亂主要是由權臣控制朝政、君臣名實不符而起,或者說,這是一個很好的借口。相反,若權臣在眾人擁護下取代舊皇,正名即位建立新政權,則能消彌不少此類禍亂。因此時若有人再行反叛,那便是以下犯上,反而名不正、言不順,被置于極不利地位。所以說,這種情況下之“正名”,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為了政權的穩定。
正名思想在中國社會由來已久,其最初產生的目的正是為了穩定政權,消除社會混亂。春秋時期天子失政,社會動蕩,當時諸侯既不忠君,也不從君,而是稱王稱霸,各自為政。面對這種情況,孔子提出為政必先“正名”的主張。他認為“君”“臣”“父”“子”等每一個名,都有其一定意義,即這個名該有的行為規范,它所指事物應該如此的標準。“正名”就是要求處于君、臣、父、子等不同地位的人,所行符合此名應有的標準規范,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16](P66),“事君不貳是謂臣”[17](P347)等。君臣各自履行自己的職責,不得逾越,做到名實一致,只有這樣才能消除社會動蕩。正名思想在后世一直為人們所重視,相關論述甚多,不一一贅述。大體而言,這種思想與儒家禮教關系密切,其政治上的內涵,主要是通過正君臣之名來穩固封建統治,君實施名賦予它的統治權力,臣子無條件服從君主命令。徐復觀先生在“名”之作用方面曾有過精辟論述,他說:
在以老子、孔子為中心的文化活動中,可以說原始的咒語,完全由合理的思維和合理的言語所代替了。但名的神秘性雖在宗教中褪色或消失,卻在政治上還發生很大的作用。貴族的統治階級,把自己由地位而來的名,認為即是政治權力的真。有此名,即無條件地應有此統治權力,人民即應無條件地服從他的權力。[18](P208)
封建統治階級認為,他們由地位而來的“名”本身就是“權力的真”,是權力正當性的來源,代表著在社會上擁有絕對的統治權、處于支配地位,其他人應無條件服從,如“諸侯之義,非天子之命,不得動眾起兵誅不義者”,[19](P213)“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國則受命于君”[15](P386)等等。名位正,且在君無過失、無暴政情況下,諸侯不聽命就是對“名”的破壞,是背離“禮”和君臣倫理,為逆天而行、大逆不道,那將遭致眾人的反對,天子更可以發號司令、“恭行天罰”以征討剿滅之。正名之作用實顯而易見。
“正名”是合法政權建立時必須重視的。任劍濤先生在探討中國政治的合法性時,就提到儒家在建立政治合法性過程中禮與正名缺一不可,他說:“‘正名’,即按照倫理道德的規范端正政治行動的名分,就是一個樹立政治合法性權威必須重視的事情。”[20](P27~34)也就是說,正名可以較好地解決政治合法性問題和避免政治危機的出現,它在封建社會政治上有著明顯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見,勸進正名的最終目的,或是為便利地穩定局勢、實現一統,或是為國家的長治久安。
三
勸進中穩定心態的第三種表現,是“天命”“人心”的表述,此為證明被勸進者進位乃順天應命、順人心之舉,許多勸進事件中均存在。如劉秀部下勸進時說:“帝王不可以久曠,天命不可以謙拒,惟大王以社稷為計,萬姓為心。”諸葛亮等勸進時稱劉備:“圣姿碩茂,神武在躬,仁復積德,愛好人士,是以四方歸心”。[2](P888)隋末混戰中,段達等人以“天命不常,今鄭王功徳甚盛,請揖讓,用堯、舜故事”[21](P3693)勸進王世充。安史之亂暴發后,裴冕等人以“萬姓颙颙,思崇明圣,天意人事,不可固違”等勸進唐肅宗,希望他“即皇帝位以系中外望”。[6](P242)后漢劉知遠功勛卓著,張彥威等勸進說:“今遠近之心,不謀而同,此天意也。王不乘此際取之,謙讓不居,恐人心且移,移則反受其咎矣。”[14](P9340)完顏阿骨達維護女真部落聯盟有功,阿里罕普嘉努宗翰等人稱:“大功已建,若不稱號,無以系天下心。”[22](P26)金攻陷遼都后遼天祚帝逃亡,李處溫等勸進耶律淳:“主上蒙塵,中原擾攘,若不立王,百姓何歸?”[23](P352)北宋亡臣勸進宋高宗趙構:“大王皇帝親弟,人心所歸,當天下洶洶,不早正大位,無以稱人望。”希望趙構“早正大寶,以定人心,以應天意”[8](P11701)等等。
在新舊王朝禪代期間的勸進里,這種“天命”、“人神屬望”表述更集中,勸進者同時還列天地祥瑞之出現以證明它。此乃為權臣進位造勢。如曹丕稱帝前,“侍中劉廙、辛毗、劉曄、桓階、陳矯、陳群等,爭陳符命勸進。”[24](P286)司馬倫執政期間,“宗室諸王、群公卿士咸假稱符瑞天文以勸進。”[3](P1601)群臣勸進劉裕時說:“‘有命自天’……‘勛格天地’者,必膺大寶之業。”“太史令駱達陳天文符瑞數十條,群臣又固請,王乃從之。”[4](P48)勸進蕭衍:“君臨萬方,式傳洪烈,以答上天之休命。”[5](P29)楊堅上位前,百官列舉當時出現的“赤雀降祉,玄龜效靈,鐘石變音,蛟魚出穴”[25](P12)等祥瑞勸進,北周靜帝禪位詔中也說道:“上則天時,不敢不授,下祗天命,不可不受。”[25](P12)徐知誥被群臣勸進時,認為“人望己歸”[26](P767)而即位建國,等等。
這其中的“天命人心”、祥瑞之說,并非如有些人所認為是勸進者自欺欺人之談。古人多認為,受命于天,其政權便是合法的。如班固就曾說:“受命之君,天之所興,四方莫敢違。”[19](P349)而祥瑞的出現,正是天意認可的表現。勸進中明言這些,也是意在解決政權合法性問題,是為避免出現政治危機所作的努力。然眾所周知的是,漢代董仲舒主張“天人感應”神學理論,他融合先秦儒家“天命論”和陰陽家的五行學說,提出“天”是有意志的至高無上的神,皇帝受命于天,體現天的統治權力,君權神圣不可侵犯;并認為政通人和,得上天認可,天降祥瑞以昭告;而君王失政,致民怨國危,天便降災難以警示、懲罰——“凡災異之本,盡生于國家之失。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異以譴告之。”[15](P318)后來這又與河圖、洛書等神話傳說相結合,發展出荒誕不經的讖緯之學。此說漢魏之際已不時受人批判,逐漸為人們所拋棄。然勸進中為何一而再地提及天命、祥瑞?其實,此中天命、人心思想及祥瑞意識,非漢代讖緯思想之翻版,更多地是對傳統天命、民心思想的繼承。
天命思想在夏和西周時代便已產生。《尚書·召誥》有“有夏服天命”[27](P471)之說,即夏王朝受天之命統治萬民。商代,天命思想仍和宗教迷信思想有密切關系,但已經有了“天命即人心”觀念的萌芽。《尚書·泰誓》中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27](P329),已包含人心即天命思想。《湯誓》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27](P227),謂天命欲亡夏桀,是因其“多罪”,若“有夏無罪”,天命則未必“殛之”。以此而論,天命實際在人而非在天。春秋戰國時期,天命思想有了新的發展。孟子在論天人關系時注意到人的作用,既認為君權天授,又強調君權要“民意”認可,提出了“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28](P194)及“以人為本”等主張。而漢代賈誼在論及王朝興衰時,也認為人的善惡行為與天命有著直接關系:“知善而弗行,謂之不明;知惡而弗改,必受天殃。天有常福,必與有德;天有常災,必與奪民時。”(《大政》)[29](P268)等。可見古人認為執政者需受天命、得民心,這樣才能長治久安,否則統治難以持久。劉澤華先生研究古代政治思想時認為:“植根于天人之際的權力合法性較之訴諸武功和先祖列宗而言,無疑是一種更為廣泛和深厚的傳統。”[30](P314)這種傳統思想是勸進中天命、人心說的基礎。
勸進中與天命相關的祥瑞意識,與其說與讖緯有關,不如說是原始先民祥瑞祈求的表現。祥瑞思想起源甚早,原始部落的圖騰已包含有祥瑞意識,它源于先民對災難、死亡的畏懼,對幸福、美好、平安的追求,體現了趨吉避兇、消災保平安的本能。徐華龍《中國祥瑞文化》、寧業高《中國祥瑞文化漫談》等著作對此有詳細闡述,此不贅。“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出妖孽”[31](P1693)類思想早有萌芽,如《詩·小雅·十月之交》中寫日食、月食、地震等自然現象,并將之與朝廷用人不善聯系起來,認為它們是上天對人類的警告——“日月告兇,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32](P845)便是其表現。
傳統的天命、祥瑞思想,積淀在人們內心形成受天命、得民心將會天地呈祥、國泰民安觀念。勸進中應天命、順人心內容的陳述,正是這種觀念的不自覺體現,表現了勸進者對穩定政治的渴望。也可以說,是用人們對盛世、德世,對和平、穩定生活的期盼,為被勸進者上位尋求穩固的統治基礎。
四
穩定心態的第四種表現,是勸進文中功德的陳述。如言劉秀“平定天下,海內蒙恩”,[1](P22)完顏阿骨達維護女真部落聯盟有功,抗遼中戰功顯赫,阿里罕普嘉努宗翰等人說“大功已建,若不稱號,無以系天下心。”明代臣子勸進燕王朱棣時強調:“殿下為太祖嫡嗣,徳冠群倫,功在社稷”等。這方面更明顯的表現是禪代過程中群臣勸進權臣。如王莽進位過程中,群臣上書稱頌其“收復絕屬,存亡續廢,得比肩首,復為人者,嬪然成行。所以藩漢國、輔漢室”[33](P4083)等功德者比比皆是。趙翼曾說這一過程:“始則頌功德者八千余人,繼則諸王公侯議加九錫者九百二人,又吏民上書者前后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34](P71)可見人們對此之重視。其他勸進中都或多或少有這方面內容。
因種種原因,前人對此功德之陳述一直頗有微詞,禪代過程中這方面內容尤受詬病,被認為是為進位者歌功頌德,是為求個人名利而阿諛奉承。如趙翼曾說:“蓋自漢魏易姓以來,勝國之臣,即為興朝佐命,久已習為固然。其視國家禪代,一若無與于己,且轉藉為遷官受賞之資。”[35](P322)后世人也多持此見。實際上,這種認識有失偏頗。無論禪代還是混亂之際的勸進,這種功業的陳述乃是必須,是新政權穩定之基礎,無此則不能服眾,易致混亂敗亡。就目前所見眾多勸進言辭看,這方面陳述或有所夸大,然大多實有所據,非純粹阿諛奉迎類溢美之詞。亂世中功勛顯赫者,如劉邦、劉秀、完顏阿骨打、朱元璋等自不用說,禪代時被勸進之權臣也都是有相當聲望、有堅實政治基礎者,如王莽、曹丕等;許多更是在天下分裂、皇權衰弱之際累建戰功而功勛卓著者,劉裕、蕭道成、蕭衍、陳霸先等無不如此。沒有這種聲望和功德,沒有自己的勢力集團,欲受禪絕無可能。傳統德治思想是勸進中功德陳述的內在原因。
中國古代儒家一直信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這一點。《左傳?僖公三十三年》中便有“德以治民”語。《尚書·堯典》稱堯“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于變時雍。”[27](P31)認為“克明峻德”可致“協和萬邦”,統治穩固,即君主個體道德是政治的基礎。孔子則明確提出“為政以德”的政治理念,他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16](P15)又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16](P16)將德和禮有機地結合了起來。為政治民需以德,則大德者當有天下。《中庸》中說道:“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31](P1705)謂只有具仁德者方可治理天下,樹立天下之根本法則。禪代過程中舊皇之退位詔,也多有對受位者功德的陳述,如漢獻帝退位詔中說:“是以前王既樹神武之績,今王又光裕明德以應其期”[36](P861),魏元帝禪位于西晉詔曰:“惟王乃祖乃父,服膺明哲,輔亮我皇家,勳德光于四海”[3](P50)等等,幾乎無有例外。雖其中所說未必是真心之言,然“天命無常,惟歸有德”思想卻十分明顯。
“有德者居天下”之思想影響深遠。被勸進者若無功德則無法服眾,功高德大者上位,才能得到最大多數人的支持,“協和萬邦”,建立穩固的統治。勸進中功德的陳述明顯體現出這種德治思想,或者說是勸進者進行的仁德宣揚與勸說,也正是他們渴望國家穩定的表現。
最后須提的是,常被人批判的勸進者謀取個人利益這一點我們并不完全否認,那在一些勸進中客觀存在,然這不僅與本文所論其中穩定心態的存在不矛盾,反而更能證明之,因穩定的局勢方符合士大夫階層的利益,進一步說,個人利益本就與國家命運息息相關,二者本為一體,政局不穩,天下混亂,個人、家族、國家利益均將受損。綜而言之,無論從哪方面看,謀求穩定都是古代勸進的重要目標之一。
縱觀中國歷史上的諸多勸進,許多確實在特定歷史階段發揮了重要作用,促進、維護了國家的統一、穩定。對此,我們應給予客觀而全面的評價。
注釋
①中國古代勸進有兩種類型,一是勸即最高帝位,如侍中劉防等勸曹丕代漢等,這類勸進較多;一是勸權臣接受帝王給予的九錫之禮等賞賜,如鄭沖等勸司馬昭受禮等,此類較少。兩類雖有差別,然無實質的不同,本文側重論述前一類.
②裴寂等勸進說:“桀、紂之亡,亦各有子,未聞湯、武臣輔之,可為龜鏡,無所疑也。寂之茅土、大位,皆受之于唐,陛下不為唐帝,臣當去官耳。”(《舊唐書·裴寂傳》,中華書局1975年版,2287頁。)裴寂等人從唐王處得土地、封號,唐王不稱帝,則此分封名不正言不順。這與群臣勸進劉邦時所說“大王不尊號,皆疑不信”情況類似.
③封建時代士人效忠之對象、最終之歸屬是國家,而國家之代表為皇帝。國亡世亂,天下無主,士人無所歸依,內心惶惶,故渴望自己所屬集團首腦盡快“正位”,建立合法政權,使自己有歸屬感.
④武則天情況特殊,她在唐高宗時控制朝政,雖不屬權臣執政,實無甚差別,均造成君主名存實亡之結果。故列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