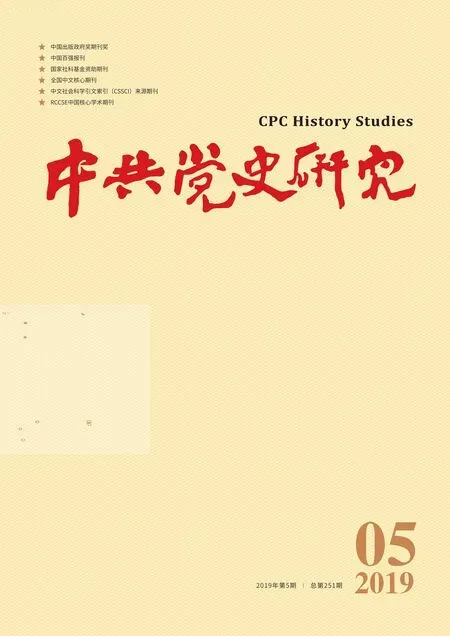“解放時代”的來臨
——五四時期“解放”觀念的歷史演變
王 鴻
在近代中國的思想演變中,“解放”無疑是一個重要的觀念,它不僅廣泛出現在五四時期的文獻中,而且是把握革命時代不可忽視的關鍵面相,甚至在后革命的20世紀80年代前后,公共輿論中還依然強烈回響著“思想解放”的口號。然而,綜觀新近的史學研究,“解放”這一橫亙百年中國近代史的觀念,卻出乎意料地受到研究者的冷落[注]從相關研究來看,德國學者李博(Lippert Wolfgang)留意到這一觀念在近代中國的重要性,但他并未深入探討,對于相關歷史脈絡也未具體梳理。參見〔德〕李博著,趙倩等譯:《漢語中的馬克思主義術語的起源與作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225—228頁。相比于研究者對于近代中國思想中的“解放”觀念的忽視,國外學者關于“解放”(Emancipation)觀念在西方世界的演變,倒是有不少直接的研究。經典性的研究,參見德國概念史家科塞雷克 (Reinhart Koselleck),“The Limits of Emancipation: A Conceptual-Historical Sketch”,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l History: Timing History,Spacing Concept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248-264. 新近的研究則有〔墨西哥〕M.P.勞拉(María Pía Lara)著,高靜宇譯:《概念變化的語義學:解放概念的出現》,《世界哲學》2011年第6期。另外,在2015年,《希帕蒂亞》(Hypatia)期刊還組織了一組關于“解放”(Emancipation)的研究性論文,比較深入地探討了其與女性主義的關系,參見Susanne Lettow, “Emancipation: Rethinking Subjectivity,Power,and Change”,Hypatia, Volume30, Issue3, pp.501-512.。一方面,這自然與“解放”觀念在當前公共輿論中的逐漸退潮有著緊密關系;另一方面,則或多或少受到史學研究“碎片化”趨勢的影響,促使像“解放”這樣跨越不同歷史時期、有著重大歷史內涵的觀念,得不到應有的嚴肅討論。可以說,在新的時代情境下,對“解放”作出重新探討,直接考驗著研究者能否沖破不同歷史時期的層層限制,以一種長時段、跨時代的視野捕捉其間的歷史變動,重新發掘其所內蘊的“問題意識”。
當然,作為一項初步的研究,本文并不會全面考察“解放”觀念的百年變遷史,而是主要聚焦在“解放”觀念興起的五四時期[注]按照余英時先生的說法,“五四運動”有廣、狹兩種含義:狹義的“五四”是指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發生的學生愛國運動;廣義的“五四”則指在這一天前后若干年內所進行的一種文化活動或思想活動,它可上溯至1917年的文學革命,下推至1927年的北伐戰爭。參見《余英時文集》第2卷,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82頁。本文所謂的“五四時期”是就其廣義而言。至于下文提及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則將時間點上溯至《新青年》(原名《青年雜志》)創刊的1915年。。本文認為,正是在這一時期,“解放”開始逐步成為影響近代中國思想變遷的重要觀念,它所代表的那種解脫一切束縛的思想趨向開啟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解放時代”。同時,正是在這一時期,“解放”觀念發生了一個內涵上的重要裂變,從作為啟蒙觀念的“個人解放”轉變為作為革命觀念的“階級解放”和“民族解放”。這一轉變是如何發生的?“解放”觀念何以成為啟蒙時代與革命時代共同使用的觀念?在這一轉變的過程中,是否存在某種同一性的、跨越不同歷史時期的“問題意識”?這些問題,雖然主要涉及五四時期的思想變遷,但也是我們把握百年流變中的“解放”觀念,不可不面對的問題。
一、何謂“解放”?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除“科學”和“民主”之外,“解放”亦是把握那個時代脈搏的重要觀念。早在1915年,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便對“解放”作了這樣一番解讀:“解放云者,脫離夫奴隸之羈絆,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謂也。我有手足,自謀溫飽;我有口舌,自陳好惡;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絕不認他人之越俎,亦不應主我而奴他人。蓋自認為獨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權利,一切信仰,唯有聽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斷無盲從隸屬他人之理。非然者,忠孝節義,奴隸之道德也。”[注]陳獨秀:《敬告青年》,《青年雜志》第1卷第1號,1915年9月15日。而四年后,剛剛經歷了五四學生運動的蔣夢麟,也以“解放”為出發點,對青年群體說:“你有情感,為何不解放?你有思想,為何不解放?……這回五四運動,就是這解放的起點,改變你做人的態度,造成中國的文運復興;解放感情,解放思想,要求人類本性的權利。”[注]蔣夢麟:《改變人生的態度》,《新教育》第1卷第5期,1919年8月。在這里,陳獨秀、蔣夢麟二人的看法,雖有著不同的時空語境,但異曲同工,均以青年讀者為寫作對象,也都以“解放”作為他們論述的核心觀念,強調青年應該勇于“解放”,以養成“自主自由之人格”,要求“人類本性”。問題在于,“解放”為何會成為他們論述的核心觀念?而尋求“自主自由之人格”和“人類本性”,又為何需要通過“解放”的途徑來實現?這些問題,著實有必要進行一番細致檢討。
事實上,陳獨秀、蔣夢麟此處看似信手拈來的“解放”二字,同“科學”“民主”一樣,都屬于外來的“新名詞”,在新舊之際的五四時期有著遠為復雜的面相。當然,這不是說傳統中國并未有“解放”二字,而是說五四時期的“解放”觀念在西潮與新潮的沖擊下,已然有了全新的意義。大致而論,傳統中國的“解放”一詞,主要有三種含義:其一為解開(如船繩、牽引動物的繩子)[注]《朱子語類》第138卷中便有“解放”馬匹的用法。在晚清的《大清光緒新法令》中亦有“解放他人所系牛馬及其他獸類未至走失者”“解放他人所系舟筏未至漂失者”等語。;其二為釋放(主要指罪犯)[注]《三國志·魏書》在記錄趙儼事跡時,便提及“縣多豪猾,無所畏忌。儼取其尤甚者,收縛案驗,皆得死罪。儼既囚之,乃表府解放,自是威恩并著”;在清代的《刑案匯覽》中,還有“解放賊人”“令該犯解放”等語。;其三為發放(如賑災財物)[注]在《申報》的諸多籌款賑災文告中,曾提及該種含義。如在一募賑文告中,論者提及“祈諸善士接閱后,迅解腰囊,趕即隨冊擲交該公所,俾得集成大批解放,實為無量功德”。參見《申報》1887年11月29日。以上關于“解放”一詞的古典含義,參考了愛如生的中國基本古籍庫、《申報》數據庫以及羅竹鳳主編的《漢語大辭典》。。但這三種含義均未有陳獨秀、蔣夢麟所指稱的那種與“自主自由之人格”“人類本性”結合在一起的意涵。具有現代意涵的“解放”觀念,如“女子解放”“奴隸解放”等,是直到晚清最后十來年才出現的觀念[注]參見何震:《女子解放問題》,《天義·衡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33—141頁。此外,《湘報》在關于當時美國總統威廉·麥金萊(William Mckinley)的介紹中,提及其“為民政黨員,主倡解放奴隸論”。參見《美總統末金咧氏小傳》,《湘報》第117號,1898年8月2日。《新民叢報》在提及俄國農奴解放時,則有“一八六一年亞歷山大下解放奴隸之令”等語。參見《西伯利亞鐵道說略》,《新民叢報》第40—41合期,1903年11月2日。這幾篇文章都是轉譯日本報刊,顯示晚清的“解放”觀念與日本背景有關。值得注意的是,在《國民日日報匯編》第1集的《箴奴隸》一文中,作者使用“放免奴隸”“黑奴一聞林肯釋放之說”“天下之能沖決奴隸之網羅者惟強盜”等語。這里的“放免”“釋放”“沖決”等均有“解放”的內涵,但未用“解放”,顯示在當時“解放”仍未是公共輿論中的普遍用詞。參見《箴奴隸》,《國民日日報匯編》第1集,東大陸圖書譯印局,1904年,第18、17、24頁。。不過,這些觀念在晚清主要流行于無政府主義群體之中,并未成為社會的主要思潮。真正讓“解放”在公共輿論中成為一種重要的觀念,是在五四學生運動后,與當時女子解放思潮頗有關系。
五四學生運動后的女子解放思潮,是鑒于女子在傳統綱常倫理社會的受壓迫地位,而尋求女性獨立的一種思想運動和社會運動。我們仔細閱讀當時留下的諸多文獻,會發現是否應該以“解放”來形容這場運動,是一個備受爭議的問題。葉楚傖直言:“解放的意義有三種:(一)對于禽獸的。(二)對于罪犯的。(三)對于奴隸的。女子是禽獸么?是罪犯么?是奴隸么?……如何可將‘解放’二字來污蔑她作禽獸、罪犯、奴隸。”[注]楚傖:《女子解放兩問題》,《民國日報·覺悟》1919年8月13日。而張申府也強調“‘女子解放’這個名詞,乃是大大的一個不妥當”,認為“解放、解放,細剖起來,實含著輕侮的意味”,甚至不無怒氣地說:“宰豬吃的人,捆個豬來放在圈里,也可說是解放。解放是不是如此的?”[注]張崧年(張申府):《“女子解放”大不當》,《少年中國》第1卷第4期,1919年10月15日。在他們看來,以指涉罪犯、動物的詞匯來指涉女子,顯然是一種不合適的用法。
除了對“解放”一詞所指涉對象的不滿外,當時對于使用“解放”的另一種不滿,在于“解放”蘊含著被動的意味。在上述葉楚傖的文章中,他便主張應該用“復權”來替代“解放”一詞,認為二者實含有“自動”與“被動”之分別,而女子解放理應是一種自動而非被動的行動[注]楚傖:《女子解放兩問題》,《民國日報·覺悟》1919年8月13日。。張申府甚至指出,“敬重別人的價值的,絕不說去解放人;曉得自己價值的,也必不甘受人解放。有志氣的人,有真知識的人,絕不要求人,絕不向人請愿;要求請愿,都是懶惰的表示,都是弱者的行為,自居下劣的行為”,因而“解放,只有向自己說”。由此,他主張“吾們現在應當倡導的不是‘女子解放’,只是‘女子獨立’”。[注]張崧年:《“女子解放”大不當》,《少年中國》第1卷第4期,1919年10月15日。除了葉楚傖、張申府外,康白情也留意到當時上海輿論界對于女子問題有“解放”與“打破”的名義之爭,諸多女性不滿“解放”二字,認為應該以更具主動意涵的“打破”二字取而代之。他還特地在《救國日報》作了一篇《“解放”和“打破”》的文章,來論述這場名詞之爭。[注]康白情:《女界之打破》,《少年中國》第1卷第4期,1919年10月15日。關于康白情的《“解放”和“打破”》一文,沈定一在《星期評論》中有提及,參見玄廬:《名義重?事實重?》,《星期評論》第12號,1919年8月24日。另外,在《星期評論》中,一位署名為“蒼園”的女士也頗不滿意“解放”一詞,認為“這兩個字從改革家口里說出來,犯了傲慢男性的毛病,不知不覺把那誠摯的精神,被那缺少敬意的辭氣打消了”,強調“不要說‘解放’女子,要說‘保重’女子”[注]蒼園:《女子神圣觀》,《星期評論》第22號,1919年11月2日。。直到1920年初的《北京大學學生周刊》中,也仍然有作者指出應該放棄使用“解放”,而改用“自決”一詞,其理由與前述幾位知識分子的看法大致相同,認為“‘解放’是被束縛的人,想法子去懇求那束縛的人,解去束縛,或是那束縛的人自己覺悟解去被束縛的人;‘自決’是被束縛的人,想法子去反抗那束縛的人,解去束縛。換言之,一是他動的,一是自動的;一是客觀的,一是主觀的”[注]悲吾:《“解放”和“自決”》,《北京大學學生周刊》第5號,1920年2月1日。。
就此而言,無論是以“解放”的傳統意義理解“女子解放”一詞,還是試圖以“復權”“獨立”“打破”“保重”“自決”等來替代“解放”一詞,都反映了在新舊之際,“解放”從舊義轉變到新義過程中的復雜性。而在這種舊義不斷“擠占”新義的情況下,如果新義試圖破繭而出,那么也只能在這種嬗蛻過程中,借由強調有別于舊義的厘清方式得以實現。戴季陶留意到關于“解放”的這種名詞之爭,指出之所以部分知識分子不滿于“解放”一詞,是因為“‘解’和‘放’這兩個字,古時節都是用在禽獸身上的”。不過,他認為在新情境下的“解放”一詞,實際上已經有了全然不同的內涵,因為“這個字本來是從外國來的,不是從《說文》上、《爾雅》上、《廣韻》上來的,要在那些地方去訪問它的出身,永遠也訪問不出來。英文就叫作Liberate,人人都曉得這是和‘自由’的意義相同。不過,Liberty是名詞,它是動詞罷了”。在新情境下,“解放”不再是對于禽獸、罪犯而言的,而是對于一切“束縛”而言的。因此,按照戴季陶的看法,“這個字本不專是用在女子身上,凡是一切打破偶像、恢復自由的事件,都可以用得著的。比方說,對于貴族的平民解放,對于雇主的工人解放,對于地主的農夫解放,對于主權國的殖民地解放”。[注]戴季陶:《還是要解放》,《民國日報·覺悟》1919年8月25日。
匡僧也解釋了“解放”的新內涵。與戴季陶將“解放”視為“Liberate”的翻譯不同,他認為“解放就是英文的Emancipate。這個字的解釋,就是To set free from the power of another,或是To liberate from any bondage。將他的意思概括譯出來,就是說‘脫離外力的束縛,還于自由’”。因而,按照他的理解,“解放就是恢復自由”。人之所以不自由,都是因為外力的“束縛”,“除去這個‘束縛’,就是叫作‘解放’。再詳細說:凡是妨害了自覺、自尊、自發、自全、自主、自治,都是叫作‘束縛’,排除那些妨害,就是叫作‘解放’”。[注]匡僧:《什么叫解放?什么叫自由?》,《解放與改造》第1卷第6號,1919年11月15日。
另外,像陳獨秀這樣的新文化運動的急先鋒,也直言不滿于當時關于“女子解放”的名詞之爭,特地在《新青年》雜志上作了一篇以《解放》為題的隨感錄,他雖然未像戴季陶、匡僧那樣以英文解釋“解放”[注]值得一提的是,在臺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開發的英華字典資料庫中,收錄了1815年至1919年間的英華字典,在近代諸多英華字典中,并未以“解放”來翻譯liberate、emancipate,而是多以“釋放”“放”“釋”等來翻譯。甚至直到1916年出版的赫美玲(K.Hemeling)《官話》(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Standa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and Handbook for Translations)也是以“解脫女子”來翻譯“emancipation of women”。另外,“解放”一詞則是作為release、acquit、free、loosen、discharge、deliver、disassociate等英文單詞的翻譯。可見以“解放”作為liberate、emancipate的對應翻譯,其實是相對晚近的事件,這也說明戴季陶、匡僧的文章其實頗具開創性。參見赫美玲:《官話》,總稅務司署造冊處(上海),1916年,第449頁。,但也同樣鮮明地指出了“解放”的新義。在他看來,對于“女子解放”的名詞之爭,實際上是源于中國人喜歡“打筆墨官司”、“迷信名詞萬能”而輕視實際運動的惡習,那些“說‘解放’不是自動,辱沒了女子的人格”的主張,不僅妨礙女子解放的實際運動,而且“惹得大家懷疑”,導致“連口頭上也幾乎不好說了”。為此,他強調“‘解放’就是壓制的反面,也就是自由的別名”,“‘解放’重在自動,不只是被動的意思,個人主觀上有了覺悟,自己從種種束縛的、不正當的思想習慣迷信中解放出來,不受束縛,不甘壓制,要求客觀上的解放,才能收解放的圓滿效果。自動的解放,正是解放的第一義”。與戴季陶一樣,他也認為“解放”不僅是對于女子而言的,強調“近代歷史完全是解放的歷史,人民對君主貴族,奴隸對于主人,勞動者對于資本家,女子對于男子,新思想對于舊思想,新宗教對于舊宗教,一方面還正在壓制,一方面要求自由、要求解放”。因而,如其所言,“我們生在這解放時代,大家只有努力在實際的解放運動上做工夫,不要多在名詞上說空話!”[注]獨秀:《解放》,《新青年》第7卷第2號,1920年1月1日。
戴季陶、匡僧、陳獨秀這些在當時代表不同思想派別的知識分子對于“解放”觀念的厘清,既顯示這一觀念在當時的復雜性,又顯示這一觀念的重要性。正是在他們的厘清中,我們看到了五四時期知識分子對于“解放”新義的理解,建立在以下幾個面相的基礎之上:其一,“解放”是“自動”的,而非“他動”的,如對于女子解放而言,最重要的,并非外力的協助,而是自身的努力;其二,“解放”是對于“束縛”而言,只有通過脫離外在束縛的方式,才稱得上“解放”,也才能獲得“解放”之結果,即“自由”;其三,“解放”不僅是對于女子而言的,凡是一切處于被壓迫地位的個體(或某種同質性的群體),都可以行“解放運動”。從這些理解中,我們可以看到,五四時期知識分子對于個體獨立性的追求,意味著一種自主脫離一切束縛、壓迫的運動,它雖非以“解放”為目的,但是以“解放”為起點。
從“解放”的視角,而非從我們所熟知的“科學”與“民主”的視角出發,可以發現當時知識分子借由對于“解放”這一新名詞的推介,逐漸催生出了一種普遍性的、彌漫于全社會的“受縛感”。在知識分子的諸多論述中,不僅女子尋求解放,男子也尋求解放,乃至勞工、農夫、商人、學生等群體,全都希冀通過解放,走出受束縛的困境。在五四學生運動前三個月,向來對思潮變化頗為敏感的李大釗,便敏銳地覺察到這種時代氣息,認為“現在的時代是解放的時代,現代的文明是解放的文明。人民對于國家要求解放,地方對于中央要求解放,殖民地對于本國要求解放,弱小民族對于強大民族要求解放,農夫對于地主要求解放,工人對于資本家要求解放,女子對于男子要求解放,子弟對于親長要求解放。現代政治或社會里邊所起的運動,都是解放的運動!”[注]李大釗:《聯治主義與世界組織》,《新潮》第1卷第2號,1919年2月1日。
這種廣泛性的解放運動,自然與民初知識分子對于舊倫理的批判有著緊密的關系。正如陳獨秀廣為研究者所引用的《吾人最后之覺悟》一文所指出的那樣,在經歷了晚清以來的“政治的覺悟”失效之后,“倫理的覺悟”成了“最后覺悟之最后覺悟”[注]陳獨秀:《吾人最后之覺悟》,《新青年》第1卷第6號,1916年2月15日。。雖然在陳獨秀那里,“倫理的覺悟”仍指向一種現代政治的建構,但問題在于,當他將箭靶射向三綱、名教或禮教,隨后掀起的卻不是正面性的政治建構,而是新派人物對于舊倫理的普遍不滿。舊倫理標榜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等人倫關系準則,已然不再是一種和諧關系,而是一種束縛關系,構成了需要被立刻解放的對象。
除了對于舊倫理的批判之外,還有一點較少為人注意的,則在于五四時期的解放運動還兼具對于晚清以來形成的以“國家”為中心的新倫理的批判。事實上,五四時期對于舊倫理的批判,并非破天荒的舉動,比如晚清時譚嗣同的“沖決網羅”、梁啟超的“通”等觀念[注]《譚嗣同全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78頁;《梁啟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0—59頁。,也一定程度上具有“解放”的意涵。但是,這種觀念在當時仍然只是潛流,流行于晚清知識分子中間的主潮流,是以“國家”作為舊倫理的替代物,應對當時列國并立的新形勢。而到了五四時期,不僅舊倫理在掃除之列,晚清形成的“國家”新倫理也在否定之列。其中的關鍵在于,民初以來議會民主制的亂局,袁世凱強人政治后的軍閥亂局,以及一戰之后全世界掀起的對于軍國主義的批判,促使作為新倫理的“國家”也被視為一種“偶像”[注]陳獨秀:《偶像破壞論》,《新青年》第5卷第2號,1918年8月15日。關于五四時期知識分子對于晚清以來國家觀念的重新思考及其反映出的世界主義取向,可參見許紀霖編:《啟蒙的遺產與反思》,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56—284頁。,成為與舊倫理一樣需要被解放的對象。
新倫理與舊倫理的雙重解放,帶來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解脫一切束縛的時代氛圍。李大釗在一篇題為《我與世界》的隨感錄中便指出:“我們現在所要求的,是個解放自由的我,和一個人人相愛的世界。介在我與世界中間的家國、階級、族界,都是進化的阻障、生活的煩累,應該逐漸廢除。”[注]守常(李大釗):《我與世界》,《每周評論》第29號,1919年7月6日。學生輩的傅斯年也以類似的口吻指出:“我只承認大的方面有人類,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實的。‘我’和人類中間的一切階級,若家族、地方、國家等等,都是偶像。我們要為人類的緣故,培成一個‘真我’。”[注]傅斯年:《新潮之回顧與前瞻》,《新潮》第2卷第1號,1919年10月。就李大釗、傅斯年二人的論述來看,當“解放”指向新倫理和舊倫理的一切束縛時,所留下的僅僅是獨立個體,以及超越所有個體之上的“人類”和“世界”。“解放”一方面意味著個人主義時代的來臨,另一方面意味著世界主義時代的降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把握五四時期“解放”觀念的真正內涵。
二、“解放時代”的烏托邦想象
倫理革命是五四時期觀念變遷的重要思想背景,無論在廣度上還是在深度上,都有著豐富的內涵。從五四時期知識分子所要求的“解放”來看,它不僅囊括了家庭革命和女性解放的倫理革命,還涉及解除在政治、宗教層面的束縛。在政治層面,“國家”被視為一種“偶像”,晚清以來極端的國家主義被世界主義所替代。在宗教層面,隨著倫理革命的進行,以綱常倫理作為重要標志之一的儒家文化飽受批判,同時流行于晚清知識分子中的那種濃烈的佛道信仰也趨于邊緣。除去了一切束縛之后,“解放時代”最重要的標志,便如傅斯年所期待的,是“拿人生解釋人生”[注]傅斯年:《人生問題發端》,《新潮》第1卷第1號,1919年1月1日。。不帶一絲束縛的、“赤裸裸”的個人,構成了五四時期大部分“解放”論述的出發點。
對于這樣一個“解放時代”的來臨,部分知識分子樂觀地相信這正是重整人生和社會的契機。我們可以看到,在“解放”觀念興起的同時,“改造”逐漸成為五四時期的一個核心觀念。如果“解放”強調的是個人從各類束縛中解脫出來,那么“改造”則指向個人解放后的社會重建。1919年9月,張東蓀等研究系知識分子便以《解放與改造》為名創辦了一份刊物。在這份刊物的《宣言》中,面對當時全新的時代情境,張東蓀便指出:“我們當首先從事解放,就是使現在的自我完全從以前的自我解放了出來,同時使現在的世界也從以前的世界完全解放了出來”,“解放不是單純的脫除,乃是‘替補’(Complement)”,而“‘替補’就是‘改造’。所以,一方面是不斷的解放,他方面是不斷的改造”[注]張東蓀:《宣言》,《解放與改造》第1卷第1號,1919年9月1日。。除張東蓀外,周佛海亦注意到“解放”與“改造”這兩個觀念。他發現當時的言論界“關于‘解放’的議論,似乎一天多似一天了,但是關于‘改造’的議論,還是很少”。在他看來,“解放”與“改造”其實有著十分緊密的關系,“改造是解放的目的,解放是改造的手續”,“不講改造,專事解放,就是沒有目的的手續;沒有目的的手續,就是無意識的行動了”。[注]周佛海:《物質生活上改造的方針》,《解放與改造》第2卷第1號,1920年1月1日。換而言之,“解放”并非純然的破壞,在破壞的同時,要著手從事建設,而所謂的建設便是“改造”。
在《解放與改造》中引人注目的是以“寄生生活”與“共同生活”來形容“解放”與“改造”前后不同的生活形態。在該雜志第1卷第1號中,便有日本學者河上肇的《共同生活及寄生生活》一文[注]《解放與改造》雜志僅注明該文是筑山醉翁(指陳筑山——筆者注)譯,未指出原作者為何人,筆者核查《民國日報·覺悟》和《晨報》,發現這兩份報刊均登載了《共同生活和寄生生活》一文,并注明作者為河上肇,譯者則為髯客,基本內容一致,但在具體字句上略有不同。參見《晨報》1919年7月6日、1919年7月7日;《民國日報·覺悟》1919年7月10日、1919年7月11日、1919年7月12日、1919年7月13日。,認為“共同生活是大家為相互的利益共同協力來營生活”。而要是多數的人“雖然集在一個場所營生活”,但“只有一部分勤勞,其余的部分,全然不動,依他人的勤勞,靠他人的產物來生活”,則可稱之為“寄生生活”。作者以寄生蟲來作比擬,認為與協同互助的“共同生活”相比,“寄生生活”則是強抑弱、主抑奴的生活。“共同生活于增進我們相互的幸福最有利益”,而“寄生生活卻有非常的妨害”。[注]筑山醉翁譯:《共同生活及寄生生活》,《解放與改造》第1卷第1號,1919年9月1日。河上肇的這篇文章雖然未針對當時的中國狀況,但是為《解放與改造》作者群深化對“解放”與“改造”的理解提供了觀念上的助力。《共同生活及寄生生活》的譯者陳筑山也在《解放與改造》中撰文,以一種二元對立的方式列舉了“寄生生活”與“共同生活”的區別,認為“寄生生活——只圖片面的利益——是強迫關系——是主奴生活。共同生活——為相互的幸福——是契約關系——是平等生活”,強調只有從“寄生生活”中解放出來,朝著“共同生活”的方向進發,才是“社會的目的”[注]筑山醉翁:《舊社會》,《解放與改造》第1卷第1號,1919年9月1日。。另外,陳真伯以“寄生生活”來指稱舊有的家族制,認為“家族制把社會分為無數私有的小范圍,利害不一致,各不相謀的壁壘,那些社會上不健全的分子不是依賴著他強取豪奪,就是依賴著他保存寄生生活”,因而“家族制是社會共同生活的大障礙”。在看到當時風生水起的解放運動后,他直言“以后的社會,是共同生活的社會,這種社會的基礎應該建筑在能發展個性、發展社會的倫理上”。[注]陳真伯:《倫理改造論》,《解放與改造》第2卷第3號,1920年2月1日。
在關于“寄生生活”與“共同生活”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知識分子似乎已然找到了打開“解放”的真正秘鑰所在。如果說“解放”前的生活是束縛的、壓迫的、等級的、黑暗的寄生生活,那么“解放”后的生活,經歷了“改造”,則應該是自由的、互助的、平等的、光明的共同生活。這種解放后的“共同生活”最重要的特征,是附和當時“勞工神圣”的理念,試圖將社會全體轉變為勞動者,共同勞動,合作協力,以創造新的生活。張東蓀便主張在落實“解放”和“改造”觀念的時候,要首先將知識分子改造成勞動者,因為“中國的知識階級最沒有互助的道德和團結的引力”[注]東蓀:《中國知識階級的解放與改造》,《解放與改造》第1卷第3號,1919年10月1日。。李達在論述女子解放問題時,也借用了“共同生活”的觀念,認為“解放女子,并不是破壞家庭,不過使婦人加入共同生活,要她變為共同生產者的一員,完成社會的真價值”[注]李鶴鳴(李達):《女子解放論》,《解放與改造》第1卷第3號,1919年10月1日。。概而言之,在這種關于“共同生活”的信念中,個人從過去的等級性的、寄生性的職業和身份中全面解放出來,成為勞動者,共同生產,互助團結,從而形成一個新的社會共同體和新的倫理道德規范[注]在五四時期,這種“共同生活”和“勞工神圣”的理念,最直接反映在“化兵為工”的構想中。參見王鴻:《“主義之軍”的崛起——近代中國軍人形象的變遷》,《二十一世紀》2017年12月號。。
觀念的變化往往緊密聯系著當時知識分子對于現實世界的認識。五四時期知識分子對于“解放”與“改造”的這種看法,不僅是一種紙面上的構想,實則還反映了五四運動后高漲的社會改造熱潮。在《解放與改造》創辦前兩個月,匯聚了一大批青年知識分子的“少年中國學會”中的左舜生、王若愚等人便提出要以“小組織”的方式,逐步實驗新生活的構想。關于“小組織”的探討,最初緣起于1919年7月左舜生在《時事新報》上所發表的《小組織的提倡》。在他看來,當時“家庭的生活,是一種無意義的機械生活,是消磨志氣的生活,若要打起精神做個人,便不能不與他疏遠些”,但這種“疏遠”不是一蹴而就的,他主張先從志同道合的“小組織”開始建構,經過“小組織”的訓練,然后逐步進入社會的“大組織”。而所謂的“小組織”,便是“由少數同志組織的一種學術事業生活的共同集合體”[注]該文被《少年中國》轉載,參見左舜生:《小組織的提倡》,《少年中國》第1卷第2期,1919年8月15日。。對于左舜生的構想,王若愚表示十分贊同,認為這正是重建“人的生活”的契機。較之左舜生的粗略構想,王若愚還進一步就這一“小組織”如何開展提供了更為細致的分析,認為應該在鄉村租一塊菜園,在這個以菜園為中心的“小組織”中,成員們每日“種菜兩鐘”,“讀書三鐘”,“翻譯書籍三鐘”,“其余鐘點,均作為游戲閱報時間”。王若愚認為,通過這樣的“小組織”生活,不但可以滿足物質上的需求,而且可以獲得精神上的快慰。[注]若愚:《與左舜生書》,《少年中國》第1卷第2期,1919年8月15日。他們的這種構想,按照宗白華的理解,便是“脫離了舊社會的范圍,另向山林高曠的地方,組織一個真自由、真平等的團體,從合力工作,造成我們的經濟獨立與文化獨立,完全脫去舊社會的惡勢力圈”[注]宗之櫆(宗白華):《我的創造少年中國的辦法》,《少年中國》第1卷第2期,1919年8月15日。。
遺憾的是,我們并未在《少年中國》上看到“小組織”真正落實的案例。不過,在稍后由“少年中國學會”的王光祈等人所發起的、引起全國思想界普遍關注的工讀互助運動中,還是能夠發現這種“小組織”在落實過程中的具體境況[注]康白情在《少年中國》雜志中提及“小組織”的落實情況時,將“小組織”與工讀互助團聯系在一起解讀:“就說實行吧,我們也同時在進行,而且毫沒有懈怠新村的變相‘小組織’,因為時機的必要,還沒有做,不用說了。近來如北京和上海的工讀互助團,是我們所提倡的;漢口的互助社,也是我們所提倡的,還有好些脫離家庭的,我們也偶然替他們想法子。”參見《會員通訊》,《少年中國》第1卷第11期,1920年5月15日。。如果說左舜生、王若愚等人設想的“小組織”注重的是“鄉村間的新生活”,那么工讀互助運動強調的是“城市中的新生活”[注]王光祈:《城市中的新生活》,《晨報》第347號,1919年12月4日。。工讀互助運動在1920年前后的青年群體中頗為流行,北京、上海、天津、武漢、南京等地均出現了各種類型的工讀互助團。從最初發起的北京工讀互助團來看,它的理念是“本互助的精神,實行半工半讀”,從而實現“教育和職業合一的理想”。而上海的工讀互助團,則直接點明他們的目的,在于讓有志于從“舊社會”“舊家庭”中解放出來的青年,以半工半讀的方式,另外產生一種“新生活”“新組織”。至于工作種類,北京工讀互助團有石印、素菜食堂、洗衣服、制漿糊、印信箋、販賣商品及書報、裝訂書報、制墨汁及藍墨水等,而上海工讀互助團則規劃有平民飯店、洗衣店、石印、販賣商品及書報等。[注]關于工讀互助團的相關情況,參見張允侯等編:《五四時期的社團》第2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第366—496頁。工讀互助團的組織者們期待著自由組成的成員們可以每天共同工作數小時,從而形成自給自足的新生活,并且以“小團體大聯合”[注]王光祈:《工讀互助團》,《少年中國》第1卷第7期,1920年1月15日。的方式逐步改造中國社會。
對于工讀互助團,學界已有豐富的研究[注]較早的研究參見郭笙編著:《“五四”時期的工讀運動和工讀思潮》,教育科學出版社,1986年,第44—58頁。新近的研究參見李培艷:《“新青年”的“新生活”實踐——以工讀互助團為中心的考察》,《文藝理論與批評》2018年第5期;趙妍杰:《試驗新生活——“五四”后北京工讀互助團的家庭革命》,《北京社會科學》2018年第8期;等等。,而從本文的視角看來,它恰恰反映了解放后的個人試圖進行社會改造的努力。《北京大學學生周刊》便從積極和消極兩方面,各羅列了工讀互助團的七項好處。從消極方面,它可以與家庭完全脫離經濟的關系,打破個人的依賴性、懶惰性,打破知識界與勞工界之間的尊卑關系,打破重學理教育而輕生活教育之趨勢,打破役人、治人之惡習,打破一切知識界、道德界不平等之觀念,打破舊日階級制度之社會。從積極方面來看,它可以得生活上完全之獨立,養成個人的獨立性、勤勞性,養成勤工之道德,養成生活上必須之知識技能,養成共同生活之習慣,養成真正平等互助之道德觀念,造成真正之平民社會[注]吳康:《介紹“工讀互助團”》,《北京大學學生周刊》第2號,1920年1月11日。。概而言之,一方面,這種工讀互助團試圖打破舊有的制度和觀念;另一方面,它又強調要重建一套新的生活方式和價值理念。若是以當時流行的“解放”與“改造”兩觀念來看,工讀互助團恰恰想要實現的是它們的有機結合。“解放”正上路,“改造”亦隨行,工讀互助團似乎為那些試圖從舊社會、舊家庭、舊信仰以及一切舊制度中解放出來的個人,提供了一種可資庇護的新生活。
然而,這種樂觀沒有持續多久,最初發起的北京工讀互助團在實行了兩三個月后就傳來解散消息,而其他互助團也都難逃陸續解散的命運。工讀互助團的失敗,是1920年前后的重要思想事件,包括《新青年》《解放與改造》《星期評論》《時事新報》等不同思想派別的刊物均對此作出了細致檢討。以當時《新青年》的一組關于工讀互助團的文章來看,失敗的原因顯然是多種多樣的:胡適認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當時的工讀互助團只注重“工”,而忽視了“學”[注]胡適:《工讀主義試行的觀察》,《新青年》第7卷第5號,1920年4月1日。;王光祈則認為原因“完全是人的問題,而非經濟的問題”,“就是不善經營、不善計算、不善辦理,別無他故”[注]王光祈:《為什么不能實行工讀互助主義?》,《新青年》第7卷第5號,1920年4月1日。。而在這些細致的檢討外,逐漸有一種聲音越來越有力,那就是認為工讀互助團的失敗,實際上反映了那種試圖通過局部改造社會的設想的失敗,真正的關鍵在于能否對社會進行根本性改造。戴季陶在《新青年》中便認為工讀互助團雖然只是一個普通的理想,但是要實現這個理想,“只有對著全社會的改造事業上去作工夫”[注]季陶:《工讀互助團與資本家的生產制》,《新青年》第7卷第5號,1920年4月1日。。而當時作為北京工讀互助團成員的施存統,在《星期評論》中則撰文指出,這一次的工讀互助團試驗帶來了兩大教訓:“一,要改造社會,必須根本上謀全體的改造,枝枝節節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二,社會沒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試驗新生活,不論工讀互助團和新村。”[注]存統:《“工讀互助團”的實驗和教訓》,《星期評論》第48號,1920年5月1日。
對于戴季陶、施存統這種尋求全面改造的思想傾向,當然可以作出多種解讀,但它毫無疑問地反映了掩蓋在“解放時代”知識分子短暫樂觀取向下的悲觀姿態。它證實了從各類束縛中解放出來的個體試圖以自由結合的方式改造社會的失效。關鍵的問題不在于工讀互助團的愿景之美好,而在于當時中國社會問題之復雜。它雖然短暫地饜足了解放青年尋求新倫理、新組織的需求,但它無法根除深植于解放背后的諸多社會問題。戴季陶便認為之所以要進行根本性改革,是因為工讀互助團所反映出的“時間問題、工銀問題、幼年保護問題、女子保護問題、社會的保險、勞動者住宅、教育、娛樂、慰安這些問題”無法依靠工讀互助的方式獲得解決[注]季陶:《工讀互助團與資本家的生產制》,《新青年》第7卷第5號,1920年4月1日。。而在施存統的文章中,我們也可以發現在工讀互助團的實踐過程中,有兩大問題始終困擾著他們:其一是經濟問題;其二是思想問題。前者指向社會上的財產私有制;后者則指向團員間的“感情隔閡和精神渙散”[注]存統:《“工讀互助團”的實驗和教訓》,《星期評論》第48號,1920年5月1日。。不根本解決這些問題,社會改造無法繼續,而解放的個體亦無處安身。
事實上,到底是以局部性改造的方式逐漸解決社會問題,還是以根本性改造的方式全面解決社會問題,正是稍早前胡適和李大釗在《每周評論》中關于“問題和主義”論戰的核心議題。二人都不否認當時的社會問題繁雜,但胡適從他的實驗主義立場出發,并不相信那種包治百病的“根本解決”做法[注]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每周評論》第31號,1919年7月21日。;而李大釗則反對那種枝枝節節的改造社會的方式,認為“要想使一個社會問題成了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問題,應該使這社會上可以共同解決這個那個社會問題的多數人,先有一個共同趨向的理想、主義”[注]李大釗:《再論問題與主義》,《每周評論》第35號,1919年8月17日。關于“問題與主義”論戰的相關情況,參見許紀霖編:《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論》上卷,東方出版中心,2006年,第296—303頁。。二人的爭論隨著《每周評論》被查封戛然而止,然而其中所反映的思想趨向持續延續著。如果“小組織”、工讀互助團無法由點及面,通過自由個體的結合實現社會改造,那么對于“解放”與“改造”的理解顯然有必要進行重新調整。這當然不意味著五四時期的個人解放在價值上的隕落,而是意味著對于個人解放的理念有了更為深入的理解。關鍵性的問題在于,如果通過工讀互助團這樣以自由個體的結合而形成的團體,無法建立“解放”后的新共同體,那么真正的、徹底的改造方案在哪里?正是在這一問題上,我們實有必要轉向五四時期知識分子對于“解放”的另一種理解。
三、另一種“解放”
五四時期最曼妙的神話之一,或許在于認為個體從家庭、國家等各類束縛中解放出來后,可以急速進入一個自由平等的共同體。面對著各種類型的束縛,如果說個人解放是無可避免的時代議題,那么如何從個人解放走向社會改造,從而重新建構一套新倫理,則是這個過程中必然需要面對的問題。當時的知識分子顯然意識到這一問題,但他們所主張的替代性方案是幼稚的,充斥著烏托邦色彩。這種片刻的樂觀,無法掩蓋彌漫整個“解放時代”的悲觀氛圍。對于五四時期,過去似乎都過于強調新與舊在對決過程中的樂觀氣息,卻較少注意到這個“解放時代”的種種悲觀氣息。“解放時代”的悲觀,當然仍包含著晚清以來對于外患頻仍的無奈,但也有對于個人解放后倫理喪失、信仰無著和生活無可憑借的控訴。
“解放時代”的悲觀,首先便在于“解放”觀念在誘發人們對于傳統家國倫理的不滿后,出現了一種人生觀上的彷徨。在洋溢著樂觀的社會改造言論的同時,羅家倫面對當時青年的自殺問題,便發現“‘五四’以后,我們青年的人生觀上發生一種大大的覺悟,就是把以前的偶像一律打破,事事發生一種懷疑的心理。在中國這樣的社會里,自然東望也不是,西望也不是。舊的人生觀既然打破了,新的人生觀還沒有確立,學問又沒有適當的人來作指導,于是消極的就流于自殺”[注]志希(羅家倫):《是青年自殺還是社會殺青年?》,《新潮》第2卷第2號,1919年12月。。瞿秋白對于這一問題,也形象地說道:“大凡一個舊社會用他的無上威權——宗教、制度、習慣、風俗……造成了精神上、身體上的牢獄,把一切都錮閉住了,當時的人絕不覺得不自由的痛苦,倒也忘其所以,悠游自在。一旦這個牢獄破壞了,牢獄的墻上開了一個洞,在里面的人可以看得見外面,他心里就起了一種羨慕的心,頓時覺得自己處的地位沒有一處是適意的、合理的。可是他又不能出去,心是在外面,身體是在里面,那真一刻多不能容忍,簡直是手足無所措了。”[注]瞿秋白:《林德揚君為什么要自殺呢?》,《晨報》第346號,1919年12月3日。可以說,像“個人解放”這樣的新思潮日益流行,讓樂觀推介“解放”和“改造”觀念的張東蓀,也警覺到它只是促使“一班青年由昏沉的生活而到了煩悶的生活”。若從正面而言,這是一個“解放時代”;而若是從負面而言,則是一個“青年的煩悶時代”[注]東蓀:《青年之煩悶》,《解放與改造》第1卷第8號,1919年12月15日。。
除了人生觀上的彷徨外,“解放時代”的另一種悲觀,則是由于生活上經濟問題的頻發。如果說人生觀的彷徨是一種精神上的煩悶,那么經濟問題的頻發則可謂物質上的困頓。1920年初,周佛海便撰文指出,“改造的事業,要包括精神和物質兩方面的。單在物質上改造,是不徹底的改造;單在精神上改造,是不著實的改造。所以要徹底和著實的改造,于精神和物質兩方面中,就不能丟開那一面了”,而所謂“物質上的改造”,便是“經濟生活的問題”[注]周佛海:《物質生活上改造的方針》,《解放與改造》第2卷第1號,1920年1月1日;周佛海:《精神生活的改造》,《解放與改造》第2卷第7號,1920年4月1日。。張東蓀稍早前亦強調“中國的普遍生活困難雖則有種種的原因,但我敢說可以大概分為兩種,就是物質方面的原因和精神方面的原因”。如果說精神方面的困難,是由于“舊日制約的道德完全破壞”,那么物質方面的困難,則是來自“西方物質文明的壓迫”,“若詳細說起,生產機關因為機器的發明與外貨的輸入,幾乎驅逐干凈。生產機關愈少,自然是貧困了”。[注]東蓀:《我們為什么要講社會主義?》,《解放與改造》第1卷第7號,1919年12月1日。而經濟上的困境,除了所謂“西方物質文明的壓迫”外,對于解放的個體而言,更重要的,是脫離家庭后生活的無可援助。在《星期評論》上開展的一場由胡適、胡漢民、廖仲愷、戴季陶等人參與的關于“女子解放從哪里做起?”的討論中,便在強調女子解放需要有精神上的覺悟外,發現脫離家庭后的經濟獨立,亦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是更難實現的一環[注]胡適等:《女子解放從哪里做起?》,《星期評論》第8號(1919年7月27日)、第9號(1919年8月3日)。。
人生問題與經濟問題的交雜,精神問題與物質問題的混合,表明“解放時代”并不是一個前途光明的時代,而是一個問題重重的時代。諸如“小組織”、工讀互助團等烏托邦方案的失敗,毫無疑問地顯示了解決這些問題的艱難性。在片刻的樂觀過后,如何回應“解放時代”的這些困境,構成了五四時期知識分子不可回避的問題。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五四學生運動后的幾次思潮變動,都在某種程度上試圖回應“解放時代”的這些問題。其一是關于東方文化和基督教問題的探討,特別是由此所引發的關于信仰問題的爭議。《少年中國》上曾分三次組織了“宗教問題號”[注]見于《少年中國》第2卷第8期(1921年2月15日)、第2卷第11期(1921年5月15日)、第3卷第1期(1921年8月1日)。,梁漱溟、屠孝實、王星拱、周太玄、李石曾、惲代英等人都對宗教信仰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雖然這些人看法不一,但正如周太玄所指出的,青年“由苦悶的生涯中逃到神前去”是當時的一個普遍社會現象[注]周太玄:《宗教與中國之將來》,《少年中國》第3卷第1期,1921年8月1日。。其二是1923年的科學與人生觀論戰。在這場思想論戰中,雖然科學派和玄學派在關于“科學”是否可以作為一種人生觀的問題上爭議不休,但也毫無疑問地凸顯了當時的人生觀已然處于一種不確定的狀況,亟待重建[注]參見胡適編著:《科學與人生觀》,上海亞東圖書館,1923年。。其三則是國家主義的復歸。過去被視為束縛個人解放的“國家”觀念,重新被搬上臺面,以改頭換面的方式,成為解決時代問題的藥方。五四時期“個人解放”觀念背后的人道主義和世界主義被推翻,醒獅派的陳啟天便直言“中國今日之急務,不在大吹大擂所謂世界主義與人道主義,而在使中國如何成為世界上之一國,可與列強同等,然后有進于世界主義之可能,又如何使中國人成為世界之人,可與西人同等,然后有進于人道主義之可能”[注]陳啟天:《新國家主義與中國前途》,《少年中國》第4卷第9期,1924年1月。至于當時國家主義的諸多論調,可參見《醒獅》雜志和《孤軍》雜志。。
不過,在這些思想方案之外,真正完整回應“解放時代”的諸多困境,并進一步深化對“解放”的理解的,是當時標榜“階級解放”和“民族解放”的社會主義思潮。經歷了短暫的工讀互助生活之后的施存統,在《新青年》上發表了《第四階級解放呢?全人類解放呢?》一文。他否定那種籠統講全世界解放、全人類解放的說法,認為“籠籠統統講全人類解放,乃正是全人類解放的罪人。真正熱心全人類解放的人,應該努力促第四階級覺悟,使第四階級來擔任這全人類解放的大事業”。所謂“第四階級解放”指的便是“一切被壓制階級”從奴隸境遇中解放出來。具體言之,“一切窮人、勞動者、佃戶、被使役者、被壓制者、被掠奪者,都要有‘階級的自覺’,覺悟自己是一個階級,彼此利害完全相同,應該聯合成一個團體,以與富人、資本家、地主、使役者、壓制者、掠奪者——強盜階級作戰。而那些不屬這兩階級的中間階級,也應該加入一方面去,絕不該彷徨中立”。[注]存統:《第四階級解放呢?全人類解放呢?》,《新青年》第9卷第5號,1921年9月1日。如果說過去的“個人解放”側重于個人主動從一切束縛中解脫出來,那么現在的“階級解放”強調的則是無產者、被壓迫者作為一個群體合力從束縛中解脫出來。“解放”的力量,不再是孤立的,而是遍布的;“解放”的目標,也不再是分散的,而是明確的。施存統的“第四階級解放”,在隨后的歷史文獻中逐漸固定化為“無產階級解放”的用語[注]關于“第四階級”與“無產階級”等階級觀念的關系,參見蔣凌楠:《“第三階級”與“第四階級”在中國——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四階級話語》,《蘇區研究》2017年第3期。,而它所反映出的那種尋求被壓迫階級聯合起來進行解放運動的思想趨向也一直延續下去。
在“階級解放”外,另一種相伴而生的“解放”觀念,則是“民族解放”。“民族解放”觀念,一方面是“階級解放”觀念的合理延伸,另一方面則與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廣為援引的列寧“帝國主義論”及其對殖民地問題的看法緊密相關。在列寧的論述中,無產階級解放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東方)的民族解放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構成了從一切壓迫中解放出來的重要觀念利器。按照他的判斷,當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形式而變成帝國主義后,人類世界便發生帝國主義和殖民地民族之間明顯的對壘。如果說無產階級、被壓迫者要解放他們自己,就要打倒資產階級、壓迫者,那么殖民地的弱小民族要解放他們自己,就必須打倒作為資本主義最高形式的帝國主義。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與階級解放運動理應相互配合,指向各種類型的經濟壓迫、思想束縛,合力摧毀帝國主義及與之相互配合的力量(如軍閥勢力)。[注]列寧的論述,可見《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關于中共革命中的“帝國主義”觀念的新近研究,參見畢玉華:《建構與調適:中共革命意識形態中的“帝國主義”概念》,《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5期。
在20世紀20年代初,我們可以看到這種“階級解放”和“民族解放”及與之相關的打倒帝國主義與軍閥的口號廣泛出現在諸多的歷史文獻中,與稍早前強調“個人解放”的時代氛圍形成了鮮明對比[注]較為顯著的例子是中共中央機關報《向導》中的一些文章在文末往往都會有“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解放萬歲!全世界被壓迫的階級解放萬歲!”之類的標語。。如果說五四時期的“個人解放”強調的是無差別的個人從一切束縛中解脫出來,那么“階級解放”和“民族解放”則將“解放”的視野鮮明指向被壓迫階級和被壓迫民族。這種“階級解放”和“民族解放”的觀念有別于五四時期的“個人解放”觀念,卻正是它們為解釋和解決“解放時代”的諸多困境,提供了一種在當時被認為切實可行的方案。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面向革命青年群體、并有著較大影響力的《中國青年》雜志中[注]《中國青年》由惲代英、蕭楚女等人主編,是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機關刊物。,這套全新的“解放”理念正在逐漸成為解釋和解決“解放時代”青年精神困境和物質生活困難的良方。在該刊上登載的《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大會宣言》便指出:“中國的青年、工人、農民、學生、女子,處于這種列強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之下,非努力奮斗,與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同起民族革命,尤其非輔助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根本鏟除資本主義,不能得到徹底的解放。”[注]《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大會宣言》,《中國青年》第69期,1925年3月7日。換而言之,所謂“徹底的解放”,包含著兩個不可分割的方面:一方面是謀求結合“中國的青年、工人、農民、學生、女子”等被壓迫群體的階級聯合和階級解放,另一方面則是將這種階級的解放與世界范圍內的弱小民族的解放進行結合。它否定了過去那種單兵作戰式的個人解放,也指明了個人解放能否徹底完成的關鍵,在于被壓迫階級的解放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弱小民族的解放能否成功。
在《中國青年》中,這種全新的“解放”理念首先表現在對五四時期風行的女子解放運動的批判。惲代英便批判五四運動以來的女子解放運動,認為它不過是“造就了幾個出風頭的新女子,幾對享樂主義的戀愛婚姻”。在他看來,“只有全體的解放,沒有個人的解放”,一方面“不打破現在的家庭,婦女永遠是不能免于為家事奴隸的”,另一方面“不打破現在社會的經濟制度,婦女永遠是不能到獨立自由的地位的”。[注]惲代英:《婦女運動》,《中國青年》第69期,1925年3月7日。除惲代英外,有論者也發現過去的女子解放運動,只注重女子從家庭中解放出來,不過是使女子“從家庭奴隸變成為工錢勞動奴隸”,重要的應該是將女子解放運動與勞工等一切被壓迫階級的解放運動聯合起來,因為“徹底的解放,只有協同勞動者共同推翻現在的經濟組織,以創造平等自由的社會,這平等自由的社會,也只有勞動者得了解放之后,才有創造的可能”[注]一知:《婦女解放與勞工解放》,《中國青年》第67期,1925年2月21日。。中國女子的“完全解放”,按照《中國婦女運動的歷史的發展》一文的說法,其實完全是有賴于能否“與全世界被壓迫者攜手”,從而打破壓迫全世界的“整個的經濟制度”[注]純一:《中國婦女運動的歷史的發展》,《中國青年》第155期,1927年2月19日。。
除女子解放運動外,對于青年群體普遍性的經濟困境,現在也有了全新的理解視角和解決方案。當時知識青年在面對因失業而導致的經濟困難時,劉仁靜提醒他們有必要將個人失業與整個被壓迫階級的境遇結合起來,認為“中國知識者的失業,是一階級的問題,并非一個人的偶然的事。所以我們必須聯合全階級和全中國人民的力量來解決他,掃除剝削我們的衣食、妨害我們的生產的障礙物——軍閥與帝國主義”[注]仁靜:《告天津的學生》,《中國青年》第102期,1925年11月20日。。而惲代英在回答讀者關于生活和學習的經濟難題時,也將矛頭指向帝國主義,認為“青年欲求學而不能求學,欲謀生而無處謀生,這是帝國主義壓迫下之中國社會經濟所造成,我們除了根本改正中國社會經濟狀況,是無法救濟這般青年的”[注]綱樞、惲代英:《想到民間去者的生活問題》,《中國青年》第112期,1926年1月31日。。這當然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正如惲代英指出的,如果過去那種試圖“脫離這樣的生活,而另創一個獨立的生活”的烏托邦方案已經失敗,那么“要救自己,只有先打倒外資的壓迫”,“除了革命是沒有法子完全解決這個問題的”[注]代英:《生活、知識與革命》,《中國青年》第57期,1924年12月13日。。
事實上,這種解放方案,不僅可以解決受帝國主義支配的不平等的經濟問題,而且被當時的革命青年視為解決個人解放后信仰失落和精神煩悶的良方。任弼時便直接指出:“無產階級革命不僅只是奪取政權、人類物質上得著解放而已,他還須掃除舊社會所遺留的一切思想道德,還須求人類精神上的根本解放。”[注]辟世(任弼時):《蘇俄與青年 》,《中國青年》第52期,1924年11月8日。不過,在這種“精神上的根本解放”進行的道路上,劉仁靜發現當時的各種思想,“如老莊的虛無主義、孔教的折衷主義、佛教的寂靜主義,都是勾結著西洋類似的學說在那里復活,都是在那里爭奪青年的靈魂”。因而,在他看來,“青年的解放除了為改善自己的生活奮斗而外,還要克服自己的主觀上、心理上所受的成見與障礙”。[注]敬云(劉仁靜):《青年運動與革命運動》,《中國青年》第6期,1923年11月24日。劉仁靜并沒有對于如何克服這種“主觀上、心理上所受的成見與障礙”作出自己的解讀,但在后來《中國青年》的相關文章中,我們還是能夠看出真正的解決方案所在。在一篇題為《怎樣打破灰色的人生》的通訊中,一位青年讀者坦言他當時面臨著無法疏解的煩悶:“每每想到我的前途,好像一只小船在大洋里漂泊,不知將來作何歸宿?由愁而怨,由怨而恨,有時一人默思半天,恨不得拿手槍結果性命,以求一個干凈。”對于這位讀者的精神困境,惲代英對他說:“你要不愿居這悲苦之境,不是去幻想那不可能的自殺,是要去設法應付他,去做一個改革社會國家與打倒帝國主義的人。而且我相信你須得交結一些比較勇敢的朋友,與他們結伴前進。”[注]淮陰兒、惲代英:《怎樣打破灰色的人生?》,《中國青年》第79號,1925年5月9日。惲代英的解答實際上并非僅僅針對這位讀者,他在稍早前《煩悶的救濟》一文中便發現這是一個群體性現象,認為“或者是因為沒有錢讀書升學,或者是因為沒有機會得著適當的配偶,或者是因為學校與家庭的生活太難滿意,他們便感覺著人生的悲哀苦痛,找不著一條出路。有些青年因此養成他的悲觀的哲學,有時甚至因此發狂,或者要企圖自殺以求超離這種煩悶的命運”。在他看來,解決這種困境,無法靠個人孤立奮斗,只有加入革命隊伍,“打倒帝國主義與軍閥”,從而“根本割除中國貧乏的原因”,才能“求順遂滿足的愉快感情”。[注]但一(惲代英):《煩悶的救濟》,《中國青年》第73號,1925年4月4日。
《中國青年》在當時相當具有代表性地反映了革命青年在新的歷史形勢下對于經濟困難和思想困境的新認識。對于《中國青年》中所廣泛呈現的這種新的思想進路,王汎森曾獨到地指出,這反映了一個全新的“主義時代”的來臨[注]王汎森:《“主義時代”的來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一個關鍵發展》,許紀霖、劉擎主編:《中國啟蒙的自覺與焦慮》,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29—201頁;王汎森:《“煩悶”的本質是什么——“主義”與中國近代私人領域的政治化》,許紀霖、劉擎主編:《新天下主義在當代世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63—304頁。。不過,若是我們不把五四時期的思想運動分作兩橛來看待的話,其實它也反映了從五四運動以來知識分子對于“解放”的理念和運動有了進一步的理解。如果說“個人解放”帶來了一種烏托邦式的解放方案,那么“階級解放”和“民族解放”則帶來了一種另類的解放方案。在這種解放方案中,整體的、團結的被壓迫階級解放取代了過去那種分散的個人解放,而被壓迫階級的解放運動又與世界性的打倒帝國主義運動相聯結。在某種程度上,它一方面繼承了五四時期對于個人解放的承諾,另一方面也延續了五四時期個人解放的世界主義情結,只不過現在都以全新的方式呈現。可以說,被壓迫階級聯合的“階級解放”和“民族解放”的理念,提供了一種解決“解放時代”人生問題和經濟問題的整全性方案,成為理解那個時代觀念變化的不可或缺的面相。
四、余 論
呈現在五四時期思想界中的“解放”觀念及其所反映的歷史變化,不是中國獨有的現象,而是一個普遍的世界性現象。概念史學家科塞雷克在考察歐洲的概念變遷時,便追溯了“解放”(Emancipation)概念發端于中世紀、盛行于啟蒙時代、遍布于現代世界的歷史過程[注]Reinhart Koselleck,“The Limits of Emancipation: A Conceptual-Historical Sketch”,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l History:Timing History,Spacing Concept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248-264.。不過,與歐洲的解放主要是從上帝、專制政治中解放出來的宗教革命和政治革命不同,五四時期中國的解放,主要是一種倫理革命,帶來了一種個體從家國的束縛中全面脫離出來的思想和運動。這種“解放”觀念在帶來短暫的烏托邦想象的同時,個人精神的迷茫和經濟生活的困頓隨之而來,亟須一套整全性的解決方案,解決“解放”觀念落地生根的問題。正是在這個時刻,一套以“階級解放”和“民族解放”為中心的“解放”觀念進入中國,替代了“個人解放”的烏托邦方案,主導了此后“解放”觀念的內涵。
當然,這種全新的“解放”觀念,除內在的思想史脈絡外,也與五四時期中國嚴峻的歷史形勢不可分割。特別是與“階級解放”和“民族解放”相連的打倒軍閥和帝國主義的時代任務,更是反映了這種“解放”觀念的興起離不開內憂外患的歷史形勢。不過,這并不意味著作為啟蒙的“個人解放”與作為革命的“階級解放”和“民族解放”之間是截然對立的,或者說,并不像一些研究者所強調的那樣,在新的歷史時勢面前,后者壓倒了前者[注]對于這種觀點,胡適的看法具有代表性。他曾對五四時期的思想狀況做過一個判斷,認為大致以1923年為界,此前是“個人的解放”時代,此后則是“集團主義(Collectivism)”時代。參見《胡適日記全編》第6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57頁。相關研究,可參見Vera Schwarcz: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李澤厚:《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五四”回想之一》,《走向未來》第1期,1986年,第18—40頁。。事實上,五四時期的“解放”觀念誘發了一個中國前所未有的“解放時代”:個人如何面對一個解放后的全面脫離了束縛的社會?在這樣一個“解放時代”,是否有可能通過個體的自由結合形成新的共同體?如果不能的話,那么真正的解決方案在哪里?這些問題,不僅是啟蒙時代的困境,也是革命時代的難題,持續考驗著歷史的局中人,構成了中國近百年持續轉型下的普遍性問題,即使在當下的社會情境中,也仍然有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