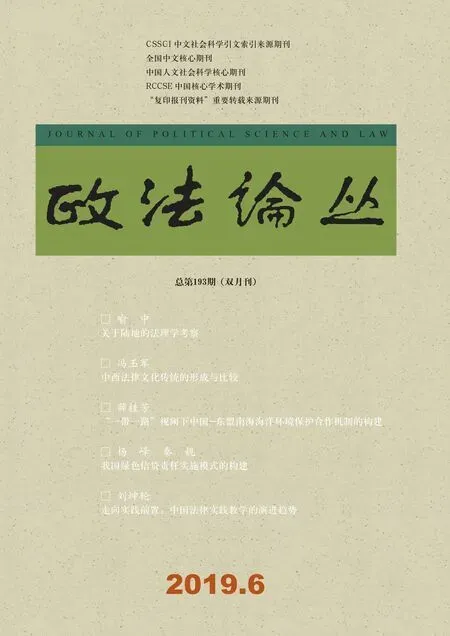關于陸地的法理學考察
喻 中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北京 102249)
一、“人是一種陸地動物”
當代作家余華創作的小說《活著》影響很大,至少有韓文版、日本版、英文版。改編成同名電影,葛優主演的,也很精彩。這部小說洋洋灑灑十余萬字,最后一個自然段是:“我知道黃昏正在轉瞬即逝,黑夜從天而降了。我看到廣闊的土地袒露著結實的胸膛,那是召喚的姿態,就像女人召喚著他們的兒女,土地召喚著黑夜來臨。”[1]P201土地與黑夜,是余華為他的這篇小說劃上的句號,標志著一個漫長敘事的最后定格。但是,在土地與黑夜之間,土地在主動地召喚,黑夜居于被動地位,因而土地更加重要。再說,黑夜跟它的前奏黃昏、尾聲黎明一樣,都不具有恒久性,很快都將消逝。唯有土地,雖然無言,卻總是袒露著胸膛一直在召喚。那召喚的姿態,是讓無數中國人為之動容的姿態。
還有詩人氣勢磅礴的吟詠:“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2]P120在這句詩詞里,讓無數英雄如此傾慕、為之折腰的“江山”,只不過是關于土地的另一種修辭而已——無論是“江”還是“山”,其實都是土地。土地素面朝天,土里土氣。江山是經過精心修飾的土地,它的泥土氣息被遮掩起來,所以“如此多嬌”,所以“無數英雄”為之“折腰”。這就是土地與江山的差異。
土地或“江山”的召喚,與法理學的召喚交織在一起,把我們引向關于土地、陸地與大地的法理學。關于陸地的法理學思考,同時也是關于土地、大地的法理學思考。至于陸地、土地、大地的關系,則是一個需要略加辨析的話題。筆者也沒有完全想好。大致說來,陸地是一個標準的地理概念,與陸地相并列的概念是海洋。內陸河流、內陸湖泊雖然也有水面,但它們屬于陸地,是陸地上的水面。相比之下,土地是一個法律概念,土地可以被占有、轉讓、征收、征用、出租、繼承,甚至還可以被奪取,因而,土地是法律關系中的一個客體。至于土地法,則是一個固定的法律術語。在早期中國,一度還盛行通過分封土地以建立諸侯國的理論與實踐,這就是說,土地可以被分封,譬如晉國的由來,就是周成王“桐葉封弟”的結果。[3]P240史籍中記載的“桐葉封弟”雖然有很強的戲劇性、娛樂性,但“封土建國”畢竟是它的核心信息。從理論上說,土地的范圍可以覆蓋所有的陸地。在土地這個大概念之下,可以有耕地,也可以有林地,還可以是山地,等等。至于大地,則是一個與天空相對應的概念,它帶有一些文藝色彩。譬如,川端康成有一部代表作叫《雪國》,此書開篇就告訴讀者:“穿過縣境上長長的隧道,便是雪國。夜空下,大地一片瑩白。”[4]P3據說,這一句已經成為日本文學中的名句,被認為是典型的“新感覺派”的文學手法。雖然是文藝理論的外行,我也無端地覺得,這個意境很美:火車駛出隧道,盡管是一片夜色,但白雪覆蓋大地,令人頓生豁亮潔白之感。這里的大地,就是跟天空(夜空即夜里的天空)相對應的。當然,如果不那么“文藝”,如果一定要坐實,大地似乎可以理解為地球表面,當然側重于地球表面的陸地部分——我們總不能把海洋也稱為大地。這就是我對陸地、土地、大地的一些理解。
必須承認,這些關于陸地、土地、大地的區分是大致的,中間還有一些模糊地帶或過渡地帶。譬如,海洋一般不能被占有,但是,臨海的國家對于周邊一定范圍內的海域,可以擁有某些專屬性的權利,這種權利已經得到國際法的承認。南極、北極是陸地,但這些地區至今尚未被占有,也不能被轉讓,至于很多年以后是否會被占有,則另當別論。
在當代中國的法學研究中,特別是在民商經濟法學領域,當然也包括憲法學、行政法學、法律史學等領域,關于土地的研究,已經積累了比較豐碩的學術成果。但是,關于陸地、土地及大地的法理學研究,卻是一個有待于進一步深化的學術主題。從法理學的角度思考陸地或土地,既是拓展法學研究的需要,也是對人的生存狀況,甚至是對人的本性的一種察看。
人的生存狀況是什么?人的本性又是什么?讓我們做一個簡單的對照:對于鯨來說,海洋是最真實的生存狀況。但是,在人的記憶里,陸地、土地、大地才是最古老、最真實的生存狀況。在人的記憶里,雖然有很多關于海洋的神話傳說,譬如,西方有海神的故事,中土有龍王的故事,等等。但是,人的歷史畢竟是從陸地開始書寫的,文明也主要源出于陸地——哪怕是島嶼上的文明也是陸地上的文明,換個角度來說,無論多大的洲相對于海洋的面積來說,都是一個島嶼。正如卡爾·施米特在《陸地與海洋》一書的開篇所言:“人是一種陸地動物,一種腳踩陸地的動物。他在堅實的陸地上駐足,行走,運動。那是他的立足點和根基;他由此獲得了自己的視野;這也決定了他觀察世界的印象和方式。作為一種在土地上誕生并在土地上運動的生物,他不僅因此獲得了自己的視野,而且也由此獲得了行走和運動的各種方式。因此,他將他生存于其上的這個星體稱為‘地球’,盡管存在著這樣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即這個星球表面幾乎四分之三的范圍被水覆蓋著,只有四分之一是陸地。而且,即使是最大的洲也不過像是一個浮動的島嶼罷了。”[5]P1
施米特還為人的這種陸地性生存找到了神學上的依據:“根據圣經的說法,上帝把陸地分配給人作為居所,而把海洋置于這個居所的邊界,作為人類的永恒的危險和威脅在那邊窺伺著。上帝的善良遏止住了海洋,使它無法吞沒我們,像那場大洪水一樣。海洋對于人類而言是陌生的,充滿敵意的。它并非人類的生存空間。依據圣經,人類的生存空間只是堅實的陸地。”[5]P102-103這樣的論證,無論是否反映了施米特自己的主張,至少,這種論證本身是在闡明人的陸地性。
在中西學術史上,曾經有過各種各樣的關于“人是某種動物”的說法。譬如,人是政治的動物,人是經濟的動物,人是文化的動物,人是符號的動物,諸如此類的學說,都各有其理據。但是,施米特的這段話卻揭示了人的地理本性:人是陸地的動物。由于人是哺乳動物,沒有鰓,不能在水下進行常態化的生存,因此,站在陸地上是人的基本生存狀態。這是一個決定性的約束條件,它決定了許許多多的問題,包括提問的方式,包括問題的答案。像施米特刻意舉出的例子:人習慣于以“地球”稱呼我們寄居的這顆星球,只是其中之一。在這顆星球上,海洋面積是陸地面積的數倍,人為什么不以“海球”稱呼我們這顆星球呢?只是因為,我們腳下踩著的是陸地。
由人的這種陸地動物的性質出發,我們可以看到一種陸地性質的法理思維。這是人類歷史上的一種根深蒂固的法理思維,既見于中土,也見于中土之外。在下面的討論中,我們首先著眼于中國固有的觀念,然后把目光轉向異域的相關理論。希望通過不斷變換的視角,揭示出陸地可能蘊含的法理意蘊。
二、“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先說《尚書》。在中國固有的五經中,《尚書》與政治學、法理學的關系最為密切。據說當年孔子教學生,一本詩經,一本書經。詩經相當于人文學科。書經相當于社會科學,主要是政治學與法理學。書經就是《尚書》,“尚書”的意思是上古時代的書。《尚書》其實是上古時代圣君賢相的言行記錄之匯編,其中的很多內容相當于現在的領導人講話。在《尚書》各篇中,直接講地理的是《禹貢》。20世紀30年代,中國還有一個學術團體叫禹貢學會,由顧頡剛牽頭,主要研究中國歷代地理沿革,研究歷代正史中的《地理志》,等等。他們還編輯了一個《禹貢》雜志。為什么這個研究歷史地理的學術團體要取名禹貢學會?因為《禹貢》是《尚書》中的地理學文獻。從法律地理學的角度來看,它也是一篇法律地理學的文獻。當然,說它是政治地理學文獻也是可以的。
《禹貢》主要記載大禹勘定華夏大地的事跡,試看其開篇:“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根據近代學者曾運乾(1884-1945)的解釋:“敷,分也,《書序》云‘禹別九州’也。隨山刊木者,鄭云:‘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為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奠,定也,正也。”[6]P41禹經過這樣一番艱難的勞作,“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禹終于大功告成,《禹貢》也至此結束。這就是《禹貢》所描繪的地理空間:“訖于四海”,亦即四海之內。其實,“訖于四海”或“四海之內”只是一個修辭,嚴格說來,只有東邊才至大海,西邊是到流沙,具體地說,是“自蔥嶺以東諸流沙之地皆禹功德所覆也”。[6]P72禹的功德所及之處,就是華夏文明的范圍,這個范圍,就是四海之內。
只有四海之內的這一片陸地,才是文明所及之處,同時也是政治所及之處,當然也是教化所及之處。四海之內才是政治、教化、文明的舞臺,一切政治、教化、文明都發生在陸地上。《論語·公冶長》記載了一個小小的典故:“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7]P51對于仲由來說,最關心的事情是孔夫子對他的認可,但是,對于法律地理學來說,我特別看重“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這句話。這是一個假定,意思是,如果我秉持的道在這片陸地上得不到推行,我只好乘著竹木筏子飄到海外去。由此可以看出,海上或海外作為一個政治空間,已經不在現實的政治法律的管轄之內,它是一個人出世之后的歸處。
另據《國語·越語下》,范蠡協助越王打敗了吳王,“反至五湖,范蠡辭于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越國矣。’王曰:‘不谷疑子之所謂者何也?’對曰:‘臣聞之,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于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為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終極。”[8]P442《越語下》至此結束,整部《國語》也至此結束。范蠡的話,堪為《國語》這部巨著的結束語。這段結束語涉及人的選擇,實在是意深旨遠。范蠡明白功成身退的道理,但往哪里退呢?如果還在越王的管轄范圍內,那就要承擔“身死,妻子為戮”的后果。只有遠離越王的政治轄區,才是可靠的全身之道。于是“乘輕舟以浮于五湖”。這里的五湖雖然是指太湖一帶,但從“莫知其所終”的最終結果來看,尤其是就當時的通訊條件、交通條件來看,這里的“五湖”也相當于國家權力所不及的海了。
事實上,孔子不大可能真正走上“乘桴浮于海”的道路,這只是孔子一時的怨言。但是,孔子在無意之間說出的這名句,卻體現了“道”與“海”的對立。道是“大道”,是孔子想像的文明秩序及其建構之道,具體地說,就是源出于西周的禮樂文明秩序原理。但孔子堅守之道得不到推行,就只好“浮于海”,言下之意,是海上或海外不需要推行孔子堅守的大道。
在春秋時代,孔子堅守之道,其實是“舊道”,這個舊道可以概括為儒家之道。儒家是守舊的,與儒家相對應的法家則是維新的。經學大師蒙文通在《法家流變考》一文中說:“儒家之傳本于周,而法家之術大行于戰國而極于秦,則儒法之爭者為新舊兩時代思想之爭,將二家為一世新舊思想之主流,而百家乃其余波也。知兵、農、縱橫之俱為法,而后知《孟子》書中多斥法家之論,而法家之盡與東方之儒相遠也。”[9]P86蒙文通以新舊論儒法,確為不刊之論。蒙文通還把農家以及兵家、縱橫家歸屬于法家,也是值得注意的。
在追求維新的法家群體中,商鞅是主要代表之一。在《商君書》中,第一篇是“更法”:“孝公平畫,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于君。慮世事之變,討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在孝公的主持下,公孫鞅與甘龍、杜摯進行了反復的討論,秦孝公支持了商鞅的主張,最后的結果是:“于是遂出《墾草令》。”[10]P1-8亦即秦國政府發布了《墾草令》。《商君書》第二篇就是《墾令》:“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為私利于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余日。邪官不及為私利于民,則農不敗。農不敗而有余日,則草必墾矣。”[10]P9第三篇為《農戰》,最后得出的結論是:“故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以強兵辟土也,惟圣人之治國作壹,摶之于農而已矣。”[10]P35這就是見于《商君書》中的邏輯:以開墾荒地,發展農耕,加強軍力,從而征服更多的土地。土地面積擴大了,就是大國、強國。割讓土地,通常都是弱國、戰敗國的被迫選擇。
正如前面已經提到的,在周代,分封建國是一種具有憲制意義的安排,分封建國就是把一塊土地交給某個人,讓他成為那個地方的主人,而且這塊土地還是可以世襲的。由此可見,土地是國家建構或政治建構過程中的關鍵性因素。從此以后,土地總是成為國家政治、經濟的核心問題、樞紐問題。在傳統中國,普通的地主總是以擴大自己擁有的土地(主要是耕地)作為最大的追求;歷代農民起義總是會涉及土地的重新分配;“打土豪、分田地”是現代中國人非常熟悉的一個口號;“土地法”是中國現代革命史上最常見的法;甚至當代中國的改革開放,都可以找到一個標志性的起點:將集體土地包產到戶。如前所述,土地固然不能等同于陸地,但土地是陸地的法律化表達。中國固有的陸地性格,由此可見一斑。
三、斯巴達的陸地性格
陸地性格的文明既見于中土,也見于西方。先看古希臘。眾所周知,古希臘有兩個城邦的名氣較大,一個是斯巴達,另一個是雅典,它們代表了兩種類型的城邦。其中,斯巴達有強大的陸軍,是陸地性格的城邦;雅典有強大的海軍,是海洋性格的城邦。在很多人的印象里,生活在雅典的哲學家可以說是群星璀燦,因而都喜歡把雅典作為希臘文明的典型代表。所謂“言必稱希臘”,幾乎可以縮減成為“言必稱雅典”。但是,大哲人色諾芬的看法卻令人意外,在斯巴達與雅典之間,他貶低雅典,他高度評價斯巴達。他為什么對斯巴達情有獨鐘呢?
《希臘史》是色諾芬的代表作之一,此書的中文版附錄了他的兩篇“政制”研究,一是《雅典政制》,二是《斯巴達政制》。他在這兩篇文獻中,開篇就表達了他的價值立場。他在《雅典政制》中寫道:“我不贊賞雅典人的現行政制,不贊賞他們所選擇的政制類型和風格;因為他們作出這樣的選擇,就使得劣等公民過得比優等公民還要好,我認為這種做法并不公平。惟其如此,我認為雅典人的政制并不是一種優良的政制。”[11]P360-361雅典政制并非優良政制,原因就在于,雅典政制的運行,讓劣等公民過得好,讓優等公民過得不好。我們不知道“好”與“不好”的標準是什么,是物質財富的多少,還是社會地位的高低?抑或是兼而有之?不論是哪種情況,都可以看出,色諾芬具有強烈的精英意識、精英立場,這種人很容易看不起別人,特別容易看不起眾人。也難怪,寫過《回憶蘇格拉底》這種著作的人,不可能沒有強烈的精英感。但是,過度的精英感,過度強調自己與普通民眾之間在智識、德性諸方面的差距,恰恰是導致“蘇格拉底之死”的一個根源。
再看《斯巴達政制》,色諾芬籍此書坦露心跡:“猶記昔日,斯巴達雖是人口最為稀少的城邦之一,卻也是全希臘最為強大、最有聲望的城邦。斯巴達何至于此?我曾百思不得其解。直至想到斯巴達人所特有的制度和習俗,我的困惑才隨之消解。”斯巴達特有的好制度、好習俗從何而來?回答是:來自“來庫古斯(Lycurgus)立法”。按照色諾芬的說法:“來庫古斯是斯巴達人所遵從的法律的制定者。正因為遵從了這些法律,斯巴達人才迎來了邦國的強盛。我對來庫古斯既敬佩又好奇。在我看來,他的智慧達到了人間的極致。他并未一味模仿其他城邦,而是創立了一種與其他城邦截然不同的制度,并由此將他的邦國推向了繁榮的頂峰。”[11]P374-375來庫古斯的立法智慧達到了“人間的極致”?這種不留余地的、極端化的表達方式,表明色諾芬對斯巴達政體的無限推崇。
根據《斯巴達政制》,再參考普魯塔克的《希臘羅馬名人傳》,來庫古斯立法涉及多項內容。譬如,建立元老院,等等。其中,與法律地理學有關的主題是土地制度改革。針對來庫古斯的立法改革,普魯塔克寫道,在“元老院產生30名議員以后,他的下一個任務,也可以說是最危險的工作,就是進行土地的重新分配。從這方面來說,絕大多數人過著貧窮和困苦的生活,全部的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里,貧富極其懸殊的狀況成為國家最大的負擔;因此,他的目標是要驅除從而產生的傲慢、猜忌、奢侈和罪惡,特別是積習已深的弊病‘不患貧而患不均’。他獲得人民的支持愿意放棄產業,同意重新分配土地,然后大家處于平等的立足點開始共同的生活”,來庫古斯“等到人民同意這些建議,按照程序馬上開始實施,他把拉柯尼亞(Laconia)的一般農地劃分為3萬份面積相等的單位,附屬于斯巴達市府的土地有9000份;后面這些土地他分配給斯巴達人,至于其他的3萬份分配給拉柯尼亞地區的公民。”[12]P87這段史料表明,在來庫古斯推動的土地改革之前,斯巴達的土地集中在少數土地貴族手里。
來庫古斯(公元前700-630)在公元前六世紀推行的土地改革,旨在把少數土地貴族占有的土地平均分給更多的人,很可能促成了斯巴達的樸素與平等。但是,到了公元前4世紀后期,希臘地區又暴發了著名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前431-404),斯巴達最后贏得了這場戰爭。由此產生的后果是:在斯巴達重新形成的土地兼并現象。亞里士多德(前384-322)在他的《政治學》一書中描繪了這種現象:在“那里,有些人家產甚巨,而另些人則頗為寒酸,從而土地漸漸為少數人所兼并。在這方面斯巴達的法制是有缺點的。立法者規定每一公民所有的土地都不得作任何賣買,這當然不錯;但他同時又許可各人憑自己意愿將財產給予或遺傳于任何個人——這在長期以后就形成全邦的財產不均,恰好和自由兼并的結果相同。事實上全邦五分之二的土地歸屬于少數家族和一些婦女;斯巴達嗣女繼承遺產的特別多,而且當地又盛行奩贈的習俗,于是她們成了邦內的大財主。奩贈實際不是良法,最好是不給陪嫁,如果必需要有的話,也應限于少數或某些適當的財物。照斯巴達的法制,一位公民可把繼承他產業的女兒嫁給任何或貧或富的男子;倘若在他死前女兒尚未出嫁而遺囑又未經言明,這個女兒的合法保護人也可以把她嫁給他所選中的任何男子。這種法制所造成的后果是:拉根尼全境原來可以維持一千五百騎兵和三萬重裝步兵,直到近世,它所有擔任戰事的公民數已不足一千人了。歷史證明了斯巴達財產制度的失當,這個城邦竟然一度戰敗,不克重振。”[13]P85-86
中國史學界也有這樣的看法:“在斯巴達,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勝利為它帶來了空前的榮譽和財富,這就像催化劑一樣急劇地腐蝕著一向以樸素和平等為特征的斯巴達社會,人們瘋狂地聚斂錢財,侵奪他人的利益,致使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平等人公社的原則被廢止了。例如,斯巴達的統帥山德一次就從小亞運回2000他連特巨款,這筆錢相當于波斯的巴比倫和亞述省一年的稅金總額。公元前4世紀初,土地私有化發展很快,原來屬于國家、不能夠轉讓和買賣的土地可以公開進行轉讓,開禁的后果就是土地迅速集中到少數人手里,公民人數大幅減少,由從前的4萬人銳減到2000人左右,到公元前4世紀下半葉,僅剩下1000人。”[14]P161-162中國史學界這些論述,想必吸收了亞里士多德著作中的素材。
除此之外,蘇聯學者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亦曾論及斯巴達的土地集中現象:“在斯巴達占據主導地位的所有制形式是對土地的奴隸的公社所有制。如眾所知,這種情況的形成是由于征服了拉哥尼亞和美塞尼亞,并奴役這兩個地區相當部分的居民。既然征服是依靠整個斯巴達公民公社的力量實現的,因而每個公民便都可以同樣地要求成為所占領的土地以及固定于土地之上的奴隸的主人。”[15]P97
把這些見于古今中外的論述綜合起來,我們可以發現這樣一個過程:在來庫古斯的土地改革之前,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后,土地兼并與土地集中現象都盛行于斯巴達,大土地所有者成為了社會財富的擁有者。色諾芬(公元前440-355)生于伯羅奔尼撒戰爭發生之前,很可能是在這場戰爭結束之前,就完成了他的《斯巴達政制》一書。因而,他所看到的斯巴達政制,還保留著來庫古斯立法改革的制度成果,色諾芬對斯巴達政制的贊賞,也是因為來庫古斯以土地改革為中心的立法安排。由于土地在斯巴達政制中占據的地位,由于斯巴達人對于兼并土地的熱情,我們可以想像,斯巴達城邦的權貴階層,就像中國古代的大地主。這樣的經濟狀況與政治狀況,為斯巴達城邦涂上了強烈的陸地色彩,斯巴達城邦也因此成為一個陸地性格的城邦。色諾芬之所以偏愛斯巴達,或許就是因為偏愛斯巴達的陸地性格。
四、奪取土地背后的政體考量
在古希臘之后,再說說意大利佛羅倫薩的馬基雅維里(1469-1527)。此人生活的年代與中土的王陽明(1472-1529)大致相當,甚至年壽也只差一歲,而且他們同為東西方影響深遠的思想巨人,殊為難得。通常認為,馬基雅維里是西方近代政治學的奠基人,他的學說近似于中土的韓非子。在他的代表作《君主論》第四章中,馬基雅維里提出了一個與土地有關的問題:為什么亞歷山大大帝所征服的大流士王國在亞歷山大死后沒有背叛其后繼者?
亞歷山大奪取了大流士王國的土地,在亞歷山大死后,亞歷山大的后繼者居然還可以繼續占有這塊土地,這可不是一個常態。這與大流士王國的政制、政體有關系。在這個問題的背后,蘊含了一個法理問題:奪取土地與政體有關。一個君主,如果想奪取別國的土地,需要考量別國的政體。當然,按照現代的國際法原則,別國的土地是不能奪取的,奪取別國的土地是違反國際法的。但是,我們這里是側重于思想史研究,算是“關于馬基雅維里的思考”。政治哲人斯特勞斯有一本著作就叫《關于馬基雅維里的思考》(申彤譯,譯林出版社2003年版)。在這里,讓我們根據《君主論》第四章的內容,跟著馬基雅維里做一些思考,既思考土地,也思考政體,姑且算作是關于馬基雅維里的一點思考。
馬基雅維里首先區分了兩種君主政體:一種是土耳其式的君主政體,另一種是法蘭西式的君主政體。雖然都是君主政體,但兩種君主政體是不同的。土耳其君主政體的特質在于,只有君主一個人是主子,協助君主統治的其他所有人,都是君主的臣仆。土耳其的人民群眾只認可君主一個人,君主的臣仆只是君主的代理人或臣仆,并不會受到人民群眾的特別愛戴。用現在的通俗語言來說,只有君主一個人是老板,其他人都是老板的雇員,都是君主的打工仔。相比之下,法蘭西也是君主政體,但它的特質在于:既有君主,也有一大群貴族,這些貴族其實就是諸侯,諸侯的身份與地位并不是現任君主賞賜的,而是由古老的世系得來的,或者說是由祖上傳下來的。在通常情況下,諸侯在自己的轄區內享有的統治地位,君主是不能隨便剝奪的。某個諸侯轄區內的人民群眾,雖然也愛戴法蘭西的君主,但對本地的諸侯或貴族有更多、更直接的愛戴,有更深的情感。用現在的話來說,君主相當于法蘭西這個王國的大股東,所以成了董事長,但諸侯或貴族也是股東,雖然不是大股東,但也是董事會成員,也對企業享有股權。
馬基雅維里說的這兩種君主政體,中國歷史上都出現過。譬如,周武王建立的周王朝,有歷代君主(周天子),但從姬周政權建立伊始,就產生了很多諸侯。自周成王以后的周天子,就很難去剝奪譬如魯國伯禽或唐國(后來的晉國)叔虞的歷代繼承人的身份與權力。當然,其他諸侯的身份與權力同樣不能剝奪。按照馬基雅維里的分類,周代的君主政體與法蘭西的君主政體就比較類似。但是,自從秦王贏政完成了“六王畢,四海一”的偉業之后,封建制改為了郡縣制,在正式制度上,法蘭西式的君主政體就終結了。當然,秦亡漢興之后,制度上又出現了一些反復。在漢初的特定情勢下,劉漢王朝又有了分封建國的實踐,但帶來了很多問題,譬如漢景帝時期的“七王之亂”。漢代以后,分封制逐漸退出了中國的政治舞臺。特別是隋唐以后,隨著科舉制的逐漸成熟,協助君主統治國家的官員,包括中央政府官員與地方政府官員,都是君主的雇員,都相當于君主的“臣仆”。如此稱呼傳統中國飽讀四書五經的士大夫,他們可能不太高興。但是,我們看電視劇,清代的很多官員在“老佛爺”面前都是自稱“奴才”,這就是“仆”,甚至是比“仆”更低的“奴”;當然,也有一些官員在君主面前自稱為“臣”。這就是說,“臣”與“仆”都有了,“臣仆”這個概念也就完整了。從制度上嚴格細分,“臣”與“仆”當然不一樣。“臣”有身份,是協助君主治國的“公仆”,“仆”沒有身份,是協助君主日常起居的“私仆”。但是,也有一些“仆”,譬如像魏忠賢這樣的太監,居然成為了國家治理的操盤手。這些細節問題暫且不予深究,大致說來,中國自隋唐以后的君主政體,相當于土耳其式的君主政體。
在區分這兩種政體的基礎上,馬基雅維里告訴我們,如果你要奪取別國的土地,你就要注意區分,對方的君主政體是土耳其式的君主政體呢,還是法蘭西式的君主政體。如果對方是土耳其式的君主政體,對你來說,那就是奪取對方的土地很困難,但奪取之后,要長期占有對方的土地就很容易。這種情況,我們可以概括為易守難攻。按照馬基雅維里的理論,奪取困難的原因在于:你在對方國家里找不到有效的內應。對方國家的某個臣仆,即使想當內應,他也沒有多大的實力;他作為臣仆或奴才,沒有人跟隨他一起“反水”。但是,如果奪取者憑借自己的強大實力把對方徹底征服了,把對方的君主成功地廢棄了,就沒有人能夠重整旗鼓,重新與征服者叫板,因為被征服的國家失去了君主,就會群龍無首。所以,征服者要守住奪取過來的土地,那是比較容易的。
反之,像法蘭西那樣的君主政體,如果你要奪取他的土地,你面對的情形就是易攻難守。原因在于:在法蘭西這樣的國家里,有眾多的諸侯或貴族,容易在其中找到一兩個作為內應,君主對眾多諸侯的整合能力有限。君主發號施令,諸侯們不大聽。諸侯們的“核心意識”很弱,全國上下不容易擰成一股繩,你作為外來的征服者,很容易在這樣的國家撕開一個突破口,然后各個擊破,把對方的土地取得過來。但是,這樣的土地即使已經奪取過來,若要長期守住,那就困難了。因為每個諸侯都有一定的號召力,即使君主的勢力已經不復存在,總有一些諸侯或貴族會試圖挑戰外來的征服者,從而讓征服者已經奪取的土地面臨著喪失的風險。
根據以上的理論,馬基雅維里回答了他提出的問題:“如果你考察一下大流士政府的性質,你就會察覺它同土耳其皇帝的王國相似;因此,亞歷山大大帝首先必須把大流士完全打垮,并且從他手中把土地奪取過來。在贏得這樣的勝利之后,大流士死了,亞歷山大大帝終于牢固地占有這個國家就是由于上述的理由。而且,假如亞歷山大的后繼者們團結一致的話,他們本來能夠牢牢地并且安逸地享有這個國家,如果不是由于他們自己引起騷亂,那個王國是不會發生其他騷亂的。但是,那些像法國這樣組織的國家,可就不能這樣平穩地被占有了。在西班牙、法國和希臘之所以屢次發生反羅馬人的判亂,就是因為這些國家里面有無數的小王國。當他們的記憶尚未消失的時候,羅馬人總是不能夠穩然占有其地的。但是,一旦由于羅馬帝國的權力和統治的長久性使他們的記憶煙消云散的時候,羅馬人就成為這些地區牢固的占有者。”經過這樣的比較與分析,馬基雅維里得出的結論是,“當我們考慮到一切事情的時候,對于下述情況便不會感到驚訝:亞歷山大保持亞洲的領土頗為容易;而別的人,象皮爾羅以及許多人,保全所獲得的地方卻有困難,這并不是由于勝利者的能力有大有小,而是由于被征服者的情況有所不同使然。”[16]P20-21
征服就奪取其土地,奪取土地是為了長期占有其土地。但是,奪取誰的土地,能否長期占有其土地,則要視對方的政體而定。對方的政體并不能決定一切,但對方的政體是一個很大的變量與制約因素。在法學理論中,關于政體的研究很多,但很少通過這樣的視角去研究政體。這是馬基雅維里對于政體理論及法律地理學的一個貢獻。
五、“土地被看作是本體”
在馬基雅維里之后,再看德國人對于陸地、土地、大地的理解。我們找兩個很有代表性的德國人,一個是康德(1724-1804),一個是黑格爾(1770-1831),看看他們如何闡釋關于陸地、土地與大地的法理。
先說康德。他與清代的戴震(1724-1777)同年出生,但比戴震長壽。為什么要提到戴震?以我個人的私見,在與康德同年出生的中國人里,戴震應當是思想地位最高的中國哲學家,其代表作是《孟子字義疏證》。①這里我們先不說戴震。我們先看康德的《法的形而上學原理》,這是一部法哲學著作,此書論及物權時有一個值得注意的論斷:“第一種獲得物只能是土地。”討論物權,應當從土地開始,土地是一切物權的起點,具有“本體”的地位。按照康德的原話,那就是:“這里所說的土地要理解為所有可以居住的土地。對于土地上一切能夠移動的每一件物來說,土地被看作是本體;那些可以移動的物的存在模式被看作是土地的一種固有屬性。從理論所承認的見解來看,這些偶然存在物不能離開它們的本體而存在,所以,在實際關系中,在土地上能夠移動的物不能認為屬于任何人,除非假定他以前已經在法律上占有那塊土地,如果這樣,就可以考慮那些東西是屬于他的。先假定土地不屬于任何人。那么,我便會有資格從土地上搬走所有可以移動的東西,那怕土地上所有的東西都消失,為的是占領這塊土地,而不至于侵犯任何人的自由,但是必須有個前提,即這塊土地根本不存在所有者。每一種可以被毀掉的東西,如樹木、房子等等——從它的質料看至少如此——都是可以移動的,如果一物除非毀壞它的形狀,否則不能移動,我們稱之為不動產,在此物中的‘我的和你的’不能理解為可以適用于此物的本體,只適用于附屬于本體的東西,以及那些主要地不是構成此物自身的東西。”[17]P76-77這段話主要在于強調土地的基礎地位,只有占有了土地,才能占有土地上的樹木、房子等等附屬物。只有在土地不屬于任何所有者的前提下,才能占有土地上的樹木、房子。
如果把物權看作是私權,那么,私權的第一個環節就是占有土地。公權呢?康德從“統治者”的角度解釋了這個問題,他說:“統治者,從他作為具體化的立法權力來看,他是否應該被認為是土地的最高所有者,或者僅僅作為通過法律去統治人民的最高統治者?由于土地是最高的條件,只有根據這個條件,才能把外在物變為個人所有,對土地可能的占有和使用,構成最初可能獲得外在權利的基礎。因此,一切外在權利必須來自作為土地的主人,和土地的至高無上者的統治者;或者,也許可以更恰當地比作土地的最高所有者。”[17]P153這就是說,土地不僅是私權的起點,土地還是公權的起點。公權的獲得,必須來自“土地的主人,和土地的至高無上的統治者”。統治者,無論是什么樣的統治者,個體的統治者(君主主權),或群體的統治者(人民主權),首先必須成為土地的主人。土地既然是公權與私權的本體、基礎、起點,那么,是否可以說,土地是法權的第一個環節?康德的“法的形而上學原理”,能否從一個特殊的視角上,理解為一個“以土地為本體的法權體系”?
再看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這是黑格爾的晚期著作,這部著名的法哲學論著由他在柏林大學的講義加工而成。全書分成三篇,分別是“抽象法”、“倫理”與“道德”,每篇再分三章,結構很均衡,也很工整。其中,第一篇“抽象法”的第一章就是“所有權”。所有權的第一個環節就是“取得占有”。黑格爾在此寫道:“物的占有有時是直接的身體把握,有時是給物以定形,有時是純粹的標志。”就占有的方式來說,“占有的這些方式包含著由單一性的規定到普遍性的規定的進展。身體把握只能行于單一物,反之,標志是借觀念而占有。在后一種情況,我用觀念來對待物,并且認為全部是我的,而不僅僅以我身體所能占有為限。”[18]P62由這段話可以看到,黑格爾法哲學的起點是“占有”。
《法哲學原理》的第三篇是“道德”,此篇的第三章,亦即全書的最后一章,以“國家”為題,這就意味著,國家是黑格爾法哲學的歸宿。國家不僅是法哲學的歸宿,國家也是個人的歸宿,因為,“成為國家成員是單個人的最高義務”,“由于國家是客觀精神,所以個人本身只有成為國家成員才具有客觀性、真理性和倫理性”。[18]P253-254反之,如果不能成為國家成員,則個人就不具有倫理性,個人就是殘缺的個人,個人就是未完成的個人。相對于個人,“自在自為的國家就是倫理性的整體,是自由的現實化;而自由之成為現實乃是理性的絕對目的。國家是在地上的精神,這種精神在世界上有意識地使自身成為實在,至于在自然界中,精神只是作為它的別物,作為蟄伏精神而獲得實現。只有當它現存于意識中而知道自身是實存的對象時,它才是國家。在談到自由時,不應從單一性、單一的自我意識出發,而必須單從自我意識的本質出發,因為無論人知道與否,這個本質是作為獨立的力量而使自己成為實在的,在這種獨立的力量中,個別的人只是些環節罷了。神自身在地上的行進,這就是國家。”盡管在現實生活中,“國家不是藝術品;它立足于地上,從而立足在任性、偶然事件和錯誤等的領域中,惡劣的行為可以在許多方面破壞國家的形相。”[18]P258-259但是,至少在理論層面上,國家畢竟是神圣的。立足于大地的國家,乃是大地上的神物。
渴望什么,是因為缺乏什么。黑格爾如此頌揚國家,是因為黑格爾時代的德意志,小邦林立,四分五裂,眾多邦國的統治者目光短淺,普遍昏庸無能。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德意志作為一個政治共同體,糟糕到什么程度呢?恩格斯在《德國狀況》一文中,有一段生動的描述:“這是一堆正在腐朽和解體的討厭的東西。沒有一個人感到舒服。國內的手工業、商業、工業和農業極端凋敝。農民、手工業者和企業主遭到雙重的苦難——政府的搜刮,商業的不景氣。貴族和王公都感到,盡管他們榨盡了臣民的膏血,他們的收入還是彌補不了他們的日益龐大的支出。一切都很糟糕,不滿情緒籠罩了全國。”簡而言之,“一切都爛透了,動搖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簡直沒有一線好轉的希望,因為這個民族連清除已經死亡了的制度的腐爛尸體的力量都沒有。”[19]P633-634在這種背景下,黑格爾把外來的征服者拿破侖稱為“馬背上的世界精神”,其實已經暗含了對德意志各邦君主的貶斥。對于德國的這種散亂的政治狀況,遠在大洋彼岸的“聯邦黨人”甚至已經洞若觀火,他們寫道:“日耳曼的歷史就是一部皇帝與諸侯和城邦之間的戰爭史,諸侯與城邦之間的戰爭史;強者橫行,弱者受壓的歷史,外國侵犯和外國玩弄陰謀詭計的歷史;對人力的征調和財富的征收置之不理或部分服從的歷史;企圖實行完全無效或伴隨殺戳和破壞,包括無辜犯罪的強制征募的歷史;也是一部普遍的無能、混亂和苦難的歷史。”[20]P93這段話,可以從相反的方向解釋:黑格爾為何如此傾慕一個貨真價實的國家,因為那是德意志最需要的“倫理性的整體”。
綜合康德與黑格爾的法哲學,我們可以發現其中蘊含的基本精神:“土地被看作是本體”,通俗地說,那就是尊重土地、強調占有、推崇國家。這是一種具有陸地性格的法哲學。如果把這些精神跟海洋性格的法哲學做一些比較,就會更加清析。對于這一點,擬另作討論,這里不再展開。
六、“大地的法”
討論土地、大地、陸地的法,不能避開另一個相對晚近的德國人卡爾·施米特(1888-1985)。他的《陸地與海洋》固然是把陸地與海洋置于相互并列的地位,他的《大地的法》卻是一部以“大地法”為主題的專門著作。他所謂的“大地的法”,其實就是歐洲大陸的國際法;他所說的大地,就是指歐洲大地。在西方學界,施米特通常被稱為“歐洲公法學家”,甚至是“最后一位歐洲公法學家”。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最后一位歐洲公法學家”?難道在施米特之后,就沒有研究“歐洲公法”的法學家么?
原來,所謂“歐洲公法”,自有其特定的含義。歐洲公法是指歐洲國際法,更具體地說,就是歐洲大陸主導的國際法,也就是施米特所說的“大地的法”。在施米特之后,或者更準確地說,在二戰以后,由歐洲大陸主導的國際法確實不復存在,當然也就不會再出現新的“歐洲公法學家”。在這個意義上說,他的這部《大地的法》,實為歐洲大陸主導的國際法的一曲挽歌。
為什么是挽歌?根本的原因在于:近代以來,主要是從19世紀末期以來,曾經由歐洲大陸主導的世界秩序在消退與淡化,歐洲大陸正在由世界的中心走向邊緣。施米特說:“在先前的數個世界中,都是由歐洲會議決定世界空間秩序,但是在1918-1919年的巴黎和會上,第一次乾坤顛轉:由世界決定歐洲的空間秩序。這意味著人們試圖在一個完全失序的世界里為歐洲創設一種新秩序。”[21]P222這里的“人們”,顯然是指歐洲大陸以外的“人們”,主要是指英美主導的海洋國家及其所代表的勢力。我們中國人看到這句話,想必會回憶起清朝末年流行的李鴻章的那句名言:“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在中國,是三千年以來的乾坤顛倒。在歐洲大陸,在施米特看來,是三百年的乾坤顛轉。無論是三千年還是三百年,失落感都是一樣的。
把施米特稱為“最后一位歐洲公法學家”,是因為在他之后,歐洲公法根本就不復存在,歐洲公法已經遁入歷史深處。在施米特的眼里,“歐洲中心主義的傳統國際法秩序在走向衰落,古老的大地法亦日薄西山。”[21]P2這個過程是怎么發生的?施米特告訴我們:1884年4月22日,美國政府承認了剛果協會的旗幟,這標志著美國政府承認了非洲土地上存在著正常的國家。但是,在此之前,非洲的土地上只有殖民地,沒有新國家。美國政府的這個行為,當時的歐洲人盡管“都不以為然。殊不知,這正是傳統的特定的歐洲國際法逐漸走向衰亡的先兆,然而無人理會。歐洲公法日薄西山,繼而向無差別普世化之世界法的轉變乃大勢所趨”。在施米特看來,歐洲公法的落幕始于1890年,因為,“直到1890年,主流觀點仍然認為國際法就是專指歐洲國際法。歐洲大陸特別是德國視之為理所當然。盡管那些外交理論和語匯中所規定的一般概念諸如人權、文明和進步等普遍適用于世界范圍,但是整體的觀念完全是歐洲中心主義的。因此,所謂‘人類’主要被理解為歐洲的人類,‘文明’自然也只是歐洲的文明。‘進步’即是歐洲文明的直線發展。”[21]P208-209而且,“人們常說‘文明國家的國際法’,而且堅持認為在國際法上,歐洲的土地或者與歐洲有同樣地位的土地,與那些未開化的或非歐洲人所有的土地具有不同的法律地位。殖民地或被保護地在國際法上沒有被賦予同國家領土一樣的地位。”[21]P211這就是讓施米特懷念的“歐洲公法”。
但是,這樣的歐洲公法與19世紀同時壽終正寢。19世紀末,學者們不再撰寫歐洲國際法,而是直接使用“國際法”這個概念。東方的日本“在1900年與歐洲大國平起平坐,參加了鎮壓‘義和團運動’的遠征軍,一個亞洲大國從此而崛起并得到承認。與1907年第二次海牙會議相比,1899年第一次海牙會議的氛圍依然是純粹歐洲式的。但是,通過觀察這期間亞洲與美洲與會國的數量和角色的變化,可以清楚地發現,在不到十年的時間里,已經實現了從歐洲公法時代向非歐洲意義之國際法的巨大跨越。”[21]P212隨后,施米特還指出,“1919年日內瓦國聯在巴黎郊區會議的領土分會上,歐洲中心的空間秩序已經完全被拋棄了。”“歐洲不再是世界的神圣中心了。”[21]206-207從此,歐洲從世界國際法中心的云端上跌落下來。歐洲國際法或曰歐洲公法不復存在,這是一個令人傷感的結果。“先前的秩序,無論好壞,至少是一種具體的秩序,也就是說,主要是一種空間秩序,是由諸歐洲王室、國家和民族所組成的真正的共同體,但這些都已走向消亡,無可替代的消亡。代之而起的并非一套諸國家組成的‘體系’,而只是一種既沒有空間也不成體系的混亂雜處的現實關系。這是由五十多個據稱是地位平等、主權平等的異質國家及其散落各處的領地所組成的混亂局面,雜亂無章,缺少空間和精神上的關聯。在這種無結構的亂局中,共同的戰爭框架無法建立,‘文明’的概念最終亦無法再充當同質性的實質內容。”[21]214-215
施米特認為,歐洲公法的終結者主要是英國,或者說,英國是歐洲公法終結者的主要代表,這是一個延續了幾個世紀的過程。起初,“15世紀的英國人,一面是好斗的騎士,在法國搶掠戰利品;另一方面是牧場主,將自家牧場出產的羊毛賣給佛蘭德斯。自16世紀中期以來,英國的海盜遍布世界各大洋,不僅在友好界線和大型占取方面,而且在海洋上都建立了新的自由,海洋對英國人來說不啻為獨享的海上大型占取。”在這個過程中,“英國成功地完成了從中世紀封建的、區域性國家轉變成為一個純粹海洋性的、能夠在全世界建立均衡性力量的海洋性大國。”由此,“英國徹底地轉向了海洋的那一面,并且從海上決定著大地法。英國因此成為歐洲中心主義全球秩序中全部海洋領域的主導者,成為歐洲公法之海洋部分的保護者,還是維持陸地與海洋間均衡的掌控者”。[21]P152-153
我相信,施米特在寫下這些句子的時候,一定是帶著滿腔怨氣的。英國,這個來自海洋上的家伙,這個以充當海盜發跡的暴發戶,憑借著強勢的海上霸權,把歐洲大陸從世界秩序主導者的位置上硬生生地拉下來,以空洞的沒有實質內容的國際法取代了數百年來一以貫之的歐洲公法,讓獨立自主的大陸屈從于海洋,至少是屈從于海洋與大陸的均衡狀態,無論如何都是一件令人沮喪的事情。而且,更加讓人沮喪的是,這個均衡狀態的掌控者,居然不是歐洲大陸,更不是德國,而是來自海洋的英國。
眾所周知,名滿天下、毀譽參半的卡爾·施米物與希特勒的納粹帝國有一些糾葛。有些人據此抵毀施米特,有些人則為施米特辯護。但是,施米特“附逆”畢竟是一個不容回避的事實。施米特為什么“附逆”?一個根本的思想根源在于:在思想深處,施米特對“第三帝國”還是有認同感的。我個人猜測,對于英國這個新興的海上帝國,特別是這個海上帝國對德意志主導的歐洲公法的終結,不好說施米特有“抱恨”的情緒,但他至少是耿耿于懷的。在“神圣羅馬帝國”、“德意志帝國”之后建立的“第三帝國”,或許代表了德國乃至整個歐洲大陸重振其雄風的希望所在。施米特在經過觀望與猶豫之后,一度擁抱了這個可能讓歐洲公法或“大地的法”起死回生的政治實體,對于這樣的選擇,我們不必贊同,但至少是可以理解的:這是一個飽含著情感的選擇。
七、大陸法系的特質及其地理根源
在法律的世界里,就世界范圍來看,與陸地、土地、大地密不可分的法就是大陸法系。大陸法系也稱羅馬日耳曼法系或法典法系。這些不同的名稱指出了這個法系的不同側面。大陸法系旨在強調,這是一個在歐洲大陸上生長起來的法系。羅馬目耳曼法系旨在強調,這個法系是源于羅馬法。法典法系的含義是,這個法系特別注重體系化的法典。法國人達維德喜歡用“羅馬日耳曼法系”這個概念,他說:“羅馬日耳曼法系是在歐洲大陸形成的,今天它的主要中心還在那里,盡管由于傳播或接受現象,很多歐洲以外的國家加入了這個法系或引進了它的某些成分。”[22]P35
大陸法系的特質,由大陸法系的其他幾個名稱,大體上已經體現出來了。如果要進一步索解,美國人梅利曼的《大陸法系》一書還可以參考。在這個大陸法系的旁觀者看來,“大陸法系的總體形象”可以概括為七點:“(1)法律領域里的主體僅僅是國家與個人;(2)立法至上;(3)立法、司法和行政的嚴格分權制;(4)有限的和缺乏創造力的司法活動;(5)對‘遵循先例’原則的否定;(6)民法典及民法理論的重要性;(7)高度發達和嚴密的法律概念體系;(8)對法律‘確定性’的執著追求。”[23]P158
對于這些特質,梅里曼還有進一步的解釋。譬如,關于民法典及民法理論的重要性,梅里曼認為:“大陸法系所運用的主要法律概念、法的基本結構以及基本法律制度,無一不是直接從民法中推演和發展而來。法學研究方法的形成也是由于民法學家的努力。在民法領域中發展起來的系統化、概念化的結構,最后為其它法律部門所采用。人們至今還常常認為,適用于整個法律制度的一般法學理論是由民法學家發展起來的。”[23]P72大陸法系的這個特質,其實是羅馬法的影響所致。
再譬如,對于大陸法系偏好的“確定性”,梅里曼告訴我們,“大陸法系國家的法學著述均十分強調法律的確定性。當然,在任何法律制度中,‘確定性’都是追求的目標,但‘確定’在大陸法系國家獲得了至高無上的價值,它已成為勿庸置疑的信條,是最為基本的目標。盡管眾多的大陸法系學者們承認與‘確定’相并行的尚有其它一些基本價值,維護這些價值將可能以犧牲‘確定’為其代價。但這些原則通常并不用這種詞語進行討論。大陸法系國家總是以改革法律制度將會損害法律的確定為論據,反對改變既存的法律制度。例如,在意大利墨索里尼統治時期,法西斯主義者企圖把法變成極權國家的工具,但是法學家們以保持法的‘確定’為由,成功地抵制了這種企圖。法西斯主義倒臺建立了共和國后,許多要求對意大利法律制度進行改革的主張,又一次遭到法學家們的反對,理由也是為了維護法的‘確定’。‘確定’是抽象而重要的法學概念,它就像一盤國際象棋中的皇后,可以向任何方向移動。顯然,‘確定’這一主張的出現是出于多種目的,但最主要的是由于對法官的不信任而產生的。”[23]P49其他幾個方面的特點,不再逐一展開討論。梅里曼概括的這幾個特點,想必能夠得到較多的認同。
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的問題是,大陸法系的這些特質緣何而來?對于這樣的追問,我們當然可以從歷史學的角度,詳述大陸法系的形成機理,以此解釋大陸法系的特質。但是,我們也可以從地理學的角度,來解釋大陸法系的特質。第一,大陸法系既然是歐洲大陸上盛行的法系,必然與歐洲大陸的大陸屬性具有血肉聯系。歐洲大陸既然是一片大陸,那么,大陸本身體現出來的確定性,就迥異于海洋本身的不確定性,大陸本身的確定性促成大陸法系對確定性的執著追求。第二,大陸上的土地是可以占有、轉讓的,海洋是不能占有、轉讓的,大陸的這種屬性決定了傳統的民法典與民法理論的重要性。第三,大陸法系的司法活動缺乏創造性,與大陸生活的低風險是互為表里的,與之相對應,海洋生活的高風險與海洋法系的創造性也許具有隱秘的聯系。第四,大陸法系強調國家這種主體,特別是黑格爾的法哲學對國家的推崇,也與大陸生活對確定性、權威機構的需求有關。與之相對應,在海洋性生存方式中,更加強調個人或群體的冒險活動,對權威機構的需求沒有那么強烈。英國的君主長期以來都是“虛君”,這是為什么?1787年的美國人為了把松松垮垮的“邦聯”改建成稍稍緊密一些的“聯邦”,就費了很大的勁。甚至到今天,美國的州長也毋須聽從聯邦總統的命令,這又是為什么?這些年來,美國的聯邦政府經常“停擺”、“歇業”,似乎也沒有在實質上影響美國的公共秩序,但在歐洲大陸,你聽說過中央政府停擺歇業的情況么?英美國家的這些特質,可以反襯大陸法系與海洋法系的一個差異:前者的大陸格性、大陸性生存方式,導致了它對國家、權威機構的尊崇。最極端的表述——如前所述——出自黑格爾:“神自身在地上的行進,這就是國家。”如此崇拜國家的法哲學,大概只能出自大陸的法哲學家。
八、結語
從比較法學的視野中看,“大陸法系”是一個高頻出現的概念,與“大陸法系”有關的學術文獻,可謂汗牛流棟。相比之下,關于“大陸”、“大地”或“陸地”本身的法理學研究,卻是一個相對薄弱的學術環節。有鑒于此,本文立足于中國與西方兩大法律傳統與思想傳統,揭示了陸地本身的法理意蘊。在此基礎上,可以得出以下幾個方面的結論。
首先,法律傳統與地理密不可分。對此,孟德斯鳩在他的傳世名著《論法的精神》一書中已有原則性的論述。他說:“法律還應該顧及國家的物質條件,顧及氣候的寒冷、酷熱或溫和,土地的質量,地理位置,疆域大小,以及農夫、獵人或牧人等民眾的生活方式等等。”[24]P15這些因素,雖然都與地理有關,但是,更為明顯的地理差異或地理特征,畢竟還是陸地與海洋。在比較法學中,大陸法系與海洋法系的劃分,就根源于大陸與海洋在地理上的根本差異。大陸法系作為一種法律傳統,它的基本特性,其實都根源于陸地本身的特性。
其次,關于陸地的法理學思考,主要出于大陸國家的思想家。如前所述,康德的法權體系以土地作為本體,黑格爾的法哲學把國家作為地上的神物。他們的理論都有一個至為明顯的底色,那就是陸地、大地、土地。在現代,施米特以“大地的法”命名自己的著作。這些關于陸地的法哲學,都出自德國這個歐洲大陸國家。相比之下,我們可以發現,荷蘭的格勞秀斯著有《海洋自由論》,英國的培根著有《新大西島》,美國的馬漢提出了著名的海權論。無論是英國、美國還是荷蘭,都是海洋性格的國家。海洋性格的國家關注海洋,大陸性格的國家關注大陸,這是一個大致的區分,也是一個基本的趨勢。
最后,中國在傳統上是一個大陸性質的國家,但是,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必須認真對待海洋,必須更深入地理解海洋。因此,在展開關于陸地的法理學考察的同時,還有必要進一步展開關于海洋的法理學考察。對此,我在《關于海洋的法理學考察》(未刊稿)一文中,已有專門的論述。這里不再贅述。
注釋:
① 在這里專門提到戴震,主要是因為,在修改這段文字的間隙,我正在零星地閱讀戴震。在戴震生命的最后一年,亦即丁酉(1777)年正月十四日,他在給段玉裁的一封信中寫道:“仆自上年三月初獲足疾,至今不能出戶,又目力大損。今夏纂修事似可畢,定于七八月間迄假南旋就醫,覓一書院糊口,不復出矣。竭數年之力,勒成一書,明孔、孟之道,余力整其從前所訂于字學、經學者。”([清]戴震著:《孟子字義疏證》,何文光整理,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185頁)這段話寫出了戴震的晚景,可以與康德的晚景做一比較,庶幾可以看出東西哲人之晚景到底有何異同。關于康德的晚景,可以參看[美]庫恩:《康德傳》,黃添盛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35-474頁。大致說來,哲人的晚景,集中體現了哲人的出與處、去與留、取與舍。再順便提一句,與戴震(1724-1777)差不多同時代的重要人物還有曹雪芹(1715-1763),他比戴震早生9年,早死14年。據說,曹雪芹的晚年是在北京西山的黃葉村度過的,那里的曹雪芹紀念館據說就是他晚年的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