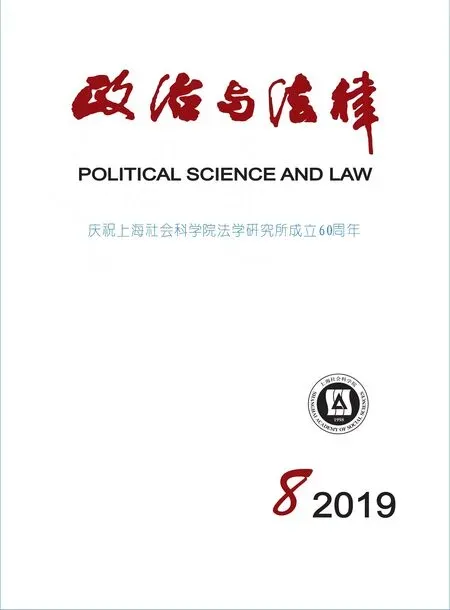正當防衛的司法偏差及其糾正
(北京大學法學院,北京 100088)
正當防衛是我國刑法中重要的制度,在行為符合刑法分則規定的構成要件的情況下,如果該行為被認定為正當防衛,則否定其違法性,對防衛人不以犯罪論處。因此,在刑法理論上,正當防衛屬于違法阻卻事由。在司法實踐中,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在處理案件過程中,如果認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行為構成正當防衛,公安機關應當撤案、檢察機關應當絕對不起訴、審判機關應當做出無罪判決,以上述方式結案并終止刑事訴訟程序。與此同時,辯護人也往往將正當防衛作為重要的辯護理由,以此維護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合法權益。然而,目前在我國司法實踐中,正當防衛制度未能得到有效實施,防衛人的合法權益未能得到有力保護。這種現象,筆者稱之為正當防衛的司法偏差。筆者于本文中擬對正當防衛案件處理中存在的司法偏差現象進行深入探究,并提出相應的解決措施。
一、正當防衛司法認定的偏差
1979年我國刑法第17條對正當防衛做了具體的規定,(1)孫明亮故意傷害案發生在1997年之前,當時所適用的是1979年我國刑法。因此,在本文中,筆者關于孫明亮故意傷害案的論述所引刑法條文,均為1979年我國刑法條文。該規定為司法機關正確適用正當防衛提供了規范根據。然而,正當防衛制度實施過程中出現了明顯的偏差,這就是司法機關難以掌握正當防衛和防衛過當的界限,因而在較大程度上影響了公民采取正當防衛措施制止不法侵害的行為,甚至出現了對不法侵害,由于害怕掌握不好界限而不敢防衛的情況。(2)參見郎勝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釋義》,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6版,第21頁。正當防衛和防衛過當之間界限的混淆現象,在當時我國司法實踐中確實客觀存在,發生在1984年的孫明亮故意傷害案就是一個十分典型的案例。
【案例1】孫明亮故意傷害案。1984年6月25日晚8時許,被告人孫明亮偕同其友蔣小平去看電影,在平涼市東關電影院門口,看到郭鵬祥及郭小平、馬忠全三人尾追少女陳××、張××,郭鵬祥對陳××撕拉糾纏。孫明亮和蔣小平上前制止,與郭鵬祥等三人發生爭執。爭執中,蔣小平動手打了郭鵬祥面部一拳,郭鵬祥等三人即分頭逃跑,孫明亮和蔣小平分別追趕不及,遂返回將陳××、張××護送回家。此時,郭小平、馬忠全到平涼市運輸公司院內叫來正在看電影的胡維革、班保存等六人,與郭鵬祥會合后,結伙尋找孫明亮、蔣小平,企圖報復。當郭鵬祥等九人在一小巷內發現孫明亮、蔣小平二人后,即將孫明亮、蔣小平二人攔截住。郭小平手執半塊磚頭,郭鵬祥上前質問孫明亮、蔣小平為什么打人。蔣小平反問,人家女子年齡那么小,你們黑天半夜纏著干啥,并佯稱少女陳××是自己的妹妹。郭鵬祥聽后,即照蔣小平面部猛擊一拳。蔣小平挨打后與孫明亮退到附近街墻旁一垃圾堆上。郭鵬祥追上垃圾堆繼續撲打,孫明亮掏出隨身攜帶的彈簧刀(孫明亮系郊區菜農,因晚上在菜地看菜,在市場上買來此刀防身),照迎面撲來的郭鵬祥左胸刺了一刀,郭鵬祥當即跌倒。孫明亮又持刀對空亂掄幾下,與蔣小平乘機脫身跑掉。郭鵬祥因被刺傷左肺、胸膜、心包膜、肺動脈等器官,失血過多,于送往醫院途中死亡。
從以上由判決書認定的案件事實來看,郭鵬祥被殺的起因是郭鵬祥等人尾隨并糾纏兩位少女,孫明亮和蔣小平見狀出面阻止因而發生爭執。就此而言,孫明亮和蔣小平的行為具有見義勇為的性質,值得肯定。當然,在雙方發生爭執以后,蔣小平率先打了郭鵬祥面部一拳。在這種情況下,郭鵬祥逃離現場去搬救兵。就此而言,似乎蔣小平對于矛盾的激化負有責任。因此,該案的性質按照我國司法慣例就會被認定為互毆。甘肅省平涼地區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定孫明亮在打架斗毆中,持刀傷害他人致死,后果嚴重,犯有故意傷害罪,于1984年11月23日判處孫明亮有期徒刑15年。考慮到當時正處在“嚴打”的背景之下,這一判決結果還是較為輕緩的。因此,法院宣判后,孫明亮放棄上訴,接受判決結果。
值得注意的是檢察機關對于該案的態度,甘肅省平涼地區人民檢察分院是以故意殺人罪對孫明亮提起公訴的。這里涉及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罪和故意殺人罪的區分問題,這個問題在司法實踐中本來就是一個十分疑難的問題。在上述兩種情況下,都發生了死亡的結果,因此難以從行為所造成的結果上對這兩種犯罪加以區分。從行為性質上分析,故意傷害與故意殺人當然不同,然而在都造成了死亡結果的情況下,單獨以行為為根據區分兩者,是十分困難的。因而,從主觀心理狀態上區分兩者就具有重要意義。就傷害行為和殺人行為而言,當然都是故意的。故意殺人罪是在殺人故意支配下所實施的致使他人死亡的行為。故意傷害致人死亡則屬于結果加重犯,即行為人對傷害行為是故意的,但對死亡結果是出于過失。因此,對死亡結果到底是故意還是過失,就成為兩者區分的關鍵所在。
從該案的情況來看,死者郭鵬祥叫來九人,可以說是人多勢眾,且郭鵬祥還手持半塊磚頭,對孫明亮和蔣小平進行圍打,將兩人逼到墻角的垃圾堆上。面對郭鵬祥的毆打,孫明亮拿出隨身攜帶的彈簧刀,對繼續撲打的郭鵬祥胸部刺了一刀,致其死亡。在這種情況下,孫明亮對其持刀反擊行為會造成的傷害結果具有故意,這是沒有問題的。然而,對于郭鵬祥死亡結果卻不能認為就是故意的。因為雖然孫明亮所刺部位是郭鵬祥的胸部,但在當時緊急狀態下,孫明亮對于所刺部位沒有選擇的余地。所以,對于孫明亮的行為認定為故意傷害是較為穩妥的。基于“嚴打”的背景,檢察機關將該案認定為故意殺人,其理由是孫明亮在打架斗毆中,對用刀刺人會造成被刺人死亡或者受傷的后果是清楚的,但在其主觀上對兩種后果的發生,均持放任的態度。在這種情況下,是定(間接)故意傷害罪還是(間接)故意殺人罪,應以實際造成的后果來確定。鑒于郭鵬祥已死亡,應定(間接)故意殺人罪。第一審判決對孫明亮定(間接)故意傷害罪不當。在這一理由中,涉及對“用刀刺人會造成被刺人死亡或者受傷的后果是清楚的”這一主觀心理事實的認定。只有在該事實得以認定的前提下,才能得出“在其主觀上對兩種后果的發生,均持放任的態度”的結論。然而,檢察機關對于孫明亮在捅刺時是有意識地選擇胸部還是在打斗過程中無意刺中胸部,并沒有進行充分的論證。在這種情況下,將孫明亮的捅刺行為認定為故意殺人罪是存在疑問的。檢察機關不僅指認該案定罪錯誤,而且還指稱該案量刑畸輕,認為孫明亮持刀致人死亡,造成嚴重后果,無論以故意傷害罪還是故意殺人罪,判處有期徒刑15年均屬量刑失之于輕。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對我國刑法第134條作了補充,規定對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的,可以在刑法規定的最高刑以上處刑并可直至判處死刑,其精神在于對持刀行兇者,要予以嚴懲。1979年我國刑法第132條對故意殺人罪處刑規定的精神是:故意殺人的,首先應考慮處死刑,其次是無期徒刑,然后才是有期徒刑。因此,對孫明亮判處15年有期徒刑,不符合上述法律規定的精神。也就是說,對孫明亮無論是認定為故意傷害罪還是故意殺人罪,只判15年有期徒刑都失之于輕,因而提出抗訴。
甘肅省高級人民法院依照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第二審程序對該案進行審理過程中,發現第一審判決適用法律有錯誤。與此同時,甘肅省人民檢察院調卷審查平涼地區人民檢察分院的抗訴,并于1985年1月28日經檢察委員會討論,認為:孫明亮的行為屬于防衛過當,第一審判處15年有期徒刑失之于重;平涼地區人民檢察分院以定罪不準、量刑失輕為由抗訴不當,決定依照1979年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2款的規定,向甘肅省高級人民法院撤回抗訴。由此可見,甘肅省人民檢察院認為本案具有防衛性質,構成防衛過當。
在抗訴撤回后,第一審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甘肅省高級人民法院依照1979年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49條第2款的規定,決定提審該案。1985年3月27日經該院審判委員會討論,認為第一審判決對孫明亮行為的性質認定和在適用刑罰上,均有不當。孫明亮及其友蔣小平路遇郭鵬祥等人在公共場所對少女實施流氓行為時,予以制止,雖與郭鵬祥等人發生爭執,蔣小平動手打了郭鵬祥一拳,但并非流氓分子之間的打架斗毆,而是公民積極同違法犯罪行為作斗爭的正義行為,應予以肯定和支持。郭鵬祥等人不聽規勸,反而糾結多人攔截孫明亮和蔣小平進行報復,其中郭小平手持磚塊與同伙一起助威,郭鵬祥主動進攻,對蔣小平實施不法侵害。蔣小平挨打后,與孫明亮退到垃圾堆上,郭鵬祥仍繼續撲打。孫明亮在自己和蔣小平已無退路的情況下,為了免遭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持刀進行還擊,其行為屬正當防衛,是合法的。然而,由于郭鵬祥是徒手實施不法侵害,郭小平手持磚頭與同伙一起助威,孫明亮在這種情況下,持刀將郭鵬祥刺傷致死,其正當防衛行為超過必要的限度,造成不應有的危害后果,屬于防衛過當,構成故意傷害罪。依照1979年我國刑法第70條第2款的規定,孫明亮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應當在1979年我國刑法第134條第2款規定的法定刑以下減輕處罰。第一審判決未考慮這一情節,量刑畸重,應予糾正。據此,甘肅省高級人民法院判決撤銷第一審判決,以故意傷害罪改判被告人孫明亮有期徒刑2年,緩刑3年。顯然,甘肅省高級人民法院也同意甘肅省人民檢察院的意見,認為該案應當認定為防衛過當。通過再審程序,該案的原判決得到糾正。孫明亮的刑期從15年有期徒刑改為2年有期徒刑,并且適用緩刑。從這一判決結果來說,相對原判決的結果已經發生重大變化。尤其是甘肅省高級人民法院的判決認定孫明亮和蔣小平對郭鵬祥進行反擊的行為具有防衛性質,由此而使兩人的行為獲得了法律的肯定性評價。
對于該案,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1985年6月5日第226次會議,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第11條第1款的規定,在總結審判經驗時認為:“對于公民自覺地與違法犯罪行為作斗爭,應當予以支持和保護。人民法院在審判工作中,要注意把公民在遭受不法侵害而進行正當防衛時的防衛過當行為,與犯罪分子主動實施的犯罪行為區別開來,做到既懲罰犯罪,又支持正義行為。甘肅省高級人民法院對該案的提審判決,正確認定了孫明亮的行為的性質,且適用法律得當,審判程序合法,可供各級人民法院借鑒。”因此,該案被作為具有指導性的案例刊登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報》1985年第2期。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對甘肅省人民法院對孫明亮的判決結果進行了充分的肯定,就其將普通犯罪糾正為具有防衛性質而言,這當然是正確的,這也是在當時全國性“嚴打”的特殊背景下所能取得的最好結果。尤其值得肯定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提出“對于公民自覺地與違法犯罪行為作斗爭,應當予以支持和保護。人民法院在審判工作中,要注意把公民在遭受不法侵害而進行正當防衛時的防衛過當行為,與犯罪分子主動實施的犯罪行為區別開來,做到既懲罰犯罪,又支持正義行為”。應該說,這一對待正當防衛的態度是完全正確的。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對該案的總結,既有將正當防衛視為與違法犯罪行為做斗爭這一具有政治和政策高度的司法理念,又有正確區分正當防衛和防衛過當的司法準則。
然而,從刑法理論分析,該案仍然錯誤地將正當防衛認定為防衛過當。這里涉及正當防衛必要限度的判斷,就該案而言,如果肯定孫明亮和蔣小平的行為具有見義勇為,甚至是和違法犯罪行為做斗爭的性質,則將孫明亮的行為認定為防衛過當,也不能不說是對防衛人的苛求。該案主要涉及正當防衛與防衛過當的區分。孫明亮和蔣小平見義勇為反遭侵害人的群體性圍打,對方人數達九人之多,并且將孫明亮和蔣小平圍逼在墻角。因此,從人數和攻勢來說,顯然是對方占優勢。在該案中,郭鵬祥手持磚頭對孫明亮進行毆打,在這種情況下孫明亮取出彈簧刀進行還擊。因此,從武器上來說,兩者具有一定的對等性。孫明亮的刀具是作為郊區的菜農為防身而隨身攜帶的,具有不可選擇性。如果從防衛行為和侵害行為基本相適應的傳統觀點判斷是否超過正當防衛的必要限度,也不能認為孫明亮的防衛行為就已經構成防衛過當。如果從客觀需要說,只要是為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的強度,就應當認為沒有超過正當防衛的必要限度。應該說,孫明亮故意傷害案的最終處理結果雖然具有象征意義,但還是未能準確地區分正當防衛和防衛過當。正當防衛司法規則的建立可謂艱難曲折。
孫明亮故意傷害案雖然只是關于正當防衛認定的司法個案,它還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司法機關在鼓勵公民采用正當防衛與違法犯罪行為做斗爭上存在較大問題。因此,在1997年我國刑法修訂過程中,立法機關對正當防衛的規定作了以下兩點修改。第一,將防衛過當的規定從1979年我國刑法的“超過正當防衛的必要限度造成不應有的危害”修改為“明顯超過正當防衛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這就放寬了正當防衛的限度條件。第二,增設了無過當防衛制度,對于嚴重侵害人身權利的暴力犯罪進行正當防衛的,即使造成重傷、死亡的后果,也不屬于防衛過當,不負刑事責任。這就使公民可以放心大膽地進行防衛,不會受到刑事追究。無限防衛權的立法在我國刑法學界存在一定的爭議,我國學者對無限防衛權的法律規定提出了防衛權可能被濫用的擔憂。他們指出:“刑法既然允許防衛者在受到暴力侵害時可以不受防衛限度的約束,也即防衛者可以在防衛反擊時毫無顧忌,這實際上放棄了對防衛者的責任要求,走向防衛者只享有防衛權,不承擔防衛后果責任的極端。立法的這種規定有可能造成防衛者對防衛權的濫用。不僅如此,有些不法分子還可在防衛挑撥后,借口無限防衛而將對方置于死地。無限防衛權變成了某些犯罪人實現非法目的的手段。這恐怕是立法者所始料不及的。”(3)盧勤忠:《無限防衛權與刑事立法思想的誤區》,《法學評論》1998年第4期。這種擔憂完全是多余的,因為法律雖然做了修改,但司法機關對于正當防衛的認定卻依然如故,對于正當防衛案件的處理仍然束手束腳,立法者鼓勵公民正當防衛的初衷沒有得到落實。尤其是近些年來,雖然在司法實踐中也存在處理結果較恰當的正當防衛案件,然而不得不說大多數案件的處理并不符合民眾的期待。這就形成超前的正當防衛立法和滯后的正當防衛司法之間的鮮明反差。
正當防衛是刑法規定的不構成犯罪的情形,不僅如此,在正當防衛中,除了保護本人權益的防衛以外,還包括某些為保護他人權益而實施的正當防衛,這種正當防衛具有見義勇為的性質。把這些見義勇為的行為認定為犯罪,明顯挫傷了公民見義勇為的積極性,并且混淆了罪與非罪的界限。在司法實踐中,幾乎每一起正當防衛案件都會發生爭議,發生在2016年的楊建偉、楊建平故意傷害案,就是一個典型案例。
【案例2 】楊建偉、楊建平故意傷害案。2016年2月28日13時許,在武漢市武昌區楊園街,楊建偉(51歲)、楊建平(55歲)住所門前,遇彭某某遛狗路過,因楊建平摸了彭某某所牽的狗,雙方為此發生口角,彭某某當即揚言去找人報復。楊建偉、楊建平便返回家中將尖刀藏在身上。10分鐘后,彭某某邀約黃某、熊某某等人持洋鎬把至楊建偉、楊建平住所報復,雙方相遇發生打斗。其間,被告人楊建偉、楊建平分別持尖刀朝彭某某的胸腹部猛刺數刀,致使彭某某因失血過多而死亡,并將黃某、熊某某刺傷。2017年2月7日,武漢市武昌區人民法院一審判決認定,被告人楊建偉持刀猛刺彭某某的胸腹部數刀,手段較為殘忍,對致被害人死亡后果負有主要責任,其行為已不屬于僅為制止對方的不法侵害情形。楊建平系在看到楊建偉被打的情況下出手幫忙而持刀對被害人進行傷害,不存在自己面臨他人的不法侵害情形,其行為亦不符合防衛過當的法律特征。辯護人關于被害人有重大過錯,應減輕被告人罪責的辯護意見,一審判決認為,正因為被害人彭某某存在過錯,該案在定性及確定審判管轄時已作減輕處罰考慮。武漢市武昌區人民法院判決如下:楊建偉犯故意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15年,楊建平犯故意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11年,兩人共同賠償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經濟損失56萬余元。
楊建偉、楊建平故意傷害案發生在孫明亮故意傷害案的32年之后,其間,1997年我國對正當防衛的法律規定進行了修改,設立了無過當防衛制度。然而,對正當防衛的司法而言,并未有所改善。
楊建偉、楊建平故意傷害案的一審判決涉及正當防衛認定的兩個問題,第一是楊建偉是否存在防衛起因,即楊建偉的行為是認定為對彭某某的防衛行為還是互毆行為;第二是楊建平在看到楊建偉被打的情況下出手幫忙而持刀對被害人進行傷害,是否就不能成立正當防衛。對于這兩個問題,一審判決都做了否定的回答。
對于第一個問題,一審判決將該案的性質認定為“打斗”。這里雖然沒有使用“互毆”一詞,但打斗的性質等同于互毆,即相互之間的打斗。打斗只是客觀地描述了雙方之間發生的暴力沖突,而并沒有對該暴力沖突的性質進行界定,這實際上就否定了楊建偉行為的防衛性。對此,楊建偉辯護人認為,楊建偉面對彭某某一伙人的不法侵害,出于對胞兄楊建平人身安危的防衛動機,對找上門挑起事端的彭某某實施了自衛,其行為明顯是在人身遭受緊迫危險情勢下所為的私力救濟,具有天然合理的正當性。應該說,這一辯護具有充分的法律根據。從該案的具體案情來看,一審判決已經認定彭某某邀約黃某、熊某某等人持洋鎬把至楊建偉、楊建平住所報復,面對這種報復,楊建偉在其人身受到侵害的情況下,采用事先準備的尖刀進行反擊,這難道不具有防衛性嗎?
對于第二個問題,一審判決亦存在值得商榷之處。楊建平辯護人認為,楊建平看見胞弟被人打倒在地,頭破血流,洋鎬把都打斷了,為了解救弟弟,且對方人多勢眾年富力強,楊建平的行為屬于依法行使無限防衛權。然而,一審判決卻認為楊建平系在看到楊建偉被打的情況下出手幫忙而持刀對被害人進行傷害,不存在自己面臨他人的不法侵害情形,其行為亦不符合防衛過當的法律特征。按照這個邏輯,只有本人受到不法侵害才能實行正當防衛,如果是他人受到不法侵害就不能進行正當防衛。這一結論明顯和法律規定相違背。我國刑法第20條第1款規定,為了使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和其他權利免受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的,都可以實行正當防衛。為保護國家、公共利益實行的正當防衛具有與犯罪行為做斗爭的性質,為保護他人的人身、財產和其他權利實行的正當防衛具有見義勇為的性質,這都是法律所肯定的,卻被一審判決認定為犯罪。從這個案件的一審判決可以看出,我國司法機關某些人員對正當防衛的法律規定可以說是達到了十分欠缺的程度。
一審判決后,楊建偉、楊建平以及彭某某家屬均提出上訴。2017年4月5日和5月26日,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此案進行二審。二審判決認為,楊建偉、楊建平犯故意傷害罪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撤銷武昌區人民法院的一審判決,發回該院重新審理。2018年5月11日,武昌區人民法院進行重審后認為,楊建平、楊建偉犯故意傷害罪的犯罪事實成立,分別判處9年和13年有期徒刑。兩人再次當庭上訴。12月19日,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終審判決認為,楊建偉持刀捅刺彭芳明等人,屬于制止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其行為具有防衛性質;其防衛行為是造成一人死亡、二人輕微傷的主要原因,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構成故意傷害罪,依法應負刑事責任。上訴人楊建平為了使他人的人身權利免受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制止不法侵害的行為,對不法侵害人造成損害,屬于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楊建偉的行為系防衛過當,具有自首情節,依法應當減輕處罰,原審判決審判程序合法,認定基本事實清楚,對楊建偉定罪準確。然而,原審判決未認定楊建偉屬于防衛過當、楊建平屬于正當防衛,系適用法律錯誤,應依法予以糾正。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如下:撤銷湖北省武漢市武昌區人民法院(2017)鄂0106刑初804號刑事判決;上訴人(原審被告人)楊建偉犯故意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4年;上訴人(原審被告人)楊建平無罪。
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的終審判決糾正了原一審判決關于楊建平不存在自己面臨他人的不法侵害情形,因此不構成正當防衛,當然也就不存在防衛過當的結論,認為楊建平為了使他人的人身權利免受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制止不法侵害的行為構成正當防衛,這是完全正確的。對于楊建偉的行為雖然認定為具有防衛性質,但認為構成防衛過當,該判決結果還是將正當防衛混同于防衛過當。楊建偉面對彭芳明等多人使用兇器實施的暴力犯罪,楊建偉為保護本人的人身權利免受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進行反擊,這一行為完全符合我國刑法第20條第3款的無過當防衛的構成條件,即使是楊建偉面對彭芳明等人手持洋鎬的暴力侵害,終審判決仍然拒絕適用我國刑法第20條第3款的無過當防衛之規定。由此可見,正確處理一起正當防衛案件,即使是在輿論的壓力之下,仍然步履維艱。社會上出現這樣一種調侃的說法:面對不法侵害,防衛人處于“打輸了住院,打贏了坐牢”的兩難窘境。
綜上所述,在目前我國司法實踐中,對正當防衛制度的適用沒有嚴格遵循立法精神,對正當防衛和防衛過當未能依法認定。當個別案件經過媒體曝光以后,社會輿論普遍同情防衛人。因為正當防衛案件涉及倫理道德和是非觀念,所以基于心同此理的公眾意見,對此類案件的認知具有正當性和合理性,值得司法機關高度重視。雖然司法機關回應公眾關注,對這些案件做了改判,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社會公正觀念,但每一次改判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司法公信力。
二、正當防衛司法理念的更新
正當防衛的司法偏差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司法的公平性,也不利于鼓勵公民利用正當防衛的法律武器維護本人或者他人的權益,因此需要認真對待。
這里首先涉及對正當防衛性質的正確認識。正當防衛是一項較為特殊的刑法制度。刑法屬于制裁法,因而刑法所規定的犯罪行為都是法律禁止的行為,從這個意義上說,刑法規范具有禁止規范的屬性。然而,正當防衛恰恰是一個例外,它是授權規范。正當防衛又不同于一般的授權規定,它是在特定條件下的授權規范。對于正當防衛的合法化根據,在大陸法系刑法理論中存在兩種觀點,這就是自我保護理論和法確證理論。有德國學者指出,自我保護理論只允許為保護個人的利益而行使正當防衛權,體現了不能夠為保護公共秩序或者法秩序本身而行使的立場。因此,維護法秩序的公共利益,只能夠通過保護個人權利這一媒介加以實現。(4)參見[德]漢斯·海因里希·耶賽克、托馬斯·魏根特:《德國刑法教科書(上)》,徐久生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450頁。如果嚴格遵循保護個人理論,則正當防衛的范圍是較為狹窄的,甚至為保護他人利益的正當防衛都不被承認。法確證理論則允許為維護法秩序而進行正當防衛。例如意大利存在一種斗爭需要理論,認為正當防衛是與犯罪作斗爭的需要。(5)參見[意]杜里奧·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學原理(注評版)》,陳忠林譯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3頁。這里的斗爭需要說顯然是從維護法秩序的角度揭示正當防衛根據的,由此而賦予正當防衛更多的社會價值。上述兩種理論不能說是對立的,它們實際上是互相補充的。正如意大利學者所言,如果僅使用自我防衛說,很難解釋為了救助第三人而實施的防衛行為。如果僅使用斗爭需要說,則不僅無法說明為什么無罪過的侵害,也可以成為防衛行為的對象,也不能解釋為什么正當防衛不能超過必要的限度。(6)參見上注,第173頁。從歷史的眼光來看,正當防衛的根據存在一個從以個人本位的自我保護理論向法確證理論傾斜的過程。當然,在現實生活中絕大多數都是為保護個人利益的正當防衛,因此自我保護理論還是占優勢的。
我國刑法對于正當防衛的規定具有鮮明的特點,這主要體現在對正當防衛的目的的規定上。正當防衛的目的對于理解我國刑法中正當防衛的性質和根據,具有重要指導意義。根據我國刑法第20條第1款的規定,正當防衛的目的是為了使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和其他權利免受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根據這一規定,我國刑法中的正當防衛從防衛目的上可以區分為三種類型:第一,保護國家、公共利益的正當防衛;第二,保護本人權利的正當防衛;第三,保護他人權利的正當防衛。由此可見,我國刑法明確地把保護國家和公共利益的行為規定為正當防衛,由此而使我國刑法中的正當防衛具有十分明顯的和違法犯罪行為作斗爭的性質。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國刑法中的正當防衛還包括職務正當防衛,這就是人民警察在執行職務過程中實施的正當防衛。在其他國家刑法理論中一般都界定為執行職務的行為而不是歸之于正當防衛。這一點,是我國刑法和其他國家刑法的主要區別之所在。在其他國家刑法理論中,違法阻卻事由可以分為法定的違法阻卻事由和非法定的違法阻卻事由。正當防衛和緊急避險都是法定的違法阻卻事由,執行職務的行為在有些國家刑法有規定,因而也是法定的違法阻卻事由,在有些國家刑法則沒有規定,屬于非法定的違法阻卻事由。例如,《日本刑法典》第35條規定:“基于法令或者正當業務的行為,不處罰。”這里的法令行為,是直接基于成文的法律、命令的規定,作為權利或者義務所實施的行為。(7)[日]大塚仁:《刑法概說(總論)》(第三版),馮軍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401頁。法令行為又可以進一步區分為以下三種:第一種是職權(職務)行為;第二種是從政策理由排除違法性的行為;第三種是由法令引人注意地明示了違法性的行為。上述第一種就是中國研究者所稱的執行職務的行為。因此,在日本執行職務的行為屬于法定的違法阻卻事由。《德國刑法典》對執行職務的行為并無規定,但在德國刑法教義學中,將基于公務員的職權行為予以合法化。有德國學者指出:“在許多法律中,行使國家強制手段被作為執行不同公務行為的最后手段加以規定。國家機關基于這樣的職權并在該職權范圍內,滿足刑法的構成要件的行為是合法的(例如,故意殺人、傷害、剝奪自由、強制、侵入他人住宅、拆開信箋、破壞財物)。”(8)同前注④,漢斯·海因里希·耶賽克、托馬斯·魏根特書,第528頁。由此可見,在德國刑法中,執行職務的行為屬于非法定的違法阻卻事由。
在1979年我國刑法中,對于執行職務的行為并沒有規定。至1983年9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聯合發布了《關于人民警察執行職務中實行正當防衛的具體規定》(以下簡稱:《具體規定》),為職務上的正當防衛認定提供了規范根據。在1997年我國刑法修訂過程中,對于是否在刑法中規定職務上的正當防衛存在爭議。立法機關認為,對于人民警察依法執行職務的行為,1983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等五單位聯合發布的《具體規定》中有過類似規定,但其中所列必須采取正當防衛的情形,大多屬于人民警察依法執行職務的行為,與正當防衛行為有所不同。為了加強對人民警察依法執行職務行為的保護力度,避免將這類行為與正當防衛行為混同,《刑法修訂草案》曾兩次設專條作了規定。經八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審議,認為“人民警察依法執行職務,受法律保護”,我國《人民警察法》有明確規定。對于人民警察在執行職務中,在什么情況下依法使用警械、武器不承擔責任,違法使用警械、武器要承擔責任,《人民警察法》和《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條例》也都已有規定,這個問題可以不在刑法中另做規定,因而刪去了刑法草案提出的這一條規定。(9)參見周道鸞等主編:《刑法的修改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80~81頁。由此可見,立法機關傾向于認為人民警察依法使用警械和武器制止正在進行的違法犯罪行為,是執行職務的行為而不是正當防衛,但對此在刑法中沒有規定,而我國《人民警察法》等的規定只是對職務行為的實體和程序的規定,并沒有涉及對該行為的定性。并且,《具體規定》沒有廢止,仍然有效。因此,我國刑法中的人民警察執行職務的行為仍然屬于正當防衛的范疇。在司法實踐中,存在職務上的正當防衛案例,例如張磊職務正當防衛過當案。(10)參見陳興良:《張磊職務正當防衛過當案的定罪與量刑》,載陳興良主編:《刑事法判解(第15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54~62頁。當然,考慮到職務上的正當防衛具有其特殊性,在具體認定的時候,還要參照其他的法律或者法規。例如,涉及使用槍支的正當防衛,就需要參照有關人民警察使用槍支的相關規定,才能正確地認定職務上的正當防衛。應當指出,我國刑法中的正當防衛雖然可以分為保護國家和公共利益的正當防衛、保護本人利益的正當防衛和保護他人利益的正當防衛這三種類型,但在現實生活中絕大多數正當防衛還是屬于保護個人利益的正當防衛,保護國家和公共利益的正當防衛則較為罕見,當然也存在見義勇為的正當防衛。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國法上正當防衛的范圍是極為寬泛的,立法機關對正當防衛采取了積極鼓勵的態度。因此,我國司法機關對于正當防衛的理念應當及時更新。
我國刑法第1條明確將“懲罰犯罪,保護人民”作為刑法的立法目的。其實,“懲罰犯罪,保護人民”不僅是刑法的立法目的,而且也是刑法的司法目的,對于司法活動就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懲罰犯罪和保護人民是不可分離的兩部分內容,刑法目的在于:在采用刑罰手段懲罰犯罪的同時,還要有效地保護人民。因此,在司法活動中,不能片面地強調懲罰犯罪,而且還要時刻銘記保護人民的根本宗旨。正確地認定正當防衛,就是刑法保護人民的生動體現。在正當防衛案件處理中,司法機關實際上是在保護刑法賦予公民的防衛權。如果把正當防衛混同于犯罪,就是侵犯了公民的防衛權。只有從這個高度看待正當防衛制度,才能在司法活動中妥善處理正當防衛案件。因此,正確處理懲罰犯罪和保護人民的關系,對于糾正正當防衛的司法偏差具有重要意義。在涉及正當防衛案件的處理過程中,如果僅僅根據致人重傷、死亡的結果定罪,而不問造成這一結果的起因,就會導致司法判決“不分是非”,其結果必然是既不能獲得辦案的法律效果,同時也不能獲得辦案的社會效果。司法活動當然是一種法律適用活動,但司法機關也并不是機械地適用法律,而是在判決結論中灌注公正和合理的社會倫理觀念,由此使判決獲得公眾的認同。這樣的判決就必須首先分清是非。在涉及正當防衛案件中,分清是非就表現在法律支持和鼓勵正當防衛而懲治不法侵害。如果公民面對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實行正當防衛,造成侵害人的傷亡結果,司法機關根本就不認定其具有防衛性質,而是簡單地判決防衛人對傷亡結果承擔刑事責任,這就在案件處理結果中沒有體現是非曲直。
【案例3】趙宇過失致人重傷案。2018年12月26日晚23時許,李華與鄒過濾酒后一同乘車達到鄒過濾位于福州市晉安區岳峰鎮村榕城公寓4樓C118的暫住處。兩人在鄒過濾暫住處發生爭吵,李華被鄒過濾關在門外,便酒后滋事,用力踢踹鄒過濾暫住處防盜門,強行進入房間與鄒過濾發生肢體沖突,引來鄰居圍觀。此時,暫住在該樓5樓C219單元的趙宇,聽到叫喊聲,下樓查看,見李華把鄒過濾摁在墻上并毆打其頭部。為制止李華的傷害行為,趙宇從背后拉拽李華,兩人一同摔倒在地。起身后,李華揮拳打了趙宇兩拳,趙宇隨即將李華推倒在地,并朝倒地的李華腹部踹了一腳。后趙宇拿起房間內的凳子欲砸向李華,被鄒過濾攔下,隨后趙宇被其女友勸離現場。李華被踢中腹部后橫結腸破裂,經法醫鑒定,李華傷情屬于重傷二級。鄒過濾傷情屬于輕微傷。2019年2月20日,福州市公安局晉安分局以趙宇涉嫌過失致人重傷罪向晉安區人民檢察院移送起訴。2019年2月21日,晉安區人民檢察院以防衛過當做出相對不起訴決定。2019年3月1日,在最高人民檢察院指導下,福建省人民檢察院指令福州市人民檢察院對該案進行了審查,經審查認為,趙宇的行為屬于正當防衛,不應當追究刑事責任,原不起訴決定書認定防衛過當屬適用法律錯誤,依法決定予以撤銷,依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7條第1款規定,并參照最高人民檢察院2018年12月發布的第十二批指導性案例,對趙宇作出絕對不起訴決定。
趙宇故意傷害案從公安機關認定為普通犯罪,即過失致人重傷罪,到晉安區人民檢察院認定為防衛過當,作出相對不起訴決定,最后再到福州市人民檢察院認定為正當防衛,作出絕對不起訴決定,可謂一波三折。然而,這并不是正常司法程序的結局,而是最高人民檢察院介入的結果。趙宇過失致人重傷案反映了我國司法機關在正當防衛認定上的兩個難點問題,這就是如何區分正當防衛與普通犯罪以及如何區分正當防衛和防衛過當。
趙宇的行為明顯具有見義勇為的性質,且具有制止李華的不法侵害的目的。否則的話,趙宇完全可以袖手旁觀。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趙宇之所以介入該案,是為了制止李華的不法侵害。如果李華就此罷手,也就不會有此后案情的進一步發展。趙宇將李華拉拽致使李華倒地以后,李華起身轉而對趙宇毆打。此時,趙宇為鄒過濾解圍,但卻受到李華對本人的不法侵害。趙宇當然沒有束手挨打的義務,因而將李華推倒在地,并朝李華腹部踹了一腳。正是這一腳導致李華腹部橫結腸破裂,由此造成重傷后果。總之,趙宇在該案中的行為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其中,第一階段的行為明顯具有制止李華對鄒過濾的不法侵害的防衛性質,對此沒有爭議,第二階段的行為如何認定,則容易產生分歧意見。其主要爭議在于:在制止了李華對鄒過濾的不法侵害以后,趙宇和李華發生扭打,此種不法侵害是否還正在進行?對鄒過濾的不法侵害因為趙宇的及時制止已經結束,然而,李華又對趙宇進行毆打,形成對趙宇的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趙宇的行為就轉化為制止李華對趙宇本人的不法侵害,同樣具有防衛性質。因此,公安機關對趙宇的行為沒有認定為具有防衛性質,是對該案的定性錯誤。
那么,趙宇的防衛行為是否明顯超過了正當防衛的必要限度呢?從該案情況來看,在面對李華毆打的情況下,趙宇將李華拽倒在地并踹其一腳,行為本身不能認定是明顯超過正當防衛必要限度的,因此不存在行為過當。就該行為造成的重傷結果而言,確實具有一定的嚴重性。在李華沒有明顯要重傷趙宇的情況下,這個重傷結果是超過必要限度的。然而,這個重傷結果并不是趙宇主觀上故意追求的,而是過失造成的結果。在李華進行不法侵害而受到趙宇防衛的情況下,這一結果屬于李華應當承受的不利后果。綜上所述,筆者認為趙宇的行為不構成防衛過當,不應當承擔過失致人重傷罪的刑事責任。
從趙宇過失致人重傷案的處理過程可以看出,對于這樣一起簡單的正當防衛案件,司法機關之間還是存在較大的意見分歧。這涉及司法理念的問題,并且涉及司法機關內部的案件考評機制。
在正當防衛問題上還涉及如何對待暴力的國家壟斷問題。暴力可以分為非法暴力和合法暴力。在任何一個法治社會,只有國家權力機關才能依法實施暴力,這是一種合法暴力。非法律授權的私人暴力是違法的,被法律所禁止。因此,國家具有對暴力的壟斷權。然而,正當防衛是國家暴力壟斷的例外。在公民受到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的情況下,法律賦予公民防衛權,這種防衛權就是一種合法暴力,它是對國家暴力的必要補充。在我國司法人員中存在一種擔憂的心理,認為如果允許公民實行正當防衛,尤其是無過當的防衛,就會導致隨意使用暴力的社會后果,形成對公共秩序的破壞。筆者認為,這種擔心是完全沒有必要的,也是沒有根據的。事實上,每個公民都不愿意受到不法侵害因而行使防衛權,只是在迫不得已的緊急狀態下,才進行正當防衛。因此,正當防衛并不是公民主動選擇的,而是面對不法侵害被動實施的,鼓勵公民采用正當防衛保護本人的權益并不會導致暴力泛濫。至于為保護他人權益的正當防衛,具有見義勇為的性質,更是法治社會應當鼓勵的。如果將見義勇為的正當防衛認定為犯罪,則將損害社會公正,從而放縱不法侵害人,這才是對法治的破壞。在我國目前犯罪案件高發,公權力對公民合法權利的保護還不能做到及時有效的情況下,更有必要放寬公民的防衛權,而不是限制公民的防衛權。1997年我國刑法關于正當防衛的規定已經體現了這一點,但司法機關對正當防衛案件的處理則明顯滯后。因此,司法機關應當轉變對正當防衛的認識,只有這樣才能為處理正當防衛案件提供正確理念。
目前在我國司法實踐中,對正當防衛認定存在較大影響的是維穩思維。如果把維穩界定為維護社會秩序,包括公共秩序,這當然是司法活動所追求的正當目的。然而,現在對維穩存在理解上的一定偏差,這就是以涉訟上訪率作為維穩的指標,同時將這種意義上的維穩作為考察司法活動社會效果的重要指標。在正當防衛案件中,不法侵害人因為正當防衛而發生重傷或者死亡的后果,因而成為刑事訴訟中的被害人。如果司法機關將造成其重傷或者死亡的行為認定為正當防衛,則被害人一方往往會無休止地到司法機關纏訟和上訪,有的還會采取擾亂辦公秩序等非法手段向辦案人員和司法機關施加壓力。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司法機關認定正當防衛就會面臨來自各方面的維穩壓力,維穩優于維權遂成慣例。(11)參見陳璇:《正當防衛、維穩優先與結果導向——以“于歡故意傷害案”為契機展開的法理思考》,《法律科學》2018年第3期。為此,司法機關根據重傷或者死亡后果認定為犯罪是最為簡單的結案方式。長此以往,司法機關在維穩思維的指導下處理正當防衛案件,在司法活動中對各方當事人不分是非,只是根據重傷或死亡結果認定犯罪的做法,使正當防衛制度形同虛設。
此外,司法機關內部的案件考評機制對正當防衛案件的處理也帶來較大的負面影響。案件考評機制是指根據辦案結果對辦案人員進行優劣評價,以此作為獎勵和升遷的重要參考指標。在對司法機關辦案人員的具體考核中存在一種傾向,這就是簡單地將對案件改變定性或者改變量刑設定為負面指標,這對辦案人員造成不利后果,也扭曲了公檢法機關之間的關系。例如,公安機關的處理結果如果被檢察機關改變,就會影響公安機關辦案人員的考評績效。同樣,檢察機關的處理結果如果被法院改變,就會影響檢察機關辦案人員的考評績效。在法院內部,如果下級法院的處理結果被上級法院改變,就會影響下級法院辦案人員的考評績效。在這種機制的影響下,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在處理案件時,為了不給他人帶來不利后果,就會互相遷就。因此,公安機關移送起訴的案件,檢察機關做不起訴難;檢察機關起訴的案件,法院做無罪判決難;下級法院判決的案件,上級法院改判難。這極大地影響了各司法部門職能的正常發揮。反映在正當防衛案件的處理上,除非公安機關直接認定為正當防衛而撤案,凡是公安機關移送起訴的,檢察機關認定正當防衛一般都會受到來自公安機關的阻力。因為如果檢察機關認定為正當防衛,就是公安機關辦了錯案。在這種情況下,檢察機關為照顧公安機關,也就不認定為正當防衛,即使認定,也只是認定為防衛過當,這樣就照顧了公安機關的面子。在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的關系上,對正當防衛案件的處理也是如此。因此,目前我國司法機關的案件考評機制不利于正確認定正當防衛。
司法機關的案件考評對于司法業務活動具有導向功能,對于依法辦案具有保障作用。目前司法機關的案件考評機制在指標設置上存在值得商榷之處,對于司法人員依法辦案(包括處理正當防衛案件)帶來消極后果。司法機關的辦案活動包括兩項主要內容,一是查清事實,二是適用法律。在這兩者中,查清事實是前提,只有查清事實才能為正確適用法律奠定基礎。相對來說,事實本身具有客觀性,因而查清事實的標準相對明確。法律適用則分為兩種情形,第一種是簡單案件,這種案件的法律標準明確,法律適用相對簡單;第二種是復雜案件,這種案件往往存在較大爭議,法律標準較為模糊。筆者認為,基層司法機關主要應對案件事實負責。如果出于主觀原因,沒有查清案件事實,在案件考評中應受到消極評價,承擔不利后果。然而,對于法律適用,尤其是復雜案件的法律適用,不同司法人員和不同司法機關之間存在不同看法,這是十分正常的。在這種情況下,就不能因為法律適用結果的改變而對司法人員和司法機關的案件考評產生不利后果。對于爭議案件,應當按照司法程序推進,以有權的司法機關的判斷為最終標準,但被改變處理結果的司法人員和司法機關不能因為處理結果的改變而承擔不利后果,更不能將這種處理結果的改變誤認為是錯案,對于正當防衛案件也是如此。
以趙宇案為例,福州市晉安區公安分局認為構成犯罪,移送檢察機關起訴。晉安區人民檢察院認為趙宇的行為屬于防衛過當,做出相對不起訴的決定。之后,由于最高人民檢察院介入,福州市人民檢察院指令晉安區人民檢察院重新審查,認定趙宇的行為屬于正當防衛,做出絕對不起訴的決定。在這個案件處理過程中,公安機關在查清事實以后,以趙宇犯過失致人重傷罪移送檢察機關起訴,公安機關對趙宇的處理只是一種起訴意見,最終有權決定是否起訴和以何種罪名起訴的是檢察機關。因此,即使檢察機關改變處理結果,也不能認為公安機關辦了錯案。以此類推,由于上級檢察機關的介入,晉安區人民檢察院將相對不起訴改變為絕對不起訴,這也不能認為晉安區人民檢察院辦了錯案。因為根據法律規定,上級檢察機關對下級檢察機關有指導的權限。假如檢察機關將趙宇案起訴到審判機關,審判機關認定為正當防衛,做出無罪判決,也不能認為檢察機關辦了錯案。因為在刑事訴訟程序中,法院具有獨立的審判權,包括對案件判決有罪或者無罪的權力。各個司法機關只要在自身權力范圍內,依法對案件做出處理,即使隨著訴訟程序的推進,案件處理結果被其他司法機關改變,都不能認為被改變處理結果的司法機關對案件處理結果發生錯誤。更何況,我國刑事訴訟法還設置了司法機關之間的制約程序,例如公安機關對檢察機關處理結果的復議、復核權;檢察機關對法院判決的抗訴權等。如果要求下一個程序的司法機關必須維持上一個程序的司法機關的處理結果,那么,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之間只有協同一致的互相配合而沒有互相制約,這就會扭曲其關系。在正當防衛案件處理上,同樣應當糾正這種扭曲的關系,為正當防衛的正確處理提供順暢的司法程序。
三、正當防衛司法規則的形塑
正當防衛構成條件的把握,以及正當防衛和防衛過當的區分,是刑法理論和司法實務中的難題。刑法本身對正當防衛的條件規定較為抽象,類似正當防衛必要限度這樣的授權性規定,要求司法機關根據案件具體情況行使裁量權。正當防衛案件的正確處理,對于司法人員來說,不僅需要具備較高的法律素養,而且要求具備較高的政策水平。而且,正當防衛并不是常見案件,對于某個司法人員來說也許一生只遇到一起正當防衛案件。因此,其對于正當防衛案件的法律界限的把握顯得較為生疏。在這種情況下,正當防衛案件的處理結果不能達到法律和社會的期待,確實具有一定的客觀原因。
正當防衛案件的正確處理,既是司法公正的體現,也是司法機關建立公信力的途徑。在目前我國自媒體日益發達的社會環境中,由于先前正當防衛案件的示范效應,只要正當防衛案件不能得到司法機關的公正處理,相關當事人就會通過媒體曝光的方式尋求社會輿論的聲援,由此對司法機關造成外在壓力。司法機關應當正確化解社會輿論的影響,更應當化被動為主動,依法、合理、公正地辦理正當防衛案件,以此建立并強化司法公信力。
正當防衛的認定與處理是司法人員較為生疏的業務類型,而我國刑法對正當防衛的規定又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在這種情況下,為了指導司法機關辦理正當防衛案件,首先應當加強案例指導。我國已經建立案例指導制度,它能夠為司法活動提供更為細致、更具有可操作性的規則,對于疑難案件的處理尤其具有其他規范性司法解釋無法替代的指導功能。值得肯定的是,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已經發布的指導性案例中,都已經包含了正當防衛案件。例如于歡故意傷害案、劉海明故意傷害案等曾經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的案例都以指導案例的形式公布,對于處理正當防衛和防衛過當案件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此后,還應當結合指導案例,進一步出臺指導性司法文件,總結正當防衛和防衛過當的認定規則,從而明確正當防衛和防衛過當的法律界限,這對于正確處理正當防衛案件必將起到積極作用。筆者認為,對于正當防衛的認定來說,亟待形成以下三種司法規則。
(一)防衛與互毆的區分規則
在正當防衛的認定中,如何區分防衛與互毆是涉及案件是否具有防衛性質的問題,因而具有重要意義。以往在我國刑法實踐中,相當一部分正當防衛案件被認定為普通犯罪。究其原委,就是司法機關未能正確區分防衛與互毆之間的界限。在致人傷亡的案件中,如果僅從客觀上看,其行為已符合過失致人死亡罪或者故意殺人罪的構成要件,只有認定致人傷亡的行為屬于正當防衛,才能阻卻行為的違法性。在正當防衛成立與否的判斷中,先要排除互毆,因而互毆就成為認定正當防衛的重大障礙。
互毆是互相斗毆的簡稱,在正當防衛中討論互毆,主要是為了正確地將防衛與互毆加以區分。在刑法理論上,互毆是指參與者在其主觀上的不法侵害故意的支配下,客觀上所實施的連續的互相侵害的行為。(12)參見陳興良:《互毆與防衛的界限》,《法學》2015年第6期。日本將互毆稱為打架,我國民間也將打架與斗毆相提并論,稱為打架斗毆。日本學者大塚仁在論及打架是否可以成立正當防衛時指出:“在打架的情形中,只要把爭斗者雙方互相攻擊、防御的一系列行為作為整體來觀察,就難于認為一方的行為是不正的侵害、他方的行為是針對它作出的防衛行為。”(13)[日]大塚仁:《刑法概說(總論)》(第三版),馮軍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78頁。日本歷史上流傳下來對打架的法律規制原則是“打架兩成敗”,即對打架雙方都予以否定的法律和道德評價,各打五十大板。日本學者鹽田見對“打架兩成敗”的法理進行了考察,認為“打架兩成敗”的含義是:對打架不問是非對錯,對雙方均施加制裁。鹽田見將“打架兩成敗”的法理歸結為自力救濟的禁止。(14)參見[日]鹽田見:《打架與正當防衛——以“打架兩成敗”的法理為線索》,載陳興良主編:《刑事法評論(第40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295頁。然而,此后日本判例發生轉變。對此,日本學者山口厚指出,判例當初提到了“斗毆各打五十板”,認為就斗毆作為而言沒有容納正當防衛觀念的余地,后來則接受學說的批判,認為有必要觀察斗毆狀況的整體來進行判斷,遂轉移到了肯定斗毆中有適用正當防衛之余地的立場。(15)參見[日]山口厚:《日本刑法總論》(第3版),付立慶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32頁。
我國歷史上雖然也有類似現代刑法中正當防衛的制度,但對于防衛自己(即自衛)卻嚴格加以限制,這就包括對打架無曲直法理的肯定。例如我國法制史學者戴炎輝在論及《唐律》防衛自己的規定時指出:“唐律以請求公力救濟為原則,不許以私力防衛自己。查斗訟律,相毆傷兩論如律,雖后下手理直,亦只減二等。關于后下手理直,疏議說:‘乙不犯甲,無辜被打,遂拒毆之,乙是理直。’惟拒毆而致甲于死者,則不減。乙無辜被打,既是受甲的不法侵害,因而對甲加以反擊,在現代法應是正當防衛,但律不許乙拒甲而予毆擊,只酌情(后下手理直)減刑而已。再查別條:縱使他人以兵刃逼己,因而用兵刃拒他人而予傷殺者,仍依斗傷殺法(只不以故殺論其罪)。”(16)戴炎輝:《中國法制史》,三民書局1979年第3版(臺北),第60頁。由此可見,我國古代法律將自衛等同于互毆而予以禁止。如果造成傷亡后果的,則對雙方都論之以罪,無論有理無理,這也就是“打架無曲直”。這種法律規定表現為重視社會秩序維護而輕視人身權利保護的法理,它是社會本位的法律觀念的征表。德國學者曾經明確提出這樣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究竟應當如何解決公民自身防衛的權限與既存的現代社會秩序,以及與國家的專有的法律保護權之間的矛盾。(17)同前注④,漢斯·海因里希·耶賽克、托馬斯·魏根特書,第528頁。可以看出,我國司法機關對于防衛與互毆的混淆,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國歷史上嚴厲禁止自我防衛觀念的遺痕,與當今法治社會的理念可以說是格格不入的。這里應當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區分互毆和防衛。如果確實構成互毆,當然應當對雙方都進行懲罰,但如果一方是不法侵害,另一方是正當防衛,則應當對防衛人進行保護。因此,防衛與互毆的區分實際上是對案件的是非之分。筆者認為,防衛與互毆的區分應當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考察。
其一,互毆以事先預謀或者臨時合意為成立要件。互毆從客觀上來看,表現為雙方之間的互相毆打,并且雙方具有毆打的故意。然而,僅此還不能正確地區分防衛與互毆,還要考察行為人是否具有事先預謀或者臨時合意。這里應當指出,互毆的預謀和合意在其內容上不同于毆打的故意,對此需要加以區分。毆打是單方面的行為,即一方對另一方進行人身侵害,因而毆打的故意是指對他人實施人身侵害的主觀心理狀態。互毆是相互之間的毆打,因此雙方具有互相毆打的主觀心理狀態。如果雙方事先約定在某個時間、某個地點進行互相毆打,這就具有事先預謀,因而應當將其互相毆打行為認定為互毆。此外,雖然沒有事先預謀,而是在現場發生沖突,雙方臨時合意進行互相毆打,這就具有臨時合意,因而應當將其互相毆打行為認定為互毆。如果雙方雖然進行毆打,但雙方既沒有事先預謀,又沒有臨時合意,則不能認定為互毆并以此否定防衛的存在。
其二,在沒有事先預謀和臨時合意的情況下,先動手一方理虧,具有不法侵害的性質,后動手一方理直,具有防衛的性質。互毆都是由糾紛或者口角引發的,在發生糾紛或者口角的情況下,我國民間存在“君子動口不動手”的規則。率先動手的一方,明顯違反該規則。面對他方的動手,另一方如何應對。逃跑當然不失為上策,然而并不是每一個人面對他人的毆打都會選擇逃跑,并且在某些緊急狀態下,根本來不及逃跑。因而,對他人的毆打進行還擊,就成為面對毆打的應對措施,這完全符合人性。如果一次性反擊就制止了對方的侵害,當然也就不會混同于互毆。然而,如果面對反擊,侵害人再進一步進行毆打,由此就形成雙方互相打斗的狀態,因而在客觀上類似于互毆。筆者認為,在對方首先發難進行打斗的情況下,他方的反擊行為應當認定為防衛。這種防衛性質并不因為打斗的延續而改變,即使存在多輪相互的打斗,仍然應當根據先動手與后動手的順序對行為的性質進行判斷,而不能僅僅根據客觀上所呈現的互相打斗的事實,就將雙方行為整體認定為互毆。
其三,在后動手一方的防衛中,如果造成先動手一方的死亡結果的,應當根據具體案情判斷是否超過正當防衛必要限度。先動手和后動手,在法律上加以不同的評價,對于認定案件的性質具有重要意義。如果先動手一方對后動手一方造成傷亡結果,則先動手一方應當承擔故意傷害罪或者故意殺人罪的刑事責任。如果后動手的一方對先動手的一方造成傷亡結果,應當先肯定其行為的防衛性,然后再進行是否超過正當防衛必要限度的判斷。
(二)反殺案的處理規則
反殺的原意是指報殺人之仇而殺人。《周禮·地官·調人》有這樣的描述:“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鄭玄注曰:“反,復也;復殺之。”賈公彥疏曰:“謂既殺一人,其有子弟復殺之。”在這個意義上,反殺就是復仇殺人。現在,反殺的含義演變為將準備要擊殺自己的敵方擊殺的行為,即反而殺之。在這種反殺的情況下,他方先實施對己方的殺人行為,行為人在反擊中將他方殺死,尤其是奪取他人的兇器將他人殺死。現在需要討論的是在反殺的情形中,反殺行為是否構成正當防衛。反殺行為具有以殺對殺的性質,這本身就包含了某種防衛性。爭議的問題在于:奪取他人兇器進行反殺,是否具備防衛時間;如果不具備防衛時間,則這種反殺就不能成立正當防衛。因此,在反殺案件中,是否構成正當防衛的判斷就在于不法侵害是否已經終止。
【案例4】于海明故意傷害案。2018年8月27日21時30分許,于海明騎自行車在昆山市震川路正常行駛,劉某醉酒駕駛小轎車向右強行闖入非機動車道,與于海明險些碰擦。劉某的一名同車人員下車與于海明爭執,經同行人員勸解返回時,劉某突然下車,上前推搡、踢打于海明。雖經勸解,劉某仍持續追打,并從轎車內取出一把砍刀(系管制刀具),連續用刀面擊打于海明頸部、腰部、腿部。劉某在擊打過程中將砍刀甩脫,于海明搶到砍刀,劉某上前爭奪,在爭奪中于海明捅刺劉某的腹部、臀部,砍擊其右胸、左肩、左肘。劉某受傷后跑向轎車,于海明繼續追砍2刀均未砍中,其中1刀砍中轎車。劉某逃離后,倒在附近綠化帶內,后經送醫搶救無效死亡。
該案也被稱為昆山反殺案。因為現場的攝像鏡頭正好將案發過程記錄下來,影像在媒體上流傳以后,反殺過程的畫面清晰地呈現在公眾面前。因為是死者劉某首先持刀追砍于海明,對此進行的防衛屬于我國刑法第20條第3款規定的無過當防衛,對此沒有異議。關鍵在于:于海明搶到砍刀,劉某上前爭奪,在爭奪中于海明捅刺劉某,造成劉某傷害。劉某受傷后跑向轎車,于海明繼續追砍2刀均未砍中。那么,對于這一反殺行為如何判斷是否具有防衛性。從案情來看,傷害致死行為是在爭奪砍刀過程中實施的,此時不法侵害仍然處于正在進行的狀態。死者劉某奪取砍刀以后,完全有可能繼續對于海明實施不法侵害。因此,此時的不法侵害沒有終止。對于不法侵害不能狹義地理解為只是舉刀砍殺之時,而是應當廣義地理解為實施砍殺前后的一個持續的過程。在該案中,于海明奪取砍刀以后,繼續追砍劉某,砍了兩刀沒有砍中。由此可見,劉某是被奪刀時砍傷致死的。因此,對于海明的反殺行為認定為正當防衛沒有問題。假如該案劉某是在追砍過程中被砍死的,問題就更為復雜了。在這種情況下,于海明的反殺行為能否認定為正當防衛就要根據當時的主客觀情況進行細致分析。例如,于海明是明知劉某已經喪失侵害能力而繼續砍殺,還是主觀上認為劉某跑向轎車去拿兇器繼續進行侵害等。
對于該案,8月27日當晚公安機關以故意傷害立案偵查,8月31日公安機關查明了該案的全部事實。9月1日,昆山市公安局根據偵查查明的事實,依據我國刑法第20條第3款的規定,認定于海明的行為屬于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決定依法撤銷于海明故意傷害案。其間,公安機關依據相關規定,聽取了檢察機關的意見,昆山市人民檢察院同意公安機關的撤銷案件決定。
昆山反殺案將于海明的行為認定為正當防衛,這是一個成功的案例,因而成為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布的指導性案例。在處理反殺的過程中,關鍵在于侵害行為正在進行的判斷,以便將正當防衛與事后防衛加以區分。對此,最高人民檢察院在于海明案的“指導意義”中指出:“正當防衛以不法侵害正在進行為前提。所謂正在進行,是指不法侵害已經開始但尚未結束。不法侵害行為多種多樣、性質各異,判斷是否正在進行,應就具體行為和現場情境作具體分析。判斷標準不能機械地對刑法上的著手與既遂作出理解、判斷,因為著手與既遂側重的是侵害人可罰性的行為階段問題,而侵害行為正在進行,側重的是防衛人的利益保護問題。所以,不能要求不法侵害行為已經加諸被害人身上,只要不法侵害的現實危險已經迫在眼前,或者已達既遂狀態但侵害行為沒有實施終了的,就應當認定為正在進行。”上述“指導意義”明確了不法侵害正在進行的三個判斷要點。
其一,不法侵害正在進行的含義是不法侵害已經開始但尚未結束。在不法侵害開始之前或者結束以后,防衛時間尚未到來或者已經喪失,因而不存在防衛問題。應當指出,這里的已經開始但尚未結束,是對不法侵害正在進行的一種客觀狀況的描述。《日本刑法典》第36條采用“急迫的不法侵害”這樣的表述,因而不法侵害的急迫性就成為正當防衛成立的重要條件。對于這里的急迫性,日本學者山口厚認為是指被侵害的法益遭受侵害的危險必須是緊迫的。山口厚對各種具體情狀下急迫性的判斷進行了討論,(18)參見前注,山口厚書,第121~122頁。對于我國研究者判斷不法侵害的正在進行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因此,在我國司法實踐中,對于不法侵害之正在進行的判斷,不應該是形式性的判斷,而應該是實質性的判斷。判斷的根據是侵害的急迫性,例如不法侵害的開始是指侵害行為已經對防衛人形成一定的危險,不法侵害的結束是指侵害行為的危險已經消失。
其二,不法侵害正在進行的判斷應當以防衛人的利益保護為優先考慮,不同于犯罪行為的著手和既遂的判斷。因此,不法侵害的開始不同于犯罪行為的著手,不法侵害的結束也不同于犯罪行為的既遂。在司法實踐中考察不法侵害是否正在進行的時候,應當從不法侵害對于防衛人是否已經具有法益侵害的急迫危險出發加以判斷,而不是根據法益侵害的實害結果發生作為判斷的標準。例如,日本學者討論預期的侵害問題,即預期侵害的場合是否也能肯定侵害的急迫性。對此,山口厚指出,即便是預期到了侵害,一般地說也不存在回避侵害的義務。要是肯定了存在這一義務,就意味著必須忍受我們的正當利益受到侵害。從法益盡量不受侵害、盡可能全部予以保護是最理想的這樣的見地出發,在預期到“急迫不法的侵害”并且回避這一侵害也并不會增加額外的負擔的場合,為了全面地保全法益,就要求去回避侵害。(19)[日]山口厚:《日本刑法總論》(第2版),付立慶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20頁。根本不考慮防衛人的權益,機械地根據侵害行為確定防衛行為的時間條件,顯然是偏頗的。
其三,不法侵害正在進行的判斷應當根據不法侵害的行為類型和防衛的具體情境進行判斷。考慮到不法侵害的復雜性,對于不法侵害正在進行不能采取機械的標準,而應根據侵害行為的具體情狀加以判斷。有德國學者對不法侵害屬于繼續犯情況下的防衛問題做了論述,其指出:“在繼續犯(例如,剝奪他人自由、侵犯住宅安寧)的場合,只要違法狀態處于繼續狀態,侵害應當屬于正在發生。雖已經對被保護的利益實施侵害,但一經反抗便處于全部或者部分消除的狀態,此等情況下仍然屬于繼續犯。”(20)同前注④,漢斯·海因里希·耶賽克、托馬斯·魏根特書,第458~459頁。我國學者也對在持續侵害的情況下,防衛時間的判斷進行了討論。例如周光權教授指出:“在持續侵害中,不法行為的成立和既遂往往都相對較早,但犯罪行為在較長時間內并未結束,在犯罪人徹底放棄犯罪行為之前,違法狀態也一直持續,犯罪并未終了。在此過程中,防衛人理應都可以防衛。”(21)周光權:《刑法公開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70頁。此外,對不法侵害的防衛并不能畢其功于一役,而往往轉而發展為互相之間的打斗。此時,不法侵害就轉化為持續侵害,防衛行為也就呈現出相應的持續性。在這種情況下,應當根據案件的不同情況判斷不法侵害的終止時間,以此作為認定是否存在防衛時間要件的根據。在不法侵害人已經明顯喪失侵害能力(例如受傷倒地、昏迷等),或者已經放棄侵害行為(例如脫離侵害現場、求饒等)情況下,防衛人仍然加害于侵害人并造成死傷結果的,應當認定為防衛不適時,不屬于正當防衛。
(三)防衛限度的判斷規則
在正當防衛案件的處理中,最為困難的就是防衛限度的把握問題,它關系到正當防衛與防衛過當的區分。我國刑法第20條第2款明確地將防衛過當規定為正當防衛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的行為。根據上述規定,我國刑法中的防衛過當是行為明顯超過防衛限度和造成重大損害結果的統一。因此,防衛限度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加以判斷。
其一,防衛行為是否明顯超過正當防衛的必要限度。這是行為過當的問題。防衛行為與侵害行為之間首先可以從性質上進行對比,這種對比呈現出三點差異。
第一,防衛行為的人身損害性與侵害行為既包括人身侵害又包括財產侵害等非人身侵害之間的差異性,由此引申出的問題是:對于非人身的侵害行為是否可以進行正當防衛。例如,對于入室盜竊的防衛,造成盜竊犯死亡是否屬于正當防衛,以及防衛限度如何掌握,都是容易引起爭議的。筆者認為,我國刑法第20條關于正當防衛的規定中,明確將防衛目的描述為保護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和其他權利。因此,刑法并沒有將防衛范圍限制在人身侵害,對于財產侵害等非人身侵害,只要符合正當防衛的條件,都可以進行防衛。只是在防衛限度上應當有所節制。當然,也不能認為只要是以人身損害的方式對非人身侵害行為進行防衛的,無論造成損害結果如何,都構成防衛過當。
第二,防衛行為的暴力性與侵害行為既包括暴力侵害又包括非暴力侵害之間的差異性,由此引申出的問題是:對于非暴力的侵害行為是否可以進行正當防衛。防衛行為具有防衛方式上的單一性,即以造成侵害人的人身損害的暴力方式(包括身體傷害和剝奪生命)進行防衛。因而,防衛行為具有暴力性。侵害行為則具有侵害方式上的多樣性,既存在暴力侵害,也存在非暴力侵害。在對暴力侵害進行防衛的情況下,具有以暴制暴的性質,具有防衛行為與侵害行為之間性質上的對稱性。然而,在對非暴力侵害進行防衛的情況下,以暴力的防衛性質制止非暴力的侵害行為,具有防衛行為與侵害行為之間在行為方式上的不對稱性。因此,對于非暴力的侵害行為能否進行防衛,以及防衛限度如何掌握也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對于這個問題,最高人民法院指導案例93號于歡故意傷害案的裁判要點明確指出:“對正在進行的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行為,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二十條第一款規定的‘不法侵害’,可以進行正當防衛。”由此可見,對于非暴力的非法拘禁、侵入他人住宅等不法侵害是可以進行正當防衛的。當然,在防衛限度的判斷上應當有別于對暴力侵害的防衛。
第三,防衛行為的構成要件該當性與侵害行為既包括違法行為又包括犯罪行為之間的差異性,由此引申出的問題是:對于尚未達到犯罪程度的侵害行為是否可以進行正當防衛。這里涉及對不法侵害的理解,即不法侵害是否既包括違法行為又包括犯罪行為。對此,我國立法機關認為,該款規定的“不法侵害”是指對受國家法律保護的國家、公民一切合法權益的違法侵害。(22)參見前注②,郎勝主編書,第22頁。可見,對于違法行為也可以進行正當防衛。例如對于毆打行為進行防衛,即使造成輕傷結果,也不能認為超過了防衛限度。
綜上所述,行為過當的判斷應當從侵害行為和防衛行為這兩個方面,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進行綜合分析,最后得出行為是否過當的結論。
其二,防衛行為是否造成重大損害結果。這是結果過當的問題。進入司法視野的正當防衛案件,防衛行為必然已經造成侵害人傷亡的結果,因此,該防衛結果是否過當需要認真進行分析。在正當防衛案件中,將侵害結果與防衛結果進行對比,可以分為兩種情形。
第一,侵害行為已經造成人身損害結果,例如造成防衛人傷害,在這種情況下,防衛人在防衛過程中造成侵害人死傷結果。其中,傷害結果是對稱的,而造成侵害人死亡結果則是不對稱的。因此,如果僅僅根據死亡結果判斷,必然會得出防衛過當的結論。其實,死亡結果還要分析是否是傷害行為造成的,即故意傷害致人死亡,還是殺人行為造成的。因此,不能將死亡結果作為認定是否過當的唯一根據或者主要根據,而是應當考察造成傷亡結果是否為防衛所必需。
第二,侵害行為尚未造成人身侵害結果或者只是造成輕微的人身侵害結果,防衛行為卻已經造成重傷、死亡等較為嚴重的人身損害結果。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僅從結果來看,防衛結果已然超過侵害的嚴重程度。那么,能否由此而認定為超過防衛限度呢?對此,最高人民檢察院在檢例第47號于海明正當防衛案中指出:“在論證過程中有意見提出,于海明本人所受損傷較小,但防衛行為卻造成了劉某死亡的后果,二者對比不相適應,于海明的行為屬于防衛過當。論證后認為,不法侵害行為既包括實害行為也包括危險行為,對于危險行為同樣可以實施正當防衛。認為‘于海明與劉某的傷情對比不相適應’的意見,只注意到了實害行為而忽視了危險行為,這種意見實際上是要求防衛人應等到暴力犯罪造成一定的傷害后果才能實施防衛,這不符合及時制止犯罪、讓犯罪不能得逞的防衛需要,也不適當地縮小了正當防衛的依法成立范圍,是不正確的。本案中,在劉某的行為因具有危險性而屬于‘行兇’的前提下,于海明采取防衛行為致其死亡,依法不屬于防衛過當,不負刑事責任,于海明本人是否受傷或傷情輕重,對正當防衛的認定沒有影響。”雖然于海明被認定為無過當防衛,不存在對防衛限度的判斷問題,但在對該案的司法審查過程中,涉及對在防衛結果與侵害結果不對稱情況下,對防衛限度的判斷問題,因而值得注意。在對防衛行為是否超過正當防衛必要限度的判斷的時候,如果侵害行為不是實害行為而是危險行為,則不能僅從結果是否對稱上進行考量,而是應當結合案件的具體情況,例如使用工具、人數、時間、地點等,綜合判斷防衛行為是否超過正當防衛的必要限度。
其三,行為過當與結果過當的統一。對于防衛行為是否超過正當防衛必要限度的判斷,既不能僅考慮行為是否過當而不考慮結果是否過當,也不能僅考慮結果是否過當而不考慮行為是否過當,而是應當同時考慮行為與結果這兩個要素,只有在行為過當與結果過當同時具備的情況下,才能認定為防衛過當。行為過當與結果過當的概念來自日本刑法理論中的相當性概念,日本學者一般以相當性考察防衛行為或者防衛手段。例如山口厚指出:“反擊行為作為針對侵害的防衛手段,應具有相當性。因此,只要反擊行為并非超過上述限度,作為針對侵害的防衛手段便具有相當性,即便由該反擊行為所造成的結果偶爾大于所被侵害的法益,也應該認為,該反擊行為并非不屬于正當防衛行為。”(23)同前注,山口厚書,第129頁。根據這一觀點,即使防衛結果大于侵害結果,只要防衛手段具有相當性,也應當成立正當防衛而不是防衛過當。因此,防衛行為是否過當并不完全取決于結果,而是先要考察防衛行為是否具有相當性。防衛行為的相當性應當與結果分開判斷而不是混為一談。山口厚指出:“被正當化的防衛行為的范圍,不應該根據所產生的‘結果’,而應該通過所使用的‘防衛手段’本身予以判斷。”(24)同前注,山口厚書,第129頁。以上觀點與防衛限度判斷中的唯結果論的觀點是對立的。在防衛限度的判斷中,先要確定的是結果的過當性。如果沒有結果過當也就不可能成立防衛過當。然而,僅有結果過當是不夠的,更為重要的是還應當考察行為的過當性。只有在同時具備行為過當與結果過當的情況下,才能認為超過防衛限度。如果只是結果過當而行為并未過當,或者只是行為過當而結果并未過當,都不能成立防衛過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