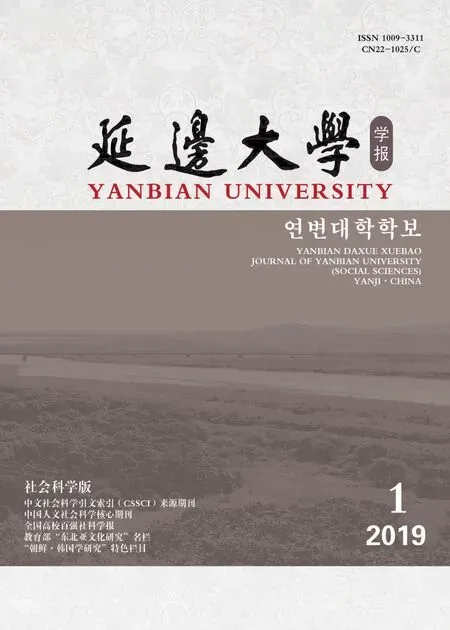中朝兒童抗日敘事比較研究初探
——以《小兵張嘎》與《她當時九歲》為例
李 想 禹尚烈
二戰期間,法西斯軸心國之一的日本發動了侵略戰爭,給東亞各國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和不可磨滅的傷害。中國14年的艱苦抗戰和朝鮮受到的30多年殖民統治,成為了20世紀的一個重要文學主題——抗日文學。這是一份有待挖掘的寶藏,“國內外在這一研究領域還沒有比較全面系統的研究”。[注]牛林杰:《20世紀東亞抗日敘事研究現狀與展望》,《東疆學刊》2016年第2期,第6頁。而中朝兒童抗日敘事文學作為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相關研究相對較少,從比較文學角度開展的研究則更是空白。
兒童抗日敘事文學既是抗日文學也是兒童文學,兒童的主人公身份不僅讓作品充滿童趣性,又通過這種純真的童趣凸顯出革命的必要性和革命成果的珍貴,格外增強了作品的革命教育效果。在中國,管樺早在1948年就在《晉察冀日報》上發表了《小英雄雨來》(原名《雨來沒有死》),之后又陸續有呂慶庚的成名作《小砍刀的故事》(《小砍刀傳奇》)、延安時期參加革命的老作家陳模創作的革命傳統紀實小說《少年英雄王二小》、當代作家李心田的《兩個小八路》、著名兒童文學作家邱勛的少年英雄故事長篇小說《烽火三少年》、胡樹國的長篇小說《地下兒童團》、華山的中篇小說《雞毛信》等兒童抗日文學作品問世。而在朝鮮,關于抗日文學的創作是十分受推崇的,其中的兒童抗日敘事作品有金成哲和金龍瑞的《尋找紅發帶的少女》、李明源和李泰華的《游擊隊里的杜鵑鳥》、白仁俊的《我們的同志們》、尹善默的《駕駛員的兒子》、韓福奎與安成甲的《鐘聲響起》、張光南的《小海南》等。
在這些兒童抗日敘事文學作品中,中國的《小兵張嘎》和朝鮮的《她當時九歲》可謂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小兵張嘎》在中國早已家喻戶曉,出自中國當代著名作家徐光耀之筆,作品發表于1961年,后改編成影視作品,是新中國幾代人童年成長記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朝鮮作家樸賢的《她當時九歲》取材于真實人物、真實歷史事件,于1981年由金城青年出版社出版發行,也是一部廣為朝鮮人民熟知的兒童抗日敘事文學作品。本文擬通過運用原型理論分析這兩部作品中共有的兒童革命成長敘事模式,再從兩部作品在敘事時間、敘事空間上的不同特點,探討其在歷史細節描寫、色彩渲染、人物形象塑造、主題升華上的共性或差異。最后,通過對兩部作品的深入分析,進一步對兒童抗日敘事文學的意義加以審視和探討。
一、兒童革命成長敘事模式
縱觀《小兵張嘎》與《她當時九歲》的整體故事情節可以發現,兩部作品最顯著的不同在于一個是喜感十足的革命喜劇,一個是徹頭徹尾的革命悲劇。《小兵張嘎》的主人公張嘎的純樸可愛、機靈調皮一以貫之地呈現在故事始終,從而消減了他悲慘遭遇的悲劇性。而《她當時九歲》的主人公金順的命運悲劇層層演進,悲傷、痛苦不斷升華,伴隨著整個故事的發展,悲壯成為了作品的主要色彩。但剝離掉這層情感基調的外衣可以看到,兩部作品在兒童革命成長敘事上采用了相同的結構模式,在塑造革命小英雄形象上都離不開成長主題和傳統英雄原型的支撐。
(一)嵌套式U型兒童革命成長敘事結構
U型敘事結構通過從下降到上升的模式一步步將小說的故事推向高潮,是眾多作品中塑造人物形象、體現故事情節戲劇性發展的一種敘事策略。就本文所討論的《小兵張嘎》和《她當時九歲》而言,從敘事起點來說,兩個小主人公出身相同、家庭背景相似,都是農民階級,也是代表千萬勞苦大眾的典型人物,這種身份的設定是為反封建主題而服務的。雖然與反帝國主義主題相比居于其次,但反帝反封建必然會交織在一起同時出現在抗日文學之中,這是時代大背景中社會主要矛盾的反映,是時代特征的體現。兩個小主人公雖然出身平凡,但和眾多普通孩子一樣幸福快樂,生活在長輩的呵護和寵愛之中。然而,侵略戰爭改變了他們的生活,敵人的鐵蹄踐踏了他們年幼的幸福時光,張嘎失去了相依為命的奶奶,金順與母親、弟弟失散,他們失去了親人,失去了家。這便是U型敘事結構的最低點。
敘事的上升線從加入革命組織開始,兩個小主人公的命運發生了轉折。張嘎跟著八路軍隊伍開會、做宣傳、打野戰、學文化,還參加組織的娛樂活動,從放哨站崗到在一線戰斗中圓滿完成任務,從對黨的不了解、不熟悉到暗下決心要努力成為一名黨員,張嘎從一個莽撞少年成長為一名革命后備軍戰士。而金順進入游擊根據地后獲得了平等上學的機會,參加兒童團早會、到學校學習、完成指導員分配的各項任務,從思念母親一蹶不振到成為在各根據地小有名氣的演講演員,從在戰爭后方幫助大叔制作炸藥到在地下一線工作中成功傳遞秘密消息,從對保守黨組織秘密的不理解到寧可犧牲也絕不出賣組織,金順最終從一個乖巧嬌弱的小女孩成長為一名堅強勇敢的革命小英雄。兩部作品在敘述兒童革命成長過程時都套用了“無憂無慮,快樂生活——家破人亡,加入組織——成為革命小戰士”這樣的U型敘事結構。同時,前半段下降線的內容較短,后半段上升線的內容較長,呈現出以成長過程為核心的非對稱U型結構。而在上升線這部分主要內容之中還分別嵌套著一個接一個的小U型結構敘事單元。將這些小U型敘事單元抽離出來,便是兩個小主人公在兩個方面的成長,一個是實踐本領的磨煉,另一個就是思想認識的提升(詳見表1)。

表1 張嘎與金順在實踐本領和思想認識上的小U型敘事單元
無論是大U型敘事結構,還是一系列的小U型敘事單元,都是“死亡—重生”母題的具體表現。“死亡”是平靜幸福的家庭生活的“死亡”,是簡單快樂的童年的“死亡”,而“重生”是戰斗本領的習得,是革命思想的形成。這正是一個革命者所必備的兩個要素。如果說本領的磨煉是那個時代下的一種生存方式,那么革命思想的成長則是那一代人擁有的最強大的武器,是整個民族生生不息、艱苦斗爭取得勝利的法寶。革命精神就是當時的時代精神,對革命的認識是從小家之仇上升到關系民族、關系眾多百姓利益的偉大事業,“報仇雪恨”被賦予了更新、更豐富、更具高度的內涵,“革命”也因此有了更深刻、更長遠的意義,所以“重生”的意義更在于精神上的“重生”。
(二)成長主題下英雄原型的演繹
抗日兒童敘事文學作為東方20世紀成長小說的代表,與同時代下西方文學中的成長小說形成了鮮明對比。西方的成長主題基本上圍繞少年在走向成人過程中所遇到的煩惱、焦慮,展現人在成長中的迷茫,書寫的是人性的成長。而東方的成長小說則更側重于表現帶有時代印記的政治性、使命性的革命成長。所以在這種革命成長主題中,張嘎和金順的成長煩惱表現為仇恨敵人的情緒、對革命任務的理解與認知、渴望參與戰斗又受年齡限制的苦惱心理等。而幫助他們解決這些煩惱的領路人便是老鐘叔、老羅叔、錢區隊長和許明姬指導員、哲民哥哥、浩范大叔、金日成將軍等革命者。他們是艱苦革命道路上的一盞盞明燈,不僅為兩個小主人公指明了方向,還對他們在思想上及時教育批評,在生活上給予關懷愛護。于是,張嘎和金順找到了成長的出路,那就是成為一名優秀的革命戰士,在失去親人的痛苦中強大起來,重新獲得生活下去的信仰,用勇敢和革命理想書寫人生的意義。這種成長是成功的,是“經典的成長小說概念”,[注]張國龍:《成長小說:中國文學亟待拓展的新空間》,《中國圖書評論》2018年第6期,第10頁。與成長小說原初的啟蒙意識相吻合,是按照那個時代下成年人對兒童的期許所書寫出來的。
所以,成長的終點必然要落腳于革命英雄,而革命小英雄的塑造離不開傳統英雄原型。盡管在階級斗爭這一時代主題的限定下,小主人公平民百姓的出身解構了傳統英雄原型必須具備高貴血統的要素,但英雄成長過程中的“流亡”“追尋”“劫難”“自我犧牲”母題依然存在。當失去了親人、無所依靠的時候,為了報仇,為了尋找更強大的支撐力量,兩個主人公都經歷了尋找組織的過程。嘎子獨自一人進了城,錯把老羅叔當成了漢奸,上演了一場有驚無險的趣劇。金順跟著比自己大幾歲的哲民哥哥離開了在鬼子燒殺掠奪后變為廢墟的村子,赤腳向游擊根據地走去,一路上挨餓受凍,渾身傷痕累累。這是整部作品承上啟下的關鍵內容,是英雄原型中典型的“流亡”與“追尋”母題。“流亡”與“追尋”是人類最初在原始社會以求生存的必然方式,是英雄原型模式中英雄獲得新生、建功立業的前奏。褪去了神話中的神秘色彩,立足于行為能力受限的兒童主人公身份,這種“流亡”與“追尋”以承受現實的考驗而表現出來。而從整部作品來說,兩個小主人公在革命組織中的成長也是一種“流亡”與“追尋”。從失去了親人和家的那一刻起,他們就注定要以“流亡”的方式生存,在“流亡”中,他們一直“追尋”著如何復仇、如何快點長大、如何完成任務、如何成為革命戰士,一直“追尋”著什么是革命以及革命的意義。當歷經了戰爭的“劫難”,歷經了戰斗負傷、違反組織紀律被罰,以及自責、悔恨等身心上的“劫難”后,張嘎和金順獲得了自我犧牲的精神和勇氣,在最關鍵的戰斗中不顧個人的安危,發揮了最重要的作用,通過“自我犧牲”實現了成長為革命小英雄的價值。
兒童抗日敘事文學的核心在于嵌套式U型敘事結構下的兒童革命成長敘事,而在普遍意義上兒童邁向成人的本位成長受到消解。同時,革命成長主題下的革命小英雄形象,是傳統英雄原型在抗日主題下的新演繹,是自古以來“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這一集體無意識的再現。而兒童英雄通過站在道德制高點的“自我犧牲”推動大義的實現,也體現了東方根深蒂固的集體主義價值觀。
二、直線型與循環式敘事時間
現代敘事學對于敘事時間常常強調文本時間與故事時間兩個概念。“文本時間指的是文本敘述的時候用于敘述事件的時間,而故事時間指的是所述事件實際上發生所需的時間。”[注]楊春:《敘事時間策略和敘事時間維度》,《學術探索》2015年第2期,第120頁。要想把事件實際發生的時間在文本中體現出來,就需要利用時間向度和時間刻度。時間向度即為過去、現在和將來,當然三者是相對的,取決于事件參與者的位置。在時間向度的橫坐標上,作者還會用年月日、季節、晝夜、朝夕、年齡、生死等標注具體的時間刻度。
從時間向度來說,兩部作品都是以順敘的手法,按照事件發生、發展的先后順序講述主人公的成長歷程。不同的是,在故事發展的過程中,《小兵張嘎》除了晝夜的描述,并沒有再給出更多的時間定位,故事時間的流逝僅依靠一件事接著一件事的發生來體現。而《她當時九歲》一共有四章,其中第二章和第四章開頭部分都描寫了秋天的景色,也就是說這給出了一年的時間概念。因此,從第二章金順正式開始根據地生活到第四章開篇金順在一路的演出中深受各戰地的喜愛和贊揚,還被宰民大叔叫做“小革命家”,這展現了主人公在一年的時間里所獲得的成長。而緊接其后的便是整個故事的最高潮,即金順肩負起傳遞秘密消息的重要任務,任務完成卻被捕犧牲。這是較之于前一階段更高層次的成長。也就是說,“第二年秋天”的出現,既是金順一個階段性成長的終點,又是下一個更高階段成長的起點。季節的循環與輪回,既縮小了文本時間與故事時間的倒錯,讓讀者對金順成長的時間歷程有了概念性的感知,也讓作品的悲劇主題更為濃厚。因為循環的時間,尤其是季節的更迭往往給人一種悲涼滄桑的感覺,更何況秋天代表著蕭條、落寞并預示著死亡的來臨。
而小說的結局作為文本時間和故事時間的雙重結束點,是最終體現小說時間結構的關鍵。“‘終結意識’是理解敘事結構和意義的一個重要的概念”,[注]張隆溪:《比較文學研究入門》,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73頁。我們閱讀一部小說時,只有到了結尾,有了完整的故事,才能回過去看清情節發展的軌跡,明白整個故事的意義。張嘎在祝捷大會上受到表揚,得到了嘉獎,并悄悄跟小伙伴玉英吐露了自己想參加共產黨的革命愿望。至此,文本時間結束,但故事時間仍在延續。而《她當時九歲》以金順的壯烈犧牲為結局,她年僅九歲的生命結束了,文本時間與故事時間同時終止。
可見,無論從時間刻度的安排上,還是從結局中故事時間的設定上,都可以發現《小兵張嘎》的時間結構是一條無限延伸的直線,具體時間點被模糊化,以事件的排列體現時間的概念。這種直線型敘事時間結構所表現的是革命道路無限光明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是為作品的喜劇色彩而服務的。而《她當時九歲》的時間結構則明顯呈現為循環型,父親遇難,母親跳崖,金順犧牲,而犧牲前她腦海中出現的是弟弟回到祖國朝鮮的情景,這種“前仆后繼”正表現了一種生死循環的時間概念,既是一種革命希望的象征,也是一種革命悲劇的渲染。加上生死循環與季節輪回的相呼應,既將悲涼之感融于通篇作品之中,也更襯托出肉體消亡但靈魂永生的革命獻身精神的寶貴,體現了生命價值和生命意義的美學主題。
不同的敘事時間結構服務于不同主題思想的升華,但無論是展現革命樂觀主義精神,還是彰顯革命獻身精神,兩部作品都是對革命的謳歌和贊美,是典型的革命浪漫主義文學,展現了革命英雄主義的崇高美。這種主題的文學作品有其產生的歷史必然性。魯迅曾分析說:“大革命成功后,這時候底文學有二:一種文學是贊揚革命,稱頌革命,因為進步的文學家想到社會改變,社會向前走,對于舊社會的破壞和新社會的建設,都覺得有意義。”[注]魯迅:《革命時代的文學》,《魯迅雜文經典全集》,北京:北京明天遠航文化傳播有限公司,2013年,第138頁。對于中國和朝鮮來說,抗日戰爭是抵御外來侵略的正義之戰,無數革命志士用鮮血才換來了符合廣大人民利益的幸福生活,而在兩部作品問世的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正是中國和朝鮮大力開展新國家建設的時期,需要這種旗幟鮮明、思想積極、號召人民投身社會主義國家建設的文學作品,這便成為了培育這種謳歌革命作品的肥沃土壤。同時,這兩部作品也是戰后人們對于革命英雄無比崇拜的社會氛圍下的必然產物。
三、社會空間與心理空間的構筑
空間敘事是近幾十年來,眾多學者在敘事學領域尤為關注的焦點之一,戴維·赫爾曼曾指出:“空間是有助于建構事域的核心特質。敘事在人、物、地點之間建立了關聯,從而造成了空間與事件之間的多姿多彩的融合”。[注][日]香山壽夫:《建筑意匠十二講》,寧晶譯,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6年,第135頁。也就是說,空間的構筑是使故事細節豐滿的必要內容,是作品的血肉。本文僅從能夠反映時代特征的社會空間和突出兒童人物特征的心理空間兩方面進行比較分析。
(一)社會空間:八路軍敵后戰場與金日成游擊根據地
社會空間的概念是列斐伏爾在其《空間的產生》中所提出的,是體驗的、生活的空間,是一種開放的、沖突的和矛盾的動態進程。[注]程錫麟:《敘事理論的空間轉向》,《江西社會科學》2007年第11期,第26頁。在具象的物質性空間里,各種人物才能展開一系列活動,社會空間的構筑才能拉近話語世界與真實世界的距離。同時,社會性是人的根本屬性,置身于復雜社會關系中的人才是真實飽滿的人物,所以社會空間既是具體的又是抽象的,它展現的是人的生存方式、活動內容以及人際關系。
作為以戰爭為歷史背景的兩部小說,《小兵張嘎》和《她當時九歲》中都構筑了軍隊的社會生活空間。
《小兵張嘎》中,小嘎子進城見到老羅叔后,跟著他第一次找到八路軍部隊時描寫道:
“從丁字街往南剛一拐,老羅就跳下車來,停在一個小茶館的門前。”[注]徐光耀:《小兵張嘎》,武漢:長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5年,第39頁。“推開風門子,又朝里走。小嘎子緊隨著進院一看:一溜兒五六間正房,正房對面是一排草廈子,把小院擠成了細長的一條,很像個歇業的小草料店。可是,老羅并不進屋,帶了小嘎子又向深處走去。到了天井,往左一拐,又有個小寨籬門;推開小寨籬門,是敞亮亮一座小跨院,可里頭連一間房子也沒有。只平地上栽著幾畦茄子,兩溝大蔥,靠北墻搭著個大葫蘆架,搭得比墻頭還高出二尺……卻見他把車子一靠,往葫蘆架底下一鉆,登著一大一小倒扣著的兩口甕,撥開枝蔓,翻過墻那邊去了……那邊又是一層院子。”[注]徐光耀:《小兵張嘎》,武漢:長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5年,第40頁。“這邊院子,出了正房,還有一溜兒五間西屋,像個冷落的倉房……整個院子很寧靜,幾乎沒有任何聲音……羅金寶盯他一眼,就過去把西屋的門推開一道縫,側身子掩了進去。”[注]徐光耀:《小兵張嘎》,武漢:長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5年,第41頁。
“小茶館”“正房”“草廈子”“天井”“小寨籬門”“小跨院”“葫蘆架”“墻頭”“又一層院子”“西屋”,這一系列接續性的場域,構筑起了一個復雜飽滿的空間,充分凸顯出當時八路軍作戰的隱蔽性。
《她當時九歲》在故事情節中描寫到,這里的抗日根據地有許明姬指導員帶領的兒童團,有負責印刷教科書和宣傳冊的出版所,有負責慰問演出的文藝隊,有負責修理槍支、制作炸藥的武器修理所,還有炊事班、裁縫所、醫院、學校,這里還接收了數百名在日軍屠村中逃亡的村民,在本就艱苦的斗爭條件下還要解決他們的穿衣、吃飯和傷病治療問題。這些已勾勒出了朝鮮抗日革命根據地的整體面貌。
可以看出,《小兵張嘎》中所呈現的部隊生活是隱蔽的、游動的,這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領導人民軍隊開辟敵后戰場、深入敵人內部、以打游擊戰為主要戰略的顯著特點。而《她當時九歲》中展現的是一個體系完整、制度化的生產生活空間,它是小汪清游擊根據地的寫實描寫,記錄的是金日成在中國東北開展的抗日游擊活動。同時,這也是朝鮮自20世紀60年代確立主體思想后,將領袖視為賜予人民生命的慈父和恩人的集中表現。
然而,無論是隱藏在百姓家中的秘密據點,還是駐扎在深山里的游擊根據地,對于兩個小主人公來說部隊的生活空間就像一個“世外桃源”。戰士們都成為了張嘎的好朋友,“他有的叫哥、有的叫叔,好像同宗連族”,[注]徐光耀:《小兵張嘎》,武漢:長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5年,第46頁。“大家原本喜歡他的聰明鬼仗,再加上他年紀小,天性快活,就愈發待他赤誠親熱,真個親弟弟似的”。[注]徐光耀:《小兵張嘎》,武漢:長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5年,第49頁。金順也在根據地得到了叔叔阿姨的喜愛和關心,獲得了與兒童團小伙伴們一同玩耍成長的快樂,得到了指導員的照顧和幫助以及金日成將軍的親自教導。從白洋淀淺灣中的小院到八路軍部隊的藏身據點(張嘎),從村落里的四口之家到根據地的集體生活(金順),盡管有各種艱難困苦,盡管面對著各種危險,但在他們的眼中這里的生活就是幸福快樂的。這種簡單的快樂和滿足是兒童所特有的,是可以為成年人的艱苦斗爭注入革命信念和斗志的。
兩部作品所構筑起的社會空間是主人公成長的環境,記錄了兩國人民不同的抗戰史實特征,但都重點表現了這個社會空間中和諧團結、互幫互助的人際關系,展現了革命所要追求的平等幸福生活,也著重放大了革命者們充滿大愛與希望的精神光輝。
(二)心理空間:調皮莽撞的男孩與情感細膩的女孩
心理空間是作者通過語言文字所構筑的主人公的精神世界,心理空間的構建不僅是塑造人物形象個性化特點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更是渲染作品風格、表達主題思想的重要內容。
心理空間的構筑使抗日兒童的形象更加豐滿,尤其凸顯了性別的不同特征。張嘎在找到組織之前一心想繳把槍,好以此來邀功以便于加入八路軍,后來因偷偷藏槍受到批評,內心充滿了委屈和氣憤;與胖墩賭氣打架,用草堵住胖墩家的煙囪,還對胖墩爹的“告狀”滿懷“仇視”,這些心理活動都突出了張嘎作為男孩子的莽撞調皮和率真。而金順在未能完成好宣傳演講時心中充滿了自責,看到哲民被捕后血肉模糊的樣子時對自己曾經埋怨哲民悔恨不已,知道了父親犧牲的消息后仍假裝堅強,毅然隨文藝隊到前線演出。這些無不體現出女孩特有的乖巧細膩和感性。通過心理空間的構筑塑造了兩個截然不同的、充分體現性別特征的小主人公形象,而這種形象的搭建也是凸顯喜劇與悲劇色彩的著力點。不同的心理世界烘托出不同的基調和主旋律,張嘎的嘎勁正是《小兵張嘎》最討喜的地方,而金順的善解人意也正是《她當時九歲》最讓人感到悲傷和遺憾的情感基點。
同時,作為一個情感細膩敏銳的小主人公,金順對祖國家鄉的想象貫穿了小說的始終。這是在本土開展抗日活動的小主人公張嘎所沒有的情感體驗。金順在村子里與父親去小溪邊捉蝲蛄時,聽到父親的描述,她想象著祖國的溪水、土地和天空。后來到了根據地,和浩范大叔站在山崗上望著祖國的方向時,金順又想象著今后一起回家鄉。最后在監獄中,金順再次想象家鄉的樣子,她對浩范大叔說:“我還沒能回去看看家鄉的樣子,沒見過那的大海,一次也沒有……我好想看看,好想在那里生活,想看看我們國家的大地,蘋果樹,還有房子,還有山……。”[注][朝]樸賢:《她當時九歲》,平壤:金城青年出版社,1981年,第292頁。這條心理線表達了一個兒童心中對家鄉的執念。而這種感受從想象變為向往,從向往變為渴望,從渴望變為遺憾,這種變化成為了整個小說悲劇色彩中濃重的一筆,直擊人的內心。這層心理空間的構筑是借兒童的內心表達了所有在異國他鄉戰斗的仁人志士深切的思鄉之情和真摯的愛國之情,這是一份尋根意識的體現,這種情感是流亡在外戰斗的任何成果都永遠無法彌補的裂痕和缺失。
然而,無論是男孩還是女孩,他們的內心世界都并存著孩子氣和英雄氣。張嘎調皮搗蛋,對組織的管教十分不服氣,卻對槍懷著一份執著和渴望,對革命者的戰斗事跡充滿了向往和崇拜。金順會因為哲民隱瞞兒童團團員的身份而生氣,會在莫東打擾自己練習演講的時候偷偷抽走小溪里墊在過河石下的小石頭,讓莫東險些栽倒在河里,但她卻一直羨慕哲民總是可以負責重要的任務,戰斗打響的時候她也十分想上前線殺敵。這些都展現了他們既有孩子的本性,又懷揣著一個強烈的英雄夢。他們內心充滿了對成長的迫切渴望,他們內心急切,急于表現,也對每一次完成一份任務充滿了自豪感。這種革命小英雄的內心世界是年齡與時代所共同賦予的復雜心理。
通過對心理空間的解讀,我們可以看到內心世界的構建造就了嘎勁十足的張嘎形象和乖巧溫和的金順形象,這兩種不同形象的塑造服務于悲喜主題的表現,而金順的思鄉心理又重點體現了流亡在外的朝鮮人民普遍具有的歸鄉情結和心理傷痕,由此可以看出人物心理空間的構筑與故事情節、主題思想的關聯性。但在彰顯性別特征的外化形式之下,隱含著同是抗日兒童的復雜心理。
四、結語
20世紀的兒童抗日敘事文學形成了抗日革命小英雄的原型,無論是張嘎還是金順,都是時代的產物,他們不僅是個性化的個體人物,更是千千萬萬“張嘎”和“金順”的人物典型,是農民兒童成長為革命小英雄的代表。兩部作品都通過U型結構完成了兒童革命成長敘事,塑造了永不磨滅的抗日小英雄形象。在敘事時間和敘事空間上展現出各自的藝術特色,又都凸顯了謳歌革命的主題,其中展現出的不同歷史細節正是這些抗日敘事文學作為歷史資料的珍貴價值。
從兒童文學的角度來說,在救亡圖存的時代主題下,兒童文學必然與其他文學一樣承擔起“斗爭工具”的角色,充滿革命性、階級性,其創作目的就是革命教育性,無論是兒童成長的煩惱,還是成長的出路,都始終圍繞著革命二字,脫離了兒童成長本位,忽略了成長主題的多元性和復雜性。這是具有歷史必然性的,也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但當時代跨過硝煙和戰火,當我們在和平主題下尋求民族發展之時,回歸理性的我們應當看到,兒童文學作為一種教育媒介,更應重點探討如何通過文學讓兒童在向成人過渡的過程中建立“人格”和“人性”的問題。正如周作人所說的:“我們對于教育的希望是把兒童養成一個正當的——‘人’”,[注]孫銀芳編:《周作人幸福的藝術》,西安:太白文藝出版社,2013年,第142頁。“兒童的文學只是兒童本位的,此外更沒有什么標準”。[注]高瑞泉編:《理性與人道——周作人文選》,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第110頁。
戰爭的本質是毀滅,這是戰后當我們經歷了渴望英雄、崇拜英雄、反思戰爭這樣一個轉變過程后,對戰爭的客觀認識。當我們更加客觀、全面地審視戰爭,拷問人性的時候,和平才更顯其珍貴。正如莫言在《捍衛長篇小說的尊嚴》中說到的,“只有正視人類之惡,只有認識到自我之丑……才可能具有‘拷問靈魂’的深度和力度,才是真正的大悲憫”。[注]莫言:《捍衛長篇小說的尊嚴——代序言》,《蛙》,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年,第3頁。關于人性的思考,關于戰爭的審視,是兒童抗日敘事文學帶給當下最重要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