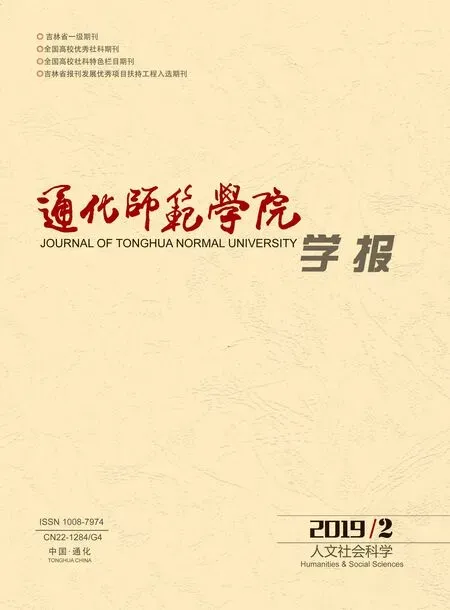保羅·奧斯特小說:從名字游戲看人物身份懸置狀態
管秀梅,李金云
一、引言
人的名字是個人在社會上工作、學習、與人交往的代表符號。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的語言學理論認為符號的能指與所指緊密相連的,作為概念的所指和作為聲音的能指是緊密連結的整體。人名作為一種符號,具有專屬作用,一個人名對應相應的所指對象。“一個人沒有名字編碼無法成為‘我’”[1]。“命名是對秩序的渴望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2]。專名的唯一性、區別性和確定性,使得在法律文書上的親筆簽名指向某一個特定的人,以區別他人的名字。“我能用我父母給我取的名字將我與其他人區別開”[3]。沒有名字或者專有稱謂則意味著人物身份缺失,迷失自我,從而導致人物身份不確定,在變化中要去重新尋找自我,身份懸而未決,處于懸置狀態。
專有名詞具有特定指向性和符號性。當作者在小說主人公名字上不斷變化,不斷進行這種名字命名的游戲時候,就會使得人物變得模糊不可分辨。“游戲,游戲乃是在場的斷裂[4]”,小說游戲中的符號并不存在確定的所指,存在的只是這一能指與其他能指的種種相異關系。小說主人公沒有確定的名字,缺乏穩定的個體身份,名字游戲帶來的是小說中心意義的喪失。“中心并不存在······中心是一種非場合,而且在這非場所中符號替換無止境地相互游戲著”[4]。這種名字游戲會對文本理解的影響,李金云[5]早就關注到,名字,作為標注人物的符號總是處于不停變化中,缺乏穩定的社會身份和自我認同感,象征秩序所建構的人的主體性便呈現出一種分裂狀態,主體實際上已被消解,身份變得模糊。名字游戲帶來的是“主體的穩定性消失了,它被不斷的改寫、擦抹、重寫。不斷建構、重構[6]”。這些反應在作品中,小說中的人物身份不斷被改寫,人物很難進行自我身份確認,在不斷變化名字和身份的過程中迷失了自我。
保羅·奧斯特小說中的人物不斷把玩名字游戲的目的各異,有的是為了刻意隱藏自己的身份,有的僅僅覺得好玩,有的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由于這種游戲,小說中的人物有的在精神幻滅與失落中不斷追尋;有的把自己困于封閉空間中,保持內心的孤獨與寂寞,盡量與社會保持一定距離;有的漫游在自我封閉的內心世界,與周圍的一切格格不入。人名懸置狀態同樣也是人物內心精神無所寄托,無所追求的表現。在秩序化世界中,“名字”即是一種標識和象征個人的符號,保羅·奧斯特在給庫切的信中所說,“要讓我們確信自己與名字本是一體,是要在世界的眼中取得一種身份[7]”。在保羅·奧斯特小說中,文中的主人公玩名字游戲,簡單的改變名字就使得個體在社會主題中變得不可識別,自我身份也變得不可確定,作品也變得撲朔迷離,情節曲折多變。
二、名字游戲導致人物身份懸置
小說是通過虛構的文本揭示世界的“非現實性”,而文本則是通過塑造人物形象來表現作品。虛構文本中的人物雖然也是虛構的,但那是語言文字構成的符號,或者說是能指。“人物是虛構的存在,他或她將不再是完整的、有固定本體的人物。這個固定本體是一套穩定的社會和心理品質——是一個姓名,一種處境,一種職業,一個條件等等[8]。”
不同民族、不同的個體對人名有不同的理解。保羅·奧斯特曾經和庫切通信談到名字這一符號。庫切認為名字是人的命運。奧斯特則認為,名字與個體自我緊密相連,名字預示著個體存在、自我身份穩定性,名字一旦與現實中的人失去了聯系,人物身份無論是自我認同還是社會認同都會造成混亂和麻煩。人物名字和和人物的命運緊密相連。同一篇小說中人物名字不斷變化,導致人物身份不確定性,懸置漂浮。保羅·奧斯特小說中的主人公們自我名字在不同的場合、與不同的人對話都會出現名字前后不一致,甚至出現同時利用多個名字,懸置的名字、懸置的自我身份,促使在社會中存在的個體為了實現自我身份認同不斷探索和尋覓,比如《幻影書》中的為逃避法律制裁,不斷易名,過漂泊流浪海克特·曼、《幽靈》中懷疑自我存在感的雇主懷特;陷入多個名字、多重身份,人格分裂的有《玻璃城》中的奎恩;自我頻繁命名,意識混亂的如《玻璃城》的小斯蒂爾曼。下面就針對上述人物作出論述,讀者可從中體會名字給人帶來的身份懸置狀態。
(一)不斷易名,過漂泊流浪生活的海克特·曼
在《幻影書》中主人公海克特·曼就多次改變自己的名字和身份,甚至到最后連自己也無法分清自己到底是誰。海克特·曼初入演藝圈時為了隱瞞自己猶太人身份,他給自己起了新的名字:錢恩·曼德波,這個名字使海克特·曼更容易被圈內人所認可,而不至于忍受別人對猶太人異樣的眼光,“要想在非猶太世界獲得成功,猶太人就得像他的公民同胞那樣穿著打扮,就得避免意第緒語口音,克制自己不去遵守猶太飲食法,并使用非猶太人的名字”[9]248。 最初海克特·曼使用的非猶太人名字確實為他在演藝圈提供了很多優勢,贏得了很多非猶太人的喜愛,在二、三十年代成為一名出色的默片電影演員,在演藝圈已經有很大的影響力,但是一場意外導致他的出走。他的未婚妻德洛麗絲·圣瓊意外槍殺了他已經懷孕的前女友布莉姬·奧夫倫,為了免受法律懲罰,他選擇了協助未婚妻將前女友尸體秘密掩埋。在這種情況下,他拋棄了海克特·曼的身份,剃掉了他標志性的小胡子,完成自我外形的改造,把自己偽裝起來。當他在廁所隔間找到一頂“赫爾曼·萊斯”的帽子時候,海克特覺得這個名字極好,正如小說所說:“海克特被這個名字打動了,這是個好名字,甚至可以說是個極好的名字,甚至不比任何名字差。海克特·曼連在一切就是赫爾曼,不是嗎?如果他稱自己為赫爾曼,他就既能改變身份又不用完全與過去斷絕關系”[9]248。在選用這個名字時候,海克特·曼覺得這個名字和他以前的名字有聯系,才選用這個名字,說明他自身身份認同上不想和以前徹底隔絕,還想擁有自己以往的身份。之后海克特·曼開始了自我流浪漂泊的生活,先是在碼頭上工作,又做過守夜人,之后他突發奇想來到了已故前女友夫妻開的運動用品商店,在近一年的時間里他一直扮演著勤勤懇懇、任勞任怨的店員身份,他的內心也漸漸變得平靜,這種自我贖罪也大大減輕了他內心深處的負罪感。但當老奧芙倫暗示他去向諾拉求婚時,他再一次落荒而逃。他無法克服內心的負罪感,幾次企圖自殺均未遂的情況下,在妓女西爾維亞·彌爾絲的引誘下,他們搭檔進行公開性表演,海克特·曼以這種自我毀滅的方式消解內心對誤傷前女友的負罪感。在他和妓女西爾維亞·彌爾斯因薪酬分配不均起爭執,西爾維亞揭露他的真實身份后,海克特·曼又逃走了,開始了另外一次流浪生活,直至他在流浪中去銀行取暖時候,偶遇芙芮達·斯貝林,并與其相愛結婚。婚后他隨妻姓,他的名字再一次變為海克特·斯貝林,并用這個名字在藍石農場生活,直至在農場去世。
縱觀海克特·曼所更改的名字,從海克特·曼——錢恩·曼德波——赫爾曼·萊斯——海克特·斯貝林,如果說海克特·曼到錢恩·曼德波是為了取得事業成功,這個名字倒是為他帶來了短暫的聲譽和穩定富有的生活;后面的赫爾曼·萊斯和海克特·斯貝林卻是逃亡路上為躲避法律制裁而掩人耳目的臨時名字。海克特名字的變化,他的所扮演的不同的社會角色,是他自己,又不是他自己,人物身份的自我認證出現危機,人物身份也處于懸置狀態。這種幽靈般的存在,時隱時現,使得海克特呈現在人們面前的永遠是不完整的、碎片化的,主人公在自我失落的生活中痛苦的掙扎。“名字身份的不斷變更,使得自我和名字一直處于分裂狀態,自我意義充滿了不確定性,名字符號在建構、消解、重構中自我的源頭已經消失,自我在本質上成為了不可知[10]。”
(二)《玻璃城》人物的名字懸置研究
1.多個名字致多重身份、人格分裂的奎恩
在后現代的語境下,人物專名消失,使得名字的能指和所指不能統一起來,變得混亂,這種混亂使得表征自我逐漸分裂。自我分裂導致主體喪失整體意識,在不同時間獲得的不同名字,主體統一的自我狀態不能形成。正如所說“我們包含相互矛盾的身份認同,力量指向四面八方,因此我們的身份認同總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11]208-222。
在《玻璃城》城中的奎恩曾經遭受家庭災難,因為妻子和兒子意外身亡,令奎恩對生活變得萬念俱灰,從滿心抱負的年輕人變成了一直盼望死亡的消沉者,只是生活在表面,過無意義的生活。“他每一次散步出去,都會覺得他把自己撇在身后了。一邊走一邊就把自己丟在了街上,因為把感知能力降至僅僅是一雙眼睛的視覺,這就逃避了思考的義務。只有這種方式,才能使他得到一種內心的平靜,一種驅邪安神的虛空。——這種感受,最后就成了他所期望的情形:身處烏有之鄉[12]。”他開始用威廉姆·威爾遜的筆名寫懸疑小說;用威廉姆·威爾遜的名字跟編輯、經紀人、書商聯系,發表小說,自己的真名奎恩反而變得如此陌生,無人知曉。奎恩也用自己作品中人物的名字麥克斯·沃克來命名自己,他在生活中頭腦里認為自己要么是威爾遜,要么是沃克,不停轉換的雙重身份,后來在頻繁使用中,他用作品里虛構的人名沃克取代了威爾遜,成為奎恩使用的唯一身份,“威爾遜如同口技的表演者,奎恩自己是傀儡,沃克則是賦予表演以意義的充滿活力的發生者。威爾遜不存在,他不過是奎恩由自身通向沃克的橋梁[12]。”奎恩就活在這三個人名中,到底哪一個是他本身,連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了。這里貌似主人公接受了新的名字,與過去的自我一刀兩斷了,但是新的名字并沒與獲得真正的認同感,舊名字又不用了,這造成了名字的能指與所指出現了斷裂,人物身份陷入懸置狀態。一般來說名字是個人的標識,沒有名字存在的個體往往也不存在自我,更被排除在社會體系之外[11]。因為別人偶然三次打錯電話要找叫保羅·奧斯特的偵探,于是他接受了別人賦予他的名字,從而拋棄了自己作家身份和名字,成為了名偵探保羅·奧斯特。名字改變使得舊有的自我喪失了,雖然獲取了新的身份、新的自我,但是新名字和新身份,并沒有使得主體獲得安全感和穩定的身份定位,反而使個體喪失了主體性。他開始用保羅·奧斯特的名字去跟蹤、監視老斯蒂爾曼,開始了一段近乎流浪而又毫無意義的生活。在長時間跟蹤無果,毫無收獲的情況下,奎恩開始故意近距離接近老斯蒂爾曼,前后三次使用了不同的名字。第一次是自己的真實名字奎恩,第二次是用老斯蒂爾曼作品中的名字—亨利·達克,第三次使用老斯蒂爾曼兒子小斯蒂爾曼的名字跟蹤。他也用改變名字的方式使得自己變得模糊不清,個體身份變得不可識別,以此來迷惑老斯蒂爾曼,掩蓋自己真實的身份。從中可見名字的專屬性和人物身份的變化。
2.自我頻繁命名、意識混亂的小斯蒂爾曼
被父親囚禁了九年之久的小彼得·斯蒂爾曼也是自我頻繁命名,導致語言秩序混亂,人物身份變得懸置不清。小彼得曾經被其父老斯蒂爾曼囚于一間與世隔絕的房間,讓其自然習得上帝的語言,當被解救后,即便在醫院里住院治療了十三年,也不能完全掌握人類的語言,導致他無法確立自己的身份,喪失獨立主體性。他在和偵探奎恩的談話中,起初說“我的名字是彼得·斯蒂爾曼。那不是我的真名。我的真名是賽德先生(Mr Sad)[12]。”這個名字是有內涵的,Sad就是“傷心”的意思,小斯蒂爾曼之所以變成現在這樣子,應該說是他人生的悲劇,從而我們可以看出老斯蒂爾曼為了獲得純正的上帝語言的瘋狂之舉。后來,小斯蒂爾曼把自己稱作Nobody,翻譯成漢語就是“沒有人”,而這一個名字也是有很深的含義的,因為“沒有人”一般是指人的肉體存在方式不存在,Nobody的名字其實是對自身存在感的自我否定,沒有感情,沒有發展人類智慧,無法認清自己的身份,如同空心的機器人一般,毫無感情可言。對于小斯蒂爾曼而言,他作為父親語言實驗的犧牲品,雖然經歷了長達十三年的醫院治療,并沒有幫助他恢復到正常人的認知水平,他的存在其實就是如同沒有情感、冷漠無比的機器人。一個名字折射出人物自身的精神狀況和作者對其恰如其分的評價。在交談了幾分鐘后,他又宣稱:“我是彼得·斯蒂爾曼。那不是我的真正的名字。我的真名是彼得·萊比特(Peter Rabbit)。在冬天我是懷特先生(Mr White),夏天我是格林先生(Mr Green)[12]。”從文中我們能看到名字與人物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能指符號與所指之間聯系的直接斷裂,而且在隨后與奎恩的對話中,小彼得再次聲明,:“就現在而言,我仍然是彼得·斯蒂爾曼。那不是我的真名。我不知道我明天會是誰。我每天都是新的,我每天都會出生。”加上之前他所說的“我在早晨醒來時出生,在白天長大,在晚上睡覺時就死去。”一個一個的名字,人物無法獲得穩定的社會身份,人物的思維是混亂的,呈現精神分裂者的主體認知模式。語言是一套特殊的表達人類思想和情感的符號,而人名也是一種特殊的語言。索緒爾說:“語言是表達思想的符號系統,因此,它類似于文字、聾啞語字母表、象征儀式、社交禮節、軍事信號等等,只不過語言是這些系統中最為重要的一個。”沒有正常語言和認知,人物也不能正常表達思維感情,小說中人物名字懸置在塑造人物形象和推動故事發展起到了單純語言不能表達的作用。
3.懷疑自我存在感的雇主懷特
在《幽靈》中雇主懷特雇傭布魯監視布來克(Black)。布來克是懷特意撰出來的人物,沒有實體存在的城市幽靈。布魯自從接受雇主交給他的監視布來克的任務后,每天跟蹤布來克,這樣過了很長一段時間,發現布來克的生活幾乎沒有什么變化,只是每天坐在桌前看書、寫作、吃飯。布魯試圖揣測布來克的行為,而布來克本來就是一個不確定的、沒有實際意義的個體,雇主本身是依靠他者實現把握自我,擺脫自身茫然若失的情緒狀態的,但是布魯對此卻完全不知情,他在監視和追尋布來克的過程中迷失了自我,變得不可知,在現實和虛構之間分不清自己的身份,“我叫什么名字,我是誰”,身份也變得模糊不可見,名字本身的所指意義也消失了。索緒爾認為,“語言不是簡單將任意的名詞分配給我一組獨立存在的概念,而是在其自選的能指與所指之間建立一種任意的聯系。每一種語言都用過一種獨特的,因而也是任意的方法將世界構建成概念和類別”。從索緒爾的語言學角度來看,人物名字的喪失意味著自我存在的喪失和主觀意識上認同感的缺失。追尋者布魯監視跟蹤別人,熟不知自己也成為被別人監視追蹤的對象,其自我主體意識完全喪失,迷失在多種可能的迷宮中不能出來。布魯在長期無意義的監視和跟蹤中迷失了自我,一方面他懷疑自己工作的專業性,對工作變得無所適從;另一方面開始懷疑他所接受的偵查案件的真實性,從而考慮自身存在的意義,身份的迷失和自我能指與所指完全斷裂。
三、名字懸置狀態與后現代性關系
后現代主義思潮是最早興起于20世紀60年代,其影響從文學藝術、社會文化逐步進入哲學領域。它是一種與現代主義相對立的一種對待文化和思想的態度。后現代主義強調不確定性,去中心化,反傳統,過分強調否定性,其中不確定性是后現代主義的主要特征。后現代主義打破了世界的理性秩序,使整個世界呈現出多元化、無序性、不確定性。而小說解構深度模式,走向邊緣,走向不確定性是后現代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英國后現代主義文論家戴維·洛奇在他寫的《現代主義、反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書中說,后現代主義反對現代主義典型觀,反對對確定性的追求,認為不確定性是后現代主義的本質特征,從文本的不確定性到作品人物的不確定性。以色列著名學者布萊恩·麥克黑爾認為后現代主義和現代主義的最本質區別是,后現代主義傾向于本體論的多元性和不確定性,現代主義用來解決認識論的難題。文論家伊哈布·哈桑的著作《后現代主義轉折》總結了后現代文藝的主旨和形式特征,“去中心”和“不確定性”就是其中他主張的后現代主義文學的根本特征之一。
在奧斯特筆下描寫的變幻莫測的世界里,人物自我身份無法確認,甚至連自我也無從完整展現在自己面前。奧斯特這種迷宮式寫作手法被用來表現當代人的自我生存狀態,打破傳統的時空觀和線性敘事,人物名字和自我身份都充滿了不確定性。他的這種寫作手法符合后現代的寫作風格。
保羅·奧斯特作為后現代主義作家,他的作品也打上后現代文學的烙印,他的作品“不確定性”具體表現為:人物形象的不確定性,虛實結合,文章解讀和中心意義具有不確定性。通過人物自身多變的名字,作為全知全能的第三敘事方式,讀者了解到不同人物名字的指向性,如威廉姆·威爾遜、麥克斯·沃克,保羅·奧斯特都是指奎恩,雖然他在不同場合使用不同的名字,但是作為讀者還是能立刻識別人物身份。至于小斯蒂爾曼對自己名字反復無常的變化,蘊含著作家描寫人物形象的手法,混亂的名字恰恰是表明他是其父語言實驗的犧牲品。他父親沒有獲得純正的上帝語言,他的兒子也沒有獲得普通人的語言交流能力。
曾有美國評論家查理斯·巴克斯特(Charles Baxter)評價說:奧斯特的小說從主題上來看,反映了當代人對身份和本體性缺失的恐懼。奧斯特的小說具有獨特的后現代小說特性,并結合后結構主義、精神分析學等后現代主義文論,具備特有的創作技巧。他作品里人名的不確定性恰恰反映了作者對現代語言的關注,這種能指與所指的斷裂表達了對主體消失零散化的迷茫,同時也反映作者自我焦慮以及對這個破碎世界的擔憂。保羅·奧斯特本人是認同穩定的身份構成的,他認為身份是個體在個人生活中的種種角色,體現出個體作為特定名族成員的歷史身份以及參與世界事務的穩定身份。在小說支離破碎、不確定的后現代語境里,人物因名字的變化不再是原有的固定形象,人物性格也因語境變化變得捉摸不定,人物的真實性也變得不確定。索緒爾的語言觀還認為:符號的所指和能指并沒有必然的固定聯系,能指和所指具有任意性。當語言符號鏈條上能指和所指斷裂時,最終語言喪失明確的意義。當代表所指意義上的名字和能指意義上的小說主人公本人失去統一性時,那么人物身份變得不可識別,人物名字懸置最終導致能指變成了“漂浮的能指”,兩者之間不再具有穩定的意指關系。這種表現手法是奧斯特對人物主體性探討,是后現代語境下不確定的主體觀,讀者從中可以對后現代理論下的文章有更深入了解。
四、結語
本文通過閱讀保羅·奧斯特的小說文本,分析其中主人公和各色人物名字頻繁變幻,或者自我命名,導致人物因這種名字游戲身份懸置、身份不斷變化,自我社會認同感喪失,與社會脫節等。奧斯特作為一名寫作手法高超的著名作家,通過這種人物頻繁命名,將人名與社會中的個體陷入無盡的能指鏈條,喪失主體性,這點恰好是他后現代寫作手法的集中體現。“去中心、不確定性”——后現代的主要特征在其小說文本中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