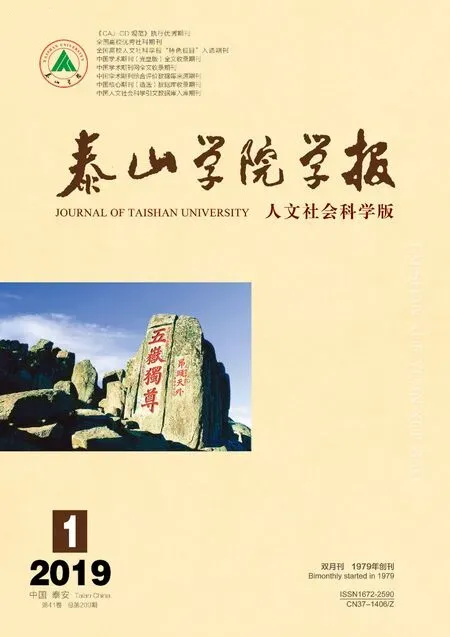論晚清四大詞人與光宣吳中詞壇
閆毓燕
(蘇州大學 文學院 江蘇 蘇州 215123)
作為引領一時風會的詞壇人物,晚清四大詞人王鵬運、朱祖謀、鄭文焯及況周頤對于晚清乃至民國詞壇影響深遠。因緣際會,光宣時期這四位詞人與蘇州都有著很深的淵源,吳中詞壇的結社雅集、序跋批校或詞箋往來等詞學交游活動與他們都有直接或者間接的聯系。這些群體性的詞學活動對吳中詞學風氣的興盛產生了不容小覷的推動作用,他們的主導和積極參與,成就了清代吳中詞壇最后的輝煌,也使得吳中詞壇成為可以媲美京、津、滬、寧等地的詞學重鎮。
一、晚清四大詞人與蘇州的因緣際會
蘇州作為江南文化中心之一,向來以風物清嘉、人文薈萃著稱,并以其地理位置之優越、文化積淀之深厚、生活環境之清雅成為文人雅士向往的生活與文學創作的勝地。晚清時期蘇州仍然保持著巨大的吸引力,許多文人流寓蘇州,或為幕客,或作退隱,成為此時蘇州文化發展的重要力量,晚清四大詞人則是其中對詞壇影響最大的流寓文人群體。
王鵬運光緒二十八年(1902)辭官南歸至光緒三十年(1904)寓居揚州期間,曾數次往來于蘇、滬間,會晤詞友,參與詞學交游活動,最后亦因暴病客死于蘇州。朱祖謀光緒三十年(1904)曾出任廣東學政,三十二年(1906)“以病乞解職,卜居吳門”[1](P537),先居蘇州韓家巷鶴園,又于光緒三十三年(1907)獲鄭文焯相助,租蘇州聽楓園而居,至辛亥革命后雖移居滬上,但與吳中詞人唱和交游仍持續不斷。而詞人況周頤平生多輾轉四方,羈遲他鄉,蘇州則是其“十年萍泊”的一處棲息地。況氏曾于光緒十七年(1891)及光緒三十年(1904)兩次客居蘇州,參與當地詞學交游活動,并且在第二次客居時作《玉梅后詞》一集。至晚年寓居滬上時,又時而往還蘇、滬間,與蘇州詞人詞學交游唱和亦往來不斷,如其光緒三十二年(1906)七月二十八日曾與繆荃孫、金武祥等同游蘇州靈巖山。鄭文焯則“以貴公子羈滯吳下”[2](P384),是晚清四大家中在蘇州生活、創作持續時間最長久的一位。自光緒六年(1880)入江蘇巡撫吳子健幕府后,雖因多次進京參加會試,曾有旅居他鄉的經歷,但蘇州依然是其詞學創作、交游活動的主要陣地。光緒二十九年(1903)因多次會試落第,鄭氏遂絕意進取,自刻“江南退士”之印,自此定居于蘇州。鄭氏在蘇州客居三十余年,與吳中詞人結社雅集,交游唱和不斷,其足跡遍及吳中各地。蘇州不僅為其詞學活動提供了活動空間,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其詞學創作的精神家園。其與吳中詞人的雅集唱和較其他三家更為豐富,可以說是四大詞人與吳中詞壇唱和交游的核心人物。
概言之,在光宣時期,晚清四大詞人都或多或少曾在蘇州生活和進行過詞學創作及交游活動,他們與吳中詞壇的因緣際會不僅在表面表現為蘇州這一地域中介為他們提供了詞學交游的地域空間,更在深層次上體現為四位詞人在這一地域內所進行的詞學交游活動,對于吳中詞壇產生的深刻影響。
二、晚清四大詞人與光宣吳中詞壇的詞學交游
晚清四大詞人與光宣吳中詞壇的詞學交游頻繁且形式多樣。以年譜、詞集、詞話、筆記、書札等文獻為依據,本文將晚清四大詞人與吳中詞壇詞人的交游狀況按照交游形式分為結社雅集、詞集序跋與批校以及詞箋往來三類,以便更好地窺見光宣時期四位詞人與吳中詞學發展的緊密聯系。
(一)結社雅集
晚清四大詞人在吳中詞壇的詞學活動首先體現為結社雅集。文人結社雅集是詞學交游活動中最為常見的一種形式,它對于文學風氣的形成和文學趣味的發展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沙先一《清代吳中詞派研究》曾稱:“吳中詞人篤于友情,并非常看中彼此的往還對于文學的影響作用。”[3](P15)加上可借園林之盛作為唱酬之地,文學活動空間充足,故有著悠久的文學雅集結社的傳統。在光宣之前,由戈載等詞人倡導的吳中之社,主要以本籍詞人為主,不僅形成了以嚴審韻律為特色的吳中一派,同時也對后世詞壇產生了深遠影響。至光宣時期,以鄭文焯為代表的寓吳詞人在吳中地區所舉詞社以及所主導的雅集活動,又為吳中結社雅集增添了新的活力。
作為晚清四大詞人中在光宣年間與吳中詞壇聯系最密切的鄭文焯,較之其他三家,對于吳中地區雅集結社的倡導尤為突出。根據鄭氏年譜以及詞序和相關詞社成員記載的資料,可以得知光宣年間吳中重要的詞社和雅集活動大多與鄭氏有關。
鄭文焯在蘇州最早的結社活動為光緒十二年(1886)舉吳社。戴正誠《鄭叔問先生年譜》稱鄭氏“立吳社聊吟,歌弦醉墨,頗具文宴之盛。”[4](P408)戴安常《張祥齡小傳》亦載張氏“僑寓吳中,近烏橋。適鄭文焯在蘇撫幕,共結詞社。十三年有《吳波漚語》和白石詞一卷,凡八十余首,皆叔問、祥齡、順鼎弟兄及成都蔣鴻文聯句之作。”[5](P28)當時參與詞社活動的詞人除鄭文焯外還有易佩紳、易順鼎、易順豫父子三人、張祥齡、蔣文鴻等,他們多為寓吳詞人。有關吳社的具體活動在鄭氏《瘦碧詞》中多有反映,如其《木蘭花慢》小序云:“蔣子次香蜀中詞人也,朅來吳門……今行有日矣,同社既集西樓連句送之,余意更著此解。”[6](P131)《垂楊》詞序:“風雨吳城,屬引凄異,同社方制餞秋詞。”[6](P143)《大酺》詞序亦曰:“余與吳社諸子既連句和石帚詞八十四闋。”[6](P157)鄭氏年譜亦載有其因以詩易鶴而得吳士艷稱,遂置酒林下,招同社賦詞的雅事。以上皆可想見當時鄭文焯與吳社詞人之間過從談宴的盛況。
光緒十四年(1888)鄭文焯在寓所壺園又結壺園詞社。此時,“文廷式離京南下至蘇州,與鄭叔問、蔣次香、張子苾等結社于壺園”[7](P132)。社內成員在景色秀妍的壺園中,“遍和白石詞,以姜詞作為學詞之課程”[8](P480),詞學唱和往來不斷,互相砥礪,推尊白石詞風,體現出鄭文焯早期詞學宗尚所在。
較之前兩次社員人數較為固定,規模相對較小的詞社活動,鄭文焯于光緒二十一年(1895)七月初七日所舉的鷗隱詞社,參與人數和范圍都相對廣泛。鷗隱詞社初期社員有夏敬觀、陳同叔、夏孫桐、劉炳照等人,后來陸續加入唱和的還有繆荃孫、張祥齡、易順鼎等。從劉炳照詩句“更有繆張來不速,壺園宴罷又怡園”可見當時雅集盛況。同時此時期鄭氏與況周頤的交往比較密切,與王鵬運、朱祖謀亦書札詞箋往還不斷,時有唱和。可以說,鷗隱詞社推動了晚清四大詞人與吳中詞人的交往,同時也由于各地詞人的相繼加入,擴大了吳中詞壇在全國的影響。
除了以上詞社活動外,梳理四位詞人的年譜和詞集等相關資料,還可以看到四位詞人積極倡導或參與了此時吳中詞壇的多次雅集活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如光緒十一年(1885),鄭文焯與吳昌碩、金心蘭、潘鐘瑞等人在壺園餞春,此次雅集有金心蘭作圖,同時又有諸位詞人以詩詞題跋,極一時之盛。
此外,光緒十八年(1892)客居蘇州的況周頤與鄭文焯、易順鼎、張祥齡等人同游虎丘,雅集結束后況氏作詞《壽樓春》(遲南枝滿芳)記之,鄭文焯亦有同調詞為贈。況周頤《浣溪沙》詞序亦載:“辛卯、壬辰間,余客吳門,與子芾、叔問素心晨夕,冷吟閑醉,不知有人世升沉也。某夕漏未三商,招子芾集,未至。叔問得浣溪沙前四句,余足成之。”[9](P426)可見當時雅集之盛,唱和之勤。
光緒二十八年(1902)十月,王鵬運自揚州至蘇州,與鄭文焯、沈硯傳、王壬秋等人集天平鄧尉諸山,鄭譜云:“王幼遐給諫受揚州儀董學堂之聘,十月過江來蘇,與先生同游天平鄧尉諸山,晚泊虎山橋,于是有《古香慢》詞。”《古香慢》詞序云:“壬寅歲十月同半塘老人遊鄧尉諸山,晚泊虎山橋,和夢窗滄浪看桂韻。”[6](P9)可為佐證。另,光緒三十四年(1908)春,朱祖謀邀張次珊、褚伯約、鄭文焯、陳銳、夏敬觀等人集其寓所聽楓園,賦詞唱酬。陳銳《瑞龍吟》詞序云:“春光向盡,古微先生邀同張次珊、褚伯約、鄭叔問諸君,集于聽楓園。拍照聯詞,極客中之清致。”[10](P217)此次雅集,朱祖謀有《霜花腴》(聽楓園春集,用夢窗韻)、《瑞龍吟》(寓園餞春,伯弢和清真韻見貽。率酬一解)諸詞,張次珊亦有《霜花腴》(聽楓園禊吟)。
除此之外,朱祖謀與鄭文焯還參與了光緒三十四年(1908)五月十八日,與陳銳、陳三立、張仲炘、張伯琴、吳永、黃小魯等詞人的顧園雅集,宣統二年(1910)夏,與夏敬觀、劉福姚、成多祿等人滄浪亭雅集,宣統三年(1911)正月初七日,與夏敬觀等人的人日雅集等等。
根據以上具有代表性的雅集活動,可以看到晚清四大詞人在蘇州所倡導和參與的詞學雅集,其參與者既有本籍詞人,也有寓吳詞人,雅集地點則多為吳中地區環境高雅的園林之內或者景色宜人的山水之間。這樣的雅集活動不僅使得吳中詞人雅集蔚然成風,同時也促進了各地詞人與吳中詞人的詞學交流。
(二)詞集序跋及批校
詞學交游活動中,詞家往往以詞籍序跋、題詞、題詩等形式互相推舉與標榜,一定程度上亦促進了詞學理論發展。鄭文焯作為晚清四大詞人中與吳中詞壇詞學交游活動最頻繁,范圍最深廣的詞人,對其詞集序跋的梳理,亦能夠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四大詞人與吳中詞壇的交游狀況。
鄭文焯于光緒十四年(1888)冬在蘇州刊刻《瘦碧詞》,寓吳詞人俞樾、易順鼎、張祥齡為之作序。俞樾在序文中稱譽鄭文焯“精于音律”,且為詞“情文相生”。同時,對于吳中詞派代表人物戈載則批評其“深于律,而不甚工于詞”,由此提出了“夫律之不知,固不足言詞,而詞之不工,又何以律為”的詞學主張。[6](P107)張祥齡與易順鼎作為此時期與鄭氏在蘇州結社唱和的重要詞人,在為鄭文焯所作的序文中則各有自己詞學觀念的呈現。張祥齡將鄭文焯與宋詞名家吳文英、張炎、王沂孫、史達祖、姜夔、周邦彥等詞人并舉,以此推尊鄭文焯的創作成就。而易氏則不僅敘述二人徜徉于吳中勝跡中得其“所適之性”,而且提出“詞之為道,言外意內,哀樂橫生,涕笑交沸,百靈奔赴,萬感寂會,邈接神思,妙遺言詮”[6](P116-117)的詞學主張。這些都有助于我們了解光宣時期吳中詞學宗尚的潛衍變化。
鄭文焯《冷紅詞》刊刻于光緒二十二年(1896),前有刊刻者沈瑞琳以及詞友陳銳序。沈瑞琳序稱:“叔問丈之所謂詞者于傳則意內而言外,于詩則出入變風小雅之間,漢魏樂府之遺音,唐宋燕樂之律本也。其為詞造乎端也。……又隱繆其辭,要眇其致,旁寄于一物一事以喻夫忠愛離憂。”[11](P425)陳述了鄭文焯“意內言外”“比興寄托”的詞學主張,表明鄭文焯此時詞學主張向常州詞派的轉向。陳銳在蘇州時與鄭文焯多有唱和,其序中言鄭氏“于詞導源樂府,振騷雅于微言,掩周姜而孤上”[11](P421),也是對鄭氏詞學主張的闡發。此外,朱祖謀序鄭文焯《苕雅余集》,稱許鄭氏“聲文之感人深”[6](P4-5)的詞學成就,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兩人對于注重詞作立意與韻律兼備的追求。除了上述序文外,還有不少序跋散見于與四位詞人有詞學交往的詞人的詞籍中。這些詞籍序跋作為晚清四大詞人與吳中詞人詞學交游文獻中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可以很好地反映出詞人的交游狀況。同時在序跋中對于詞學理念和詞學宗尚的闡發,對吳中詞壇群體趣味的形成也會有推波助瀾的影響。
晚清時期,詞籍校勘開始興盛,詞學交游不僅僅體現在傳統的結社雅集、序跋題詞等在創作手法和藝術宗尚的切磋上,同時也表現在校詞上的相互交流。晚清四大詞人中王、朱二人于詞籍校勘有開創之功,并取得了巨大成就,鄭、況二人則在兩位先導的指引下也取得了諸多校勘實績。因此“在晚清民初的一段時間里,王、鄭、朱三家在詞集校勘上是聲氣相求,互相溝通的,構成了一個詞籍校勘團體[8](P339)。”而與吳中詞壇有關聯的詞集校勘則主要以王、朱二人至蘇州以后與鄭文焯在校勘上的探討最具代表性。
光緒二十八年(1902)九月二十八日,王鵬運南游至蘇州,將其與朱祖謀精校過的《夢窗甲乙丙丁稿》贈予鄭文焯,并且敦促鄭氏致力于校詞之學。鄭文焯據此本批校,先后校勘數十次,可謂用力至深,其校勘成果在《鄭文焯手批夢窗詞》中可知一二。光緒三十二年(1906)朱祖謀退隱吳門,與鄭文焯卜鄰而居,二人素心晨夕,有了更加密切的交往。兩人此時在校勘蘇東坡、周清真等人詞集的同時,也致力于對夢窗詞的校勘。三位詞人對夢窗詞的校勘,大到校勘理念的探討,小到詞律字聲的細究,“使得詞籍校勘成為了晚清民國的專門學問,為后人的詞學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8](P349)”,后來民國時期吳中詞人致力于校詞的風氣與此不無關聯。
(三)詞箋往來
書札也是詞人交游的重要載體,光宣時期,晚清四大詞人彼此之間,以及與活躍在吳中詞壇的其他詞人間亦多有論詞書札往還。這些書札或呈現眾人詞學交游的細節,或商討詞籍校勘與刊刻,或闡發詞學主張,推揚詞學風氣,具有較高的詞學研究價值。
其中有關詞學理念的討論,可以舉鄭文焯致張爾田信一札為例,時張爾田正寓居蘇州,與鄭文焯詞學交游甚密。在這份“明陰洞陽,深抉詞隱”[12]的書札中,鄭文焯提出了自己關于詞學問題的諸多見解,其中既有“總之體尚清空,則藻不虛綺,語必妥溜”的關于詞之“清空”風貌的闡發,亦有“聲調從律呂而生,依永和聲,聲文相會,乃為佳制”的關于立意與聲律并重的揭示,同時也有尊體思想的體現。類似的還有鄭文焯與夏敬觀、王鵬運、吳昌綬、朱祖謀、陳銳、劉炳照等人之間的詞學信札往來。[13]這些信札內容豐富,大多涉及詞學相關問題,對于考察晚清四大家與吳中詞壇的詞學交往及理解詞人的詞學思想具有重要價值和意義。
除了關于詞學理念的討論外,對于詞集校勘進行專門的探討也是晚清四大詞人詞箋往還的重要內容。誠如楊傳慶《論詞書札萃編前言》所揭示的那樣:“鄭文焯與朱祖謀同居蘇州期間,二人有不少專門討論詞籍校勘之事的信札。”[8](P346)此外,龍榆生所輯朱彊村論詞遺札按語稱:“以上各札從彊村先生遺篋中錄出,尚有吳伯宛、曹君直諸君與先生商量校詞書簡一束。”[14](P166)皆可從中窺見朱祖謀、鄭文焯等與吳中詞壇其他詞人通過書札商討詞籍校勘信息。
總而言之,除了傳統意義上結社雅集的詞學交游之外,晚清四大詞人亦通過詞集序跋與批校以及詞學信箋往還與吳中詞壇的相關詞人進行詞學交往。這樣形式多樣的詞學交游活動,不僅加深了四位詞人相互之間的詞學理論交流,同時也對圍繞在他們周圍的諸多詞人,以及其所處的詞學創作中心產生深遠影響。
三、晚清四大詞人詞學交游活動對吳中詞壇的影響
正如曾大興《文學地理學研究》中所稱:“一個文學家遷徙流動到一個新的地方,除了有選擇地吸收、消化當地的人文養料,他在當地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活動,也會對當地人文環境的總體構成給予或多或少的影響,即反哺于當地的文化。”[15](P25-26)晚清四大詞人在流寓吳地過程中的詞學交游自然會對吳中詞壇產生一定的影響,概言之,以下幾個方面體現得最為明顯:
(一)詞學理念的繼承與新變
晚清四大家流寓吳地時,都有選擇地接受了吳中詞壇固有的詞學理念,特別是嚴審聲律的詞學思想。當然吳中詞派本身游離于浙西、常州兩派的詞學追求,也對晚清四大家產生了影響,兩者之間是雙向互動的關系。而晚清四大家作為主導光宣詞壇的巨擘,其在吳中詞壇的唱和交游,自然會帶來自身獨有的詞學觀念,進而深刻影響到吳中詞人的詞學思想和吳中詞壇的風貌。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促進了活躍在吳中詞壇的詞人對于吳中詞學傳統的繼承。吳中詞學向來以追求聲律謹嚴為主,且詞風多宗南宋,而晚清四大詞人在詞學主張上亦嚴于聲律,在諸多詞學交游討論中多有對持律謹嚴的闡發。當他們融入光宣時期整個吳中詞學大環境時,其自身以及在詞學交游中的影響力,自然會使得本來就重視承繼“吳派宗風”的吳中詞人加強對于詞學傳統的認同和繼承。這使得吳中詞壇能始終保持著一脈相承的詞學傳統,甚至直至民國時期我們依然可以看到這種傳統的延續;其次,晚清四大詞人詞學宗尚不主一家,特別是朱祖謀后期熔鑄常、浙兩派的詞學觀對吳中詞壇的詞風宗尚產生積極影響;第三,由于吳中詞壇自嘉道時期吳中詞派崛起,詞多寫山水清幽與詩酒風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對現實社會生活內容的反映。此種缺陷發展至光宣時期有所改觀,這除了是由于詞壇因應晚清衰世沉重的社會所作的自然調整外,晚清四大詞人詞學理念的濡染之功亦不容忽視。
(二)創作風氣的浸潤與重振
群體性的詞學活動顯然對詞學風氣的形成產生著巨大的推動作用。“一個詞人群體在統一地域的反復唱和,這一現象本身就極易造成很大的聲勢,使群體的影響不斷擴大。”[3](P17)作為光宣時期活躍在吳中詞壇的核心人物,晚清四大家在創作上形成的濃郁氛圍對于這一時期吳中詞人的創作風氣有一定的熏染浸潤的作用。清代吳中詞壇以嘉道年間吳中聲律詞派的興起而發展至盛,到咸同時期由于吳中大亂而導致詞壇不再如往日興盛,走向了岑寂衰落,詞壇創作風氣不復往日之盛。雖然也間或有詞人結社交游創作,但是并未形成聲勢。而到光宣時期,晚清四大詞人以及其他流寓詞人,與吳中本籍詞人頻繁地交游唱和,各種詞學活動吸引了眾多詞人的加入,吳中詞壇風氣遂得以重振。流風所及,直至民國時期,吳中詞壇依然是弦歌不輟。
(三)詞史地位的提升和奠定
光宣時期,詞人“結社唱和活動十分頻繁,已經進入了理論自覺和組織嚴密的階段,因而極大地促進了晚清詞學的復興”[16](P274)。京津、滬寧是最重要的詞學中心,而晚清四大家在光宣時期除了寓居蘇州,與吳中詞人交游唱和外,亦常往來于京、津、滬、寧之間,與各地詞人多有詞學往還。這種廣泛的詞學交游,加強了吳中詞壇與其他詞學中心的互動,使得吳中詞壇在這一時期發展成為可與其他詞學中心相頡頏的又一詞學重鎮。可以說這一時期的吳中詞壇,正是由于晚清四大家所引領的切磋唱和與校勘交游活動,使其在承上啟下的發展過程中,呈現了新的發展成就,也成就了吳中詞壇在清代最后的輝煌。
綜上所述,光宣時期晚清四大詞人在吳中詞壇豐富的詞學活動,不僅為吳中詞壇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且在其廣泛的交游中拉近了吳中詞壇與其他地域性詞壇的距離,加強了與其他詞壇更為深入的交流,提升了吳中詞壇的地位。吳中詞學所以能成為晚清詞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晚清四大詞人可謂居功至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