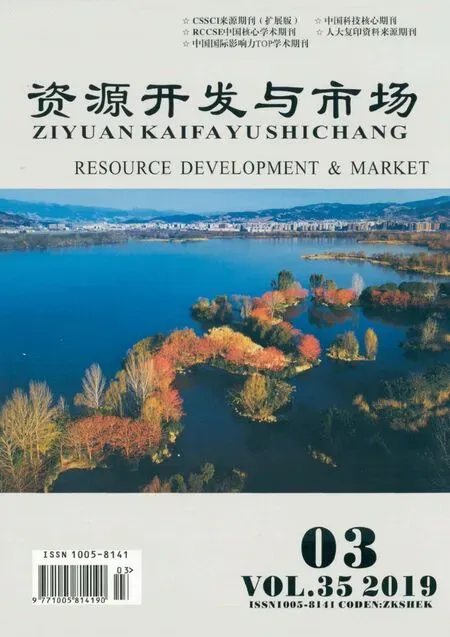多民族共生區農村聚落研究綜述
王若菲a,李 君b,王 濤a,陳長瑤
(云南師范大學 a.旅游與地理科學學院;b.經濟與管理學院;c.泛亞商學院,云南 昆明 650500)
1 引言
農戶居住空間即農村聚落,是農戶與周圍自然、經濟、社會、政治環境長期相互作用的結果。目前,我國城鎮化建設進程不斷加快,建設范圍逐步擴大,影響正在向農村地區拓展。截止2017年,我國農村仍有5.76億人,占全國總人口的41.48%。同時,我國民族多樣化特征明顯,各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相互交融、共生發展,形成了現有的“大雜居、小聚居”的空間分布形態。多民族共生區農村
聚落同樣承擔著重要的居住、生產、生活等功能,但由于多民族地區共生關系和形態、宗教、經濟貿易、文化融合、社區發展等特點,其聚落發展也呈現出一定的獨特性。
本文主要從地理學的視角對多民族共生區農村聚落區位、規模形態與等級、功能結構、空間演變、優化與重構等方面對國內多民族共生區農戶居住空間的研究進行了綜述。
2 多民族共生區的農村聚落研究
2.1 農村聚落區位及其影響因素研究
基于人地關系的聚落區位及其影響因素一直是地理學界研究的重點,探討區位選擇與環境、資源、經濟、社會、文明間的關系及作用機制,農村聚落的區位是聚落區位研究的主要模塊,是國內外研究的重要內容。目前,農村聚落區位研究主要側重于單一民族地區的研究,從定性描述轉向定量研究,依托遙感技術的發展,采用多元化的手段對農村聚落區位及其周邊的環境、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的關系進行建模分析[1],涌現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多民族共生區農村聚落的區位研究發展緩慢,主要是對多民族地區現有的區位布局特征形成的歷史原因、現狀、空間分布特征其發展趨勢等進行分析。賈偉等分析了安多地區多民族文化共生格局的特點,認為安多地區多民族共生格局形成的基礎性因素是社會經濟互補性,其作用會隨著時間變化在廣度和深度上持續增強[2];周智生、張黎波從歷史地理學的角度出發,基于特殊地域空間尺度與歷史的交集中,梳理了云南多民族共生格局的基本形貌,總結提煉了歷史形成機理與啟示[3];楊宇亮等以GIS技術方法結合田野調查,探討了云南元江南岸4個縣不同級別的多民族共生聚落空間特征,從宏觀層面總結了該地區的多民族共生聚落具有沿流域水平方向分布、沿垂直方向的垂直分層、按時間累積的同源聚居特征[4]。
2.2 農村聚落規模形態與分類研究
農村聚落形態和分類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農村聚落地域空間分異的規律和特征[5],不同地形下,農村聚落的大小、形狀都有所差別,而在此基礎上多民族地區的聚落形態和類型的多樣性特征更加明顯。民族聚落規模形態研究起步于建筑學,現今融入了民族文化學、地理學、景觀生態學等多學科的觀點,進入綜合性研究階段。管彥波認為,西南民族聚落具有顯著的地域差異,聚落形態受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的雙重影響而形成,與該地區民族的分布特征相關聯,呈現“大分散、小聚居”的特征,主要分為聚集型和散漫型兩種基本形態[6];吳雨濃、張縱以務川仡佬族古村落為例,從聚落地理人文環境、分布形態、內部結構和聚落特征方面,對具有特色文化的少數民族聚落景觀進行了探析[7];杜佳對貴州喀斯特地區民族農村聚落進行了調研,選取13個典型村落分析了喀斯特山區不同類型聚落的空間形態特征、當代演變特征、影響因素與各類型聚落形態表征間的關系[8];侯兆銘等對西南地區土家族聚落形態進行了實地測繪,歸納了聚落形態的典型特征,揭示了土家族傳統聚落形態是人地關系、生產力水平和民族風俗文化的綜合體現[9]。
2.3 農村聚落空間結構與功能研究
在農村聚落空間研究中結構和功能是一組不可分離的命題,組成農村聚落的環境、民居、基礎設施、公共場地等與村落提供的生產、生活、生存等基礎功能是相互依存的關系。多民族共生區農村聚落的空間結構和功能比普通的農村聚落更復雜,它不僅具有一般農村聚落的結構和功能,還是民族文化產生和發展的載體。目前學界對多民族共生區農村聚落空間結構和功能研究主要是從建筑學或規劃學的視角出發,通過對單一民族聚落的現有空間形態特征進行分析,再進一步探討其空間結構與功能演化。鄭景文分析了廣西桂北多民族共生區農村聚落的空間結構,從聚落空間特征與構成出發闡述了聚落內部和外部網絡的關系[10];楊寶康從佤族聚落的內部空間結構要素,如建筑、防御設施、水利、道路、寨樁、墓地等入手,分析了佤族聚落與地形、氣候、水文、土壤和植被等自然環境要素和生產力發展水平、家族制度、宗教信仰等人文因素的關系[11];金雙對貴州侗族傳統聚落的公共空間進行調研,從歷史性、功能性、社會性三方面分析了其空間特質[12];王莉莉選取云南院落式、民居聚落干欄式民居聚落和土掌房式民居聚落的三個典型村落作為個案研究,從建筑學視角出發解析了多民族共生區農村聚落的空間結構和影響因素[13];馬少春通過分析環洱海多民族地區農村聚落的歷史表征和現有聚落情況,構建了多民族共生環境下的農村聚落系統“結構—功能雙維度”動態分析框架[14]。
2.4 農村聚落空間演變與影響因素研究
農村聚落空間形成是區域自然、社會、經濟、政策和歷史發展環境影響下的行為主體居住區人為選擇過程的綜合體現。在自然情況下,農村聚落空間演變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其特征反映在區域內外綜合環境因素作用下農村聚落空間布局以及功能組合的變化中[15]。多民族共生區農村聚落的空間演變研究主要是從宏觀層面對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的景觀格局、空間形態的演變及其影響因素進行探討。宗路平等以紅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觀區內的農村聚落景觀為研究對象,通過實地調查、訪談和GIS制圖分析等方法,分析了哈尼聚落景觀的組成要素與內部結構、景觀空間格局及其演變[16];王禹皓分析了1999—2015年大理雙廊聚落空間的演變歷程,運用大量圖片和調研成果對聚落空間演化規律進行了探究,揭示出雙廊鎮演化過程的內外因素[17];馬文參、徐增讓基于高分影像數據,借助ENVI和ArcGIS,從村落—庭院尺度刻畫了西藏當雄縣當曲流域聚落的演變,分析了聚落演變的影響因子和影響機制,探討了牧區聚落優化的路徑[18]。
2.5 農村聚落空間優化與重構研究
農村聚落空間重構包含對農村聚落空間的現狀評價和重新規劃的過程,在一定程度上關系到農村聚落空間布局的重新定位,包括微觀上的農戶用地規模、用地類型、聚落的集中布局[19,20],以及中觀、宏觀上對農村聚落數量和布局的重組[21]。多民族共生區農村聚落空間重構作為新農村規劃建設和城鎮化進程的主要內容,涉及民族和諧共生背景下的農村各類資源要素的重新重組與整合。鄧春風、石曉紅、黃耀志從社會和空間兩個視角分析了桂北少數民族聚落空間重構特征,從轉變價值觀念、提高就業水平、注重特色引導和集聚發展等方面提出策略以解決重構出現的問題[22];唐承麗等基于農村聚落空間與生活質量的雙向循環互動機理,從農村聚落空間功能整合、空間結構優化、空間尺度調控研究了農村聚落空間優化問題[23],對民族聚落具有較好的指導意義;張璐等在少數民族村落農戶問卷調查的基礎上,運用二元Logistic模型對農戶遷居至中心村的影響因素和遷居意愿進行了回歸分析,并對少數民族地區農村聚落空間的重構研究進行了補充[24]。
3 多民族共生區農村聚落發展衍生研究
多民族共生區農村聚落是在多因素交互影響下的共生環境中形成的。資源博弈下的生計發展、不同文化的調適認同、社會控制下的制度約束共同作用于聚落共生研究系統之中。因此,把握聚落發展的共生基礎、共生模式、形成機制,有利于更清晰地理解聚落發展的過程。
3.1 共生理論、形成機制及共生模式研究
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我國各民族共同適應、共同發展、共同優化,既強調“最高認同意識”,又積極承認各民族在共生系統中的能量釋放和匹配都處于“族內認同”的地位[25],形成了多民族和諧共生的格局。多民族共生區的民族族際關系研究一直是學者關注的重點。袁年興構建了多民族地區共生體系理論框架,認為民族共生發展的運作機制是民族間平等互惠合作,分析了多元一體化條件下的民族共生對稱性互惠合作模式[26,27];丁龍召從各民族間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共生態出發,探討了多民族共生地區正確處理民族關系的方法[28];周智生、張黎波分析了云南多民族共生格局的形成發展,發現多民族共生區的形成既有由地域環境所決定的特殊性,也有社會環境營造塑化成型的一般性[3];李燦松等分析了多民族共生區的自然資源系統和社會文化系統之間交織演進的動態過程,得出多民族地區族際共生關系的演變和調適路徑[29];馬光選、劉強分析了云南多民族共生地區民族關系演變的集中和影響因素,歸納總結出民族關系的“互嵌—共生”模式[30];蔣士會、黃慶雷基于多元文化交往碰撞的客觀前提下探索了我國多元民族共生融合模式[31],對促進多民族共生區的文化的交融、優化與發展提供了幫助。
3.2 經濟貿易關系與影響因素研究
我國少數民族早期大多居住在交通不便、經濟發展較慢的區域,特殊的地理環境下,各民族為尋求自身的發展,在長期的過程中形成了一種依托經濟貿易的共生格局,通過以物易物或經濟鏈條維系各民族間的和諧共生。研究多民族地區的經濟共生格局,總結其發展機理,構建發展模式,有利于多民族共生區的持續與協調發展。20世紀80年代就有學者提出多民族經濟開發區的設想與研究實施。例如,蘇克勤以黃河上游甘寧青三省少數民族聚居區為發展區域,分析了三省的資源、區位及其發展潛力,在政府的協商探討后,對多民族聚居區的經濟發展提供了發展思路和方向[32];周智生、李燦松等在近十年間對滇藏交界帶上的藏彝走廊多民族經濟共生格局的民族族際關系、格局、時空演進模式和優化路徑做了深度研究,揭示了經濟因素作用下藏彝走廊多民族的共生機理[33-36];紀國峰從少數民族經濟和地區經濟形態的關系出發,概述了各民族經濟和多民族間經濟關系的發展模式、特征、現在、歷史和相互間的聯系[37]。另外,對多民族聚居區的經濟發展進行剖析,探討經濟與多民族共生格局的形成、作用機制、模式總結等為多民族共生區的經濟發展提供了借鑒經驗,也有助于為多民族共生區和諧關系的持續發展提供理論支持。
3.3 宗教信仰與文化共生研究
民族文化是一個民族存在的依據,民族文化各具特色、各自獨立,但又相互印證,共同構成了中華民族璀璨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包含一個民族各方面的內容,主要是語言文字、節日習俗、生活習慣、宗教信仰,在自然、人文和歷史的作用下,各民族的文化呈現出和諧共生發展現象。在這一大背景下,關于民族各方面的研究層出不窮,一方面是宗教和諧共存的現象討論和機理研究。邵媛媛、石弈龍對云南省丙中洛鎮多民族地區多元宗教和諧共存的現象進行了研究探討,并分析了形成機制[38];陳光軍基于康定市的實地調查數據,分析了多民族互嵌式社區和諧宗教關系的現狀、成因和構建,總結了形成的經驗[39];郭志合探討了甘肅省合作市藏回漢多元宗教的歷史和現狀,分析了當地多元宗教信仰共生共榮又相對獨立的共存關系,總結了這一區域存在的模式[40]。另一方面則是文化共生現象的研究。尹未仙對怒江中部多民族共生區的文化共生現象的歷史、現狀進行了研究,分析了該區域多民族文化共生現象的傳承與發展的困境[41];邱仁富構建了我國少數民族地區文化共生發展的傳統模式,將其分為主—客模式、沖突—妥協模式、由邊際共生走向中心共生模式等,反映出遠離國家政治中心的少數民族地區多元文化的傳統交往模式[42];張俊明、劉有安對地處青藏高原文化、中原儒家文化、西域伊斯蘭文化等多元文化交匯之地——河湟地區的多民族文化共生和制衡現象進行了探析,發現該地區各類文化都有相對固定的信仰體和較清晰的邊界,形成了一種既相互滲透又相互制衡的多元文化格局[43];朱慧珍探討了相互影響、相互兼容、相互促進廣西各民族文化的共生態勢,從民族歷史、民族心理、民族生存環境、宗教信仰、民族政策等方面揭示了民族文化共生態勢形成的機理[44]。
3.4 社區的構建和發展研究
在2014年9月召開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我國正式強調了“要推動多民族地區建立相互嵌入式社會結構和社區環境”的必要性,互嵌式社區的建設和研究成為社會和學術界關注的熱點。閆麗娟、孔慶龍在探討民族互嵌型社區概念論爭的基礎上,提出構建民族互嵌型社區需要達成居住空間的互嵌、組織網絡的互嵌、文化接入的互嵌和認同的互嵌四個條件,分析了構建民族互嵌型社區的現實基礎[45];楊昆鳥飛辨析了民族互嵌型社區的基本屬性、民族互嵌型社區建設的內涵和基本特征,結合中央戰略意圖的基礎上,對民族互嵌型社區建設的功能定位進行了探討[46];王茂美基于云南農村多民族社區的實證分析,認為多民族社區無疑是構建和諧民族關系的具體載體與基本單元[47];魏冰研究了互嵌社區的內涵、建設的理論依據,分析了新疆多民族社區建設的基礎,認為互嵌式社區建設是解決新疆民族問題的關鍵[48]。多民族社區的建設研究雖然起步晚,但已有較健全的理論依據和思考,是未來對多民族地區研究的重點。
4 多民族共生區農村聚落研究存在的問題
隨著國內學術界對少數民族地區農村聚落研究的不斷深入,現有研究手段十分豐富,大量運用了定性與定量相結合、實證研究、“3S”技術分析、空間分析、科學建模等多元研究方法,并從不同的學科視角出發,對平原、丘陵、山地等不同地貌以及單一民族地區和多民族聚居區的農村聚落的宗教、文化、經濟等進行了研究探討,取得了較多的成果,但仍存在一些問題。
4.1 理論基礎研究較薄弱
我國農村聚落研究起步晚,發展明顯落后于城市聚落研究。國內學者對農村聚落相關基礎理論的構建不夠重視,目前國內對這一方面的研究理論基本照搬國外,但我國農村聚落發展落后于國外,理論發展更難以媲及。多民族混居情況是一種獨特的民族關系形態,一直以來都是民族學研究的范疇,在學術界雖然有將兩者相結合的研究成果,但都未曾提出相關的理論依據。農村聚落研究理念的空缺、混亂以及多民族共生區聚落的研究理論的空白,局限了國內農村聚落的理論發展。
4.2 基于微觀視角的研究不足
就已有的研究成果來看,大部分學者對多民族共生區農村聚落的研究都是以自然村或行政村為基本研究單元,甚至把整個縣域作為研究單元,將其研究區定義為一個“點”,忽略了各民族的屬性,從較宏觀層面對整個研究區的人地關系進行了分析,忽略了農村聚落的基本構成對象“人”和“人”對聚落產生的影響;或從民族學的視角出發,單一地探討民族間的共生關系、模式、文化融合等現象,忽略了民族生存的環境和各民族的組成成員。隨著研究的深入,人本主義思想和多元化理念在現代學科的思維中越來越重要,原有研究層面顯得較為單薄,研究局限性日益突顯。
4.3 對多民族共生區的聚焦度不夠
目前學界關于農村聚落研究成果的研究區域大都是集中在沿海地區,研究對象偏向傳統村落、空心村、城中村、城鄉交接地帶;對多民族的研究主要是探討現有的多民族聚居區各民族間的共生現象、模式、宗教、文化融合或特殊地形下的個別少數民族聚落發展研究。當前,多民族共生區和農村聚落兩者之間多是獨立研究、各成體系,對兩者結合的多民族共生區的聚居主體即聚落的分析鮮見。研究區過于集中、研究對象普遍,忽略了多民族地區的農村聚落發展,制約了地理學對我國多民族地區美麗農村建設的指導作用。
4.4 研究視角和方法單一,手段運用較少
農村聚落本身就是一個復雜的巨系統,加之多民族聚居區的農村聚落民族構成又為農村聚落研究增加了一層關系。多民族共生區的農村聚落研究涵蓋了眾多學科,需要從一個綜合的角度進行分析。目前地理學界對農村聚落的研究已邁出了多視角融合的一步,空間分析、數學建模、定量分析等手段取得了不錯的成果,但研究視角較單一,多從民族學、景觀生態學、經濟學、社會學角度出發,各學科雖然各有優勢,但相互之間的關聯性差,不能全面揭示多民族共生區農村聚落的演變。
5 多民族共生區農村聚落研究展望
5.1 聚落發展響應及其功能變化研究
我國高度重視西部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對多民族共生區農村聚落的研究符合社會轉型時期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要求,也是響應可持續發展、人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發展的需要。從新農村建設、農村土地利用、農村經濟合作社、農村旅游發展、供給側改革等農村發展的地理現象出發,分析農村聚落的經濟功能變化及其與地理環境間的關聯,從單一的居住功能向居住、工農業生產、經貿場所、旅游地、生態保護地等多元化、綜合性功能轉變的機制和影響因素研究,了解多民族共生區經濟農村聚落經濟發展的路徑和模式,提高多民族共生區社會經濟的發展水平。
5.2 農村聚落發展類型和模式研究
科學研究的目的就是通過對一個區域的研究,總結經驗和模式,為更多的地區提供借鑒,多民族地區農村聚落的研究意義也在于此。選取現代多民族地區農村聚落較典型的區域,通過研究多民族地區農村聚落的空間形態、民族構成、經濟水平、文化宗教融合等,構建可控和定量的預測、方法、指標體系,總結多民族地區農村聚落發展的類型和模式,進行普適性研究,對其進行推廣,可實現西部多民族地區農村聚落的分類調控和優化重構。
5.3 農村聚落空間演變機制研究
學術研究已不再是一門學科單打獨斗的時代了,學科開放性越來越強勁,各學科間的聯系也更加緊密。地理學本身就是一門包容性極強的學科,結合社會行為學、經濟學、生態學等學科觀念,從多元層面分析多民族共生區農村聚落的各系統組成要素及其影響因子。在此基礎上,利用“3S”技術手段對多民族共生區農村聚落的民族屬性、空間格局、空間演變進行綜合分析,脫離原先的研究局限,探討多民族地區農村聚落的空間演變機制,全面解決“是什么、怎么樣、為什么”的問題。
5.4 加強多民族共生區聚落的農戶視角研究
現有的多民族共生區農村聚落是長期歷史過程中自然環境和社會文明相互作用的產物,目前各民族共生區的居住環境更是多重系統在長期歷史過程作用下和諧演進的結果,對其研究一般從宏觀、微觀兩個層面出發。宏觀層面主要通過分析農村聚落的區位、空間分布特征、影響因素、演變機理等來揭示多民族共生區人與環境間的關系,優化居住空間;微觀層面的研究更符合現在的社會背景,是將來各學科的發展重點。多民族共生區農村聚落的微觀層面主要是以農戶為研究單元,借助社會行為學手段,通過研究農戶的行為與區域資源環境間的關系,深入分析農戶的居住現狀、居住需求和遷居意愿,構建農戶行為對多民族共生區農村聚落空間、功能演變的分析框架。
5.5 多民族共生區農村聚落的優化研究
在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農村經濟發展迅猛,但多民族共生區農村聚落的人口、經濟發展、生態環境、空間演變過程間存在較大的地域差異和發展不協調的問題。多民族地區的農村發展問題涉及人口、環境、資源、社會、經濟的各個層面,牽一發而動全身。如何通過對多民族共生區農村聚落的組成、空間形態、演變機制、類型、模式的分析、構建多元的調控指標,提出有針對性的對策,以達到促進其協調發展、保持現有的和諧共生的民族關系,避免產生民族矛盾的目的。未來,要對多民族共生區農村聚落的“三生”環境進行改善,需要綜合利用系統論、統籌發展理論、民族學、社會行為學的觀點,了解其現狀、形態、演變過程、影響因素,研究重點放在多民族共生區農村聚落在現有政策下農戶自愿的前提下全面綜合地進行優化調控或重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