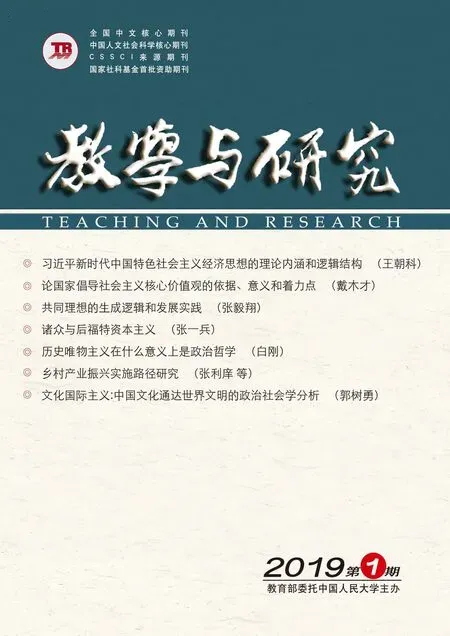超越整體的混沌表象
——資本邏輯系統結構的當代理解
理論只有足夠明晰才能真正切中和引領現實。從抽象上升到具體、從籠統推進至明晰,是對理論的基本要求,也是理論發展的重要進路。對資本邏輯的批判性考察,是解剖現代世界的核心視角,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本質內容。駕馭和超越資本邏輯,建構揚棄資本文明的新型文明,是當代中國通達更高發展之境的關鍵路徑,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標識。然而,學界以往更多地以資本邏輯為工具解剖世界和中國的現代性問題,對資本邏輯本身的解剖,特別是基礎理論的研究卻不夠充分,至今仍然存在較多籠統和模糊的認識,嚴重制約了對資本邏輯的理論澄明與實踐超越,也深層阻礙了以資本邏輯為鑰匙和武器對現代性的反思與批判。在一系列基礎理論問題中,資本邏輯的內容及其結構是一個值得深入思索的前提性問題。資本究竟存在怎樣的邏輯?如果有多種邏輯,它們的關系如何?不無遺憾的是,目前許多研究尚未對這一問題形成足夠自覺的意識,仍然停留在資本邏輯“總體”的層面上,從而,所得到的結果在某種意義和程度上仍然是“關于整體的一個混沌的表象”。[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中央編譯局編譯,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1、513頁。
海爾布隆納分析了資本主義在其本質支配下的邏輯演進與發展階段。哈特和奈格里考察了以帝國作為統治形式的當代資本的統治邏輯。豐子義主張資本具有創造文明與價值增殖的雙重邏輯,并提出后者比前者更為根本、更有決定意義。[注]豐子義:《全球化與資本的雙重邏輯》,《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5期。這是目前對于資本邏輯形態的主要理解范式。馬擁軍考察了資本誕生的邏輯和成長、衰落的邏輯。[注]馬擁軍:《超越對“資本邏輯”的模糊理解》,《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8期。任平等著重剖析了資本的創新邏輯。[注]任平:《資本創新邏輯的當代闡釋》,《學習與探索》2013年第3期。高云涌認為,馬克思將資本本性的邏輯細分為增殖邏輯、運動邏輯、競爭邏輯和風險邏輯。[注]高云涌:《資本邏輯的中國語境與歷史唯物主義的當代使命》,《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16年第1期。必須看到,這些研究有力推進了對資本邏輯內容特別是形態的理解,相較于以往的籠統把握向前邁出了很大一步。但應該說,資本邏輯的系統結構還沒有足夠清晰地顯露出來。無論是具體形態,還是形態間的相互關聯,都需要運用復雜性思維進一步加以敞開。本文嘗試在諸多先賢前輩的基礎上,提出一種對于資本邏輯結構新的理論理解。
學界目前主要將邏輯理解為事物所存在的機理、法則、順序規則等,可進而概括為必然性。例如,海爾布隆納就說自己“是在因果關系意義上使用這個詞的”。[注][美]羅伯特·海爾布隆納:《資本主義的本質與邏輯》,馬林梅譯,東方出版社,2013年,第11頁。從已有文獻看,馬克思不曾直接使用“資本邏輯”的表述,但他經常論及資本的規律、資本的趨勢和資本的機制等問題,亦即資本運動的“必然”。基于此,可以將資本邏輯理解為資本在運動過程中所具有并顯現出的必然性及其展開過程,包括規律、機制與趨勢等具體內容。規律是資本運動的本質的必然聯系,是最高層次和最為抽象的邏輯。規律通過一系列機制展開和實現,這些機制是資本邏輯運行的必然方式與中介。由規律和機制所決定的趨勢是資本運動的必然方向,表征資本邏輯的未來向度。當然,不同層面、不同領域邏輯的力量、效應和地位存在較大差別,有強邏輯與弱邏輯或“大邏輯”與“小邏輯”之分。但只要是資本運動的具有必然性的機理,就可以認定為資本的邏輯或其構成內容。筆者以為,這種理解有助于凝聚學界關于資本邏輯概念的本質共識,較大程度地涵蓋相關研究成果,進而有益于對資本邏輯實際的駕馭與超越。資本運動所呈現出的各具規定性與影響力的邏輯,大致可以界分為四個層次,即總邏輯、核心邏輯、基本邏輯和具體邏輯。它們之間存在著有機聯系,形成了資本邏輯復雜而精密的系統結構。
一、總邏輯:形成、擴張與揚棄
從本質向度看,資本“所進行的總運動”[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中央編譯局編譯,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82頁。或“生活過程”,表現為“資本的生成、它的成長”[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中央編譯局編譯,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1、513頁。和“滅亡”,即在整體上展開為必然性的形成、擴張與揚棄的過程。作為現代世界的主體性存在,資本在形成之后必定不懈增殖和膨脹自身,但又必然由于這種擴張而否定和超越自己,最終走向徹底揚棄,成為更高社會形態的內在因素。這是資本運動過程內含的總的必然性,亦即資本運動的總邏輯。馬克思以畢生心力揭示并論證了這一邏輯。《資本論》及其手稿所分析和強調的主旨正是資本由于無限擴張而根本地揚棄自身的必然性。但到目前為止,它并未得到足夠明晰的闡釋。形成、擴張和揚棄是資本歷史運動的三個關鍵性環節,可以將總邏輯進一步界分為形成邏輯、擴張邏輯和揚棄邏輯。
貨幣轉化為資本,是資本的形成過程。作為商品流通過程的最后產物,貨幣是資本最初的表現形式。每一個新資本開始時都是作為貨幣“出現在市場上——商品市場、勞動市場或貨幣市場上,經過一定的過程,這個貨幣就轉化為資本”。[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中央編譯局編譯,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72、181頁。具體而言,當貨幣將增殖作為主觀目的,把占有抽象財富作為唯一動機,并且能夠較為穩定地“生出”更多貨幣——剩余價值時,資本就真正形成了。一般而言,工業資本和商業資本起初均以貨幣資本形式出現。生息資本更是以貨幣資本的面貌問世。貨幣轉換為資本,本質上是價值轉化為資本。作為一般等價物,貨幣代表的是價值。在資本產生過程中,價值是“自動的主體”。當“價值成了處于過程中的價值,成了處于過程中的貨幣”,[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中央編譯局編譯,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72、181頁。亦即成為自行占有新價值的主體時,也就成為了資本。進一步看,價值轉變為資本,本質上是勞動轉化為資本。價值不過是凝結在商品中的人類勞動而已。資本的形成表面上看是貨幣成為資本,但歸根結底,是勞動轉化為資本。在這個意義上,資本不是在“出生”之后,而是在“出生”之中就將勞動掌控在自己手中。
資本的“成長”集中體現為擴張。資本的擴張首先表現為價值的不斷增大,這是其擴張的核心內涵。資本主義是一個“自我擴張的價值體系”。[注][美]約翰·福斯特:《生態危機與資本主義》,耿建新、宋興無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第29頁。這以作為死勞動或物化勞動的資本,對活勞動尤其剩余勞動的吸吮為基礎。除價值增殖外,資本的擴張也表現為統治和權力的擴大,以及意識形態層面各種拜物教的強化。從主體角度看,資本的擴張表現為對工人以至“諸眾”反抗的瓦解。“在現代意義上的斗爭中,資本所展現出的瓦解由工人階級發起(在經濟和政治兩個層面上)的抵抗的動力是極具擴張性的”。[注][意]安東尼奧·內格里:《超越帝國》,李琨、陸漢臻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4頁。資本既在廣度上竭力擴張,拓展統治空間,在全球絕大部分地區布展開來,完成了真正意義上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又大力開辟支配領域,將社會、文化、生態、道德和身體等盡數納入操控范圍,使它們成為自己的內在構件,衍生出“社會資本”“文化資本”“知識資本”“數字資本”“生態資本”“道德資本”乃至“身體資本”等眾多人們津津樂道的“資本”形態;還在深度上強化擴張,滲透進各種微觀層面,愈加深入地座架和型塑當代人的日常生活,操攝人們的靈魂與行動。持續強化的擴張邏輯讓資本的收益率越來越高于經濟的增長率和勞動的回報率,并使資本的統治和“教化”愈發膨脹。
但擴張邏輯的過度強化也意味著資本揚棄邏輯的來臨。擴張是資本辯證運動的環節,也是其根本揚棄的“前夜”。在馬克思看來,資本的結局并非簡單的“滅亡”,而是徹底揚棄,并且是自我揚棄。這是資本的“天命”。資本構成自身增殖最根本的界限。當價值增殖到一定程度,用馬克思的話說,“超過一定點”,資本就會發生根本性揚棄,成為理想社會的現實基石。從而,人類進入嶄新的發展階段,迎來“真正的人類史”。至此,資本的運動邏輯完整地實現了。雖然鮑德里亞等人認為資本不存在這樣的“辯證法”,但馬克思認為,系統性矛盾推動資本不斷觸碰和突破自身的內外界限,展開具有必然性的內在超越與自我揚棄。不斷擴張的資本在歷史進步中實際地為建構更具合理性與優越性的社會形態提供了越來越豐富的器物、制度與觀念條件,使揚棄邏輯逐步顯露和發展。準確地講,這種揚棄并非如一些論者所認為的是對資本及其邏輯的外在超越,而是資本的內在運行邏輯,是資本運動總邏輯的基本組成部分。還必須注意,資本的自我揚棄并不是外在于人的純粹客觀的過程。這種揚棄同人類主體性的發展與發揮密不可分。事實上,它只有通過人的能動性活動特別是革命性實踐才能真正展開和實現。盡管“主體性”成為被人唾棄的“黃昏”,但不同于“主體主義”,它具有內在的合理因素,只能被超越而不能被取消。一味取消主體性,走向的可能是前主體性,而非“后”主體性或“超”主體性。事實上,對主體性的取消本身就動用了主體性。
雖然這一總邏輯在《資本論》中沒有被直接標示,但卻是內在地蘊含著的。它規定并呈現了資本運動的整體過程。包括價值增殖邏輯在內的其他各種邏輯,所規定和展現的只是資本運動的某個方面或向度。缺失了對總邏輯的理解,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完整、清晰地把握資本邏輯的。因此,它理當得到同其地位相匹配的更為透徹的洞察。
二、核心邏輯:價值增殖
在資本總邏輯當中,存在著一個核心性的內容:價值增殖邏輯。增殖價值不僅是資本的本性,而且是生命線和靈魂。馬克思精辟地指出,資本只有不斷增殖才能存在下去。所以,“資本只有一種生活本能,這就是增殖自身,創造剩余價值,用自己的不變部分即生產資料吮吸盡可能多的剩余勞動”。[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269頁。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積累“對于任何單個資本家都成為一種必要”。[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中央編譯局編譯,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2頁。資本不懈的價值增殖,成為一種既利用人而又超乎人的強大邏輯。“資本劃了一個圓圈,作為圓圈的主體而擴大了,它就是這樣劃著不斷擴大的圓圈,形成螺旋形。”[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中央編譯局編譯,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46頁。大衛·哈維形象地將資本的運動比喻為水的循環,但他也特別強調二者的根本差異:資本運動不是一般的循環,而是不斷增殖和擴張的螺旋。
作為一直以來最受關注的資本邏輯,價值增殖邏輯得到了大量研究。然而,它的整體過程實際上還較為欠缺哲學清理。筆者以為,價值增殖邏輯可以理解為資本生產、實現和分割剩余價值的具有巨大強制力量的必然性。《資本論》三卷分別剖析了剩余價值生產、實現和分割的機理。資本在生產領域生成剩余價值,在流通領域實現剩余價值,之后各種資本形態按照自己的份額及其所蘊含和代表的權力分割剩余價值。剩余價值的生產、實現和分割,作為一條完整連貫的線索,構成資本運動的核心內容,貫穿于《資本論》整個理論部分。
第一卷——資本的生產過程的主要內容就是剩余價值的生產。價值增殖是資本生產過程的真正目的,勞動過程不過是實現這一目的的手段而已。在關于資本形成的必要考察之后,第三篇分析絕對剩余價值的生產,第四篇分析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第五篇則分析絕對剩余價值生產和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綜合及總過程。以上三篇直接分析剩余價值的生產過程。第六篇從勞動力價格的角度考察了剩余價值的形成與增加。第七篇——資本的積累過程中的第二十二章,分析了剩余價值轉化為資本這一整個資本主義生產的關鍵轉換,它讓資本源源不斷地獲取剩余價值。第二十三章所分析的資本主義積累也同剩余價值生產內在一致。顯然,有充分理由認為,剩余價值生產構成資本主義生產的核心。
第二卷——資本的流通過程主要分析的是剩余價值的實現。按照馬克思的看法,“一切現實的危機的最后原因,總是群眾的貧窮和他們的消費受到限制,而與此相對比的是,資本主義生產竭力發展生產力,好像只有社會的絕對的消費能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548頁。換言之,消費能力同生產能力的矛盾,即有效消費能力同實際生產能力不相匹配,構成經濟危機的最后原因。從剩余價值的角度看,這也就是剩余價值的生產和實現之間“永恒”的深刻矛盾。作為資本主義生產的核心性矛盾,它始終內生于資本主義之中,導致經濟危機頻繁爆發。馬克思先在第一卷中假定剩余價值的實現完全沒有問題,而把研究焦點集中于剩余價值的生產。在第二卷中,他反過來“假設剩余價值生產領域沒有任何困難,而把驚險且不穩定的剩余價值實現過程放到顯微鏡下分析”。[注][美]大衛·哈維:《跟大衛·哈維讀〈資本論〉(第二卷)》,謝富勝、李連波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年,第1頁。于是,剩余價值的實現構成了這一卷的主題。無論是單個資本的流通(資本形態變化和周轉),還是社會總資本的流通(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核心目的都是克服剩余價值實現的困難,降低剩余價值實現的成本,最大限度地實現剩余價值。
第三卷——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雖然從標題上看是對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分析,但其內容主要是不同資本形態對剩余價值的分割。誠如馬克思所言,這一卷所要考察的是資本“各種具體形式”的運動。[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9頁。有研究考證,在馬克思手稿中,第三卷的題目為“總過程的各種形態”,研究的重心是資本的“各種形態”。一至三篇分析產業資本和資本一般分割剩余價值的機理。剩余價值轉化為利潤、利潤轉化為平均利潤、利潤率趨向下降,這是作為現代資本典型形態的產業資本分割剩余價值的基本規律。四至六篇分析其他資本形態或所有權形式對剩余價值的分割。商業資本分割商業利潤,生息資本分割利息,土地所有權分割地租。第七篇則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剩余價值分割作了總結。馬克思強調,產業利潤、商業利潤、利息、地租等都不過是作為“純粹形式”的剩余價值的不同組成部分與表現形式而已,它們的本質和源泉都是無產階級剩余勞動所形成的剩余價值。在馬克思心目中,這是他的剩余價值理論超越全部資產階級經濟學的關鍵之點。因而,馬克思對整個剩余價值理論史作了這樣的“總的評論”:“所有經濟學家都犯了一個錯誤:他們不是純粹地就剩余價值本身,而是在利潤和地租這些特殊形式上來考察剩余價值。”[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中央編譯局編譯,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頁。
由此可見,《資本論》理論部分以相當大比重甚至可以說主要篇幅,揭示了剩余價值生產、實現和分割的整體過程。為了揭露整個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剝削無產階級所創造剩余價值的事實,馬克思將剩余價值的生成、實現和分割這一線索暗含在資本的生產、流通和總過程這一邏輯主線之中。或許可以說,剩余價值的生成、實現和分割同資本的生產、流通和總過程的邏輯主線在根本上是同一的。因為,剩余價值和資本在根本上是同一的。資本“創造”剩余價值,而剩余價值又轉化成新的資本。在這個意義上,《資本論》也可以稱為《剩余價值論》。《資本論》理論和歷史兩部分可分別稱為《剩余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史》,亦即馬克思的剩余價值論和馬克思之前的政治經濟學家們對于剩余價值的看法。哈維甚至認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聚焦于剩余價值的生產,將其他一切都暫時擱置”。[注][美]大衛·哈維:《世界的邏輯》,周大昕譯,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337頁。
三、基本邏輯:創造—消解文明
在價值增殖邏輯支配下,資本同時內含創造文明邏輯(或文明化邏輯)與消解文明邏輯(或反文明邏輯)這對相互矛盾的邏輯。學界對創造文明邏輯已有相當深入的研究,在此不再贅述。值得注意的是,資本現實地存在著與之相反的邏輯:使文明成果喪失,文明程度降低,倒退至野蠻、蒙昧的狀態,乃至完全消除文明,即消解文明邏輯。現代是一個眾多思想家紛紛指認的文明與反文明并行和對抗的極其矛盾的時代。西方最早使用文明概念的米拉波就提醒人們,文明和野蠻存在“自然循環”,現代文明有墮落的危險。[注]參見[美]布魯斯·馬茲利什:《文明及其內涵》,汪輝譯,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14頁。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更加直截了當地指出:“人類沒有進入真正的人性狀態,反而深深地陷入了野蠻狀態”。[注][德]霍克海默、阿道爾諾:《啟蒙辯證法——哲學斷片》,渠敬東、曹衛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前言第1頁。當然,根本而言,現代性的這一特質并不源于啟蒙思想,而是源于資本同時具有創造文明和消解文明的邏輯。馬克思從資本邏輯角度揭示了現代性深刻的悖論性之根源。資本既具有“文明因素”,[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47、390頁。又具有反文明因素;既具有“文明面”,[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927頁。又具有反文明面;既具有“文明化趨勢”,又具有反文明趨勢;既具有“偉大的文明作用”,[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47、390頁。又具有嚴重的反文明效應。哈維尖銳地批判資本的掠奪式積累。“在真正的文明世界,這種野蠻掠奪行徑根本不應出現。”[注][美]大衛·哈維:《世界的邏輯》,第325頁。然而,在資本文明的世界中,它終究還是切切實實地存在著,展示資本反文明邏輯的強大力量。羅莎·盧森堡甚至認為,人類如果不是走向社會主義,就必然被資本主義拖回至野蠻狀態。在文明由于資本宰制而面臨深度危機的現時代,重視這一向度尤為必要。
略顯遺憾的是,人們雖早已明了資本的反文明面并加以猛烈批判,但沒有將其提升至與創造文明邏輯相對應的消解文明邏輯的高度。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人們往往將這一邏輯等同于價值增殖邏輯。事實上,與消解文明邏輯不同,價值增殖邏輯不一定就是反文明的。正如近年研究所呈現的那樣,為了實現價值增殖,資本雖然會阻礙文明,但也可能創造文明。事實上,與文明化一樣,反文明也不只是資本外在的、偶然的和相對的效應,而是內在的、必然的和絕對的運動,并且在資本自身范圍內不可能被消除,從而,它也是資本一種鐵的邏輯。[注]具體論證參見劉志洪:《論資本的核心邏輯與附屬邏輯》,《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7年第1期。資本主義數百年“創造性破壞”與破壞性創造的并置交織,增長與衰退、繁榮與危機的周期輪轉,解放與奴役、自由與束縛的相互纏繞,反復證明了資本同時包含創造文明和消解文明的邏輯,總是既創新、推進而又破壞、消解文明。資本消解文明的力量同創造文明的力量并不完全是此消彼長的,在某種范圍內一道增長著。雖然到目前為止,創造文明的邏輯仍然是主要方面,但是消解文明的邏輯一旦充分爆發,將是毀滅性的,可能完全吞噬資本的文明。質言之,這兩種悖反的邏輯并存且共同作用于資本的全部生命周期之中,構成一對真實的矛盾。在這個意義上,可以將資本之于文明的矛盾邏輯,標示為創造—消解文明邏輯。
為了最大程度地增殖價值,只要是有助于實現增殖的方式與手段,資本都會積極地采用。而無論是創造和發展文明,還是阻礙和消解文明,都不是資本的目的,只是其增殖的方式與手段。資本并不是只能通過創造和發展文明實現價值增殖,它也可以通過阻礙和消解文明這種相反的方式做到這一點。譬如,掠奪自然資源、污染生態環境、壓榨弱勢的原材料供應者、剝奪勞動者的應有報酬等侵害人類文明的方式,是資本節約成本獲取更大利潤的基本手段。確如阿克洛夫和席勒所言,“市場競爭的壓力會迫使他們以設局和欺騙為手段,誘導顧客花冤枉錢購買自己原本不需要的東西,使員工做毫無意義的工作,使我們的生活最終變得一團糟”。[注][美]喬治·阿克洛夫、羅伯特·席勒:《釣愚——操縱與欺騙的經濟學》,張軍譯,中信出版社,2016年,前言第1頁。雖然這兩種方式明顯異質,但對于資本而言,它們是一致的,能夠起到相同的效果。而且,更要緊的地方還在于,創造文明對于價值增殖并不總是有利的,正如消解文明對于價值增殖不都有害一樣。當創造文明有助于價值增殖,或者說價值增殖需要創造文明的時候,資本會賣力地發展文明;而當消解文明有助于價值增殖,或者說價值增殖需要消解文明時,資本也會義無反顧地阻礙乃至破壞文明發展。這是價值增殖邏輯同時衍生與支配創造文明邏輯和消解文明邏輯的機理。
雖然從理論上說,發展文明比破壞文明更有利于資本的“長遠利益”,但在現實中,處于殘酷競爭壓力下的資本并不都是理性而目光長遠的,往往還是反理性和目光短淺的。反文明手段能夠增加資本在與其他資本激烈競爭中勝出的可能性,從而總是令資本趨之若鶩。從“主觀目的”上看是如此,從“客觀效果”上看更是如此。雖然諸如《資本論》所批判的“面包素”這樣“假冒偽劣”的東西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被一定程度地遏制,但在發展中國家卻仍然十分流行。而從根本上危害人類文明的軍工企業、轉基因企業等則在整個世界蔓延開來,獲取了強大的力量,在某種程度上決定著人類的命運。創造文明和消解文明這對邏輯既是資本作用于世界的主要過程,也是作用的主要結果,以悖論的方式清晰表征了資本作為現代世界主體的總體歷史效果,因而成為資本的基本邏輯。它也可以被理解為人化—物化邏輯或解放—奴役邏輯。這三種邏輯在本質上是一致的。文明同人特別是“文化”的人內在相通。創造文明就是人化,使人從非人或低級的存在狀態中解放出來,通達更高和良性的生存之境。資本消解文明也就是令人物化,將人奴役在資本這種最強大“物”的魔掌之下,為物所用,進而成為物,墮入物化的生存樣式而難以自拔。
四、諸相反相成的具體邏輯
從不同視角看,資本創造—消解文明的基本邏輯可以進一步分解為諸相互對立的具體邏輯,如提高效率邏輯與降低效率邏輯、競爭邏輯與壟斷邏輯、創新邏輯與守舊邏輯、公共性邏輯與私獨性邏輯。資本總是內在地包含這些相反相成的邏輯。它們以各自的方式展示資本作用于人與世界的過程和機理。雖然力量強弱和顯豁程度各不相同,但它們都具有資本邏輯的本質規定,因而都是資本名副其實的邏輯,和其他三個層次邏輯一道,共同構成了資本邏輯總體。限于篇幅,在此以節約邏輯與浪費邏輯、理性化邏輯與反理性邏輯為例進行解析。[注]關于提高效率邏輯與降低效率邏輯、競爭邏輯與壟斷邏輯、公共性邏輯與私獨性邏輯的分析,參見劉志洪:《論資本的核心邏輯與附屬邏輯》,《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7年第1期。
相對于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資本主義大幅提高了生產效率。效率是產出同投入的比率。高效意味著資本在總的生產過程中節約了大量不必要和低水平的投入或成本。這種成機制、成體系的節約是資本主義重要的歷史進步性。“傳統社會主義”模式之所以沒能根本超越資本主義,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雖然在特定的方面或環節更能集中力量,但在總體上不及資本主義高效和節約。然而,資本“推崇節約是為了生產出財富即奢侈”。[注][德]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央編譯局編譯,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24頁。資本主義模式在生產和消費兩端都制造出大量浪費。新的、時髦的代替了舊的、不時髦的,但還沒等到穩固下來就已經被更新、更時髦的取代了。生產過剩所造成的浪費顯而易見。在當代,資本主義體系的生產過剩在一些領域已經越出相對過剩的范圍,而達至絕對過剩的程度。這既過分消耗自然資源,無可挽回地破壞生態系統,也過度耗費“人力資源”,占用人們本可以享有的自由時間。鮑德里亞深刻地指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浪費“具有特別的社會功能”。對于個人而言,“在浪費出現盈余或多余現象情況時,才會感到不僅是生存而且是生活”。”[注]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論述摘編》,第41、20、21頁。“商品只有在破壞中才顯得過多,而且在消失中才證明財富。”[注][法]讓·鮑德里亞:《消費社會》,劉成富、全志鋼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22、27、26頁。對于整個生產方式來說,“這種最高形式的‘消費’與個人對商品如饑似渴的渴望一樣屬于消費社會的一部分。兩者共同保證了生產范疇的再生產。”從而,“浪費式消費已變成一種日常義務”。[注][法]讓·鮑德里亞:《消費社會》,劉成富、全志鋼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22、27、26頁。即便生產不過剩,即使眾多“想要”仍舊嗷嗷待哺,但對“想要”而非需要的“滿足”本身就是浪費。資本主義總是對“需求不足”憂心忡忡,但對于人的良性生存而言,過度充盈和活躍的“需求”并不是有益的。
在資本驅使下,現代人也和資本一樣高度注重效率,時時處處、一舉一動都小心翼翼地貫徹效率原則。然而,人們所執行的只是資本而非真正人的效率原則,對根本的人的效率問題視而不見,甚至漠不關心。在孜孜不倦地追求“成功”的道路上,人們投入了生命這一最大的成本。然而,不加節制地損耗和透支生命,實際上極大地抬高了“成本”。可見,即使按照效率“法則”,不顧身心健康地提高所謂效率也是不明智的。更重要的是,既然以寶貴的生命作為“成本”,那么“產出”應該配得上所付出的生命。然而,在資本的魔法城堡中,人們迷失了方向,往往忘記或者根本看不到這一點,趨之若鶩地追逐一些配不上生命的東西,從而也只能得到對于生命而言不值一提的東西。事實上,既然最根本的投入是生命,那么最重要的“產出”也應該是生命——高質量的生命。在這個意義上,資本是對人的生命和生命的人的根本否棄。
可見,兩極相通。于資本而言的節約,往往是于人而言的浪費。馬克思早就作過嚴厲的批判:“國民經濟學這門關于財富的科學,同時又是關于克制、窮困和節約的科學,而實際上它甚至要人們節約對新鮮空氣或身體運動的需要”。[注][德]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第123、124頁。資本使人不僅在直接感覺如吃等等方面,“而且也應當在普遍利益、同情、信任等等這一切方面節約”。[注][德]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第123、124頁。一句話,資本總是試圖“節約”一切對增殖不利或無益的東西,至于這些東西對于人的意義并不是資本所關心的內容。即便資本關心起來,也是因為它們同資本的利益發生了關聯。在當代,資本這種表面節約下的浪費愈演愈烈。自然、社會和人越來越商品化、貨幣化特別是資本化,受資本宰制,淪為增殖和統治的工具,成為資本的構件或者說派生物,而無法恢復或超拔至應有的境界。這是自然、社會和人最根本的浪費。自然、社會和人的一切特點,無論缺點還是優點,都被資本處心積慮地加以利用。有理由認為,浪費是資本主義的內在基因。而且,多數的成本和代價并不在自己的“賬簿”上,資本可以無意或有意地忽略,從而可以更加肆無忌憚地發揮這一基因。
理性化是資本內含的強大邏輯。在資本主導下,整個世界不斷體制性地“祛魅”。這得到學界充分的重視和研究。需要進一步注意的是,反理性化同樣是資本必定發生的趨向。事實上,資本和全部現代人與世界,始終處于理性化與反理性化交糅變換之中。資本生產以至整個資本文明,在表面和局部范圍內是理性乃至高度理性的,但在深層和總體上卻是反理性甚至高度反理性的。每個資本主義生產的單元都擁有發達的理性,但整個資本主義生產卻表現出強烈的不理性乃至反理性,難以產生社會總體的界限意識。公共的反理性甚至往往由私人的過度“理性”造成。連以阿克洛夫和席勒等許多擁護自由市場的西方經濟學家都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在金融資本主義世界中,為了獲得最大化的收益,理性人越來越必須理性地跟著不理性的人行動,最終造成社會的反理性。資本主義生產非但不以人的存在及其優化為目的,而且不惜以人作為手段乃至代價。不僅物質生產如此,精神生產、社會關系生產乃至人本身的生產也都如此。資本文明在本質上是一種使人物化的文明。事實上,當我們依據現實把人類所創造的現代文明稱為資本文明時,就已然內在地表征和泄露了這種文明的反人性。
資本對自然加諸了殘酷的掠奪與破壞,甚至威脅到自然和人類存在的底線。誠如社會學家格羅·詹納所言,“高度發達的工業文明對自然具有如此強大的統治力量,以至于它像一個危險的火藥桶,它本身激起的威力就可能使它爆炸”。[注][德]格羅·詹納:《資本主義的未來:一種經濟制度的勝利還是失敗?》,宋瑋、黃婧、張麗娟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88頁。然而,人們卻近乎盲目和瘋狂地把對自然的傷害也歸入經濟增長,并且還為此自鳴得意,從而進一步加劇了這種傷害。在現行的經濟評價體系中,“人們沒有把對自然的毀壞作為借方項目從國民生產總值的計算中扣除……卻把它計入貸方項目。……根據目前計算的國民生產總值,對自然的不斷破壞卻體現了人類‘福利’的增加!”這不僅是對自然的傷害,而且也是對人類自身的傷害。“由此勾勒出的國民經濟產值增加的假象是十分危險的,因為它抹煞了現實存在的威脅”,[注][德]格羅·詹納:《資本主義的未來:一種經濟制度的勝利還是失敗?》,第184頁。將人類置于危險卻不自知的境地。
作為本質上反人類、反自然的文明,資本文明當然也是反理性的文明。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揭露了啟蒙理性的自反性。事實上,啟蒙理性之所以走向它的反面,根本原因正是資本的宰制。資本所看重的理性主要是工具理性或形式理性,而非價值理性或實質理性。工具理性的過度膨脹,意味著價值理性的式微乃至消弭和對虛假價值理性的追逐,進而反轉為非理性乃至反理性的勃興。社會越是工具理性化,就越是反理性化。在這個意義上,資本促成工具理性的統治,也就是反理性的過程,亦即韋伯所說的理性化的中斷,理性被拘押在“鐵籠”之中。市場社會主義的代表人物——大衛·施韋卡特甚至認為,資本主義全部功能都是非理性的。[注][美]大衛·施韋卡特:《超越資本主義》,宋萌榮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4頁。在資本統治下,人與社會表現出顯著的反理性特別是反價值理性的面相,變得盲目、偏執乃至瘋狂,反對理性的聲音愈發強勁,令一些學者不得不強調重建理性主義信念的必要性。
五、四個層次的關聯
“具體之所以具體,因為它是許多規定的綜合,因而是多樣性的統一。”[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2頁。四個層次間的內在聯系與相互作用,使資本邏輯成為一個有機整體。考察這些關聯,是解剖資本邏輯系統結構的必要環節。然而,到目前為止,這還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資本運動的總邏輯通過其他三個層次邏輯加以實現,并規約它們運行的整體走向。這些邏輯都蘊含于總邏輯之中,或者說共同表征、構成和推動總邏輯,從而都是總邏輯的組成部分,可視為這一有機體的器官和細胞。其中,價值增殖邏輯構成總邏輯的主要動力。正是不斷增殖價值的需求與行動,才使資本形成、擴張直至根本揚棄。創造—消解文明邏輯是總邏輯的基本內容與效應。既促生和發展文明,又阻礙乃至消解文明,表現為資本運動的必然態勢。提升—降低效率、創新—守舊、理性化—反理性等具體邏輯則為總邏輯的具體內容與效應。資本的運動在具體層面上呈現為既提升效率、創新和理性化,又降低效率、守舊和反理性化的眾多矛盾狀態。沒有這些邏輯,總邏輯就不可能運行和展開。但這三個層次邏輯的運作并不是雜亂無章的,而是在總邏輯所確定的范圍內和軌道上展開,不會根本性地偏離和悖逆整體方向。只有在資本形成之后,這三個層次的邏輯才能出現,同時也必然出現;當資本強勢擴張時,它們變得十分活躍;而當資本走向消亡,它們就無法繼續存立了。
提升—降低效率、競爭—壟斷、創新—守舊、節約—浪費、理性化—反理性、公共性—私獨性等具體邏輯,都是創造—消解文明這對基本邏輯的具體化或展開,從不同角度或側面構成和呈現這對邏輯。從而,這些具體邏輯和創造—消解文明邏輯的運作具有同構性,在本質或總體上協調一致,連它們受價值增殖邏輯支配的機理都是一樣的。甚至可以說,它們同創造—消解文明邏輯是一體的,猶如“理一分殊”。這也部分地說明了創造—消解文明邏輯緣何能夠成為資本的基本邏輯。不過,換個角度說,正是得益于這些具體邏輯的運作,創造—消解文明邏輯才能現實地實現出來;并且,這些邏輯的具體操作雖不會“各自為政”,但也不可能對創造—消解文明的基本邏輯“亦步亦趨”,而是有著各自具體的運行軌跡。換言之,它們具有不同程度的獨立性和影響力,任何有機系統的構成部分和整體都處于這樣的關系中。
價值增殖邏輯之所以成為資本的核心邏輯,一是因為它構成總邏輯的核心,二是由于它衍生和支配諸從屬邏輯。增殖邏輯貫穿資本運動始終,是資本必然性運動的核心內容,亦即資本總邏輯的根本。本質地看,增殖是資本作為主體自我形成、擴張和揚棄的主要條件乃至過程本身。對剩余勞動的吮吸,是資本總邏輯運行最根本、最源始的動力。用海德格爾的話說,是“偉大的開端”。不僅資本的產生和發展,而且連揚棄,也都源于價值增殖邏輯的運作。沒有增殖價值作為前提,資本不可能自我揚棄。剩余價值的生成、實現和分割,構成資本生產、流通和總過程亦即“生命”運動的中心。在這個意義上,價值增殖邏輯本質地規約了資本的整個“生命”歷程,在很大程度上型塑了資本的總邏輯。但同樣需要看到的是,增殖邏輯再強大,也不可能改變總邏輯及其所表征的資本運動的整體進程,不可能改變資本的最終命運;甚至,價值增殖邏輯越是強勁,資本的自我揚棄邏輯就可能越早實現,資本也就越早完成其歷史“使命”。當然,這也再次確證了價值增殖邏輯的核心地位。
另一方面,價值增殖邏輯規約另兩個層次的邏輯。在總邏輯之下,只有增殖邏輯是核心、根本和起決定作用的邏輯,統馭其他所有邏輯的形成、運作乃至消亡。如前所述,價值增殖邏輯同時內在地衍生與支配創造文明邏輯及其諸具體邏輯等正向邏輯和消解文明邏輯及其諸具體邏輯等負向邏輯。換言之,增殖邏輯塑造了資本運動邏輯的悖論性。其他邏輯都只是非核心、非根本、不起決定作用的從屬邏輯,在歸根結底的意義上服從和服務于價值增殖邏輯。無論是創造—消解文明的基本邏輯,還是各種具體邏輯,都以價值增殖為最高目的,都是實現這一目的的手段。在相互對立的兩種從屬邏輯中,何者在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與程度實現,均以核心邏輯的實現為旨歸。價值增殖邏輯驅使創造文明邏輯和消解文明邏輯以及構成它們的全部具體邏輯,制造出不同乃至相反的現實影響與歷史效應。
但反過來看,價值增殖邏輯的運作也需要具體地通過諸從屬邏輯加以實現。這些邏輯的運行狀況直接推動和型塑增殖邏輯的運作及其力量,使資本得以增殖,并影響增殖的程度與速度。誠如豐子義所言,“創造文明的邏輯也并不是被動決定的,文明創造的能力、狀況如何,直接影響到資本的活力和生命力。”[注]豐子義:《全球化與資本的雙重邏輯》,《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5期。不僅創造文明邏輯如此,事實上,所有附屬性邏輯均如此。從屬邏輯的運行在令價值增殖邏輯實現的同時,也以之為中介和橋梁使資本總邏輯得以實現。有理由認為,它們對資本的“生命”運動發生了間接卻實質性的作用,而非可有可無的存在。沒有各種從屬邏輯的“工作”,增殖邏輯乃至總邏輯一定是虛弱的、非現實的。因此,雖然價值增殖邏輯是資本邏輯的核心,是當中最為關鍵的內容,但也不能像一些研究者那樣只是從增殖角度理解資本邏輯,過于偏狹地將資本邏輯認定為價值增殖邏輯。
余論:資本邏輯系統結構研究的啟示
在對資本邏輯這把鑰匙本身理解不透徹的情況下,以之解剖現代世界當然也不可能得到透徹和最為有益的結果。直接而言,關于資本邏輯系統結構的考察,啟發我們更為深入地理解資本邏輯本身的構成。不應再像以往那樣只是一般性地談論資本邏輯,而應清醒地意識到資本具有多種邏輯,并且這些邏輯存在不同的層次和類型,進而辨明在特定條件下發生作用的具體邏輯及其特定效應。在面對具體問題時,需要自覺地運用恰適的資本邏輯予以分析,以增強研究的針對性與有效性。還應明悉資本邏輯形態間的內在關系與相互作用,并有意識地以之分析相關理論和現實問題。進而言之,這一研究還啟示我們對資本邏輯基礎理論問題展開更為深入的研究。應該看到,不僅在資本邏輯的系統結構中,而且在其他許多問題上,都存在亟需廓清的模糊認識。
資本邏輯縱然強大,人類也并非毫無作為的可能,而是能夠加以規制和改變的;正如我們可以依靠更為強大的力量擺脫地球引力一樣。借用馬克思的話來說,雖然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資本邏輯,但我們能夠縮短和減輕它所造成的痛苦。資本主義不斷地自我調整,相當程度上正是人類批判和反抗資本邏輯的結果。當代人類尤其是中華民族,既要總體地把握資本邏輯,又要具體邏輯具體對待。資本邏輯是一個有機整體,存在獨立的系統質和相對一致的運行軌道,必須切實地作為總體加以應對。但資本的每一種邏輯又都具有獨特的規定與效應,應該根據其特點有針對性地加以處理,方能獲得最佳效果。如果沒有強大外在力量的干預,資本必然裹挾整個現實世界按照其形成、擴張和揚棄的總邏輯運動。這啟迪當代人類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在客觀條件不成熟時不是簡單地消滅資本,而是既利用與發展,又加以制約和引導,并積極創造條件促成其揚棄。這將是中華民族在很長時間內行動的方向。資本遵循增殖價值的邏輯運動,必定同時內在地形成正向與負向兩類不同的邏輯。我們需要重視價值增殖邏輯的核心地位,以有效方式發揮正向邏輯,實現其積極意義,抑制負向邏輯,規避和減輕其消極影響。特別關鍵的是,創造條件盡可能使資本傾向于并實際地以正向邏輯而非負向邏輯增殖,從而更多地形成積極作用,更少地造成消極效應。這一點對于當前中國十分重要。但是,對正向邏輯的發揮和對負向邏輯的限制,只可能在一定范圍內和程度上有效,因此,必須始終秉持對資本的積極揚棄;即使在利用和發展資本時也不能松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