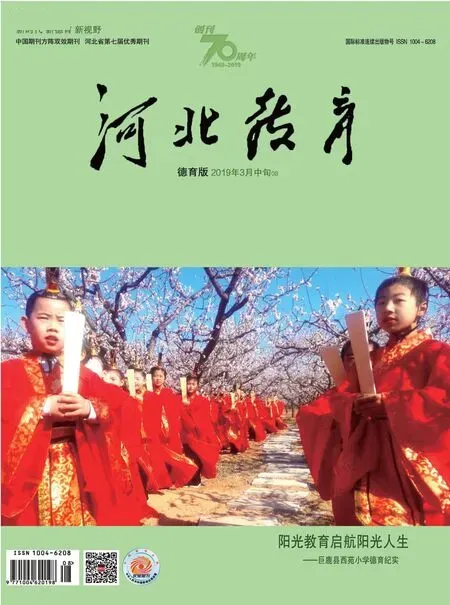擊壤歌
○郗文倩
古代早期歌謠,有一種別樣的趣味,就好像人的童年少年,興之所至,隨口而出,聲音的抑揚頓挫,無意中形成的節(jié)拍韻律,會帶來別樣的快感。這種快樂和后世的所謂“創(chuàng)作”最大的區(qū)別,就是少了很多“目的”,甚至就是無意識的。嘴里發(fā)出來的這些音聲,到底算說話,還是算歌,還是謠,還是詩,還是詞,那時候是沒有這些個分別的,我們后人越來越細(xì)致,才一一安排歸類。總之,肯定不是正兒八經(jīng)對著紙筆冥思苦想的產(chǎn)物。《淮南子·齊俗訓(xùn)》曾說遠(yuǎn)古的人們,“其歌,樂而無轉(zhuǎn)”,所謂“無轉(zhuǎn)”,就是說樸拙,快意,率真,直白,不像后世歌詠,一唱三嘆,抑揚曲折。
不假思索,脫口而出,這是一種難得的通透心境,也是特殊的審美境界,成年后,也許求還求不來呢。《擊壤歌》大概就屬于這樣的歌謠。它很有名,很多古歌謠集都收錄下來,把它看作最古老的、具備完整形態(tài)的詩歌,比如清代沈德潛《古詩源》就把它列為古詩第一首。其實,如果看看史料,就會發(fā)現(xiàn)最初就是老翁說話而已。我們看最流行的版本,出自《藝文類聚》,書中引《帝王世紀(jì)》曰:天下大和,百姓無事,有五十老人擊壤於道。觀者嘆曰:大哉帝之德也。老人曰: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
這里的“天下”一般指帝堯時代,說那時堯無為而治,百姓安居樂業(yè),無憂無慮。有五十老翁在大道上玩“擊壤”的游戲。有人路過贊嘆說:啊呀,這就是堯帝的政德偉大、治國有方啊,否則百姓們怎么能過得這么閑適逍遙呢。老翁并不認(rèn)同,反駁說: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鑿井飲水,耕田而食,自給自足,堯帝與我何干?
這段文字,四言為主,言辭整飭,很多史料都引用,把它當(dāng)作一首歌謠,具體詞句雖有增飾,但大同小異,最大的不同就是老翁最后那句反問。比如更早一些的《論衡·感虛篇》作:“堯何等力?”晚些的《初學(xué)記》作:“帝力何有於我哉?”《太平御覽》作:“帝何德於我哉?”今人逯欽立整合了前人多個版本,把它收入《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最后一句也做了細(xì)微調(diào)整,改作:“帝力于我何有哉?”七言,句式更符合后世習(xí)慣,整段就成了四言和七言組合的歌謠,老翁那句信口而出的答詞就變成了《擊壤歌》了。
中國人好古,總覺得世風(fēng)日下,今不如昔,帝堯,包括接下來的舜禹時期,就是最理想的太平年景,究其實,不過都是想象而已,白首老翁也好,懵懂幼童也好,都是個代言人。可是,一個社會的發(fā)展,卻是需要美好想象牽引的。黃發(fā)垂髫有所依,鰥寡孤獨有所養(yǎng),無憂無慮,自給自足,不假他求,這是古人的理想。《莊子·讓王》里,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拒絕了,他說:“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一種夏布),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于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這段文字,可作《擊壤歌》的注解。
所以,《擊壤歌》代表的是一種愿景,歌謠本身的藝術(shù)性倒可以不必太計較。也正因此,后世文人寫詩,“擊壤”就變成了一個典故,以表達(dá)類似的心愿。比如宋代李石《扇子詩》:“無適無莫羲皇人,不憂不懼擊壤民。只有太平容易事,更于何處費精神。”不過,也有以此歌頌圣德的,如司馬光《春貼子詞皇帝閣六首》:“盛德方迎木,柔風(fēng)漸布和。省耕將效駕,擊壤已聞歌。”古代文人有一類詩,主題就是“頌圣”,主動的或被動的,擊壤老人“帝何力于我”之類的話是不容易說出口的。
“擊壤”怎么玩?東漢劉熙《釋名》說:“擊壤,野老之戲,蓋擊塊壤之具,因此為戲也。”意思是擊打土塊兒之類,解說太簡單。《太平御覽》卷七百五十五“工藝部”引《藝經(jīng)》則說是擊打梯形木塊,命中靶子取勝:“壤以木為之,前廣后銳,長尺四,闊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cè)一壤于地,遙于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敲之,中者為上。”可見游戲器具、方式都在變化。明代似乎又變成棗核形:“二月二日龍?zhí)ь^……小兒以木二寸,制如棗核,置地而棒之,曰打柭柭……古稱擊壤者耶。”(《帝京景物略》卷二)擊打棗核狀木桷,這與今天的“打棒棒”很像。手握槳狀木板,前端垂直擊打地上“棗核”一端,“棗核”反彈,旋轉(zhuǎn)騰空,遂就勢再次擊打,或致遠(yuǎn),或以中的為上。所以擊壤得名,或是因“必先擊地以取勢”。不過,幾千年的老游戲了,中間多少變化也難以說清。
明末清初秣陵童謠云:“楊柳青,放風(fēng)箏;楊柳黃,擊棒壤。”(周亮工《書影》)擊壤是游戲,游戲時,人才放松,放松了,發(fā)自心聲的歌謠才會信口脫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