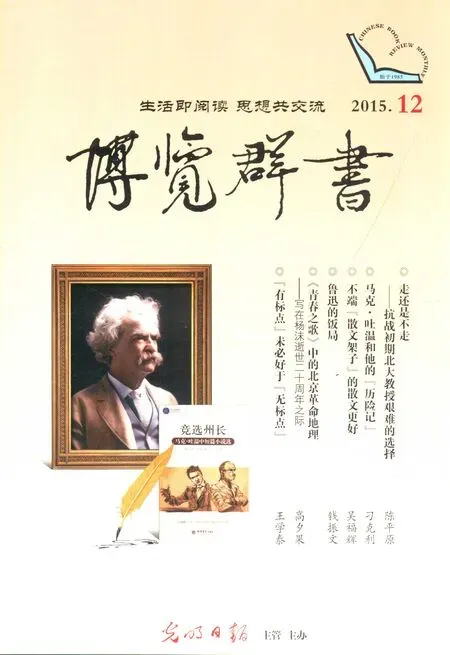王玉哲與《中國上古史綱》
趙伯雄

壹
先師諱玉哲,字維商,河北深縣人。生于1913年,卒于2005年。先生系農家子弟,早年曾接受過當時的所謂新式教育,在高中階段,就對文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1936年,先生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在北大期間,受顧頡剛、錢穆等先生的影響,逐步走上了古史研究的道路。不久,日寇全面侵華,平津淪陷,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南遷,合組為長沙臨時大學(后遷至昆明,更名為西南聯合大學)。先生先是與同學歷盡千辛萬苦,輾轉來到長沙,后又參加“步行團”,隨校遷往昆明,在西南聯大完成了他的大學學業。先生自述,在西南聯大期間,曾廣泛修習文史各類課程,學中國哲學史于馮友蘭先生,學《莊子》于劉文典先生,學《詩經》《楚辭》于聞一多先生,學聲韻、訓詁于羅常培、魏建功先生,學甲骨文、金文于唐蘭、陳夢家先生。正是由于有這些學術前輩的指引、教導,先生的學術功底日益深厚寬博,這為他日后的中國古史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40年,先生在西南聯大畢業,旋即考取了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導師是唐蘭先生。經過三年刻苦學習,1943年,先生研究生畢業。
1943年以后,先生先后在武漢華中大學、長沙國立湖南大學教書數年,其間所撰論文《鬼方考》獲國民政府教育部1945年度學術發明獎金。1948年,先生北上天津,侍疾于父親病榻之側,此時接受了南開大學的聘書。僅僅半年之后,天津解放,從此先生再沒有離開過南開。他在這里教書、治學,兢兢業業,成為中國享有盛譽的先秦史專家,同時也為南開歷史學科的建設和發展作出了杰出的貢獻。先生一生淡泊名利,勤勉刻苦,直至耄耋之年,仍舊筆耕不輟,可以說把畢生的精力都獻給了學術和教育事業。
貳
《中國上古史綱》(以下簡稱《史綱》),是王玉哲先生根據在南開大學歷史系講授中國上古史的講義整理而成的。當年先生講中國上古史,是作為中國通史課程的一個段落來講授的,故《史綱》雖斷代于秦,其實具有通史的性質。通史貴在貫通,貴在全面,而且立論要求盡量穩妥,今觀《史綱》,正是具有這樣的特點。本書從原始社會講起,歷夏、商、西周、春秋、戰國,直至秦的統一,舉凡中華文明的起源、華夏民族的形成、各時期歷史發展的大事件和重要的歷史人物,以及各個歷史時期的經濟生活、政治制度、社會形態、民族關系、思想觀念、文化發展、科技成就,均有涉及。內容雖然豐富,全書卻僅有20余萬字,我想這與此書本來是為大學生授課的講稿有關。作為上課用的講義,必須簡明,不能枝蔓太多,不能論證過細,先生當年以“史綱”命名此書,大約就有這層意思吧。
先生為文,求真求實,從來不發空論,而且心思細密,所見常常出人意表。我看過一些先生早年的作品,大多是考證文章,寫得十分精彩,旁征博引,追求實證,每立一說,必廣泛搜求各方面證據,論證如剝繭抽絲,所以結論往往令人信服。這種風格,在先生晚年的文章中依然可以看到。先生說他最欣賞王國維的治學方法,并將這種方法貫穿他學術活動的始終。
今天我們重讀這部《史綱》,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作者長于考證、實事求是的特點。許多立論和觀點,都是先生精心推尋考證的結果,諸如商代的繼統法、先秦的民族問題、西周的社會性質、楚族的來源及遷徙路線等問題,都有相關的研究論文做基礎,故全書內容頗顯扎實厚重。當然,限于通史教材的體例,有些論點不可能充分展開論證,即使這樣,作者往往也要將證據的要點一一列出,以備讀者進一步深入研究之用。例如講到中國上古存在過母系氏族社會,就列舉了上古“知其母,不知其父”“族外婚”“古時婿稱岳父為舅;稱岳母為姑;婦稱丈夫之父為舅;稱丈夫之母姑”“父子不相續相處,而祖孫相續相處”“古帝王稱‘毓稱‘后”“圖騰痕跡”“姓的性質”等七個方面的證據,來說明中國上古確曾存在過母系氏族社會。這七項證據,如果詳細論證,每一項都可以寫成一篇論文,但在《史綱》中,則只做了簡要的概述,然而言必有據、論不空發的精神已躍然紙上。
寫這種通史性的著作,善于考證,固然是一大優長,但懂得裁斷,同樣重要。因為事實上,在敘述歷史的過程中,并不是對每一個史實的認定及提法都要列舉出種種證據的,哪些該詳,哪些可略,全在作者的裁斷。在《史綱》中,先生對一些問題的處理方法很能給人以啟發。例如舊說商人的祖先“不常厥邑”,從契到湯曾有“八遷”。我知道先生對這個問題曾做過深入的考證,但在《史綱》里,先生只是概括地引用王國維的考證結果,指出八遷之地,“或不出山東、河北與河南之間”,而不是為了炫博,在這個并非重要的問題上浪費筆墨。這就叫作善于裁斷。有時為求簡明,往往將考證的線索放在頁下附注之中。如周初的“三監”,學者間頗多聚訟,至今也難有明確的結論。《史綱》只在正文中略述通行的舊說,然后用附注的形式,介紹了這個問題的癥結所在,以及作者所贊成的王國維的考證結果。關于周公稱王之事也是如此。武王死后,周公是否踐位稱王,古來爭議甚多,莫衷一是。《史綱》正文對此不做糾纏,直言周公“踐天子位”,然后在附注中詳述立說的根據。此類的處理,都反映出作者具有對史事權衡輕重以及取舍裁斷的史識。
先生對自古流傳的舊說,每多考而后信。但在沒有確實可信的新結論的情況下,則寧肯沿用舊說,也不追新騖奇,不在證據尚欠充足時改立新說,表現出一位治史者應有的審慎態度。當然,不肯矜奇立異,并不意味著盲從舊說。對某些在古代屬于非主流的說法,經過細致的辨析,有時也會改從。對于今日已有確鑿證據證明是誤說的,也會加以糾正。例如兩周之間的“共和行政”,自來說者多取《史記》,以為是周公和召公的聯合行政;而《竹書紀年》記此事,則稱是共國之君名和者干王位。先生通過考證,認為《竹書紀年》之說更為合理,遂在敘述此事時摒棄了《史記》的說法,而改用《竹書紀年》之說。又如古人一般視華夏民族之外的“蠻夷戎狄”為四個種族,并將此四者分配于四個方位,即南蠻、北狄、西戎、東夷,這種認識對后世治史者影響不小。先生經過深入研究,破除了這種成說。先生以為,戎、狄、蠻、夷的含義,其實是隨時代而變化的。早在殷商時,東方有夷,北方有狄,而蠻、戎二名尚未興起。這四名也不是四個種族,《詩經》、金文中均有“百蠻”之名,蠻而有百,可知其非一族之專名。到春秋戰國時,四方諸小族統名為“夷”,南方之族尚未專有“蠻”稱。而且“戎”“狄”二名可以互稱,文獻中多有其例,可見不能把戎、狄理解為兩個不同的種族。直到秦統一中國之前,中原諸小族多被驅逐于四塞之地,戎、狄、蠻、夷四個名詞才開始被分配于四個方位,“東夷”“北狄”“南蠻”“西戎”之說,始正式形成。
叁
先秦史號稱難治。難在哪里?首先難在材料的短缺。無米之炊,巧婦難為,故學者每有“文獻不足”之嘆。商、周兩代比較起來,商代問題更為嚴重,文獻資料極少。西周稍好一些,有《尚書》《詩經》等可資利用,但真正屬于西周時代的材料也很有限。所幸近代以來,甲骨文、金文大量出土,為治先秦史者提供了許多珍貴的史料。這就要求治史者除了熟悉文獻之外,還要懂甲骨文,懂金文,具備考古學方面的知識。王玉哲先生在古文字學上有很高的修養,對甲骨文、金文都有精深之研究。在《史綱》一書中,先生在商史的部分利用了大量的卜辭資料,在講述商代國家的特點、奴隸的狀況、社會經濟、政治制度、繼統法等問題時,卜辭往往被用作起決定性作用的骨干材料。其實這也是不得不然,因為非如此不足以說清商代社會(主要是盤庚以后的商代后期)各方面的實際情況。但在講西周史的部分,先生則仍然以文獻資料為基礎,為骨干。因為一來西周的文獻較商代為多,利用文獻資料構建西周歷史的框架已有可能;二來在先生看來,青銅器銘文作為史料,有一定的局限性,使用起來必須慎重。例如對銅器的斷代,學者間往往歧見甚多,搞不好就有張冠李戴之虞。再有就是青銅器銘文涉及的社會面比較窄,內容比較單調,有些問題如果完全依據金文或以金文為主來論證,還是有一定困難的。此外,金文的文字釋讀也是個問題。很多銘文當中的關鍵文字,在釋讀上往往還有很大爭議,字義尚不確定,這種材料怎能放心使用?故按照先生的說法,對一件銅器銘文,“非有十分之見,不敢輕易利用”。所以我們看到,《史綱》中的西周史部分,還是以傳統文獻為本,而利用一些意思明確、爭議不大的銅器銘文來補苴罅漏。
以傳統文獻為主來講古史,其實也不簡單。且不說上古文獻之文字艱深、佶屈聱牙,單是史學與經學糾纏在一起,就是個不易解決的難題。先秦文獻如《尚書》《詩經》《周易》《儀禮》《周禮》等,同時也是儒家的經典,自漢以來,說解雖多,但大都以解經為目的,故現代學者利用起來,首先就要廓清經學的迷霧,分辨出古人的解說哪些是主觀的解經,哪些是客觀的述史。這是很能考驗治史者見識的事情。先生在這方面也有其獨到的眼光。例如關于周代的宗法制,先秦禮書里有大量的記述,不可否認其中確有些是當時實際的宗法規則,但也有相當一部分屬于經師的發揮,或者是想當然的理想化設計。漢以來歷代學者解說周之禮制、解說宗法的著作可謂汗牛充棟,現代學者必須從大量的說經之作中披沙揀金,挖掘古人之說中那些真正反映周代歷史實際的東西。《史綱》在講解什么是大宗、小宗,什么是繼祖、繼禰,什么是百世不遷、五世則遷等問題時,就基本上以先秦禮書為根據,因為先秦禮書上的這些記述,就我們現在的認識水平來說,可能確實是周代宗法的主要規則。同時,在這一基礎上,《史綱》又從現代學者觀察的角度,將宗法制的特點歸納為“共同的祀典”“親族服喪”“異居而同財”“族人會議”“同宗不婚”等五個方面。這樣,所論既有堅實的文獻支撐,又有現代學者的理性分析。
肆
先生是一位從舊社會走過來的知識分子,在他盛年之際,迎來了舊政權崩塌、新政權建立這樣翻天覆地的變化。先生像同時代的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由衷地歡迎這個新的政權,同時也真心實意地要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發展形態的學說,深為他們這一代學者所服膺。先生就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階段的理論來思考中國上古史問題的。但先生從來不會盲從,不會把教條、原則作為出發點。他信奉“論從史出”,在研究中絕不先給歷史帶上某種框框,而是主張先去發現歷史的真相,然后從大量的真相中去提煉歷史的發展規律,來驗證理論指導的正確性。有時他的觀點不為多數人所贊同,但他既自認為是從事實中來,有堅實的史料依據,則持之益堅,不為潮流所動。在20世紀50年代,寫先秦史著作,最要緊的也是最不能回避的,就是社會形態問題。先生是堅定的西周封建論者,他積極參加了那場關于古史分期問題的大討論。在《史綱》中,對于這個問題的論證,首先是著眼于西周的土地制度。先生認為,天子是當時最高等級的領主,他把王畿以外的土地分封給諸侯,讓他們各自為政,各自治理他們的封地;而諸侯在國內,也同周天子一樣,分封卿大夫以采邑,這樣就形成了等級制的各級領主的土地所有制。在這一基礎上,《史綱》把考察的重點放在了生產者的身份上。大量的無可辯駁的事實表明,西周的主要生產者“民”(或庶人、庶民)不是奴隸,他們有自己的小塊耕地,有自己的少量勞動工具,他們一方面受勞役地租的剝削,同時也有自己的經濟生產,這樣的勞動者,已經與奴隸有了本質的區別。因此,西周社會已不可能是奴隸社會了,按照先生的說法,西周“已經進入初期的封建社會”。為什么要加上“初期”二字呢?因為先生實際上也注意到了,西周社會還存在著許多奴隸社會的遺跡,例如《逸周書》上所反映的周初對敵人“重俘虜而不重殺戮”的現象,某些金文中還記載有奴隸買賣的實例,等等,他認為,“一種社會形態的階段之劃分,絕對不是像刀切斧斫的那樣整齊”,“兩個階段之間,有著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新舊兩種社會形態交錯存在”。這種認識,在今天看來,依然是十分精當的。
關于商代的社會性質問題,先生的見解也與多數學者的看法不一樣。先生不否認商代存在著奴隸制,但他說,盤庚以后的商王朝才能說是奴隸社會,而商代初葉,距原始公社的末期還不甚遠,應當處于從原始社會向階級社會過渡的階段。經過長期的發展,至盤庚時期,商人才進入奴隸社會,國家機構才正式形成。先生的這一結論,是對盤庚前后的社會經濟狀況做了深入分析的結果,其中也包括對盤庚遷殷的原因的探索。在先生看來,商人屢遷與當時的粗耕農業直接相關,而盤庚以后273年不再遷都,則是由粗耕農業轉為半精耕農業的證明。所以,盤庚遷殷,稱得上是商代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重要的轉捩點。這個觀點,雖然未被主流學界所接受,先生卻直到晚年仍在堅持。我想,今日的學者,即使不完全贊同先生此說,亦不妨認真看一看先生的論證,或許能夠從中得到一些啟發。
《史綱》一書的初稿,實際上在1955年前后已經完成了,故此書可以看作是20世紀50年代前期的作品。毋庸諱言,在今日看來,此書的有些內容確實已經過時或者應該修正了。例如原始社會部分,近幾十年來,考古學發展突飛猛進,使這一部分的許多內容都顯得陳舊了。甲骨學、金文學的長足進步,也為先秦史研究增添了不少新的史料。此外,如今思想的解放,理論的創新,也是當年的學者無法想象的。盡管如此,今日再版此書,仍然有其重要的意義。這本書在不長的篇幅之中,講述漫長的先秦歷史,脈絡清晰,史實準確,史料精而不繁,論證約而有法,既有學術界普遍接受的成說,又有作者的創見,對于治中國史的學人來說,不失為一種重要的參考書。而且此書所體現出來的作者的嚴謹學風、樸實文風,對今日浮躁的學術空氣不啻一劑對癥的良藥。特別應該指出的是,本書是老一輩學者在20世紀50年代那樣一種歷史條件下,運用新的理論指導先秦史研究的可貴實踐。這種實踐有哪些地方值得繼承,有哪些地方還可加以改進,值得今日的年輕學者深長思之。
(作者系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先秦史、經學史及歷史文獻之教學與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