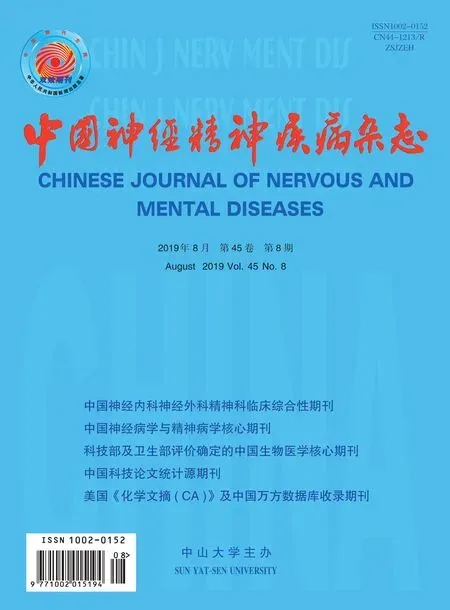自身免疫性癲癇研究新進展☆
李艾青 龔雪 林靜芳 周東洪楨
隨著免疫性中樞神經系統疾病研究的快速發展,癲癇與免疫因素的關系成為一個研究新熱點,目前“免疫性”已被正式列為癲癇病因,進而逐漸提出自身免疫性癲癇(autoimmune epilepsy,AE)的概念并被癲癇學界認可[1]。雖然AE在人群中患病率、診斷標準、治療指南方面尚無定論,但近年來國內外發布的文獻為AE流行病學的發展、臨床診療方案的選擇提供了更多的證據,同時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觀點。本文將從AE概念的確立及分類,流行病學、診斷、治療研究新進展做一綜述,旨在加深神經科醫生對AE的認識。
1 自身免疫性癲癇概念的確立與分類
上世紀六十年代人們注意到免疫炎性機制參與癲癇的發病,如嬰兒痙攣癥、獲得性失語綜合征等,均以免疫治療為一線治療[2]。2002年Levite在日內瓦舉行的國際自身免疫大會上首次提出AE的概念,并將一系列免疫細胞或自身抗體介導的癲癇稱之為AE[3],并在同年Nat Immunol正式發表了關于AE的內容,并指出這是癲癇病學史上革命性的歷史事件[2]。2014年有學者提出對于檢出抗神經元抗體、合并有自身免疫性疾病或免疫調節治療有效的癲癇患者均懷疑為AE[4]。2017年國際抗癲癇聯盟(International League Against Epilepsy,ILAE)正式將“免疫性”列為癲癇的六大類病因(結構性、遺傳性、感染性、代謝性、免疫性、未知)之一,根據ILAE2017年癲癇的分類,AE主要指一些病因可歸于自身免疫介導的中樞神經系統炎癥,或者以癲癇作為核心癥狀的免疫疾病[1]。
根據目前文獻的觀念來看,AE可分為:①系統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合并癲癇發作[4-5]:包括系統性紅斑狼瘡、橋本氏甲狀腺炎、1型糖尿病合并癲癇等。②神經系統抗體陽性合并癲癇發作[6-7]:包括抗電壓門控鉀離子通道(voltagegated potassium channel,VGKC)、 抗谷氨酸脫羧酶 65(glutamic acid decarboxylase65,GAD65)。③自身免疫性腦炎相關性癲癇[1]:包括抗N-甲基-D-天冬氨酸受體(N-methyl-D-aspartate receptor-antibodies,NMDAR)腦炎、抗富亮氨酸膠質瘤失活 1蛋白 (leucine-rich glioma nactivated l,LGll)腦炎、抗 γ-氨基丁酸 B型受體 (γ-aminobutyric acid,GABAbR)腦炎、抗α-氨基-3-羥基-5-甲基-4-異惡唑丙酸受體 (α-amino-3-hydroxy-5-methyl-4-isoxazole-propionic acid receptor,AMPAR)腦炎、抗接觸相關蛋白類似物2(contactin-associated protein-like2,Caspr2)腦炎、抗甘氨酸受體(GlyR)腦炎、抗二肽基肽酶樣(DPPX)腦炎、抗 γ-氨基丁酸 A型受體(γ-aminobutyric acid,GABAaR)腦炎相關性癲癇等。
AE概念的確立及分類的完善為識別AE提供了一定的依據,為難治性癲癇的治療提供了新的方向。但要闡明AE的發病機制,仍亟待開展進一步的相關臨床及基礎研究。
2 自身免疫性癲癇流行病學
據現有文獻報道,癲癇患者中有10%可歸類為AE,但AE的患病率尚不清楚[5]。近年來一些關于神經抗體在各類型癲癇中的新研究為AE流行病學的發展提供了更多、更廣泛的證據。BRENNER報告,在既往診斷(住院或就診于癲癇專科門診)和新近診斷的癲癇患者血清中,11%檢測出有一種或多種抗體,其中抗VGKCs-Ab占5%,抗GlyRAb占3%,抗GAD-Ab和抗NMDAR-Ab各占1.7%。此項研究還表明既往診斷癲癇和新診斷的癲癇患者之間抗體檢出率沒有明顯差異,全面性癲癇或局灶性癲癇患者之間的抗體檢出率也不存在明顯差異。然而,原因不明的局灶性癲癇患者抗體陽性檢出率比結構或代謝的原因所致的局灶性癲癇更高(14.8%vs.6.3%;P<0.02)[6]。2017 年 VON PODEWILS前瞻性地納入了自2011年至2016年就診的66例新發的晚發性癲癇(癲癇病程小于6個月,年齡≥55歲),有4例患者由免疫性因素所致,提示了晚發性癲癇發作中至少有6%為免疫性病因[8]。2018年TECELLIOGLU[9]納入研究的77例病因不明的耐藥癲癇患者中,17例癲癇患者血清抗體陽性,其中抗 TPO-Ab(+)占 5.2%,抗 GADAb(+)占 1.3%,抗 VGKCs-Ab(+)占 5.2%,抗核抗體(Antinuclear antibody,ANA)(+) 占 10.3%, 副腫瘤性抗體(+)占2.6%。而且腦電圖局灶異常、局灶性癲癇發作和頻繁發作在抗體陽性的患者中更為常見。此研究得出:自身免疫性因素可能與原因不明的耐藥性癲癇尤其是伴有局灶性腦電圖異常和頻繁發作的局灶性發作癲癇病因相關。也有部分新研究提示在新診斷的癲癇患者中,自身免疫抗體具有更高的陽性率,如DUBEY[7]連續納入112個病因未確定的癲癇患者,檢測出血清抗體的陽性率為34.8%;新診斷的癲癇較既往確診的癲癇患者在血清中抗體檢出率更高(13/35[37%]vs.10/77[13%])。
3 自身免疫性癲癇的臨床特征
識別具有潛在自身免疫因素的癲癇患者至關重要,因為這部分患者對免疫治療可能有效[7]。由于目前缺乏統一的診斷標準,又缺乏有效的抗神經元抗體的評價指標,臨床診療活動中出現一些過度依賴于自身抗體檢測診斷AE的趨勢。此時,兩種依據患者臨床特征預測AE的模型應運而生。
DUBEY等[7]納入127新發(至少間隔24 h的2次無誘因癲癇發作或1次發作后具有高風險再發)或病因未明的癲癇患者,結合其臨床特征提出一種能夠預測癲癇自身免疫病因(神經抗體血清陽性)的模型。這份具有9項15分的量表——癲癇患者抗體患病率(Autoantibody Prevalence in Epilepsy score)APE評分的內容包括:①新出現的癇性發作,或1~6周內精神癥狀迅速進展(1分)。②神經精神改變:激動、攻擊性、情緒不穩(1分)。③自主神經功能障礙:持續房性心動過速或心動過緩,多汗,頑固性血壓不穩,室性心動過速或心臟驟停(1分)。④病毒前驅癥狀(流涕、咽喉痛、低熱),且無潛在惡性腫瘤(2分)。⑤面部運動障礙或面臂肌張力障礙(2分)。⑥難治性癲癇(至少2種抗癲癇藥物治療癲癇控制欠佳)(2分)。⑦腦脊液呈炎癥改變:當腦脊液紅細胞<100/L時,腦脊液蛋白>5 mg/L和(或)白細胞增多>0.5/L(2分)。⑧頭部磁共振成像顯示信號的變化與邊緣葉腦炎一致:顳葉內側T2加權成像/液體衰減反轉恢復序列信號的改變(2分)⑨存在潛在惡性腫瘤,但不包括皮膚鱗狀細胞癌或基底細胞癌(2分)。在得出APE評分后測試血清樣品的抗神經抗體,并對其APE評分進行內部驗證。結果說明抗體陽性的患者APE評分≥4的比例較抗體陰性的患者顯著更高 (82.6%vs.19.1%,P<0.001),APE評分≥4預測神經自身抗體的靈敏性和特異性分別為82.6%和82.0%。且與病因不明的癲癇患者相比,血清抗體陽性的患者更有可能獲得良好的癲癇預后(15/23[65.2%]vs.24/89[27.0%])。DUBEY 對 2014 年 6月30日至2016年6月30日就診于梅奧診所患有自身免疫性腦病、AE或自身免疫性癡呆的1736例患者的血清和腦脊液樣品進行回顧分析,并再次驗證了APE評分:抗體陽性的患者APE評分≥4的比例顯著更高 (97.7%vs.21.6%,P<0.01)。APE評分≥4預測神經自身抗體陽性的靈敏性和特異性分別為97.7%和77.9%[10]。與此同時,他根據接受免疫治療患者的臨床特征提出另一種可預測免疫治療效果的模型——(response to immunotherapy in epilepsy score)RITE評分,總分為 19分,以 APE評分內容為基礎,添加了兩個附加變量。兩個附加變量分別為:①臨床癥狀出現6個月內開始免疫治療(2分)。②檢測到神經元表面抗體(2分)。RITE評分≥7預測良好免疫治療效果的靈敏度和特異度分別為87.5%和83.8%。在一定程度上,RITE評分可協助臨床醫師預估AE患者在接受免疫治療后的療效。
總而言之,對于新發難治性癲癇患者來說,若存在精神改變、自主神經功能障礙、頭顱影像學及腫瘤證據等臨床特征,即使AE抗體陰性也不能排除AE的可能性。目前對于APE評分與RITE評分的研究集中于成年的AE患者,是否可以擴大研究范圍包括兒童患者,還需進一步的研究來確定。毫無疑問的是,這兩種預測AE的模型將會為我們臨床診療工作規范化管理提供一種新思路。
4 自身免疫性癲癇的治療
關于AE的治療目前尚無標準化方案,被廣泛認可的治療手段主要包括免疫治療、抗癲癇藥物(antiepileptic drugs,AEDs)治療及其他治療。
免疫治療手段含一線治療及二線治療。一線治療包括糖皮質激素、免疫球蛋白、血漿置換[11]。如果一線藥物依然治療無效或效果不明顯,則可選用二線藥物如利妥昔單抗、環磷酰胺等免疫抑制劑。除利妥昔單抗、環磷酰胺之外,環孢霉素A、他克莫司和雷帕霉素三種免疫抑制劑同樣被報道具有控制免疫性癲癇的作用[12]。霉酚酸酯(mycophenolatemofetil,MMF)常作為免疫抑制劑用于預防排斥反應,有案例報告一例30歲男性,新近出現記憶障礙及頑固性顳葉癲癇,并伴有高滴度的血清及腦脊液GAD65抗體。聯合使用AEDs,大劑量丙球沖擊治療及靜脈注射糖皮質激素后記憶障礙及癲癇再發,在加用每日2 g MMF的治療后,記憶力得到改善,癲癇也未再發作[13]。當急性期免疫治療有效時(癲癇發作頻率減少超過50%),通常建議繼續長期免疫治療。如果急性期治療結束后未繼續給予免疫治療,許多患者可能會出現復發。因此,加用硫唑嘌呤或麥考酚嗎乙酯等長期口服免疫抑制劑可能會取得較好的療效[14]。然而,另有一些研究表明,即使在免疫抑制劑控制免疫炎癥反應之后,一些患者仍處于癲癇復發的危險中,所以,AEDs對于部分患者而言也是必要的[15-18]。近年有研究表明使用AEDs能有效控制免疫性癲癇發作。FEYISSA對252例診斷為自身免疫性腦炎和副腫瘤性腦炎的成年患者進行回顧分析,以癲癇發作為初始表現者50例(20%),大多數(n=43.86%)接受至少聯合一種AEDs的免疫療法,而其余僅接受AEDs治療。其中27例患者(54%)在接受治療后達到無癲癇發作;18例(36%)接受免疫治療,5例(10%)僅接受 AEDs治療,4例 (8%)在免疫治療失敗后接受AEDs治療。AEDs治療后達到無癲癇發作預后的治療方案分別是:卡馬西平(3/16,18.8%),拉科酰胺(3/18,16.6%),苯妥英〔1/8,12.5%)及奧卡西平(2/11,18.1%)。 該研究得出結論:沒有一種AEDs在AE中效果更突出。然而,部分患者確實對AEDs治療有效果,目前尚不清楚這究竟是與藥物作用相關還是與疾病的自然進程相關[18]。另外,有學者綜合近年發布的研究AEDs對AE有效性的文獻后發現:雖然左乙拉西坦是最常用的抗癲癇藥物,但沒有一個AE患者通過這種藥物達到了無癲癇發作的預后[19],這一發現與既往的觀點是相左的。有趣的是,學者們還發現無論采用何種治療手段,抗VGKCs-Ab陽性患者較抗GAD65-Ab 陽性患者(12/17vs.2/10,P=0.0183)更易得到無癲癇發作的預后。最終,學者們估計AEDs對AE的有效率為10.7%。對AEDs有效的AE患者中,血清神經抗體陰性者占18%,抗VGKCs-Ab陽性者占11%,抗 GAD65-Ab陽性者占8%。可喜的是,73%的對AEDs有效的患者接受了鈉通道阻滯劑單藥治療或包括鈉通道阻滯劑在內的聯合藥物治療[19]。盡管如此,鈉通道阻滯藥物改善癲癇發作背后的病理生理機制目前尚不清楚[18]。
其他治療包括癲癇手術、外源性睪酮替代治療、副腫瘤性癲癇的腫瘤切除及腫瘤治療等。有研究表明,與抗GAD65-Ab相關的難治性癲癇可考慮癲癇手術。然而,與顳葉癲癇合并海馬硬化患者顳葉切除術后70%~80%的患者可達到無癲癇發作的預后相比,抗GAD65-Ab相關性癲癇患者手術后達到無癲癇發作預后的概率更低。在一例多中心回顧性研究中,8例抗GAD65-Ab相關性顳葉癲癇患者行顳前葉切除術,兩例患者達到了EngelII級結果(一年內發作不超過3次),有3例達到EngelIII級結果(一年內發作>3次,但發作減少75%),三例達到EngelIV結果(未有明顯改善)[20]。另外,也有案例報道外源性睪酮替代治療對癲癇發作的控制也是有效的,一位血清抗GAD65-Ab陽性的AE患者使用外源性睪酮替代治療后,癲癇發作頻率和強度持續降低(從每天15至20次發作到每天1~4次發作)[21]。根據部分副腫瘤性腦炎的報道,腫瘤摘除對于患者生存期的延長是必要的,但因此而改善癲癇發作等神經系統癥狀的證據尚不充分[22]。對于懷疑此類AE的患者而言,學者推薦盡早開始免疫治療的同時進行定期腫瘤篩查及規范化腫瘤治療[23]。另外,對于合并系統性自身免疫疾病的AE患者而言,控制免疫性疾病進展對減少癲癇發作是必要的。因為有研究表明在使用氨基水楊酸以及非甾體類抗炎藥和生物制劑治療的AE患者中,癲癇發作的頻率有所降低[4]。
免疫治療與傳統的AEDs治療能夠控制大多數的AE。免疫治療更是為AE治療開辟了一條新的途徑,尤其是對于自身抗體陽性的癲癇患者的療效顯著,但仍須開展進一步基礎及臨床研究以闡明免疫調節治療的機制并指導規范化的治療方案。此外,其他治療如外源性睪酮替代治療及外科手術治療對于AE的療效,僅在部分案例得以報道,尚缺乏大規模臨床及基礎研究以證明其對AE的有效性。
5 小結與展望
AE概念及分類的完善、流行病學的新發展、診療預測模型的出現無疑為識別AE患者并盡早選擇恰當的診療方案以達到更好預后提供了更多的證據。綜合考慮患者臨床特點之后進行抗體檢測及評估免疫治療的預后可能會成為未來AE患者臨床管理的一個新方向。AE治療方案的選擇也不應局限于免疫治療,傳統的AEDs尤其是鈉離子通道阻斷劑的效果不應被忽視。AE標準化診斷及規范化治療方案的提出仍需進行更多更深入的臨床及基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