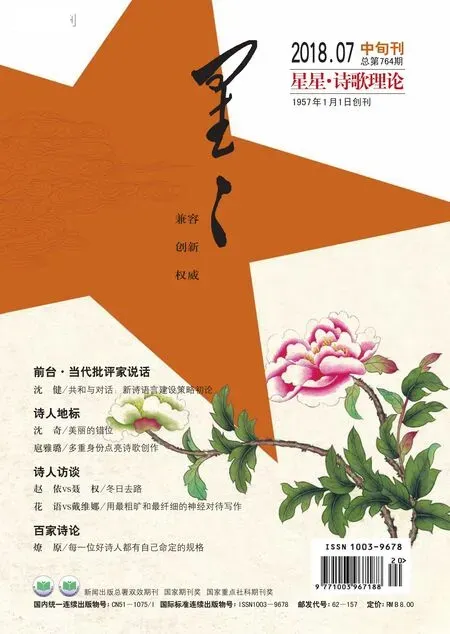用最粗獷和最纖細的神經對待寫作
花 語VS戴維娜
花 語:你是否堅持統一完整的詩寫風格,還是在不斷的人生歷練中,求新求變?
戴濰娜:如果把人生看作一件藝術品,主人翁就好像思想馬戲團里的演員,必須不停地嘗試扮演另外的人,過上嶄新的人生。這意味著他/她必須時刻創造自己,創造生活,更新知識,也包括更新性格。而這些變化都會毫不留情地暴露在詩里。詩歌是撒不了謊的。
花 語:在你的詩歌創作中,是更注重詩學技巧的運用,還是更注重直觀感受?
戴濰娜:對于作詩這門“絕境中的古典主義”,我有技術執迷。但你知道,當一個人擁有某種癖好時,他的第一要務是想方設法掩藏這怪癖。所以我不希望別人在我詩里看到技巧,我希望他們獲得直覺。
花 語:慣性寫作、定向思維使我常常將用過的話和詞語像藥棉一樣反復擦拭著靈魂中的痛處,有時不但沒有止痛,反而越擦越難受,請問,什么是你詩歌寫作中的敵人?
戴濰娜:平庸的優秀,是詩藝最大的敵人。詩歌真的是需要天分的。詩人都是天生的。靠勤勉練習,只能獲得某種優秀,但在詩歌里優秀是無效的!可以說,80%的爛詩人和19%的優秀詩人,最終都是為了那1%的真正詩人而生,為他們而寫。這殘酷極了。
花 語:在日常生活中,你是一個喜歡依賴習慣生活,并對習慣有著嚴重依賴的人嗎?你的應變能力和適應能力如何?
戴濰娜:詩歌尊重幾千年積攢下來的語言習慣,但更要反對語言慣性。這大概也可以解釋,為什么詩人的人生往往充滿了布朗運動。適應力的問題比較復雜。萊維曾經描述過,在奧斯維辛集中營里那些最優秀的人都死了,而那些糟糕的人類,他們由于最能適應非人化惡劣環境而幸存下來。當然,如今在“犧牲者”和“幸存者”之間存在很多種過渡角色,畢竟我們不是活在極端環境下。究竟要做演化鏈條的哪一部分,要有多強的適應力?這其實也取決于我們對身處的這個時代的判斷。
花 語:有人說,細節決定成敗,你是否認同?
戴濰娜:我想,要同時用最粗獷和最纖細的神經對待寫作。生活里,我是個缺乏細節感的人,神經太大條了,這可能就是我失敗的關鍵。算了,反正蠻快樂的。
花 語:現代詩歌里的書寫者,像徐志摩,戴望舒,朱湘的詩歌,寫得唯美,清新又有格調和韻致,我早期的詩歌深受其影響,后來有人說,新詩的寫作不必一定押韻,你怎么看這三個人的作品,又怎么看待新詩的不需要押韻?
戴濰娜:誰說新詩不需要韻?只不過現代詩的格律內化了。如果要寫好,其嚴苛程度不下于古詩,力氣都用在了看不見的地方。您提到的徐志摩、戴望舒、朱湘,今天看可能有些不滿足,畢竟新詩在成長,白話文在飛速演化,時代的節奏也變了,感知都變了。但不能用50歲否定30歲,20歲否定12歲。他們都是過去時代的天才。
花 語:因何與詩結緣進入詩行,最早寫詩是哪一年?
戴濰娜:初中偷偷開始寫了。詩埋伏在所有人的生活里,就看誰先扣動扳機。
花 語:你心中好詩的標準是什么?
戴濰娜:就像教堂這種建筑是對上帝的禮贊,詩歌這種文體本身就是語言的圣殿,每一行都是朝圣之路。
花 語:有沒有哪一首詩或某部文學作品的人物形象,對你產生過深刻的影響,以至改變你的人生軌跡?
戴濰娜:愛過的文學中的人物太多了。每次全情投入一部作品一個人物,就好像在書里獲得了一個分身。反之,現實中的我,也不過是這些書中人物的分身和投射。
花 語:你畢業于牛津大學,算女詩人里學歷較高的,從小到大一直都是學霸嗎?學霸的滋味如何!?
戴濰娜:比較會考試而已。但詩歌和學歷沒啥關系。
花 語:你的海外留學生涯如何?英國人最值得國人學習的品質是什么?你最喜歡英國的哪個城市?
戴濰娜:最喜歡也最懷念牛津了。那可能是我到目前為止人生最好的一段時光。古銅色的城,仿佛是智者的眼淚,歷經千萬年凝結而成一顆琥珀。只有偉大的思想才值得炫耀,這也是為什么人們念“oxford”這個詞時,要微微仰起臉面,把那個“o”音吐得尤為圓融綿長,以表對學術星空的敬畏仰慕。牛津那個地方會讓誰都想停下來思考,坐下來做學問,躺下來仰望星空。即便是我這樣的懶姑娘,當初也愣是撐起一副做學問的架勢,捧著半人高的“Reading List”孜孜地讀經典、查資料、寫論文。城里的書屋數量甚至超越了夜店,書籍比跳舞更能讓年輕男女擦出火花。我方才明了“書籍”原來可以和“性感”聯系在一起。當時身邊也盡是一群“性感生物”,一個個抱著學術如愛侶,眠在這花花世上。
花 語:翻譯是你的工作嗎?你是否喜歡翻譯這個活兒?
戴濰娜:翻譯是性價比最低的工作,也是迄今為止我所了解到的最辛勞、最不討好、最毀容的工作。從事翻譯的人都是真愛。
花 語:是否有長遠的寫作計劃并按計劃寫作?
戴濰娜:有一百個計劃等著完成,一百個戲劇開頭躺在抽屜里,家里本子上、紙殼背面、發票上、手紙上到處都是半首詩。可惡的是,激情一過就缺乏耐心和力氣完成它們。早上醒來欠著稿債,晚上又負著更多債務睡去……
花 語:詩歌之外你是個怎樣的人?
戴濰娜:我做人太乖,實在和作詩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