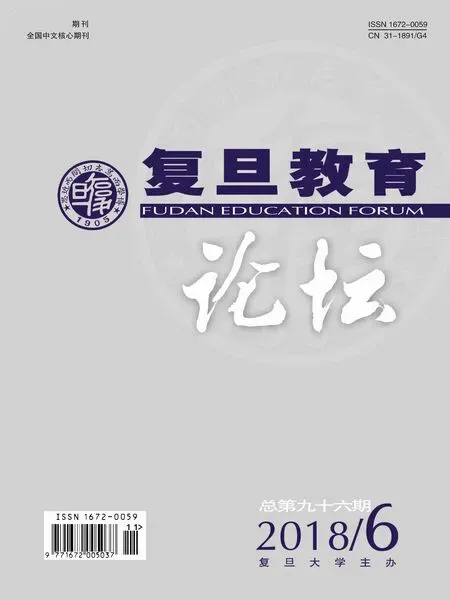學生傷害事故責任認定及風險防范
——基于2017年510例司法訴訟案件的實證研究
方 芳,陳 濤
(1.天津市教育科學研究院,天津300191;2.天津唯睿律師事務所,天津300100)
隨著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的不斷變化,校園安全隱患和安全糾紛呈多元化樣態,而公民不斷增強的權利意識和法治意識使得學校與學生之間因安全事故而產生的糾紛日益復雜化。近年來,學校毒跑道事件、校園欺凌與暴力事件、學生體育運動傷害事件等一系列學生傷害事故接連發生,學校與學生之間因事故責任的認定而頻起紛爭。受害的學生家長往往指責學校沒有盡到對學生安全管理的職責,而校方則主張自己已盡所能,不能承擔“無限責任”。面對雙方的紛爭與訴求,一些媒體基于同情弱勢群體而偏向利益受損方,對學校進行“道德審判”。由此導致校方走向另一個極端,試圖通過減少體育活動、取消校外實踐活動,甚至課間休息等來盡可能降低發生學生傷害事故的風險,繼而又引來家長對學校教育活動的不滿,加劇雙方的矛盾。究竟如何認定學生傷害事故中各方主體的責任,如何防范學生傷害事故的發生,通過真實的司法案例我們可以從中窺之一二。
一、研究方法與法律適用
(一)概念界定
教育部2002年8月21日頒布的《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2010年修訂)將學生傷害事故界定為“在學校實施的教育教學活動或者學校組織的校外活動中,以及在學校負有管理責任的校舍、場地、其他教育教學設施、生活設施內發生的,造成在校學生人身損害后果的事故”。從該規定的表述來看,凡在學生與學校存在交集的時間、地域、活動中發生的造成其傷害的事故,都屬于學生傷害事故的范疇。從主體身份來看,受害者受傷時需為在校學生,即已經取得學校正式學籍并在校就讀的學生。從時間上看,事故主要發生在學生就學期間。按照中小學的一般作息時間,上學到放學的全過程,學校都負有相應的安全管理職責;在某些特定情形下,“在學期間”還會延伸到上學之前以及放學之后。例如,學校提供校車服務時,從學生在指定地點上下校車開始,即使活動區域不在校內,學校仍負有安全責任。從地域上看,事故發生的范圍涵蓋了整個校園、宿舍等學校管理控制的全部區域;在學校組織學生從事校外活動期間,該地域范圍也覆蓋了校外活動區域。從活動內容上看,不僅包括學校在校內組織的各類教育教學活動,還包括學校組織的校外活動。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司法案例大數據和個案分析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司法案例,是指真實發生的,且已經法院審判形成正式生效判決書的案例。司法案例既不同于媒體的報道,也不同于當事人的主觀陳述,而是由法院這一具有司法權威的國家機關經過縝密的審理和判斷,最終依法形成判決的案例,從而保證了數據的客觀性、真實性和公信力。通過對判決書的分析,我們可以了解到法院最終認定的客觀事實、法院審判的理由和最終的判決結果,從而挖掘出該類案件的主要類型、案件特點以及事故責任主體對責任承擔的具體情況。
筆者采用中國裁判文書網作為檢索平臺,檢索方法采用“法條檢索法”,即通過分別輸入學生傷害事故案件所適用的法律條款(《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38條、第39條和第40條)為關鍵詞進行檢索。篩選出發生在2017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的510例學生傷害事故案例,進行深入分析。主要研究不同類型學生傷害事故中的責任認定情況,以及學校未盡到的教育管理職責,從而為學校安全風險防范建議提供依據。
(三)法律適用
根據學生傷害事故案件的審判焦點,該類型案件所適用的法律依據主要分為兩類。一是判定學校是否盡到教育管理職責的法律依據,這是認定學校如何承擔責任的前提。主要的法律依據包括《未成年人保護法》《教育法》《義務教育法》《教師法》《中小學幼兒園安全管理辦法》《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等法律法規中對學校安全管理職責的規定。二是判定傷害事故案件責任認定的法律依據,主要是《侵權責任法》第38條、第39條和第40條。《侵權責任法》依據《民法通則》中對公民行為能力的劃分,將學生傷害事故的責任認定分為三種情形。第一種(第38條)針對無民事行為能力人(一般為8周歲①以下的學生),只要是在學校學習、生活期間受到人身損害的,幼兒園、學校或者其他教育機構應當承擔責任,但能夠證明盡到教育、管理職責的,不承擔責任。該種情況適用的是過錯推定原則,即學校要承擔盡到教育管理職責的舉證責任。該種情況對學校注意義務的要求程度比較高。第二種(第39條)針對限制行為能力人(一般為8歲到18歲的學生),其在學校學習、生活期間受到人身損害,只有學校或者其他教育機構未盡到教育、管理職責的,才承擔責任。該種情況適用的是過錯原則,即只有學校有過錯才承擔責任。相對于第一種情況,該種情況對學校注意義務的要求程度相對偏低。第三種(第40條)主要針對的是學校之外的第三方對學生造成的傷害事故,由侵權人承擔責任,幼兒園、學校或者其他教育機構未盡到管理職責的,承擔相應的補充責任。
二、學生傷害事故的責任認定
隨著校園環境的復雜化,學生傷害事故的類型也呈現不同特征。不同類型的學生傷害事故在責任認定中具有不同規律,而其中所折射出的學校安全管理職責疏漏也為學校提供了不同的風險預警。為了進行更進一步的分析,我們將篩選出510個案例,對學生傷害事故的類型進行劃分。按照事故原因的不同,把學生傷害事故劃分為六種類型,如表1所示。

表1 學生傷害事故的主要類型及所占比例
(一)學生之間的行為引發的事故
學生之間的行為引發的事故是學生傷害事故案件的主要類型,在整體案例樣本中占到近半數。學生之間的行為引發的事故具有至少兩方學生主體,主體雙方是否具有主觀過錯是判定各方責任的重要依據。基于此,我們把該類事故又細分為三種類型,每種類型事故中學校承擔的責任比例不盡相同,如表2所示。

表2 三種不同類型學生行為引發的事故中學校承擔責任的情況(單位:件)
第一種是各方均無過錯的行為。該種行為最為常見,通常表現為學生之間的玩耍、無傷害故意的打鬧或者發生在參加某種活動、隊列、行進過程中的誤撞等情形。由于雙方均沒有主觀過錯,學校承擔責任的比例較大。在樣本案例中,學校無責的情況僅有2件,而承擔了主要責任以上的案件超過了50%,學校承擔全部責任的案件數量則在三種類型中占比最高,超過70%。例如,在(2016)吉0721民初3441號案件中,法院通過監控錄像查明受害學生在大課間時與其他學生嬉戲過程中倒地受傷,在學生相互游戲過程中,雙方都沒有傷害對方的故意。對此,法院認為學校在課間管理方面有疏漏,判決學校承擔全部責任。另外,該類型的另一部分案件,法院一般會通過傷害發生的過程判定直接致害的學生和受害學生也存在法律上的過失,因此要承擔相應的責任,這也是大部分案件中法院認定學校承擔部分責任而非全責的理由。
第二種是學生之間一方或雙方主觀上具有過失。從法律上講,這種過失既包括疏忽大意的過失,也包括過于自信的過失。樣本案例中通常表現為直接產生致害行為的學生不合理地使用某種器物,如削尖的鉛筆、有尖頭的圓規、玩弄飛鏢等情形致傷。在這種情形下,由于實施致害行為的學生存在主觀過失,該學生或者其監護人必然會被認定承擔部分或者全部責任,而學校在該類案件中承擔責任的比例將相對降低。此類案件中,學校完全沒有責任的案件占11%,學校承擔了全部責任的案件不足10%,但大部分情況下(占樣本案例近60%的比例),學校都會承擔小于50%的較輕責任。(2016)粵0607民初4844號案件比較典型。實施致害行為的小學五年級學生在自習課上,將修改過的作業、粘有紙屑及筆頭的透明膠卷成一團,從其座位處隔空拋向遠處的垃圾筒,在拋砸過程中,透明膠卷直接砸中受害學生左眼,導致受傷。該案中,致害學生與受傷學生不存在相互玩耍的情形,兩者本無關聯,僅是由于前者做出的某種非常規行為,造成了后者無辜受到傷害。致害學生作為限制行為能力人在應當預見其行為可能導致其他學生受傷害的情況下,仍然為之,其對所導致的傷害后果,存在主觀上的過失。而受害學生在事故中被動受傷,不存在任何過錯。因此,法院認定致害學生由于其過失行為對受害學生承擔80%的主要責任,而學校則由于負有教育、管理職責而被認定承擔20%的次要責任。
第三種是學生之間一方或雙方具有主觀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為會帶來損害后果,而希望或放任這種后果的發生,如互相斗毆或者故意找人打架致對方人身損害。此類情形需要判斷學生在傷害過程中的具體情況,區分單方致害,還是互相致害,又或者是受害方原因引起的致害方傷害行為,這對學生之間以及學生與學校之間承擔責任的結果有重要影響。在(2017)皖1323民初102號案件中,致害方與受害方都是寄宿學生,因事先有矛盾,致害方趁受害方去廁所時對其進行毆打,后經學校老師發現及時通知家屬。法院最終認定,由于致害方已屬于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由其承擔全部責任,而老師發現學生受傷后已經履行了及時告知家長的義務,學校對此不承擔責任。值得注意的是,該類型的學生傷害事故屬于校園暴力或校園欺凌的范疇,該類型案件的責任承擔方主要是實施暴力或欺凌的學生主體,但并不意味著學校就完全沒有責任,學校仍然具有教育、管理、救助等義務和責任。
(二)體育運動傷害事故
體育運動本身具有高風險性。特別是競技性運動,如足球、籃球等身體接觸較多,對抗性較強,其危險性更高。如表3所示,從樣本案例中不難發現,近90%的由體育運動造成的學生傷害事故中,學校都承擔了責任,學校承擔全部責任的案件更是超過了三分之一,加上主要責任的案件數量則達到了三分之二以上,學校沒有承擔責任的案件僅占11.61%。可見,從法院對學生參加體育運動的態度來看,其更傾向于保護學生的人身安全,也就意味著學校對此要履行更高的注意義務。在(2017)粵13民終2325號案例中,初三學生羅某在體育老師的組織下進行跳高訓練,由于起跳過桿過程中動作變形,身體向前沖出,肩背著地落在保護棉墊之外的地上受傷。法院認為學校保護措施不到位,具有一定過錯,而判定其承擔90%的責任。在(2017)粵07民終2256號案件中,體育課上老師組織八年級學生分組練習跨欄運動和標槍,在給一組同學講完跨欄動作要領和示范后,即讓體育委員進行帶隊練習,老師轉向標槍區域進行教學。學生顏某第一次做跨欄運動,助跑接近欄桿時沒有成功跨過而跌倒在地,欄桿倒在顏某右腳導致受傷。法院認為,跨欄運動屬于難度較大的教學科目,體育老師在顏某練習跨欄動作時,離開跨欄教學區域,未能給予及時有效的指導、管理和保護,存在過錯,學校應當承擔70%的責任。

表3 體育運動傷害事故中學校責任占比
當追求體育運動本身所承載的價值時,必將伴隨可能產生傷害的風險,而這一風險在從事運動之前就應當可以預見,這也對學校開展體育活動提出了更高的風險防范要求。但體育運動風險也引發了學界關于體育功能發揮與傷害事故風險之間兩難選擇的討論。“過分地強調學生傷害事故的風險,法律中又缺乏自甘冒險免責,教育活動的開展必然缺乏保障,學校教育功能難免萎縮,背離教育的宗旨。”[1]
(三)學校場地及設施引發的事故
依照《物權法》的規定,學校是建筑物、構筑物、教育教學設施和物品等物的所有權人,享有占有、使用、收益、處分的權利。相應地,《侵權責任法》則規定了物件損害責任,所有人對其享有權利的物,由于違反法律法規規定的情形,應當承擔侵權賠償責任。《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則規定,學校具有保證學校的校舍、場地、其他公共設施,以及學校提供給學生使用的學具、教育教學和生活設施、設備符合國家規定標準的義務。由此可以看出,學校具有保證學校場地、設施及教具等安全的義務。如果學校違反此項義務而導致學生傷害事故發生,學校將承擔相應責任。如表4所示,通過樣本案例可以看出,學校承擔學生傷害后果的責任比例非常高,超過95%的案件中學校被法院認為應當承擔責任,而接近一半的案件中學校承擔了全部責任,學校免責的案件僅有5件。

表4 學校場地及設施引發事故的原因類型及學校責任
需要注意的是,在該類型案件中,學生受傷的原因并非全部是學校對自有設施維護管理不當。例如,學生在跑步、走路、上廁所甚至在宿舍換衣服過程中不慎摔倒,或者學生在使用學校的某種物品過程中發生了意外,從法律的注意義務上說,引起學生傷害的原因,不僅僅是學校對物的維護管理行為,更多的仍是教育職責。(2016)湘0104民初4028號案件中,法院查明的受傷事實僅僅是小學一年級學生在上學期間摔倒,即認定學校應當承擔賠償責任。(2017)湘0623民初845號案件亦是如此,小學一年級學生在下臺階過程中摔倒,法院認為學校在臺階處沒有防護措施,遂認定學校承擔全部責任。該類型案件中的受害學生多為無行為能力人,法院對學校要求的注意義務非常高,相應地學校承擔責任的比例會比較大。
當然,也存在學生不當行為與學校對場地和設施管理的疏忽相結合造成的損害,例如學生攀爬樹木、窗臺,翻越護欄等。對此,學校被認定存在過錯的理由通常是未能及時發現、制止學生的危險行為,沒有對相關設施設置防護措施。(2017)鄂1202民初536號案件中,小學三年級學生在學校二樓教室的后墻窗戶玩耍,不慎從沒有安裝防護設備的窗戶平臺上摔下致原告摔傷。法院認為學校未在教室窗戶上安裝安全防護設施,教學樓存在明顯不安全因素,且沒有對在校學生的安全意識盡到足夠的教育、管理職責,導致原告能夠輕易翻越而摔傷,學校應當承擔80%的賠償責任。
(四)學生自身原因引發的事故
學生自身原因引發的事故,其風險來源為學生自身因素,學校在不可預見的范圍內,無法對學生自身原因造成的損害后果作出判斷與提前采取措施。因此,學生本人是該類型事故責任的主要承擔者。從表5可見,該類型事故中學校沒有承擔責任以及承擔較輕責任的案例占樣本案例的70%以上,特別是學生自身危險行為導致的事故中,學校沒有承擔責任的案件達到50%。

表5 學生自身原因引發事故的原因類型及學校責任
對于學生自殺行為學校是否承擔責任,應從三個方面來考量。一是學生的自殺行為是否與學校的過錯行為具有因果關系,如教師的體罰、學校的不當處分導致學生自殺。(2017)吉0822民初166號案件中,受害學生與其他同學發生口角后,因受到老師體罰,氣憤之下吞食學校投放的老鼠藥受傷。法院認為,學校對學生的不當批評、教育及對校園內的管理不善,是導致受害學生最終造成傷害后果的直接原因,因而判定學校承擔90%的責任。二是學生的自殺行為是否有明顯征兆,學校如果已經發現,是否采取了防范措施。(2017)豫1522民初1530號案件中,高中生在校期間割腕自傷,法院認為,事故發生前受害學生已經出現異常,老師未加注意亦未及時疏導,學校存在過錯,應承擔50%的責任。三是學生自殺后學校是否盡到了救助和通知的義務。這是學校對學生看管、救護義務的自然延伸,具體包括學校的安全保障措施能否及時發現學生存在自傷行為,發現自傷行為之后是否積極履行救助義務以及救助義務的履行是否適當。
對于學生自身危險行為引發的事故,一般是由學生本人承擔主要責任,但是,如果學生的危險行為是由于學校管理疏忽所致,學校也會承擔較重的責任。(2016)閩0922民初1875號案件中,17歲中學生因疲倦在教室中獨自一人睡著,被值班學生鎖住了教室門,由于教室門窗沒有防護網欄,受害學生被迫嘗試從教室窗戶沿著下水管道爬下樓,不幸在順爬過程中跌落受傷。法院認為,在未確定教室無人的情況下,教室門被鎖上,致受害學生被困其中而無法正常放學,學校存在過錯,對事故的發生承擔60%的責任。學生作為限制行為能力人對自身行為的危險性應有一定認知,所以也應承擔相應責任。
對于學生自身疾病引發的事故,要看學校是否提前知曉學生的特異體質情況。如果學生家長提前告知學校學生的特異體質,學校就具有了防護職責。(2016)蘇0206民初2455號案件中,受害學生母親曾口頭告知老師該名學生患有QT間期延長,曾有過暈倒癥狀,平時不能劇烈運動。體育課上,活動內容是跳繩體測,體育老師事先知道該學生患有心臟病,遂進行詢問,在得到肯定答復后,允許其測試,但測試開始不久該學生發病。法院認為,在跳繩測試前,體育老師雖對其能否跳繩進行了必要詢問,但輕信其參加跳繩測試不會出現意外,并未盡到謹慎的安全保護及管理責任,對此存在一定過錯。根據原因力大小分攤責任的原理,認定學校承擔30%的賠償責任。反之,如果家長并沒有提前告知學校學生所具有的特異體質,學校又進行的是常規教學活動,對于學生自身疾病導致的傷害,學校不應承擔主要責任。原因在于,“盡管學校對學生負有的注意義務相當高,但這種注意仍有其合理的預見范圍,應以學校對能夠和應該預見到的將會受其行為影響的人承擔的注意義務為限,而不能要求學校履行超出其職責范圍、能力范圍的無限的注意義務。”[2]
(五)校外第三人導致的事故
該類型中的第三人是指除學校工作人員、本校學生之外的第三人,也可以統稱為校外人員。例如,校外機動車在校園內撞傷學生,校內第三方施工人員造成學生傷害等。也存在校內學生因不當事由離開學校而在校外環境下發生的損害,如擅自離校或者在上學或放學過程中受到校外人員傷害等。雖然致害方來自第三方,但學校對其導致學生傷害事故的安全責任,仍屬于其管理職責范圍。“該類型學生傷害事故按加害人主觀狀態是故意還是過失可以區分為兩類,但不管是故意還是過失,都首先應由第三人承擔侵權責任,學校在未盡到教育、管理和保護職責時,如門衛管理松懈、安全管理混亂等,承擔相應的補充責任。”[3]
三、學生傷害事故的風險防范
學校的教育功能往往是通過各種形式的教學活動來實現,而教育活動本身又具有風險性。這就使得學校面臨一個兩難的選擇:“活動可能對學生身體帶來傷害,而如果單純為了防止傷害事故的發生而限制學校組織活動,那么最終又會影響教育功能的發揮,對學生的未來發展造成無可挽回的損害。”[4]對此,學校在不可能完全消除風險的情況下,應當盡量降低風險發生的概率,保證教育功能的實現。通過法院在司法案例中對學生傷害事故責任的認定,我們可以直觀地感受到學校在學生安全管理中容易發生失職的環節和細節,從而可以為學校的安全管理提供更有針對性的風險防范建議。
(一)提升學校安全教育的實效性
安全教育是預防各類學生傷害事故的前提和基礎。然而實踐中,學校安全教育的實效性并不高。在學校的教育活動中,很多學校迫于升學的壓力,不重視對學生進行常規的安全教育,特別是不能保證學生安全教育的時間。“一些學校安全教育課程設置比較零散,缺乏系統性,安全教育內容大多偏重于學生安全知識的簡單傳授,缺乏對學生安全意識的培養和安全行為的訓練。”[5]安全教育方式單一、缺乏實效。針對學生傷害事故司法案件所折射出的學校安全教育短板,我們建議,學校安全教育應著重提升其教育的實效性。安全教育不同于學科教育,其教育的目的是要提升學生的安全素養,提高學生的安全防護技能,所以安全教育的實踐性很強。這就要求安全教育要滲透在學科教學和實踐活動中。在高風險性的活動中,教師必須對學生進行專門性的具體安全教育,而這一點在實踐中容易被忽視。在(2017)渝05民終2163號案件中,一年級學生陳某與溫某在校園內操場云梯玩耍時用手抓住云梯橫桿身體懸垂,溫某用腳夾了陳某,致陳某從云梯上掉落受傷。學校在該案中雖然提供了諸多計劃、課件、兒歌、預案、記錄、公約、照片等證據來證明其進行了安全教育,但法院認為,學校未舉示充分證據證明針對該云梯對學生進行了具體的安全教育,故判定學校承擔60%的責任。另外,建議學校安全教育要立足學校常規教育活動的內容和途徑,以生動多彩、學生喜聞樂見的方式進行。在安全教育活動中強化學生的自主參與,強化學生的自我控制和管理能力,強化學生的危險判斷能力和不參與危險活動的自主意識。同時,教育行政部門及研究機構等應為學校開發更多的適合教師和學生安全技能提升的教育資源和機會,切實提升安全教育的實效性。
(二)強化學校安全管理制度執行的有效性
學校的安全管理職責基本上通過兩方面體現。一是建立完善的學校安全管理制度,包括學校的安全保衛制度、飲食衛生安全制度、校車安全制度、消防安全制度、實驗室安全制度、大型集會安全制度、住宿安全制度等。建立起完整、規范的校園安全工作制度與實操流程,可以確保校園安全問題應對的常態化、長效化。二是形成有效的執行機制。我們認為,切實有效地執行安全管理制度是學校安全管理的核心環節。安全管理制度的執行需要學校明確安全管理的責任主體,把學校安全防范部位和重點問題落實到人,全方位地建立健全安全責任體系。事實上,學校的全體教職工都是學校安全工作的直接責任人。所謂直接責任,即崗位責任,如班主任、任課教師、司機、電工等均為具體工作崗位。由于事故總是發生在某個具體工作崗位上,因此直接責任是學校安全管理工作的最基本責任單位。從司法案例可以看出,很多學生傷害事故都是在執行安全管理制度、落實具體安全責任的過程中因疏忽發生的。在(2017)皖13民終2125號案件中,學校沒有按制度規定安排學生到餐廳就餐,而是允許學生在教室就餐,學生張某站在教室后面的辦公桌旁時,被同學朱某推了一把,撞到宣傳欄銘牌上受傷。法院認為學校沒有遵守學校的制度,放任學生在教室內就餐,也沒有教師值班管理,導致學生處于無人管理狀態,判定學校承擔全責。在(2017)皖08民終1157號案件中,學生方某在校園大門內等候校車時,去校園兩側的小賣部購買零食,在其買完返回校內等車的路上,被校內職工所騎的電動車撞倒受傷。該案中,校內職工未遵守校內規定騎車穿行學校,學校的校車等候點設置在學校門口,小賣部設置在學校門口兩側,校園出口未設置減速帶等,都屬于學校管理制度的缺失與執行的無效,最終法院判定學校承擔85%的責任。
所以,強化學校安全管理制度執行的有效性,要求所有的安全責任主體都應增強安全意識,學習安全知識,嚴格遵守學校的安全管理制度。“每一個教育工作者都要常懷保障學生安全之心,常思保護學生安全之策,常做有利學生安全之事,形成全覆蓋、無盲區、立體化的學校安全管理網絡。”[6]學校應針對安全管理工作形成主次分明、協調良好的部門聯動機制,建立統一的調度部門,摒棄協作中的“形式主義”、“部門主義”,并引入監督、審查機制,對政策的執行情況予以評估。[7]
(三)建立學校傷害事故的應急處理機制
學生傷害事故一旦發生,如果沒有及時有效地處理,不僅可能使學生的傷害損失范圍擴大,也可能會使學校與家長產生糾紛、激化矛盾。根據教育部頒布的《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的規定,學校應當建立符合實際的學生傷害事故處理流程,特別需要注意以下幾個環節。其一,救助與告知義務。當發生學生傷害事故時,學校應當及時救助受傷害學生,并及時告知未成年學生的監護人。這里學校需要注意兩點。一是學校對學生的救助不僅要及時,還要恰當。學校應當對學生的傷情進行相對準確的判斷,不要因學校的誤判貽誤了學生的病情。二是學校及時告知學生的監護人,應窮盡學校所掌握的所有聯系方式。讓監護人在第一時間知曉學生所發生的事故情況,是對家長知情權的保護,也有助于避免后續處理過程中家校矛盾的擴大。其二,信息報告與公開制度。學校發生學生傷害事故,情形嚴重的,應當及時向主管教育行政部門及有關部門報告。在處理安全事故的過程中,學校和教育行政部門應當注意信息的公開與溝通,在尊重當事人隱私權的同時要保證其知情權,保證公共信息的公開性、及時性和暢通性,引導輿論的客觀和公正。學校在事故發生的第一時間應迅速啟動危機處理預案,成立危機處理小組,在救助學生的同時盡快調查事件發生的整個過程,并及時將調查結果公布。學校及教育行政部門積極、公開應對校園安全事件的過程,其實也有助于防止由媒體不實報道引發傳聞與謠言四處散播的不利局面。
四、余論
在強調學校建立和完善學生傷害事故風險防范機制的同時,我們還需要關注對學校責任的合理界定。從前述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到,學校并不是在所有類型的學生傷害事故中均需承擔全部責任。但在現實中,很多家長和公眾基于對學校與學生法律關系的錯誤認知而在學生傷害事故責任的認定上與學校產生分歧。事實上,學校與學生之間是一種教育管理法律關系,這種關系不同于學生與家長之間的監護關系。學校對學生的教育、管理職責主要應以法律法規的規定為主,同時,應根據風險來源的大小、學校對風險的可預見性、學校控制風險的成本大小等來合理判定學校承擔責任的邊界和限度。法律法規中所規定的一些預防性措施并不足以完全避免學生傷害事故的發生。畢竟未成年學生活潑好動的天性,注定其周圍存在各種各樣的風險,如果一味強調學校責任,則很可能導致教育功能的萎縮。在司法實踐中同樣如此。“法律雖然應當以保護受害人利益為其根本出發點,但不應不合理地偏向受害人,如果只考慮保護受害人的利益,但卻極為苛刻地限制了行為人的行為自由,這樣必定會使整個社會陷入畏首畏尾的境地。”[8]所以,面對學生安全問題,一方面需要學校通過建立風險防范機制來盡量降低事故發生的概率;另一方面,司法及媒體等領域應合理界定學校的責任限度,盡可能地平衡學校與學生之間的利益關系,維護和保障正常教育活動的開展和教育功能的發揮。
注釋
①2017年10月1日起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第二十條將無民事行為能力人的年齡由原來的10周歲改為8周歲,但由于本研究收集的多為2017年10月1日之前發生的案件,法院適用的無民事行為能力人的年齡還為10周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