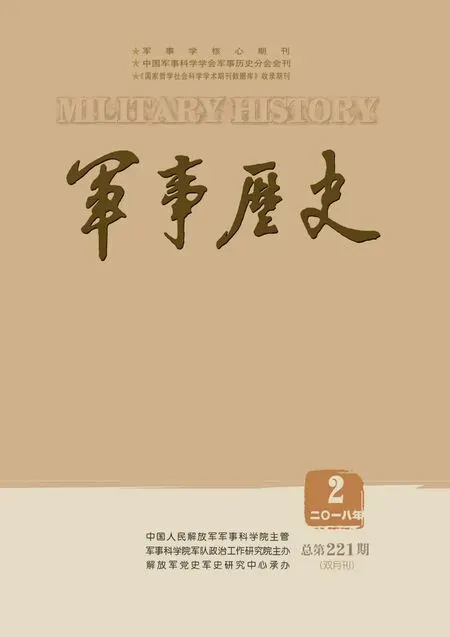在二機部第九研究所
★ () ()
1950年夏天,我謝絕導師玻恩教授的挽留,放棄英國皇家化學工業研究所研究員年薪750英鎊的待遇,回到了中國。
回國后,我先在浙江大學工作了兩年多。1952年,全國高等教育院系大調整,我調到南京大學物理系。當時,南京大學的教授很少,學校把我當作歸國高級知識分子,給我定為二級教授,但在填表時,我堅持只領三級的薪金。在南京大學,我聽從組織安排,與施士元教授一起創建了南京大學金屬物理和核物理兩個教研室。1956年7月,我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
一、秘密使命
1960年夏的一天,郭影秋校長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遞給我一張紙條,要我第二天按照上面的地址到北京報到,具體做什么不知道。
我沒有多問,第二天就動身。按照紙條上寫的地址,我來到二機部一個搞煤炭的地方,卻沒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幾圈電話詢問下來,他們讓我去城北某地報到。
第二機械工業部第九研究所(簡稱“九所”),在北京城北郊,元大都土城附近,那里有兩棟普普通通的紅磚小樓,一棟四層的灰樓是九所的辦公樓。土城墻外有條護城河,后來成為小水溝。周圍是大片空曠的土地,沒有什么人。據說,當時為建灰樓,二機部的領導和錢三強、鄧稼先等許多人都來參加勞動,聶榮臻、陳賡、張愛萍、宋任窮、萬毅等一些開國將帥也到過工地搬磚、和泥、推車。
我來之前,根本不知道要做什么。到了所里,吳際霖副所長跟我說:“要你來,是搞原子彈的,與南京大學商調你,南大不放,你先兩邊兼著。”實際上,我回學校工作總共也只有一次。1961年,我正式調入九所,開展原子彈方面的研究。
南京大學接到調我的調令,不想放。他們召回在北京學習的劉圣康,要讓他代替我去二機部,二機部不同意。于是,核物理教研室的黨員向系黨總支申請,要學校出面申請免調我,還找到校長郭影秋。郭校長來南大前是云南省省長,他是主動申請來教育戰線的。郭校長說:“你們要服從國家需要,以后會知道程開甲調去從事的工作。他今后工作的成就,也是南京大學的光榮,你們要把眼光放到年輕人的身上。”
就這樣,我改行進了中國核武器研制隊伍。后來,我才知道,調我參加原子彈研制是錢三強點的將,鄧小平批準的。
說起來,歷史還曾有一些機緣巧合。我在英國留學時,曾因與美國從事原子彈內爆機理研究的福克斯有過一次短暫接觸,因此曾被懷疑跟蹤過。沒想到10多年后,我還真的搞原子彈了。
福克斯是玻恩的學生,我的師兄。1949年11月14至16日,在愛丁堡召開的基本粒子會議上,我見到他。玻恩為我們作了介紹,雖是第一次見面,但我們談得很投機。當時美國政府正對有人將原子彈的核心機密泄露給蘇聯的事進行調查,福克斯在被懷疑之列。他傾向共產主義,被懷疑向蘇聯人泄露原子彈制造技術,卷入間諜案。會后不久,他就被捕了。開會時就有人監視他,而因為我們是師兄弟,我又是中國人,也受到了懷疑。我去法國的時候也有人跟蹤我。他們將原子彈機密—福克斯—程開甲—中國共產黨—紅色蘇聯聯系起來,跟蹤調查我。事后,導師玻恩將這段離譜的插曲告訴我說:“他們已經將福克斯當間諜逮捕了,當初他們懷疑與福克斯聯系的第一個人,就是你。”
玻恩后來說:“我的許多學生,奧本海默、盧森堡、海森堡,福克斯、彭桓武,程開甲……都去搞原子彈了。”
二、拋棄一切依賴思想
原子彈的研制,是國家的最高機密。我知道參與這項工作,就要做到保密、奉獻,包括不參加學術會議、不發表學術論文,不出國,與外界斷絕聯系,不隨便與人交往。這項工作與我原來的教學和科研不同,但我認為自己有基礎,可以干,更重要的這是國家的需要。
我從事如此絕密的工作,根據國家保密規定,對外只允許說我在研究核反應、加速器、反應堆等。有一次回南京大學,同事們要我說說工作情況。在核子組我就講核能、原子核的輸運、中子輸運等。我懂得一些,總可講一點,但到底不是做這方面實際工作的,講得不好,內行的施士元覺察到了,他感到奇怪。
原子彈研制的組織領導工作,由二機部九局負責。局長李覺,曾任西藏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1958年7月,九局在北京建立二機部九所(1963年改制擴編為二機部九院),李覺兼任所長。最初確定研究所的任務是接受、消化蘇聯專家提供的原子彈教學模型和圖紙,以及調集、培訓人員。蘇聯毀約停援后,研究所承擔了第一顆原子彈的理論探索工作。
我到研究所時,李覺所長還在“招兵買馬”,做大量的協調和后勤保障等工作,兩位行政副所長吳際霖、郭英會全力協助他。我與朱光亞、郭永懷同為技術副所長,朱光亞是技術總負責人。
最初的探索工作大致是圍繞著理論設計、爆轟物理、中子物理和放射化學、引爆控制系統、結構設計等幾個方面進行。我的任務是分管材料狀態方程的理論研究和爆轟物理研究。
當時,我有許多東西不懂,尤其是爆轟實驗。但工作分下來了,也就硬著頭皮上。后來,王淦昌、彭桓武來了,被任命為技術副所長,我們又走到了一起。由于王淦昌是搞實驗的,所以爆轟物理研究的實驗工作他就接了過去,我專管狀態方程及爆轟物理的理論研究及其他一些工作。
中國原子彈研制初始階段所遇到的困難,現在的人根本無法想象。對于這樣的軍事絕密,當時的有核國家采取了最嚴格的保密措施。美國科學家盧森堡夫婦因為泄露了一點秘密,受電刑處死,福克斯也因為泄密被判了14年監禁。中蘇關系蜜月的時候,聶榮臻元帥和宋任窮部長去蘇聯參觀,也只能在廠房、車間外面透過玻璃窗看看,不讓進去。來中國的蘇聯顧問常是不念經的“啞巴和尚”。有一次,面對中國專家,一位顧問想念一點點“真經”,但顧問團的領導一聲咳嗽,就把他的話打掉了,可見其戒備之深。那個時候,我們得不到資料、買不來所需的儀器設備,完全靠自力更生、艱苦奮斗,自己闖出一條路來。
1960年1月,二機部在“科研工作計劃綱要”中明確提出:“我們的事業完全建立在自己的科學研究基礎上,自己研究,自己試驗,自己設計,自己制造,自己裝備”,“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低級到高級”。同年8月,二機部向所屬單位發出了《為在我國原子能事業中徹底實行自力更生的方針而奮斗》的電報,指出:今后我部的事業完全由我們自己干,思想上、組織上和行動上必須迅速適應新的變化,必須拋棄一切依賴思想。
三、解決一個大難題
九所一室是理論研究室,室主任鄧稼先原來是研究場論的,他選定中子物理、流體物理和高溫高壓下的物質性質三個方面作為原子彈理論設計的主攻方向。高溫高壓下狀態方程組有胡思得、李茂生等幾個年輕人,他們在求解高溫高壓下的材料狀態方程時遇到了困難。
核材料中的狀態方程,無論對象、溫度和壓力范圍,都不同于普通的狀態方程。當原子彈中的高能炸藥爆炸時,原子彈中的各種材料就處在與常溫常壓極不相同的極高溫度壓力狀態。核反應起來后,介質的溫度可達幾千萬度,壓力達幾十億大氣壓。當時,國內沒有實驗條件獲得鈾235、钚239的狀態方程,國外視此為絕密,我們只有靠自己摸索。
用什么方法求得核反應起來后介質的狀態方程呢?托馬斯-費米理論能夠描述在極高密度和壓力下的介質狀態方程,但它是一種統計模型,不能用于千萬大氣壓以下的范圍。對這個理論各種各樣的修正,雖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都不能徹底解決低壓范圍的使用問題。鄧稼先主任曾去請教過當時在研究所里的蘇聯專家,得到的答案是:托馬斯-費米理論包括它的修正在內,只能用于研究像中子星一類極高密度的天體物理,在核武器物理中用不上。盡管他們對蘇聯專家的意見有所保留,還是缺乏理論上的自信。
我到研究所后,狀態方程小組負責人胡思得向我詳細匯報他們已經做過的工作,也講到利用托馬斯-費米理論的擔心。我認真聽取他們的匯報,不時與他們討論。有些概念,例如沖擊波,我也是第一次碰到,好在我在南京大學時研究過托馬斯-費米理論,1958年還在《物理學報》上發表過一篇關于TFD模型方面的文章。當時,這個小組的成員大部分沒有學過固體物理,更沒有學過類似托馬斯-費米統計理論。為了讓大家掌握托馬斯-費米理論及相關的修正,我給他們系統講課。系列課程講完后,又追加了固體物理方面的內容,還幫他們復習了熱力學、統計物理方面的知識,指導他們查閱國外文獻資料。事實證明,這些不僅提升了他們的業務基礎,也使他們能在更高的理論平臺去開展研究工作、攻克難題。
大家對新任務都很陌生,所以我們經常召開技術和業務方面的討論會。有些數據結果,物理、數學、力學方面的專家和科研人員從各自熟悉的專業角度進行審議,提出分析和質疑,辯論很激烈,有時爭得面紅耳赤。誰都可以登上講臺,誰都可以插話,沒有權威,但人人都是權威。即使剛出校門的年輕大學生提出的稚嫩想法,也會受到關注和鼓勵,每個人的智慧和創造力都被激發出來。
那段時間,我沒日沒夜地思考和計算,滿腦子除了公式就是數據。有時在吃飯時,我突然想到一個問題,就會把筷子倒過來,蘸著碗里的菜湯,在桌子上寫公式幫助思考。
后來,別人常說起我的一個笑話。一次排隊買飯,我把飯票遞給窗口賣飯的師傅,說:“我給你這個數據,你驗算一下。”弄得賣飯師傅莫名奇妙。鄧稼先排在我后面,提醒我說:“程教授,這兒是飯堂。”
經過半年艱苦努力,我終于第一個采用合理的TFD模型計算出原子彈爆炸時彈心的壓力和溫度,即引爆原子彈的沖擊聚焦條件,為原子彈的總體力學設計提供了依據。
拿到結果后,負責原子彈結構設計的郭永懷高興地對我說:“老程,你的高壓狀態方程可幫我們解決了一個大難題啊!”
我們在理論上摸清了原子彈內爆過程的物理規律,但原子彈起爆條件,必須進行炸藥爆轟實驗。這種沒有核材料的炸藥爆轟實驗,稱為“冷試驗”。
當時,我們在河北省懷來縣燕山山脈的長城腳下官廳水庫旁的一個沙漠地帶,借助工程兵試驗場一角,建立了爆轟實驗場,稱為“17號工地”。為了解實驗開展情況,我和郭永懷有時來這里,在帳篷里討論問題,在野外吃帶沙粒的飯菜。當時正值三年困難時期,大家連飯也吃不飽,但積極性很高。讓我們犯愁的是實驗儀器的落后和技術方案的確定。那時化爆場只有0K-15、0K-17兩種陰極示波器。針對實驗測試的需要,我擔心性能極差的兩臺陰極示波器會影響測量數據的準確性。
1960年10月,張愛萍將軍來研究所視察,聽完匯報后,他提出去爆轟實驗場考察。張愛萍、我、郭英會、郭永懷等人一起坐軍用吉普車去17號工地。一路上,我們向他匯報爆轟物理實驗場的情況。到了實驗場,我讓技術人員向張愛萍現場演示了兩臺陰極示波器的工作狀況和性能,張愛萍問得非常仔細。趁此機會,我向他提出需要性能更好的示波器,他當即表態,“我回去后立即解決。”
在回北京的路上,我們乘興在官廳水庫游玩。我和郭永懷、郭英會3人乘船來到水庫中央,突遇狂風,船差點被打翻,3人狼狽而逃。在岸的張愛萍,挎著相機一直在官廳水庫拍攝,目睹了我們幾個遇險的過程。經過八達嶺,我們還下車與張愛萍一起合影留念,可惜這張珍貴照片現在我已經沒有了,九院辦展覽借走后就沒還給我。
張愛萍是位一諾千金的將軍。不久,我們實驗急需的先進示波器就運到了實驗場。正是這次考察,張愛萍將軍樸實、隨和、敬業、尊重知識分子、敢于擔當的作風,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里。
由于工作過于緊張,我病倒了。1960年冬天,我不得不中斷工作回南京養病。為早日康復,我想盡辦法,向物理系魏榮爵教授學打太極拳、練氣功,我學會了,一直堅持。
另外,我還決心戒煙。我抽煙始于抗戰流亡年代,后來每天要抽兩包。這次為了工作,下決心不再抽煙,成功地戒掉了。
我的夫人高耀珊一直精心照料我,默默地支持我的工作,我做的每一件工作,都有她的一份功勞。平時我吃飯時考慮問題經常走神,她就剔凈魚刺,把魚肉放到我碗里。回到南京養病,她每天陪我走到中山陵。當時國家處于經濟困難時期,物資極度匱乏,為給我補身體,她想方設法買高價雞煲湯,全給我吃,孩子都沒有吃。她特別能吃苦,剩菜、剩飯都自己吃,水果爛了削削自己吃。
1961年初,春節一過,我就立刻趕回北京。這年夏天,所里派人到南京幫忙,把家搬到了北京,老大、老二仍留在南京上學。從1969年到1985年,我們一直生活在新疆羅布泊試驗基地。
到1962年夏,在我接受主抓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任務時,雖然炸藥引爆原子彈的沖擊聚焦條件的理論研究已經突破,但還沒有通過實踐驗證。后來,青海的原子彈研制基地進行了多次化爆驗證實驗(化爆沖擊壓縮ND3出中子),我則一直緊張地準備第一顆原子彈的爆炸試驗,無法參加。而我在九所時從事了這一問題的理論攻關,又兼任九所副所長(后九院副院長),所以,關鍵的最后一次化爆試驗仍然通知了我,我也立即從新疆試驗基地趕到研制基地,參加試驗。當炸藥的沖擊聚焦最終得到引爆原子彈的條件時,我們都十分激動,十分高興,因為原子彈研制的最后重要一關終于突破。
四、一碗紅燒肉
1961年下半年,原子彈的理論設計、結構設計、工藝設計都陸續展開,原子彈爆炸的一些關鍵技術也初步搞清,有的已經突破和掌握。正當我們力爭加速進程時,國防工業和國防科研戰線上出現了有關兩彈的“上馬”“下馬”之爭。后來是毛主席下的決心,結束了爭論,并成立了中央專門委員會加強領導。
三年困難時期,全國各地災害饑荒嚴重,廣大科技人員也每天餓著肚子。電力供應不足,經常點著油燈查閱資料,不分晝夜工作。聶榮臻了解到這種情況,曾打電話給周總理,要求給科技人員補助,并以個人名義向各大軍區、海軍募捐,請他們支援副食品。各大單位在物資同樣緊缺的情況下,省吃儉用,慷慨相助,保證為我們每個月提供兩斤肉和帶魚。北京軍區打了一些黃羊,也拿出一部分送給17號工地。這在那時都是極其珍貴的。國家對科學家如此關心,大家很感動。
1962年春節前,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專門招待我們,桌上有大碗紅燒肉。席間,總理談笑風生,對科技人員十分關懷,親自過來敬酒,讓我們感到總理的謙和。當時,我和朱光亞、王淦昌、李覺、吳際霖在一桌。總理到我們這桌敬酒后,國防科委二局的劉伯祿說:“總理坐中間,左邊是錢學森,右邊是錢三強,你們看出怎么回事了嗎?一看就明白中央搞兩彈的決心,兩樣都要上。”他是說錢學森代表導彈,錢三強代表原子彈。
這是我第二次見到周總理,第一次是1956年,中央領導同志在懷仁堂接見參與制定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的科學家,并合影留念。那次,周總理宴請大家,親自走到每一席和科學家握手,感到他是那樣地關心和尊重科學家。這次宴請,讓我再次感受到周總理的厚愛和重托,特別是那大碗紅燒肉,在當時真是十分不易,至今讓人難以忘懷,讓我記了一輩子。之后,隨著核武器研制和試驗的推進,我前后向周總理匯報和受到接見有十次之多,每次的感動和感受都不同。
五、 轉入核試驗
1962年夏,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研制的關鍵理論研究和制造技術已取得突破性進展,自行設計的原子彈理論方案也接近完成,爆炸試驗問題提上了日程。此時,九所正為原子彈研制全力以赴,沒有精力另外開辟原子彈爆炸試驗新領域。經研究,李覺、朱光亞等人提出建議,錢三強同意,組織專門的試驗研究隊伍,由我代表九所開展工作。
隨后,吳際霖副所長找我談話。他說:“研究所在第一顆原子彈研制中還有許多工作要做,需要集中精力繼續把這些工作做好,而對下一步要進行的原子彈爆炸試驗的技術準備工作也需要有專人來考慮。經上級領導研究決定,由你專門考慮試驗的研究與準備。”他還說:“你先去,我們后面來。”之后,他和我一起去國防科委,與二局局長胡若嘏見面。當時二局統管全國原子彈研制及試驗。
胡若嘏局長開門見山地說:“程副所長,軍委分析了國際局勢,要求我們加緊試驗準備。我們必須制定一個日程表,提出具體進度,確定大致的試驗時間。盡快拿出試驗技術方案。”
我清楚自己的優勢是理論研究,但組織上決定要我去搞原子彈爆炸試驗,我堅決服從。只要國家需要,我義不容辭。
就這樣,我又一次轉變專業方向,轉入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
由于這項工作與九所的彈體研制本身暫時關系不大,研究所也根本沒有精力考慮下一步的試驗工作,那時的我真可謂“光桿司令”。那個年代,沒有現在這樣的科研管理模式,我的工作也沒有定制的上報程序。朱光亞是所里全面負責技術工作的第一副所長,我們倆無論在什么場合見到,他都會問我工作情況,我也會毫無保留地將自己在技術方面的一些思考和打算與他交流。比如,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我不同意第一次就采用空爆方式來試驗,首先應采用地面靜態試驗方式,以后再用空爆方式;比如,我認為爆炸不是試驗的唯一目的,應開展盡可能全面的測試分析研究,還有對核試驗研究所的組建與各類技術人員需求的考慮,等等。我根據進一步的分析與計算,明確提出第一顆原子彈試驗采用塔爆方式。我的每一步工作思考,都及時與朱光亞交流,他都表示了贊同和支持。
1962年9月14日,朱光亞起草了《第一種試驗性產品的科學研究、設計、制造與試驗工作計劃綱要(草稿)》(簡稱《計劃綱要》)。我提出的有關爆炸試驗研究就成了1962年的《計劃綱要》中核爆炸試驗部分的內容。草稿完成后,他專門征求李覺、吳際霖和我的意見:“計劃綱要(草稿)已寫出。(1)不知問題和看法反映的全不全?對不對?(2)好幾個數字,不知是否估得恰當?……請審閱修改。如果不合用,當再寫合用的。”
大家都很贊賞朱光亞科學、民主的工作作風,而我與朱光亞之間則一直互相關心、信任、支持,保持著珍貴的友誼。
隨后,二機部正式向中共中央寫報告(注:名稱為《關于自力更生建設原子能工業情況的報告》),提出爭取在1964年,最遲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國第一顆原子彈,實際上是給中央立下了軍令狀。這個“兩年規劃”得到中央批準。
1962年10月16日,在國防科委大樓,張愛萍、錢三強及二機部九局的領導進行工作協調。錢三強說:原子彈試驗是一個十分復雜的、集多學科為一體的高科技試驗。僅就核爆炸試驗靶場開展的技術項目就很大,這一個個項目都需要研究、定題,并在靶場進行工程建設。這樣,就需要有很強的技術隊伍,立即著手研究立項。張愛萍提出,可以成立一個獨立機構,專門從事核試驗靶場技術工作的研究,請錢三強同志提出一個方案并推薦專家。錢三強同志表示贊成,并推薦我負責靶場技術工作。
1962年10月30日,張愛萍主持召開國防科委辦公會議,要我參加。他希望我就試驗靶場的技術準備問題進行匯報。在會上,我談了關于試驗技術方面的研究思考。我說:“關鍵是人,要有一支隊伍盡快開展工作,提出研究課題來。”
張愛萍說:“好。三強同志也是這個意見,他推薦你來主管這個研究機構。”
我的工作早已調整并轉了過來,我說:“請給我調人,我們馬上投入工作。”
張愛萍說:“馬上投入工作很好,也是必要的。不過,要房子暫時沒有,儀器無法馬上買到,機構短時間內也難健全,但研究工作要立即開始。”
11月初,呂敏、陸祖蔭和忻賢杰來了。他們3人經常擠到我在九所的辦公室里,研究討論原子彈爆炸試驗的理論、方法和工程技術研究中的問題。
呂敏,我在浙江大學教書時,他是學生,畢業后到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工作,1959年在蘇聯杜布納聯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1962年回國。陸祖蔭,是錢三強的得意門生,清華大學畢業,分到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忻賢杰,浙江大學時是王淦昌實驗室助教,動手能力很強,從王淦昌那里繼承了許多好作風。他們后來都成為有名的核試驗專家。不久,又調來了哈工大的孫瑞藩和北京航空學院的董壽莘。其他技術骨干,基本上是我提出的專業要求和人選,由鄧小平同志批示,由中央組織部、總政治部從全國全軍各地選調來的。選調時,各單位全力支持,點名要誰就給誰。先后調來的技術骨干有:理論計算專業的喬登江、謝鐵柱、白遠揚;放射化學專業的楊裕生、高才生、陸兆達;力學專業的王茹芝、俞鼎昌;光學專業的趙煥卿、楊惕新、李茂蓮、張慧友、徐世昌;電子專業的龍文澄、史君文、于冠生、李鼎基、莊降祥、曾德汲;機械專業的傅燮陽、沈希軾;地下試驗相關專業的寧培森、張忠義、丁浩然和核物理專業的葉立潤、錢紹鈞等。他們是重要的技術力量,結合每人的專長,我安排他們在研究所中分別擔任各級技術領導。
1963年春,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一批學生提前畢業來報到。夏天,又有100多名全國各重點大學分配來的大學生報到。
根據核試驗研究的需要,經過論證,我們很快提出了研究所學科專業需求和組織結構的基本框架。研究所下設5個研究室,分別為沖擊波研究室、光測量研究室、核測量研究室、自動控制與電子學研究室、理論計算研究室,同時還有資料室和加工廠。之后,為開展地下方式的核試驗,又增設了地質水文研究室。理論計算研究室(五室)室主任,在1963~1970年間一直由我兼任。
事實證明,研究所的設置完全符合核試驗任務的需要,是科學合理的。后來,除分出放化分析研究室外,最初設置的體制一直延續了20多年。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后,我們研究所成為全軍最大的研究所。
1963年7月12日,在國防科委禮堂召開核試驗技術研究所成立大會,命令由林彪簽發,大會由張愛萍主持,所長張超,政委張少華,我和董壽莘任副所長,我負責全面技術工作。成立大會上,張愛萍將軍、劉西堯副部長等與全體同志合影留念。
這樣,我不僅是核試驗技術研究所副所長(后任所長),也兼任九所副所長,1963年九所改制為九院,兼任九院副院長,直到1977年我被任命為核試驗基地副司令員,免去九院副院長。
作為九院的領導成員之一,我對產品情況是清楚的,每次試驗產品的參數和設計都會專人告知我,產品進入試驗準備前的會議,也會通知我參加討論。武器設計的檢驗必須通過試驗,根據試驗和測試為武器研制提供有價值的各種數據,提出有實際意義的建議,改進設計,解決問題。
我的雙重角色,使我不僅能更好地完成試驗任務、檢驗產品設計,還能從試驗測試的角度對設計提出看法。例如,一次試驗中,核試驗技術研究所沒有測到某重要數據,我帶著理論研究和測試人員反復查找出現問題的原因,指出這是彈體設計問題。于是提出改進建議,問題很快得到了解決。這大概是我國核武器研制與試驗之間的一種特色關系。我國核武器的發展,走出了理論、試驗、設計相互依存的良性循環之路,這種研制和試驗之間的有機結合是一般研制單位與靶場之間沒有的,對我國核武器的研制和改進起到了重要作用。
核試驗技術研究所建所初期,沒有自己的辦公和實驗地點,開始時,在總參謀部北京西直門招待所,半年后,搬到通縣倉庫。我仍住在二機部九所宿舍,每天來回跑。
1964年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后,核試驗技術研究所搬到新疆紅山,我把家也搬到那里,直到1984年調回北京,為了中國核試驗,我在戈壁灘上工作、生活了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