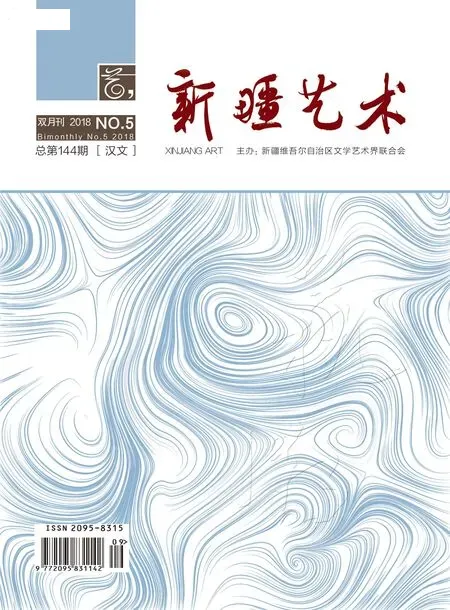唐代西州的屏風畫
□ 劉文鎖

牧馬圖屏風畫(唐)
一、屏風畫的發現與問題
屏風畫是中國古今美術形式的一種,得自于作為家具的屏風,屬于人們社會生活的一方面。因古屏風存世者極少,據考古發現僅有漢代以來的若干架,且都是墓葬里的隨葬品,我們對古代屏風和屏風畫的了解遠為不足。雖有不少文獻記載,但也只能提供一個大體的觀察,欲知其詳細則須依賴屏風和屏風畫實物的發現。
屏風在唐代社會生活中已頗為流行,因使用者的社會階層而有不同的品類,屏風畫的制作也在前代基礎上得到大的發展,有不少的創新。據記載,唐太宗時虞世南曾恢復列女傳屏風畫的圖樣,薛稷則創制了六扇鶴樣屏風畫。①唐憲宗著《前代君臣事跡》,令畫師“寫于六扇屏風以示宰相”。因六扇式的屏風是主流,六扇式屏風畫也成為屏風畫的主流樣式。這些都是根據文獻的記載而了解到的唐代屏風畫情形。
有人試圖根據唐墓中的屏風式壁畫,來窺測唐代的屏風畫,不失為一個探討的途徑。根據考古發現,這種屏風式壁畫的例子在30座以上,集中在關中、太原及新疆吐魯番地區。它們在繪制上的特征是:布局上依照墓室的結構,以棺和棺床(墓主人位置)所依靠的墓壁為中心而展開,例如太原南郊金勝村唐墓群的3座屏風式壁畫墓(屬武周時期),其八扇連屏的所謂“樹下老人圖”即繪制于墓棺所依靠的壁面上。②屏風式壁畫發現數量最多的屬關中地區。據研究,此類墓葬的年代經歷了從初唐到晚唐的各個階段,而屏風式壁畫在布局與題材上也相應經歷了幾次變化,總體上是屏扇的數量逐漸減少(自22扇減至獨幅);在題材上,由單純的侍女畫發展為十扇式樹下仕女(美人)和八扇式的樹下老人;天寶年間新創的樣式六屏式和三扇式或獨幅立屏題材大為豐富,六屏式保留侍女、樹下老人、樹下仕女,新增花草、山水;三扇連屏及獨幅立屏有樂舞、宴飲、雙鶴、胡人牽牛;中、晚唐時六屏式仍是主流樣式,保留有獨幅式,題材上流行樂舞和云鶴、花鳥等翎毛圖。③
如以墓葬壁畫中的屏風式畫來觀察唐代的屏風畫,自然存在著不小的問題,譬如屏風式壁畫所處的墓葬情境問題。似乎不可以認定墓室里的屏風式壁畫就是其當代所流行的屏風畫。最好的辦法是找到唐代屏風和屏風畫實物,但這是可遇不可求的。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凸顯出吐魯番出土屏風和屏風畫的價值。它們出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地,屬于唐西州時期。從畫史上看,它們是稀世的唐人繪畫真跡。以下是這些發現的基本信息。
1972年自阿斯塔那古墓群張氏家族墓地中的三座墓(72TAM187、188、230墓),發掘出土三架木框絹畫屏風,其畫作分別以弈棋(圍棋)仕女、人物鞍馬、樂舞為題材。④三架屏風出土時均已殘破,其中的《弈棋仕女圖》經故宮博物院修復后,重現了大體完整的十七個人物的形象。其余二墓所出的畫屏殘件,已無法復原。由于歷史原因,發掘時的考古信息殘缺不全,而所存的各幅(扇)繪畫散刊于不同時間出版的圖錄中,畫作的名稱也因人而異。
與此屏風畫有關的,另有兩種發現:一種是從墓葬出土的成組的絹本和紙本設色屏風畫殘片,有三組,系早年分別為斯坦因和橘瑞超從阿斯塔那墓地掘獲的兩組,⑤及1969年自哈拉和卓墓地出土的一組。⑥此外,還有若干以仕女、樂舞伎和花鳥為題材的絹本、紙本殘片,出自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的墓葬,分別為橘瑞超掘獲及新中國時期考古所得。⑦另一種是在三座墓的墓室后壁,保存了屏風式的壁畫(38、216、217號墓)。這幾種繪畫都是有關聯的,尤其是屏風畫與墓室的屏風式壁畫之間。
有關畫作的研究還是少見的。三墓所出絹畫的報道,見于1973年10月21日的《新疆日報》,⑧及《文物》1975年第10期上發表的李征與金維諾等的文章。當時關于絹畫的名稱還沒有確定下來。金維諾對畫面內容的考釋是很詳細的,他并且還作了初步的復原。令人遺憾的是,對于研究來說十分重要的詳盡出土信息,在2000年《新疆文物》上刊發的1972年墓葬發掘報告中未予介紹。⑨我們所能依據的仍然是那些簡單的報道。
幾乎所有關于唐代屏風畫和屏風式壁畫的論著都會引用阿斯塔那的材料,例如楊泓關于屏風和唐代六曲畫屏以及唐代墓室壁畫的論著,⑩以及賀西林與李清泉所著《中國墓室繪畫史》[11]等。他們都指出了吐魯番出土屏風畫的重要性,但是我們需要知道這些畫作研究的真正問題之所在。
在我們看來,需要將屏風、屏風畫、屏風式壁畫三者結合在一起,置于屏風和屏風畫史以及墓葬情境中去討論。這一兼及了美術史與墓葬考古的視角涉及到下述幾方面問題:(1)墓葬的結構、年代與墓主人身份;(2)屏風、屏風畫的復原與畫作的定名;(3)屏風式壁畫的內容與定名;(4)關于墓葬的隨葬屏風與屏風式壁畫關系的問題。在此我們看到了幾個有意義的研究,關注到了壁畫墓結構與壁畫配置、墓室隨葬屏風與屏風式壁畫的制作等問題。[12]簡要的說,唐代延續了至少始自漢代的墓室隨葬屏風習俗,將屏風擺放于棺(或棺床)的三圍,或者以繪于棺床邊側墓室壁面的屏風式壁畫來象征。這些屏風畫與屏風式壁畫之間存在密切關系。
對各畫作的定名也是個問題,但這需要深究畫作的內容并作出復原,涉及到了唐畫題名的意義和唐代畫師的習慣做法。除了人們關注最多的《弈棋仕女圖》在定名上比較一致外,其余諸畫作皆各自表述。它們都需要做復原和定名的研究。
二、屏風畫的年代與墓主人
出土屏風畫和屏風式壁畫的墓葬,年代上主要屬于盛唐時期。盡管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擾動,根據隨葬墓志、出土文書及尸骨等推斷,它們應都是夫婦合葬墓。這一流行葬俗對判斷墓室隨葬屏風的制作年代制造了困難,因為無法確定屏風究竟是哪一位逝者的隨葬品。我們知道這些屏風畫都是繪于入葬前的某個時段,但這個時間也是無法確切推定的,惟有的繪畫年代的參考只能是依據同樣證據推定的墓葬年代。
斯坦因和橘瑞超所得的絹本和紙本屏風畫,以及1969年從哈拉和卓墓地出土的紙本屏風畫,由于考古信息缺失嚴重,其年代的推定較費周折。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可以將所有這些畫作所出的墓葬年代,大體上給予推定。三座隨葬屏風的墓葬以及兩座繪有屏風式壁畫的墓葬,其墓主人的身份可以推知,為麴氏高昌國以來本地望族的張氏,在西州時期他們都任有官職,至少我們知道其中的一位張氏娶了麴氏高昌王族的后裔(188號墓)。因此,可以說這些屏風畫和屏風式壁畫的墓主人屬于西州的上層人士。

屏風墓與屏風式壁畫墓的年代與關系
對屏風和屏風畫的復原并非易事。當1972年發掘時,三座墓葬隨葬的聯屏木框屏風都已經殘破,在木框上保存了裝裱的絳紫色綾邊,絹畫皆已成殘片。其中,《弈棋仕女圖》屏風被發現于187號墓停尸臺的西北隅,所謂《侍馬圖》屏風被發現于188號墓停尸臺下,230號墓所出畫有樂舞伎圖像的屏風則被發現于墓室入口的積沙下。這些出土位置表明了當時屏風的擺放位置(187、188號墓),以及遭受了擾動的情形(230號墓)。
絹本與紙本的屏風畫,其中如《弈棋仕女圖》是可以復原的。其它殘存的屏風畫作,亦可以根據內容討論其原件及可能的題名。
三、《弈棋仕女圖》的復原與題名
故宮修復后的《弈棋仕女圖》畫作,常見的說法是共有十一位左右的人物;[13]但據《中國美術全集》所刊布的畫面,計有十七位人物,以及草木、云霓和飛鳥等。[14]
畫面描繪的是兩名(闕一)對弈圍棋的仕女,左右有親近觀棋、侍婢侍候、兒童嬉戲,構成一幅以對弈圍棋為主題的仕女圖。[15]關于此畫作的題名,金維諾和衛邊曾將畫作稱作《圍棋仕女圖》。[16]《中國新疆古代藝術》和《天山古道東西風》兩書中,它被分作了四幅左右分別命名,最核心的部分,被稱作是《仕女弈棋圖》和《弈棋貴婦絹畫》。[17]在《中國美術全集·隋唐五代繪畫》里,將這幅畫命名為《弈棋仕女圖》。[18]而同年出版的《中國繪畫全集》則分解為七幅畫作,各自表述和命名。[19]這種題材尚不見于唐代的傳世畫作,不過,《宣和畫譜》著有周昉的《圍棋繡女圖》。[20]遵照唐朝仕女畫的題名習慣,這幅畫作題名作《弈棋仕女圖》是比較適宜的。
當初,金維諾、衛邊曾就修復后的畫面提出過一個基本的復原方案:以弈棋的仕女居中,大體上左側視者居其左側,右側視者居其右側。[21]但是,仍然有不少的問題需要解決。顯然,它們如何構圖、是否采用了分屏的方式,是個費解的問題。
復原整幅畫作的依據,除以左、右側視的姿式確定人像的分班排列外,尚須酌定畫作的主題。側視像是主要的,但也不排除少見的正視像。在故宮修復后的畫面中,見于多幅的飛鳥亦采取左、右側視的姿勢,與人像相一致。須注意《弈棋仕女圖》畫作的完整性,它與230號墓隨葬的樂舞伎畫及188號墓的人物鞍馬畫所選取的題材是不同的,后二者及樹下人物和花鳥等更適于作屏風畫。我們從單幅畫面的角度來嘗試復原整幅的畫作。
(1)畫面一:弈棋仕女

弈棋仕女(采自《天山古道東西風》沈昕璐摹)
殘存畫幅縱69厘米、橫59.7厘米。[22]所存為右側弈棋仕女及完整的棋盤,并座下之榻,仕女取右側視四分之一坐像。殘損的左側弈棋仕女畫面,推測約占五分之二畫幅,故其整幅的寬度在約100厘米(約3尺);而縱高上參照人像的比例及其它保存較完整的畫面,應該在90厘米左右。這應該是最大幅的畫面,居于整幅畫作的中心位置(因而涉及構圖的問題)。這幅畫面的尺寸,可推定為90×100厘米。

右班觀棋仕女(采自《中國美術全集·隋唐五代繪畫》沈昕璐摹)
(2)畫面二:右班觀棋仕女
縱96厘米、橫91厘米。為右側視四分之一的仕女與隨侍侍女的立像,二者的頭頂上方畫了飛鳥(燕子)、白云和紅霓。[23]在尺寸上,仕女像大于其身后侍女像的處理手法,是為了表現二者位置的斜向遠近(偏向中景的位置)而采取的類似透視的畫法,它令人想起周昉在《簪花仕女圖》里用過的技法。
(3)畫面三:右班侍女
殘幅尺寸:縱83.5厘米、橫89.3厘米。三位侍女的立像。左側著紅衣者取左側視四分之一姿式,左手持蘋果;其身左著紫衣侍女取正視姿式,二者貼身,為一組;右側紫衣侍女為右側視四分之一像,手執高圈足金盤,內置一高足金杯。與畫面二相同的頭頂上方處理法,亦是云霓和飛鳥。[24]從內容上看,這三幅像為一組。
(4)畫面四:左班觀棋仕女

右班侍女(采自《絲路瑰寶》沈昕璐摹)
殘幅尺寸:縱61.4厘米、橫65.5厘米。與右班觀棋仕女相對應,為一仕女及其近侍侍女的左側視四分之一立像。仕女的衣飾和手式與右班不同,以抵消因對稱造成的呆板視覺。在身后侍女的選位上也有所不同,幾乎站在了同一條線的近景位置。在頭頂上方的處理上,沒有描繪云霓和飛鳥。[25]
(5)畫面五:左班仕女與童子
由兩片修復時被分拆開的殘幅組成,即所謂的“樹下美人圖”和“童子圖”。“樹下美人圖”尺寸:縱89.8厘米、橫74.4厘米;“童子圖”尺寸:縱63.9厘米、橫52.6厘米。仕女取左側視四分之一姿式,在她身側的中、遠景位置畫了一片樹林和竹林,注意它們的尺寸,以及分別描繪的樹林與草甸,處理為近、中景的人像構圖法,表明二者是可以拼合的。拼合后的畫面尺寸,可能如畫面三和畫面六,高約90厘米,寬約90厘米。童子所踐的草甸,應該出現在林間,所以這幅所謂的“童子圖”應該移至樹林的下方,因此也可以解釋左側懷抱拂林狗的童子,其向右側身,并以右手指向其上方的林木。[26]

左班觀棋仕女(采自《天山古道東西風》沈昕璐摹)

左班仕女與童子(采自《天山古道東西風》沈昕璐摹)
(6)畫面六:侍仆
這是最后一幅畫面。殘幅,尺寸不詳。比例較小的畫像。一共畫了六位侍仆,呈侍立或坐姿。在頭頂上方亦繪畫了飛鳥。注意殘存的一截雕欄,表示是在園林中。兩個碩大的花蕊形的圖像可能是陽傘。有兩人畫成了右側視四分之一的姿式,余者皆左側視四分之一。[27]這與最右側的畫面三的右班侍女中的兩幅左側視像,在構圖上有了呼應。因此也加深了我們的印象:畫面三和畫面六,一定是分處在整幅畫作的右和左端。

侍仆(采自《中國美術全集·隋唐五代繪畫》沈昕璐摹)
六幅畫面的高度應該是一致的,推擬為90厘米;而各幅的寬度可能大致相同,為90厘米左右。在形式上可以看成是類似橫卷軸畫。從殘存跡象看,似乎不存在類似Ast.iii.4.010和人物鞍馬、樂舞伎畫那樣顯示分屏裝裱的絳紫色絹帶或棕色畫框,表示它們是屏風畫,這一形式也是紙本的屏風畫所采用的。因此,問題是:橫長卷的《弈棋仕女圖》絹畫,如何裝裱在屏風的木框上?
屏風本身已經難以復原。但我們根據六幅畫面的存在,可以推理裝畫的木框,也相應地分為六個屏格,其尺寸應該大于畫面的畫幅,可能在100×100厘米左右(約合3×3尺)。這個寬度似乎不允許作相聯的曲屏處理。因此,它們實際上可能被分成了六架,每架裝有一幅畫面(一扇)。這種形制,類似于六架“插屏”,在擺放上比較自由。
根據上文的推想,不妨試著模擬《弈棋仕女圖》的原件,分占六個架子的六幅畫面,以畫面一的弈棋仕女為中心,依次展開了其余的五個畫面。但是,在布局上弈棋仕女的畫面不可能居中,它偏在了右側的一組三格中。它們的出土位置在棺床的西北隅,如果未被擾動的話,這表明當時屏風是集中擺放那個位置的。

《弈棋仕女圖》復原
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此畫作的作者以及屏風的制作。唐朝仕女畫是一個流行題材,有張萱、周昉等名家。《歷代名畫記》《唐朝名畫錄》《宣和畫譜》等著錄有仕女畫多幅,如周昉《游春仕女圖》《烹茶仕女圖》《憑欄仕女圖》《舞鶴仕女圖》《紈扇仕女圖》《游戲仕女圖》《圍棋繡女圖》等。[28]又有“得周昉筆法為多”的杜霄,畫作有《游行仕女圖》《撲蝶仕女圖》等。[29]《圍棋繡女圖》不存,此《弈棋仕女圖》畫作以園囿中弈棋及觀弈仕女為題材,似乎是京師流行的弈棋仕女畫的仿作。鑒于三座隨葬了六扇和八扇屏風的墓葬(230、187、188號),其男墓主為張禮臣及其兄弟或從兄弟,據188號墓出土墓志,其女墓主麴娘出身于前麴氏高昌王族,是一位畫家(“晨搖彩筆,鶴態生于綠箋;晚弄瓊梭,鴛紋出于紅縷”[30]),由此我們不妨猜測,《弈棋仕女圖》及其它二墓隨葬的屏風畫,很可能都是出自這位麴娘之手筆。
四、其它屏風畫
1.人物鞍馬畫
出自188號墓,木框連屏設色絹畫,八扇。各扇畫面的尺寸為縱53.7厘米-56.5厘米、橫22.5-27.0厘米。[31]屏風以木框為骨架,有的木框保存還很完整。出土情況顯示出,絹畫是裱糊在木框上的,但絹上有用墨點模擬的釘眼(存疑)。[32]有三幅還保存了用絳紫色絹帶裝裱的分屏框,這些框對應的是背面的木框架。
每扇的畫面都是獨立的,描繪的是相同的題材:在樹下的侍仆和鞍馬。保存較佳的畫面上,樹的上方還畫了云霓和飛鳥,以及樹下的草甸,各有兩幅分別采取左側視和右側視的人物鞍馬,其中,右側視者畫成了靜立的姿式,左側視者則取行走的姿式。我們推測,全部的八幅(扇)畫面,應該是左、右側視像各占了半數。
人物鞍馬題材是唐代流行的繪畫題材之一種,京師等地的畫家中也不乏擅長畫人物鞍馬畫的名手,如張萱、韋無忝、張遵禮等輩。[33]這種題材適宜作屏風畫,即所謂“鞍馬屏障”。很可能,西州的這幅“人物鞍馬畫”是京師流行的同類題材的仿作。

八扇式“人物鞍馬畫”(局部)(采自《中國繪畫全集》第1卷、《絲路考古珍品》等)

六扇式樂舞伎絹畫(采自《絲路考古珍品》等)
2.樂舞伎畫

絹本樂舞伎畫(采自《西域考古図譜》)
230號墓(張禮臣墓)出土的絹本設色六扇連屏畫,出土時也有一段木框相連,框上裱了絳紫色的綾邊。每扇畫一位樂舞伎,既有正面像,也有分向左、右的側身像,取四分之一側視姿式。據說為樂伎四,舞伎二。[34]其中的兩幅保存較佳者,見諸多種圖錄中,一幅是著胡服的舞伎的正面像,其尺寸是縱51.5厘米、橫25.0厘米;另一幅是持樂器(阮咸)的樂伎。這應該是全部六扇畫的畫面規格。
前述為橘瑞超所得的一塊絹畫殘片,畫一位取左側視姿式的著胡服的樂舞伎。看上去,無論從題材還是畫法上,似乎是出自230號墓的殘片。《西域考古圖譜》里把它標注為出自吐峪溝,[35]應該是錯誤的。
《歷代名畫記》記談皎“善畫人物,有態度,衣裳潤媚,但格律不高”。其畫作有《武惠妃舞圖》《佳麗伎樂圖》等。[36]大抵伎樂畫亦是唐時京師畫師所取的一類題材,而西州張氏墓所出土的此幅樂舞伎屏風畫,也可能是本地畫師的一個仿作。
3.《觀樂仕女圖》
斯坦因所得的絹畫(Ast.iii.4.010),出自他編號的Ast.iii.4墓中,出土時被發現卷成卷擱置在墓室的地面上。他推測是盜墓賊所為。這幅絹畫最初由安德魯斯(Andrews)做了描述,收入《亞洲腹地考古圖記》有關阿斯塔那獲得文物的“清單”中。[37]隨后賓勇(L.Binyon)對絹畫做了復原研究,他根據保存下的較完整的分屏裝裱的棕色絲框,推測每屏的尺寸是21×8?英寸,約當53×22厘米[38];絹畫表現的是樂舞伎和站立在樹下的仕女(所謂“樹下美人”),他推測至少有5屏以上,畫面可以分為兩組,分屬于不同的屏格。[39]
實際上,這幅畫作在題材上有些類似《弈棋仕女圖》,它不是人物鞍馬畫和樂舞伎畫以及花鳥畫,那種各自相對獨立以宜于聯屏的無情節的題材。它的內容由兩部分組成:取左側視觀賞姿式的仕女,一共有三位以上,每人的身后都有一位隨侍的侍女;取右側視或左側視的樂舞伎,有三位以上,作表演的姿式。畫作表現的是仕女們觀賞樂舞的情節,樂舞伎的畫面應該是在仕女畫面的右方。
每位帶了侍女的仕女,連同她們所立身其下的樹以及樹上方畫的飛鳥和云霓,被安置在了一個屏格(扇)內。在第三位仕女的左側,還有兩扇,殘損得很嚴重,殘存有侍仆像的局部,因此這兩幅可能畫的是在仕女們的后面侍應的仆從,類似于《弈棋仕女圖》的畫面六。位于右端的三位樂舞伎像,應該是畫在了同一幅(扇)內。這樣,就構成了一架六扇式的畫屏,畫作本身是表現仕女們觀賞樂舞的主題,可以暫定名為《觀樂仕女圖》。[40]它的畫功不亞于《弈棋仕女圖》,筆法很嫻熟。

《觀樂仕女圖》摹本(采自Innermost Asia,Pl.CV-CVI)
4.紙本“樹下美人圖”與“樹下人物圖”
橘瑞超所得的一件兩屏紙本設色“樹下美人圖”和“樹下人物圖”,著錄于《西域考古圖譜》,為東京國立博物館收藏。[41]尺寸分別是138×54厘米和149×57厘米。“樹下美人圖”的里張為一份先天二年(713)和開元四年(716)的賬,指示該畫的年代在此年份之后。它是為了使紙本的畫張厚實、耐用而裱糊上去的。兩件畫作的出處不詳,大約也是出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地的某座墓葬,由于尺寸大體相當,故可以推測它們為同一架屏風的殘余兩屏。

紙本“樹下美人圖”與“樹下人物圖”(采自《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第15卷)
在構圖上,兩幅畫面都由側視站立在樹下草甸上的一主一仆畫像構成,樹的上方未畫出云霓與飛鳥。每幅畫面用棕色的粗線畫出屏格的畫框。這一畫法來自于絹本的屏風畫,它們應該是一架六扇式屏風畫中的兩幅(扇),比絹本畫屏高一些。
所謂的“樹下美人圖”是一幅身后隨侍侍女的仕女畫。另一幅“樹下人物圖”畫的是一位由侍從扶持的戴帷帽的男子。一般說,一樹一人(或兩人)的題材是屏風畫所適用的,在構思和畫法上,樹是為了避免單純人像的呆板而點綴到畫面上的,這與有情節的畫作不同,所以不宜作過多的解釋。前述的“人物鞍馬畫”也是如此。這種屏風畫因為沒有情節而缺少主題,在定名上可以總稱之為“樹下人物圖”,就仕女、老人等不同身份的人物來說,自然也可以稱作“樹下美人圖”和“樹下老人圖”。
這幅屏風畫的扇數不得而知,大約也是六扇屏風形制,其余的四扇所繪也是相同的樹下人物畫。人物畫(包括仕女)是唐代繪畫的題材之一,如唐中宗時畫師周古言,“善寫貌及婦女”,作有《宮禁寒食圖》《秋思圖》等。[42]以樹構圖是一個長期流行的畫法,尤適宜仕女畫,可減少單純人像的呆板,亦可起到區隔畫面的作用。這種樹下人物畫,很容易令人聯想到南朝盛行的“竹林七賢”圖,而一樹一人(或主仆二人)的構圖也是適宜屏風畫的。
5.紙本花鳥屏風畫
另一件紙本屏風畫1969年出土于哈拉和卓墓地,保存了連在一起的三扇畫張。尺寸為縱140厘米、橫205厘米,單扇的畫幅寬約68厘米,高度上接近前述的“樹下人物圖”,但略寬一些。外框和分屏(扇)的框都是用較寬的暗紅色線描繪的。

紙本“花鳥畫”(采自《中國繪畫全集》第1卷)
我們相信應該還有另外三扇畫張,它應該是一架六扇式紙屏風的畫張。每扇都畫了在不同的花下的不同的鳥,站在怪石嶙峋的草甸上,在花的上方畫了紅色的云霓和飛鳥。[43]在題材與畫法上,它與阿斯塔那217號墓的六屏式壁畫“花鳥畫”如出一轍。這種花鳥畫是唐朝流行的題材之一,其最為馳譽者為京兆人邊鸞,張彥遠贊其花鳥畫“精妙之極”、“花鳥冠于代”。《唐朝名畫錄》說其“凡草木、蜂蝶、雀蟬,并居妙品”。[44]顯然,西州的這些花鳥畫作品又是當地畫師對京師所流行畫樣的仿作了。這種花鳥畫極適宜于作屏風畫。

阿斯塔那217號墓屏風式壁畫花鳥畫
五、唐西州屏風畫的樣式
上述保存的唐西州屏風畫作品,其樣式大致可推測如下:
畫作以絹本為主要的形式,另有少數的紙本,這是唐代繪畫的一般情形。在扇(屏)數上以六扇(屏)為主,這是盛唐以來流行的屏風和屏風畫樣式,甚至三座屏風式壁畫墓也采取了六扇屏風的樣式。僅有一例(188號墓)是八扇(屏)的人物鞍馬畫(絹本)。六扇絹本是一個主要的形式,其題材有“樂舞伎圖”和《弈棋仕女圖》《觀樂仕女圖》。它至少出現了兩種規格:一種如《弈棋仕女圖》,很像是尺寸較大的方形屏風畫,大約在3尺見方;另一種屬于小型的屏風畫,其縱、橫尺幅大約在2尺和1尺。就其屏風來說,我們還不能確知它們是如何制作和使用的。
從發現數量上看,紙本的屏風畫似乎不如絹本那樣流行。橘瑞超獲得的二屏紙本設色屏風畫應該也是六扇式的,其題材為所謂“樹下美人圖”與“樹下人物圖”。1969年出土于哈拉和卓墓地的另一套紙本設色花鳥畫,可能也是六扇式。這兩套屏風畫規格相當,都是較絹本大的大屏,在題材上也與絹本不同。

阿斯塔那38號墓屏風式壁畫“樹下人物圖”

阿斯塔那216號墓屏風式壁畫“鑒誡圖”
因此,我們可以把這些屏風畫區分為紙本和絹本兩種,其規格也可以明確地區分為大、小兩種。這種差異當然取決于屏風的制作和使用方式。絹本的屏風一般是較小型的,而紙本屏風則是六扇大屏的形式,它們的繪畫題材也不一樣,似乎存在各自的流行樣式。
比較三座壁畫墓中的六扇屏風式壁畫,它們的題材包括了“樹下人物圖”、“鑒誡圖”及花鳥畫三種,與紙本屏風畫是類似的取材。此外,在繪畫的尺寸上,“樹下人物圖”(38號墓)每幅高約140厘米、寬約56厘米,而“鑒誡圖”則為高約140厘米、寬約71厘米。這與紙本屏風畫是接近的。[45]據此推測,墓室里的屏風式壁畫所依據的粉本似乎是紙本的六扇式大屏。
注釋:
①[唐]張彥遠著、俞劍華注釋《歷代名畫記》卷九《唐朝·上》,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64年,第182頁:“薛稷,字嗣通,河東汾陰人……善花鳥人物雜畫,畫鶴知名,屏風六扇鶴樣,自稷始也。”
②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太原南郊金勝村唐墓》,《考古》1959年第9期;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太原市金勝村第六號唐代壁畫墓》,《文物》1959年第8期。
伴隨企業的發展,在企業集團戰略性成本管理創設中,應該將成本企劃作為企業集團的重點,按照企業經營領域以及產品方向定位,進行產品成本管理方案的設計,提升企業運行的價值性。在企業成本企劃的過程中,其作為一種現代性的成本管理方案,可以對企業新產品的發展進行規劃,結合戰略性的發展目標,進行成本管理制度的創新,為企業成本管理理念的確定提供支持。而且,在企業成本企劃中,相關人員應該結合預期銷售的內容,確定期望利潤,明確目標的成本,并根據這些內容進行產品工藝流程、流通加工以及包裝成本等問題的確定,展現企業集團成本企劃工作的價值性[3]。
③參見張建林《唐墓壁畫中的屏風畫》《遠望集——陜西考古研究所四十周年華誕紀念文集》,陜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98年,第720-729頁。
④有關墓葬資料參見李征《新疆阿斯塔那三座唐墓出土珍貴絹畫及文書等文物》《文物》1975年第10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魯番阿斯塔那第十次發掘簡報(1972-1973年)》《新疆文物》2000年第3-4期;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等編《吐魯番出土文書》第八冊,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418-467頁。
⑤分別見:Stein,M.A.,Innermost Asia,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Kan-su and Eastern īrān,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1928,Vol.II,pp.693-694;Vol.III,Pl.CV,CVI;香川默識編《西域考古図譜》,東京:國華社,大正四年,圖51。分屏的兩幅畫作收入《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第15卷《中央アジア》,小學館,1999年,第272頁,圖294-295。亦收入金維諾主編《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編2·隋唐五代繪畫》,人民美術出版社,1997年,圖版十二。
⑥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編《中國繪畫全集》第1卷《戰國—唐》,文物出版社,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圖七十,“圖版說明”第11頁。
⑦參見:《西域考古図譜》,圖52;《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編2·隋唐五代繪畫》,第15頁,圖版六;《中國繪畫全集》第1卷《戰國-唐》,圖七一,“圖版說明”第12頁。
⑧新疆博物館考古隊《吐魯番新出土一批古代文物》,載《新疆日報》1973年10月21日。
⑩楊泓《屏風》《“屏風周昉畫纖腰”——漫話唐代六曲畫屏》,孫機、楊泓著《文物叢談》,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222-243頁;楊泓著《美術考古半世紀——中國美術考古發現史》,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268-269頁。
[11]賀西林、李清泉著《中國墓室壁畫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210-211頁。
[12]李星明著《唐代墓室壁畫研究》,陜西人民美術出版社,2005年;馮筱媛《唐代墓室屏風式壁畫研究》,中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6年。
[13]見金維諾、衛邊《唐代西州墓中的絹畫》,《文物》,1975年第10期,及《新疆文物》2000年第3-4期。
[14]《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編2·隋唐五代繪畫》,圖九,第18-23頁。
[15]《新疆阿斯塔那三座唐墓出土珍貴絹畫及文書等文物》。
[16]《唐代西州墓中的絹畫》。
[17]穆舜英主編《中國新疆古代藝術》,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1994年,圖210,第86頁;中國歷史博物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局編《天山古道東西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208-211、228-233頁。
[18]《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編2·隋唐五代繪畫》,圖九,第18-23頁。
[19]《中國繪畫全集》第1卷《戰國-唐》,圖五九至六五,“圖版說明”第9-11頁。
[20]參見[宋]佚名撰《宣和畫譜》卷六,于安瀾編《畫史叢書》第二冊,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63年,第61頁。
[21]《唐代西州墓中的絹畫》。
[22]數據采自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局編《絲路瑰寶——新疆館藏文物精品圖錄》,新疆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7頁。
[23]參見《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編2·隋唐五代繪畫》,圖九,第18頁。
[24]參見《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編2·隋唐五代繪畫》,圖九,第19頁。
[25]參見《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編2·隋唐五代繪畫》,圖九,第21頁。
[26]參見《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編2·隋唐五代繪畫》,圖九,第22-23頁。
[27]參見《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編2·隋唐五代繪畫》,圖九,第23頁。
[28]《歷代名畫記》卷九《唐朝·上》,第184頁;卷十《唐朝·下》,第204-205頁。另參見《宣和畫譜》卷六,第61頁。
[29]《宣和畫譜》卷六,第65頁。
[30]侯燦、吳美琳著《吐魯番出土磚志集注》下冊,成都:巴蜀書社,2002年,第628-629頁。
[31] 數據取自《中國繪畫全集》第1卷《戰國-唐》,“圖版說明”第11頁。
[32]《唐代西州墓中的絹畫》。
[33]《唐朝名畫錄》記張萱“嘗畫貴公子鞍馬屏障、宮苑士女,名冠于時”,韋無忝“善鞍馬,鶻象、鷹圖、雜獸皆妙”(引自《歷代名畫記》卷九,第184-186頁),即人物鞍馬題材的屏風畫,此即當時的稱法。開元年間的名家陳閎有《人馬圖》。這種人物鞍馬畫,與曹霸、韓干等所擅的鞍馬畫有所不同。
[34]《中國繪畫全集》第1卷《戰國-唐》,第8頁。
[35]《西域考古図譜》,圖52。
[36]《歷代名畫記》卷九,第186頁。
[37] Stein,Sir Aurel,Innermost Asia,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Kan-su and Eastern īrān,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1928,Vol.II,pp.693-694;Vol.III,Pl.CV,CVI.
[38]這一數據顯然是就殘存的畫面計算的。
[39]“Remains of a T’ang Painting,Discovered by Sir Aurel Stein,Described by Laurence Binyon”,Burlington Magazine,June 1925,pp.266-275.
[40]《宣和畫譜》卷五《人物一》,《按樂仕女圖》《樓觀仕女圖》等畫作。
[41] 參見:《西域考古図譜》,圖51;《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第15卷《中央アジア》,第272頁,圖294-295;《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編2·隋唐五代繪畫》,圖十二、十三,“圖版說明”第8頁。
[42]《歷代名畫記》卷十,第197頁。
[43]《中國繪畫全集》第1卷《戰國-唐》,圖七十,“圖版說明”第11頁。
[44]《歷代名畫記》卷十,第204頁。
[45]關于這些壁畫墓,參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吐魯番縣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發掘簡報》,《文物》1973年第10期;《吐魯番阿斯塔那第十次發掘簡報(1972~1973年)》,等。
(本文圖片由劉文鎖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