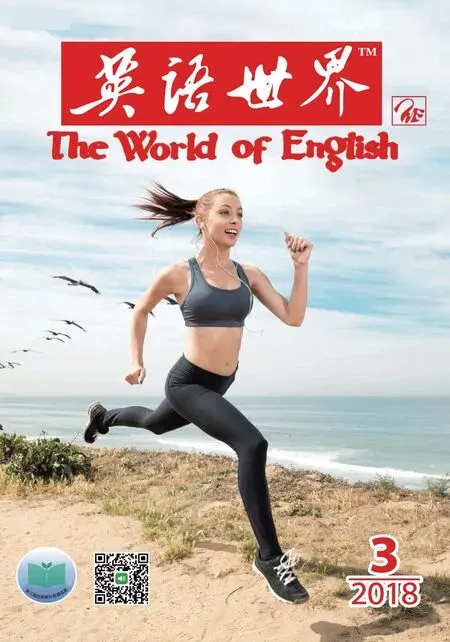披著蝶衣的蜜蜂1
文/金圣華
按照一般看法,蝴蝶是悠閑的,蜜蜂是辛勞的。蝴蝶身披彩衣,栩栩穿花,整天在姹紫嫣紅、秀蘭芳菊中尋艷探香,日子過得好不逍遙!蜜蜂卻天生勞碌,不停在芳菲盛放處來回穿梭,營營役役,為采花釀蜜而殷勤不息。
根據傳統觀念,男主外,女主內,男性為了養家糊口,在工作上力爭上游,有所表現,是理所當然的;女性卻完全不同,在事業上哪怕全心全意,努力拼搏,總有人會不以為然,不是質疑你的能力,就是譏諷你的動機,冷不防來一句:“這么拼命干嘛?還不是賺錢買花戴!”
女性在職場上悉心投入,鞠躬盡瘁之余,最安全的做法是打扮中性,面目模糊,讓人一時不記得你的性別,置身西裝革履群中毫不顯眼;萬一儀容出眾,個性鮮明,這就不免會招來異樣的眼光,認為你不夠水平,有失專業,并惹上“花蝴蝶”之譏了!
這種根深蒂固的偏見,在今時今日看來,固然不合潮流,但也并未銷聲匿跡。回憶往昔,個人學術生涯中,就曾經親歷其境,深諳其味。所幸在人生道路上,曾遇見不少優雅端莊的先賢,她們成就卓越,永不言休,活得雍容而有尊嚴。有她們在遠方遙遙領路,盡管途險道窄,吾輩后進當可勇往直前而無懼了。
1982年冬,一個寒風凜冽的午后,跟隨旅法學者沈志明一起去拜訪波伏瓦。波伏瓦是法國最享盛譽的作家及存在主義大師,在法國人心目中,地位無與倫比。波伏瓦的府邸坐落在巴黎南端,聽說是以《達官貴人》一書獲得龔古爾文學獎后購置的。抵達后,主人早已打扮停當,在府中候客了。記得那是一所特別的房子,樓高兩層,中間打通,似乎工作室、休憩處都在一塊,不分間隔,四壁都是書架,放滿了林林總總的書籍刊物和各式玩偶(法語為poupee,發音極近“寶貝”),漫溢出一片熏人的書香與難掩的童真。室內還陳設了許多薩特的相片,小幾上插滿黃色的鮮花。那天她身穿白衣藍褲,外罩一件毛衣,色彩由下至上,從深藍漸變為淺白,頭上則系了一條白色的緞帶,將頭發攏起,看來舉止優雅,氣度從容。我們談起了她的種種著作、日常生活,以及中法文化的異同。談話間波伏瓦得知她的名著《第二性》已經有了中文譯本(當時指的應是臺灣晨鐘的版本)時,笑得特別開懷。整個過程,知性與感性交融,并沒有因為主人女性的溫柔與敏銳,而沖淡了濃濃的文化氣息和學術氛圍。那年波伏瓦七十四,薩特逝世兩年,堅強的她已經從傷痛的低谷中站立起來。
1985年初,香港翻譯學會執行委員一行六人到內地訪問交流,在拜會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時,首次會晤了楊絳先生。記得那天的會上,座位恰好安排在楊先生旁邊,因此,更增加了不少交談請益的機會。初晤楊絳,印象中的她氣韻嫻雅,行止婉約,穿了一身剪裁得宜的深色旗袍,說起話來輕聲細語,一派溫柔。當時完全看不出眼前嬌弱的身影,數年前曾經歷過“文革”,劫后余生,寫出具備“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格調的不朽杰作《干校六記》。那一年,楊絳七十四歲。2000年后,曾經四訪三里河,在那儉樸清雅而蒔花不斷的小樓上,親眼見證年逾九十的老人,如何在痛失伴侶的哀傷里重新振作,自強不息。原來,羸弱的外貌下,竟然藏有鋼鐵一般的意志,她才是災難過后,收拾一切、打掃現場的強者!
因此,這世界上只有勤懈之分,而無男女之別。
本書以“披著蝶衣的蜜蜂”為名,共分五輯:第一輯“成長”,概述個人從小到大接受教育的過程,并論及緣結文字、情系母語的起因;第二輯“親情”,講述與父母兄長、夫婿子女的情分,并省視在雙親離世和伴侶長逝后,如何面對孤寂,重新出發;第三輯“友誼”,以感恩之心,念及畢生相交相知的友好,如白先勇、林青霞、林文月、傅聰;孺慕敬佩的前輩,如余光中、勞思光、楊憲益、楊絳等,并縷述如何從他們身上學習所長和深受教益;第四輯“文藝活動”,追憶一些曾經參與投入的文學和藝術活動,在為文學奔波、為翻譯吶喊的前提下,悉心籌劃、努力推動的過程中,常因旁觀者漫不經心一句“船到橋頭自然直”的評語,不乏錘木敲釘、徒手造船的艱辛,以及赤手空拳、獨闖天下的困頓;第五輯“著作序言”,列出歷來一些個人創作和翻譯作品的序文和前言,原本還加添每本書的選段,讓讀者一窺作者于多少個無眠夜晚在煢煢孤燈下筆耕的點滴,惜因篇幅所限,最后不得不一一刪去。
本書承蒙柳鳴九先生推介,深圳海天書局出版,特此致謝。
謹以此書,獻給世上所有追求美善,而又內外皆及、表里兼顧的女性朋友,只要勤勉不懈、自淬自礪,不管身在灼灼桃林,還是幽幽小院,你們都是披著蝶衣的蜜蜂,活得辛勤而燦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