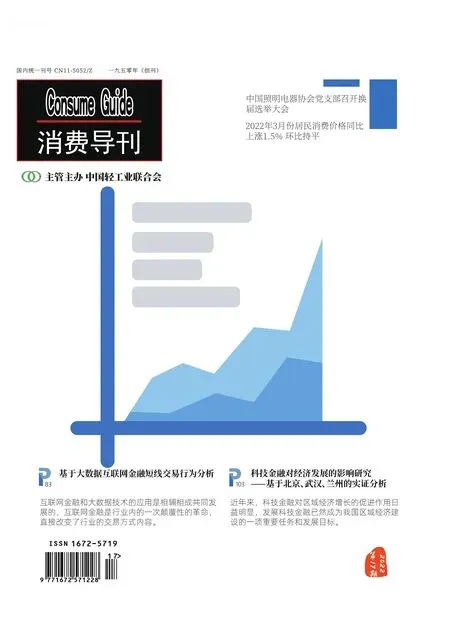探析《論語》中的“時中”思想
王雪菲
摘要:“時中”思想是孔子思想中的一大特色,《論語》對其有著深入闡釋。“時”、“中”在用法以及含義上有些許的差別,但究其根本,從它們所要求人們達到的境界來看,兩者的目的是一致的。相時而動,取中而行。“時中”的根本在于“義”,以“義”支撐起的“時中”,才是孔子的本意。“時中”絕非是與“內圣外王”對立的思想,而恰恰是相輔相成,有著統一的歸宿。
關鍵詞:《論語》 時中 義
“時中”思想是孔子思想中的一大特色,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底蘊之一。孔子認識到堯舜“執中”“使民以時”的重要性,開始將“時”與“中”聯系起來,加以發展。隨后歷代儒學家不斷拓寬“時中”思想的內涵,逐漸形成了時中思想的理論體系。
一、歷代學者對“時中”思想的研究
早在民國時期,梁啟超先生就曾在《時中的孔子》一文中分析孔子對于“時中”的態度,以及孔子思想中蘊含的“中”和“中庸主義”。2003年,董根洪與李智分別在《孔子研究》上發表論文《儒家真精神——“時中”》、《析“時中”在孔子生存境域中的魅力》,論述了孔子“時中”思想的形成及其精神意義。此后更有李偉哲、楊世宏、陳科華等諸多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此進行研究。學界對“時中”思想研究經久不衰,尤其是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體系提出后,“時中”思想作為符合唯物辯證理論、追求積極進取精神的思想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
孔子一生“述而不作”,《論語》作為孔子及其弟子以及再傳弟子集中編纂的關于孔子及弟子言行的典籍,可以說是對孔子思想最直接的記錄。所以本文將從《論語》入手,對其中所表現出的“時中”思想進行分析,從思想發生的源頭探究“時中”思想的相關問題。
二、孔子思想中的“時”與“中”
“時”從字面上講就是時間。《說文》云:“時,四時也”,“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古人認為寒暑交替、草木生息隨四時而自然發生。在《論語·陽貨》篇中,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當順應“時”的變化,時行則行,時止而止。孔子還進一步引申,將“時”定義為不同情境下所做出的不同行為。如《論語·憲問》篇中孔子通過評論公叔文子的不言、不笑、不取,并非“呆若木雞”,而是“時然后言”、“樂然后笑”、“義然后取”,來說明做事并不是教條成規,而要根據實際情況判斷行為,隨時而動,合時因而合宜。
“中”在《論語》一書中出現的次數不多,觀其出現的語境可知其除了表層的“中間,一半”(《論語·雍也》篇“中道而廢”)外,主要是“恰到好處,沒有過猶不及的地方”的含義。如《論語·子路》篇“不得中行而與之”,《論語·堯日》篇“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可見“中”所包含的不僅是事物本身所處的自然狀態,還是人們在認識事物過程中持有的理性態度,同時也是君子在實施行動時所采取的合理方式。由此觀之,“時”、“中”雖然在用法以及含義上有些許的差別,但究其根本,從它們所要求人們達到的境界來看,兩者的目的是一致的。
三、
“時中”的根本在于“義”
《論語·鄉黨》篇中記載著一段孔子對雌雉的描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錢穆先生認為此處的“時”應該是“時宜”的意思。孔子稱贊雌雉懂得“時宜”,遇到對它們沒有威脅的人就飛落下來。但若順此含義繼續翻譯下面子路與雌雉的狀況似有不妥:既然雌雉懂“時”,那么子路投喂的食物,雌雉為何又嗅而不食呢?我認為明末王夫之對此篇的理解很獨到。他認為雌雉“知常而不知變”,“人之拱己而始三嗅而作,何其鈍也!”雌雉是愚鈍的。它們過于警惕,沒有享用到子路給它們的美食,仍舊是不懂“時中”之理。孔子正是借此表明他對時中的理性態度,教我們明白人要知時知中。
正如郭店楚簡《唐虞之道》中所說“圣以遇命,人以逢時”。“時中”重要,如何才能做到呢?按梁啟超先生所講,“《春秋》的三世,也是把時的關系看得最重。因為孔子所建設的是流動哲學,那基礎是擺在社會的動相上頭,自然是移步換形,刻刻不同”。在《論語》中,孔子給后人展示了一個圣人的完美形象,而從“子見南子”等事件看,即使是圣人也會有“不中”之時。孔子說“吾十五而志于學……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即使早已認識到“時中”的重要性,孔子修煉一生,竟到七十歲才敢說不逾矩而至“時中”。可見,“時中”說易行難。
“時中”之所以難以達到,是因為“時中”要求人們隨具體情況而判斷自己的行為,更是因為在此之上還有“義”的核心不可動搖。一個人僅僅做到隨遇而安卻沒有原則,就像草兒隨風擺動是極其可憐的。人沒有“義”作為衡量的標準,僅僅取“中”,就會無是無非,沒有底線,失去做人的根本原則。這樣的“中”是沒有意義的,反而比知“義”而不知“時中”危險得多。上文的雌雉起碼可以保證自身的安全,但無“義”之人不但將自己的人生價值拋棄,還會威脅到他人禍害國家。孔子所說的“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是在“義”的基礎上進行必要的權衡,根據實際情況改變行事方式方法。
以“義”支撐起的“時中”,才是孔子的本意。正如《論語·子罕》篇中孔子所論述的“毋意,毋必,毋固,無我”,就是一種動態的“義”,是一種有根本的“時中”。莊子講求“與時消息”,從本質上是一種消極避世的心態,而孔子的“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與之比”,是在“義”的標桿下相時而動,取中而行的積極入世的態度。所以“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日:‘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心中始終懷著自己的宗國,行也遲遲啊!
中華民族數千年來的“時中”之中深藏著“大義”,為歷代先賢所孜孜以求也正在于此。“時中”絕非是與“內圣外王”對立的思想,而恰恰是相輔相成,有著統一的歸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