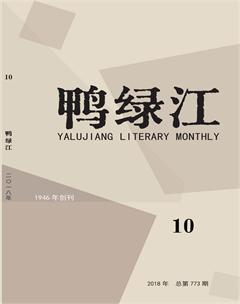影子獨自行走
張大威
我們坐在此處,卻總是疑心一個貌似我們的影子,于彼處正在別人的話語、目光、尺度中徘徊、呼吸、生長。我們被他者所言說,所創造,所臆想,所涂抹。我們的影子時而彎曲,時而挺拔,時而紅臉,時而黑臉,時而端正,時而歪斜,時而正直,時而小丑……在話語、目光、尺度的異鄉里,影子獨自行走,他顯得曖昧不清,似是而非,被層層誤解的累贅所包裹。
我們的影子,那個活在異鄉的影像,并非完全由我們的思維,我們的歷史,我們的品性,甚至是我們的相貌與行為決定的。按說,人與他的影子是互相依存的,有什么樣的主體,就應該映現什么影子。山峰會映現出山峰的影子,駱駝會映現出駱駝的影子。哪能如此確定,一張弓卻映現出了蛇的影子,幾根手指的參差扭動,卻映現出雞、狗、鳳凰等不同動物的影子。一個人的頭部,在燭光下會虛脹許多倍,看著像個小山丘,而在陽光下,比真正的頭部也大不了多少。
獨自行走的影子,閃爍不定的影子,脫離主體后便產生了變異,這事讓人吃驚與不解。在一片百合花盛開的土地上,我們會采回潔白的百合,在一片不毛之地上,我們除了沙礫什么也帶不回來。影子發生變異后,在不毛之地上我們可以采回朵朵潔白的百合,在百合花盛開的地方,我們卻一無所獲。看這世界上熙熙攘攘的人,熙熙攘攘的車,熙熙攘攘的臉孔,熙熙攘攘的大嘴巴,熙熙攘攘的腳指頭,在風片與光影中不停地晃漾,可晃漾的到底是他們的實體,還是他們的影子呢?我們評價一個歷史事件,一個歷史人物,一座倒塌的宮殿,一座蕪沒的城池,一樁消逝的霸業,一位著名的作家,一部經典的作品,他們的身后往往有著語言之山般的中間物(中間物中會摻雜著許多偏見,許多銹垢),我們在別人的語言之山遮擋下,評價的是他們的影子,還是他們的主體呢?
年代越久遠,影子越濃重,時光的流逝,對文本的誤讀,對人物的誤解,對事件的誤判,第一個影子還是薄脆的,第二個影子還是些微透明的,待到第三個影子疊加上來,事件、人物、作品的本來的形體,便一點一點被虛化,被歪曲,變形起步了,影子的五官漸漸成形,體格漸漸壯大,影子匪夷所思地成為了一個飽滿的生命個體,開始行走江湖。如此,影子壓倒了主體,影子成了主體。不是神允諾影子成為主體,是他者的話語、目光與尺度完成了這件事。更為麻煩的是人們會根據影子來評價人與事件的價值,而這種評價帶來的荒誕與謬誤,會使主體風化,剝落,甚至坍塌。
影子,往往就是那個被說壞的人,與被說壞的事。
魯迅先生身上的疊影重重,是政治說“壞”了他,使他成了刻薄的象征,峻急的象征,謾罵的象征,寒冷的象征,無情的象征。不是誰都能懷著一顆純凈的心靈,樸素的不帶雜質的眼睛,擺脫影子的影響,去閱讀原著,自己踩出一條清靜明朗的小徑,不踏入妄談者設下的未必不帶歹意的裂痕里,去咀嚼大師們思想之樹上的果實,自己品出它的滋味。望風捕影,捕風捉影,一犬吠形,百犬吠聲,跟在影子后面晃晃悠悠,人云亦云,既防止了被真話的光芒——刀鋒上的光芒所切割,又省去了獨立思考時所耗費的腦力精髓與所灑下的近于笨伯的汗水,別人種下一棵什么苗,他伸手隨便摸一下,就說有了收獲。于是,淺薄便以高深的假面出現了,向主體噴射出他抄襲來的惡意。我認識一位也算得上是個讀書的人,他說:“我最厭惡魯迅,文壇與政壇上的許多不潔都從魯迅始。”文壇與政壇——我離此二壇都相當遙遠,不知那里的“潔”與“不潔”為何物,所以沒有發言權。但魯迅我多少還是讀過的,我說:“你對魯迅是全部厭惡嗎?魯迅的《野草》《吶喊》《彷徨》《朝花夕拾》,今日仍然還可稱文壇執牛耳者。‘有人曾問羅伯·格里耶什么是新小說,他回答說,新小說已經很老了,就是卡夫卡。在中國,新小說也已經很老了,那就是魯迅。”他用睥睨的眼光瞟了我一下說:“我從來不讀魯迅。”從來不讀魯迅的人,有什么資格厭惡魯迅呢?他一定是從哪兒見過魯迅歪歪斜斜的影子,聽過別人對魯迅的指責與詈罵。別人吠形,他便吠聲了。魯迅不是不能被“厭惡”,“厭惡權”也是人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誰說我們人活著只有喜歡權,沒有厭惡權了?我們都會厭惡一些人,也會被他人所厭惡。對峙,也是一種生動與張力,完全的和諧在臆想的烏有之鄉桃花源里。但必須是了解才能產生拒斥和喜愛。影子只是光暈,并不是實體,用光暈來界定一個人,它大概會像一個哈哈鏡,使人變異得自己都無法辨認。
人,誰也無法阻擋自己生活在此處,影子在彼處獨自行走。每一次,你在他人的話語中出現,都會伴隨著你自己真正面貌不同程度的歪斜。我們當然都不會贊同偷聽,但因機緣湊巧,你恰好在他人談論你的時候偷聽到了,你的感覺十有八九如墜夢寐。他人所編織的密密實實的語言網所網住的那個人,根本不可能是你,他們可能在談論一條魚,談論的也不是你。當他們口中吐出你的名字時,你會目瞪口呆,你以為剛才只是聽了一通與已無關的“小廣播”,卻不料那個“小廣播”中的主人公就是你呀。使你甚感悲涼的是,有一天,影子會將你這樣定格,“當你死去的時候,這些錯誤的評價卻留了下來”(艾麗絲·門羅)。
當然,對于我們平凡的人,所謂死后的評價會稀薄得如珠穆朗瑪峰上的空氣,青草之上,我們默默無聞,青草之下,我們寂靜無聲。我們的存在,經常以缺失的面貌出現。評價,有評價嗎?如果有,也是那些與你相識的平凡人,在茶余飯后,偶爾想起了某件往事,你還在那件往事里行走,因而會有幾句閑話掠過你的臉龐,后來認識你的那些平凡人,或因記憶衰敗,或因記憶疲憊,你活動在他者記憶中的影子,也就漸漸淡去。再后來,那些人也已離世,有一天,你與他們在青草之下重聚,喝完忘川之水后,彼此以無言的姿態在冥界飄蕩,聽秋蟲唧唧或云雀啁啾,而塵世、家山與生之軌跡,早已成了迷霧一團。
雖然如此,我們在世的時候,還會為自己的影子歪歪斜斜而不爽,無論它向哪個方面傾斜——膨大,抽縮,拔高,矮化,我們都被篡改了,歪曲了,模糊了。
婆婆去世時,我與愛人回老家辦理喪事,見到了許多相熟的人,守靈的時候,長夜漫漫,親人悼念的淚水不干,卻不能要求別的人——即便是那些相熟的人——也流下同樣的淚水,隨著瓜子皮、花生殼的到處飛濺,大家的話語之流是那么活躍。他們首先談起了我中學時的一位同學,現在是既富且貴了。大家說他在中學時功課十分優秀,特別是數學和化學,更是優中之優,全班同學都要抄襲他的作業。一次,他生病了,住院一個星期,全班同學就一個星期沒能完成這兩門功課的作業。我像熟悉教室里那把平淡無奇的尖嘴灑水壺一樣熟悉這位同學,我的記憶力還沒有敗壞到一片荒蕪,那位同學在中學時,數學與化學最劣,考試時從來不及格。到底是從什么主體上衍生出來這么個又大又胖又虛的影子呢?全班同學都抄襲他的作業,可是他做過作業嗎?在人們語言的坦途上,這個影子蹦跶得是多么志得意滿啊!
更令我驚異的事情還在后頭,他們替我編纂了一段歷史。退一萬步說,我對那位同學的記憶有空洞,我還不了解我自己的履歷嗎?我的腳印是留在了泥濘的鄉間小路上,還是留在了寸草不生的城市柏油馬路上,我清明如水。不,我一片混沌。面對主體,我的影子竟然脫離我,在我眼前不到半米遠的地方獨自行走。言說者為我編纂的履歷是這樣的:我是一位工農兵學員,上的是中國醫科大學,畢業后自愿回鄉做赤腳醫生,后來又回到中國醫大附屬第一醫院做內科醫生。他們在說誰?難道在某個細雨蒙蒙的秋夜,我的影子脫離了我,在另一維世界里完成了這一系列詭異的行動?難道我的影子冒充我在人間另有生活?難道真像特朗斯特羅姆所說的“我們的生活有一條姐妹船,航行在一條截然不同的航道上”?可我的真實履歷與這些人語言中的履歷毫不沾邊。
我承認,那一刻我十分緊張,甚至緊張到恐懼。我被我的影子偷走了,調包了,吞沒了。影子成了我,我成了“無”。我并不是說我影子的履歷有什么污點,可它不屬于我。我張大嘴巴,大聲地抗議、申述,指出他們的謬誤,袒露我的真實。他們起先嘲笑我,繼而說我虛偽,怕他們去城里看病求著我。最后則不再理睬我,更別說理解我,聽我厘清我的履歷了。語言之流業已流向了別處。他們將繼續與我的影子交談,握手,共處,指責我,批評我,蔑視我。我在一個非我的灘涂上飄浮著。面對著一個從語言中生殖出來的我的虛幻幽暗的影子,我竟然無計可施。
我滅不掉我的影子,你也一樣。即使我們自己滅掉了,影子也會留存一段時間。人的影子總比本人多活些日子。現在令我沮喪的是我將以面目全非的姿勢繼續行走在某些鄉人的目光與記憶中。令我更為沮喪的是有一天,影子成了主體,我自身卻成了影子,而我也很可能懷疑自己就是個影子,而影子才是主體,角色發生致命反轉。這絕非危言聳聽,雖然這的確使人眩暈和不解。自身在黑暗中踉蹌摸索,影子在陽光下自在滑行。
奧克塔維奧·帕斯曾驚異地與自己的影子相遇。“一到家就在開門的時刻,我看見自己出來了。”這個“自己”不是從語言中,不是從幻覺中,而是從三維世界切切實實地走出來了,且與他的主體迎面相撞。此時,帕斯疑惑惶恐,如果有一天你面對自己的影子,而影子又在你面前高視闊步,你會如何?帕斯在疑慮中跟隨影子進了一家酒吧,他們站在柜臺邊喝起酒來。帕斯認為有必要申明自己為帕斯的正版“版權”,因此他長時間目不轉睛地盯著影子看,并且說:“相似不能成其為借口。因為不是相似而是取代問題。”影子卻說:“先生,請您原諒,可我想我不認識您。”影子虛偽地說他不認識主體,他的否認多么堅硬,他的底氣從何而來?彼此語言上的摩擦漸漸飛濺起慍怒的火花。一位酒吧的老主顧,以前經常和帕斯站在一起喝酒的人,出來為影子作證,聲稱“我認識這位先生”。他真的認識這位先生嗎?他的記憶對象是帕斯,不是身邊的這個影子,可此時他卻為影子作證。(我們在很多時候,是否也在為一表面輪廓清晰,實則一捏便是一地碎片的影子作證呢?)影子本身為一團光暈,他者的謬證又使影子的光暈增厚了一層。影子更加自信自身存在的正當性。帕斯被影子擠壓得越來越邊緣化了。“我雙眼幾乎充滿了淚水,抓住他的衣領叫道:‘你真的不認識我嗎,你不知道我是誰?”如此強勁的提問是一種挑釁,影子與酒吧的所有顧客都憤怒了,影子——民心所向的影子向帕斯高喊:“我要向諸位說明情況,這位先生在欺騙你們,這位先生是個騙子……”
結果,帕斯被影子打了個滿臉花,眾人幫助影子把帕斯舉到空中,并扔到了河溝里。他們還大叫:“他要是再回來,咱們就叫警察。”影子在眾目睽睽中取得了完整的生存正當性,就像鼻子在臉上取得了完整的生存正當性一樣。
狼狽不堪的帕斯衣服破了,嘴唇腫脹,舌頭發干,渾身疼痛。穹頂之下,萬物哪里是清晰可辨,丁是丁,卯是卯,方方正正,無一絲繚亂,無一點錯榫。如此,事情變得十分纏繞,十分迷茫,在酒吧里被影子和老熟人雙重否定后,帕斯帶著滿身的傷痛,趔趔趄趄地往家里走去,就在回家的路上,一股不祥的思緒黑暗潮水般向他襲來,使他至今難以入睡:“如果不是他,而是我……?”(引自《相遇》,奧克塔維奧·帕斯)
帕斯自己陷入了恍惚與恐慌中,他曾堅定地否定影子,推擋影子,質疑影子,他現在開始質疑自己,推擋自己,否定自己。你能準確無誤地辨認出已經走出家門,和即將走進家門的這兩位,哪一位是真正的奧克塔維奧·帕斯,哪一位是他的影子嗎?
如果有一天當你和自己的影子撞個滿懷時,你真的有辦法自證影子是影子,你是你嗎?
【責任編輯】 寧珍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