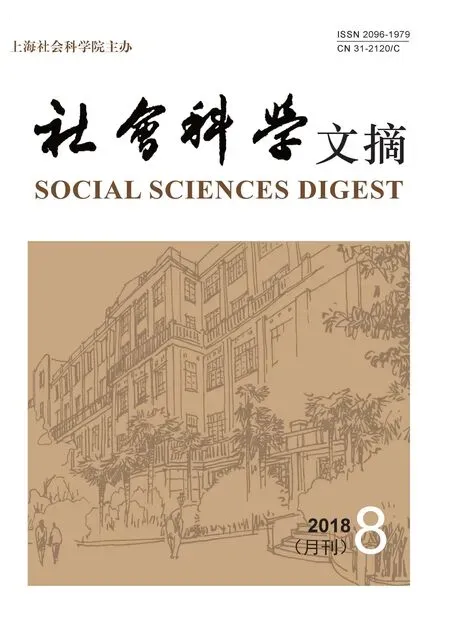近四十年來大陸宋明理學研究的幾條線索
改革開放以來,宋明理學研究以10年為一個階段,四個階段各有其研究的重點。第一階段,理學研究關注的重點是氣學,并初步開展以地域為主體的關學、浙學、閩學和洛學等理學學派的研究。第二階段理學人物的研究得到大大推進,研究更加深入到理學思想內部,社會、政治和經濟等外在因素與理學的交織分析淡出。第三階段,大陸宋明理學研究與港臺新儒學、東亞儒學乃至西方哲學的互動頻繁,宋明理學的思想史研究成為這一時期研究的熱點之一。第四階段,學界反思現代新儒家和西學對宋明理學研究的影響,經學與理學的交叉研究興盛。此外,理學學派研究得到更細致的延伸,與地域傳統學術相結合,徽學、關學、浙學、北學、黔學、閩學、洛學等研究都有豐富的成果呈現。這四個階段前后相續,存在著內在發展的線索。本文認為,貫穿于4個10年之中有幾條線索,有些可能會持續影響到未來理學的研究。
“反理學”研究
40年的理學研究中同時伴隨著一條在內部或者外部與理學對立的研究線索,即反理學研究的線索,這條線索在不同階段有著不同的表現方式。
在理學內部,最主要的反對者是氣學一派。20世紀80年代初期,學界對于宋明理學的評價逐漸由之前的全盤否定到有所揚棄,對理學家的肯定和宣揚正是從理學中氣論一派開始的。從唯物主義的立場看,氣學一派可以對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的客觀唯心主義和主觀唯心主義學說有所對治。主張氣論的理學家因而成為研究的熱點人物。理學之中的氣學學派因而很悖論地作為理學之中義理之學的對立者,保護了理學的整體地位。
20世紀80年代中期,大陸學界援引朝鮮儒學學派的“實學”一詞,批判空談心性的朱子學,提倡對生活有益的經世致用的新學風。顧炎武、黃宗羲、顏元等明清學者經世致用的思想作為實學得到表彰。陳鼓應、辛冠潔和葛榮晉等認為實學思潮從對整個宋明理學的批判中產生,在當時受到不少質疑。后來“實學”提倡者修正了原有的提法,肯定實學對理學有繼承有排斥,在理學家朱子、象山和陽明等的思想中都有體現,亦是對理學的一種和解。“實學”研究在此后20余年仍發揮著影響。然而,實學強調了理學之有,所謂實理論、實性論、實功論和實踐論,而否定其超越性的一面,必然會落入功利主義。
20世紀以來,從早期啟蒙的視域看待明清之際的思想,認為明清之際是傳統文化向現代轉型的發端和結合點,同樣可以梳理出一條明中期至清代的反理學線索。明清之際思想家的思想具有現代性的某些元素和特質,可以很好地結合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和實踐論,呼應西方啟蒙思想家的思想,被視為中國現代性的開端。啟蒙學說之間雖各有分歧,但總體上,啟蒙學說對明清之際思想與宋明理學關系的看法還是斷裂多于連續。當我們現在將明清之際思想納入理學延續的脈絡下考察時,“早期啟蒙”可以被視為明清之際理學研究的獨特視角和方法,也可以被看作是理學自身內部調整和反省的一個角度。
如果說,20世紀八九十年代關于氣學、實學和啟蒙學說受到了馬克思主義學說、東亞儒學和西方哲學的啟示,那么,2000年以后學界乃著眼理學內部的氣學問題,確實源于理學自身形而下的面向,是理學研究主體意識的體現。通過反理學的視角研究理學家,其本質上與理學內部警惕空疏虛寂以及糾正形而上脫離形而下、體用相分等弊病的目標一致。但如果因此忽略理學對于堅持德性理想和倫理生活實踐的意義,乃至蘊于其中的人性天然的自尊、平等和主體性發揮等價值,則會因噎廢食。
西學影響與中西對話
理學研究中的中西對話主要有兩種形式:一種是直接比較理學家和西方哲學家的思想系統或者具體觀點;一種是在理學研究中援引、融合西方哲學思潮或者思想家的觀點。前一種情況中,隨著大陸學者對中西方思想的深入研究和中國哲學主體意識和文化自信的增強,雙方對話越來越平等,對于理學人物和思想的評價也有所提高。后一種情況涉及理學研究中對西方哲學的自覺吸收和運用。
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學概念與問題帶入宋明理學研究的情況頗為普遍。從概念上說,理、氣、心一元論的探究,理性和意志問題的提出,宇宙論、人生論、認識論和辯證法的框架,先驗論和唯理論的定位等在大陸比較盛行,都屬于此類。隨著宋明理學研究的發展和深入,這些概念和問題意識被帶入理學,西學與理學形同自然一體,一轉而成為理學自身的問題,西方哲學深入宋明理學研究的肌膚與骨骼之中,令人渾然不覺。40年宋明理學研究脈絡中,西方哲學概念與框架的影響決不可小視。如果說反理學研究對于理學研究的區分屬于外部路徑, 那么西方哲學的范疇、系統、視角、方法乃至話語之于宋明理學的研究就是出乎其外、入乎其內的。
20世紀90年代以來,語言哲學、存在主義、解釋學、現象學等在宋明理學研究中都有運用,詮釋學的影響尤大。然而,一方面,一些成果只是再次成為西方詮釋學在中國文獻中的運用,另一方面,零星的解釋原則無法構成可以被稱為“中國詮釋學”的體系。對于理學而言,真正的損失在于雖有大量成果的產生卻沒有推動或者觸及理學的內在問題,相反,因為誤讀理學,經典注釋本身有時被視為主觀任意解釋的結果。研究者往往強調對經典語義的釋義,或將解釋結果的差異歸結為客觀的思想史脈絡和個人的主觀經歷經驗,違背了對經典涵義本身的理解而難以尊重經典意義的客觀性;將之推到歷史,則取消了歷史的客觀性而走向相對主義,將之推到哲學,則糾纏于經典的外部世界,消解或忽視了經典呈現的價值與意義。詮釋學在實際研究中意義大大被泛化,其中問題頗令人擔憂。
近年來,現象學與理學的研究頗值得關注。有趣的是,關于現象學與理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陽明心學的研究上。大致可分為從現象學的視角研究心學和進行陽明心學與現象學的比較兩種路徑。前者延續了瑞士現象學家耿寧所運用的方法,后者則是傳統的中西比較方法。基于現象學的描述運用于基于實踐和修養的理學工夫論,能否避免肢解,這確實是一個問題。中西真正意義上的對話和交融,仍在探索之中。
哲學史與思想史路徑的分野與融合
1949年以后,中國哲學史研究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是關于中國哲學史的研究對象和范圍的問題。周繼旨認為,如果哲學史內容過于泛化,則不免混同一般思想史,而如果一概排除了不屬于哲學范疇的內容,則純化以后的哲學史只剩下唯物論和唯心論,哲學家思想體系的個性被埋沒,整個中國哲學的特點和規律因而也變得模糊不清。蕭萐父先生進一步談到哲學史研究中的純化和泛化,他提出要凈化哲學概念,把一些倫理、道德、宗教、政法等非哲學思想資料篩選出去,使哲學史純化為哲學認識史。同時,他也主張哲學史研究可以泛化為哲學文化史,這樣更能充分反映人的智慧創造和不斷自我解放的歷程。他提到,在哲學史的研究中,或由博返約,或由約返博,或純化,或泛化,只有經過這樣的兩端互補和循環往復中的反復加深,才能不斷開拓新的思路。蕭萐父先生的由博返約和由約返博論預先揭示了1978年以來中國哲學史研究在哲學史和思想史之間循環往復的動態發展過程。
1950年代,任繼愈先生認為,“中國哲學史的對象應當是,關于自然知識和社會知識的概括和總結的認識過程在中國發展的歷史”。其《中國哲學發展史》和侯外廬先生的《中國思想通史》等都貫徹了這一總結。這一泛化的哲學史研究的思路一直延續到1978年以后的10年。從1988年開始,中國哲學史研究中的純化趨勢越發明顯,反映在宋明理學領域,是廓清了政治、經濟、社會等繚繞的論說方式。純粹演繹理學家思想系統、觀念、學說和概念成為一種全新的范式,逐漸成為理學研究中的主流,大大推進了理學內在問題的展開和探討。宏觀上關于理學學派的分系問題,微觀上關于理學家個案中的理氣心性等問題都展開了恰如其分的言說,理學研究進入一個新的時代。
與此同時,歷史與邏輯相結合的方法在理學史研究中繼續發揮作用。事實上,思想史在理學研究中的作用和影響從來都沒有間斷過,主要受到內外幾方面的影響和作用。1975年余英時提出“內在理路”說,強調思想史的內在發展;2000年以后,葛兆光的《中國思想史》借鑒法國年鑒學派學說,針對以政治、經濟、文化為主線的精英和經典的思想史寫法,試圖實踐“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的歷史”的寫法。前者實際上源于西學知識論的外部挑戰,后者在宋元章節中并沒有貫徹區隔精英的一般知識的寫法。但二者對于思想史的理解和示范客觀上對學界產生了深遠影響,推動了明清思想史研究的熱潮。宋明時期的士人生活與交往、書院講學、政治活動等方面確實通過思想史的再現得到深入研究,研究成果很多。哲學史的研究也進入了一個純化與泛化多元共存、互相促進的新的發展階段。可以說,近40年的哲學史研究正是在思想史研究范圍的拓展和深化中深入的。然而,我們也不能不考慮到理學因其獨特的生命經驗,其思想的內核和內在問題的推進并非思想史的外緣研究所能完全觸及,理學研究的相對獨立性也應該得到維護。
理學與經學的互動
經學與理學之間的聯系往往表現為歷史上的聯系和思想上的聯系。歷史上的聯系指漢唐經學主導轉向宋明理學發生,和宋明理學主導轉向清代經學復興之間的聯系。學界關于后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前文所說的反理學批評和歷史學、經學的轉向,反理學批評是理學內在的研究路徑,歷史學和經學的轉向則更多涉及思想史的研究。由漢唐經學向宋明理學的轉變,也是學界研究的熱點之一。
經學與理學在思想上的聯系主要體現在宋明理學和經學之中。2000年以前,理學與經學的互動體現在理學研究中,主要是以理學為主導,理學家的思想系統中往往使經學從屬于理學的解釋,經學成為理學的一種經典表達。2000年以后,隨著經學研究的呼聲漸高,理學中的經學研究開出了一個新的發展面向。相比于傳統看法,學界比較傾向于接受理學作為經學史中的一種形態,認為是經學發展的一種必然方向。以經典為主線,將理學視為經學史中的一段歷程,亦是一種新的思考角度。在此視角下,宋明理學與宋明經學共同構成了一種形態,是儒學在宋明時期的新發展。從目前的研究成果看,以易學與理學的關系闡釋最多,春秋學與理學的關系研究最少,面向社會思想史研究的禮學近來也成為理學研究中的熱點,四書學是研究的重中之重。源于經學與理學的視角,宋元明時期,朱熹是詩學、禮學、易學大家,因而也是經學與理學研究的重點人物。其他圍繞理學家的經學,學界已經展開一些初步研究,值得進一步拓展,如蔡沈、金履祥、魏了翁等的書學,宋程頤、邵雍、張栻、朱震、楊簡,明黃道周、胡居仁、馬理等的易學,宋胡安國、魏了翁、呂祖謙,元鄭玉、吳澄等的春秋學等。然而,理學與經學闡發儒學精義有同有異,理學原則和經學原則之間的捍格問題,解釋經典和理學表達之間不一致的問題不斷彰顯,對這些問題的解決亟須經學與理學兩方面的深入研究。
經學與理學的交叉研究之悖論在于,無論是五經還是四書學的研究必然主要集中在文獻整理和思想史的梳理,一旦涉及理學問題的分析,就會回到理學家的思想系統中加以理解,這時經學研究的獨立性就被取消而服從理學的解釋,而所謂的經學研究仍然只是加深理學研究的一個階段或者一項工具而已。或者,在同一理學家的著作中,經學和理學解釋不一致,往往被歸因于理學家思想前后變化,這仍然是思想史過程論的一項解釋;如果按照義理深究,當理學系統服從于經學脈絡,結果要么是理學系統不圓融,要么是經學主導,理學研究獨立性也無從談起。因而,經學與理學的交叉研究意味著必有一方為主導,而理學家的思想研究往往是以理學為主導的,以經學為線索并不利于理學結構本身的呈現。
理學內在研究的進路
以上反理學、中西哲學比較與互釋、思想史和經學的研究路徑對于當前理學研究而言,推動與挑戰并存。經學的深入理解、理學思想產生的環境和外部關聯、西方哲學的觀念和方法以及來自理學內部不同派別的反思與批評,對于理學的研究無疑都有著重要意義。同時,這幾種路徑往往交互作用,互相支持。比如,經學研究的興起涉及反理學思潮的研究,經學與理學的互動則不少是在詮釋學的背景和框架下進行的,思想史的研究借助了西方哲學的方法,經學與思想史的研究存在著交集,等等。然而,以上對于貫穿40年來大陸宋明理學研究的幾條線索,都是外部路徑。所謂外部路徑,是指這些方法沒有充分遵循理學的本來脈絡,沒有揭示理學的根本精神來推進、解決理學的內在問題。如果能夠直指理學的核心,那么反理學的方法、思想史的進路、西學的視角和經學的研究都不是問題。但是,如果方法和進路過于執著于自身的反理學、思想史、西學和經學的目標,那么,它們作為外部路徑則無疑義。
我們不得不正視一點,思想本身的深度和廣度才應該是哲學研究的主要目的和任務。外在的探索和研究都具有它們自身的研究價值或者成為它們自我研究的目的,也有助于更為精確地捕捉到思想發展的線索或者外緣,卻始終不可替代對于理學思想本身的研究和探索。
相反,理學研究中執著于以上外部路徑會構成對宋明理學研究的挑戰。比如,在詮釋學的視野下,哲學問題往往被轉化為思想史的問題而被消解。理學本體論或許可以借助西方哲學加以解說,理學工夫論則在西方哲學中找不到完全的對應,對于知的部分易陷入理學家所忌的口耳之說,知解和語言游戲之中,無法真正進入理學的世界。經學與理學不僅僅只有結合,在研究中,結合的背后經學立場與理學立場主導不同,評價和結論也會隨之不同,也可謂是新的漢宋之爭。反理學對于理學的反思既可以是內部的,也可以是外部的,外部的反思給理學研究帶來的不僅是促進,也可能是誤解。思想史在西風的助力下,更是占據了理學史研究的大半江山,表面上成果豐碩,對于理學問題的探索卻可能只是淺嘗輒止。
近年來,不少著作試圖順沿理學自身的脈絡和體系庖丁解牛,提出和解決理學內在的問題從而避免西方哲學對理學問題的支離和分裂。這些都是宋明理學主體性的自省與自覺的表現。在具體的理學人物、學派思想、理學概念和問題的研究上,近一二十年來的研究在理學人物、學派方面有新的拓展,也有新問題的提出與發現,使得理氣心性和工夫論的諸多問題在理學研究中得到更精微深入的展開和探討。由于知行合一、涵養體貼是理學研究的內在要求,本體論與工夫論的研究結合工夫的踐履和體認,可能是未來理學研究不可回避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