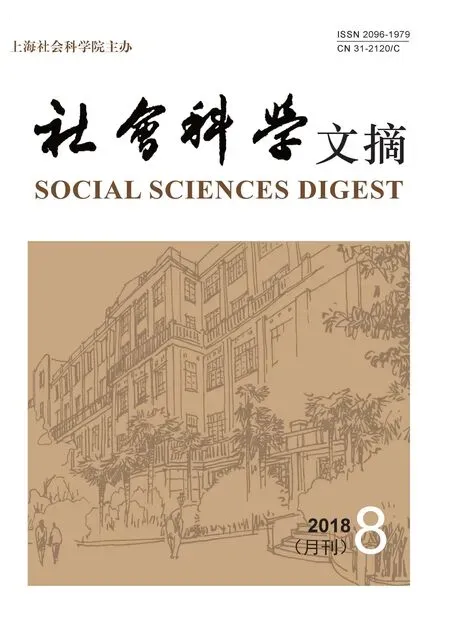“思無邪”作為《詩經(jīng)》學(xué)話語及其意義轉(zhuǎn)換
孔子曾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此后“思無邪”就成了《詩經(jīng)》學(xué)的重要命題。但當(dāng)歷代學(xué)者不斷追求這一命題的本旨,并意欲給出一種合理解釋時,他們可能在立場和認(rèn)知上犯了錯,即忽視了該命題之內(nèi)涵在歷史發(fā)展中的復(fù)雜變化。孔子這樣說當(dāng)然有自己的界定,可戰(zhàn)國中期以前,孔子后學(xué)對“思無邪”之“思”有一個誤解,促成了漢代經(jīng)學(xué)家的新解釋,奠定了人們對這一命題最基本的認(rèn)知;宋代以降,質(zhì)疑漢唐舊說者漸多,以朱熹為代表的學(xué)者為了消除舊解與《詩經(jīng)》學(xué)發(fā)展的緊張對立狀態(tài),再一次完成了對這一《詩經(jīng)》學(xué)話語的意義轉(zhuǎn)換。總之,歷史不斷地層累,而當(dāng)下對這一命題的所有詮釋,幾乎都是不同舊說的余緒。
孔子以“思無邪”概言《詩三百》之本意
《詩三百》各篇若使用重章迭句,處于各章相同功能位置的語匯,其意指常常相同或相近,至少往往可以貫通。《》詩采取重章迭句之表達(dá)方式,其第四章之“無邪”,與前數(shù)章之“無疆”“無期”“無斁”處于相同的功能位置,其意指與前三者一致,即同樣是形容空間之無邊際,便也毫不奇怪。于省吾嘗考證從吾從牙之古字可通,謂《儀禮·聘禮》“賓進(jìn),訝受幾于筵前”,鄭注謂“今文‘訝’為‘梧’”,《山海經(jīng)·海內(nèi)北經(jīng)》之“騶吾”,《史記·滑稽列傳》作“騶牙”,《公羊傳》文公二年(前625)“戰(zhàn)于彭衙”,《釋文》謂“衙,……本或作‘牙’”,等等,均可為證。而“圄”與“圉”古同用。《說文·?部》云:“圉,囹圉,所以拘辠人,從?從囗。一曰:圉,垂也。”段注云:“他書作‘囹圄’者,同音相叚也。”然則,“無邪”即“無圉”,猶言“無邊”,指牧馬之繁多。此說甚是。以上解讀的合理性,回到《》詩原文,可以看得十分清楚。《》詩自身實(shí)可證明“無邪”本指無邊際、無窮盡。
孔子引“思無邪”一語概括《詩三百》,當(dāng)是指三百篇之蘊(yùn)藏既富且廣,無所不包,是就其內(nèi)容而言的。
我們先看看“思無邪”之“思”。上海博物館所藏戰(zhàn)國楚竹書《詩論》,通常也被稱為《孔子詩論》,是現(xiàn)今所知與《論語》孔子論說《詩經(jīng)》關(guān)系最明確的文獻(xiàn)。在考辨孔子以“思無邪”論《詩》時,《詩論》提供給我們的信息是多方面的,首先就涉及孔子對“思”字的理解。傳世《毛詩·周南·漢廣》云:“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乘泭以求濟(jì))思。”《詩論》第四章論曰:“□□□□□,可(得),不(攻)不可能,不亦(智)亙(恒)(乎)?”又曰:“《(漢廣)》之(智),則(智)不可(得)也。”這些評論代表了孔子對《漢廣》的認(rèn)知。而由這些評論,可以斷定孔子并不把該詩中的“思”字理解為實(shí)詞,否則無法解釋他給出的《漢廣》“不可(得),不(攻)不可能”的斷語。實(shí)際上,傳世《中庸》第十六章記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孔子所引“神之格思”諸語,出自《詩經(jīng)·大雅·抑》篇,他的相關(guān)論說,也表明他并未把作為語助詞的“思”理解為實(shí)詞——比如“思念”“思慮”“思考”之“思”。
其次,更重要的是,《詩論》評析50余首作品或其部分文字,幾乎比后世所有舊說都更加契合對象的本旨——即便涉及較為明顯的形而上的發(fā)揮。鑒于這一事實(shí),認(rèn)為孔子予取予求、斷章取義地拿“思無邪”來概括《詩三百》就不太合理。尤其不可忽視的是,《詩論》的核心內(nèi)容可以證明,孔子以“思無邪”概言《詩三百》,乃是指三百篇之蘊(yùn)藏既富且廣、無所不包。《詩論》第一章云:“□□□□□□孔子曰:《訔(詩)》,丌(其)猷(猶)塝門與?戔(殘)民而(逸)之,丌(其)甬(用)心也(將)可(何)女(如)?曰:《邦風(fēng)》氏(是)已。民之又(有)(戚患)也,上下之不和者,丌(其)甬(用)心也(將)可(何)女(如)?曰:□□□□□□氏(是)已。又(有)城(成)工(功)者可(何)女(如)?曰:《訟(頌)》氏(是)已。”“塝門”即廣大之門。孔子是以城門之廣納人物,類比《詩》之蘊(yùn)蓄宏富,故他接下來便說《詩三百》各部分篇什因應(yīng)著政教的種種情態(tài)。《詩論》第十章嘗論《頌》《大雅》《小雅》以及《邦風(fēng)》,這里只看其中論《邦風(fēng)》者,所謂:“《邦風(fēng)》,丌(其)內(nèi)(納)勿(物)也尃(博),(觀)人谷(俗)安(焉),大(驗(yàn))材(在)安(焉)。丌(其)言(文),丌(其)圣(聲)善。”這一論說,幾乎可作孔子以“思無邪”概言《詩三百》的注腳。此語雖只是就《國風(fēng)》而言的,即是說《國風(fēng)》之詩所含之物事至多至廣,可由以觀民俗,可由以驗(yàn)政教,但移之以論《詩三百》之整體,也完全合理。《詩論》第一章謂,殘民而使之逃逸,民之用心由《邦風(fēng)》可知;民有憂患,上下不和,其用心由《小雅》可知;為政者功成德盛,則頌聲起,由《頌》詩可知;同樣的道理可以適用于《大雅》,惜乎相關(guān)論析缺軼。這些與稱《邦風(fēng)》納物博、大驗(yàn)在,同樣可以貫通。這一切,均可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第一次意義置換之啟基:關(guān)于“思無邪”之“思”
在孔子弟子至子思時代,“思無邪”的意義發(fā)生了一次深刻的轉(zhuǎn)換:“思”字實(shí)詞化,即被理解為“思想”“思慮”之“思”,對《》詩“思無疆”“思無期”“思無邪”的接受因此發(fā)生了通盤的變化。
第一次意義置換之完成:關(guān)于“思無邪”
基于“思無邪”之“思”被理解為實(shí)詞(“神思”之“思”),“思無邪”之“邪”差不多同時被理解成了“邪正”之“邪”。毫無疑問,這牽動了對《詩經(jīng)》與《詩經(jīng)》學(xué)兩方面的認(rèn)知。
孔子開啟了《詩三百》經(jīng)典化(即轉(zhuǎn)化為儒家經(jīng)典)的旅程,戰(zhàn)國時期,數(shù)代儒家學(xué)者不斷加以詮釋或再詮釋,《詩》最終被賦予了系統(tǒng)的儒學(xué)價值,成了儒家重要經(jīng)典;而至漢初,這一進(jìn)程又從民間學(xué)術(shù)層面躍升至官學(xué)層面,《詩經(jīng)》被立在學(xué)官,《詩》的經(jīng)典化最終完成。由此,對傳統(tǒng)《詩》學(xué)話語的認(rèn)知、闡釋或者再闡釋,都必然地在這一學(xué)說體系的基礎(chǔ)上進(jìn)行。
總之,包咸、鄭玄以下,絕大多數(shù)學(xué)者將“思”解釋為動詞性的思考或者名詞性的思想,將“邪”解釋為“正邪”之“邪”,將“思無邪”解為詩思之正。其所謂正,自然是基于儒家政教規(guī)范而言的。此時,關(guān)于《詩三百》的所有詮釋都可以落實(shí)“思無邪”的取向,這一取向因此就意味著三百篇或者“詩人”全都是向世間提供儒學(xué)價值的淵藪(并非本然如此,這只是《詩》經(jīng)典化的結(jié)果)。我們幾乎可以依據(jù)這一取向及其嬗變,來區(qū)隔和定義《詩經(jīng)》學(xué)發(fā)展的形態(tài)模式——就是說,這一取向凸顯了漢唐《詩經(jīng)》學(xué)的特質(zhì)。
之所以使用“《詩經(jīng)》學(xué)形態(tài)模式”這一表述,而不偏倚于歷史時段,是因?yàn)槟骋粴v史時段成熟的形態(tài)模式往往不會在后來的歷史時段中消失,會反反復(fù)復(fù)發(fā)揮其影響作用,即使新的形態(tài)模式正在生成甚或已經(jīng)成熟。作為一種形態(tài)模式的“漢唐《詩經(jīng)》學(xué)”就是如此,它至今依然會在某些歷史層面上浮現(xiàn)。比如北宋謝良佐(1050—1103)稱:“君子之于《詩》,非徒誦其言,又將以考其情性;非徒以考其情性,又將以考先王之澤。……思其危難以風(fēng)焉,不過曰‘茍無饑渴’而已(案指《王風(fēng)·君子于役》)。若夫言天下之事,美盛德之形容,固不待言而可知也。其與憂愁思慮之作,孰能優(yōu)游不迫也?孔子所以有取焉。作《詩》者如此,讀《詩》者其可以邪心讀之乎!”略早于朱熹(1130—1200)的學(xué)者張戒嘗云:“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世儒解釋終不了。余嘗觀古今詩人,然后知斯言良有以也。……其正少,其邪多。孔子刪詩,取其思無邪者而已。自建安七子、六朝、有唐及近世諸人,思無邪者,惟陶淵明、杜子美耳,余皆不免落邪思也。”呂祖謙(1137—1181)說得更加簡潔:“仲尼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xué)者亦以無邪之思觀之,閔惜懲創(chuàng)之意,隱然自見于言外矣。”這些論說雖皆出于宋人,卻都呈現(xiàn)著漢唐《詩經(jīng)》學(xué)形態(tài)模式的特質(zhì)。而張戒的說法,再次明確了漢唐《詩》學(xué)形態(tài)模式的邏輯前提,是孔子刪詩或編《詩》。
第二次意義置換以及《詩》學(xué)內(nèi)在沖突之消解
漢唐《詩經(jīng)》學(xué)形態(tài)模式遭遇的嚴(yán)峻挑戰(zhàn),來自對文本自身價值的認(rèn)同。在文本的力量被釋放后,漢唐《詩經(jīng)》學(xué)的整個體系便出現(xiàn)了塌陷。所以朱熹提出,變風(fēng)“多是淫亂之詩”,“今但去讀看,便自有那輕薄底意思在了”。《詩序》解《鄘風(fēng)·桑中》云:“《桑中》,刺奔也。”朱子則說:“此正文中無戒意,只是直述他淫亂事爾。”總之,朱熹認(rèn)為,就三百篇之本文而言,“思有邪”者正多。他指出:“若以為作詩者‘思無邪’,則《桑中》、《溱洧》之詩,果無邪耶?……如《桑中》、《溱洧》之類,皆是淫奔之人所作,非詩人作此以諷刺其人也。”又說:“若言作詩者‘思無邪’,則其間有邪底多。”朱熹反對《詩大序》“變風(fēng)發(fā)乎情,止乎禮義”的說法,稱:“中間許多不正詩,如何會止乎禮義?”
在漢唐《詩經(jīng)》學(xué)形態(tài)模式成熟以后,朱熹《詩經(jīng)》學(xué)說從各個方面看都稱得上是與之并列的新的形態(tài)模式,它絕對不是宋代《詩經(jīng)》學(xué)的全部,卻足可命名為“宋代《詩經(jīng)》學(xué)形態(tài)模式”。在這一學(xué)說體系面前,漢唐儒者以詩人、詩思之正定義的“思無邪”這一《詩》學(xué)命題已經(jīng)不能成立,它跟這一新體系發(fā)生了嚴(yán)重沖突。在傳統(tǒng)《詩經(jīng)》學(xué)發(fā)展的整個過程中,孔子的論說都受到高度的尊重。既然孔子以“思無邪”概言《詩三百》,那么這一命題就不會被朱熹徹底拋棄,再度進(jìn)行意義置換于是成了歷史的必然。
朱熹認(rèn)為,孔子以“思無邪”概言《詩三百》,不是說“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而是說《詩》之“用”歸于使人“無邪”,是《詩》之“立教如此”,是讀《詩》之“功用”如此。朱熹認(rèn)定《邶風(fēng)·靜女》《鄘風(fēng)·桑中》《王風(fēng)·大車》《鄭風(fēng)·將仲子》等幾十首詩歌為“淫詩”,卻沒有像王柏(1197—1274)那樣力主把這些詩歌逐出《詩經(jīng)》,他認(rèn)為孔子將這些詩歌編入三百零五篇,目的是使讀者“即其辭而玩其理以養(yǎng)心”(《詩集傳·關(guān)雎》),“淫詩”雖有邪志而無妨,“讀三百篇詩,善為可法,惡為可戒,故使人‘思無邪’也”。
這一《詩經(jīng)》學(xué)形態(tài)模式凸顯了《詩》學(xué)立教者的存在——很明顯,他就是通常所說刪詩、編《詩》的孔子。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回到儒家《詩經(jīng)》學(xué)最原初的立意來重新定義“思無邪”。太史公謂:“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三百五篇……”(《史記·孔子世家》)朱子則說得更加細(xì)致:“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dá)于鄉(xiāng)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于正者。……是以其(孔子)政雖不足以行于一時,而其教實(shí)被于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為教者然也。”(《詩集傳序》)在《詩經(jīng)》學(xué)的這一種形態(tài)模式中,閱讀主體必須發(fā)揮其積極性和主導(dǎo)性——由于《詩三百》中存在“淫詩”,由于其中思有邪者正多,堅(jiān)持“即其辭而玩其理以養(yǎng)心”的朱熹必然會強(qiáng)化閱讀主體的自覺批判,缺少這一點(diǎn),致力于使讀者“思無邪”的立教期待就會落空。
朱子《詩》學(xué)代表的這種新的《詩經(jīng)》學(xué)形態(tài)模式雖然重新給出了一些定義和設(shè)計(jì),目的則仍在實(shí)現(xiàn)《詩經(jīng)》所負(fù)載的儒學(xué)價值(毫無疑問,儒學(xué)價值本身也有承繼前人和重新解釋的問題)。
朱子《詩》學(xué)代表的這種新的形態(tài)模式可以說是儒學(xué)內(nèi)部“撥亂反正”的結(jié)果。不過,這一體系既釋放了文本,又釋放了閱讀主體,最終會導(dǎo)致一切經(jīng)學(xué)附會的崩塌,而走向現(xiàn)代《詩經(jīng)》學(xué)形態(tài)模式的建構(gòu)。這恐怕是朱子本人未嘗料及的更偉大的歷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