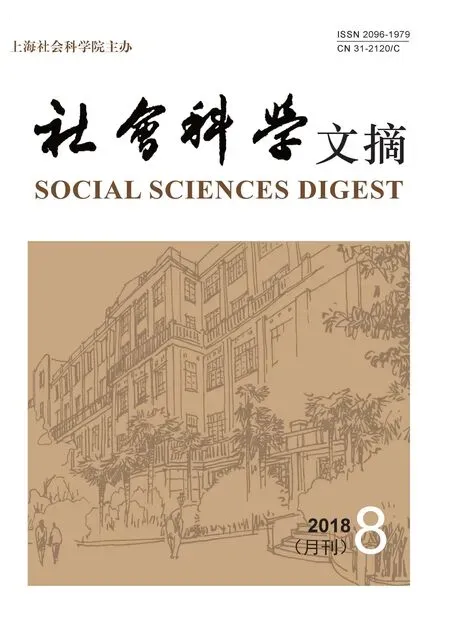關于中國樂文化傳統視域下的《牡丹亭》評價問題
——兼與朱恒夫等商榷
《牡丹亭》歷來被視為明清文人戲曲的代表作。它在以“妙處種種,奇麗動人”而不斷為人稱頌的同時,其主題思想的矛盾與劇情關目之不足甚至戲詞中之淫詞褻語也常常為人所詬病。朱恒夫教授等數年前發表了《作品的缺陷與評論的缺陷——讀湯顯祖的<牡丹亭>及其評論》一文(以下簡稱《缺陷》),該文認為《牡丹亭》“具有很大的思想及藝術價值”的同時,“它的缺陷也是很明顯的”;一一列舉了《牡丹亭》劇情構造的“蕪雜”、關目編織的“松散”以及人物形象及主題思想的矛盾;指出了當代評論界對于《牡丹亭》思想價值的誤解。
追根究底,《牡丹亭》乃是根植于一個深厚的中華樂文化的傳統當中,它不僅屬于一般文人自我述說與傾訴的傳統,即抒情詩的傳統,更是屬于在不斷被演述、被生發、被重組改造的話語系統,即樂文化的傳統。故而,本文意在將《牡丹亭》置于其所賴以生存的中國古代樂文化的傳統當中來加以釋讀和評價,以期獲得關于《牡丹亭》的更為準確和全面的理解,消除一些不應該有的誤讀。
《牡丹亭》的傳統基因
很顯然,人們已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不能以一種理想的甚至西式的戲劇樣態來衡量和剪裁《牡丹亭》,更不能以所謂“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的原則來“硬評”《牡丹亭》。因為,對于《牡丹亭》因夢成戲、慕色而亡、人鬼幽媾、還魂復生的劇情構造來說,“如果僅僅將‘還魂’情節解釋為浪漫主義手法或超現實主義方法,實際上很難讓今天的欣賞者進入湯顯祖所設置的語境中并獲得真正的審美認同”,甚至很可能造成對于《牡丹亭》思想與藝術的恣意曲解。于是,我們也就有必要去追問:湯顯祖所設置的語境具體是什么?《牡丹亭》究竟屬于什么樣的傳統?它有著怎樣的文化傳統的基因?
在劇情構造上,《牡丹亭》全劇共有52出,以主人公杜麗娘游園之際的春閨一夢為關節點,一線綿延,多有穿插,且起伏不定,以至于給人以“結構松散”“篇幅過長”的感覺;且自《牡丹亭》誕生以來,就很少有全本演出,甚至每有演出,必加刪減。《缺陷》一文對于《牡丹亭》“作品的缺陷與評論的缺陷”的分析雖由此出發,卻沒有追根究底,至少并未曾顧及到《牡丹亭》的傳統基因。該文只是拿著所謂“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的尺度來要求《牡丹亭》的“真實性”而排斥其“虛幻性”。殊不知,《牡丹亭》雖有其取材淵源,卻絕非因襲成篇。它其實更屬于一個文人的奇思妙想。
中國傳統樂文化大致有著三個層面的建構:其一是巫樂文化,其二是禮樂文化,其三是俗樂文化。三種類型文化的層壘疊合構成了中國古代樂文化的基本形貌。它們相互關聯,又各自有別,不斷重組,衍生出包括歌舞表演以及戲曲等在內的豐富多彩的中國傳統樂文化的樣式。中國傳統樂文化成為戲曲藝術的真正母體。戲曲蘊含并傳承著中國樂文化的傳統基因,同樣,樂文化也影響并制約著戲曲的形態樣式及其演變。無論是曲還是樂,無非都是對于戲曲樂文化傳統的一種體認和追溯。某種意義上,《牡丹亭》也許更近乎“古之樂”的。當然,戲本于樂,卻不等于樂。顯然,《牡丹亭》并非只是古代版的“人鬼情未了”,而主要還是古代文人基于民間傳說基礎上的奇思妙想或傳奇構制而已。
《缺陷》一文認為“《牡丹亭》中許多摹寫生活的情節是經不住推敲的”,指出:“用浪漫的的手法所構造的情節,我們應該用浪漫主義創作原則來審視;而依據實際生活創作的內容,則必須用‘生活的真實’與‘藝術的真實’之標準去衡量”。這難免顯得與《牡丹亭》的“語境”及傳統有些格格不入。
確實,《牡丹亭》難以扯得上所謂“浪漫主義”或“現實主義”的原則的,但如果不去顧忌所謂“浪漫主義”“現實主義”在歐洲文學中的具體所指,《牡丹亭》確實不失為一部具有浪漫情懷的精心的文人之作。但是,應該更確切地說,它雖然代表著這樣一種顯在的“文人敘事”,而同時又與勾欄瓦肆的“民間敘事”有著割不斷的情緣。既有民間故事的素材取舍,更有著劇作家個人化的大膽想象。它就是一個夢,一個關于情愛的生死之夢。它不僅是主人公杜麗娘的,更是劇作家湯顯祖的。
從戲班搬演的角度來看,《牡丹亭》固然不是當行本色,卻也并非完全沒有舞臺意識,《牡丹亭》關目之“蕪雜”與戲詞之戲謔,并非不堪,而是不甘。湯顯祖不屑于追求文人的雅潔,《牡丹亭》中就有意穿插了“戲”(戲耍、戲弄)的成分,當然亦不能混同于民間俚俗雜耍。湯顯祖的創作完成了一次真正的回歸,回歸到樂文化的根基處。作者不是不熟悉舞臺,只是不肯屈就于舞臺而已;不是他不配合演唱,而是不能“為文造情”“以辭害義”,故而才“不妨拗折天下人的嗓子”。
如果說,《牡丹亭》猶如一棵自然生長的大樹,那么,中國傳統樂文化便構成了適合它生長的土壤,并且提供了必要的精神養料。湯顯祖遵從一種“真情”“至情”的自然美學觀,自覺或不自覺地繼承了中國樂文化的基因,批判地吸收并融合了禮樂、俗樂、巫樂等諸多文化因子,才成就了這部作品的偉大。故而,也只有回歸到中國傳統樂文化的語境當中,才能夠做到對于《牡丹亭》全面的理解與獨到的闡釋。
《牡丹亭》的巫樂精神
《牡丹亭》有著深厚的巫文化根源,這不僅與湯顯祖出生、為官的地域有關,與劇作的取材有關,更是與湯顯祖所接受的思想淵源及巫樂文化傳統的影響有關。湯顯祖的祖籍在江西臨川,其一生的行跡,也多在吳楚之間。吳楚之地原本就有著深厚的神巫文化的基礎,并且經過長時期的流傳而形成獨特的巫樂傳統。先秦商周時代的巫風熾盛,深刻地影響到自屈原以來的中國藝術精神,形成所謂南方文化的“浪漫”傳統。而這一傳統的延續,追根究底,無非都是與巫樂文化的傳承有關。延至明清,中國藝術的神巫色彩已然褪去不少,但是,巫樂文化的底色依舊,傳統也并未終結,甚至內化為藝術家的心理結構的一部分。循乎此,明代湯顯祖《牡丹亭》能構造一個“因夢生情、慕色而亡、超越生死”的情色世界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從湯顯祖的思想傾向來看,道家的“任自然”與其“一生兒愛好是天然”正好契合。而道家思想的根源恰在于巫風熾盛的南方。于是,湯顯祖與吳楚文化中源遠流長的巫樂傳統也就有了千絲萬縷的聯系。這不僅顯示出湯顯祖之于老莊乃至佛道思想的汲取,而且其創作中具有鮮明的神話思維的色彩。
唯其如此,神巫,在《牡丹亭》的形象譜系中,也就有了某種特殊的地位及表現。一方面,人鬼神仙雜處,甚至相親相戀;另一方面,《白蛇傳》之類亦復如是。
細加分別,《牡丹亭》之神巫譜系大致可以歸為三類。其一是花神,花神在民間信仰中是司花的神祗。以花神舞的方式表現一種性的隱喻,一種生命活力與激情的宣泄。其二是閻羅殿里的判官、丑鬼。這些判官、丑鬼形象多與民間信仰有關,但又何嘗不是現實官場的直接映射,甚至比現實官場還稍多些人情味。從而,在中國民間信仰的神鬼譜系中,他們也就具有明顯的二重性。其三是主人公杜麗娘的神魂。有別于《李慧娘》乃至《活捉》中的“鬼魂”,杜麗娘之神魂是穿越陰陽,超越生死。
因此,有關神鬼世界的描繪,在《牡丹亭》中絕非可有可無,而是顯示出《牡丹亭》之于巫樂文化的汲取,或者說,巫樂文化成為《牡丹亭》的一種精神源頭。正是受巫樂文化的影響,湯顯祖的創作總是穿越于神鬼與人間,糾纏于現實與夢幻的二元世界。夢,既是《牡丹亭》的主題意旨之所寄托,也是其劇情構造的核心。或者說,正是巫和夢,不僅在《牡丹亭》的心理原型的構成的意義上實現了人神的溝通,體現出《牡丹亭》創作的神話思維的特性,而且也使得《牡丹亭》更具批判性色彩與超越性品格,體現出一種自然天成的浪漫氣質。
《牡丹亭》與禮樂傳統
《牡丹亭》之于禮樂文化傳統關聯,不僅屬于意義層面上的,與全劇的主題思想的表現有關,而且是結構層面上的,甚至進而影響到舞臺形制。
迄今為止,一般人認為,湯顯祖《牡丹亭》的思想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而事實上確是如此嗎?
其一是反封建。湯顯祖及其《牡丹亭》都明顯不構成對于“封建”政治文化的反思與批判,何來所謂“反封建”?如果說,杜麗娘出生成長的環境屬于封建官僚家庭,她所接受的教育也基本上屬于“封建式”的,那么,其官僚家族文化以及封建觀念對于人性的禁錮是明顯的,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牡丹亭》具有某種“反封建”的色彩。故而,與其籠統地說《牡丹亭》“反封建”,不如更確切地說是對于杜麗娘所置身于其中的封建家庭與社會倫理關系的一種批判。因此,“反封建”一說也就不免顯得有些大而無當。
其二是破禮教。所謂禮教,原本就是傳統禮樂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對于主張溫柔敦厚、樂而不淫的禮樂來說,《牡丹亭》的作者無疑采取了一種反思和批判的立場和姿態。然而,《牡丹亭》對于禮樂教化也不是全盤否定。在《牡丹亭》所構建的生與死、神鬼人的二元世界當中,如果說,人的現實世界充滿著禮教的束縛,禮教成為人的精神桎梏,那么神鬼或者人死后的世界則完全可以擺脫這一切。湯顯祖對于禮教的這種二元化的處理,既是他對于禮教意識的大膽質疑,同時也確實是《牡丹亭》主題表達的矛盾之處。
其三是反理學。隨著王學左派的興起,人們才開始了對于理學的系統反思和批判。王陽明提出的“良知”觀念無疑成為對“天理”的有效的校正和補充。湯顯祖就是站在王學左派的立場上,旗幟鮮明地強調人間“至情”,而反對“滅人欲”,主張揚“情”抑“理”,張揚“至情”。在湯顯祖看來,天理只有順應了人情,才是真正的“天理”。
確實,如《缺陷》一文所揭示的,究竟是頌揚愛情,還是表現情欲,確乎造成《牡丹亭》主題思想表現的一些矛盾性,也為人們認識和評價《牡丹亭》的思想和意義平添了一道迷障。但是,過分強調《牡丹亭》之宣揚“情欲”而無關“愛情”顯然又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其內在邏輯仍是“天理”與“人欲”的對立。
可以說,《牡丹亭》不是簡單的對于禮樂傳統的反叛,而只是對于禮教中的非人性的反思和挑戰。比如,性愛,無疑是《牡丹亭》著力表現的主題之一。情與欲,從而表現人的七情六欲也就成為詩歌乃至全體藝術的根本,成為傳統中國詩藝的基礎。
誠然,《牡丹亭》的主題表現是有矛盾性的。因為,恰恰是禮樂文化的傳統賦予了《牡丹亭》一個特殊的精神立場和價值標準。這種獨特的立場和標準也使得《牡丹亭》有了基本的“奇”與“正”的定位:《牡丹亭》所傳之“奇”無非是相對于禮法之“正”而言的,“奇”和“正”,實則相反而相成,沒有“正”,也就無所謂“奇”。在這個意義上,湯顯祖的藝術貢獻并不完全在于所謂“反禮教”,而是在禮樂文化的傳統規訓下一種新的價值倫理維度的探求與突破,即以情為據,以生死為期許,它自是對于理學教條的一種反撥,更是對于禮樂文化的價值訴求的一種積極的拓展。從而,《牡丹亭》中對于個體情欲的抒寫,其實并沒有徹底擺脫禮教的羈絆,而是在古老的禮樂文化的根基上長出鮮活的嫩芽來。
《牡丹亭》與俗樂文化
作為一部文人創作的《牡丹亭》,究竟與俗樂文化傳統有著怎樣的關聯?
《牡丹亭》之所以在表現“幽怨”“冷靜”的同時又很“熱鬧”,就是因為它的根深扎在傳統俗樂文化的土壤之中,從而在其舞臺表現上俚俗不拘。可以說,俗樂文化的喜樂精神與文人的悲憫情懷,造就了《牡丹亭》的特殊的品格和品味。
俗樂,乃是相對于禮樂而言,是基于民間民俗娛樂之上的一種樂文化形態。從歷史的發生來看,俗樂的興起與巫風的退隱有著一定的關聯。俗樂與巫樂,原本是相表里的,而與禮樂文化相并立。如果說,巫樂的主要功能是娛神,則俗樂主要是娛人與自娛。
唯其如此,俗樂文化之于《牡丹亭》,不僅構成了它生長的土壤和動因,而且直接構成其劇情發展及意象呈現的有機組成部分。因而,《牡丹亭》當中就不僅有著諸多喜鬧的場面排場,同時更明顯地表現出一種特殊的世俗化的格調。
就《牡丹亭》的排場而言,自《牡丹亭》誕生以來的各種演出文本,尤以喜劇性的鋪陳排場為甚,雖然這種鋪陳并不為多數文人所認同,但卻吸引了更多的觀眾。
就《牡丹亭》的格調而言,俗樂文化多以嬉鬧見長,至于《牡丹亭》的所謂“低俗”、粗俗,其實更多屬于舞臺上常有的科渾,目的主要還是適應觀眾的俗趣,以及有著更多的民間典儀的直接展示。
唯其如此,《牡丹亭》中,大雅和大俗、文人雅趣與民俗娛樂才得以相互交融。雜而不越,也就成為《牡丹亭》的魅力所在。
結論
究竟如何全面地理解與評價作為中國戲曲文化的經典文本之《牡丹亭》?無疑,《牡丹亭》的成就與瑕疵并存。只是《缺陷》一文對于《牡丹亭》思想及藝術上的不足的揭示稍顯浮表化,而未能深及根源,且其“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的評價視野顯然與《牡丹亭》的產生土壤、生存環境是不適宜的。
就主題表達而言,如果說《牡丹亭》一劇的傳奇故事在世俗的眼光中似乎顯得荒誕不經,但在戲劇舞臺上卻又在情理之中,它驚世駭俗,卻又入情入理。
就劇情構造而言,既然《牡丹亭》所言無非一個“情”,一個女子上天入地、尋覓真情的故事,那么,其情境設置與意象營構也就無不圍繞此“情”而展開。這種“情”也就成為《牡丹亭》“還魂再生”的劇情模式的主要動力源。
故而,唯其以“情”為綱,以“禮樂”“俗樂”“巫樂”為緯,融傳統樂文化于一體,《牡丹亭》的主題表達與劇情構造才顯得既一以貫之又包容性極強。而并非像朱恒夫教授等人文章中所揭示的那樣“在現實主義故事情節的板塊上隨意編構內容,淡化了作品的藝術真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