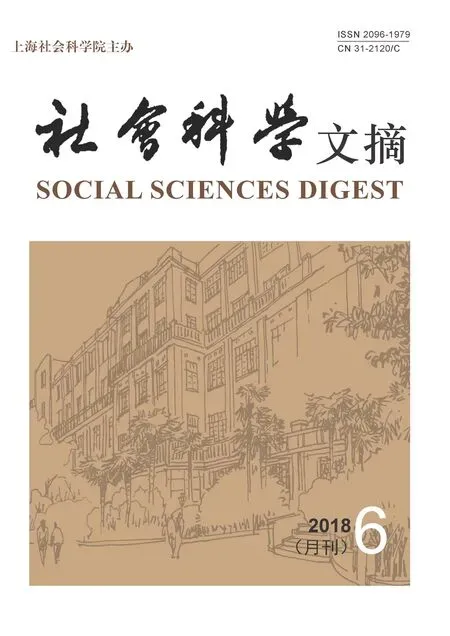技術治理的悖論:基層政府在民調中如何“制造”民意?
文/彭亞平
導言
迄今為止,技術治理依然是個無處不在又令人捉摸不定的“幽靈”。它為精細化治理、網格化治理、大數據治理等理念提供了方法論自信;它是深埋在項目制、運動式治理和行政發包制等理論觀察中的草蛇灰線;它因奔走在電子政務、精準扶貧、土地資源管理、流動人口管控等治理實踐中而被研究者捕捉。在歡呼技術時代來臨的同時,人們也在批判技術治理對社會的裁剪、對個體施加的權力,揭示其想要“將體制和結構層次的問題化約為行政技術的問題”卻又深陷在現有治理框架的困境(黃曉春、嵇欣,2016)。與此同時,治理的困局又不斷地召喚新的、更好的技術。以基層治理為例,個人偏好如何反映到公共偏好之中,是基層治理的癥結所在。居民二元分化、中產階級參與社區事務的興趣缺乏、社區抗爭愈演愈烈、居委會弄虛作假等治理難題都傳達了一個根本問題——民意難以正確、及時表達和有效回應。
技術治理的使命正是通過識別、處理源源不斷的問題進而把社會清晰地呈現在國家面前。那么,它能夠完成其使命嗎?為此,本文取材民意調查領域,去追問技術治理的邏輯及其命運。將其轉化成經驗問題,即通過揭開民意生產過程的暗箱,探究由基層政府實施的民意調查為何普遍公信力不高,甚至被質疑造假?它能反映真實的民意嗎?如果不能,原因何在?
某街道以項目的形式成立民調小組,對轄區內34個居民區進行連續三年的民意調查,內容涉及社區安全、衛生、環境、鄰里關系、民生設施、居委會工作等基層治理各方面,并編制成各社區排名指標體系,用于街道各部門對居民區兩委的考核、街道行政決策的參考。圍繞著民調,有街道、職能科辦、居民、技術人員等幾類相關主體。街道及各職能科辦負責問卷設計、擬定指標;居委會負責配合街道抽樣和組織問卷調查;居民負責填寫問題;技術人員即第三方學術機構負責提供技術指導以保證民調的科學性。
民意化簡程序:案例過程
(一)化簡程序一:從“社會情境”到“問題”
1.問卷設計:如何篩選情境?
問卷是社區情境的集合,即將民意搜集限制在一定的范圍內。作為民調的執行者和組織者,街道面臨的任務是從數十個社區內無數個可能的社會情境中,抽取組成問卷的代表情境。是什么樣的經驗標準左右了民調問卷中情境集合的篩選原則?“上級、老百姓關心的”是情境篩選的經驗標準,但這是個泛指。在實際操作中,哪些情境被篩選進入集合,則基于官員和相關工作人員的日常經驗。
與2015年相比,2016年的民調做了一些調整,主要是新增了幾個版塊。個中緣由,既有街道(特別是負責民調的領導人)與各職能科辦關系的因素,也有民調與街道其他項目兼容的考慮,還與時事變化相關。新增的“協助街道工作”版塊,分別對應各個職能科辦的具體工作任務,即讓居民評價其所在社區兩委在這些工作上的表現。為什么新增該版塊呢?負責民調的副主任在可行性分析會上說:“前兩年的民調,效果很好,我們很多科室年終評估就用到了這些民調的排名……(街道)其他職能科辦希望能共享這個數據。”民調是以街道的名義進行的,使用財政撥款,取得街道各職能科辦的支持是關系到民調工作能否繼續開展的因素之一。民調結果到底有沒有用,很大程度取決于各職能科辦是否用得上。要想數據用得上,必須在版塊設計上加以體現。新增的自治和黨建特色項目,也是這兩年區里和街道主推的政府創新項目。街道的用意,除了檢驗它們在各社區推廣的效果如何外,還能與區里和街道目前的工作重心相配套。
2.情境的壓縮方向:如何問問題?
情境樣本框確定好之后,接下來的程序是如何將情境定義為問題?一個問題的誕生,意味著一個情境朝著某個方向被限定好了。以代表情境“社區組織的人大選舉和業委會選舉”為例,居民與該情境發生聯系的途徑有多種,隨之會產生多種對情境定義的可能性,并對應各自的目標問題。當問題最終被定義為“您認為居民區內人大選舉和業委會選舉組織得如何”時,街道的權力在于,基層民主這一情境被定義到居民對所在居委會組織類似活動的能力上了。對一個社區基層民主“能力”的衡量,既不是人大代表能否履職、選舉過程是否公正,也不是造成目前選舉冷漠的原因等問題,而是詢問居委會組織選舉的能力。顯然,居委會的組織能力無法支撐起民主監督活動這個主題,卻又帶著這個主題的帽子,并成為計算基層民主指數時的標準。
街道為何如此命題呢?這樣符合科學原則嗎?民調的目的是居民對社區的評價,街道把民調與績效評價結合起來后,民調就變成了居民對居委會的評價。人大代表的履職、選舉過程的公正性不屬于社區兩委的工作范圍,選舉冷漠是一個敏感的政治話題,加上兩委對選舉工作的影響范圍也只在于組織這項活動,所以只能朝著這個方向命題。類似的例子廣泛存在。公共衛生方面不問醫患矛盾、看病難、看病貴等熱點問題,而問健康知識講座做得好不好;外來人口管理方面不問城管執法、落戶困難,而問群租合租治理問題;法律援助方面不問上訪、拆遷、業主維權、環境抗爭,而問家庭暴力的調解問題、法律宣傳力度。顯然,上述學界和社會關心的基層治理熱點問題,幾乎都沒有進入問卷,但進入問卷的問題又都跟它們沾邊,得以支撐背后的主題。當民意調查的操作權掌握在基層政府手中時,它內在的基因如管轄范圍、上下級關系就會植入到從社會情境化簡為問題的過程之中。
(二)化簡程序二:從“問題”到“數字”
1.“做卷子”:集中填寫問卷的理由
此次民意調查最終的抽樣方法是以各社區人群分類為層級的分層抽樣,調查方式是集中填寫問卷。把樣本集中起來填寫問卷的方式在西方民調中很難見到。用居民常說的話叫“做卷子”,填一份問卷好比考一場試。在成本和儀式化的考慮下,一場民意調查要跟其他不少活動結合起來,安排得緊鑼密鼓。具體流程有:各位居民代表在會場坐定后,該社區書記上臺作年終述職報告;在技術人員的監督和輔導下,受訪者填寫問卷并回收;部分居民代表參與街道組織的結構性訪談,對社區兩委工作人員進行打分和評價;街道工作人員對社區兩委逐一訪談,并相互打分。
在各社區的民意調查過程中,街道人員、技術人員、社區干部、居民代表全部到場,工序明確、高效運轉。半天時間,所有事情都趕在一起辦了,一個社區的任務就完成了。
然而,民調抽樣最重要的隨機性指標能保證嗎?技術上的解釋同樣有說服力。集中填寫問卷可以保證調查環境、調查時間和調查人員造成的影響是同質的,控制住常見的情境、訪員和季節等因素。另外,街道也設置了針對各個社區的小樣本隨機測試,采取街頭偶遇的方式,以便測試問卷的信度和效度,并作為集中填寫問卷方式的穩健性檢驗。
2.居民人數的控制權:分層抽樣的政治學
抽樣時如何分層呢?各社區樣本數量的下限被統一規定為50人。這些人從哪里來?民意調查通常很難取得一張載有所有人口成員的名冊,街道無法掌握各個社區人口的實時和動態信息,并沒有一個質量較高的可供抽樣的總體。就算能夠調動戶籍數據,因拆遷、工作變動、升學等因素的人口流動也會造成大量的無響應誤差。
民調的分層抽樣方案是社區向街道上報總體數量作為抽樣庫,由街道確定樣本。為保證隨機性,街道對每個社區的總體庫做了一些規定,如人數的最低限制、居民樣本標準、居民類型的規定、居民基本信息。各社區提交符合規定的樣本庫后,交與街道方進行分層抽樣。將確定抽樣總體的權力交與居委會可能存在一些問題,居委會選擇被抽樣居民時,依然依據成本原則。事實上,掌握所有居民的資料對不少居委會來說難度很大。能夠被掌握資料的,一般是信息被社區登記了的人。因此,全社區居民已經依據“與居委會有無交集”這一指標經過了篩選。只要對問卷中的個體特征變量如居民年齡、受教育程度、工作性質分布情況稍加考察,比如做個散點圖,馬上就會發現存在不同程度的偏態,退休老年人作為參加社區活動的主力軍的局面依然沒有改變。然而,分層的依據不是年齡、職業或者收入,而是黨員、樓組長、志愿者、群眾活動團隊成員、物業管理人員、駐區和共建單位人員、業委會成員、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社區民警和其他居民十一類人群,只要保證這些類型的人員比例符合要求,在技術上就算抽樣質量良好。人群劃分方式與基層政府對現有人群的分類相對應,以便民意調查的數據結果能夠作為參數直接輸入到科層機器之中。樓組長的意見呈現什么形態、群眾團隊成員對哪些問題反響比較熱烈、共建單位比較在乎什么問題,等等,都是街道所關心的。
居委會的控制力還體現在樣本數量上。根據樣本量設置規則,每個社區填寫問卷的居民數原則上不少于50個。從2016年民調實際到場人數來看,各社區填寫問卷的居民平均數為51.14,其中到場人數剛好為50的社區有15個。社區居委會對到場填寫問卷的居民有著怎樣的控制權?對精準到場人數的一個解釋是,人群分類標準的漏洞給了居委會轉圜的余地。按照十一類人群的劃分標準,抽樣庫里居民類型重疊的現象較為普遍,某人可以既是志愿者也是群眾團隊成員更是黨員。社區干部可以任意配置類型重疊的居民以符合要求,操作的空間更大。
(三)化簡程序三:從“數字”到“數字”加總
居民為所有刻度賦值后,街道可依照各個加總原則將刻度值累加,得到不同的指標和對應的社區排名、檔次,最終繪制成民意地圖。構建指標體系是民調操作的最后一個階段,也是街道和社區最為看重的部分。各個指標基于各個版塊制作而成,最終計算出來的指標既要給各個職能科辦使用,又要呈給街道領導閱讀甚至上報區里,還會直接制作成《XX社區診斷書》下發到各個社區。自然,民調結果怎么做出來,他們的意志是個重要變量。
1.分值權重
構成民意的意見本無優/劣、重要/次要之分,但暗含操作者目的的民調卻對此進行了排序。在擬定民調指標時,構成指標的各個問題的分值權重,就是街道對各個社區情境的重要性排序。2016年的各個版塊被分配了不同的權重,甚至每題的分數都不一樣。為了獲得職能科辦的支持,使民調結果能為其日常工作所用,問卷中的所有問題都可以與各個職能科辦的工作范圍相對應。由此,可以排列出各職能科辦在問卷中所占的百分比。服務辦、平安辦、管理辦等分值高達16%,婦聯、團工委、武裝部、工會卻只占1%,部門之間極不均衡。分值權重既反映了目前基層工作的重心,又把街道各部門的地位作為結構的基因植入了民調。
2.計算方法
作為對街道所有社區的情況摸排,從2015年起,每個年度的民調都設置了進步指數,計算素材是各社區歷年的民調得分。從結果看,較之2015年,2016年的分數出現下滑,也就是說大部分社區在2016年是退步的。在成果說明會上,副主任表態:“進步指數得要,不然上面看到了(這一部分缺失),會很顯眼。進步指數這個東西,就是我們街道工作搞得好不好(的直接體現),一眼就看出來了……有沒有別的辦法想?”在長時間的討論中,技術服務人員提供了幾種計算指數的基準法,在場的街道民調小組成員(由街道工作人員組成)則一一詢問這些方法的科學性。最終,動態指數和靜態指數這對統計學概念提供了“技術支持”。繁瑣計算的成果“令人欣慰”,進步的社區稍占多數。
3.各指標檔次劃分
在指標和排名計算好之后,要區分檔次。然而,到底分為幾檔,按什么標準分檔次,得視情況而定。各社區在各個指標中被分為非常優秀、比較優秀、一般、較差四檔,詞語邏輯對稱的“非常差”則缺失。街道設置的分檔原則是:前兩個檔次是指數為100及100以上的社區,后兩個檔次是指數為100以下的社區;除首尾外,每個檔次劃分的區間是均等的,如以10為區間。然而,設置檔次的玄機在于,具體以多少為區間各不相同,以5、10、15為區間的情況都存在。原因也很簡單,各個指數的社區分布情況差異明顯,不能采用統一的分檔次方法。在此作用下,檔次呈現如下規律:中間兩個檔次比首尾兩個檔次的社區數量要多;“非常優秀”比“較差”的社區數量要多。各社區檔次直接表現在各個指標組成的民調地圖上,以形成可視化成果。在街道各社區的行政地圖上,代表中等水平的“比較優秀”和“一般”的社區分別被涂成橙色和藍色,代表極端水平的“非常優秀”和“較差”的社區被涂成紅色和綠色。每個地圖上,紅和綠總是少數,而紅色大都比綠色多。
小結與討論
縱觀整個民調過程,各級權力主動或被動設置自己的規則,卻以“事事有理由、步步講科學”為宗。最終,富含信息的社會情境消失了,可視化的指標和地圖被呈現出來。經過街道、居委會在各個環節上的層層加工,民調反映出的民意對他們來說再熟悉不過了。不同的是,街道在某些方面獲得了合法性。持續多年的社區民意調查是街道實實在在的社會治理創新項目,民調的成果將作為職能科辦年終評估各社區的量化參考,成為決定社區干部評優、確定編制甚至去留的標準,甚至有可能納入決策參考。對居委會而言,一張以本社區居民的名義開具的《社區診斷書》從街道下發,為以后的工作確定了方向。政策合法性、官員政績、官僚機器運轉參數、社區工作方向等,都是民意調查為基層各主體帶來的好處。唯一用不到民調數據的反而是居民。
然而,民調本來是個統計學過程,如何變成了權力入侵的政治過程?上述問題讓我們回到最初的疑惑——技術治理能夠完成其使命嗎?從我們對民意調查全過程的解剖來看,問題的關鍵似乎并不在于技術的發展水平和嚴謹程度,而是技術治理的邏輯。當民調技術將“潛在”的復雜民意轉變為“實在”的民意數據和指標時,民意被一步步化簡、壓縮。在此過程中,再嚴格的技術都只能保證化簡的程序“合法”,而化簡的方向則由操作者決定。同理,政務微信/微博技術管不了頁面新聞或推送千篇一律,網格化治理技術管不了網格員拍照上報容易解決的事務,輿情監測平臺管不了對事件識別、分類和定性的現實考量。行文至此,技術治理的悖論逐漸清晰。國家通過技術治理打量社會的同時,也在制造其眼中的社會,它必然會把自己的基因植入其中。因此,技術治理的悖論是:國家通過技術之眼觀察社會圖像時,它看到的可能是自己的倒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