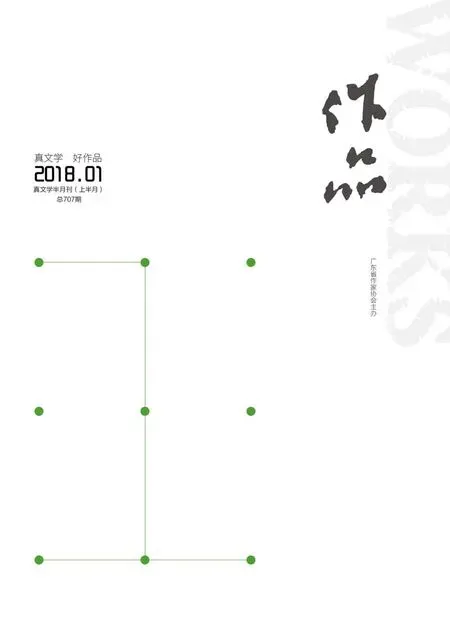飛鐵首乘紀聞
文/索 耳
1. 馬力①
我最近遇上了一些小資類型的煩心事。我從辦公室下班回家,臂膀夾著公文包,公文包里有一份“迷幻醫療”的病歷表(今天朋友寄過來的)。一切都跟往常一樣,只是心情不太好。從寫字樓出來,走過天橋,穿過玻璃望去,能看見遠處巨大的充滿幸福感的廣告牌。這時我聽見有人在喊我名字。
“喂!”一個穿著藍色制服,三十歲左右的男人朝我揮手,“你好呀!”他站在天橋的旋梯一側。
我走近他的時候記起來,他是一個跟我見過八九次面的推銷員。一年前外出跑業務時,每周的飯局上面偶爾出現他的身影。他常常坐在大人物的旁邊,而且給我的另一個印象是,擁有驚人的酒量。此時第一次跟他私人會面,我得以看清他的容貌:兩只被燒焦了的大眼,以及一綹蒜苗般的頭發撇在額前——這樣一種蜜袋鼯似的丑陋模樣使我更加藐視他了。
“你好,”我說,“好久不見。”
“是呀!差不多半年了。”他這話說得好像我們倆有什么交情似的。
“最近有啥新產品出來呢?”
他愣了一下,馬上回過神來,笑著說:“我已經不干那行啦。”
“那你現在干啥?”我驚奇地問。
“在飛鐵上工作,待遇可好了。”
我才想起,這是最近在首都里試行的一種新型公共交通,但我還沒有坐過。據說飛鐵上面的時間是平常時間的六倍,這對那些辛勤上班而無暇鍛煉的人群來說無疑是一個福音。他們會利用這多出來的幾個小時進行體育鍛煉(最流行的自然是:拉單杠)。試行的第一天,報紙上還記錄過一件趣事:從飛鐵上下來的胖子們都瘦了一半。我當時看到新聞拍案大笑,打算過兩天去過把癮。但是兩周后我忘了這事。
“真好啊,”我說,“恭喜你找到了一份好工作。”
一種尷尬的神色從他臉上一閃而過。他從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一粒軟糖,放進嘴里。“謝謝咯。”他邊嚼邊說。
我瞟他一眼,打算說點什么,同他禮貌作別。這時他卻突然問我:“你坐過飛鐵了沒?”
“還沒呢。”我如實回答。
“真的?那我帶你去坐坐。”
“不了不了,我還得趕回家去做飯呢。”
“你家在哪邊?”
“西門附近。”
“那正好哩。那邊有站臺,不一會兒就到,可方便了。”他不住地慫恿我,“快走吧!我也正趕著去接班。”
我推辭不過,跟他一塊走了。說到底,我還是被自己的好奇心給打敗了。有時我對自己這種空虛的欲望感到厭惡。
我們倆快走到電梯塔的時候,一陣突如其來的塵沙偷襲了我們的眼睛。馬力(我記起了他的名字)罵了一句,肏。他問我知不知道有關政府遷都的計劃。我搖頭說不清楚。他說上次在飛鐵上有人跟他說了這么一件事。政府正秘密地在西部新建一個干凈優美的都城。很少有人知道,保密是必須的,因為他們知道民眾絕不會支持。連流浪漢們都不愿意離開他們原有的支援窟。“要我說,”馬力狠狠地吞了一口唾沫,“我也反對遷都。沒人想著走人,也走不動。全天下都被一種復古主義和懷舊情結籠罩著。大家都好逸惡勞,但是意識很清醒。誰要是背棄我們幾千年的老祖宗,大家就一致用腳踹死他。你覺得對不對?”
我說:“沒錯啊,我也是這么想的。”(實際上我想的是:無論他對錯,我只要回答“沒錯啊,我也是這么想的”就對了。)
我們走進電梯后,馬力按下頂層按鍵。電梯四面是透明的玻璃墻壁,透過它們可以看到種植在電梯通道兩側的玉蘭花裝飾帶。真美。它提醒著每一個人這是一個和平的年代。當然,白色也同時象征著性交、肥胖和虛無。當我將要迷失于這疾走的炫目花影里面時,頭頂上方叮咚一聲的通報音把我驚醒了。電梯門在我面前再次打開。
“走吧。”馬力在身旁催促我。
2. 容貌等級制度
從電梯出來,沿著通道走幾步的距離,到達一塊圓形的懸空區域。這就是站臺。上面已經站了好些人,令人驚訝的是,其中大部分都有著健康苗條的體型。一半人在打瞌睡(對他們而言是最好的時機),嘴角流涎,有人還說著夢話。我沒有馬力那種在半空中俯視城市的興致,因為我留意到了這些人腳邊的拄杖。黑乎乎的棒子。有種不舒服的預感。
大概兩分鐘后飛鐵停靠在站臺前面。它看起來像只銀灰色大蜻蜓。馬力介紹說:它叫前進號,最多能容下三千五百人。人們開始陸陸續續地通過前門走進去。我最后走進去,找了個空位坐下。那些拄著拐杖的瘦子們像一群被打亂的棋子,散落在車廂的各個位置。馬力站在我身邊,跟我聊幾句,然后他要跟我暫時分別了。
“我得去上班了,”他說,“有事情聯系我。”
“可是我還不知道你在哪里工作。”
“你很快就會知道了。”
他拋下一句莫名其妙的話,矮胖的身影在車廂后面閃了幾下就不見了。這時我突然對他有點不舍(盡管我依然討厭他)。那是一種廉價的神經電流,沒來由地一直揪著我的發梢不放。我琢磨著馬力最后一句話的意思,半天沒頭緒。左手側是窗邊,但沒什么可看,滿目是白團團的霧氣,地上的建筑區看上去如一塊微型的芯片。我倚靠著,座位傾斜角讓人十分舒服。我開始胡思亂想,情人醫生的胸部時不時在腦海里閃過。她是有夫之婦,而且是兩個丈夫,兩個丈夫是兄弟。我跟她好了半年多,當我提出要成為她的第三個丈夫時,她表示了堅決反對。她的兩個丈夫也不同意。他們認為維持現狀挺好的,他們的三人協定并不需要第四個人的參與。之后我們就鬧翻了。我的情人醫生有禮貌地把我請出了她的生活圈。包括那張醫療表,她也已經清算完畢,所以我現在跟她一點關系都沒有啦。說真的,我一點也不傷心。我盯著車廂頂部,一塊透明的玉蘭花圖案晃得耀眼。
玉蘭魚紋羽氅蛇腹巨人太陽耳環星宿烏氈左右圖。博物館三樓展覽廳4937號。我最后一次跟她約會時,兩性的匯合點。她站在穿藍袍的保安身側,右手托腮,左手指著那幅圖畫。他們的尾巴真漂亮啊,她說,真不敢相信他們是我們的祖先。她說這話時仿佛身邊有一股回旋的氣場,把我的衣領都吹了起來。女醫生望著我,我也望著她,她的眼光把我整個身體托住。在古老的祖先面前,我們用目光交媾。過了幾分鐘,我忍不住牽了她的手。她觸電似的一陣戰栗,但沒有抗拒。我用手指纏上她的手腕,撫摸她的手背,掌骨和血管令我驚訝(它們的存在先前并沒有如此明顯);很快地她抽回了手,嘴角露出驕傲的神氣。她轉過頭去,這個過程里,鼻尖泛起青色的光芒。
“尊敬的先生們!”女人的聲音在大喊,“請珍惜你們的機會!”
我嚇了一跳,從半迷糊的狀態中醒過來。只見通道上不知何時已經擠滿了一群妙齡女郎,全都穿著藍色制服,放肆地大笑著。一個燙了頭發的姑娘手指夾著一根煙,不住地在一個瘦子面前比畫著。她長得真美!像個仙女一樣,只可惜是個啞巴。從她打出的手勢來看,她是在拼命地展示著一個數字。那瘦子一直搖頭。這時旁邊的其他女人們開始起哄:這位可是我們中間最漂亮的!這價格已經相當便宜您啦!無奈瘦子就是不動心,他一只手緊緊抓著身邊的黑拐杖,一臉戒備,好像即將有什么重大事件降臨。女人們見勸導無望,便逐漸從瘦子座位旁邊走開,擁擠著,如一團雪球向我滾來。我朝著走在前面的幾個招了招手。
“一看您就令人印象深刻,”她們喜笑顏開地走近,“您跟其他人完全不同。”
“你們這是干嗎呢?”我說,“恕我冒昧問一句。”
“您是新乘客吧?”一個梳中分的圓臉女人用手指著自己身上的制服,說,“我們也在飛鐵上工作,專門為客人們提供中級的服務。”
“中級服務?是指什么?”
“咳,”她突然俯下身來,直視著我的眼睛,“您剛才也看到了,就是接吻和上床。”
“接吻的價格是……?”
“那得看您挑的是誰。”
“我要剛才那位,”我用手朝著人群中間一指,“打手勢的姑娘。”
漂亮的啞巴仙女鉆了出來。這時我得以仔細地端詳她的面容,她比想象中小了四五歲,身材不高,皮膚白皙,有著完美的唇珠(這一點使我傾倒)。她勻稱的瓜子臉在我的注視之下籠上了一層紅暈。
“你叫什么名字?”我說。
她目光轉動,隨即打了一個手勢。我并不懂手語。旁邊的女人回答我:“她叫小琴。”
我點了點頭,接著問:“價格呢?”
她干脆利落地打出了“6”的手勢。這次我無須提示就領會了她的意思,六個硅幣,接一次吻。確實比歡樂場里的貴很多。但是我只思考了幾秒鐘就給了肯定的答復。女人們高興地歡呼起來,彼此相視而笑。叫小琴的姑娘越發顯得害羞了起來,她的神情讓我想起了我在博物館里見到的另一幅畫面,那是被捆綁在玻璃墻里頭的一幅海報,不記得是舊式電影還是舞劇的了,上頭的女主人公手戴鐐銬,身上的裙子靠近腹部的地方給畫上了一個黑色的十字。她的表情非常奇怪。不同的觀眾有著不同的解讀。我從她的臉上看到的是羞澀,一種不明顯的下垂的羞澀。我的頭皮頓時被帶起了一股灼熱感。小琴效仿(不,當然不是效仿)著我的一位膽小的情人,身體向一側傾斜,輕輕依偎在我的胸前。接著她向前抬起上半身,光滑的脖頸前伸,定住,兩人的臉部保持平行。我跟她對視,她的眼睫毛快速地眨動了幾下。然后她閉上眼睛,朝我嘴唇吻去。唇舌交觸的一瞬,我大腦頓時一片空白。小琴有著高超的吻技,想必是通過無數次的練習得來的。她的唇珠超越了一切預想。
這時,我腦海里突然出現了一幕:那是在博物館衛生間對面的一條長廊里,她孤零零地望著下方(那里什么也沒有),我走過去,抱住她,想吻。她一下子就把我推開了。她用的力氣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發出了一聲悶響。砰。小琴的脖子撞在了前方的座位上。她茫然失措地盯著周圍一張張鏡子似的臉(它們折射著同樣的驚慌和困惑),再轉回去看了我一眼,情緒轉為窘迫乃至羞憤,喉嚨里嚶的一聲,站起身來迅速地跑開了。女人們沉默了數秒,開始鄙夷地冷笑,她們認為我是一個大混蛋。她們克制住朝我臉上噴唾沫的怒火,陸續地抬步向后方散去。我不停地挽留她們,但只有一個微胖的大嘴女人(但看上去依然漂亮)站住了腳步。
“你真可會消遣別人!”她口氣里帶著不快,“我們雖然干這行買賣,卻也不是小孩子的玩具,讓人隨便摔著玩。”
我繼續謙卑地賠著禮,將事故原因歸咎為自身的生理缺陷。我得了一種怪病,癥狀就是不時地手腳毛躁,偶爾還會伴隨著眩暈和反胃。我的謊言天分征服了面前這個三十多歲的善良女人,(基于一種分娩情感)她很快就原諒了我。她甚至安慰我,為了使我免于內疚。接著我從口袋里掏出六個硅幣,遞到她手里,“這是她應得的報酬,”我說,“麻煩你代我向她道歉。”
大嘴女人不含糊地收下了錢幣。“你是個好人,”她說,“我們早該知道的。”
我讓她在我身邊坐了半個小時,報酬是三個硅幣。她跟我聊了一些她的家庭情況。她有三個孩子,其中有一個是自然培育的。她丈夫在保險局工作,薪金不錯。而她堅持干這行則是因為少女時代的性幻想。她說,年輕時候做了好多好多奇怪的夢,令她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個在遠古帝國的空中城堡當妓女的夢境。在月經初潮的幾個月內,她在夢里和形形色色的各種男人。從那時起,她就開始注意自己的容貌,每天對著鏡子,祈愿自己將來成為絕色美人。
“你非常漂亮,”我說,“你夢想成真了。”
“謝謝,”她溫柔地笑著,“就是年紀大了,沒有小姑娘吃香。”
“那可不一定,很多人很喜歡你這種類型的。”
這時天花板上的壁燈突然閃爍了一下。我想起了一件事情,問她:“你們這個既然是中級服務,那還有什么是更高級的?”
“當然有啊,”她回答,“那里的人們,長得可美了,比我們這群人里最美的姑娘還要美上十倍。”
“真好奇他們的服務內容到底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她搖頭說,“他們是最神秘的群體,只有顧客才真正了解他們的工作。”
“這里面隱含的是怎樣一種架勢和邏輯啊,他們所從事的工作和他們的容貌掛鉤,我是說,為什么非得長得好看不可呢?”
大嘴女人驚訝地瞪著我,隨即她忍不住笑了出來。
“你真的是什么也不知道嗎?”她用手掩住嘴巴,說,“這是這里的第一規矩啊——不,這是全世界的規矩。你不知道?”
“什么規矩?”
“容貌等級制度。”
“這不是你們這行業才有的嗎?”
“傻瓜,我再說一遍,它是屬于全世界的。”
“怎么可能!”
“你上來飛鐵多長時間了?”
“什么?我上來有一個多小時了。”
“都這么長一段時間了,”她搖著頭說,“你都沒注意到嗎?這可是一個相當豐富的樣本呀。”
“我什么也沒看到。”
“你肯定是走神了,”大嘴女人站起身來,樣子有點生氣,“你一直心不在焉的。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是你讓人覺得非常粗魯。你太自我中心了,你甚至忽略了周圍的一切存在。無論對誰,任何人,你都是。對不起,我不想跟你再聊下去了。再見。”
她說讓我一個人好好反省,然后就走了。當然我并沒有挽留她,她已經做了她所能做的事。我繼續獨坐在位置上(連屁股都未曾挪動),只是此時感覺不太舒服。湖藍的座椅,白色的內壁和天花板,薄霧般的窗簾,繡著巨嘴鳥的地板。兩分鐘后,迎面走來一位乘務人員(穿著千篇一律的制服),大眼睛,粗眉毛,真丑。她推著一輛圓筒形的垃圾車,面無表情地從我旁邊走過去了。過了一會,走過來一位衣領上別著擴音器的乘務員,她瞧上去順眼多了,只是眉毛蹙在一起,有點兇巴巴的。再過片刻,帶著掃把的、推零食車的、按時巡邏的,依次從我身邊走過,那些臉龐變得越來越漂亮。最后蹦蹦跳跳跑過來一個八九歲的小男孩,十分俊俏,制服上的徽章閃閃發亮。他跑到我旁邊時差點摔了一跤。但他馬上爬起,然后沖我咧嘴一笑。天使般的笑容。媽了個屄的。
3. 瘦子革命
她說的竟然是真的。
我頓時看見了恐懼。世界的又一條奇怪規律真實地擺在眼前。我想起了馬力,他不久前跟我說的那句話:你很快就會知道了。知道什么?馬力有一張惡心的臉,“大嘴巴”使他遠離了上中層階級的社交圈,嗜酒的習慣則令他失了業。他注定是一條寄生在機器渦輪上面的油精蟲。這是我在一本小說上看到的一種奇異生物。它有著人的軀體四肢,有智慧,但它注定只是機器的守夜人。有一條被默許的規則使它那樣做。一旦機器出現了阻滯,它就會毫不猶豫地跳進去,它以自身潤滑著機器的運轉。在下一個流程里,它又會被重新收集并制造出來,繼續執行任務。馬力就是這種存在。他長得太丑了,我不知道他會被派往哪里工作(很有可能是最下賤的地方),我開始為他擔憂。
幾分鐘后我忍不住站起身來,打算去找他。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我只能到處亂跑。已經到了午餐時間,大家都安安靜靜地呆在座位上進餐。每個人都嚼著面包,慢條斯理的,但是能吃很大分量。汗珠沁出在他們粗壯的手臂上,像覆上了一層細鹽。我不停地穿過每個車廂,目光掃視過那些最骯臟可恥的角落,可是并沒有什么發現。他似乎根本就不在飛鐵上面。最后我停了下來,因為又餓又困。當時我在老年艙里,周圍都是鶴發童顏的老人。其中一位用方言跟我交談了幾句,他問我是不是市政府里面的人(因為那里供職的都身形中等)。
就在這時,一個黑衣人沖了過來,差點把我撞倒。他直起身來的時候發出了一聲冷笑。我看到他手里拿著一把槍,槍口對準了我。我頓時被嚇退了好幾步。接著黑衣人轉過身去,把黝黑的槍口展示在所有人面前,大喊:都給我呆著,不許動!人群里一陣恐慌和騷動。人們緊盯著那把手槍,仿佛在下一秒子彈會塞進他們的喉嚨。黑衣人舉著那只拿槍的手,得意揚揚地,等待人們漸漸安靜下來,他清了清嗓子,開始講話(他唇角的肌肉生硬地與顴骨相連,每吐出一個字那里就要扭動一下)。我認出了他是那伙帶拐杖的黑衣瘦子中的一員。
“聽好了,”他高聲說,“這不是搶劫,我對你們的財物不感興趣。我們是革命者,我們要革的是政府里那些中等人的命。同時,我們需要民意,我們是態度收割機,你們的支持對我們非常重要。聽明白了嗎?我們不需要錢,也不強求大家親身加入,我們需要的,只是你們的指紋。如果有支持我們的,請將拇指頭在這上面按下去。”說著,他從腰間掏出了一個圓盤模樣的指紋機。
老人們面面相覷,小聲地討論著,但沒有一個人愿意上去觸摸機器。
“誰能保證你們會成功呢,”有人說,“萬一失敗了,支持你們的豈不是要遭殃?”
“我們一定會成功。”黑衣人堅定地回答。
過了好一會,還是沒人上去。黑衣人開始變得煩躁。他突然走上前去,用槍指著座位上的一個戴花邊帽的老人,惱怒地說:“你按不按指紋?你敢說不我就一槍崩了你。”
“你在強迫民意呢。”老人不慌不忙地答道。
“這是必要的!”黑衣人大喊,“革命需要適當的殺戮!”
“滾你娘的,老子才不愿意把國家交到你們這些瘋子手里。”
黑衣人眼露殺機,作勢要扣下扳機。這時我站了出來:“慢著!”我扯著喉嚨喊道。包括黑衣人在內的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我這邊來。我像個鴨子那樣走過去,晃著腦袋,實際上我緊張得要死。黑衣人打量著我,問:“你想說什么呢,大英雄?”
“把這些老人家們放了,”我說,“我跟你走。”
“你以為你是誰?”
“我既不胖也不瘦。”
“看得出。”
“你還沒懂嗎?”我一攤手,說,“我是在那個地方工作的,機密工作。”
黑衣人聽到后睜大了眼睛。他的瞳孔使勁地在眼眶里轉了幾圈,傳來咯咯的笑意。他把槍收回去,轉過身來,沖我努了努嘴。“好家伙,有膽子,”他說,“跟我來吧。”說完他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槍眼頂住了我的腰間。我跟他一前一后地從通道走過,穿過了幾個車廂(那里的乘客們也已被黑衣人控制),最后到達了一個很大的房間。里面很臟,有一股霉味,但是很空蕩,什么物件也沒有。一進去就能聽見類似發動機的轟轟聲響。房間里站著一個穿黑衣的家伙,像一根桅桿立在那里。等他轉過臉來,我差點沒喊出聲來——他可能是我一生中所見過的人里面瘦得最可怕的了,一張臉全由倒三角的骨頭組成,下巴向里側轉了九十度的彎,雙眼從下陷的另一平面透出冷幽幽的光芒。身旁的黑衣人走過去,跟他附耳說了幾句話。他點著頭,把我直盯得頭皮發麻。
“你好啊,”這個鬼魅般的首領開了口,“初次見面。”
“你好。”我小聲地回應。
“很高興你能加入我們,”他說,“一同為摧毀這個由少數中等人統治、喂飽胖子并餓死瘦子的腐朽社會而奮斗。對了,容我夸獎你一句,你的身形可真漂亮。”
“謝謝。”
“你提到你從事的工作——能清楚地再告訴我一遍嗎?”
“嗯,我在安全部工作,監督委員會,知道吧?我是其中一員。”
他的語氣中顯露著驚訝:“真沒想到!如果你愿意提供情報,那真是幫了我們天大的忙。你知道嗎,監委會是我們唯一沒有任何人員安插的機構。它的防御墻,又硬又厚。”
“是的,”我說,“那里的每一個成員都要求基因純正。”
“所以我要懷疑與你相關的真實性,”首領冷冷地說,“包括身份和言語。”
“你不相信我嗎?”
“肯定的。你得證明自己。”他說,“我不希望隊伍里留著一棵軟弱的墻頭草。你有什么要說的嗎?”
“暫時沒有。”我回答。
4. A.M.D.
我被允許留了下來。在這個臨時的作戰指揮室里,我跟黑衣首領呆在一塊。他把這里稱作“肛門”,是他自認為(得意揚揚地)可以寫在衣襟上面的哲學判語。這里又臟又臭,卻沒有容納任何東西,它只是一個無意義的關口。我安靜地站在一旁,聆聽黑衣首領的思想講演,中間或插上幾句贊美語。有時候我覺得他那離譜的驕傲令人難以忍受。他并不急著從我口中套問出情報(他認為我將會自然而然地屈服),反而,他拼命地要把話題轉移開,為了使我以為自身并非處于審訊之中。他跟我聊了一堆三姑六婆、文昌門一帶的游樂場、社交網絡和兒童培育的話題。最后談及那位心理教育大師、人類歷史最后一位哲學家,也是他的靈魂導師裴永鄉的時候,我已經開始不住地犯困。我可以睜著眼睛打瞌睡,這也是長期在辦公室里培養出來的技能。
之后我借機去上廁所,廁所在“肛門”的另一面。那是一個像蝸殼的狹小而扭曲的空間。我并攏雙腳,小心地解開褲鏈,膠質水管緊挨著我的脖子穿行而過。一股難聞的氣味彌漫在周圍。我強忍著惡心,對著那只不斷冒著綠色氣泡的馬桶眼撒了一泡尿。完事后我對著一個臟兮兮的洗手盆洗手。這時,身后突然傳來一個幽怨的聲音:您需要衛生紙嗎?如果需要,請按下水盆上方的綠鍵。我驚詫了半天才發現聲音是從馬桶眼里傳出來的。水盆上方的墻壁上,果然有一個綠色的微凸的按鍵。我剛按下去,幾張紙巾就從天花板上飄落下來。我說了聲謝謝,用紙巾擦干手上的水珠。這時馬桶眼又發話:請把用過的紙巾扔進來。我沒反應過來,問:哪里?它回答:馬桶眼里。我按照指示把廢紙擲進了那個深不可測的洞里。隨后傳來一陣咕嚕咕嚕的聲響,過后那個熟悉的聲音又響起:“十分感謝。”
我已經知道這個聲音是誰的了。我對著馬桶眼,高興地說:“總算找到你了。你知道我是誰嗎?”
“啊!是你。咱又見面了!”馬力的聲音隔著坑道傳來。
“你在里面嗎?”我問。
“是的,”馬力過了好一會才回答,“現在你都知道了吧。這就是我的工作。”
我認為他的口氣里并不帶有一絲感情。“你感覺怎樣?”
“有點無聊。”他回答。
于是我跟他說了在飛鐵上的全部遭遇。他認真地聽著,在我提到啞巴仙女和黑衣人時哈哈大笑。“你真是個混蛋,”他說,“你說得我都想出去瞧瞧了。”
“那你快出來啊。”
“現在可不行。”
“你是對的,”我說,“外面全是恐怖分子。”
“你害怕他們嗎?”
“不,”我搖搖頭,“他們不可怕。我感覺飛鐵上的每一件東西都比他們可怕。”
馬力沉默了一會,說:“飛鐵上到處都有著神奇的鍵鈕,你知道不?”
“是嗎?我不清楚。”
“真的。各種功能的大大小小的都有。只是一般的乘客不知道罷了。其中有一種按鍵,名字叫‘A.M.D.’,紅色的,功能類似于復位鍵。只要一按下去,整個飛鐵大系統里面的不安定分子就能立馬被抹平,一切恢復成原先的樣子,好像什么也沒發生過。”話末馬力又添加了一句,“當然,知道這個絕密鍵位的人,只有乘務長等寥寥幾個人而已。”
“你是怎么知道的?”我奇怪地問道。
“嘿嘿,任何地方都有廁所啊。換句話說,任何地方都有我的耳目。”
“真厲害。所以你的意思是……”
“按下那個鍵,‘A.M.D.’。它那縮寫的拉丁文名字意思是‘偉大的圣母’。”
“你是要我抹殺掉革命?”我說,“按下去,他們就完蛋了?”
“沒錯,他們太煩人了。”
“不,我不能這樣做。這跟他們有什么區別!這是血腥粗暴的鎮壓!”
“笨蛋,”馬力的聲音陰沉無比,“我跟你說過的,這樣的按鍵無處不在。你明白了嗎?他們的命運一開始就注定了,他們沒機會贏的。這里最美貌的家伙掌控著這些按鈕,他們隨時都能通過按下‘A.M.D.’干掉反叛者。”
“……難以置信。”
“快按下去吧,沒有時間了。”他說。
我依照馬力的指示,在馬桶背后的根部找到了按鍵的位置。那里本來長著一片青苔,我將唾沫吐在指尖上,在上面擦拭,漸漸地一抹杏色的圓點就顯現出來了。它越擦越亮,到了后來活像一個閃耀的小燈泡。我湊近觀察,果然發現了上面刻著的幾個黑色字母。一切確信無疑了。我閉上雙眼,深呼吸,腦海里浮想起在博物館里跟女醫生目光交媾的畫面(反正我一想就只想到這個)。當時我們只是相互交纏在一起,但并沒有交換精子和卵子,因為缺少一個適當的機栝。現在,我在冥想中完成了這個舉動。
“嘟——嘟——嘟——”尖銳刺耳的警示音。
我忍不住掩住了耳朵,匍匐在地面上。地面也在晃動,每一顆灰塵仿佛都要鉆進我的鼻孔里。
5. 馬力②
飛鐵最后臨時停靠在西門的站臺上。警察們從外頭進來,逮捕了那些已經動彈不得的黑衣叛亂者。馬力送我從側門出來。世界的時間只過了十分鐘左右。正午的陽光猛烈地炙烤著被汗水浸潤的衣衫,像是在大海的中心漂浮著的感覺。我長長地呼了口氣。
馬力把我送到站臺邊緣,他站住不走了。“下次再見吧,”他說,“我很快就要繼續上班了。”
“真是一次難忘的經歷。”我說。
“你會把它記下來吧?”
“當然了。”我說。
“以后我們會再見的,”他笑著說,“尤其是當你變成了一個大胖子的時候。”
接著我跟他揮手告別。我依舊不喜歡他,他的外表不管怎么說都令人厭惡,而且身上總有一股排泄物的難聞的氣味。我看著他轉身,像一只禿尾鼠,很快地又不知鉆進哪個地洞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