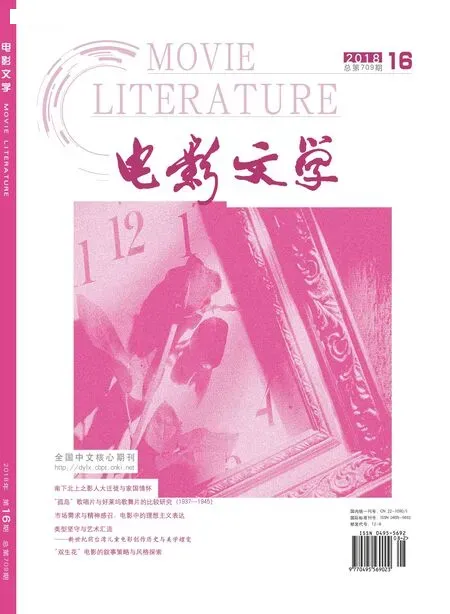《刺客聶隱娘》的意境美學
馬 瑩
(天津科技大學 藝術學院,天津 300457)
在當前影院觀影行為已經被賦予了一種消費和感官娛樂的儀式化功能時,侯孝賢延續了自己“電影作者”風格的《刺客聶隱娘》(2015)在這種氛圍中無疑是顯得格格不入的。盡管這部侯孝賢“八年磨一劍”的電影在戛納等電影節上攬獲好評,但由于與國人所習慣的傳統武俠電影區別較大,電影在上映后引發了較大爭議,貶者多詬病其沉悶的敘事,而褒者則注意到了電影中獨特的、屬于侯孝賢的藝術風格。應該說,在中國的傳統文化風格,個性化表達與觀眾普遍的審美趣味上,侯孝賢選擇了前者,在電影中營造了略顯曲高和寡的審美意境。
一、意境美學與侯氏電影
“意境”的概念在我國傳統藝術文論中由來已久,已成為一種跨越不同藝術領域,且具有民族性的美學理論范疇。自唐代王昌齡的《詩格》至今,人們對于意境有著林林總總的闡釋,在詩詞、戲曲等的理論批評中,意境所代表的審美價值和審美理想也略有不同。一般而言,人們普遍接受,所謂意境,指的就是創作者的一種主觀的藝術聯想,有形、有限的景與物經由創作者匠心獨運的熔鑄,被賦予了無形、無限的,接受者能夠領略、理解到的情感。
人們已經意識到,電影作為一門訴諸觀眾視覺的敘事藝術,既是繪畫藝術在銀幕上的變體,又是敘事文學的另一種書寫方式,它是完全可以實現對意境的追求,制造“虛實相生”“境生于象外”的美感的。但必須承認的是,主動地對意境美學進行追求,將中式美學在銀幕上外化,即使在中國導演中,依然是屬于較為少見的。電影藝術更多地承襲了西方的戲劇藝術,而非中國的“劇詩”(張庚語)。而西方戲劇自誕生以來,就高度重視敘事性,曲折的情節和嚴峻的沖突是西方戲劇的最高要求,也是自古希臘戲劇到莎士比亞、莫里哀等一以貫之的藝術追求。而在批評上,如亞里士多德和黑格爾都將戲劇視為一種寫實主義的“模仿”,可見西方戲劇強調的始終是行動與具有敘事性的斗爭沖突。及至到電影中,中西方電影人也已經接受了電影的重點在于人的行動與沖突,斗爭的出現和斗爭的解決。詩的生命很難在這種電影觀中得到延續。
也并非沒有電影人主動在創作中吸納中國傳統美學理念,這在武俠電影中體現得尤為明顯。武俠電影是中國電影藝術中較為獨特的,承載了中國傳統文化底蘊與俠義精神的類型片。如李安、張藝謀等有意為電影打上中式烙印的導演在進行武俠電影的拍攝中無論就場景設計、人物造型或敘事結構上,都有了對意境美學的追求。如《臥虎藏龍》(2000)中李慕白與玉嬌龍的竹林之戰,《英雄》(2002)中無名與長空的琴館對敵,無名和殘劍在意念中完成的水上對劍等,都成為武俠電影在影像表達上注重意境美的典范,也為中國武俠電影驚艷世界奠定了良好基礎。但值得注意的是,李、張從不會將意境構建與電影的商業追求對立起來。李慕白和玉嬌龍在竹林中穿行本身就是視覺奇觀的打造,《英雄》中更是以具有懸疑色彩的“羅生門”敘事結構全篇,影片對比鮮明、濃艷的色調本身也是服務于這一敘事的。
而初次嘗試武俠電影拍攝的侯孝賢則不然,整部《刺客聶隱娘》中,電影矯矯不群,幾乎難見任何一點對商業的妥協。聶隱娘在“殺”和“不殺”之間徘徊,就已經是整部電影最具有張力的戲劇沖突。正如編劇謝海盟表示的,聶隱娘的“刺客”身份是非常明晰的,身為刺客她理應遵從組織或雇主的要求,“劍道無親,不與圣人同憂”,而拋棄屬于“俠客”的個人是非判斷。然而聶隱娘卻屢屢自作主張,先是因為“不能斷絕人倫至親”而放棄刺殺大僚,后是因為擔憂魏博動亂,加上內心的舊情而對田季安不加刺殺,反而護衛。聶隱娘的情懷越來越趨近家國天下,而與《英雄》中復雜的、令人情緒激蕩的殘劍刺秦王,殘劍衣袂飄飄地為無名在黃沙之上書寫“天下”,無名以“天下”囑托秦王不同,《刺客聶隱娘》只是不厭其煩地展現著聶隱娘沉默的、面無表情的凝望,全片中聶隱娘的臺詞也極少。原著唐傳奇中的神怪色彩,聶隱娘和磨鏡少年神秘的、令人遐想的情感,這些本可以成為消費時代電影“賣點”的內容,在電影中也遭到了壓縮。
而只要對侯孝賢之前的電影,如《風柜來的人》(1983)、《海上花》(1998)等稍作了解,就不難發現這種對劇情的弱化,正是侯孝賢一以貫之的風格。相對于建立起一條有著開端、發展、高潮、結局的敘事李安,和精心鋪排戲劇沖突,或是打造奪人眼球的刺激畫面,侯孝賢更愿意以一種內斂甚至是令人昏昏欲睡的方式敘事,讓人物長時間處于靜止狀態,并尋找自然景觀中的氣韻,將其與人物曖昧幽深、難描難言的情感相結合,最終形成深遠而悠長的意境。而《刺客聶隱娘》也不例外。
二、《刺客聶隱娘》意境美學透視
(一)虛實相生的取景
侯孝賢的電影一貫熱衷于以一種極為安靜、舒緩的節奏完成敘事,長達數秒的長鏡頭,在敘事上形成跌宕的空鏡頭比比皆是。《刺客聶隱娘》中,嘉信公主和聶隱娘在漫天白霧中結束對話,以及或秋水長天、煙波浩渺,或秋草枯黃、古道西風瘦馬的鏡頭都是例證。在無聲的湖泊山林中,侯孝賢以固定機位展現了天地大美,甚至為兼顧膠片拍攝和景致之美而專程去日本取景,但也被觀眾批評為使電影過于沉悶,這主要是觀眾并未能站在侯孝賢的角度“以我觀物”。有學者曾指出:“在侯孝賢電影所提供的想象域中,自然景物始終是作為某種自我認同的對象化自我展示的,作為物我合一的契機,提供了對社會現實的超離。”如外景與內景,都市公寓與小鎮景象等的對比,在侯孝賢電影中,都大有深意。而在《刺客聶隱娘》中,電影盡管脫離了侯孝賢擅長的對“前現代鄉土臺灣”的范疇,但在將景物轉化為符號域這一點上,電影與侯孝賢之前的電影,如《在那河畔青草青》(1983)、《戀戀風塵》(1986)等是如出一轍的。在電影中,靜美開闊的外部自然世界,和華美、陰暗的魏博幕府內景形成了一種對比,而自然世界才代表了主人公的一種理想自我。草長鶯飛,蟬鳴陣陣,云舒云卷的景物是“實”,而聶隱娘對于自由的向往,以及在磨鏡少年等人身上得到的心靈慰藉則是“虛”,穿行在自然草木中的聶隱娘幾乎和自然景觀融為一體,放下了手中的劍,進入到了“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自由境界中。尤其是在電影結尾,聶隱娘和磨鏡少年在極富古韻的美景中騎馬遠去,觀眾能從這浪漫幽遠的景色中意識到,這意味著身體和靈魂都獲得自由的聶隱娘終于得到了自己的幸福,終于超離了唐代藩鎮割據、同室操戈的丑陋現實。
(二)意象的選用
意象來自于“立象以盡意”的美學追求,指的是在詩歌創作中將獨立的客觀外物視為特定抽象情感的載體。而電影也有著這樣的“有意味的”鏡像話語,正如馬塞爾·馬爾丹在《電影語言》中指出的:“由于電影畫面含有各種言外之意,又有各種思想延伸,因此我們倒是更應該將電影語言同詩的語言相比。”精妙的意象提供了觀眾一個從能指走向所指的思維挑戰,是電影意境美學能否成功建立的關鍵。在《刺客聶隱娘》中,“劍”和“鏡”的意象是最為關鍵的。聶隱娘的人格完整,是在從嘉信公主宣揚的“劍道無情”走到自我選擇的“劍道有情”中完成的,在劍這一外物中,侯孝賢賦予了其仁恕、不殺等儒家道德理念。聶隱娘對劍道的把握,也是她突破精神困境的過程。武俠電影將劍上升到人格高度,并非侯孝賢的獨創,這里有必要著重提及貫穿全片的“鏡”意象。
在嘉誠公主落寞撫琴的長鏡頭中,侯孝賢為觀眾介紹了“青鸞舞鏡“的典故,而這也是理解嘉誠公主、聶隱娘,乃至侯孝賢本人的關鍵。這個典故出自南朝宋范泰的《鸞鳥詩序》,孤鸞被罽賓王得到后,三年不鳴,臨鏡后以為見到同類,便慨然悲鳴,最終展翅奮飛而死。嘉誠公主從京師遠嫁到魏博,并且遣散一切隨從侍女,表示從此“京師自京師,魏博自魏博”,與曾經的生活一刀兩斷,陷入了“一個人,沒有同類”的寂寞中。而聶隱娘在被嘉信公主收養后,也喪失了自己的原初身份,在失去親情之前,她又因為田季安已經和元氏女定親而失去了愛情,在背負了刺殺任務時,聶隱娘早已失去了自我。嘉誠公主和聶隱娘都是極度孤獨之人,悲鳴而死似乎成為她們唯一的命運。只是在面對“鏡”時,聶隱娘開始了對自我的凝視和反思,終于找回自我,完成了對自我主體的塑形,即結束自己的刺客身份,與磨鏡少年經由新羅歸隱東瀛。而這也充盈了磨鏡少年這一幾乎沒有臺詞的人物形象。磨鏡少年來自倭國,與聶隱娘原本語言不通,但聶隱娘看到了磨鏡少年為小孩微笑磨銅鏡的場景,瞬間滌除心塵,從有礙突破到了無礙,磨鏡少年就是聶隱娘這一只“青鸞”的“鏡”,只是聶隱娘這只青鸞最終選擇振翅飛走。
(三)敘事的留白
在意境美學中,留白是極為重要的。留白原為書畫藝術中,以“空白”為載體,進一步渲染出美的藝術手段。在《刺客聶隱娘》中,電影的留白是多種多樣的,如各種點到即止的鏡頭:精精兒面具的掉落代表了激戰后聶隱娘取得了勝利,鳥群驚飛暗示了幕府中人在林中馳騁,聶隱娘后背衣服的撕裂,代表了她也為精精兒所傷等。電影省略了大量本可以成為奇觀的打斗過程,體現出一種淡泊至簡的美感。更值得一提的是,聶隱娘少年時代,曾在田季安生病時緊張地注視他,因為田季安被定下了和河洛元氏的婚事而成為棲于樹梢的“鳳凰”,甚至去元家大打出手的情節,這些本是極具戲劇張力,甚至對于觀眾理解劇情極為重要的情節全部被電影省去,而改為由田季安對愛妾胡姬講述。觀眾與隱在簾幕之后的聶隱娘一起傾聽,加上聶隱娘將內心的五味雜陳隱藏在沒有表情的面孔下,使得電影顯得平淡不少,也使得部分觀眾無法理解為何聶隱娘母親說公主“屈叛了窈娘”后聶隱娘掩面痛哭。而也正是在這各種留白之中,電影進行的始終是一種向內聚斂的敘事,即讓觀眾關注的始終是聶隱娘的心靈世界,而非娛人耳目的、熱鬧的各種斗爭。聶隱娘對“我”的找尋,對既定命運的突破,以及她一次又一次地在窺視和偷聽中,愈發不忍和拖延對田季安的刺殺,這種深邃微妙的心靈體驗,才是侯孝賢希望觀眾領略的。
正如侯孝賢所言,《刺客聶隱娘》是一部他“拍給自己看的電影”。可以說,《刺客聶隱娘》并非觀眾所習慣的、符合觀眾審美期待的武俠電影。侯孝賢有意摒棄了如張藝謀、李安等導演在武俠片中常用的商業元素。盡管愛情、政斗、武打都存在于《刺客聶隱娘》中,但電影并不以一波三折、情天恨海的兩性情感糾葛,聲勢浩大、令人炫目的打斗場面來吸引觀眾,而是高度重視在內容及表現形式上意境美學的營建,豐富、擴充著人們對于武俠電影的理解。在《刺客聶隱娘》中,觀眾得以看到“俠”文化和唐傳奇故事的一種以山水寫意,以風聲抒懷,以蟬鳴為詩的新的講法,而浮躁的當代中國電影市場,也多了一種可貴的美學坐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