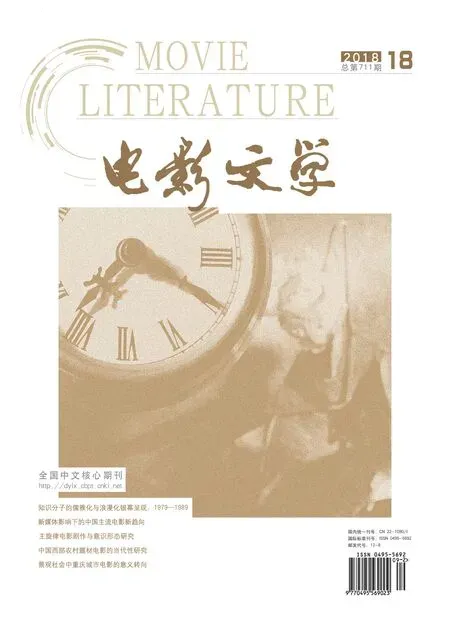“軟硬電影”之爭的文化闡釋
劉 昊
(遼寧大學 文學院,遼寧 沈陽 110036;黨建文匯雜志社,遼寧 沈陽 110006)
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電影界出現了一場在當時乃至當下也極具影響的電影理論之爭,這場在當時堪稱為電影理論問題的最大論爭是左翼文人和“第三種人”“自由人”之間的“對峙和互滲”在電影領域的持續和延展。論戰雙方分別是左翼電影批評家與“軟性電影”論者,其論爭之激烈、規模之龐大、成果之豐富,對當下探析中國電影走向和電影理論問題具有深遠意義。從當下視角檢視中國電影“軟”“硬”之爭,從實踐維度探析“軟硬電影”,可以為中國當下電影事業發展走向提供新思路;從理論維度上回歸對電影本體的思考,更有利于厘清中國電影的發展脈絡;從藝術維度解析這場爭論的歷史價值與局限,可以重現其歷史進步意義和現實啟迪作用。
一、“軟硬電影”之爭的社會語境
近年來,“軟硬電影”之爭又一次站到文藝批評的前沿,成為文藝理論界和電影史學界的一個熱點話題。研究者力圖擺脫政治和意識形態視角,想從電影本體的立場出發去重新檢視這一歷史事件。李今在《海派小說與現代都是文化》中認為,這是一場電影社會性與娛樂性的爭辯,是文化消費主義和文化工具主義之間的爭論。在《百年中國電影理論》的序言中,丁亞平則提出,這是一場影戲論和影像論、娛樂論的另類式美學交鋒。酈蘇元認為,“‘軟性電影’論是中國電影歷史上一個復雜的理論現象,需要我們以今天的眼光并聯系過去的歷史來重新認識和評價它”。那么,想要還原出這場論爭的真正面貌,我們首先要回到論爭發生的現場,厘清20世紀30年代初期電影理論領域的基本局面。
1930年3月,“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并將“文藝大眾化”的方針確定為邁向電影界的行動綱領。1931年“九一八事變”和1932年“一·二八”事變之后,中國文化界尋求救國救亡之道、啟蒙民眾心智的呼聲空前高漲。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左翼文化運動也開始加大力量投入到電影實踐中。隨后,夏衍、鄭伯奇、錢杏邨等具有中共黨員身份的左翼文藝工作者進入電影領域,在“左翼戲劇家聯盟”的領導下組建了左翼影評隊伍——影評人小組。從1932年5月開始,影評人小組借助上海各大報刊的副刊作為其批評發聲的主戰場。1932年7月,左翼影評人創辦了自己的影評雜志《電影藝術》。可以說,左翼影評人在1932年一年間就幾乎占據了上海所有的電影評論陣地。1933年,左翼電影的實踐創作也達到了高潮,史稱“中國電影年”。在“軟”“硬”之爭開始前,左翼電影人在理論批評和電影實踐上均未受到明顯的阻礙和打壓。
1933年3月,由新感覺派創始人劉吶鷗創辦的電影理論雜志《現代電影》,作為左翼電影的對立面橫空出世,為“軟性電影”論者提供了戰斗堡壘和輿論陣地。其代表人物劉吶鷗、黃嘉謨等人在《現代電影》雜志上陸續發表電影理論批評文章,劉吶鷗認為當下中國電影最嚴重的詬病就是“內容偏重主義”;黃嘉謨提出“電影是軟片,所以應當是軟性的”“電影是給眼睛吃的冰激凌,心靈坐的沙發椅”等軟性論調,與左翼影評人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抗衡。1934年6月,唐納連續發表了《太夫人》《“民族精神”的批判談軟性電影論者及其他》兩篇文章,尖銳地批評了“軟性電影”論調,以此打響了“軟”“硬”之爭的理論反擊戰。以夏衍、王塵無、魯思、唐納為代表的左翼影評人開始密集撰文聲討“軟性電影”論,系統闡釋了左翼電影理論思想,針對“軟性電影”論調展開了有力回擊。從1933年開始到1935年結束,再到之后電影創作上的不斷糾葛,這場論爭幾乎貫穿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左翼文化運動進入電影實踐的整個時期。
二、“軟硬電影”的文化訴求
無論“軟性電影”與“硬性電影”的文藝觀、電影觀如何,都不能離開當時特定的文化語境,革命文藝與商業文化的雙生與互動是順應歷史文化潮流發展的必然。“軟硬電影”文藝訴求的碰撞與交互有效推動了我國電影和文化事業的發展,以當下文化視域再次檢視仍不乏進步意義。
首先,電影本體論的問題是“軟硬電影”論戰的一個關鍵性問題。左翼影評人認為在民族危亡的關鍵時期,電影應該成為階級斗爭和爭取民族解放的強大武器。王塵無強調:“電影是階級意識的反映、階級斗爭的武器。”魯思也認為:“電影決不是什么玩意兒,它是一種教育,一具武器——比槍炮更有力的武器。”可見左翼影評人賦予了電影崇高的使命,把“武器論”“工具論”作為其電影觀,認為電影應當承擔揭露社會黑暗現實、對民眾進行階級意識塑造,實現民族救亡之功能。
左翼影評人“武器論”“工具論”的電影觀緣于中國傳統的文論觀。“文以載道”規定了文藝要肩負著宣傳和教育大眾的使命光環,判斷文學藝術價值高下的重要標準就是有益于世道人心。同時,受蘇聯電影理論的影響。“電影必須經黨之手,使之成為社會主義啟蒙及鼓動的有力武器”等論點被左翼影評人反復引證,用以證明電影對大眾的教化作用。總之,左翼影評人的電影觀是建立在政治與藝術的關系上的。
作為“軟性電影”論旗手的劉吶鷗并沒有從政治和意識形態視域對左翼影評人進行批判和攻擊,而是從電影藝術基準的角度來強調電影的藝術屬性。劉吶鷗受日本新感覺派影響,很早便開始研究西方電影理論,他在《中國電影描寫的深度問題》中認為,電影是科學(光化學、工學)和藝術結婚的混血兒。在《影片藝術論》一文中,他重點論述了電影的本質問題、蒙太奇思維以及對歐洲先鋒電影和蘇聯“電影眼睛”學派的分析,并把電影的機械要素作為電影的美學思想核心。劉吶鷗認為蒙太奇思維是電影藝術的生命,應該運用其特性去創造電影藝術之美,如畫面組接、鏡頭角度、聲音處理、字幕等方面,將理論視點擺在了電影的機械性和藝術性上,從而一再強調“美的觀照態度”。另一位“軟性電影”論者黃嘉謨則是從電影的娛樂屬性入手對左翼電影進行攻擊,其批評程度更為直接和激烈。黃嘉謨批評左翼電影人“硬要在銀幕上鬧意識,使軟片上充滿著干燥而生硬的說教的使命”,他在《電影之色素與毒素》一文中說道:“好好的銀幕,無端給這么多主義盤踞著。”黃嘉謨更多的是從接受美學的理論視角去分析電影與觀眾的關系,認為應該拋掉一切說教的主義,讓電影藝術用其藝術技巧自由發展以達到娛樂觀眾之功能。
其次,在內容形式與藝術傾向方面,“硬性電影”重內容與“軟性電影”重形式成為論爭的焦點。劉吶鷗、穆時英等人受到日本文藝思潮的影響,認為是形式而不是內容決定了作品的價值,“怎么樣描寫”比“描寫著什么”更重要。穆時英指出:“電影藝術存在于它的形式上,而不是存在于它的內容上,只有形式是把電影和別的藝術區別開來的,內容與形式的關系相當于精神與物質的關系,物質可以脫離精神的存在。”“軟性電影”論者批評左翼電影不講究藝術形式,只是一味的、填鴨式的向觀眾灌輸“主義”。
在當時的社會語境中,左翼電影看重電影的內容主要基于三個方面:一方面,當下的民族危機和緊張的政治形式促使左翼電影相對忽略了電影的形式問題,而更加注重電影的內容。左翼影評人反復論爭在民族危機的嚴峻時刻,應該暫時放棄對藝術上的精益求精,即使以犧牲影片的藝術性為代價,也要去拍攝有利于解決民族危機的影片;另一方面,中國傳統文論向來比較重視文學藝術的內容,強調形式和內容是互相依存、互相影響的,但強調內容是主,形式為輔;再者,夏衍等左翼影評人普遍接受了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文學觀,這些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從一個側面影響了他們的創作觀念。
1935年,穆時英發表了《電影批評底基礎問題》一文,認為電影的批評基準應該是傾向性和藝術性的二者結合,即社會價值與藝術價值的二者統一。只有這樣,才能決定其評價。穆時英針對左翼影評人的電影藝術理論偏頗又發表了《電影藝術防御戰——斥掮著“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的招牌者》的電影理論文章,該文長達4萬余字,分成20多次發表于《晨報》上。雖然在史料記載中少有提到,但因其涉及了哲學、美學等大量的理論闡述,不僅能指出左翼電影理論的問題,也能為自己的觀點找到理論依據,這對我們當下系統、客觀地研究“軟性電影”理論和新感覺派文學都有著十分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盡管劉吶鷗、黃嘉謨、穆時英等“軟性電影”論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攻擊過左翼電影,堅持強調電影的藝術屬性和娛樂功能,但他們在批評過程中所采用的基準、立場和見解皆存在著明顯的差異,使“軟性電影”論在不同時期呈現出不同程度的偏重和特點。
三、“軟硬電影”文藝觀的當下價值
同樣的大眾文化語境在不同的階段會有不同的社會熱點,并產生不同的商業賣點,這些“政治傾向”“社會熱點”及“商業賣點”對于不同階段的電影仍然具有值得借鑒的價值。通過對“軟硬電影”文藝觀的分析,重新審視電影的本質屬性,在當下文化語境中獲得啟示。
第一,政治立場與商業屬性的博弈。這場“軟硬電影”的論爭,由于雙方政治立場的不同,進而導致了對文藝觀念等方面的本質差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左翼影評隊伍是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的,秉承現實主義文藝精神,把電影作為革命的宣傳武器。他們是以作品是否反映社會疾苦,抨擊現實黑暗作為其唯一價值標準。而“軟性電影”論者多數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其中還包括了一些具有政治色彩的文人墨客,他們對當時社會的認知出發點必然會與左翼影評人相左。但從藝術理論和當下意義來看,在這場論爭中,“軟性電影”論對中國早期電影理論框架的建構和發展是具有重大價值和歷史意義的,對中國左翼電影批評在一些藝術理論問題上的局限和不足進行了拓展和彌補,這一點是不可回避,也是值得肯定的。“軟性電影”論者在政治立場與商業屬性中堅守藝術,避免了中國電影完全偏向政治或完全商業化,他們的電影實踐在當下的作用仍是不可忽略的。
第二,社會熱點與消費價值的融合。在20世紀30年代的社會語境中,民族矛盾成為社會的主要矛盾,也是社會的焦點,所以民族解放、革命運動等進步的社會思想可以極大程度地感染受眾;所以具備此特質的左翼文藝觀念更加符合當時的消費語境;所以當時的電影制作公司與左翼作家合作,將“救國救民”作為電影的核心亮點,并通過商業包裝,做到社會熱點與消費價值的有機融合。
第三,文藝指向與文化語境的平衡。立足當下理論視域,反觀這場“軟”“硬”之爭,不僅可以從藝術理論維度對20世紀30年代中國左翼電影進行再梳理、再研究,還可以對“軟性電影”論者的電影藝術論進行再認識、再評價。在特定的文化語境下,雙方在論戰中不僅明確了電影的文藝指向,也對中國早期電影理論的建構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這場電影理論論爭對于我們全面了解左翼文化運動,系統研究中國早期電影理論以及重新評價在“軟硬電影”論爭中所建構的電影美學觀都提供了有力的理論參照和史料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