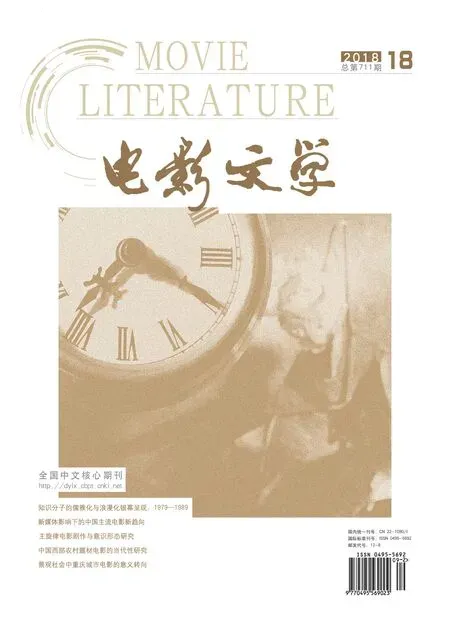論《芳華》的青春敘事
張倩玉
(中國藝術研究院 電影電視藝術研究所,北京 100029)
馮小剛新作《芳華》獨特的敘事背后的豐富意蘊讓我想到了先鋒文學,尤其是長于描寫苦難與殘酷的那些作品,雖然嚴歌苓從未被劃為這一流派。這種對苦難和苦痛的表現使影片受到了不少非議與“誤讀”。我認為,電影《芳華》講述了一個關于失敗和失落的故事,這一主題及其講述方式體現出這一電影文本的文學性與現代性。
劇作方面,普遍遭到的質疑是人物塑造的“缺失”與“模糊”,我要說的第一點就是這種對人物形象的不滿,某種程度上或許是人物形象過于特異引起了觀眾情緒上的反感。兩個主要人物劉峰和何小萍與我們熟悉的“好人”形象大相徑庭。一方面,作為英雄“候補”——意即他們只是渴望成為英雄人物卻沒有成功,他們露出了“舞臺背后”的東西,展現出他們過于強烈的對于當英雄的渴求,更不用說這渴求甚至被表現得略顯病態(tài)。這兩個人物并沒有在一開始就把“真愛”“正義”等當作信仰來追求,從而使自己區(qū)別于或說高于其他人,獲得成為主角的合法性。如果將這個電影看成青春片,那么這樣處理會變得合理一些。他們還年輕,生活還沒有把真正的價值完全展露給他們,他們也毋須做出關鍵的選擇,一些小的惡意可以解釋為幼稚。在這個意義上,可以接受將本片與《陽光燦爛的日子》做對比。
還有一種典型的批評針對馮小剛所屬的“大院”傳統(tǒng),《芳華》里的青春不是普通人的青春等。這種觀點只對了一半,在那個年代,這些軍人是天之驕子,只有無憂無慮的他們才會去嘗試當時被社會集體所禁忌的事情,也就是談戀愛,并甘愿為此付出代價。另外,文工團也有很多象征意義。《芳華》很強調回顧的視角,方式就是蕭穗子的旁白,或許可以將之和貝托魯奇的《戲夢巴黎》對比。許多人說《芳華》拍出了時代感,文工團和越戰(zhàn)的題材確實涉及歷史,但似乎僅是背景,《戲夢巴黎》則有更多時代和人的互動與互為因果。
“五月風暴”的眾多前奏之一包括法國電影迷占領電影資料館的“朗格盧瓦事件”,《戲夢巴黎》的主角就鎖定三個迷影青年。其中一對孿生姐弟伊莎貝拉和馬修仿若藝術的化身,深情而天真,他們自己甚至不知道他們早已彼此相愛,一個美國青年的到來打破了他們含混的烏托邦。美國青年先是和姐姐相愛,隨后姐姐發(fā)現了她內心對弟弟深藏的情感。他們三人經歷了友誼、性和藝術,但將這些都拋棄了,姐弟倆最終選擇了他們愛的烏托邦——死亡。在美國青年夾雜嫉妒的激將之下:“你們只會說,為什么不去加入革命呢”;在對亂倫之愛絕望之后,姐弟倆手拉手投身火光熊熊的街壘戰(zhàn),留下震驚之后悵然的,失去了愛情和友誼的美國青年站在原地。他目送姐弟倆離開,仿佛看著自己的青春和理想遠去,背景音樂是皮亞芙的《不,我不后悔》。我認為影片贊美藝術與愛高于一切,甚至高于革命。年輕就是懵懂甚至有些墮落的,他們的犧牲可能并無崇高的目標或不僅為了理想,也可能是走投無路,即便這樣也是美的,因為那是不可重來的青春,美感就在于迷茫。
回到《芳華》,除了“抓豬”一段介紹了時代,影片中看不到更多革命年代的“街景”,導演似乎有意將這群人和時代隔絕了。這種隔離感在《戲夢巴黎》里也有,但側重表現的是主角三人和其他人的隔絕,而不是主角和時代。而《芳華》則是一種環(huán)境和時空的區(qū)隔,仿佛文工團和外面的人同在一個時代又不在一個時代。我以為時代問題就是理解這個電影的關鍵。
題材方面的禁忌或許是個問題,被略去背景的革命和戰(zhàn)爭之外,劇情重點有一部分轉移到了當代生活,這使劇作分成了前后兩部分。表面看似乎“斷裂”了,但如果我們的前提是分析既成文本,而不認為它是“有問題”的,那么現在這個兩段式的文本就可以作新的理解。簡言之,表現那個火紅年代的生活經驗或許不是這個片子的真正意圖。一個重要線索就是“文工團”這個影片的表現對象,它是一個集體,也是一個特殊的場域和空間。普通大眾并不了解文工團是怎樣的,好奇從一開始就支撐了影片。換句話說,文工團才是本片的“主角”,影片敘述了文工團的樣貌以及文工團的解散;而電影后半部分對文工團解散后的展現,就是為了進一步說明文工團是一個怎樣的存在。
那么“文工團”到底是什么?影片一開始的時代是“文革”,文工團跳《草原女民兵》,舞蹈表現的是“文革”之前的戰(zhàn)爭年代。問題在于戰(zhàn)爭已經結束了。戰(zhàn)爭過后,人們卻還沉浸在戰(zhàn)爭的美學中。這也可以部分解釋文工團外面正在發(fā)生的事——無盡的酷烈斗爭在戰(zhàn)爭之后延續(xù)著,從肉體蔓延到精神,又返還到肉體。而文工團里這些人免于社會上的事件,被藝術庇護,被“特權”庇護,他們是否就得到了幸福?通過小萍的遭遇可以得出,答案是否定的。時代的創(chuàng)痛波及每一個人,通過小萍這一個角色已經可以見證時代。小萍深夜給父親寫信,長鏡頭深深“注視”她默默哭泣的臉,這是比舞臺上的光鮮形象更真實和高貴的人性之光。這個鏡頭需要在時代背景下去看,如果對當時的人性扭曲沒有認識,就會覺得這是一個不必要的煽情。我欣賞這個固定的長鏡頭,它有很大的張力,表達了清晰的價值觀。馮小剛的作品不乏煽情,但這一次因為有時代的深沉底色而真正落實了。
當小萍和劉峰相繼遭遇生活的創(chuàng)傷后,他們來到了戰(zhàn)爭的流放地。在戰(zhàn)場上,劉峰才擁有了成為一個真正英雄的時刻,而他自己卻未必意識得到,觀眾也未必會發(fā)現。他從沼澤里救出了戰(zhàn)友的時候,這一段可以看成整個電影的“題眼”。劉峰一只手臂受傷,拼盡全力也無法救出戰(zhàn)友,眼睜睜看著他被污泥淹沒,他痛苦得撕心裂肺;終于,其他戰(zhàn)友及時趕到,大家合力拉出了沼澤里的戰(zhàn)友。這一段表演戲劇性充足,含義也很豐富。劉峰在這時哭了,不只是因為救出戰(zhàn)友的高興、慶幸、后怕等復雜情緒,還有一層象征是他看見了他信仰的東西——集體主義是有用的,從而重新確證了因為不公的遭際或許已不自覺開始動搖的信仰。他救了別人,也救了自己。影片最后,劉峰終于在愛情上也無私了,他和小萍在一起也是一種成全別人,盡管是互相成全。劉峰整個人生的失敗是一種對時代的嘆惋,同樣地,受盡苦難的小萍也是一位犧牲者。在今天的時代講述這樣兩個人的故事,我認為表現出了一種正視歷史和悲憫的態(tài)度。雷蒙·威廉斯在《現代悲劇》中提出“令人悲傷的無序狀態(tài)及其解決”就是悲劇,現代的社會革命與危機屬于悲劇,需要被審視并給予審美上的關注。
從慘淡的結局反推,戰(zhàn)爭才是男女主角人生的高潮。戰(zhàn)爭的作用就是為我們“篩選”出劇中真正有信仰的人,也就是劉峰和小萍這樣的人,或許還有戰(zhàn)地記者蕭穗子。值得注意的是,她同時也是最留戀文工團的人,她的情感全部寄托于此,標志就是她在離開文工團的同時失去了愛情。蕭穗子是文工團的一個象征,所以被稱為第三個“主角”。從主題來看,其實劉峰和蕭穗子這兩個人才是本片真正的主角,因為他們都經歷了刻骨銘心的失戀。
說他們倆是主角還有一個原因,只有這兩個人兼具了劇中人和旁觀者兩重身份,和作者/導演的視角合一,他們理解了一切,原諒了一切。何小萍則不具備這樣的動作,她從頭到尾都被傷害,只有一個主動的反抗就是拒絕演出,而這之后,她不得已在臺上進行舞蹈表演的片段在影片中被刪去了。如果不把她看成主角,那么這樣的刪除就是合理的:她的拒絕有沒有產生效果,或產生了怎樣的效果并不重要。她只是苦難與折磨的象征,是對時代的批判。《歸來》的女主角沒有清醒過來,小萍卻忽然痊愈了。她痊愈之前的最后一個鏡頭是她在草地上的獨舞,劇情上這里缺乏交代,也缺乏說服力。或許可以理解為身體記憶喚醒了她對于從前的記憶,并最終幫助她克服了戰(zhàn)場上的創(chuàng)傷。
影片這樣的處理確實有些“以意逆志”,文學性強而合理性不足。我的理解是她跳的那支舞是當年和劉峰搭檔跳的,那之后劉峰就離開,她從此失去了自我,這是她的第一次創(chuàng)傷,后來在戰(zhàn)場上層疊的心理創(chuàng)傷壓垮了她。她的瘋狂是有根據的,但她的痊愈過于象征性,說明這個人物只能算作功能性人物。另一個具象征性的人物是林丁丁,她拒絕劉峰這個情節(jié)也是作品的關鍵情節(jié)。她“惡心”的感覺放到全片主旨來看也是一種象征。高尚的、精神性的存在忽然顯露出身體的、本能的東西,林丁丁感到巨大的沖擊,這種體驗其實是面對商品時代的社會巨變時大眾的共同體驗。從這一細節(jié)也可以看出,影片前后兩部分內容是呼應的。
劉峰和蕭穗子的戀愛,或者說“表白——失戀”就是本片主線,因為和文工團關系最密切。對于《芳華》表現幾個時代的目的,這里提出一個假設。《草原女民兵》表現的是戰(zhàn)爭年代的事,非戰(zhàn)爭年代只能對之懷戀,“文革”時,文工團將那些青春少年隔絕在現實的殘酷之外,使他們沉浸在對上一場戰(zhàn)爭的懷舊中,并樹立信仰。這之后,劉峰和小萍真的去經歷了戰(zhàn)爭,對劉峰們來說,這戰(zhàn)爭不算殘酷,反而是他們夢想成真、變成英雄的時刻。更殘酷的其實是這場戰(zhàn)爭之后的當代生活,血腥的戰(zhàn)爭反而成了最后一段可以懷舊的時光。懷舊就是一種救贖,歷史是戰(zhàn)爭和非戰(zhàn)爭狀態(tài)的交替,只有懷舊的烏托邦可以寄身。
失戀的青春、流血的戰(zhàn)場仍是美的;失去青春,沒有了夢想,沒有夢想成真或破滅的機會的平淡生活才是最可怕的。劉峰和小萍以及蕭穗子繼承了文工團的懷舊機制,并將懷舊的對象替換為真正的戰(zhàn)爭。因此他們始終成功將自我隔絕于現實之外,他們心中是戰(zhàn)爭年代的血與淚,情與義。其他團員則對文工團沒有那么深的感情,也就是說這種懷舊沒有進入他們的骨髓,因此他們要接受生活的摧殘。況且,其他團員懷的是文工團的歌舞表演里戰(zhàn)爭想象的舊,劉峰和小萍懷的是真實戰(zhàn)爭的舊,后者的信仰因確證而真實。《芳華》有一組概念是可替換的,使這部電影具備了完整性和可闡釋性,它們是:革命—信仰—青春—愛情—美—真實。
《草原女民兵》和紅歌都是對戰(zhàn)爭年代之“真實”的致敬和緬懷,目的并不是想要回到戰(zhàn)爭年代,而是回到純真與信仰。其他團員沒有見過那足以產生信仰的戰(zhàn)爭/愛情,只有劉峰和小萍以及蕭穗子經歷過,不管多么慘痛,只要是真實的就是有價值的。跳舞的蕭穗子和小萍令人印象深刻,因為那是靈與肉的合一,是對青春的贊頌。蕭穗子是用青春的熱情去相信,這種先驗的熱情能穿越時光直抵彼岸;而穿病號服的小萍則是重新選擇相信早在文工團時期就開始失落的信仰,將無形的信仰用身體彰顯于草地夜空。同時,他們倆也是愛情的失敗者和始終不渝的信仰者。以上就是《芳華》的主題,即對于愛情理想和以戰(zhàn)爭為表征的青春理想的歌頌在影片敘事中的表現。
文工團員們對歌舞里沒有見過的戰(zhàn)爭年代的贊美和回憶,以及對于這一段回憶戰(zhàn)爭的年代的回憶造成了幾重距離。這不是有意地遮蔽某些年代,而是通過距離強調純真年代的美好可貴與難以觸及,通過懷舊的失落來召喚懷舊,甚至美好本身。與此同時,這種距離也顯示出一種懷疑主義傾向。懷舊既已是一種“逃避”,對革命年代的召喚更略顯小心地止于對于它的懷舊的召喚,這是含蓄還是懷疑?此外,如果和美好相伴生的是暴力,應如何看待?影片并未做出很好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