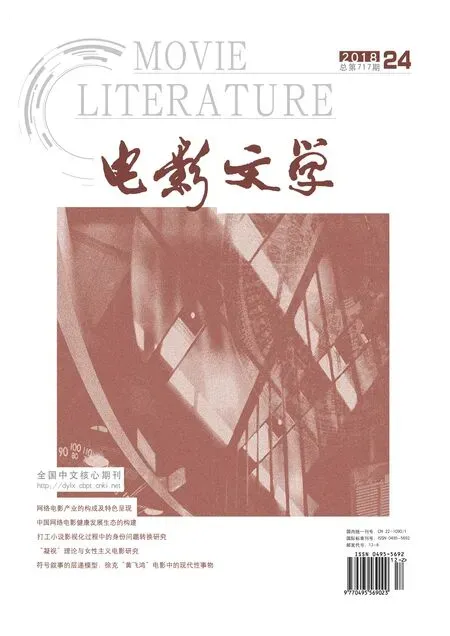從《影》看張藝謀的人性影像書寫
王麗霞
(安陽職業技術學院,河南 安陽 455000)
在結束了《長城》(2016)與好萊塢的合作,難以接受對方的制片人制度的張藝謀回歸自己得心應手的國產電影創作語境之下,交出了《影》(2018)這一答卷。相比觀眾早已熟悉的,張藝謀慣常運用豐富色彩、恢宏場面等,《影》在影像上以黑白色調為主,雖然也有戰爭場面,但都保持了一種分寸感,視覺美學被用以服務于人性的刻畫,全片體現出了張藝謀別出心裁的探索。
一、水墨風格與人性審視
從創作緣起上來說,《影》的誕生本來就與主創對人性話題的關心密切相關。張藝謀直言,《影》的靈感來自黑澤明的著名電影《影子武士》(1980)。在《影子武士》中,武田信玄臨死時要求部下將自己的死訊隱瞞三年,為此原為竊賊的替身就扮演了三年的武田信玄。這促使張藝謀開始思索為何國產電影中還沒有一部有關替身的作品。也正是出于強烈的,對表現神秘而有趣的替身題材的興趣,電影才幾乎完全改變了原著《三國·荊州》的敘事框架和設定,講述了一個全新的故事,即沛國大都督子虞自小就收養了一位替身,為其取名為境州,其目的就是一則讓境州幫助沛國收復境州,二則讓境州協助自己篡權奪位,自己取代庸懦無能,瘋瘋癲癲的沛王君臨天下。
在將敘事重心定位于替身之后,電影就有了剖析人性的必要性。毫無疑問,境州的人生是被動的。他自幼生活在境州,境州還有他念茲在茲的老母,但是他不得不來到沛國國都,以子虞的身份生活,雖然享受了子虞的榮華,但是也承擔了子虞的種種痛苦、危險與屈辱,包括子虞因為身上有楊蒼留下來的經久不愈的刀傷,境州也要被活生生地割出傷口。更令境州感到進退兩難的是,他意識到自己已經愛上了子虞的夫人小艾。與《影子武士》中的武田信玄已經死去不同,子虞卻是以自囚密室、半人半鬼的方式活著的,他依然在控制和監視著境州。境州究竟應該繼續做“影子”?還是做“真身”?又如何做“真身”?他的無奈、困惑就成為電影審視人性的出發點。
由于境州從普通的境州少年到成為一個“假子虞”的過程與結果都是充滿算計和陰謀的,因此電影才會選擇使用由黑白灰三色組成的水墨式的影像風格。張藝謀認為,這種簡易的色彩對比反而能說明人性的復雜性,灰色正是在水的暈染下產生的具有豐富層次的顏色。因為在電影中,沒有人可以用單純的好壞來定義。女主人公小艾是境州溫暖的來源,做替身的這么多年,正是對小艾的思慕讓他堅持了下來,但小艾夾在真假子虞之間,既是幫助子虞迫害境州的幫兇,又因為終于與境州發生關系而有了對丈夫的背叛,讓子虞極為惱怒。楊蒼之子楊平作為年輕人在電影中是美好、希望的象征,他個性單純,陪伴父親殺敵保國,然而他的輕敵自大,口口聲聲讓沛國長公主給自己做妾,也傷害了素未謀面的青萍,導致自己最后與青萍同歸于盡的悲劇結局。因此,沒有人屬于徹底的黑或白,每個人都游走于中間的灰色地帶,利用他人或被他人利用,傷害他人再被他人傷害。電影并不專門著力揭露人性中丑陋的一面,拷問他們靈魂深處的“罪惡”,讓觀眾對人性光明面的希望破滅,也無意于為了呼喚美好人性而樹立“高大全”式的人物,對觀眾進行說教。電影只是以影像直觀地呈現出人性的困境,讓觀眾自己完成對自我的啟發與引導。而電影中的人性困境,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替身帶來的身份認同與精神癲狂問題。
二、身份認同與精神癲狂
在《影》中,戰亂改變了社會格局,人的身份因為戰爭而發生分化和重組。以境州為例,他在被子虞割出傷口并上藥時交代了自己的身份,即原本為境州的平民,困頓之極幾乎餓死而為子虞所“救”,不得不用這種方式來對子虞報恩。事實上,境州曾經多次企圖逃跑,但總是被抓回來毒打,境州終于在威壓之下徹底放棄自己的原有身份。如今,境州的母親依然留在境州,但是因為沛、炎兩國的對峙,境州無法與這個自己在世界上的唯一親人團聚。境州脫離了故鄉的群體力量,也失去了親情的支持,在沛國因為頂替了子虞的身份,他也無法擁有正常的人際關系。田戰在知道眼前的都督并不是真都督后對待境州的態度就有了轉變。這就使得境州的精神風貌也發生了變化,他既渴望能夠從“影子”變成“真身”,從而名正言順地與小艾在一起,但境州又深知活著的子虞不可能允許他這么做,同時他也心存僥幸,希望能夠在幫子虞打敗楊蒼后就回歸境州老母身邊做一個普通人。不能選擇自己的生存狀態也就使得境州失去了純白無瑕的人性。在電影中,與子虞在地下比武之時,境州身穿白衣(在小艾臥室一旁蜷曲獨臥的境州也是一襲白衣),這代表他其時天良未泯;個性陰暗的子虞則一身灰衣,身形枯瘦。然而在朝堂之上,境州殺死子虞和沛王,讓自己由“影子”轉正而為“真身”后,他的身份由暗到明,衣著也由白到黑,此時的境州實際上已經和子虞在外貌和內心的陰暗上都完全重合,電影在直觀的人物造型上,表達了境州為自己設計的第二個身份。
與境州同為鄧超飾演的子虞,則是精神癲狂的典型形象。子虞在將無辜的境州的身體馴化為自己奪權謀利的工具時,他其實也是在自我折磨與摧殘。由于身中楊蒼刀傷,子虞日益骨瘦如柴,氣息微弱,但為了追求權力與利益,他讓境州代替自己活躍于世人面前,讓境州去面對楊蒼與沛王,自己則自囚于密室之中,窺探境州與自己妻子的親密接觸,久而久之陷入一種失常的精神狀態中。與之類似的還有沛王,沛王與子虞之間是螳螂捕蟬的關系,沛王早已猜測到眼前的“子虞”并非其人,但每日故意裝瘋賣傻,佯作不知,專等境州收復后就去都督府殺死真子虞。在子虞迷失自我的同時,沛王也為自己扮演了一個替身。兩人在形象上都是寬袍緩帶,披頭散發,舉手投足之間也搖搖晃晃,毫無身居高位者應有的整齊利落形象,這體現出的是在對權力的爭奪中,二人都日益偏執直至最終瘋癲。除了人物造型、陰暗的用光,電影中從未止歇的、令人煩躁的雨,一方面與軍事行動有關,另一方面也是境州、子虞、沛王等人邪念引導的象征。
張藝謀曾表示:“對人性的挖掘,是一個電影的目標。電影的目標就是要挖掘人性,這是我的最高目標。”“耐心的人就會仔細在那里品味。”從《滿城盡帶黃金甲》(2006)、《金陵十三釵》(2011)到《歸來》(2014),張藝謀從來沒放棄過在電影中進行人性的刻畫,以人性的復雜,以及人在各種變遷浮沉中的人性變化等來打動觀眾。在《影》中,張藝謀又一次開掘了對人性的表達空間,電影中影像成為電影人直面人心、言說人在身份認同中的困惑、在欲望誘惑下的精神癲狂等狀態的重要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