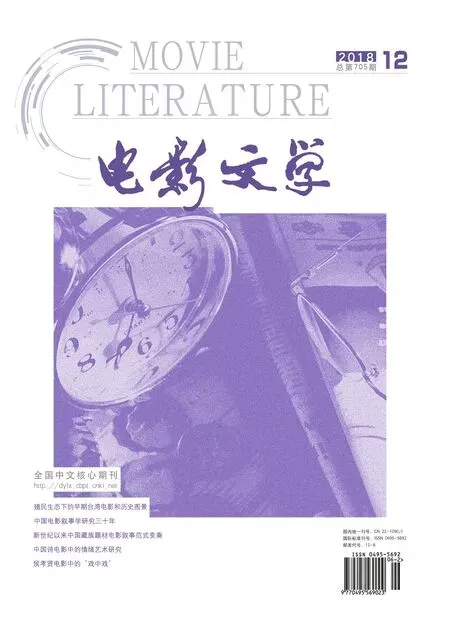英美兒童電影中的現實主義色彩解讀
袁 璽
(河南經貿職業學院 外語旅游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0)
兒童電影在其內容、目標受眾群上都有著與其他類型電影不一樣的規定,出于服務少年兒童的目的,兒童電影的內容一般為兒童(或擬人式角色)的生活以及人物的內在精神。為了更好地吸引兒童觀眾的注意力與興趣,大多數兒童電影都會為觀眾創造出一個具有幻想意義,充滿童趣的世界,以讓觀眾能夠在輕松愉快的情緒中接受電影,實現內心矛盾的調節和緩解,最終得以平衡、健康地成長。
而也正是兒童電影的這種幻想、童趣的表征,往往使人忽略了其中蘊含的現實主義色彩。然而,兒童電影自誕生便是與現實主義密不可分的。兒童電影脫胎于兒童文學,而兒童文學的創作本身就有著明確的干預現實、關注人類未來的精神。這一點并不因影像技術的加入而改變。正如巴贊所指出的:“現實主義首先是一種人道主義,其次才是一種導演風格。”部分兒童電影中的現實主義,正是以一種近乎人道主義的態度,而非一種藝術形式或風格存在的。
一、對時代的觀照
現實主義作為一種文藝思想,并非單純的教條和概念,而是與時代緊密相關的。隨著時代的不斷發展和變化,現實主義作品也必須調整關注和表現的客觀對象,以及創作中的主觀思想觀念和情感狀態。脫離了時代意識,作品也就難以引發觀眾的共鳴。
以《納尼亞傳奇1:獅子、女巫和魔衣櫥》(2005)為例,電影通過魔衣櫥連接起來的是兩個世界,一個是被邪惡女巫統治的納尼亞王國,另一個則是正面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陰影的現實世界。正是因為躲避戰火,露西等四個孩子才會被送到鄉下,發現魔衣櫥。露西等人進入納尼亞后,與牧羊神和雄獅亞斯蘭并肩作戰,打敗了邪惡女巫,使納尼亞復國成功。這一故事實際上就是對現實世界中反法西斯力量對抗法西斯的投影。一開始孩子們不愿意直面女巫,隱喻了英國在二戰前期對德國的綏靖政策,雄獅正是英國的標志之一,亞斯蘭的死隱喻著倫敦遭受的大轟炸,在此之后,孩子們終于站穩了堅決的反抗立場,亞斯蘭復活,而英國也在與法西斯作戰到底后走向了重生。與之類似的還有如直接以1941年的上海為背景的《太陽帝國》(1987),美西合拍的,直接表現了法西斯軍官殘酷折磨異見人士的《潘神的迷宮》(2006),講述了德國軍官之子和猶太人男孩友情的《穿條紋睡衣的男孩》(2008)等。電影都帶有非常明顯的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代的指涉,主人公的行為是對在二戰中遭受傷害的人們的一種情感支持或心靈慰藉。
并且,時代性并不能簡單粗暴地與在青春電影中常見的時尚、潮流等概念等同,而由于兒童電影熱衷于向童話故事取材,因此其故事往往是與當代都市五光十色的時尚生活有一定距離的。福柯曾經指出,最重要的并不是故事所講述的年代,而是故事被講述的年代。換言之,盡管故事本身有可能是發生在過去的,故事中的主客觀要素都有陳舊、古老的一面,但是創作者如果擁有一種當代的意識和立場,從當代的角度來對過去進行審視,那么“故事所講述的年代”再遙遠,也能叩動“故事被講述的年代”的觀眾的心靈。以《美女與野獸》(2017)為例,電影根據法國作家博蒙夫人創作的同名兒童故事改編而成,博蒙夫人生活于18世紀,而她創作的故事則采集自更早的民間傳說,因此,就故事本身的年代而言,貝兒和居住在城堡里,有著王子身份的野獸離觀眾是遙遠的,但是在貝兒這一人物的身上,電影注入的是一種當代精神氣質。貝兒身為女性,被以加斯頓為代表的鎮民們視為不該接受教育的對象,當時女性的人生被與結婚生育緊密聯系在一起,然而貝兒卻熱愛閱讀和幻想,一次又一次地去鎮上借書,即使鎮民們投來不屑的眼神,貝兒也毫不在意。而在被軟禁在城堡之后,貝兒最后心甘情愿地留下來也是因為野獸擁有一個龐大的圖書館,滿足了貝兒如饑似渴的求知欲。可以說,貝兒是一個超出了其所處時代,更接近于當代價值觀的女性,這也正是貝兒的可愛之處。《愛麗絲夢游仙境》(2010)中拒絕公子哥哈米什求婚,向往到更廣闊的世界中去實現夢想的愛麗絲也屬于此類人物。
二、對社會內部的洞察
現實主義的內在要求之一就是必須具有社會性,即如韋勒克所說,現實主義描寫當代社會,并且在描寫中體現出作者洞察社會內部規律,展現社會內部結構的尖銳眼力。高楠也曾指出:“根據規定嚴格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現實主義創作的根據就是揭示一定的歷史發展本質或歷史發展規律。”可以說,現實主義面向的是社會而非個體,盡管就具體作品而言,敘事是著落于個體的,但是個體遭際的背后反映出的往往是社會的一角,并且這一角的呈現出自主創的有意為之。
例如,在《查理和巧克力工廠》(2005)中,威利·旺卡挑選五個幸運小客人的方式,對于極度貧困,一家七口人蜷縮在一個搖搖欲墜的破房子里,連巧克力也買不起的查理來說,是不公平的,而家境優越的孩子可以為了得到金券而買下數輛卡車的巧克力。在進入了神奇的巧克力工廠后,查理和另外幾個孩子在經濟階層上的巨大差異更是暴露了出來。好在查理純真、謙虛的心,成為打開這座樂園最高塔樓的鑰匙,而金錢和功利心則腐蝕了另外幾個孩子,使貪婪、蠻橫的他們喪失了繼承巧克力工廠的機會。又如改編自羅琳同名小說的《哈利·波特》(Harry
Potter
)系列和《神奇動物在哪里》(2016),電影也對社會癥結進行了尖銳的諷刺,電影批判的是社會中無處不在的低效腐敗的官僚機制。《哈利·波特》中的魔法部拒絕承認伏地魔的復活而是撤了堅稱要抵抗伏地魔的鄧布利多的校長之職,派來一位只會無休止地開會、體罰學生,以嚴酷政策來鎮壓一切挑戰她的權威之人的魔法部副部長管理學校。《神奇動物在哪里》中的美國魔法部對于麻雞和魔法世界之間的隔閡也采取“一刀切”政策,使魔法師們在“第二塞勒姆”前處處被動。與之類似的還有如表現了由于律師的陰謀,皮特的房屋遺產權遭受侵占,而被迫搬家的《反斗神偷》(1997);父母艱難地經營著馬戲團這個已經陷入危機的家族產業,母親又在表演中病倒的《魔鏡面具》(2005);主人公杰西在學校里總是受到同學的欺負,在家也難以得到父母的寵愛,加上家庭貧困,杰西只能穿姐姐的跑鞋,以至于終日郁郁寡歡的《仙境之橋》(2007)等。兒童在進入一個美好奇幻的世界之前,他們遭遇的,給他們帶來巨大打擊的經歷都是現實的。
而同時需要指出的是,現實主義的社會性并不意味著個體性要被打壓。反之,個體在現實主義創作中,不僅是人們接近社會的一個介入點,同時,個體也是成就現實主義的多元性的關鍵要素,成功的現實主義體現出來的無不是個體生活與宏大的社會歷史進程之間復雜的、交互的影響。正如匈牙利美學家盧卡契所指出的,人在立體的社會現實中,與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因素相互作用,而現實主義正是要辯證地表現這種互動。如《了不起的狐貍爸爸》(2009)中狐貍爸爸所面臨的中產階級中年危機,正是當代社會中常見的,能令觀眾會心一笑的。
三、“白日夢”與真實的協調
早在20世紀50年代,美國電影人就有了電影是當代最好的娛樂的意識,也正是在這一意識的影響下,在好萊塢電影中,認識現實,解決現實中的嚴肅、深重的社會問題,或進行國家意識形態的宣傳,都是要讓位于電影的娛樂目的的。正因為好萊塢電影能夠不斷地給觀眾提供做“白日夢”,即脫離現實,獲得夢幻般的愉悅享受和體驗的機會,電影的商業價值才不斷得以實現。這種娛樂主義電影觀也很快在全球化的,消費主義下的電影格局中影響到歐洲乃至全世界,以至于出現了大量電影的娛樂性凌駕于其思想性、審美性之上的現象。
而如果說商業時代下的電影給人們創造的是“白日夢”,那么兒童電影則無疑是“白日夢中的白日夢”。無論是兒童抑或成人觀眾都不難意識到,如《小鬼當家》(1990)中,父母將年僅八歲的孩子凱文遺忘在家中,而凱文能夠憑借自己的聰明機智和對家里構造的熟悉,戲弄兩個剛剛出獄的竊賊,不僅自己未傷分毫,還讓對方大為狼狽,這是脫離現實的一種美好想象;又如《月亮坪的秘密》(2008)中,月亮公主和白馬王子的童話原來并非虛構,本是來月亮坪投靠叔叔的女孩瑪利亞能夠成為那個解開月亮公主咒語的人,這無疑也只是對兒童好奇心和善良的一種肯定。這一類電影更多的是提供給觀眾逗樂、歡笑或視覺美的震撼,是典型的娛樂產品。
但這并不意味著,兒童電影創造一個脫離現實生活本真面目的故事世界的手法和現實主義之間是格格不入的。兒童電影從“兒童本位”教育觀出發,積極向兒童傳授現實生活的法則和規律,促進兒童在現實生活中的自由發展,這本身就是對現實的關注與積極作用,是現實主義提倡的“為人生”主張的具體實踐。例如,在《獅子王》(1994)和《奇幻森林》(2016)中,草原和森林中的動物都遵循著自然法則,過著生生不息的和諧生活。如在《獅子王》中,木法沙教育兒子獅子雖然吃羚羊,但是死后尸體會變成草,而羚羊吃草;在《奇幻森林》中,動物認為大象創造了森林,在旱季,動物們為了飲水生存而停止互相捕獵。出于嫉妒或仇恨而肆意破壞這一和諧的人,如刀疤鬣狗和老虎謝利可汗,都勢必成為動物們的敵人。謝利可汗因為早年和人類搏斗時被火燒傷而要趕走狼孩毛克利,否則就要在雨季大開殺戒,讓動物們無法順利飲水。最后刀疤和謝利可汗都落入了被火燒死的下場。電影所傳達出來的一是生態主義觀念,二則是一種以和諧穩定為上,各司其職的社會規律,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彼此尊重和包容。刀疤、謝利可汗因為私利而觸犯他人利益的行為,善良的辛巴、毛克利被迫離開家人,就是真實社會矛盾的一種變形。除此之外,擁有兒童身份的辛巴和毛克利在離開原來家庭的庇護之后,一路上得到朋友或導師的幫助,歷經艱險、誘惑和欺騙等,最終完成了對自我身份和能力的認同,這類情節的設計,無疑也承擔著教育、鼓勵兒童的使命,自強、感恩等抽象的內容被融合進浪漫的動物世界的故事中,讓兒童更好地理解和接受。與之類似的還有如《沃特希普高地》(1978)、《夏洛特的網》(2006)、《野獸家園》(2009)等。電影在充分發揮電影假定性的同時,并非忽略了電影應有的真實性,其內容依舊是兒童觀眾認識現實的一個階梯。這可以視為兒童電影在其“白日夢”形式與現實主義精神之間的一種協調。
越來越多的人注意到,兒童電影與國家或民族的文化歷史、與主創對社會的體認有關,兒童電影不應該止步于低幼童趣故事的影像化,而應該被視為具有現實主義意義和深度的作品,視為人文價值的載體,這既是提升兒童電影藝術地位的必由之路,也是兒童電影向著老幼咸宜邁進,平衡不同年齡段觀眾的需求,搶占電影市場的方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