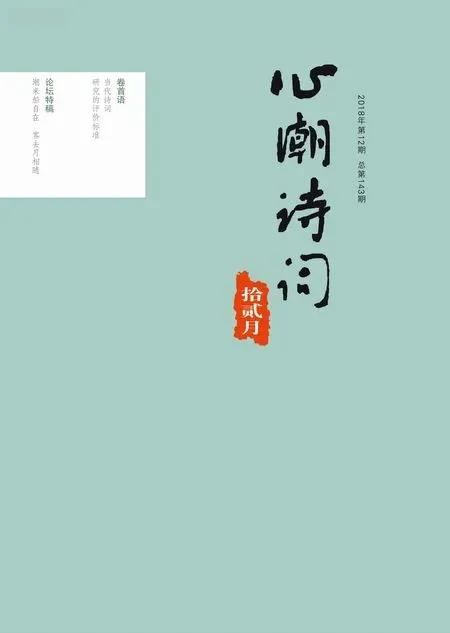星漢新邊塞詩《天山韻語》平議
為詩人星漢贏得“當代岑參”這一稱謂的,當然是他的詩集《天山韻語》中所收的那些成色上佳的新邊塞詩。《天山韻語》,作家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一印1000冊。該集作品按年代先后編排,起于1976年,迄于2005年,收各體詩作156題159首,詞作34首,共收詩詞193首。前有作者女公子王劍歌“序”,后有作者“后記”。星漢,本名王星漢,字浩之,1947年5月生,山東東阿人。12歲隨父母進疆謀生。17歲參加鐵路工作,為學徒工、信號工,歷時13年。1978年考入新疆師范大學中文系,畢業后留校任教。現為新疆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為中華詩詞學會發起人之一,曾任中華詩詞學會副會長、新疆詩詞學會常務副會長,現任中華詩詞學會顧問、新疆詩詞學會執行會長、中國散曲研究會理事。有學術著作和詩集《清代西域詩研究》《天山東望集》等20余種行世。
一
《天山韻語》如集名所示,內容構成主要是吟詠天山南北新疆地區的自然風貌、民族風情,兼及歷史遺跡、人文景觀,是一部地域色彩十分鮮明的當代舊體詩詞集。作者少小投邊,幾十年的歲月里,放足天山南北,幾乎走遍整個新疆地區,這從該集作品的標題即可見出,諸如《游天池》《絲綢古道偶成》《賽里木湖所見》《奎屯路上》《交河故城》《吐魯番過火焰山》《五家渠路上》《巴克圖路上》《賽里木湖》《伊犁河感懷》《過烏孫山》《過昭蘇草原》《輪臺路上》《過阿克蘇河》《重游克孜爾千佛洞》《過阿爾泰山》《游喀納斯湖》《題和田核桃王》《宿北庭故城》《過巴音布魯克草原》等等,新疆各地的風景人情無不為作者所攝取。從這個角度看,該集也可以說是一部新疆地區記游紀行詩詞集。
作者在表現雪山、冰川、戈壁、沙漠、草原風景的時候,在表現維吾爾、哈薩克、蒙古等少數民族地區的風俗民情、衣著長相、勞動方式、飲食習慣的時候,其實有兩個潛在的參照系、兩個潛在的參照視角:一是內地,二是江南。作者所著力凸顯的,正是內地、江南與邊地、西域的差異。在差異中,顯示出新疆地區獨特的自然景觀和人文風貌。這幾乎是一種潛意識活動,但卻無疑在最深層次上支配了星漢的全部邊塞詩創作。作者筆下的這些自然風景,是內地尋常看不到的:“一鷹驚去疾如箭,射落殘陽一捧紅”(《絲綢古道偶成》),“一片板橋殘月,幾堆鄂博輕幡”(《西江月·喀納斯河畔》),“沉靜兩山開碧落,奔忙一水送金雕。穹廬簾啟青蒼入,花草風來赤白搖”(《沿喀納斯河》),“怒吞落日地將裂,狂扯飛云天欲傾。萬里黃沙聚復散,千年白草死還生”(《過魔鬼城》),“長牽瀚海胡楊路,遠借冰峰夕照天”(《庚辰秋重游水磨溝》),“塞外新秋,我又重來,笑倚雪山。正冰峰直上,青天湛湛。瀑流傾下,白浪懸懸。荒草攔腰,閑云遮路,不放游人再溯源。回眸處,瞰松林氈帳,犬吠雕盤”(《沁園春·重登喀納斯湖觀魚亭》),“敲石馬蹄沖寂靜,破云鷹翅掠蒼涼。清愁都阻穹廬外,一片殘陽抹大荒”(《過巴音布魯克草原》)“未歇紅花,未老黃花,已放雪花”(《沁園春·癸未重九初雪晴后賦此》)。作者筆下的這些生活場景,是內地尋常看不到的:“驢車歸處,炊煙漸起,葡萄新熟”(《桂枝香·高昌故城懷古》),“掀簾少婦抬頭處,景色都收蒙古包”(《山中雨后》),“坦腹巴郎游泳后,拖泥帶水笑騎驢”(《開都河農家小坐書所見》),“試馬柳蔭揚策,捉羊河岸開刀”(《西江月·喀什巴扎》),“崎嶇山路盡,木屋自成群。奶茶新碗溢,羊肉大爐焚”(《白哈巴村小駐》),“系馬穹廬外,圍爐酒正酣”(《癸未冬游天山水西溝》),“葡萄架下煮磚茶,寫字巴郎帶看瓜”(《伊犁農家》),“避日行人來飲馬,長天風過笑聲憨”(《戈壁即事》)。作者筆下的這些聲音,是內地尋常聽不到的:“彈唱聲中草色青,牧人馬背拄頤聽。多情阿肯未終曲,俯看湖中云已停”(《巴里坤湖邊觀阿肯彈唱》),“短笛風低荒草,大杯酒映新秋”(《西江月·喀納斯湖聽潮爾笛》),“知無人到喇嘛睡,時有清風誤撞鐘”(《昭蘇圣佑寺》),“驚人何處潑天雨,卻是松濤笑欲癲”(《松下偶眠》),“山骨高撐千仞外,蒼鶻一聲遙沒”(《念奴嬌·登鐵門關樓》),“鞍橋穩坐牧鞭指,夕照群羊渡水鳴”(《托什干河即目》),“日夕牛羊下,月高兒女歌”(《游烏什柳樹泉夜宿》),“草野翻邊曲,松濤走戍鼙”(《宿天山緑野山莊》),“黑石高堆舞彩旌,夕陽垂地起邊聲”(《過烏倫古湖祭鄂博》),“莫道歸程多寂寞,穹廬外有馬蹄敲”(《天山水西溝夜話》),“石裂有聲頻入耳”(《己卯夏登冰達坂》),“星墜冰峰裂有聲”(《尋他地古道,宿天山大龍溝口》)。作者筆下的這種長相妝扮,是內地尋常看不到的:“樹蔭碧染絡腮胡,一馬輕蹄意態舒”(《吐魯番書所見》),“碧眼銀須飄拂處,胡楊木火烤魚香”(《尉犁羅布人村寨書所見》),“過街長辮步如舞,飲酒虬髯杯似澆”(《過庫車》)。作者筆下的這種風味氣息,是內地尋常聞不到的:“氈帳白煙紅日遠,奶茶香味阻征程”(《過和布克賽爾草原》),“水去游人流影俏,風來烤肉帶歌香”(《自京歸后次日登紅山》),“牧人歸處斜日晚,一縷清風馬奶香”(《果子溝》)。作者筆下的這些路遇,是內地尋常不可能發生的:“相逢哈薩克,閑話夕陽遲”(《快活林》),“晴煙遙指處,氈帳又新家”(《南山遇哈薩克老牧人閑話》),“新貨囊裝握牧鞭,馬韁輕勒跨歸鞍。重逢我問新居地,笑指松青云起山”(《巴扎逢哈薩克牧人》)。以上這些斑斑可數的描寫,都為內地讀者提供了不曾寓目的異域風光,不曾領略的風俗民情,強化了作品的地域風格特色,增添了作品的可讀性與吸引力。
潛在視角雖然隱藏于潛意識中,但也有浮出的時候,比如《詠沙棗花》二首之二:“不羨春風桃李枝,揺香莫道此時遲。離人贈別何須柳,沙棗攀來慰遠思。”中原自古以來有折柳送別之習俗,這里寫贈以沙棗花,正見出與內地不同的地域民俗風情。《過魔鬼城》云:“冷雨熱風經此城,登高四顧一身輕。怒吞落日地將裂,狂扯飛云天欲傾。萬里黃沙聚復散,千年白草死還生。縱然西去再西去,不羨江南鶯燕聲。”《石河子北湖觀魚亭二首》之一云:“春光此地舊曾諳,四望新秋意又酣。白雪山頭紅日壓,藍天云影碧波涵。棉田戀我猶懷抱,雁陣隨風正漫談。景自豪雄心自壯,何須出語比江南。”上引兩首詩的尾聯,兩處出現“江南”意象,雖云“不羨”“何須比”,西陲的狂風松濤自異于南國的鶯吭燕舌,邊塞詩中的盤空硬語自異于南國詞中的秀媚軟語,但江南盤踞胸臆,形成覽景觀物志感時揮之不去的參照視角,亦屬顯而易見。《石河子北湖觀魚亭二首》之二云:“石城北望路深諳,湖蕩清波飲已酣。踉蹌雪山能倚賴,粗疏原野盡包涵。掌收落日休輕放,胸納回風可暢談。又見橫秋遠征雁,心隨健翅欲圖南。”此詩終于借遠征雁翅,道及荒寒之地居留者的“圖南”深層心理。歸根結底,潛意識中可能還是覺得山青水綠、風景如畫的“江南好”。作者一不小心之間,透漏了些許企羨江南的隱秘消息。
二
該集中的詠史懷古、登臨憑吊之作,也值得特別拈出。《登額敏塔》《交河故城》《臨江仙·登巴克圖瞭望塔望域外》《桂枝香·高昌故城懷古》《念奴嬌·伊犁河感懷》《滿江紅·登格登山》《蘇木拜河西望》《登惠遠鐘鼓樓評志銳》《香妃墓》《水調歌頭·臨霍爾果斯河》《重登格登山》等都屬此類作品。不消說,這類作品中滿溢著作者的盛衰興亡之感嘆,如《桂枝香·高昌故城懷古》所寫:“殘城故屋。展歷代興亡,教我披讀。聞說車師五戰,山凝遺鏃。法師駐馬談經日,縱腸空,氣通天竺。侯姜威猛,戈揮雪止,馬蹄輕速。 登臨意,如城高筑。借莽蕩邊風,輸情千斛。遠望荒原一抹,無言翻綠。斜陽潑血依山久,見流霞天外如瀑。驢車歸處,炊煙漸起,葡萄新熟。”除了盛衰興亡之感嘆,便是這片特殊的地緣所喚起的民族意識和國家意識,如《滿江紅·登岳公臺步岳飛韻》所寫:“人去臺空,英雄氣,沖霄未歇。豁眸處,遠荒翻浪,晚風正烈。凝碧天山吞落日,揚塵大漠銜邊月。看江山一統共金甌,情何切。 馬嚙石,旗卷雪。千帳里,燈明滅。想戈挑泉出,劍揮山缺。蓋地青松懸鐵甲,接天蒲海盛忠血。使絲綢古道貫輿圖,通京闕。”若依照通行的說法,上引詞作中表現的就是愛國主義思想情感。對大一統的追求,對祖國領土完整的維護,對安邊開疆的古代英雄豪杰的追懷贊美,對近代以來失去的領土難以割舍的牽念之情,是這些作品的主要內涵。再看一首《臨江仙·登巴克圖瞭望塔望域外》:
雪嶺霞消碧落,春原草吐清波。牛羊背上夕陽多。炊煙繚繞處,是我舊山河。 一段人間老話,百年總駐心窩。南來征雁半空磨。隨風猶北去,不去又如何。
這種情感橫亙胸中,耿耿于懷,成了作者難以開釋的強固的心結。大一統意識和家國天下意識,是傳統士大夫文人的深度潛意識,該集作者顯然也是念茲在茲。《登額敏塔》云:“彩云翻似向東旗,大漠金戈寫史詩。登塔我來凝望久,藍天盡處是京師”,仿佛古代文人“心存魏闕”;《赴京途中作》云:“輪臺唐韻壯,送我玉關東。鐵路車來嘯,碧天鷹去空。群山抹殘日,大漠鼓長風。收拾三千里,相攜進故宮”,隱約似有“收拾舊山河,朝天闕”之意;可能都是潛意識心理,在詩作中的不自覺流露。還有《謁尤素甫墓》:“西域多才俊,書開千古香。名聲滿宮闕,文采動君王。泉涌連思路,云來接翰芒。君看吐曼水,依舊續詩行。”頷聯借對十一世紀維吾爾族詩人的贊美,折射一種以詩詞文采干動天聽的人生理想,這正是傳統中國社會讀書人的千古文人夢。
該集中的題詠詩也頗有可觀。這類詩多是七言絕句,多用比興寄托手法,一個自稱“粗豪”、常以“雄豪”的超我面目示人的強者,在這類詩中不時回歸本我,展示真實的面目性情,袒露真實的內心世界。這類詩作雖然使用比興手法詠物,但借此手法傳遞出的往往是創作主體惆悵、憂思、困惑、感慨等較為個人化的心理情緒。佳者有《新疆鐵隕石》《吐魯番過火焰山作》《邊塞清明》《坎兒井水》《過沙漠胡楊林》《經沙漠公路重到民豐》《昆侖山中拾得五彩石數枚,感賦》《泛舟布倫托海》《駱駝刺》《沿布爾津河賦向日葵》等。看一首《駱駝刺》:“根穿大漠向天爭,每借逆風抒性靈。寂寞千年堪自慰,老來依舊愣頭青。”這應是一幅托物寓己的自畫像;再看一首《昆侖山中拾得五彩石數枚,感賦》:“深埋無語不知年,剖腹昆侖現大觀。今日蒼天何用補,依然西北伴寒山。”借賦昆侖彩石,發“棄材”之慨嘆;還有《過沙漠胡楊林》:“飛沙起處任顛狂,自耐天涯四月涼。就簡刪繁也如我,苦撐詩骨向蒼蒼。”則喻示自己那一份時常刷在臉上的西部漢子的標準“酷”相,是“苦撐”出來的。于是便有了《望海潮·謁馬赫穆德喀什噶里墓》下片的心跡展露:“我來捧獻心香。有詩情未老,意氣猶狂。夜夜青燈,年年白飯,幾人識得文章。囤貨拜行商。納賄爭金印,君試評量。握筆明朝歸去,依舊寫蒼涼。”在“猶狂”的意氣中,流露出的是詩書生涯不諧于時的落寞蒼涼之感。
內心的柔軟處既被觸及,《解連環·游千淚泉寄楣卿》《塔什薩依沙漠書楣卿姓名》《重游千淚泉》等純粹私人化情感的抒寫,也就為情所不免。看一首《解連環·游千淚泉寄楣卿》:“路平沙軟。正蒹葭涌綠,小溪清淺。夕日下,身度春云,看冰泄雪消,石飛崖爛。一揖情生,思往事,血騰心顫。使悲風斜落,驚走群鴉,老樹歸晚。千年月光荏苒。奈人間兒女,尚縈幽怨。縱夜夜,魂托疏星,恨無賴天雞,夢成虛幻。寄盡愁腸,卻每每,薛箋嫌短。料這番,開書念我,淚泉萬點。”透過詞作追懷的傷心往事,可以窺見作為普通人的作者的真實而柔弱的人性悸動。由此聯系《雪中五家渠郊外獨酌》一詩:“獨步頻將野店敲,天山已慣酒杯澆。寒林風嘯雪花舞,攪合詩情到九霄”,可知借酒助興或者借酒澆愁,對久居邊塞的作者來說,已是慣常,詩句亦豪邁,亦惆悵,亦無奈,亦凄涼,一旦卸下“雄豪粗獷”的超我人格面具,作者內心的真實感覺到底如何,在此已是不言而喻。該集末首《上元烏魯木齊郊外泥飲,用荊公戲呈貢父韻》云:
縱是清光萬里同,天涯無意待春風。
馬鳴荒草河聲外,人醉穹廬月影中。
寒樹能扶青眼客,雪山莫笑白頭翁。
心隨大野長流韻,不向東君怨不公。
此作雖亦寫景,但主要目的應是寫心,首尾兩聯,透漏出作者感慨命運的深度心理。曰“無意”,曰“不怨”,不過以曠達聊作排遣而已。作者以此首為詩集殿后壓卷,當有深意存焉。
三
在《天山韻語》的詩詞文本中,出現最多的意象是鷹雕、雪山、冰峰、大漠、黃沙、駝鈴、馬蹄、牧人、牛羊、草原、穹廬、落日、殘陽、紅柳、胡楊、沙棗等,這些地域性鮮明的意象構成的景物畫面,具有某種不可移易性。如《克孜爾水庫》前兩聯“西指龜茲路,大堤橫巨垣。高收千嶺峻,遠納五河喧”,所寫是西域高原、龜茲古道旁的大型水利工程,這個水庫滿蓄木扎提河、喀普斯浪河、臺勒維丘克河、喀拉蘇河、克孜勒河五條河流之水。再如《游克孜爾千佛洞》:
胡楊樹下暫停征,東望龜茲一日程。
碧水長流接天渺,黑雕直起與云平。
石門彩畫窟風冷,古寺青崖夕照晴。
指點南山春草綠,穹廬歸騎牧煙輕。
漢魏以降,佛教傳播日廣,洞窟開鑿各地多有,但有“胡楊、黑雕、穹廬、牧煙”等意象在場,有“東望龜茲一日程”的地名里程時限,這一處佛窟就有了確定無疑的地域歸屬。又如《過沙漠公路》:“今日有勞方向盤,迷濛劃破指和田。遠沙風里推千浪,大路空中掛一弦。喇叭鳴時沖碧落,日球墜處濺黃煙。昆侖山下良朋待,夜煮冰川火正燃。”所寫的是西域沙漠公路風景,“和田”、“昆侖山”的地名,“遠沙風里推千浪”、“日球墜處濺黃煙”、“夜煮冰川火正燃”的戈壁沙漠景觀,斷不可移作它處看覷。再看一首《天山阿爾薩溝小飲》:
相逢初歇馬,氈帳便傳杯。
雕翅卷云過,松梢喚雨回。
千山收亂水,一澗放輕雷。
天外虹霓起,彎腰遠作陪。
雖曰“氈帳小飲”,亦復豪氣干云,與古典詩詞中經常寫到的長亭餞別之類“帳飲”的纏綿感傷,大異其趣。要之,該集詩詞擷取的是邊塞風物,不是內地風物;是西北邊塞風物,不是其他邊塞地區風物;是新疆天山南北風物,不是西北陜甘寧青邊地風物。該集不可移易的地域風格,鮮明特色,突出個性,就體現在這里。
該集詩詞的主體風格是豪邁雄奇。這種風格幾乎滲透在作者攝取的所有題材里面。這是他的《沿額爾齊斯河》:
拘束城垣久,今朝可放歌。
紫雕盤大漠,紅日逐長波。
晴雪峰頭遠,雄風馬背多。
行行盡詩句,不必費吟哦。
劉勰《文心雕龍·物色》云:“若乃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得江山之助乎!”今觀星漢此詩,正是“得江山之助”的形象寫照。雪峰大漠,紫雕紅日,馬背雄風,即目所見無非是詩,這俯拾皆是、不費吟哦、自然得來的“詩句”,風格自然豪邁雄奇。在這一片神奇的地域上,不僅強大之物豪邁,柔弱之物也同樣豪邁:野花“見人來,彈露猛開紅萼”(《賀新郎·乙卯夏登觀魚亭》),馬蘭“情豪不慣小籬笆,遠隨奔馬向天涯”(《達坂城見馬蘭花作》),沙棗“猶搖鐵馬裂云風”(《赤亭》),紅柳面對“地號天吼”的大漠狂風,“畏懼何曾有”,在“飽看滄桑”之后,神貌依舊,不失娟娟秀色(《點絳唇·詠紅柳》);不僅男人豪邁,女人也同樣豪邁:“馬蹄蕩處大荒開,三兩女郎香抹腮”(《阿圖什書所見》),“飲馬姑娘風落影,英姿隨浪到伊犁”(《雅馬渡書所見》);不僅成年人豪邁,小孩子也同樣豪邁:因“家居邊塞”,而生小“自有雄豪態”(《清平樂·春日將小女劍歌登妖魔山》)。作者忽而感覺自己的詩句掛在鷹翅上:“性情瞻馬首,詩句掛鷹翎”(《再過荒漠》),忽而感覺自己的詩句掛在胡楊樹上:“胡楊老去也新芽,似我詩句高掛”(《西江月·雨中游胡楊河》),忽而感覺自己的詩句被金雕銜去:“頗奈金雕翻健影,盡銜佳句剩無多”(《阿勒泰樺林公園尋詩》),這樣的詩句怎能不雄奇豪邁!當作者酣飲,飛瀉的瀑布是酒:“我出穹廬抬醉眼,狂流似向酒杯傾”(《白楊溝觀瀑》),涌流的大河也是酒:“何必穹廬愁酒盡,簾掀即放大河來”(《布爾根河邊痛飲》)。古代詩人豪放如太白,如《將進酒》所寫,亦需當掉裘馬換酒;作者只需掀簾放進大河即可,真可謂千秋飲豪,一世之雄也。當作者豪情涌起,任是鄰國邊界也關不住:“黃蘆一陣邊風起,吹送豪情過界河”(《登哈巴河鳴沙山》)。豪邁雄奇,正是該集的主體風格,重要特色。
豪放雄奇之外,作者亦能寫淡遠意境,如《宿查干郭愣,無寐,踏月賦此》:“星斗巡檐月遠明,情懷暗向小河傾。雪山淡影風吹樹,遙聽穹廬犬一聲。”或寫悠閑情調,如《西江月·伊犁河南岸逢故人》:“摘得西坡熟豆,抱來南畝新瓜。伊犁河水煮清茶,人在葫蘆架下。 只說一生難見,眼看三落春花。相逢今日莫思家,消盡天涯初夏。”或寫透徹理悟,如《西江月·浴烏倫古湖》:“目送紅霞百里,手推碧浪千層。冰峰吹下晚風輕,思緒盡傾無剩。 我本身心無垢,但來一洗癡情。沙灘回首看經行,已被清波抹凈。”或寫隨遇而安,如《鵲橋仙·天山菊花臺路上》:“林蔭染首,清風爽口,野闊花繁草厚。書生老去眼昏花,直認作前程錦繡。 雪山寒瘦,松溪急驟,不盡白云蒼狗。變牛作馬又何妨,落得個荒原睡夠。”凡此足見作者長才,擁有多副筆墨手腕,這些顯得“另類”的作品,皆對該集邊塞詩詞的總體風格構成某種補充、豐富與調劑。
四
從古今詩學承傳的角度看,該集無疑是以岑參等人為代表的古代邊塞詩、西域詩之現代嗣響新聲。作者本是歷代邊塞詩、西域詩方面的研究專家,在創作過程中自當別有會心,對之多所汲取吸攝。《沁園春·重登喀納斯湖觀魚亭》下片云:“區區恩怨如煙,更遠拓詩疆隨牧鞭。想揮風送韻,江河聯句。行杯對日,泰華張筵。兩宋蘇辛,三唐李杜,振羽誰曾至此間。微吟罷,但憑高酹酒,總覺清寒。”作者對自己“遠拓詩疆”頗為自信,以為李杜蘇辛所未及。從題材內容上看,作者所寫確已突出李杜蘇辛之范圍;但在美感風格上,作者承繼的正是李杜、高岑、蘇辛的衣缽。太白之豪放,子美之沉雄,常侍之悲壯,嘉州之奇峭,東坡之超曠,稼軒之猛鷙,共同鑄成了作者的詩膽詞心。該集邊塞詩把當代舊體詩詞的陽剛風格推向極致,豪邁、雄奇、壯烈、粗獷乃至生猛,但不打油,不諧謔,作者終不失端人莊士、意氣書生之本色。
與古代邊塞詩相比,因作者生活在邊烽盡熄的和平年代,且留居邊塞,所以少去了邊塞征戰場面的描寫和征人思婦之情的抒發,多出的是時代生活發展、科學技術進步帶來的新鮮經驗和體驗,如《甲申人日自烏魯木齊乘機赴伊犁,下望天山》所寫:
談笑乘風逐日西,亂峰借我布雄奇。
紅霞鋪錦巡天路,白雪翻波落照時。
點點穹廬云淡淡,盤盤古道樹離離。
前朝未必無佳作,這等情懷總不知。
乘坐飛機巡天俯瞰高山雪原、穹廬古道,這在古代邊塞詩人,是夢里也不曾見過之事,那時他們在馬背、驢背、駝背上。該集作者在萬米高空的飛機上,觀景點不同,視野和境界便與古代邊塞詩人、詩作有了巨大差異。還有《念奴嬌·戊寅夏陪馬來西亞黃玉奎吟兄登塔勒奇嶺》中寫到的風景拍攝:“歇鞭停馬,順長風遙瞰,萬壑千巖。數片寒云催白雪,渾欲吹破天藍。飛瀑砰訇,蒼松搖蕩,聲色滿征衫。夕陽西下,紫霞來掛眉尖。 非是沽酒無錢。張筵填餓眼,又有何嫌。且把相機開巨口,特許今日貪婪。如此風光,環球詩友,未必不清饞。明朝歸去,請君遠運天南。”《克孜爾水庫游艇上作》所寫乘快艇游湖:“驅艇云天外,排山破碧痕。清波涵日月,大壩列乾坤。歡語喧林末,豪飲起石根。明朝歸去路,染綠過千村。”這些都是古代邊塞詩人不曾有過的閱歷體驗,該集邊塞詩的時代色彩,借此得到彰顯和強化。
作為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崛起于天山南北的新邊塞詩的代表性詩人,該集作者總體上配得起當代岑參之評。但二者的差異,似乎能予人更多的啟示。該集作品的體裁擇取,以律絕為主,間有詞作,無長句大篇、開闔動蕩之七言古風,這是與盛唐邊塞詩代表詩人岑參的不同之處,岑參邊塞詩代表作多為七言歌行,韻位繁密,且變韻頻繁,形成急驟跳蕩的強烈節奏,加之心理上的強烈好奇性帶來的內容上的奇幻色彩,所以給讀者留下的閱讀記憶就是非同一般的陌生和新奇。該集作者多用律體,因律體講求對仗,勢必給人以某種工穩之感。而詞體容量有限,即使慢詞長調,也不過區區百十余字,不便恣肆蔓衍,騰挪跳蕩,鋪排展開,且詞句長短參差,表現邊塞題材就顯得過于細碎,力度不足,不能形成如七言歌行那般以長句為主的大面積的力量感,大面積的不懈不歇的打擊力和震撼力。作者出塞時年齒尚幼,及至成年寫詩,已是久居邊塞,雖然馳馬高山,有過“胯下群峰震”的獨特體驗,面對荒原盡處拔地而起、突兀而立的雪峰,吟出過“荒原過盡一山抽”的奇句奇字,但總體而言,外來者的新奇感覺在某種程度上已有所鈍化,不復如盛唐邊塞詩人岑參等,以內地之人乍臨邊塞,初度遭遇一片不曾夢見的異域風物,給其視知覺猝然帶來那樣一種充滿神奇的激動,化為詩篇,仍保有初遇的新鮮刺激。僅以岑參《白雪歌》名句“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為例略作剖析,就可看出,其創作心理機制實乃乍見時的新奇,直覺中的錯愕。若是土著,司空見慣,面對此景,視同尋常,審美感覺早已鈍化,這由美妙的聯想、比喻所構成的千古名句也就無以產生了。類似的這種由奇景引起乍見者新奇的審美心理體驗而生成的邊塞風景詩句,因其景物意象選取的純粹,而使得岑參等人的盛唐邊塞詩的寫景更見精彩,更為出色。相較而言,《天山韻語》的作者頗為自矜的“多年彩筆,長描西域,腕中圓熟”(《桂枝香·重九日登妖魔山》),這在一般意義上當然是長處,但過于“圓熟”,則必失生新之氣。還有邊荒曠遠地域的神話傳說元素、神秘驚悚感覺,諸如岑參《熱海行》等詩的傳奇性在詩中的缺位,也使此集邊塞題材作品的藝術魅力有所減損。
五
討論星漢的新邊塞詩,除了以岑參為代表的古代邊塞詩,還有一個參照系,就是當代的邊塞新詩。這樣,就必然會說到“新邊塞詩派”的命名問題。當代“新邊塞詩派”的概念,應該是由新詩界首先提出來的。來自西北的評論家周政保,注目當代詩壇現狀,從古代詩歌史上的“邊塞詩派”獲得啟示,在20世紀80年代初率先提出了“新邊塞詩派”的概念。他認為:“一個在詩的見解上,在詩的風度和氣質上比較共同的‘新邊塞詩派’正在形成。”(周政保《大漠風度,天山氣魄――讀〈百家詩會〉中三位新疆詩人的詩》,《文學報》1981年11月26日。)這一提法得到了西北詩人、詩評家和整個詩歌界的回應。1982年3月,新疆大學中文系就“新邊塞詩”問題召開了規模較大的學術討論會,編選并出版了由謝冕作序的《邊塞新詩選》。接著,甘肅的文學刊物《陽關》呼吁創立“敦煌藝術流派”,開辟“絲路上飛天的花瓣”專欄集中發表新邊塞詩。著名詩評家謝冕為1982年最后一期《陽關》撰寫了《陽關,那里有新的生命》的文章以示支持。1983年春天,甘肅的文藝理論刊物《當代文藝思潮》刊出了余開偉的《試談“新邊塞詩派”的形成及其特征》、高戈的《“邊塞詩”的出新與“新邊塞詩派”》等文章,回顧這一詩派形成的歷史,闡釋其特征和性質,并就這一詩派是否存在,其特征與前景如何等問題,展開了討論。此后,甘肅的《飛天》、新疆的《綠風》和新創刊的《中國西部文學》等刊物,都積極倡導、推動“新邊塞詩”運動。《綠風》詩刊1986年開辟“西部坐標系”欄目,集中刊發了15位詩人的作品和相關評論文章。“新邊塞詩”很快從新疆擴展開來,得到甘、青、寧、西等省區一些詩人的響應。對這一詩歌運動,詩壇也逐漸采用“西部詩歌”這一名稱來稱呼它。舊體詩詞界對“新邊塞詩派”這一概念的使用,時間上要晚一些,大約20世紀在80年代后期“中華詩詞學會”成立之后。可以這樣說,20世紀90年代以后的“新邊塞詩派”這一概念,本身就包含著操持舊體和新體的兩類詩人群體。只是在百年來舊體與新體互相排斥的慣性心理作用下,寫作、研究舊體的詩人與詩評家,在談論“新邊塞詩派”時,有意無意地忽略了用新詩處理邊塞題材的新詩人;同樣,寫作、研究新詩的詩人與詩評家,也往往無視用舊體處理邊塞題材的詩人詩作。
拿星漢的舊體“新邊塞詩”與當代的邊塞新詩相比,有幾點值得關注的地方。一是星漢的舊體“新邊塞詩”與當代邊塞新詩的同質性:諸如在題材內容上,建設與開拓的描寫,基本取代了以盛唐邊塞詩為代表的古代邊塞詩的戰爭生活的描寫;在感情抒發上,建設開拓的勞動熱情的抒寫,基本上取代了以盛唐邊塞詩為代表的古代邊塞詩抒寫的追求功業功名的豪情,以及征人思婦、生離死別的幽怨之情;在地域風格上,由于含納西北邊地景觀風貌和社會生活而顯示出的豪放、雄奇、悲壯的特色等;這是二者的大致相同之處。
但是,二者的差異也是顯而易見的。首先,星漢的新邊塞詩使用舊體,必然受到舊體體式的制約。由于舊體詩詞除古體外,篇幅一般較為短小,而星漢《天山韻語》一集無古體歌行,這就使得星漢的新邊塞詩,較少處理復雜、繁富的題材內容和思想感情。而當代的邊塞新詩,在語言形式的選擇上,與盛唐邊塞詩為代表的古代邊塞詩在不似之中存在著深刻相似性。盛唐邊塞詩多用七言古詩和七言絕句兩種詩體,這兩種詩體的七言句子較五言為長,在節奏上更為流轉、動宕。七古一體不僅每句字數較五言為多,而且篇無定句,篇幅一般較大,便于鋪排驅遣,自由開合,馳驟騰挪。無獨有偶,邊塞新詩在語言形式上也多用長句,意象繁密,作品的篇幅一般也比較長,不像星漢多用近體的新邊塞詩那樣簡明省凈、約句準篇,因而顯得形體延展,氣局開張,便于容受和處理各種駁雜的題材內容和思想情感。其次,在詩人的主體意識上,寫作舊體的星漢,更吻合長期宣傳提倡的主流意識和價值觀念,更多承繼傳統士大夫文人的情感心理圖式,像他的頌美烈士和領袖的作品,他的詠史懷古、登臨憑吊之作中的大一統意識,立功報主、心存魏闕的心理,以文采干動天聽的人生理想,都是在邊塞新詩中較少看到的。邊塞新詩作者,如同在新疆的周濤、楊牧、章德益,居住青海的昌耀,居住西藏的馬麗華,他們的作品諸如《神山》《大西北》《我是青年》《我驕傲,我有遼遠的地平線》《地球賜給我一角荒原》《一百頭雄牛》《青藏高原的形體》《慈航》《走向羌塘》《西部漢子》《百年雪災》等,都能將個人的坎坷命運,融入地域和民族的歷史、神話、傳說和現實生活進程,以現代人的意識,去發現和領略西部高原的社會自然、歷史文化所包含的全部豐富、復雜、悲愴,不得不承認,這些邊塞新詩代表作品,更富有現代性的反思、批判色彩,更具有內涵深度。復次,從景物描寫(或曰情景關系)上看,星漢多把邊塞的奇異景物視作單純的風景意象攝入詩中,或以之渲染烘托背景氛圍;邊塞新詩則更注重于在自然景物中融入深度人性。當然,星漢新邊塞詩的景物描寫,雖說更多是作為背景存在于詩中,為渲染烘托作品的氛圍服務的,但如前所論,他的個別篇章在景物描寫中亦寓有比興寄托之意,這是自不待言的。當代邊塞新詩中,單純的寫景或借寫景渲染氛圍的情形已不多見,寫作邊塞新詩的詩人,更注重在自然景物的觀照中揭示深度的人性內涵——人在嚴酷的生存環境中的價值尊嚴、力量信念、愛恨生死,人與自然之間的理解親和以及齟齬對立。試看周濤的《野馬群》片段:
兀立荒原/任漠風吹散長鬃/引頸悵望遠方天地之交/那永遠不可企及的地平線/三五成群/以空曠天地間的鼎足之勢/組成一幅相依為命的畫面。
自然的嚴酷,塑造出生命的強悍和生存的偉力。野馬群由于受滲入血液和骨髓的孤獨與寂寥的驅使,曾在暮色蒼茫中悄悄接近牧人的帳篷;但出于對同樣滲入血液和骨髓的自由與無羈的捍衛,又在一聲犬吠中消逝得無影無蹤。這是野馬群的性格,又何嘗不是西部人的性格?這樣的作品是寫景,是詠物,是喻人,已很難截然區分,讓人只覺得撲面而來的漠風中散發出的是濃重的人性的氣息。簡言之,寫景在星漢邊塞詩中是相對獨立的,可以和抒情和敘事等成分相區分的;在邊塞新詩中,寫景已很難單獨區分,它已和歷史、現實、社會、人性等因素糅合一處。因此,星漢的新邊塞詩中的寫景更純粹,更富奇光異彩,更富地域性;邊塞新詩的寫景則更繁復,更富人文情思色彩,更富社會性。以上所談的三點差異,既存在于星漢新邊塞詩與邊塞新詩之間;也可視為當代舊體詩人的新邊塞詩,與新詩人的邊塞新詩之間存在的整體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