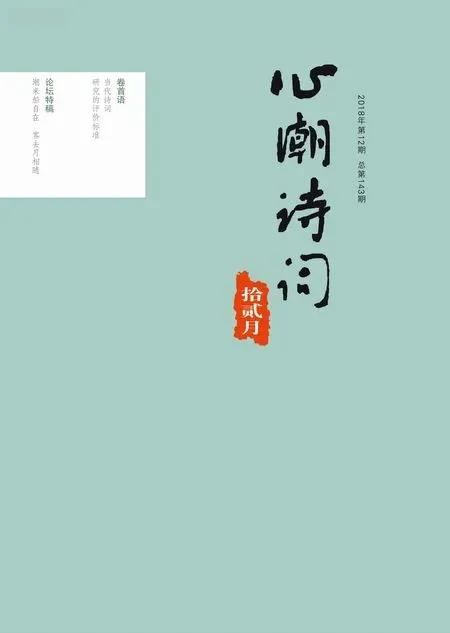舊體詩對早期新詩變革的影響初探
自晚清詩界革命以來,中國詩歌革新的試驗浪潮就一直此起彼伏喧囂不已,然而彼時詩歌改革的步伐又常令人惋惜地停留在新詞新語的簡單應用層面上,直至胡適、陳獨秀高舉“文學革命”的旗幟才真正開啟了現代中國詩歌變革的序幕。如果說1917年《新青年》第2卷第6號刊發胡適的《白話詩六首》拉開了現代中國新詩的序幕,那么1922年出版的《新詩年選》中的一段話似乎就宣告了新詩在文壇的正統地位:“胡適登高一呼,四遠響應,新詩在文學上的正統以立”。而胡適《嘗試集》的出版更是加速了白話新詩爭奇斗艷的歷史進程。從胡適號召“詩體大解放”的中國新詩草創,中經郭沫若、李金發、聞一多等新文人的多路調試,新詩在新文學的第一個十年大致呈現出“自由詩”“格律詩”“象征詩”的三張面孔,可以說,新文學第一個十年,新詩交出了一份不錯的答卷。但是,透過新詩寫作變革之因來考察新詩十年的實績,不難發現,新詩的每一次轉向都與舊詩強悍的“影響的焦慮”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換言之,舊詩成熟的體制與美學特質時時拷問并制約著新詩的寫作。毫無疑問,新詩發生期的十年,不論是“對抗”格律還是“趨律”式的回歸,舊詩在新詩寫作中或明或暗的“印痕”既是一道亮麗的風景,又是貫穿新詩寫作過程的“靈魂”式伴侶。本文試以新文學發生期的自由派新詩為討論對象,探尋舊體詩對早期新詩變革的影響,以期豐富現代中國詩歌內質要素。
出離與回返:從胡適到郭沫若的自由派對抗
1922年,距離新詩在《新青年》雜志發表不過幾年,胡適非常得意地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宣稱“《學衡》的議論,大概是反對文學革命的尾聲了。我可以大膽說,文學革命已過了議論的時期,反對黨已經破產了。從此以后,完全是新文學的創作時期”,這段豪言壯語裝扮了新文學的表面繁榮,可是倘若回首新詩發生期的艱難歷程,又不免讓人想起胡適的另一篇文章——《逼上梁山:文學革命開始了》——新詩發生期的歷程充滿了“逼上梁山”的艱辛。眾所周知,胡適赴美留學耳濡目染親身體驗到了西方文化的神奇。在民族救亡的赤子情懷驅動下,以文學來救亡、啟蒙的理念開始加速。與此同時,嚴復等人的進化論對胡適的文學革命觀顯然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在與美國友朋的詩學爭辯中以及詩歌寫作的反復親身體驗下,以白話來寫詩的想法在胡適心中越來越成熟。《嘗試集》被公認為新詩的開山之作,在文學史上的意義自不必贅言,不過,打開《嘗試集》的附錄《去國集》,翻閱新詩寫作前胡適曾經寫下的那些舊詩,其間,給人印象最深的莫過于其域外體驗在舊詩寫作中的別扭與分裂——詩中所表達的與實際想表達的場景出現了巨大的文化裂縫且難以調和,例如,《耶穌誕節歌》明明是為了敘寫胡適在美國參加圣誕節的觀感,何奈舊體詩中嚴重匱乏對應的語詞去描繪彼時的場景,所以詩中使用了諸如“明朝襪中實餳妝,有蠟作鼠紙作虎”之類的生硬句子來轉換實景的描寫,以應對舊體詩在現代場景中的寫作尷尬,而這也恰好回應了胡適自己所批評的“陳言未去”。可以說,正是因為現代文化啟蒙的需要,以及舊詩在現代語體表達上的短板,直接啟發了胡適關于文學工具革新的思路,而中西文化體驗的深厚積累正好又為胡適的新詩寫作也提供了堅實后盾,《嘗試集》的出版成功更是夯實了新詩寫作的道路。在白話新詩的創作中,胡適堅決貫徹了“作詩如作文”的詩學理念,以“詩體大解放”來推動新詩的探索與變革,比如早期發表《鴿子》《人力車夫》《一念》讀來雖然平白如話卻又別有風味,充滿了現代的情愫,一舉擺脫了舊體詩在某些時刻詞不達意的窘境。且以《一念》為例:
我笑你繞太陽的地球,一日夜只打得一個回旋;
我笑你繞地球的月亮,總不會永遠團圓;
我笑你千千萬萬大大小小的星球,總跳不出自己的軌道線;
我笑你一秒鐘行五十萬里的無線電,總比不上我區區的心頭一念!
我這心頭一念:
才從竹竿巷,忽到竹竿尖;
忽在赫貞江上,忽在凱約湖邊;
我若真個害刻骨的相思,便一分鐘繞遍地球三千萬轉!
此詩作于1917年秋冬之間,作者時在北京竹竿巷居住,突然想到家鄉的竹竿尖山而作。詩語樸實卻充滿了現代氣息,一洗板著面孔為政治說教而作的詩風。以小清新、甚至調皮的現實格調現身,在口語化的句式中借助西方科技知識將鄉愁鄉思的傳統表達予以陌生化呈現。這首詩,且不論其現代思想的表達,至少在詩歌形式上,舊體詩也難有此魄力去自由應對現代語境,估計擅長舊體詩的民國遺老也難以如此輕快、細膩地表達胡適在詩中傳遞出來的現代性體驗。還應特別指出的是,該詩在藝術手法上處理得干凈利落:以四個“我笑你”的排比句式層層推進現代情愫的表達,整首詩的節奏感很強,而分行寫作的形式也沖破了舊體詩寫作的藩籬,切合了現代閱讀求新的審美體驗。詩的篇幅雖短小,但詩中思想的表達卻很流暢,同時也回應了現代文學要突出人的這一偉大時代主題呼喚。然而,如果稍微注意一下《一念》詩中句尾之字,就不難發現,無論是“旋”“圓”還是“線”“念”都是詩人精心的韻尾安排,很顯然,這種安排終究還是逃不脫舊體詩在韻律美學訴求上內在的影響。
在胡適寫作的自由詩中還有很多此類作品,寫于1920年的《湖上》,其意境的營造與《晨星篇》非常類似:“水上一個螢火/水里一個螢火/平排著/輕輕地/打我們的船邊飛過/他們倆兒越飛越近/漸漸地并作了一個”。這首詩是與友人王伯秋夜游玄武湖時所做,雖然沒有《一念》那么明顯地追求詩韻,但細讀之下也能影影約約感受到舊體詩的味道。整首詩以“螢火”為意象,以景喻情,將傳統與現代的藝術手法溶于一首短詩之中,詩歌語言干凈凝練、意境清新典雅、淡遠含蓄。回環往復的吟詠、層層推進的韻味都令讀者難以忘懷,但這些詩都逃不脫一個共同的特點——此類新詩韻味的形成有著明顯的舊詩審美痕跡。
如果說僅僅看胡適一人的詩作尚不足以看清舊體詩對新詩影響有多大,那么再考察一下當時新詩群體的詩作,問題大概就能更為清晰。在胡適、陳獨秀、沈尹默、劉半農、錢玄同等人的影響下,以《新青年》雜志為中心,中國現代新詩開啟了多路調試的步伐。據劉福春的《新詩紀事》統計來看,僅是1917-1921年之間《新青年》一份刊物就先后刊發了如下一批新詩:《白話詩八首》(胡適)、《鴿子》(胡適)、《鴿子》(沈尹默)、《人力車夫》、《相隔一層紙》、《月夜》、《宰羊》、《車毯》、《老鴉》、《除夕》(沈尹默)、《丁巳除夕歌》、《除夕》(劉半農)、《新婚雜詩》、《雪》、《學徒苦》、《夢》、《愛之神》、《桃花》、《買蘿卜人》、《春水》、《他們的花園》、《四月二十五夜》、《月》、《三弦》、《“人家說我發了癡”》、《山中即景》、《小河》、《一顆星兒》、《散伍歸來的“吉普色”》、《D-!》、《歡迎陳獨秀出獄》、《答半農〈D-!〉》、《愛與憎》、《牧羊兒的悲哀》、《題在紹興柯巖照的相片》、《我們三個朋友》、《秋夜》、《慈姑的盆》、《夢與詩》、《鶯兒吹醒的》、《四烈士冢上的沒字碑歌》、《一個小農家的暮》、《病中的詩》。新詩僅從詩題上看就不難發現,這些詩歌整體上開始趨向了口語化。很顯然,就用詞而言,他們講究平淡、清新;在標題內容所指而言,詩作對現實生活關注得深入而貼切,敘事特征較為明顯。這一批詩歌的問世從文本實驗的角度證實了胡適所開創的新詩路徑是可取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力回應了舊體詩人群對新詩的質疑與嘲笑,盡管其間存在的問題也不少。不過,短板就是短板,早期新詩屢為人所詬病的也正于此:畢竟詩歌本是以抒情為主的藝術樣式,一旦過度追求口語化、散文化也就弱化甚至取消了詩歌的審美藝術功能。
口語化雖然開辟了新詩的一條新路,然而作為一把雙刃劍,模糊詩歌審美特質的硬傷是無論如何都無法回避的,所以,典雅深致的舊體詩對新詩所形成的焦慮日漸凸顯。簡言之,舊詩形成的審美閱讀體驗也逼迫著新詩力圖克服口語化、散文化帶來的弊端。不過,反過來看壓力也是動力,也正是因為有了舊體詩形成的焦慮才更為迅猛地推動了早期新詩的自我革新。俞平伯在寫給新潮社同人的信中,他敏銳地直陳白話詩的問題:“我現在對于詩的做法意見稍稍改變,頗覺得以前的詩太偏于描寫一面,這實在不是正當趨向。因為純粹客觀的描寫,無論怎樣精彩,終究不算好詩——偶一為之,也未嘗不可”。可見,克服一味的描寫、恢復詩歌本有的審美情趣刻不容緩。郭沫若的《女神》以及冰心、宗白華為代表的散文小詩、俞平伯《冬夜》橫空出世在新詩壇掀起的三股浪潮顯然為新詩緩解此前的焦慮帶來了新的希望。回看新詩草創之時,以胡適為代表的早期新詩寫作的窘境基本上是當時新詩人普遍困境,他們一方面大聲疾呼要打碎舊體詩的枷鎖,然而又常常不自覺地迎合舊詩的內在約束。但《女神》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早期新詩創作的尷尬,所以聞一多贊嘆:“若講新詩,郭沫若君的詩才配稱新呢,不獨藝術上他的作品與舊體詩詞相去最遠,最要緊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時代的精神——二十世紀底時代的精神,有人講文藝作品是時代底產兒,《女神》真不愧為時代底一個肖子”。郭沫若的《女神》以其氣韻生動、驚天地泣鬼神的浪漫氣息獲得了文壇廣泛的響應,而聞一多的論斷最讓新文人感到自豪的恐怕是,郭氏的新詩終于與舊體詩拉開了距離,應該說,《女神》探尋雄渾氣概的自由體詩新路令新詩面目為之一新,一洗《嘗試集》中舊體詩的明顯印痕,從這個意義上說它確實沖決了舊詩詞格律的羅網。《女神》的成功不僅因為其雄渾奔放的詩學特征,內容上美學意義上的時代氣息也引領了新詩的審美精神追求。其想象力之豐富、抒情之豪放,強力映照出了五四時期狂飆突進的時代精神。郭沫若詩中多采極富生命力的意象來增強詩歌情感表達的力量,讓時代感情的奔涌有了強力表現的符碼,而動人心魂的鼓噪力為新詩的大眾化開辟了新路。更值得注意的是,《女神》在詩歌形式上大多不講究整齊與押韻,但外在形式上擺脫了當時新詩人飽受舊體詩影響的困境,引導早期新詩逐步去除白話詩的粗糙,從而走向了真正的現代新詩。正如郁達夫所說:“《女神》的真價如何,因為郭沫若君是我的朋友,我不敢亂說,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想誰也應該承認的,就是‘完全脫離舊詩的羈絆自《女神》始’的一段功績”。與此同時,《女神》中的《鳳凰涅槃》《棠棣之花》《湘累》《女神之再生》為中國新詩的詩劇之路也打下了堅實的探索根基,郁達夫在《文學旬刊》上撰文:“我國對劇的研究本不發達。詩劇尤為鳳毛麟角——可以說完全沒有的——詩劇界得這篇《女神之再生》,做先鋒去開辟路徑,真是可喜的事”。這些同時代人所作的評論都充分說明了《女神》在當時已經取得了廣泛認可,并且為新詩變革之路做了很好的示范。
對話與圓融:從湖畔耳語到小詩心靈的探尋
當然,作為自由體詩探索現代詩歌的還有“湖畔”詩人的創作和冰心、宗白華為代表的小詩創作。但無論是翻閱動人心扉的湖畔詩歌還是閱讀頗富哲理的小詩時,一個雖顯微卻又不能忽視的特點涌現了出來——正是舊體詩的典雅意境讓作為新詩代表的小詩獲得了讀者的認同。1922年,汪靜之、馮雪峰、潘漠華、應修人在出版了他們的合集《湖畔》之后又有了《春的歌集》出版,可謂詩潮涌動。
“湖畔”詩人于新詩的貢獻更多容易體現在對情詩的勇敢抒寫,但其在人性啟蒙方面的功績顯然也不能忽視。應該說,在五四新潮的啟蒙下,“湖畔”詩人高擎愛情旗幟,強烈反對封建禮教,號召個性解放,在社會上引起了非常大的反響,同時也招致了很多批評。但廢名認為“康白情的《草兒》同《湖畔》四個少年人的詩,是新詩運動后自然的發展”,他還認為湖畔詩人的詩是“沒有沾染舊文章習氣老老實實的少年白話新詩”。的確,“湖畔”詩人大膽熔鑄中國古典詩歌的意境以及日本俳句的美妙,大膽歌唱青年人的美好情愫值得肯定,他們的詩讀來更顯得率直、清新,盡管在藝術水準上仍顯得不夠老練,但正如朱自清所言“中國缺少情詩,有的只是‘憶內’‘寄內’或曲喻隱指之作,坦率的告白戀愛者絕少,為愛情而歌詠愛情的沒有。這時期的新詩做到了‘告白’的第一步,《嘗試集》的《應該》最有影響,可是一般的趣味怕在文字的繳繞上。康白情氏《窗外》卻好。但真正專心致志做情詩的,是‘湖畔’的四個年輕人。”可見真情在新詩中的涌動對于恢復詩歌的審美抒情功能極為有益。不過,以汪靜之為例,其早期的《惠的風》確實有散文化的傾向,也不講求韻律,但隨著人生閱歷的加深,尤其是新詩整體上的自我修正潮流,及至1927年出版《寂寞的國》,汪靜之的詩風出現了大變——走向了格律體的形式探索,故此朱湘也在與他的通信中贊揚他“能在詩的形式美上做有力嘗試了”,事實上,湖畔詩人的詩風的演變恰好證實了舊體詩對新詩形成的“影響的焦慮”。
如果說率真爛漫的湖畔詩風與充滿叛逆精神的《女神》同時構建了五四詩壇的時代精神,那么1923年冰心與宗白華的哲理小詩則一掃狂飆突進之后社會的整體壓抑感,為詩壇帶來了清新的心靈安撫。這些小詩往往三五行成一首,短小雋永、令人思索回味。小詩的出現是新詩在形式上的另一次突破,豐富了新詩在表現詩人內心細膩情感方面的內涵,為現代性的抒寫提供了別致的舞臺。羅振亞先生曾專文指出小詩域外傳統的主體乃是日本俳句,小詩“冥想的理趣”與“感傷的情調”“淡泊、平易、纖細的審美趣味”等古典風格受到了日本俳句的深刻浸染,日本俳句在對中國小詩形成“詩意純粹性的構筑”“激發出‘冥想’的理趣”“精神情調上充滿感傷的氣息”等方面產生了潛在影響。眾所周知,日本俳句受中國古典詩歌影響很大,例如人們耳熟能詳的日本俳句大家松尾芭蕉就對唐詩借鏡甚多,其詩“今夜三井寺,月亮來敲門”讓人很自然就想到了唐代詩人賈島的“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其“日月乃百代之過客,今歲又是羈旅也”同樣讓人想到李白之“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也。”可見,日本俳句與中國古典詩歌之間存在緊密聯系,也正因此,日本俳句與中國古典詩歌精神氣質的相近性給中國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逐漸興盛的小詩打上了濃郁的古典詩詞烙印。再如,宗白華的詩集《流云》語言工巧,卻自有出水芙蓉之美,其短詩在意境的營造上更是廣為后人所稱道,比如這首《紅花》:
我立在光的泉上。
眼看那滟滟的波,
流到人間。
我隨手擲下紅花一朵,
人間添了幾分春色。
整首詩雖僅僅五行,但詩歌意境之開闊令人驚嘆,大有包羅宇宙萬物的情思在里面。立在光之泉上,讓人浮想聯翩,畫面感也極為生動。而那流到人間的滟滟的波,更是特別,仿佛可以看見站在天上俯瞰大地而思接千載的圖景。可以說,這首詩人生哲理與詩歌意境合二為一、卻不造作實在難得。可以毫不夸張的說,宗白華的小詩真正做到了以小見大,其詩不僅在形式上再次豐富了新詩的發展路向,尤其是在現代情感的表達上,其熔鑄古典與現代的新質為新詩的發展做出了貢獻。再如這首《夜》:“一時間/覺得我的微軀/是一顆小星/瑩然萬星里/隨著星流/一會兒/又覺得我的心/是一張明鏡/宇宙的萬星/在里面燦著”這首小詩,無論是詩人內心世界的感受,還是對外界的描寫都顯得氣度非凡、哲思萬千,作者以如此小的篇幅卻營造出了如此美妙而闊達的意境實在不易。正如宗白華自己所言:“這微妙的心和那遙遠的自然,和那茫茫的廣大的人類,打通了一條地下的神秘暗道,在絕對的靜寂里獲得自然人生最親密的接觸”。正是宗白華在詩藝上的探索讓此種靜怡的心境與詩情完全接通了古典與現代的哲思。其實,宗白華早在《新詩略談》中就曾談及新詩的音樂美、繪畫美的問題,他說:“我們要想在詩的形式有高等技藝,就不可不學習點音樂與圖畫”,這個提法實質已經觸及到了新月派后來提出的詩歌三美的問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宗白華曾經描述《流云》小詩當時寫作的情形:“往往在半夜的黑影里爬起來,扶著床欄尋找火柴,在燭光搖晃中寫下那些現在人不感興趣而我自己卻借以慰藉寂寞的詩句”,可以想見,宗白華在幽暗的花火下寫出的宇宙空幽詩情與其早年舊體詩的熏陶有著某種緊密的聯系,因為,在他看來,詩是“用一種美的文字——音律的繪畫的文字——表寫人的情緒中的意境”,很顯然,宗白華是以生命詩學來燭照古典詩歌的意境并且將之轉化為現代詩意的訴求,這一努力毫無疑問有力地拓展了現代詩歌的寫作路徑。所以說,宗白華的這一努力也從側面反映了其詩中語言的凝練與優美、意境的典雅與深遠,事實上,早已在不知不覺中有了中國古典詩歌的強大投影。而眾所周知,這一投影并非個案,投身小詩寫作的詩人非常之多,俞平伯、康白情、汪靜之、沈尹默、馮雪峰、應修人、潘漠華等新詩人都曾投身其間。可以說,小詩的閑適、淡然、典雅等諸種情趣其實正是對舊詩美學體驗所形成的閱讀焦慮而做出的圓融性回應。
結語
無論自由體新詩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文壇的認可,但新詩人內在的焦慮顯然無法掩飾,劉半農在1920年寫給胡適的一封信中提到:“舊體詩的衰落,是你知道的。但是,新體詩前途的曖昧,也要請你注意”,劉半農的此番話,一方面,證實了新文學群落對舊體詩衰落的遐想以及早期的新詩確實取得了一定的文壇地位,但另一方面,不能回避的是,劉半農此信的重點卻是為新詩的前途擔憂——舊體詩對新詩如影隨形的壓力。總而言之,不論是詩體大解放還是《女神》式的抒情回歸抑或小詩的流行,都說明早期新詩的種種變革其實始終都難以擺脫舊詩美學樣式的強大影響。應該說,當胡適等新文學先驅們借助進化論的威力樹立起“以新為美”的價值評判標準后,新舊文學在新時代文壇的地位也就逐漸形成了巨大的分野。凡是新的就是好的,在這樣的時代浪潮沖刷之下,新舊詩的文壇位置發生逆轉也就成為了必然。然而,不可否認的是,舊詩作為強大的傳統,時刻都潛隱地影響著現代中國新詩的發展,而正是新舊詩這種內在的相互映照與影響,又為現代中國詩歌的內涵注入了新的前行動力。